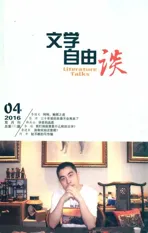文化的影响力
2016-03-16柳士同
□柳士同
文化的影响力
□柳士同
今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正好也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值此“巧合”,一些学者对这两位大戏剧家作一番比较研究,似也顺理成章,没什么不好。然而,是否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茧翁(汤显祖晚年的别号)胜过莎翁呢?翻译家屠岸先生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汤显祖的影响会传遍全世界,甚至要超过莎士比亚。”他这样说的根据是:“大英帝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世界,所以莎士比亚,还有英国文化借助大英帝国国力传遍全世界。但中国国力在很长时期里显然不如英国,现在中国崛起了,汤显祖扩大,甚至赶超莎士比亚的世界影响也就可以预期了。”(《文学报》2016年4月28日)
暂且不谈这两位戏剧家的创作成就,仅就从文化的影响力而言,是否“国力”强大,其文化影响力就必然大呢?文化是依凭它自身的力量,还是借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力量去征服受众?莫非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获得全世界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乃是拜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所赐?此类说法实在有失偏颇。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不同文明的交集和不同文化的交流,始终就不曾间断过,并不存在谁的国力强盛谁的文化影响力就大的逻辑。欧洲的希腊并没有过“帝国”历史的荣耀,但古希腊文化却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丹麦更是个弹丸小国,可安徒生的名字却在全世界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亚洲的印度也未曾“帝国”过,可印度文化的影响力之大,有目共睹;唐朝的国力够强大的了吧?却派玄奘去“西天”取经,怎么就不派大儒到天竺去建“孔子学院”呢?泰戈尔是全世界公认的大诗人,可他分明生活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呀,他怎么就走出了国门,并于191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了呢?
实际上,自16世纪起,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西人就开始将中国文化译介到欧洲去了。别说,欧洲诸国还真一度兴起过“中国热”,遗憾的是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就降温了。为什么呢?翻译难以充分展示汉语之美,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异,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西人看来,“欧洲为自由,亚洲为奴役”(孟德斯鸠语),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中国传统的“奴性”文化呢?这恐怕也正是鲁迅先生嘲讽“送去主义”的原因吧?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莎翁和茧翁。莎翁活了52岁,留下了37部剧本(近年又有新发现的莎剧手稿和演出的记载,一是1594—1595年的《爱德华三世》,二是1612年的《第二少女悲剧》,演出时剧名为《卡登尼欧》),其中包括喜剧、悲剧、正剧、历史剧、传奇剧等多种形式;而茧翁比莎翁年长14岁,只留下了四部戏剧作品。
当然,数量并不足以说明问题,那我们不妨就从“价值取向”说起,看看二者在这方面的差异。
众所周知,欧洲的文艺复兴将人性从神权的桎梏(或者说教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它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倘若一味追求个性解放,那就很容易令私欲膨胀,使社会陷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活着难道仅仅是为了享乐吗?我们不能在找回身体欲望的同时,失去精神的家园。就在这历史的关头,莎士比亚出现了,以他伟大的剧作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他的那些悲剧、喜剧、历史剧,无不引发人们对欧洲历史,对人性、人道的深刻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的命题,经哈姆雷特之口提出后,不仅在当时的欧洲,恐怕只要人类存在,就将永远“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恰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一位巨人,同时,又是启蒙运动的第一位播种者,他那些盛演不衰的戏剧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先声。相比而言,汤显祖戏剧的思想内容是达不到这一高度的。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就不曾把文学创作当过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的心中唯有“学而优则仕”的信念,只是在仕途坎坷时,才会把精力放在写作上,言志咏怀;而一旦被重新启用,便又志得意满地与同僚们步韵酬和去了。因此,即使汤显祖受到当时一些“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异端思想影响”,也不可能真正具有人文主义精神,他遵循和维护的仍然是“家天下”的秩序。他的作品尽管也表现了对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渴求,也揭露和鞭笞了官场的龌龊与黑暗,但始终未能摆脱“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礼教,甚至乞灵于科考及第和皇上圣明,就连《牡丹亭》里杜丽娘、柳梦梅二人最后成婚还是让皇上做的证婚人,“敕赐团圆”的呢!有位长者曾做过这样的比较:“如果说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是流星,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就是启明星。”此喻颇有意味。莎士比亚确实是以他的剧作为新时代迎来了黎明,这恐怕是无人企及的。
至于艺术成就,汤剧就越发不能与莎剧同日而语了。汤的《临川四梦》均“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几成套路:《牡丹亭》沿袭的不依然是才子佳人的情节模式么?而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人物形象的塑造,汤剧则更加无法与莎剧匹敌。中国传统戏曲的生、旦、净、丑本身就难避脸谱化之嫌,汤剧中的杜丽娘、柳梦梅、翟小玉、卢生、淳于棼等,形象也确实比较单薄,性格也不甚鲜明,与个性突出、血肉丰满的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以及夏洛克、鲍西娅等人物相比,实在放不到一个层面上去。还有,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位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他所属民族的语言大师。莎剧的台词不啻于诗,还吸纳了大量的民谣、俚语和古谚语。就像很难尽善尽美地把唐诗宋词翻译成外语,同样,汉译也很难原汁原味地展现莎翁的语言之美。有人评价莎剧对英语语言的贡献“足以和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比肩”,此言甚是。仅马克思著作中引用或提及莎士比亚的地方,就多达三四百处。汤剧则未免相形见绌了,尽管唱词有不少凄美动人之处,比如“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等句,但其对汉语言的贡献远不及唐诗宋词。再说,中国戏曲吸引人的主要是唱腔,观众实际上是听众,他们大都只顾闭着眼睛陶醉在咿咿呀呀的唱腔里,才不管什么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呢!他们对名角儿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剧本和剧作家的关注。白先勇改编的昆曲《杜丽娘》之所以赢得不少观众,主要不还是因为其唱腔动听么?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文化是否具有影响力,只能看文本自身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只能看这一文化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文化实力与经济实力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说经济上成为全球的龙头老大了,世界各国就都会推崇你的文化。即使从军事上征服了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在文化上令其臣服——当年,蒙人满人都一度征服过汉人,可他们的文化又对汉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有钱不等于有文化,钱再多也没法将二流作品包装成一流作品,稍有品位的读者和观众是不会买账的。近年来,我们对文化的投入够大的了,又是各种文学奖,又是各种奖励机制,可奖出几部好作品了?不饱受诟病就不错了。
没有新的思想,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是很难有文化创新的,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实力了。要想产生“世界影响”,首先得融入世界文明;倘若文化本身没有足够的实力,单凭“国力”去输出,恐怕没有人会心诚悦服地去接纳的。
不知屠岸先生当年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究竟是出于莎翁诗作的“含义深刻,韵律优美”使其折服呢,还是因为当时英国国力的强大令他服膺呢?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