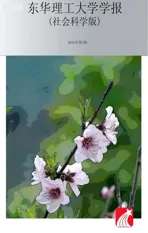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汤显祖“主情说”之承继与开拓
2016-03-07陈新瑜
陈新瑜
(东吴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222)
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汤显祖“主情说”之承继与开拓
陈新瑜
(东吴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222)
以汤显祖为首之晚明临川派主张以情作剧,而清人张坚继承其说,延续临川派主情之观念,强调“以想造情,以情造境”,藉由剧作传达情观,以梦入戏,以戏传情,其特色与临川派莫不契合,更有学者将张坚与洪升并列为“临川派之余响”。以汤显祖“主情说”为出发点,论述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主情”思想理论与创作方法之承继与开拓,冀能由此明晰张坚戏曲理论及其创作之关系。
主情说;张坚;玉燕堂四种曲;汤显祖;临川派
陈新瑜.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汤显祖“主情说”之承继与开拓[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45-254.
Chen Xin-yu.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ang Jian’s “Four Genre of Opera in Yuyan Hall” from Tang Xianzu’s theory of emotion[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45-254.
《荀子》卷十四《乐论篇》言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1]于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最早揭诸文艺与情感之关系者,乃荀子《乐论》,其所言之“乐”,不仅止于喜乐,更泛指广义之七情,然儒家诸子在肯定情的同时,更强调导情与节情之功,如上引《乐论》之文,其言由于情感宣泄之需求而有乐的产生,然“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是故,乐应有其导情功能,“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由上可知,传统儒家观念认为,“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因此,在肯定人之情感的同时,亦反对情感的放纵,故要以礼义规准约束情感之滋壮。
荀子所倡言之导情论,虽以“情”为出发点,然不可讳言,礼义之说无疑系对文艺发展之阻碍,故而历代创作者为摆脱礼教之羁,往往以“任情”对抗儒家之“节情”,于此之中,最受注目者,莫过于明清戏曲理论中之“主情说”,其产生于明代中叶以自然为本,表现真实情感之思想浪潮中,由泰州学派李贽倡其开端,汤显祖集之大成,“主情说”反对传统僵化理学,反对模拟之风、文学教条,讲求独创与性灵,倡议表现真实人性,发抒真切情感,成为明、清二代戏曲创作与批评之主流。
清代戏曲家张坚,字齐元,号漱石,别号洞庭山人,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张士生卒年之说有三,其一,生卒年不详[2];其二,生卒年为清康熙二十年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681—1763)[3];其三,根据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记载张坚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宿钱塘酒家之事,可知其享年应于九十一岁以上。若依据《玉狮坠·自叙》可知其“少攻时艺,乡举屡荐不售”,后“焚稿出游,转徙齐鲁燕豫间”且“交游日益广,而穷困如故也”。张氏博学多才,通音律,善词曲,曾作《江南一秀才歌》,藉以抒发胸中抑郁,时人遂称“江南一秀才”(唐英《梦中缘·序》)。其着有传奇《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合称《玉燕堂四种曲》[4]。
以汤显祖为首之晚明临川派主张以情作剧,而清人张坚继承其说,延续临川派主情之观念,强调“以想造情,以情造境”,藉由剧作传达情观,以梦入戏,以戏传情,其特色与临川派莫不契合,高文彦《晚明剧曲家流派研究》中更将张坚与洪升并列为“临川派之余响”[5]。本文即是以汤显祖“主情说”为出发点,论述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主情”思想理论与创作方法之承继与开拓,冀能由此明晰张坚戏曲理论及其创作之关系。
1 主情说之先声
明代中晚期,社会文化剧烈变动,经济发展兴盛、印刷事业发达、通俗文学兴起、商人地位提高,社会风尚产生急剧变化,此外,官学化之程朱理学已然僵化,文坛上出现一波以自然为本,表现真实情感之思想浪潮,其反对形式化的文学教条,讲求独创与性灵,此风在晚明文坛造成极大影响。欲论汤显祖与主情说之关系,则不可不言此说之发展,概述如下。
1.1 王艮
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身为泰州学派一代宗师,其继承王阳明之思想,并进一步地将心本论转而为身本论,在阳明心学的基础上,主张以身为本,其哲学、美学思想,不仅对泰州学派后学及明清学者产生深远影响,更对明中叶以后之文艺思潮产生前导作用。
1.1.1 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心斋语录》曰:“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6]又言:“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则知性矣。”[6]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乃传统儒家文艺美学之首要命题,王艮则融通圣人与百姓、理想境界与日常生活、心灵本体与世俗情欲的界线,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就治学而言,讲究“心悟”、“独解”,跳脱传统经学注疏范畴,反对章句诵习,讲经说书,多发明自得。就文学而言,“百姓日用即道”正为以村夫俚妇、日常生活为题材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提供有力支持,使平民化之审美倾向蔚为风尚。
1.1.2 身本论
朱熹以理为道之本体,即为“理本论”,王阳明以心及良知为本体,乃“心本论”,而王艮则以身为本,系属“身本论”。王艮言之:
身与道原是一件。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宏道,是至尊者身也。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6]。
由引文观之,其将形而下之“身”地位提高至与形而上之“道”相齐,为“身”重新定位,亦对人欲重新评价,其言:“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6]王艮将“天理”释为天然自有之欲望,将“人欲”观做理性的安排,确认了自然欲望的合理性。而泰州学派后学,诸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人,多致力推崇人欲之真意,如“三言”对人性欲望的正面叙写、“临川四梦”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刻划、晚明小品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描摹等,皆使一般百姓对于安身畅神之欲望获得满足,体现文学作品对于日常生活之关注。
1.1.3 率性自乐
王艮由“天然自有”出发,认为人欲基于自然本性,并非有意为之,故非人欲,而系天理,相反论之,有意所为、束缚人性的人为克制,才是人欲。就文学创作而言,其亦以“天然自有”为础石,讲求“率性”,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一言一语皆自胸襟流出。此外,王艮认为学习之目的即发展自然之乐,其方法须以快乐为主体,《乐学歌》云: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6]。
由此观之,王艮认为“学”之目的在于获得“乐”,乐为心之本体,学为道德修养之过程,其重视文学接受中的适情娱乐功能,将阅读、学习视为满足人类情感需求之事。至此,文以载道、诗言志之文艺传统逐步走向娱情功能。
1.2 李贽
李贽,号卓吾、笃吾,别属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师事泰州学派祖师王艮之子王襞。其倡言“童心”,以郁积于内的真实情感为基础,重视自然,以自然之为美,要求内容抒发情性,形式自由发展。李贽之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1.2.1 绝假纯真
童心,即未受污染之最初本心。李贽倡言童心,即为自然人性,乃由人的自然本体为出发之欲望、情感。就文学而言,其重视文学之真实性,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摆脱束缚,去除伪装,从而表现真实纯净的赤子之心。是故,李贽以此准则,肯定民间文艺、通俗文学为一种极具人情世俗意涵,充满强烈真实性之现实文学。
1.2.2 自然为美
李贽以童心为核,提倡“自然为美”,认为表现童心,关键要素即为“自然”,其以为通过不加修饰技巧之“化工”(天赋工巧),描绘人物情感,童心才得体现为文学形象,此即为“真文”;反之,若以“画工”(人为技巧)叙写,其人伦大道将阻碍童心,此为“假文”,拟古派重理弃情,作品违背自然人性,李贽认为“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优秀之文艺创作应重情求真,发乎自然情性,蕴含客观规律性,其据此论点,高举反拟古旗帜,为明代中晚期文坛开创新页。
1.2.3 无意为文
李贽在自然为美之基础上,主张“无意为文”,其言: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7]。
李贽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作者应蓄积情感,直至势不可遏,才自然地爆发流泻而出,其将创作视为作者对于现实不满的寄托,于评价《拜月》《西厢》时曾言:“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7]于此观之,李贽不仅将发愤视为文学创作前提,更将其当作审美评价之主要思想,而此亦为童心说之根本础石。
李贽美学思想,乃深受王阳明、王艮哲学体系之影响,带有浓厚唯心主义色彩,其以自然为本,讲究不假雕饰之童心,于李贽后活跃于文坛之公安派,则继续在李贽童心之基础上,高举反拟古旗帜,确立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原则。无论系李贽“童心说”,抑或公安派“性灵说”,皆对晚明追求个性、注重抒情及强烈世俗化之文艺思潮,起了决定性影响。
1.3 汤显祖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海若士,一称若土,晚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汤氏尝师事泰州学派三传弟子罗汝芳,并受李贽影响甚深,其作品具有明显之美学精神,反映时代思潮,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有云:
汤显祖提出来的“情”的哲理,是同程朱以来的整个理学传统相背逆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却挥动“情”的宝剑,砍伐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及其官方哲学。因此,汤显祖礼赞的“情”字,不仅在晚明的现实中起着战斗号角的作用,而且在我国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8]。
汤氏将情感能量之积聚视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把文学创作视为丰沛情感宣泄之途径,其以为情和神是构成诗歌之要素,“神”关乎诗之艺术性,而“情”则为诗之基础。不独诗歌为然,情亦为戏曲创作之根本,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阐之: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奇哉清源师,演古先神圣八能千唱之节,而为此道。初止爨弄参鹘,后稍为末泥三姑旦等杂剧传奇。长者折至半百,短者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纾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可以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此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9]!
汤氏以为,“情”乃与生俱来之存在,人类生而有情,若受外在事物触发,则生思、欢、怒、愁之绪,而此情感活动,言之不足则发为啸歌,咏歌之不足则形诸舞蹈,人类之情感宣泄管道,由歌舞衍为戏剧,发展成杂剧、传奇,可知情感为戏曲产生之基础,艺术以情为动力,才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故戏剧能使观者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通过戏曲与观众之情感交流,氍毹演出亦有其积极的教化功能,能合君臣之节、浃父子之恩、增长幼之睦、动夫妇之欢,亦可发宾友之仪、释怨毒之结、已愁愦之疾、浑庸鄙之好。故汤显祖言,戏曲之道能开通人情之大窦(孔穴),使人快乐地接受教化。易而言之,名教须与人情相合,才得以为人所接受、实现。
汤显祖“主情说”之观念不仅受当代哲学、美学思想启发甚多,且其影响汤氏之戏曲创作、戏曲理论实巨,以下即透过罗师丽容所言“主情说”内涵(见罗丽容《戏曲面面观》,2008年),将之做一简述。
(1) 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认为情乃人所具有之天性,非人为的理性所能消灭,凡欲以理来灭情者,皆非自然。此外,为情而死,不算多情,要为情复生,才算情之至。
(2)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理不能并存,而明代之时,一切以法为尊,以理为尚,故法理存而情灭亡,无情则不能容人,则有才情之士无法发挥其才于天下。
(3) 情者志也,情之所至,志之所向也。认为万物之志表现于情之中,故志就是情。以戏曲论,作者之情寄托在剧中,剧中人所流露之情,即作者之情,观者只需理解剧中人之情,即得剧作家情之三昧。
(4)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意趣神色之间。汤显祖以为,所谓情有善恶,即是指真情与矫情,“真情”出于自然,即其所谓之“真色”;“矫情”则系指扼杀、束缚人性之理教。汤显祖认为情出自人性之本然,故以自然、真情为贵,其将之发于戏曲创作,要求自然为尚,反对为求声律之美、求形貌之似,而改变自然,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而不改其自然本色。
综上所述,可知从王艮、李贽、汤显祖一脉相承之主情思想有二特色:其一为“通俗文学、平民审美”,其二为“重情求真、发乎情性”。前者肯定人的存在价值与生活意义,确认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并肯定民间文艺、通俗文学乃为极具人情世俗意涵,充满强烈真实性的现实文学,因此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中,体现对于日常生活之关注与对爱情生活之向往。此外,其更重视文学接受中适情娱乐的功能,故而文学与艺术逐渐走向娱人与娱情,使平民化之审美倾向蔚为风潮。其二,主情说讲求重情求真、发乎情性,此乃重视“率性”,认为好的文艺作品应当发于真情真性,由乎自然,将“情”视为创作、审美之根本。于作品内容,要求以郁积于内的真实情感为基础。于作品形式,则讲究不假雕饰、不落俗套的自然不羁之美。作者以真性发于作品,观者以真情与作品相应,二者融会,即得自然无伪之审美观点。
除上所言之王艮、李贽、汤显祖等人外,余者如公安派三袁、徐渭、冯梦龙、徐复祚等人,无不以泰州学派之哲学思想为础石,反对形式模拟、矫揉做作,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于明清时代掀起一股反传统文艺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嵇文甫将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泰州学派后学,归入“狂禅”一派,认为正是此狂禅潮流影响明清时期众多名士才子,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特殊时代[10]。其所崇尚之人心、人情、人性,皆与泰州学派所张扬之人欲息息相关,而张坚亦承袭此说,并加以发展,易而言之,在明中叶后之文艺思潮中,蔚为风尚之平民化审美倾向,不仅系王艮身本论之必然延伸,更赖泰州学派后学、汤显祖及张坚等人之推动与倡导。
2 主情思想之承继
清代剧作家张坚既为“临川派之余响”,自然承继汤显祖“主情”之说,其以想造情,以情造境,藉由剧作传达情观,以戏传情。本部份即由汤氏“主情说”为出发基点,透过“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及“情之所至,志之所向”等方面探究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汤显祖思想理论之继承。
2.1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
大抵而言,中国古典戏曲本有“真假相半”、“多虚少实”之艺术特征,吕天成有言:“有意驾虚,不必与实事合。”[11]王骥德亦曰:“古戏不论事实,亦不问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然尚存梗概。”[12]始自明万历中叶,于文艺浪漫思潮之鼓荡下,“脱空杜撰”蔚为时风,凌蒙初即言:“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无论,即真实一事,翻弄作乌有子虚。总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世法既自不通,鬼谋亦所不料……。”[13]又清乾隆年间戏伶黄旛绰云道:“戏者,以虚中生戈。”[14]可知,“脱空杜撰”乃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之重要环节,尤以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中叶为文人戏曲创作之“自由创造”时期,而此文学现象,不仅说明“多虚少实”符合传奇文学特征与规律,更说明了高度审美的创作自由乃系文学艺术发展之催化剂[15]。
明代中叶,汤显祖“主情说”若表现于戏剧观,即“因情成梦,因梦成戏”[16],汤氏以为“情”在戏剧中占有主要位置,其包含了复杂的生活内容与积极的人生意义,而“情”通过“梦”加以表现,“梦”则透过“戏”反映出来。易而言之,戏剧乃系通过梦幻的表现形式,以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是非善恶与思想情感。汤显祖于《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言:“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纾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9]在《赵帅生梦作序》中云:“梦生于情,情生于适。”《与丁长儒》中则自述:“弟传奇多梦语。”甚而,其于《续虞初志·许汉阳传》评语中写道:“传奇所载,往往俱丽人事。丽人又俱还魂梦幻事。然一局一下手,故自不厌。”综上观之,汤显祖认为若拘泥于生活的真实面,则无法穷尽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唯有通过梦境之描绘,藉以说尽人世之事,从而反映出比现实社会中更广阔、深刻之人世百态与浓烈情蕴。其以“梦幻”形式表达情感与理想,实为一种寄托,于当时时代条件下,真情无法真道,故以“幻”道之,不幻不足以言尽其情。因此,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之说,于角色人物个性及现实社会环境之处理,为幻与真之联系;而在作品内容及情节结构方面,则为梦与戏之统一。
于汤显祖论点之基础上,张坚一脉相承,使戏剧中的男、女主角因情成梦,共结梦中情缘,其于《梦中缘·自叙》中言:
太上无情,故至人无梦,其下不及情,故愚人亦无梦。然则梦之所结,情之所钟也,欲赋其事,则恐张皇幽渺,蔑渎神灵,乃另托人世悲欣离合之故,游戏于碧箫红牙队间,以想造情,以情造境。自春徂秋,计填词四十六出,一梦始亦一梦终。惟情之所在,一往而深耳。虽然情真也、梦幻也,情真则无梦非真,梦幻则无情不幻,夫固乌知情与梦之孰为真,而孰为幻耶[4]?
天地皆缘,浮生若梦,或因缘而成梦,梦本非真;或以梦而生缘,缘终是假。情之正而根于性者也,贵人善用其情而不为情所用,此正是《梦中缘》之旨。故张坚以为,男女相互爱悦乃系人之至性的自然流露,而欲求夫妻之欢,则合乎人之真情。王鲁川在剧作跋中说:
作者意中止写一生二美,并带写一解事,小鬟之数人者又皆斡空凿虚,而姓氏里居悉成乌有,况其余乎。至于胪列贤奸以寓劝惩,不过镜花水月,涉笔成文。作者既自谓非真读者,亦当视为幻。若定索影寻声,折白道字,势必讹以传讹,何啻梦中说梦[4]。
文学的想象及虚构之价值,在于其与历史、经传殊途同归,表达同一救世苦衷,能胪列贤奸,以寓劝惩,不过镜花水月,涉笔成文,透过想象、梦幻,体现文人心所欲表达之生命价值,故而张坚透过以想造情,以情造境,形象性地宣告“天理即在人欲中”,其《梦中缘》一剧,剧谱书生钟心与翰林学士文岸之女媚兰,梦中相遇,互生爱慕之情。钟心之友贾俊才假冒钟心之名向文家求婚,不过最终仍被识破。钟心于赴京途中遇表妹丽娟,二人订白首之盟。经一番曲折,最后钟心高中,得媚兰、丽娟双艳完婚。全剧之中,“情是开口第一字”,且“上下千古,一口咬定情字”[4],此不仅为《梦中缘》全剧之要旨,更系张坚对于婚恋之理想追求。
综上所论,梦由人的真情引发,梦中之情有别于形骸之论,而能深入浅出地表达人们灵魂深处精微隐密的情感与欲求。真情的梦幻化与梦幻之真情化,构成文学家艺术思维与审美创造的深层冲突。因而,梦幻化的艺术思维,正是文学家之审美情感、想象与审美创造得以发挥的最佳方式[15]。
2.2 情之所至,志之所向
汤显祖认为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而万物之志表现于情之中,故志就是情。以戏曲论,作者之情寄托在剧中,剧中人所流露之情,即作者之情,观者只需理解剧中人之情,即得剧作家情之三昧。孙永和《论汤显祖在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云:
主情说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提出了戏曲要表戏人生理想和自然的性情,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作者的情感要藉助舞台形象来表现,把情感这一因素通达到对人物形象的探求。……他认为作者的情感是寓于形象之中的,通过形象具体地显现出来的。在艺术欣赏中,观众又必须通过舞台形象这一中介因素来体验作者的情感,从而最后理解作品[17]。
此将汤氏之主情说导向创作论之说法,罗师丽容认为,汤氏提出观众与作家间之联系,即在剧中人所表现之“情”字,颇近于近世所谓“创作论”之观念,惟独特别强调“情”而已。
至于张坚,其一生不第,穷困出游十余年,归而闲居无事,抒愤写怀。张氏曾作《江南一秀才》歌自嘲:
原是江南一秀才,十年壮志几层灰?
任来天下无难事,只道黄金复有台。
霜堆两鬓渐堪哀,原是江南一秀才。
目到闱中迷五色,笔花何自向人开。
致君尧舜匡时策,谁道不从书里得。
原是江南一秀才,奈何常作诸侯客。
柳发新条梅有苔,邵园陶径许重开。
归来课子灯窗下,原是江南一秀才[4]。
坎坷经历与不平遭遇,使张坚对科举制度、文人现状产生强烈的愤懑,故其于《玉燕堂四种曲》中,结合自身经历与体念,形塑知识分子之文人形象,聊以抒泄怀才不遇之愤慨,寄托己身之理想。因而,张坚剧作中的男性主角皆带有作家自身影子,如《梦中缘》钟心,学饱千箱,直至念年虚度,仍为一领蓝衫;如《玉狮坠》黄损,尽管胸藏八斗,咳唾成珠,仍因时乖不遇,而无法登科及第;又如《梅花簪》徐苞,甫登场即仰天长叹:
只道男儿事可期,几年未曾下书帏。羞弹阮籍穷途泪,耻笑荆人抱璞悲[4]。
《玉燕堂四种曲》中之男性主角,或为奇祸缠身,或为家道中落,空有经纶满腹,却备受厄运捉弄,此与张坚经历相合,其早年闻名金陵,然举于乡,却屡荐不售,既乃穷困出游,隐而为人捉刀,以试行其志学,然终无所大用。张坚将饱学之士屡试不第之原委归罪于盲试官,如钟心遭人冒名顶替,冒名者竟被达官视为大名士;黄损于原籍连试数场,均为宗师所黜落,后于京师会试,竟高中巍科;而徐苞因中途耽搁,误了试期,任凭百般解释,仍遭主试官驱而逐之。由此可见,张坚游戏笔墨,对科场情弊之揭露与讽刺,力透纸背。而张坚出游十余年,归后所做之《怀沙记》中,矛头所向,更直指统治者,其揭露君王昏庸,无远虑,亲小人,远贤臣,使不学无术者之流得以把持朝政,而此无疑触及时弊之症结所在。
除愤懑与不平之外,在《玉燕堂四种曲》中,可见张坚对于科举与军功之向往。军功、科举乃系张坚创作之特殊模式,如《梦中缘》第三十八出,化名齐谐之钟心高中状元后,向皇帝请命征讨崆峒叛逆,并立下军功;又如《玉狮坠》主角黄损,其与冯梦龙《情史·黄损》之异,即在于黄损在得中状元之前,曾被安义强留府中作为幕僚,献先抚后剿之策,助其抚平苗乱,得过军功,因而封侯。或可推测,科举功名与军功乃系张坚作为幕僚文人的身份与地位追求,正因困守僚幕,故其在创作才子佳人传奇时,心理上冀望一方面能因高中科举而功成名就,另一面又盼望能顺应现实, 在幕僚中凭借谋略策画取得军功,由此富贵显赫。
《怀沙记》一剧中,张坚竭力形塑屈原忠诚爱国之形象,其讲究史实,据《史记》等历史著作为本,但塑造人物形象时却注入了作者不为重用,困守僚幕、报国无门的强烈情感。故其借屈原之口唱道:
〔黄钟引子·点绛唇〕满腹牢骚。半生离恨忧难数◎登朝无路◎举足遭时妒◎冠世文章。欲待鸣何处◎年衰暮◎借他词赋自把闲愁吐[4]◎
〔前腔〕(案:为〔绣带引〕)今古恨教人怎懂◎天公似哑如聋◎颜算殀。跖寿全终◎货权贵。孔哲偏穷◎总拗不过运途消长将人送[4]◎
此类曲文在《怀沙记》中俯拾皆是,此乃藉屈原之口,唱出张坚空有忠诚与抱负却无以施展的哀怨之词。张坚将其怀才不遇之叹、知音难遇之慨,酸甜苦涩、世情冷暖,一一谱入管弦,发乎人情,跃于纸上,正如汤显祖主情说所示,作者之情寄托在剧中,剧中人所流露之情,即作者之情。
3 戏曲创作方法之开拓
张坚虽为临川派之余响,然并未为汤显祖“主情说”所囿,其以汤氏所倡之“以情反理,寓教于情”、“贵乎真情,重于自然”为出发,杂揉各家说法,企图融会“主情说”与“教化说”,结合“临川派”与“吴江派”,并由此开拓新的创作手法,集各家之大成,发扬汤氏“主情”之观。故而本部分将透过“以情合理,寓情于理”及“秾丽清真,娴于音律”等方面探究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汤显祖思想理论之继承。
3.1 以情合理,寓理于情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开始探论人情、人性、人欲、人道等议题,如墨家以为人的本性即为男女与生利;法家认为人皆无法超脱利欲之情;道家以为人性即自然,反对社会对人类自然本性的破坏;儒家则认为感官欲望亦为人之本性,然更应强调人的社会性。先秦儒家倡议以礼义抑制情感之需求;汉代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将封建纲常与人之天性画上等号;隋唐时代,佛、道蓬勃发展,于是人性说便掺和了宗教的禁欲主义,认为七情乃败坏人性之根源;宋代,理学盛行,提倡“无欲主静”,强调“穷理尽性”,以天理、人欲相对立为基本命题,至此,对情之宣传与要求已被视为异端。
明代中晚期,经济发展兴盛,社会风尚产生急剧变化,僵化之理学教条、封建规范已无法抵挡对真实情感之渴求,文坛、艺坛无不以自然为本,讲求独创与性灵,反对形式化之文学教条,其中,以汤显祖之“主情说”对理之扞格最为猛烈,其高举情感旗帜,以情抗理,汤氏言之: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18]!
汤氏与道学家相异,道学家认为理高于一切,汤显祖则以为情、理无法并存,情高乎一切,明代之时,因以法为尊,以理为尚,故法理存而情灭亡,因此,戏曲情节、文艺创作不能以理衡量,若系情之所必有,则无须挂虑理之所必无。由此可知,汤显祖认为情、理冲突时,不应以理为宗,而该服从于情,因此,其所谓人情与名教之统一,乃在于使名教符合人情,而非以人情屈从名教。明代末期,郑元勋承掌汤氏主情旗帜,其在《梦花酣题词》中言:
情不至者,不入于道;道不至者,不解于情。当其独解于情,觉世人贪嗔欢羡,俱无意味,惟此耿耿有物,常舒卷于先后天地之间。呜呼!汤比部之传《牡丹亭》,范驾部之传《梦花酣》,皆以不合时宜而见。情耶?道耶?所谓寓言十九者非耶?
由引文可知,汤氏之主情系积极的“以情反理,寓教于情”,其虽以“情”为创作主要宗旨,然并非不顾人伦教化之说,汤氏论情真,讲教化,敢于冲破礼义之羁,拒绝比附封建道德观念,其或写情至者,或写不及情者,皆具奖善罚恶之美刺作用。其言情之理论与实践,在戏曲界、文学界皆产生巨大影响,周育德认为:
言情的理论反映在文艺创作上,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大胆批判,一是对男女爱情的大胆歌颂。一些倡导言情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社会现实,对虚伪的礼教、腐朽的政治展开了批判。用生动的形象,从社会政治和道德各方面,大胆地表抒自己的感情和认识[19]。
汤显祖以情为重,其认为透过戏曲,能使“孝子以此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9]其以为情乃道德之根本,而情感之激发与交流能使观者移情易性,敦化风俗,如前所述,汤氏所谓人情与名教之统一,系使名教符合人情,故其主情之说与道学观念所支配的教化说(系指戏曲具有教育感化观众,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为政治服务之功能.教化论者主张教化第一,艺术第二,其继承先秦孔子之儒家文艺思想,强调文学艺术有其社会功能,应为政治教化服务)[20]相互拮抗,相互争辉。
后世继承汤显祖主情说者,分为二派,其一,继承汤氏主情说之积极面向,高举“以情反理,寓教于情”旗帜,如明末郑元勋,其以情至者为最高之善,不及情者为最大之恶。另一派,则以孟称舜为首,强调“以情合理,寓理于情”,反映出明末主情论者力求与教化说沟通之思想与作为,孟称舜言之:
天下义夫节妇,所谓至死而不悔者,岂以是为理所当然而为之耶!笃于其性,发于其情[21]。
其将《娇红记》中王娇娘、申生之爱恋归因于“节义”,把人情与节义相联系,正如将人欲与天理相缠上系带,使情通于理,强调情之“正”,通过情的潜移默化,发挥戏曲之教化作用。
张坚于《玉燕堂四种曲》中,高举汤显祖“以情反理”大旗,热情讴歌不顾世俗礼教羁绊之自由恋爱,为李贽“天理即在人欲中”之具体展现,其于《梦中缘·笑引》藉众罗汉之口言:“既具人形,罔非情类,除是万劫成空,一灵俱渺,那时方可斩断情根也。”布袋和尚应之:“咳!人无情而不生,鬼有情而不死。”[4]明确表彰人世有情,无情不生,有情不死,此与汤显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8]之情至论,无疑系一脉相承。然另一方面,张坚并非一味承继汤氏之说,其以汤显祖“以情反理”之说为础石,承继孟称舜“情通于理”之思想,并藉以发扬开创,揉合教化与主情,将人情与纲常、节义相互系联,如其于《梅花簪·节概》中即明白指出:
纲常宇宙谁维系,千秋节义情而已。石上两心盟,无情却有情。新词非市价,稗语关风化。富贵草头霜,梅花雪里香[4]。
张坚所言,如《衡曲麈谈·填词训》之谓:
古之乱天下者,必起于情种先坏,而惨刻不衷之旤兴。使人而有情,则士爱其缘,女守其介,而天下治矣[22]。
易而言之,张坚着重于情之教化作用,强调情之正,重视情之诚。如其于《梅花簪·自序》中言明:
天地以情生万物,情主于感,故可以风。采兰赠芍人谓之情,而卒不可以言情,以感情非正也。夫玉不磨,安知其不磷;素不涅,安见其不淄。世途之坎壈,人心之险巇,造化弄人之巧毒,惟不失其正,乃履艰蒙难百折而其情不移[4]。
其将“性”视为“情”之根柢,认为言情即为言性,论性等同论理,故而情与理并无矛盾之处。张坚于继承汤显祖主情说的同时,其并非全然接受,而是从中开拓一条崭新的道路,将“情”一分为二,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种“情”:一系淫邪纵欲之伪情,一为冰清玉洁之痴情。前者系指为追求肉欲之欢,或浪掷千金,或权势威逼,或暴力相向之辈,如《玉狮坠》中之太师、《梅花簪》的山东巡抚及其公子等,张坚集中笔力刻画道学之僵化与在上位者淫邪纵欲之伪情,其于《梦中缘》即力斥“薄情儿枉自把风雨闹,转关儿漾李寻桃……霎时间翻云覆雨,那些个如漆似胶。”至于冰清玉洁之痴情,张坚于《玉狮坠》中言之:“那争个颠鸾倒凤,都则是心同意串缠绵。论人世夫妻虽不鲜,但恩爱淫邪须辨!是情真定冰清玉洁,不枉了风流千古名传。”何为情真?即《玉燕堂四种曲》中,冰清玉洁之男女痴情,今人单长江评曰:
以任“情”自然发展的相互爱悦为触点,以相互奉献、牺牲为热点,以义夫节妇为理想,以死则同穴为归宿[23]。
其所言冰清玉洁的男女之情,正如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所谓“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休。”[9]男女主角相互爱悦,若受外在情境触发,则生思、欢、怒、愁之绪,欲现其情,若言之不足则发为啸歌,若咏之不足则形诸舞蹈。张坚以此情为基石,将“名教”与“风流”扣上系带,使义夫节妇之概念与朝廷宣扬的理教规范析而为二,使之向“情”靠拢。其于《梅花簪·自序》中言:
梅取其香而不淫,艳而不妖,处冰霜凛冽之地,而不与众卉逞芳妍,此贞女所以自况耳。徐如山本有情而似无情,巫素媛于无情中而自有情,郭宗解为贞情所感触而忽动其侠情,是皆能不失其正而可以风[4]。
《梅花簪》一剧中,除引文所述徐如山、巫素媛之情事外,更藉狱卒之口颂赞杜冰梅身遭暴行,仍誓以死全孝义、保节操,其言:“好一个无瑕璧,把纲常整。不愧儒门女,真个罹颠沛,志不更。”以杜冰梅一介弱女子,险入虎口,其以自尽殉情为手段,表征对统治者誓死抗争之贞烈风范。又如《玉狮坠》中之黄损,为赴裴玉娥半年之约,无惧千里之遥,不顾将军挽留,不惜功名利禄,甘愿逾垣独奔,为佳人把功名看薄,张坚赞其如尾生抱柱,重然诺,轻功名,尚节义,不若悖情忘信之徒。综上观之,张坚突出“情”对世间万物之认识,加强“情”对裁决过程中的支配作用,虽说其以宣扬义夫节妇之伦理纲常为创作之道,然剧中的男女主角面临抉择之时,无不以“情”为依归,强调情之正,重视情之诚。
3.2 秾丽清真,娴于音律
如前所述,汤显祖以为,“真情”出于自然,即其所谓之“真色”;“矫情”则系指扼杀、束缚人性之理教。汤氏认为情出自人性之本然,故以自然、真情为贵,其于《答凌初成》中言道:
曲者,句字转声而已。葛天短而胡元长,时势使然。总之,偶方奇圆,节数随异。……歌诗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节,做为缓音,以舒上下长句,使然而自然也[24]。
又如《焚香记总评》:
此传大略近于《荆钗》,……作者精神命脉,全在桂英冥诉几折,摹写得九死一生光景,宛转激烈。其填词皆尚真色,所以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何物情种,具此传神手[25]。
其将之发于戏曲创作,要求自然为尚,反对为求声律之美、求形貌之似,而改变自然,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而不改其自然本色,故王骥德《曲律》即言:“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齚舌。”[12]
至于张坚,其不若汤氏过分强调才情,又吸收了吴江派依腔合律之特长,结合汤词沈律之双美,于清代曲坛,开创一方词、律并重之戏曲天地。历来曲坛,对张坚《玉燕堂四种曲》之评论甚少,若有之,亦不过寥寥数语,其中针对漱石文采之说,或有称其“清新隽逸,跌宕风流,恍听缑岭瑶笙、湘灵仙瑟,绝非凡响。”[4]或有称其“吐辞若霏玉喷珠,持一管以扫尽愁魔,琢句则惊天泣鬼。”[4]由引文观之,张坚文才极高,秾丽、隽逸,无一不可,其尝言:“词贵清真,雅俗共赏,余数种填词,虽秾艳典丽,而显豁明畅。”[4]以《梦中缘·题帕》观之:
﹝前腔﹞(案:为﹝山坡羊﹞)对纱窗明羞日影,画青山愁拖青鬓。(贴)看他意沉沉燕懒莺慵,兀自娇怯柳倦花如病。(旦梳头又止介)(贴)梳又停,翠鬓权代整。小姐,怎么忘了点臙脂?(旦)罢了。(贴)恐怕粉脂掩却天然俊,不如本色梨花柳黛青。琮璜花簪八宝横,轻盈湘裙八幅轻[4]。
杨楫眉批:“写出一段娇慵,正见春情无限。”[4]再如《玉狮坠》第十三出〈胶筝〉,女主角裴玉娥出场之唱词:
〔海棠春〕西风暗落惊鸿阵◎秋水外。芦花月。隐弦上。谱新愁。悄地添离恨◎ 〔忆王孙〕月夜怀人天际头◎碧云中断一江秋◎相思两地几时休◎动离愁◎且拨银筝对水流[4]◎
寥寥数句,借景抒情,将秋日江上凄凉景色与裴玉娥思念之情相结合,凄切宛转,动人心肠。整体说来,其词神形兼备,秾艳清丽,表面上展现相思难言之苦,内蕴里透露少女怀春之羞,故而单长江言其:“就才情而言,其秾艳典丽不让临川,就显豁明畅则汤词略逊一筹。”[23]
就曲律而言,汤显祖宁可拗折天下人嗓子而不改其自然本色,故而屈曲聱牙;张坚则吸收吴江派之长,本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王鲁川称其:
阴阳悉叶,去上必谐,即偶有变通,而蝉联伸缩,自然成声,按板固无劣调,口诵亦极铿锵,为善审音者心领而神会焉[4]。
综上观之,张坚虽为临川派之余响,然其并未为汤显祖“主情说”所囿,反而结合沈璟吴江派之曲律特长,辞藻、协律并蓄,秾艳、清丽共存,依腔行事,曲白相济,形神兼备,不可不谓之为曲中上品。
4 结语
张坚为中国古典戏曲史上著名的临川派后期代表作家,其承继汤显祖余蕴,并在其基础上开拓、创新,时人甚而将之与汤氏相提并论,如杨楫有言:
夫《临川四梦》,评者谓《牡丹》情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今漱石四种,则合女烈臣忠,配以侠义,参之仙佛,而总于一情[4]。
此说极有见地的指出《玉燕堂四种曲》与《临川四梦》于外在形式、内在思想之一致性。张坚于汤显祖之基础上,继承其“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与“情之所至,志之所向”观点,并藉戏剧作品加以阐发、呈现,以想造情,以情造境,透过想象、梦幻,体现文人所欲表达之生命价值,并将作者之情一一谱入管弦,发乎人情,跃于纸上,寄托在剧中。此外,张坚于创作方法亦以汤显祖主情说为基本论点,并结合文学潮流与社会风尚,加以开拓、创新,如“以情合理,寓教于情”即系将汤氏“以情反理”之主情说与“文以载道”之教化说相互结合,突出“情”对世间万物之认识,加强“情”对裁决过程中的支配作用,强调情之正,重视情之诚;又如“秾丽清真,娴于音律”则系保留汤显祖“以自然为尚”之基本理念,并结合沈璟吴江派之曲律特长,使辞藻、协律并蓄,秾艳、清丽共存,依腔行事,曲白相济,形神兼备。
本文于探讨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主情”思想理论与创作方法之承继与开拓,尚有不足之处,期待能藉此文对汤显祖至张坚“主情说”发展之脉络有一起头作用,并能以此为基础,更深层地探讨张坚于中国戏曲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1] 王先谦.荀子集解[M] .台北:华正书局,1988.
[2]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 .济南:齐鲁书社,1989:1681.
[3] 齐森华,陈多,叶长海.中国曲学大辞典[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65.
[4] 张坚.玉燕堂四种曲[M] .清乾隆16年(1751)本.
[5] 高文彦.晚明剧曲家流派研究[D] .台北: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5:231.
[6] 王艮.心斋语录[M]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台北:世界书局,1961.
[7] 李贽.焚书[M] //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 .台北:大鸿出版社,1998:567.
[9]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M] //徐朔方,校笺.钱南扬,点校.汤显祖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7-1130.
[10]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1] 吕天成.曲品[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1982:209.
[12] 王骥德.曲律[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1982:147.
[13] 凌蒙初.谭曲杂札[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1982:258.
[14] 黄旛绰.梨园原[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1982:10.
[15] 郭英德.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明清文人传奇作家文学观念散论[J] .中国文学研究,1990(3):77-79.
[16] 汤显祖.答孙俟居[M] //徐朔方,校笺.钱南扬,点校.汤显祖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46.
[17] 孙永和.论汤显祖在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M] //戏曲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171-172.
[18] 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M] //徐朔方,校笺.钱南扬,点校.汤显祖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 周育德.汤显祖论稿[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91.
[20] 吴双.明代戏曲的社会功能论[J] .] 中国文化研究,1994:40-41.
[21] 孟称舜.娇红记·题词[M] //中国戏剧研究资料:第1辑.台北:天一出版社,1983.
[22] 张琦.顾曲麈谈[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1982.
[23] 单长江.张坚[M] //胡世厚,邓绍基.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614,616.
[24] 汤显祖.答凌初成[M] //徐朔方,校笺.钱南扬,点校.汤显祖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1345.
[25] 汤显祖.焚香记总评[M] //徐朔方,校笺.钱南扬,点校.汤显祖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1468.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ang Jian’s “Four Genre of Opera in Yuyan Hall” from Tang Xianzu’s Theory of Emotion
CHEN Xin-yu
(ChineseLiteratureDepartment,SoochowUniversity,Taibei222,China)
Linchuan faction, led by Tang Xianzu, advocates the use of emotions in opera compositions; and Zhang Jian, from Qing Dynasty, inherits the same idea by carrying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 in Linchuan faction,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of “creating emotions through imaginations; creating sceneries through those emotions”, and conveying the emotions through opera.This feature of incorporating dreams into storylines and conveying emotions through opera is the same as Tang Xianzu’s Linchuan faction.Some scholars have even categorized Zhang Jian and Hong Sheng as the successors of Linchuan Faction.This paper begins with Tang Xianzu’s Theory of Emotion, then discusses abou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ang Jian’s “Four Genres of Opera in Yuyan Hall” from Theory of Emotion’s ideology as well as its production method.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Jian ’s own operatic theory and production.
Theory of Emotion;Zhang Jian; Four Genres of Opera in Yuyan Hall; Tang Xianzu; Linchuan faction
2016-08-10
陈新瑜(1982—),女,讲师,主要从事古典戏曲研究。
I206.2
A
1674-3512(2016)03-02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