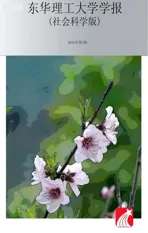汤显祖《南柯记》人文精神分析
2016-03-07张福海
张福海
(上海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上海 200040)
汤显祖《南柯记》人文精神分析
张福海
(上海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上海 200040)
汤显祖的《南柯记》是一部心理剧;淳于棼在被群体抛弃后,因情致梦,在蚂蚁国里经历人生苦乐悲欢、荣辱兴衰,梦醒后惊异于生命无常,逝者如斯,与蝼蚁何异的人生顿悟;剧中以淳于棼纯粹的个体悲剧意识,塑造了一个自我超越、自我完成的独特形象,把观众带入新异的审美体验之中;汤显祖以“情本体”立论,剧中寄予了他个人深切的人生感受,创造性地描写了淳于棼对世俗凡情的执着和挣脱与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精神升华的情感痛苦过程。
《南柯记》;汤显祖;自我实现
张福海.汤显祖《南柯记》人文精神分析[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31-237.
Zhang Fu-hai.Analysis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Tang Xianzu’s Nanke Dream[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31-237.
汤显祖的《南柯记》是一部表现人物意识流动的心理剧。剧作以作为个体的淳于棼失去群体的无奈、孑然无助的焦虑和苦闷、梦境中的人生悲欣沉浮、出梦的醒悟和超越,构成哲理性情节,引向深邃的哲思。汤显祖以“情本体”立论,剧中寄予了他个人深切的人生感受,创造性地描写了淳于棼对世俗凡情的执着和挣脱与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精神升华的情感痛苦过程,由此把个体生命意识的深度和精神自由的高度推向前所未有的心灵境地,同时也把观众带入新异的审美体验之中。晚明以来,这部剧作就受到戏剧学者的重视和关注,评价亦高,但给予的解读并不一致。《南柯记》是一部什么样的剧?汤显祖寄予的是怎样的思想和感情?当我们放下既定的观念,穿越时空接近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中国戏剧史上汤显祖和他的剧作如同世界戏剧史上那些光辉耀眼的戏剧家们一样,具有独立于任何时代的恒久的价值。
1 《南柯记》在历史上的评价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剧作中,首先被推重的是《牡丹亭》。《牡丹亭》创作于明代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而另外三部分别是创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紫钗记》,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南柯记》和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邯郸记》。明清以来,《牡丹亭》《紫钗记》和《邯郸记》都曾经上演过,尤其以《牡丹亭》影响最大,《南柯记》则因为创意独特,自标一格,从万历年间问世以后,亦上演不辍。如明末戏剧家祁彪佳在他的日记里,就记载他曾在杭州观看《南柯记》的剧目。*陆萼庭在《昆剧演出史稿》一书中,从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中,就其于崇祯五年壬申(1632)到十二年己卯(1639)7年间在北京、杭州、绍兴三地记载的所看剧目中的一部分进行的统计,排出了一份86种传奇的戏单,其中就有《南柯记》一剧在内。参见该书第90和9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个时期,演出的剧目还都是全本戏。但是到了清代的乾隆(1736—1796)、嘉庆(1796—1821)年间,全本戏消歇,舞台上演出的昆剧主要是折子戏,昆剧进入折子戏时代。在此背景下,《南柯记》也像其他昆剧的剧目一样,只有单折流传,如《瑶台》《花报》,以及《点将》《就徵》等。但是,作为折子戏的形式,演出也不是多么频繁,只有《瑶台》和《花报》两折戏(这两折中主要是《瑶台》一折),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如果从乾隆年间算起,到现在也至少有二百六、七十年的时间全本的《南柯记》没有再在舞台上出现了。折子戏毕竟不是全剧,也难以从单折戏来窥见整个戏的全貌,感受全戏的审美意蕴。但是,就《南柯记》剧作本身来说,在历史上却一直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赏识,因而流行的版本仅逊于《牡丹亭》,是最多的一种。只是到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牡丹亭》受到格外的重视,驰著中外,它的光辉把《南柯记》和另外两部戏剧几乎都遮蔽了。
因此,历史上关于《南柯记》的评价,主要是从文本出发并停留于文本,而不是剧场上的。最早对《南柯记》做出评价的是王骥德(1540—1623)。他在《曲律·杂论》中,首先批评了《紫钗记》和《牡丹亭》是“第修藻艳,语多琐屑”,“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1]的问题,然后对《南柯记》连同《邯郸记》评论说:“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类,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溪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使其约束和鸾,稍闲声律,汰其賸字累语,规之全瑜,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1]这个评论,是从形式方面立论的,也就是立足于剧作的语言即唱词的音韵方面的,不是对剧作主题思想的评价。但仅就这方面说,王骥德的评价无疑是对汤显祖戏剧语言的至评。涉及到《南柯记》思想性的,是王思任(1575—1646)。他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序》中阐述“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指”时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2]。对剧中具体人物形象的评论,则有吕天成(1580—1618),他在《曲品》中评价说:“《南柯梦》,酒色武夫,乃从梦境证佛,此先生妙旨也。眼阔手高,字句超秀。”[3]这个评价很简略,但不出王思任的“佛旨”说。超出佛旨说的,是近人王季烈(1873—1952)在《曲谈》中的点评:“《南柯》之《情尽》,《邯郸》之《生寤》,洵足发人深省。一洗寻常词曲家绮语矣”。从总体上评价《南柯记》的是近人吴梅。吴梅(1884—1939)在 《中国戏曲概论》一书中,评价《南柯记》时说:“此记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亦为见道之言。其自序云:‘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我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倐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是其勘破世幻,方得有此妙谛。‘四梦’中惟此最为高贵。盖临川有慨于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细之蚁,为一切有情物说法。又有慨于溺情之人,而托喻乎沉醉落魄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此临川填词之旨也。”[4]吴梅此番议论,超迈前贤,认为勘破世幻,得其妙谛的《南柯记》,在“四梦”中“惟此最为高贵”。他甚至不同意王思任的“《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的观点,而独辟蹊径,指出“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是曲中之主,而非作者意中之主。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曲意,则主观之主人,即属于判官等,而杜女、霍郡主辈,仅为客观之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即在此处。”[4]他还在《瞿安读曲记》中进一步议论说:“《南柯记》悟彻人天,勘破虮蚁,虽本唐人小说,而言外示幻,局中点迷,直与内典相吻合。此为见道之作,亦即玉茗度世之文。”[4]吴梅在这里所指明的《南柯记》,是“悟彻人天”的“度世”之作,因此分析说:“独《南柯》之梦,则梦入于幻,从蝼蚁社会杀青。虽同一儿女悲欢,官途升降,而必言之有物,语不离宗,庶与寻常科诨有间。使钝根人为之,虽用尽心力,终不能得一字;而临川乃因难见巧,处处不离蝼蚁着想,奇情壮采,反欲突出三梦之上。天才洵不可及也。”[4]吴梅几处对《南柯记》的评价,认定其在其他三剧之上是不改变的。
上述历史上的学者关于《南柯记》的评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固然是属于古典戏剧的立场,但是,他们作为个体的感受、认识和评价,虽属古典戏剧范畴,却又有所不同。就作品的思想指向或内在意蕴来说,王思任和吕天成都是从佛学的立场来进入和评价的,影响很大,其中王思任关于“《南柯》,佛也”的看法,直到今天还被人不断引用和认同,甚至成为对《南柯记》的定论。吴梅的评价却远不如王思任的影响那么大,但他对《南柯记》的认识和评价,不囿于佛学的诠释,剧中的淳于棼能够“勘破世幻”,“悟彻人天”,从而使《南柯记》成为“玉茗度世之文”,其所达到的效果则是与“内典(即佛学)相吻合”的,但不是佛学的注释,因此,在“三梦之上”,是“最为高贵的”。这是有关《南柯记》评价中最有见地的意见,吴梅也是自古及今唯一这样来推重《南柯记》的人。
2 汤显祖的“情本体”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即以颖悟超群,才华卓异而文名远播,14岁院试中考取诸生(就是秀才),21岁在乡试中考中举人,22岁开始参加国家最高级别的进士考试,就是会试。从此,在求取功名和仕途的道路上奔波,历经坎坷。进士及第,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唯一的进身之阶,汤显祖一共花了12年的时间才获得。12年里三次落第,一次弃考,到第五次才中第成功,这年他34岁。之所以这样艰难,不是因为他能力不逮,他是明代的举业八大家之一,以他的才能,可以轻取上乘。头两次未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后来的两次(包括他的弃考)却都是由于首辅张居正徇私舞弊,致使汤显祖科场受挫。直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掉,汤显祖才于第二年(1583)年考中。 朝廷授予他南京太常寺博士(七品)、后改任詹事府主簿(从七品)和礼部主事(六品)。他在礼部主事任上,忧心国事,提出刷新吏治,革新政治的主张,并于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他的奏疏直指神宗万历皇帝不作为、揭露首辅申时行及朝臣贪腐成风的现实,因而触怒了皇帝而被降职到广东徐闻县充任不入品阶的典史(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一职。一年后复官,委任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五年,政绩斐然,但却久令遂昌不迁,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直至去世。
汤显祖弃官固然是因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未能遂愿升迁的缘故,但也正是因为仕途多舛而深感自己真挚、热切的用世之情、忠君为国的经邦抱负得不到应有的施展,才由曾经寄予的热切期待而失望,并由失望而绝望,最后做出了弃官而归的选择。他对仕途的绝望是来自他对官场腐败和堕落的切身闻见及感受。诚如他朋友们的劝言:把耿介的性情改一改,随顺一些。但汤显祖没有接受,他以抱诚守真的精神进入官场,以性情正直、洁身自好、不与他人苟合的狷介态度对待他生存的世界,追求美的理想,不愿意违逆自己的人生信念而委曲求全去获得进身之阶。这种清高孤傲、势出尘表的可贵精神,来源于他所认定和确立的启蒙思想和佛学的自由精神。
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走着相同的路径,人类心灵的发展也相差无几。明代晚期,也就是嘉靖(1522—1566)之后的社会,从经济和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型社会开始向近代型社会转向,生长出具有近代性质的启蒙思想,即以“人的重新发现”为价值取向的近代人文主义思潮,西方社会则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种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致使以往区域的或国别的历史开始进入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汤显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了他的“情本体”的审美观。他对此阐述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5]这就是汤显祖理解的人与情的关系: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源于情,为了情。因此,情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而且充满人间,同时也弥漫于大千世界,通乎宇宙天地,所以,它的力量可以“摇动草木,洞裂金石”。
汤显祖的“情”是与宋明以来宣扬的儒家正统观念的“理”相对立的。宋明理学的“理”,作为哲学上的“本体”论,是与历史上那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别无二致。宋明理学的“理”,企图用来解释世间的一切,因而这种一元本体论对现实世界“以理相格” 的结果是人的鲜活生命都被抽空了。汤显祖认识到这个“理”的残酷,因而回答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6]汤显祖的“情”,显然是和当时专治社会推行的严酷的社会禁锢的“法”相对立的。他否定有法之天下,认为“尊吏法”的有法的天下是“灭才情”的天下,就是李白生于斯世,也只能是“滔荡零落”,低眉俯首,哪里会才情奔涌呢!
汤显祖的“情本体”是晚明启蒙思潮的产物,此时,也正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亦即摆脱中世纪神权藩篱,高举人本主义、理性至上旗帜的时代。伴随着人的地位的凸显,科学的昌明,及至近代以来,在精神领域,诞生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各类人文科学。而中国的传统道德理性的片面发展,使原本就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文精神——个体主义,自两宋以来,隐没不显。至明代心学的创立以及汤氏从事戏剧创作的时代所依赖的背景——心学异端思潮的涌起,才透显出个性解放的灵光。在汤显祖之前的心学大师陆(九渊)王(守仁)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阳明)(1472—1529)开其端绪,提出“只信自家良知”,“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心本体”;继承王学的泰州学派,以“非名教所能羁络”而推动启蒙思想的发展,继而有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李贽(1527—1602),这个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思想家讲的是“君子以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既说以人治人,则条教禁约,皆不必用。”“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7]反对“条教禁约”,主张“自治”,正视“千万人之心”,“千万人之欲”,乃是王学“良知是尔自家准则”的充分发挥,并突出表现为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
中国早期的这种阐扬自然人性论的启蒙思想,如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独抒性灵说”,以及冯梦龙、周铨、闵景贤的情感本体论等等,无不具有自然人性论的鲜明特征。因此“人的重新发现”、“个性解放”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晚明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中心内容!这个中心内容,在汤显祖这里则体现为“情本体”,并贯穿在他的全部戏剧作品中,《南柯记》是其中最为独特的表达。
3 淳于棼的自我实现与审美超越
“人生如梦”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生、对个体生命之于世间存在关系的理解和认知,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思想观念,并且带有生命母题一样的色彩。汤显祖的《南柯记》就是借用这个具有母题意义的思想观念,以人物的内心活动为视像,展现人物的意识流动和心理真实,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对此在在世生命的深切感受和哲理思考。
可是,以往关于《南柯记》的解读,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佛觉说”,即淳于棼因佛法而开悟的认识。显然这是对汤显祖创作的这部剧作的误读。汤显祖固然在戏中写了僧人契玄法师这条线,但是,契玄法师不过是戏剧中构成情节的人物,这个人物所带来的情节,不是单纯地用于写契玄的,而是为了淳于棼的思想活动设置的,是为淳于棼最后实现精神超越、自我完成做铺垫和牵引的。不限于此,历史上这几位名家画龙点睛式的评点,也大都是传统的、感性化的,如对于淳于棼因酒被逐之“被逐”的理解,淳于棼是山东东平人,为什么不在东平而客居扬州的追问,以及淳于棼因何梦入大槐安国的主观动机的认识,均缺少必要的心理探究和深层的精神分析。因此,还没能够真正揭示汤显祖在整部戏情节构成上运思的独特,及其在设计上完成的思辨性的哲理用意。
我们看到,戏中的淳于棼,因醉酒而贻误战机,遭到革职。汤显祖没有告诉我们淳于棼醉酒的原因,那么,我们以淳于棼后来的行止即对现实的执着来观察猜想,应该是因对某种事体的不满情绪所致。汤显祖无需对此有什么交代,我们可以推知。剧中因此遭弃而落魄扬州的淳于棼,虽然是被弃者,但他并不甘心、也不情愿离开那个自己指望建功立业、赢得声名的营垒——为那里的梦想和追求,曾经寄予了他的一片深情。我们理解汤显祖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淳于棼是一个不肯退步的积极入世者,且自视甚高,正如他自评的那样,“人才本领,不让于人”——他是有本事的人;恰当风华正茂之年,卓尔不群,前途无量。他的人生理想和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建功立业,功成名就,妻妾成群,锦衣玉食,权倾一方,众人景慕,荣华富贵。如今自己所努力奋斗的、期望的这一切都已经遥不可及了。而面对现实,更为严峻的是,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三十前后”的而立之年,“名不成,婚不就,家徒四壁”,每天只“守着这一株槐树”,生活是“泠泠清清”,心情是“淹淹闷闷”,于是,“想人生如此”样子,还“不如死休!”[8]被弃后的孤独、苦闷和绝望笼罩着他,他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淳于棼这种入世而不得的内心感受,被透彻地揭示了出来,从中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淳于棼被抛弃后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必然如此的根本处境和心情,这种心情无以排遣,便只能借酒浇愁,但也是内心实有不甘的表达。
淳于棼被群体所弃,是剧中的重大关目。如果说被弃前的淳于棼作为群体中的一员,那时他是在一个有着严格规范的体制里生存;这个规范的体制,剧中设计的是军队,也就是说,汤显祖把淳于棼所生存的体制其规范化的程度强调到极端——军队的整体化、规范化、等级化、理性化,是以消灭掉感性的个体生命自由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淳于棼醉酒的非理性行为,是感性个体对理性、规范的体制的破坏。于是他被这个体制驱逐除去抛弃掉,然而,在他被驱逐被抛弃的同时,他也便获得了作为一个个体人的自由,以及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完成的所有可能性。
可是,被体制抛弃了的淳于棼不仅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个体人被抛弃,他的精神寄托之地和心灵的归宿之所也就跟着丧失了。如今他是孤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为了强化淳于棼孤身面对这个世界,剧中设计的淳于棼不是回到自己的故乡东平,而是客居异乡扬州的陌生环境,这就增添了作为孤身一人的淳于棼的孤独感:既没有精神上的归宿感和安全感,也没有家乡亲人热土的情感安抚和心灵的慰藉。对此,他描述说自己的境况是“四海无家”,“群豪雨散”,“门客萧条”,“偌大的烟花不放愁”[9],无疑这是伴随自由而来的生活景象和当下心情。剧中淳于棼多次诉说自己的“愁”情,正是他离开那个主宰他的群体后,难以忍受的一个人孤寂和苦闷,心理失衡的表白。
《南柯记》中的淳于棼,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极具现代性精神品格的形象。正是淳于棼从群体里被赶出来而陷于孤独苦闷甚至绝望的境地,淳于棼作为一个有别于群体共在的独立、个体的人的存在便被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在社会群体中,社会群体的力量强大与否,取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即单独的个体的能力,因为社会群体是由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构成的。而个体自身的发展充分与否,则取决于个体获得自由的程度,而人的最高需求就是人的自由。因此,个体自由的程度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和历史前进的基础,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之境。换句话说,个体的发展优先于一切的发展,也是一切发展的前提。于是,作为社会群体中共性存在的淳于棼和作为独立于社会群体的个体存在的淳于棼,其精神处境的突转和骤变,就成为弥漫于《南柯记》中“情”的痛苦,和戏剧情节上深入思辨的编织。
随着情节的进展,淳于棼孤独、苦闷、绝望的内心情绪,在不甘于被旧营垒抛弃的心态下,他的意识深处、内心渴望回归而不得的抑郁之情,便在无以排遣的醉酒的苦闷中,主观情思转换为梦幻,意识流变为蚂蚁国选婿的情节,在大槐安国,阅历人生、实现梦想——淳于棼现实的孤独、苦闷和绝望也便于此找到了深在的心理动机和依据。
进入大槐安国,这是一个寓意性的梦,意识中织就的理想。在大槐安国的蚂蚁世界里,淳于棼的用世之情沉浸其中,夙愿得以实现。他娶妻生子,飞黄腾达:如以驸马身份和夫人瑶芳公主的裙带关系得任南柯郡太守。在二十年的太守任上,他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南柯郡物阜民丰,太平一方,政绩显著;他还大败檀罗国的来犯,保家靖边卫国,立下功勋,尊荣显贵,因而升迁入京。不幸回京途中妻子突然病故,他的感情受到重创。在京城,由于权势日盛,持宠放纵,终于在宫廷内斗中,失去荣恩,被罢官遣送回乡。可是淳于棼不愿离开这个给他荣华富贵的家国,他对蚁王的忠诚,对蚁后的孝敬,对子女的顾恋,还有对大槐安国未竟事业的挂牵……真是一份依依难舍、割不断的苦情、哀情和离情。
和《牡丹亭》的“情”不同的是,《牡丹亭》写的是杜丽娘的“至情”,而《南柯记》写的是淳于棼要从世俗凡情中抽出身,退出来、拔出去,其最高目的是实现自我超越,即从深情的痛苦中抵达自由之境,完成自我、实现自我,也就是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这是多么的艰难!但是,淳于棼终于幡然醒悟的是,瑶芳公主留给他的金钗犀盒是槐枝槐荚,这对淳于棼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由槐枝槐荚这个纪念物,一下子联想到整个梦境:那是自己现实的不如意而转换为一旦如意的人生追求的景象,虽然是压缩在一梦中,淳于棼由梦境悟到人生——现实革职,梦里升迁,友亡妻死,现实梦中,真幻一如,淳于棼由此得到启悟:“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10],此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才是它的本性。鲁迅对此评价是“假实证幻”[11]。汤显祖对淳于棼出离精神困境而抵达自由之境的处理,至此完成的是一个情节上的哲理构成,《南柯记》因此成为不可多得的哲理剧典范。
戏中有一个值得注意但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淳于棼有一个很值得回味的追问,即第八出“情著”中淳于棼到孝感寺向契玄法师询问“如何是根本烦恼”的问题。“如何是根本烦恼”,这本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实际上淳于棼是在问如何彻底摆脱烦恼的问题。这个问题向契玄法师询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寺院和尚研究的就是“人何以烦恼”这样关于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剧作在这里为淳于棼也为整个戏的情节埋下了一个伏笔,等到淳于棼完成了自我人生超越之时,契玄法师因此评价淳于棼是“淳于生立地成佛也!”[10]契玄法师的这个评价,是契玄法师作为一个僧人的身份、而且是出身禅宗,因此是以禅宗家所居于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及评价淳于棼的精神超越的。当然,剧中也把佛学的开悟理论运用到淳于棼这个人物形象的精神超越上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混淆在一起的感觉,让人容易分辨不出来,故历史上有佛觉说。可是,仔细分别一下,就明白了:戏中的淳于棼并不是一个佛教徒,他是在百无聊赖的状况下,听说寺院有新来的法师讲经,想用以打发时光、排遣烦恼才去寺院的。于是,戏便在寺院凝结为一个重要的情境:淳于棼前来看讲经的热闹,大槐安国来人选婿,契玄法师设道场度化众生。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寺院是士庶社会各阶层都常光顾的地方,无论红男绿女,不管是否是居士和信徒,到寺院或是观光、消遣,或是祈祷、还愿,是一种相沿已久的习俗和风尚。所以大槐安国派人选婿也是要到寺院来选的(这是为淳于棼的主观情思埋下的伏笔)。关于淳于棼向契玄法师询问摆脱烦恼的问题,也不是多么着意去询问的,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契玄法师的慈悲开示,是佛家人的本份,对世人而言,属于师教,听与不听信与不信,听者由之。因此,在此前和此后的情节进展中,淳于棼的情节线是按照他的情感走下去的,他没有建立领会契玄法师的暗喻的意识。而讲经说法和主持超度的契玄法师,作为剧中的一个角色,一个人物形象,他对淳于棼的评价是符合他的身份的。但这并不等于淳于棼本人以自己的精神历程所获得的体验而实现的精神飞跃和自我完成时抵达的内心澄明之境。所以,王季烈评价说是“情尽”,他虽然没有展开议论,但没有说“成佛”或“开悟”;吴梅以主情说立论,对这部戏谈论的最充分,而且认为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都在另三戏之上。这都是审美的评价,不是宗教的评价。“佛觉说”的评价则是宗教性质的评价。这里很容易发生混淆的是,淳于棼看破红尘、实现精神的升华,他所达到的终极之境是与“佛觉说”相通的,契玄法师就是这样来看待的。但淳于棼自我完成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佛门教徒为开悟而去进行自我求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就决定了《南柯记》的性质是戏剧的而非宗教教义的形象解答,它是审美的创造。
当年萨特曾对法国剧作家克洛岱尔的剧作评价不高,原因就是他利用戏剧宣传基督教教义,这和用戏剧进行道德的或政治的宣传一样,把戏剧当作载道的工具。但萨特十分推崇他的《缎子鞋》,就是因为这部戏摆脱了作为宗教信徒的克洛岱尔的宗教情结而完成审美的创造,因此获得萨特的好评。汤显祖也是一名佛教徒,但是,在《南柯记》里,他很能够节制自己的宗教感情,也就是没有因为自己是佛教徒而去借戏剧演绎佛法,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冯梦龙做得出色。汤显祖以“情尽”一出来表达淳于棼超越了社会功利与世俗感情的羁束,同时也是在彻悟了天地宇宙后,对人的本体性的亦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烦恼的超越,从而走向自由的生命意识。淳于棼的烦恼因此而从个人得失升沉的遭际上升到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哲理性感受。我想,从戏剧过问人生的终极意义上讲,这可能就是吴梅大为赞赏此戏的高贵之处并认为其在其它三戏之上的原因吧!换一个角度讲,《南柯记》可以是剧中人物契玄法师说的“开悟”的佛觉,在淳于棼的体验看来则是精神超越。其实是两者共同构成了作者汤显祖创作《南柯记》所营造的情本论的审美意蕴。
历史上对《南柯记》的评价不是很多,而我们的传统剧评中高台教化一直是居于主流地位的,独立的审美评价却停留在声色(如声韵、演唱等方面)的高低上。由于过多地流连于声色的审美品鉴,造成中国戏剧历史上出现一种很糟糕的现象,就是把戏剧当作宴享和娱乐,或者是消遣和游戏来看待。只要看看历史上的“厅堂”(即堂会)演出或茶园时代的场景,以及那些有关这方面的介绍性文字,你就会感到这完全不同于欧洲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待戏剧那种庄严、肃穆的态度。所以,有识之士就把进戏园子等同于提笼架鸟、声色犬马一样,严禁自家的子弟上戏园子看戏,以免被那里低俗的气息所熏染。戏园子因此也培养了那种专注于声色、精神品位庸下但却居于观众主体的“票友”,他们的嗜好往往影响和主导一个剧目的走向。今日流行的所谓“好看”、“好玩”之类的名词来评价戏剧的现象就是它的变种。戏剧是生命的体验过程,剧场是过问灵魂的圣殿,岂是来玩玩的地方呢!《南柯记》不好玩,它是关于现实人生问题的探索,是关于人生在世的究问,是关于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解答——这是汤显祖的精神定位。这个定位是美学上的,也是他的情本体哲学思想的艺术表达,就如同萨特的戏剧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表达一样。在中国戏剧史上还没有哪位像汤显祖这样有着明确的哲学理念来进行自己的戏剧创作的,中国古老的人文精神到了汤显祖手中重现芳华。
[1] 王骥德.曲律注释[M] .陈多,叶长海,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陈多,叶长海.中国历代剧论选注[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97.
[3] 吕天成.曲品[M]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230.
[4] 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158-160.
[5] 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M] //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497.
[6] 汤显祖.牡丹亭·作者题词[M] .北京:人文学出版社,1998.
[7] 箫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98.
[8] 汤显祖.南柯记·第十出·就征[M] //毛晋.六十种曲(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27.
[9] 汤显祖.南柯记·第二出·侠概[M] //毛晋.六十种曲(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1-2.
[10] 汤显祖.南柯记·第四十四出·情尽[M] //毛晋.六十种曲(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137,138.
[11] 鲁迅全集(八)[M] //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5.
Analysis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Tang Xianzu’s Nanke Dream
ZHANG Fu-hai
(Departmentofdramaticliterature,ShanghaiTheatreAcademy,Shanghai200050,China)
Nanke Dream written by Tang Xianzu is a psychological drama.After abandoned by his community, Chun Yufen fell into a dream in which he experienced the happiness and bitterness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all his life in the ant kingdom.He woke up when he suddenly realized that life was uncertain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was just like the flow of water, which was to people as to ants.The play shapes a unique image of self-transcendence and self-realization through the pure consciousness of Chun Yufen about individual tragedy.It brings the audience a new and different aesthetic experience.Tang Xianzu based his argument on “sentiment noumenon”, expressed his deep personal feelings towards life, and creatively depicted Chun Yu Fen’s painful experience from being attached to the secular world to struggling to free himself from the secular world and finally to self-realization and spiritual sublimation.
Nanke Dream; Tang Xianzu; self-realization
2016-08-10
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成果(SH1510GFXK)。
张福海(1957—),男,黑龙江海伦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史论研究。
I206.2
A
1674-3512(2016)03-02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