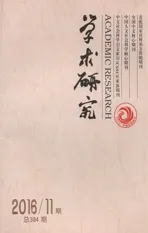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戏剧隐喻
2016-02-27沈湘平
沈湘平
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戏剧隐喻
沈湘平
将历史比喻为戏剧是马克思历史科学中一个全局性、贯穿性的隐喻,不弄懂这个隐喻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一种戏剧本体论。我们认为,马克思将历史隐喻为戏剧的深层原因是基于两者经验的相似性,借助戏剧隐喻揭示存在的历史性。马克思关于历史悲剧进程的思想是历史戏剧隐喻思想中最精髓、最富启发性的部分,具有强大的解释和预言功能,不仅启示我们认识历史规律,而且激励我们始终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真正的历史高度之上。
马克思 隐喻 历史 戏剧
历史无疑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关注对象,他致力于建立的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但是,一方面,马克思所理解的“科学”(wissеnsсhаft)比英语世界的“科学”(sсiеnсе)要广义得多,具有学问的性质,是“现有之物”与“应有之物”、真理洞见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努力使自己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的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在非神性之中歌唱着福祉的整体”[1]的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在马克思的理论写作中,娴熟自如地运用了大量文学修辞手法,其中最常用、最重要、最引人瞩目的修辞手法就是隐喻。在他所宣称的唯一的历史科学中,众多精妙的隐喻使其洞见和论断既切近真理又饱含诗意,可谓同时达到了老子所谓的“信”与“美”或王国维所说的“可信”与“可爱”,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及其文本散发恒久魅力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使用的众多隐喻中,对整个历史科学而言,具有全局性、贯穿性的隐喻是把历史比喻为戏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弄懂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戏剧隐喻,就谈不上对马克思思想的真正理解。
一
在早期诗歌、博士论文中以及《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经常信手拈来地以戏剧人物、情节来比喻现实。其中,博士论文中关于普罗米修斯的隐喻最是深入人心、令人着迷,研究者也甚众;1842年10月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说,省议会是个大舞台,演出的是“大型政治历史剧”。[2]不过,马克思真正直接地以戏剧来隐喻历史则是起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该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把历史这个本体和戏剧这个喻体表述了出来。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世代更替,也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马克思在分析新旧制度兴替时,明确地使用了“悲剧”“喜剧”“主角”“丑角”等戏剧词汇,指出在别的国家经历过的悲剧的旧制度在当时的德国正作为喜剧上演,“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马克思坚信“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历史有这样的进程,是人类为了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在此意义上,新制度的斗争或每一个人类的进步解放追求就是为了争取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3]在谈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说:“解放者的角色在戏剧性的运动中依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级担任”。[4]社会历史被看成是多幕、连续的戏剧,历史人物被比喻为不同角色,历史进程被戏剧化,不仅同一个事物先后出现有悲剧和喜剧之别,而且整个人类历史在悲剧性进程的终点是喜剧性的。应该说,这里已全息地蕴含了马克思整个关于历史的戏剧隐喻思想,以后的相关思想只是对这一思想的展开。
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在与蒲鲁东辩驳到底是“历史创造原理”还是“原理创造历史”时,认为只要去追问一个原理为什么出现在某个时代而不是另一个时代,就必须分析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接着说:“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5]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明确把历史称为“历史剧”,而且提出了人在历史中既是“剧中人(物)”也是“剧作者”这一不朽思想。这一思想是对一般历史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最好驳斥,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人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在《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持续地以戏剧语言来分析历史事件,他把巴黎的六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第一幕,把维也纳的十月起义称为欧洲悲剧的第二幕,而把当时普鲁士所策划的政变看作欧洲悲剧的第三幕。在后来的《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把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进程称为“悲喜剧”。在这场法国革命中,“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他们表演的有些是“荒谬喜剧”,有些是“流血悲剧”,有些是把“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场景。1848年12月的农民起义则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而且,“他们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尤其是在描写反动的巴罗内阁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时,马克思这样写道:“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全都变样了。”[6]这完全是调动戏剧舞台的全部要素在摹写历史事件。
马克思运用戏剧隐喻来分析历史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论述。其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又可以说是以戏剧隐喻来分析历史的最高典范、最佳范本。作为《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续篇,这篇经典文献开篇就明确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7]这一以黑格尔的话为由头的思想事实上是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相关思想浓缩地以警句的方式表达出来。①客观地说,这一思想虽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相关思想的浓缩,但表述方式可能是借鉴恩格斯的。此前的1851年12月3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明确写道:“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把历史当作世界精神来指导,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7-448页)有意思的是,中国的俗语“第一个是英雄,第二个是狗熊”和成语“东施效颦”,都与上述意思有某种神合之处。放在篇首,就如同几何学里开篇的公理,奠定了对当时法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及路易·波拿巴这一历史人物的基本性质的判定。马克思再次把当时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的历史事件称为“大型的政治历史剧”,路易·波拿巴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则 “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8]这就是二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和波拿巴的戏剧性历程与下场。在后来的文章中,马克思又多次提及这样的论断。比如,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9]在《富尔德先生》一文中,马克思说:“一次又一次地使旧的、已经演完了戏的реrsоnае drаmаtis〔剧中人〕作为崭新的主角重新粉墨登场,这套本领是波拿巴喜剧最典型的特技。”[10]
与旧制度、没落阶级的“悲喜剧”“丑剧”“笑剧”“滑稽剧”“历史的恶作剧”不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称为革命剧。例如,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宣告,当时的德国运动“这是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11]
即使是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也始终运用着他拿手的戏剧隐喻。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指出,“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这就是表现为经济舞台的历史舞台上的剧中人。同样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离开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后的历史人物的命运:“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2]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出大戏剧中两大剧中人的形象特写!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还频繁地使用“舞台”一词,把社会历史领域称为“公开的舞台”“公共舞台”“社会舞台”“政治舞台”“历史舞台”“世界舞台”,称历史人物“登上舞台”“跃上舞台”“站到舞台最前面”“在舞台上公开演出”“表演”,最终“退到后台”“退出舞台”。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戏剧的隐喻。
二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热衷以戏剧来隐喻历史?为什么会把戏剧作为其历史科学一个全局性、贯穿性的隐喻?这样的问题长期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之外,西方学者涉及的也不多,但为数不多西方学者的有限探究却贡献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思想。后现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一切有关历史的叙述都是一种历史的诗学,在“元”(mеtа)的层面都包含了情节化、论证与意识形态蕴含的模式设定,而且这种前定的模式设定主要是一种戏剧隐喻。他甚至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为例,引用文章第一句话(即一切伟大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先悲剧后笑剧地出现两次),认为这表明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已经将历史事件塑造成讽刺剧的模式,说明马克思赋予自己著作一种潜在的情节结构。怀特还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化构成了重大历史事件之戏剧的各幕”,马克思同时诉诸机械论和有机论两种实在观念,“把历史过程结构成两种情节模式,即同时是悲剧的也是喜剧的模式;但是,他运用的方式是使前者的情节化成为后者之中的一个阶段,以至于他能够声称自己是‘实在主义者’,同时又维持了他那种乌托邦式的梦想,即超越社会状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自人们经过社会分工而落入社会之中以来,悲剧情形便在历史中盛行。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扬弃这种悲剧情形,对于他声称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激进的政治立场而言,便构成了一种科学的证明。”[13]另一位美国学者维塞尔则通过研究认定,“诗人的冲动,从根本上点燃了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视人类历史为人类解放的戏剧,这是一种“戏剧本体论”,“这种戏剧本体论,就是马克思科学思考的基础,内在于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社会经济学范式。”维塞尔还断定:“在后黑格尔时代,马克思的哲学解释的深度内核,就是哲学必须成为戏剧。”[14]虽然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这些学者的观点,但他们的视角无疑是敏锐和新颖的,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和研究。
我们认为,马克思把历史隐喻为戏剧,最浅层的原因可以说是面向自己写作与面向读者写作的一个完美契合。我们知道,马克思自小就浸润于古希腊文化艺术之中,尤其是对古希腊的戏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特别喜爱,一生都经常阅读。当然,少年时代那位经常给他背诵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精神教父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影响无疑极其重要。大学期间,马克思不仅写下大量诗歌,而且创作了一部名叫《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的幽默小说,甚至撰写了一个悲剧剧本《乌兰内姆》。在回答女儿提问的著名“自白”中,马克思说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这几位其实都是伟大的剧作家;他最喜爱的女英雄是甘泪卿,正是歌德戏剧《浮士德》中的人物。在一定意义上,戏剧观念融化到了马克思的血液中,深刻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念、人生情怀和运思方式,已经构成其观察世界的一种先验的前结构,在恣肆汪洋的才情中喷涌,在理论写作中自然流露。同时,自古希腊以来,戏剧在西方文学艺术和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极高的位置,一些戏剧元素、情节、人物的隐喻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共知识,成为“加魅”的表达方式,成为高效沟通、理解的方便之门。特别是在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德国流行巡回剧团演出,这些剧团演出的戏剧往往以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为当时的人们所热捧。因此,在当时的德国,人文写作乃至历史研究中涉及一些戏剧的东西,并不新奇,差别只在于运用的巧妙与上升的高度——马克思巧妙地把戏剧隐喻上升到了历史的高度。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确实与马克思心心相印,思想交相辉映。
追溯人们自觉运用隐喻的一般原因,“不得不如此”和“最好如此”都很重要。所谓“不得不如此”,是指人们对当前的事物难以捉摸和进行理性描述,于是只能借助隐喻使人模拟得之;所谓“最好如此”,是指借助隐喻比直接描述要简明、生动得多。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人们运用隐喻的基本前提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不平衡性或所谓认知落差,否则隐喻是没有必要的。也就是说,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个相对熟悉或易于把握的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相对陌生或难以把握的事物。一个隐喻得以成立,一定要基于经验中的相互关联,甚至有专门研究隐喻问题的学者强调,“与隐喻相关的唯一相似性是经验相似性,而不是客观相似性。”[15]人类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但相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而言,历史是宏大、复杂的客观存在,人们对之往往目无全牛,难以全面把握,这也是长期以来历史总是沦为唯心主义的世袭领地的重要原因。戏剧本质上是人们创造的一种虚拟游戏,正如毕达哥拉斯的奥运会比喻所启示的,作为置身事外的观众反而可能全面、客观地把握它。这样,对于每个人来说,历史与戏剧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认知的落差,马克思正是用戏剧这一人们相对熟悉和易于把握的事物来隐喻人们相对难以把握的历史。当然,尽管历史是客观的,戏剧是虚拟的,但“经验相似性”中的历史经验是需要一种“上帝视角”或“历史、社会的天文学”才能获得的。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16]马克思所洞察到的历史经验包括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等,但其核心在于存在的历史性。因此,马克思运用戏剧隐喻的深层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理解的戏剧以艺术的形式集中体现了存在的历史性。或者说,马克思借助戏剧的隐喻,形象直观地揭示了存在的历史性。
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在古希腊,神话、史诗既是艺术的武库,又是它的土壤。一方面,神话、史诗是戏剧素材的原型,戏剧本身就意味着基于神话、史诗的反思与创制,属于广义的诗(роêsis),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黑格尔的《美学》都把戏剧理解为诗的一种;另一方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戏剧乃是对现实尤其是人的行动的摹仿,在内容上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戏剧更具有经验而非游戏的特点。马克思晚年在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时,甚至在笔记中多次将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七雄攻打忒拜》《求援人》等剧本当做一种文献资料,来证实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一些论断,[17]这无疑是基于戏剧与历史经验相似性的方面。当然,这种戏剧的“诗性模仿并不是直接断定真理,而是暗示作品本身之中隐含着某些关于人物和行为的真理”。[18]而且,正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戏剧并不呈现一切,而是呈现严肃、本质的东西,包括戏剧在内的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19]卡西尔甚至认为,包括戏剧在内的艺术“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20]因此,戏剧特别是古希腊的戏剧总体上既非对现实的抽离,也非现实的镜像。与现实的这样一个恰当距离,既保证了不陷入琐碎的事实,又不至于过于形而上学,能够以感性的方式表达生活中潜藏的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一切戏剧本来就应该像古希腊的戏剧一样,尽管它不同于哲学的形而上学,但比一般的历史记载更富有哲学意味,反映生活的本质,是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这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自觉走向真正的实证科学但又反对经验主义的旨趣是异曲同工的。
任何真正的戏剧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具有内在的有机统一性,这与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历史有机体思想是完全对应的。对于戏剧中的任何演员而言,剧本是给定的,他们只是“剧中人”,这种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人的被抛性、受动性意味着一种先在的历史情境或“天命”(Gеsсhiсk),也就是历史科学理解的条件性和规律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马克思从波拿巴们“召唤亡灵”的戏剧隐喻中说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戏剧既是舞台空间的艺术,也是时间的艺术,更是过程的艺术。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和时间内,戏剧以开端、发展、尾声等环节浓缩地展现一个故事的“演历”(Gеsсhеhеn),即事物的生成发展过程。在历史科学看来,世界乃是过程的集合,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2]戏剧进程的推动力量是剧中人的行动的矛盾冲突构成的戏剧张力,这些矛盾冲突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艺术反映。把事物看成人的行为生成的过程的存在,确认矛盾冲突是事物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正是马克思历史科学的重要内涵。
马克思不仅把历史隐喻为戏剧,而且强调优秀的戏剧必须反映真实的历史,基于存在的历史性领悟,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路线。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严厉批评卢格,因为卢格认为莎士比亚没有任何哲学体系,所以不是戏剧诗人,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23]马克思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1859年4月,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他的戏剧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漠视农民、平民阶级的作用,简单化甚至是错误地描写了社会冲突,与现实不符。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拉萨尔的出路就在于“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为此,他“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24]有意思的是,这封信之后整整一个月,恩格斯也给拉萨尔写了一封关于这个剧本的信,表达了和马克思差不多的思想。①在系统论述戏剧创作理论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要早得多,在1840年的《现代文学生活》中,他就强调戏剧要把故事放回到“纯历史的基础上”,塑造“纯历史”的人物形象,十分赞赏表现出“真正富有诗意的历史观”的戏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1888年,恩格斯还提出了著名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戏剧创作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莎士比亚化”这一命题在文学艺术界已有丰富的讨论,了解一下莎士比亚自己的创作主张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一命题。在其著名戏剧《哈姆雷特》的第三场中,莎士比亚假哈姆雷特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戏剧观:“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25]黑格尔曾经由衷赞叹:“就描绘直接生活的生动鲜明与伟大心灵的这种统一性来看,近代戏剧体诗人之中很难找到另一个能与莎士比亚媲美。”[26]马克思“莎士比亚化”的思想主要就是强调戏剧要植根于人们现实生活,以丰富、具体、生动的方式反映人们的真实愿望与实际行动,而不是单纯从所谓的时代精神、从原则出发。很显然,马克思对理想戏剧的要求其实就是历史科学的历史性要求。基于这样一种戏剧观,马克思把历史比喻为戏剧就顺理成章了。
三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尽管戏剧总有悲剧、喜剧之分,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思想家们都倾向于认为,只有悲剧才真正代表整个戏剧,甚至悲剧是整个艺术的最高形式。或者说,悲剧是戏剧乃至是艺术的真理。一如前述,在马克思的历史戏剧隐喻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历史的进程有喜剧也有悲剧,但总体上是悲剧性的,这是人类的一种命运。作为黑格尔的门徒和辩证法的最好继承人,马克思一定对黑格尔关于“悲剧是一切艺术形式中最适合于表现辩证法规律的艺术”的观点高度认同。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悲剧进程的思想是其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是其关于历史的戏剧隐喻思想中最精髓、最富启发性的部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与此同时,“凡是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27]这样一来,在新旧事物的更替中就凸现了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然性之间的永恒矛盾,历史因此从两个方面表现为悲剧性的进程。
现实的旧制度虽然从前途上已丧失了历史必然性,但现实又尚未突破其存在的极限(条件)——它在这个极限内是必然的和合理的,它不可能理智地自我灭亡,相反,它仍在为自身的存在进行真诚的合理性辩护,而且这种辩护从历史的高度看是有理有据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28]马克思还指出,往往不仅旧制度的统治阶级真诚地相信自己制度的合理性,而且“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29]人民群众也往往真诚地拥护这种合理性,从而使旧制度继续获得一种存在的合法性。这正是深刻的历史悲剧性所在!马克思以当时的德国为例说:在平庸的德国,普鲁士国王极其不堪,“但它还是足以统治那些只知道自己国王的专横而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的一个人物。”[30]
马克思在论述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事实上是把历时态的新旧制度之争变成了共时态的新旧文明方式之争。在这其中,不仅有上述的旧制度相信自己合理性的方面,还有民族—国家既有尊严、情感、道德、价值的方面。侵略者的血腥和卑鄙是如此超乎想象:“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31]马克思认为,东方殖民地仇英、抗英的“暴行”恰恰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人民战争”。这样,“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32]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33]这就是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悲剧进程。
另一方面,代表历史必然性的新制度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主要是生产力与交往的水平——远未具备或成熟,甚至是广大民众都还不能理解与接受这些新制度、新事物,真理还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而新制度、新事物暂时不可能获得现实必然性。马克思1867年在对比德国和西欧的发展状况时说,“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4]这其实是任何一种新制度诞生之初都会遭遇到的境况。
不过,新制度不会坐等条件的成熟,而是义无反顾地向旧制度发起冲击。可是,革命者终将发现,革命反而使得敌人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变得更为强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新制度和新生力量还未脱去全部陈旧的东西,也还未能训练有素,结果往往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隘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35]于是,“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36]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历史的结局往往表现为代表着“历史的必然性要求”的历史主角的挫折、失败和牺牲——一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开篇就说:“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年—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37]
但是,由于代表着历史必然性,新制度历经磨炼与磨难的彼岸又是无功不赏的,宛如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狡计”。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至1849年法兰西革命失败时指出,“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的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更重要的是,“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有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38]马克思还曾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断定:“事件的进程给思维着的人思索的时间越长,给受难的人团结起来的时间越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孕育着的成果就会越完美地产生。”[39]
精妙的隐喻一经人们接受,以此为基础的推论会把各种经验编织成连贯的一体,从而具有极强的、近乎魔力的解释和预言功能。因为“隐喻可以是自我应验的语言”,“可以成为未来行动的指南”。[40]马克思以戏剧隐喻特别是悲剧隐喻的独特方式,将我们引向存在的历史性一度之中,亲证个人与历史、意志与规律、应有与现有、理想与现实、人文与科学、激情与理性的真实辩证图景。马克思的隐喻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进步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要经历很多阶段才能把陈旧的东西最终送入历史;在此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历史主角及其事业似乎总是在注定只有失败没有收获的命定中抗争。但正是在这一历史悲剧的进程中,人类历史的恢弘、崇高、壮美涤荡了人们的胸怀,生命的意志、激情与力量灌注了人们的心灵。深入到历史性一度中的悲剧隐喻,不仅启示我们以历史规律,而且激励我们对现实面临的挫折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头脑清醒、从容不迫,对事业最终的胜利坚信不疑、矢志不渝,始终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真正的历史高度之上。
[1][德]M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3][4][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204、212、203页。
[5][6][7][8][11][21][22][31][32][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7,376、383、380、411、412、415,584,635-636,375,585,72,710、772,716、1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4、205页。
[13][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13、422页。
[14][美]维塞尔:《普罗米修斯的束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神话结构》,李昀、万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159页。
[15][40][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1、1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8、452、508-509页。
[18] [美]大卫·福莱:《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冯俊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2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8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6页。
[24][27][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555,217、216,560页。
[25]《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46页。
[26][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24页。
[29][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4、143页。
[30][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6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页。
[37][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责任编辑:罗 苹
B03
А
1000-7326(2016)11-0015-07
沈湘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