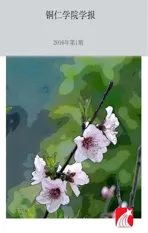枚乘《七发》的背景依托及时空调遣
2016-02-13贾学鸿
贾学鸿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
枚乘《七发》的背景依托及时空调遣
贾学鸿
(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
《七发》把对话双方设定为吴客和楚太子,是以汉初同姓诸侯分布的格局及吴、楚两国的交往为背景。吴客是枚乘本人的投影,楚太子角色的设定则反映出楚国宫廷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七发》有关狩猎事象的叙述,得益于枚乘曾经担任武职侍从的人生经历,体现的是吴地尚武风气。广陵观涛板块出现的地名,有的是确指其地,有的则是泛指,还有的采用指代的方式,应该加以区分。有的地名与神话传说存在关联,是吴地文化的历史积淀。广陵观涛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色彩描写有明暗之别;潮水涨落的曲线构成作品的叙事脉络,缓急相济,在时间的剪裁上颇具匠心。
《七发》;背景依托;空间调遣;时间剪裁
枚乘《七发》在汉赋发展史上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历来都受到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写道:“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刘勰从七体创作的角度,充分肯定《七发》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在刘勰看来,枚乘的《七发》不仅在文体上首开先河,文学成就也是后来的七体作品无法企及的。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大陆几部重要的文学史教材和著作,均对《七发》予以充分肯定。或称:“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赋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1]141还有的从问答体框架、铺陈写物的散文化、题材开拓、道德与审美关联等方面给予高度评价[2]187-189。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枚乘的研究围绕《七发》展开,据初步搜索,相关论文已达200余篇,成为汉赋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如此,《七发》还有许多可供开拓的空间,尤其在创作的背景依托及行文的时空调遣方面,有必要进行深入发掘。
一、吴客、楚太子角色设定的历史背景
《七发》开篇写道:“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吴客和楚太子,是枚乘为《七发》设定的两个角色,全文以二人对话的形式展开,是一篇问对体的散体赋。这种文体的开创者是宋玉,他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等传世作品,都以这种方式写成。宋玉的问对体散体赋,均是宋玉回答楚王提出的问题,他的长篇回答构成文章的主体部分,宋玉本人成为对话的主角。汉代许多散体赋也是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写成,其中对话主人公都有作者本人的投影。东方朔的《答客难》是东方朔与客的对话,东方朔本人是对话的主角。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设置三个角色,分别是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亡是公是对话的主角。实际上,亡是公是司马相如的代言人,在他身上留下的是司马相如本人的投影。
在枚乘之前和稍后时期,问对体形式的散体赋中对话的主角,或者明确标示就是作者本人,或是留下作者本人的投影。《七发》中的吴客列举七件人间乐事开导楚太子,前六件事都是长篇大论,是作品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楚太子的问答却极其简短,处于次要地位。作为《七发》对话主角的吴客,其实就是枚乘本人的化身。《汉书》卷五十一枚乘本传记载:“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3]2359吴王刘濞是西汉初年几大同姓诸侯之一,枚乘曾在吴王府任郎中。郎中,官名,始置于战国,秦汉沿置。关于郎官的职责,应邵《汉官仪》有如下记载:
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位。……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曰三署。署中各有郎中、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4]663
应邵叙述的是秦汉朝廷郎官的职责,其中提到郎中。西汉诸侯王官职的设置仿效朝廷,郎中的职责也是充当侍卫,并且没有正式编制,实际上是门客。《七发》中的吴客,来自吴地,前去开导楚太子,充当他的心理医生,折射出枚乘本人的身份。
《七发》中吴客与楚太子二人的对话,实际反映出吴楚两地的文化交流。这与西汉初年同姓诸侯王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收录了晁错谏书的如下话语: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3]1906
在刘邦所封同姓诸侯王中,齐悼惠王刘肥、楚元王刘交、吴王刘濞的势力最大。但是,到了吕氏执政时期,齐国已经衰落,原来的封地被分割,悼惠王的九个儿子相继为王,齐国四分五裂,无法再与吴、楚两个诸侯国相比。枚乘所处的汉文帝时期及景帝前期,吴楚两个诸侯国仍处于兴旺阶段。《七发》把问对双方设定为吴客和楚太子,从当时两个同姓诸侯国所处的地位而言,不仅旗鼓相当,而且封地相邻,可谓门当户对。楚国的都城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吴国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两地距离较近,便于进行交往。据《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记载,吴王太子的几位师傅都是楚人,他们是由楚地进入吴王宫廷的。景帝三年(前154)的七国之乱,就是吴国与楚国共同谋划的。由此看来,《七发》把对话双方的所在地域设定为吴和楚,与吴、楚两个同姓诸侯国所处的地位、相互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具有必然性、合理性。
《七发》中这位楚太子,作品开头把他写成是富贵病患者:“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逆袭,中若结轖。”对于吴客的这种推测,楚太子基本认可,承认自己是因为沉溺于享乐而生病。因耽于享乐而生疾,是当时贵族的通病。《七发》把楚太子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也有其客观依据。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枚乘是在这次战乱之前离开吴国的。由此推断,他在吴王濞那里任郎中,是汉文帝在位期间及景帝即位的前二年。这个期间,正是楚王室最受西汉朝廷宠爱的时期。对此,《汉书·楚元王传》有如下记载:
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王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文王尊崇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3]1922
楚王室受到西汉朝廷的特殊优待,楚元王刘交的儿子都享受王子的待遇。枚乘在此期间是吴王刘濞的郎中,应当对此有所了解。沉溺于声色犬马而患病,在西汉王室成员中具有普遍性。既然楚王室享受朝廷的特殊优待,楚王子对耳目口腹之乐的追求,应当可想而知。《七发》中这位贵族王子所患的富贵病,应是把当时楚国王室的特殊地位作为背景,有其客观依据,而不是全都出于虚拟。有的学者认为,《七发》中的楚太子,指的是太子辟非[5]1-8。这种推断有待确证。不过,楚王室受到中央朝廷的优待,太子的生活条件格外优裕,倒是毋庸置疑的。
二、田猎叙事对吴文化及枚乘武职的折射
《七发》中,吴客用七件人间乐事诱导生病的楚太子,前六项依次是赏乐、美食、乘车、游观、田猎、观涛。对于这六项活动所作的叙事,文中并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有轻重之分、繁简之别。作品前半部分叙述赏乐、美食、乘车、游观四项活动的乐趣,楚太子都无动于衷,拒绝参与,所作的回答是:“仆病,未能也。”而当吴客叙述田猎之乐时,楚太子则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事情出现转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学者通常都是从娱乐对象的性质方面加以解说。赏乐、美食、乘车、游观,虽然都是人间乐事,但还没有超出楚太子日常生活的空间。而田猎则不同,这一活动已经走出宫苑,并且富有挑战性,所以开始引起楚太子的关注和兴趣。从逻辑上进行推演,这种解说确实合乎实际,言之成理。可是,《七发》对田猎所作的叙事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还有更加丰富的因素。
吴客向楚太子所讲述的田猎场面,锁定的地域是方林、兰泽和江浔:“游涉乎方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李善注:“《字林》曰:‘浔,水涯也。’”[6]1080猎场是在长江岸边。当时楚国都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远离长江;而首都位于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吴国,却位于长江之畔。由“弭节乎江浔”这句判断,《七发》叙述的田猎当是以吴国为空间背景。《七发》对于前四个事象所作的铺陈,涉及到众多的地域。赏乐提到龙门之桐、《麦秀之歌》所在的殷商故地,美食提到各地的物产,游观则出现荆山、汝水等北楚之地,而对田猎所作的叙述,则没有出现吴国以外的地域。
《七发》对田猎所作的叙事,凸现的是“校猎之至壮”,其中甚至不乏血腥场面,体现的是尚武倾向。《汉书·地理志》称:“吴粤之君皆好剑,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3]1677这里所说的吴、越之君,指的是春秋末年这两国的君主。吴地尚勇,直到班固所处的东汉初期仍然如此。枚乘在吴国任郎中,当时的君主刘濞,就是因为勇武而被封为吴王。据《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记载,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前往征伐,当时刘濞年二十,有气力,充当骑将参加平叛,因有功而被封为吴王。同篇还有如下记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7]2823孝文帝期间,枚乘供职于吴国王府,是吴王濞的郎中。此时吴国太子以轻悍的楚人为师傅,吴国宫廷还沿袭着尚武的风气。《七发》把田猎作为超越赏乐、美食、乘车游观的人生乐事加以描写,这种选择体现的是当时吴国宫廷的尚武风气,应是枚乘对田猎非常推崇的文化背景使然。可以设想,没有这种文化背景,枚乘不一定把田猎作为人生乐事写入《七发》,或者即使写入作品,也未必把它置于如此显要的位置。
枚乘在吴王府任郎中,充当侍卫,属于武职。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随从吴王参加许多重要的活动,其中包括田猎。这种活动带有风险性,枚乘作为王府的侍卫,可能随从前往。枚乘有参加田猎的亲身经历,有亲眼目睹田猎的场面和过程的机会,因此,《七发》对于田猎所作的叙事也就别具特色。与对赏乐、美食、乘车、游观四事的描述相比,主要区别如下:
第一,客观陈述与主动参与之别。《七发》对前四项乐事所作的表现,基本上是客观陈述,吴客置身于这些活动之外。赏乐事项是“龙门之桐”领起,美食事项由“刍牛之腴”发端,乘车事项的首句是“钟岱之牡”,游观事项的开头是“既登景夷之台”。这四个事项的起首处都见不到吴客参与的迹象,他是游离于这些活动之外的。而田猎事项一开始便写道:“将为太子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这种表述语气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吴客要给楚太子准备车马,参加田猎活动,他是田猎的参与者之一。吴客是枚乘本人的化身,充当吴王的侍卫,为主人准备车马,随从狩猎是他的职责。田猎事项的开头语,反映出枚乘本人的职责担当。
第二,大量用典与描写为主的区别。《七发》对前四个事项所作的叙述,大量运用各种典故,多取自历史传说,在解读上有较大的难度,经常会遇到障碍。而田猎事项的叙事则明显有别,它虽然总文字量远远超过以前各项,所用的典故却极其有限,而主要采用直赋其事的白描笔法。这种叙事方式使人觉得亲切、真实,并且也比较容易解读。
第三,简与繁的差异。前四个事项都是单独一个段落完成,楚太子的回应也只有一次。田猎事项的叙事则明显不同,整个田猎过程分三段加以叙述,楚太子的回应也反复出现三次,分别置于三段的末尾。田猎事项的三段叙事,展现出它的全过程,并且在场面和情节描写方面很细致,给人以真实感。
总之,枚乘在吴王府担任侍卫官的人生经历,使他有机会亲身体验田猎活动所带来的乐趣。由此而来,《七发》对田猎所作的叙事,也就更加贴近生活现实,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枚乘《七发》对田猎所作的文学叙事,对西汉散体赋产生巨大的影响,司马相如、扬雄散体赋对天子狩猎活动所作的展示,对《七发》均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司马相如、扬雄之所以能够创作出水平很高的狩猎题材的散体赋,除了他们本身文学素养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他们在朝廷的职务担当密切相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司马贞索隐:“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7]2999司马相如曾在汉景帝时期担任武骑常侍,职责是骑马随从天子出行,担当警卫,应当有机会参与诸如天子狩猎之类的活动。张揖特别指出武骑常侍之职与天子狩猎活动之间的关联,已经隐约暗示,司马相如后来创作《天子游猎赋》,得益于早期所担任的武骑常侍这种职务。扬雄以狩猎为题材的散体赋是《羽猎赋》和《长扬赋》。他虽然没像枚乘、司马相如那样担当武职侍从,但是,他有机会参加汉成帝出席的狩猎活动,对此,《汉书·扬雄传》有明确记载。汉成帝田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3]3541汉成帝在射熊馆观看胡人手搏猛兽,“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扬赋》。”[3]3559扬雄的《羽猎赋》、《长扬赋》,是两次参与天子的狩猎活动之后所作,对狩猎场景耳闻目睹,有亲身的体验和感受,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以上,由枚乘《七发》田猎叙事的段落,引出西汉以狩猎为题材的散体赋作者职务担当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西汉狩猎题材的散体赋尽管写得铺张扬厉,但是,并非全是出自虚构和想象,而是有它的客观依据和现实基础,其中作家的阅历、职务担当,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广陵观涛板块的空间调遣
《七发》中吴客引导楚太子的第六件人生乐事是广陵观涛,开头写道:“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从行文语气判断,吴客是观涛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并诱导楚太子也参加观赏,叙事方式与前面的田猎事项一脉相承。
对于吴客所说的广陵,李善注:“《汉书》:‘广陵国,属吴也。’”[6]1081李善认为,广陵指西汉的广陵国,所引《汉书》见于《地理志·下》。颜师古注:“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四年更名广陵。”[3]1638李善对广陵所作的认定是正确的,《史记》、《汉书》可以提供许多证据予以支撑。但是,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叙述浙江钱塘潮时写道:“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8]568郦道元所引的语句出自《七发》,与今本所传稍异。他认为,《七发》所说的广陵涛是在浙江钱塘江,而不是在扬州。
郦道元断定广陵涛指的是钱塘潮,由此引发一桩学术公案,即广陵曲江究竟是在扬州,还是在钱塘江。清朝初期,毛奇龄、朱彝尊、阎若璩都把广陵曲江说成是钱塘江,稍后的扬州学派对此予以反驳。“汪中的《广陵曲江证》指出了郦道元的疏误,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广陵曲江即扬州一带的长江河段。”[9]130梁章钜的《文选旁证》则旁征博引,再次确证广陵曲江指的是扬州、镇江之间的长江区段。[10]798汪中(1744~1794),江苏江都人。梁章钜(1775~1849),福建长乐人,官至江苏巡抚。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同样确认广陵曲江是在扬州,李慈铭(1830~1894),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梁章钜、李慈铭均非扬州本土人,但他们一致断定广陵曲江是在扬州,而不是在钱塘。经过这几位学者的辨析,这桩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基本结束,广陵曲江位于扬州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力主广陵曲江位于扬州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扬州画舫录》的作者李斗。他是扬州仪征人,在扬州居住达30年之久。《扬州画舫录》卷七列有“广陵潮”条目,卷九列有“广陵潮再论”条目,都是论证广陵曲江位于扬州,而不是在钱塘,列举的证据极其充分。这部书写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同年有自然盦初刻本。李斗和汪中是同时代人,都属于扬州学派成员,并且对广陵曲江作出了相同的认定。稍后于李斗和汪中的梁章钜,在论证广陵曲江位于扬州的过程中,援引俞思谦的大段考证。俞氏的考证提到李颀诗、李绅《入扬州郭诗注》,还提到蔡宽夫《诗话》。无独有偶,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七的“广陵潮”条目,也提到蔡宽夫《诗话》,以及李颀的“扬州郭里见潮生”的诗句,并且明确标是出自“御制诗序”[11]95。这样看来,俞思谦和李斗所援引的文献来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李斗的上述考据,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七发》提到的广陵曲江观潮,指的是在扬州观赏潮水。既然如此,对于其中出现的地名,理应放到扬州、镇江之间的长江区段加以考察,从而透视观涛叙事在空间调遣方面的具体做法,揭示出相关地名所处的空间方位及其文化内涵。
《七发》的地名集中出现在两个段落,首段如:
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兮崖涘。流揽无穷,归神日母。……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
这段文字中出现的地名,南山、东海比较容易理解。扬州、镇江隔水相望,镇江在南,扬州在北。扬州临江无山,镇江则是山在江边。所谓的南山,指镇江的北固山。这个区段的长江由西向东奔流而入海,所谓的东海,指长江所汇入的海域,至今仍称为东海。对于文中出现的日母,李善注:“言周流观览而穷,然后归神至日所出也。”[6]1081李善把日母释为太阳升起之处,也就是东方,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在神话传说中,太阳的母亲确实位于东方。《山海经·大荒南经》写道:“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袁珂先生称:“日浴,宋本、吴宽抄本、毛辰本并作浴日,诸书所引亦作浴日,作浴日是也。”[12]438神话传说中,太阳的母亲是羲和,她生出十个太阳并在东方甘渊为他们洗浴。《七发》称东方为日母,既是取象于太阳升起于东方这种自然规律,又有神话传说的背景。
这段文字出现的最后一个名词是朱汜。李善注:“盖地名,未详。”[6]1082这个地名确实有些费解,因为它涉及到古代的哲学理念及词语的特殊含义。朱,在这里用以指代空间方位。《吕氏春秋·有始览》:“西南曰朱天。”高诱注:“西南,火之季也,为少阳,故曰朱天。”[13]668《淮南子·天文训》亦有相同记载。朱,亦指西南,是把色彩与方位相配。再看汜,《诗经·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毛传:“决复入为汜。”郑玄笺:“江水大,汜水小。”[14]108汜,指支流从主流分出,最后又归于主流。朱汜,指的是位于西南方向,从长江分出而最终又汇入长江的支流。扬州、镇江段的长江水域,确实存在这种先分后合的现象。对此,赵苇航先生有如下论述:
世界诸大河的河口段,都有河道弯曲或分汊的特征。扬州地区长江水道正是以这种弯曲河道的形式发展的。江中布有江水洲(或河口沙坝),使河道分汊,水流分成两段,绕行江心洲两侧,顺直河道变为弯曲。前人把洲北的汊道称为北江,或北港;洲南的汊道称为南江,或南港。……现在和畅洲的北支汊道,也呈弧形弯曲。历史演变的遗迹证实,镇扬河段具有分汊弯曲的特征,“曲江”就是这种特性的产物。[9]131
赵先生以上论述是对文中“广陵之曲江”加以解释,可谓恰如其分。同时,这段论述对于破解“朱汜”的含义,亦有借鉴意义。镇江、扬州区段的长江分汊弯曲,而“广陵潮发生在长江的北支汊道--曲江(北江)”[9]131,当时的长江是以流经广陵的一侧为主干,而流经镇江的一侧为支流,故南侧汊道可称为汜。扬州在北,镇江在南,故镇江一侧汊道可称为南汜。长江水域在镇江、扬州区段是弯曲的,而不是直线的东西流向,镇江一侧汊道不是位于广陵的正南,而是在西南方向,因此称为朱汜,即西南方向的支流汊道。
《七发》以上连续出现地名的段落,其中的地名承载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标示江水的流向,二是表现观赏者的活动。“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是叙述观赏者的活动,他关注长江对岸的南山,远望长江汇入东海。“流揽无穷,归神日母”,还是写观赏者的心理活动,想的是太阳即将从东方升起。而“临朱汜而远逝”,则是描写镇江、扬州区段长江的分汊而流的态势。
《七发》集中出现地名的第二个段落如下:
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淩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
这个段落出现的地名非常密集,解读难度较大。对于“或围之津涯”,李善注:“或围,盖地名也。”[6]1083李善猜测或围是地名,但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其实,这里的或围,是用于修饰后面的津涯。津指渡口,涯指水边。津涯,谓渡口的水边。或围,或,谓有。围,环绕。有围,即有环绕。“或围之津涯”,指有环绕的水边,这是广陵涛可以见到的兴起之处。为什么把广陵涛在视域之内的始发之处称为“或围之津涯”,这与当时长江入海口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
汉时长江口在扬州至泰州一带,河口段近似一喇叭形,喇叭口朝东北方向,这是形成广陵涛的有利条件。喇叭河口,向下展宽,向上束狭,有利于潮波在上潮传播过程中愈上愈强。加上曲江水浅,海潮从开阔的海湾骤入河口浅隘处,潮波就容易破裂而形成潮涌。[9]131
这段论述对于解读“或围之津涯”很有帮助。西汉时期长江口是喇叭形,所形成的港湾两边被陆地所环绕,是喇叭口形地势,所以称为有环绕的渡口水边,视域之内的广陵涛就从这里兴起。围,指环绕,即长江口喇叭形的两侧。
“回翔青篾,衔枚檀桓”,李善注:“青篾、檀桓,盖地名也。”[6]1083李善注语焉不详,没有出示这两个表示空间方位名词的具体所指。篾,一种竹子。张衡《南都赋》在列举多种竹子之后,称它们“澶漫陆离”。澶漫用以形容竹林,指的是散布之象。《七发》所说的檀桓,亦即《南都赋》出现的澶漫,都用以修饰竹林,指的是漫衍散布之象。檀桓,有时又写作檀栾,也是用于形容竹林。枚乘《梁王菟园赋》开头写道:“脩竹檀栾,夹池水,旋菟园,并驰道,临广衍,长穴板。”[4]236从这几句话所表达的意义判断,檀栾指的是竹木分布得很广,所占面积较大。檀桓、檀栾、澶漫,是同一个连绵词的不同写法,经常用于形容竹林的漫衍,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专用术语。《七发》前面称“回翔青篾”,指在桃枝竹生长之处回翔。紧接着又称“衔枚檀桓”,像军队成员口衔竹木片静寂无声,其中的檀桓,还是指竹林,突出它的广衍分布。由此看来,《七发》中的青篾、檀桓,虽然起着指示空间方位的作用,但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地名,而是用指代的方式表示竹林所在位置。正因为如此,李善注对它们只能含混言之,而无法落到实处。
再看文中提到的伍子之山。《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自杀之后,“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7]2180关于胥山的具体方位,斐骃集解、张守节正义,或称是在苏州东南三江口附近,或称在太湖边,确认是在吴地。从《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记载可以认定,胥山应该位于邻近太湖的长江岸边。当时的长江从扬州以东入海,还没有伸展到南通一带,距离吴地最近的长江区段,就在扬州附近。那里的太湖又称为五湖,水域面积很大,北部已靠近丹阳。胥山位于太湖边缘,又临近长江,只能是在扬州区段的江岸附近,故《七发》把它说成是广陵涛所波及之处。
与胥山前后相次的是骨母之山。对于骨字,李善注:“疑骨母字之误也。”[6]1083因此,他把骨母释为胥母,认为骨是胥字之误。骨、胥,字形相近,二者确实容易混淆,李善的说法在后代得到普遍认可。梁章钜写道:“古‘胥’字作‘’,故因而误。”[10]800从文字构形上进一步确认了李善的判断。可是,李善注又把伍子胥庙所在之山称为胥母山,这就造成混乱,把胥山和胥母之山混为一谈。胥母作为地名,见于《越绝书》,“后世学者注《越绝书》此句时,均指出‘胥母’为苏州太湖中的另一座山--洞庭东山。”[15]94-96太湖的洞庭东山,一名胥母,即今莫厘山。
把胥母说成是太湖的洞庭东山,是有它的根据的,那就是胥母与太湖的关联。《诗含神雾》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16]伏牺,即伏羲,传说中的华夏人文始祖。相传伏羲是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华胥氏是伏羲之母,当然可以称为胥母。那么,传说中的华胥氏履大迹的雷泽究竟位于何处呢?对此,《山海经·海内东经》提供了答案:“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对此,袁珂先生写道:“此《海内东经》‘在吴西’之雷泽,确当是震泽即太湖。”[12]382太湖,古称震泽、具区泽。相传华胥氏履大迹而生伏羲的雷泽,就是今太湖地区。西汉时期的太湖,其北部是今长荡湖、禹湖,这两个湖的周围是湿地,已接近今常州、丹阳,与扬州的长江岸段不过百里。《七发》提到的胥母之场,指的是华胥氏履大迹的地域,是以神话传说为依托而生成的地名。至于后来把太湖的洞庭东山称为胥母山,则是对这个神话传说进一步加以推衍、附会的产物,虽然不是很确切,但也有它的依据。至于地名为什么称为胥母山,后人却未能进一步加以考索,只是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而接受下来。
《七发》广陵观涛段落还有“凌赤岸,篲扶桑”之语。李善注写道:
赤岸,盖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并以赤岸在广陵,而此文势似在远方,非广陵也。[6]1083
李善认定赤岸是地名,但对于它是否位于广陵又表示怀疑。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由赤岸这个名称的特殊用法造成的。李善所引曹植之文,出自他的《求自试表》,其中写道:“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玄塞。”这是他叙述随从曹操四方出征的经历,赤岸、沧海、玉门、玄塞,分别指代南、东、西、北四方,依次指曹操对孙权、袁谭、马超、乌桓的征伐。或称:“赤岸,赤壁。”[17]879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这里的赤岸指长江武汉区段,那里曾发生赤壁大战。郭璞《江赋》写道:“源二分于崌崃,流九脉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馀波乎柴桑。”李善注:“《汉书》,庐江郡有浔阳县。”“《汉书》:豫郡有柴桑县。”[6]388
与赤岸并列的浔阳、柴桑,位于今江西九江的北部和南部,在长江九江区段的两侧。与这两个地方相提并论的赤岸,也应在长江的九江区段。从曹植的《求自试表》到郭璞的《江赋》,赤岸都用于指代长江的岸畔,但具体地点存在较大差异,一在今湖北武汉附近,一在今江西九江一带。这一事实表明,从曹植所处的建安三国时期,到郭璞所处的东晋阶段,用赤岸指代长江岸畔,是文人反复使用的笔法,具体空间方位则因时因地而异。枚乘《七发》中所说的赤岸,也属于这种类型,它指的是广陵区段的江岸,而不是指某个固定地点。文中赤岸与扶桑对举,扶桑指东方,是概括言之;赤岸指广陵区段的江岸,也是概括言之。赤岸这个名称,从枚乘到曹植、再到郭璞,都用于指称长江岸畔,是泛指、概指,而不能过分地以实求之。
李善怀疑《七发》所说的赤岸不在广陵,可是,对郭璞《江赋》提到的赤岸,李善注写道:“《七发》曰:‘凌赤岸’。或曰:赤岸在广陵兴舆县。”[6]388李善在这里又把《七发》和《江赋》出现的赤岸混为一谈,用《七发》为《江赋》作注。从他引用的说法推断,在李善为《文选》作注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把《七发》所提到的赤岸落实到更加具体地段的做法。到了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则称赤岸山在六合东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10]801。赤岸所处方位随着历史推移而日益具体确切,这与前面提到的胥山、胥母之场的情况相似,是经常可以见到的现象,但不能把它们作为确凿的证据。
《七发》集中出现地名的第二个段落的末尾提到“合战于藉藉之口”。李善注:“藉藉,盖地名也。”[6]1081从常理推断,把叠字作为地名,基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藉藉之口”又确实是指涛水所波及的空间,需要把这四个字放在一起加以考察。藉藉,交错杂乱,回应前面的合战。口,指长江入海口。如前所述,西汉时期的长江口近似喇叭形,河口朝东北延展增宽,犹如人口张开之象。波涛激荡于喇叭形江口,故称藉藉之口。
《七发》集中出现地名的第二个段落,所有地名都用于表示广陵涛所涉及的空间,是一组标示地理方位的词语。这组词语有确指与泛指之别,有直接标示与间接指代的差异。对于这组词语的解读,必须以广陵涛所涉及空间的地理形势为依据,同时还要参照与该地密切相关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并且注意作品空间调遣所采用的修辞手法。
四、广陵观涛板块的时间剪裁
广陵观涛板块按照时空顺序进行叙事,在出现一系列相关地名的过程中,体现出时间的流程,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广陵观涛板块明显地划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从“客曰:‘将以八月之望,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开始,结尾是“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这个段落所叙述的是观涛的前奏,“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涛水还没有兴起,所观赏的是涨潮前的长江流水。那么,观赏者是在什么时段来到江边的呢?对此,文中作了交待:“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李善注:“莫离散,谓精神不离散也。发曙,发夕至曙也。《说文》曰:‘曙,旦明也。’”[6]1082李善注基本正确。今本《说文》无曙字,李善所见本当与今本异。这里所说的发曙,指黎明、天亮,开始出现阳光。这个段落前面还有“归神日母”之语,表面是说凝神于太阳升起的东方,内里暗含期待太阳升起之意。从这两句所提供的信息判断,观赏者是在拂晓来到江边的,开始阶段天还没亮,观览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曙光。这个段落把主要时间设定在天亮之前,能见度较低,因此,对长江水势所作的描写重点在突出它的模糊不清。其中的“恍兮惚兮”、“混汨汨兮”,都是用以形容江水扑朔迷离、隐隐约约,是用暗色加以描写。广陵观涛板块第二段是对涛水加以铺陈,从“其始起也”到“遇者死,当者坏”,是描写涨潮的场景。开头写道: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
这段描写接连运用两个比喻,把初发的潮水比作白鹭下翔,比作素车白马排列前行,都是用以凸现潮水的白色。除了比喻之外,所运用的词语也往往表示色彩的白。对于浩浩溰溰,李善注:“溰溰,高白之貌也。”[6]1082溰溰,指的是白色,用于形容白马素车。对于涛水的旁作而奔起,文中写道:“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这里所说的太白,指的是作战时军事将领所持的旗帜。《逸周书·克殷解》:“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18]345太白,《史记·周本纪》作大白:“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7]124太白,指纯白色材料制成的旗面,即白旗。李善注以河伯释太白,迂曲难通,不合文意。对于纯驰浩蜺,李善注:“浩鲵,即素蜺也。波涛之势,若素蜺而驰,言其长也。”[6]1082这一解释是正确的,浩蜺,指的是白蜺、素蜺。以上句子描写涛水初涨,反复渲染它的白、素,用的是亮色,与第一个板块用暗色描写江水,形成鲜明的对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所依托的时段不同。观赏江水奔流是潮水未至之际,天还未大亮,故所作的描写用表示幽暗色彩的词语。而观涛则是天明之后,能见度高,所以,浪涛翻滚所呈现的白色清晰可见。这段文字所作的色彩描写,与天明这个特定的时段相对应,所作的调遣可谓独具匠心。
观涛板块第二个段落对于涨潮场面的描写,前一部分是叙述潮水逆流而上的情景。在此之后,又出现一段密集排列地名的叙事。先是:“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清篾,衔枚檀桓。”交待逆流而上的潮水的初发地点,以及它在向上游推进过程中所经的区域。而“弭节伍子之山”,则是说逆流而上的潮水停止向前推进,已经达到前行的终点。从“通厉胥母之场”开始,描写的是潮水回落,向下游奔流的场景。海水涨潮是一波接着一波,由此而来,前波潮水回落,必定与继续上行的潮水发生冲突,文中所说的“合战于藉藉之口”,指的就是这种场景。这段文字相继使用初发、回翔、衔枚、弭节、通厉、合战等词语,与一系列地名相对应,按照时间顺序全过程地展开,出现潮水涨落的壮观场面。从初发到回翔之后的态势,前面已有渲染和铺陈,故文中不再重复。而回翔之后的态势,则是这后一段落描写的重点。李善注:“回翔,水复流也。衔枚,水无声也。”[6]1083李善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回翔,指逆行的潮水或进或退,已是强弩之末,不再有先前的威力。衔枚,则是指潮水没有声音,上行即将停歇,弭节则是潮水停止上行。从“通厉胥母之场”开始,潮水则进入回落阶段,回归大海,并在长江入海口与后至的涨潮相互激荡。
广陵观涛板块所作的叙事按照潮水起落的时段依次推进,实现了刚柔互补、缓急相济。描写潮水的初涨,节奏急促,气势磅礴。展示潮水上行阶段的末尾,则从容按节,舒缓迂徐。最后一段表现潮水回落奔向大海,则又恢复第一段落的描写笔法,以急促的节奏收尾。在此过程中,声响、色彩、物体形态的描写穿插其间,体现出不同时段的景观特点。按照时空顺序进行叙事,是汉代散体大赋普遍采用的方式。《七发》作为汉代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为后来的赋体作家所效仿。
五、结语
西汉初期,同姓诸侯王门下的幕僚文人,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汉书·地理志》写道: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3]1668
汉初同姓诸侯王虽然同出自刘氏,但是,所分封的地域不同,各处的民风习俗及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就这些诸侯王本身而言,也是各有特点和个性,人生取向大相径庭。而那些诸侯王门下的宾客,出身经历及爱好也是差别甚多。这些文人的创作以诸侯王及其封地为背景,也以自身的经历及生存状态为依托。因此,对这些幕僚文人进行创作的背景依托加以审视,实际是对当时的文化生态进行历史还原,有利于对文学作品的生成进行深层揭示。同时,诸侯王所在区域的山川形势和人们的社会活动,一旦被纳入幕僚文人的创作视野,势必对文学作品所采用的笔法起制约作用。枚乘的《七发》作为汉赋名篇,为从上述角度切入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能,并且有助于这个领域探索的深入进行。政治背景、人生经历,决定了《七发》的选材,也制约着它的叙事笔法。沿着这个思路去审视汉初其他诸侯王门客的创作,可能还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1]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Z].北京:中华书局,2009.
[5]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J].西北大学学报,1999,(1).
[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Z].长沙:岳麓书社,2002.
[7](汉)司马迁,撰.(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北魏)郦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Z].北京:中华书局,2009.
[9]赵苇航.汪中对广陵涛研究的贡献[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
[10]梁章钜,撰.穆克宏,点校.文选旁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1]李斗注,王军,评注.扬州画舫录[Z].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袁珂.山海经校注[Z].成都:巴蜀书社,1996.
[13](秦)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4](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Z].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吴恩培.名作背后的文化之争--枚乘《七发》后的曲江观涛处及“胥山”[J].名作欣赏,2011,(25).
[16](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七十八)[Z].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17]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18]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The Background of Qi Fa Written by Meisheng and its Space-Time Dispatchment
JIA Xue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
Qi Fa, taking the kingdoms' distributions with the same surname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the intercourses between Kingdom Wu and Kingdom Chu as background, supposes one side of the dialogue as Wuke and the other as Prince Chu. The former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uthor himself, Meisheng, and the latter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pecial treatment enjoyed by royal court of Kingdom Chu. The description on the hunting scene in Qi Fa benefits from Meisheng's past experiences in serving as a military attendant, which embodies Kingdom Wu's tendancy towards advocating the martialism. Of the place names appearing in the scene of tide-watching in Guangling, some are definite
, some are generic references and others are substitute references, which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Some places are related to myths and legends, which are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Wu's culture. The tide-watching scene in Guangling is unfolde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with the color description light and shade ,the curve of tide's rising and falling makes up the narrative skeleton with the tone gentle and urgent, and the clipping of the time is expertly planned.
Qi Fa,the background,space-time dispatchment,the clipping of time
I207.224
A
1673-9639 (2016) 01-0016-09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5-11-15
贾学鸿(1969-),河北涿州人,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庄子结构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