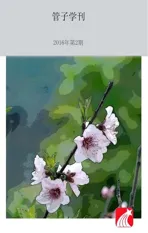简论庄子的养生思想
2016-02-01孟娜
孟 娜
(山东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古代学术思潮
简论庄子的养生思想
孟娜
(山东理工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庄子的养生思想包括养形、养神两部分内容。庄子认为养形、养神两者缺一不可。养形方面,针对世人过度保养身体导致伤身害命的弊端,他提出形神并重、内外兼养的养形思想;并进一步提出“弃世”的观点,即身虽参与世俗之事,但内心抛弃对名利的强烈追求。养神方面,针对世人被名利所困的问题,他提出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养神思想。庄子认为人们做任何事情只有抛弃个人名利,从“道”生万物的无私角度出发,才能在复杂的世俗事务中,既做到保全性命,又做到顺应自然之理,以达到游刃有余的合道境界。
关键词:庄子;养生;养形;养神;合道
养生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生活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战乱不断的战国时期。当时普通百姓因苛政、战乱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或不择手段争名夺利,或肆意挥霍掠夺来的财产,也形成了无法保全性命的悲剧。庄子基于此,将养生思想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庄子的养生思想并非仅限于保养形体,还进一步涉及到养神的问题。庄子认为养形与养神缺一不可,养形是基础,养神是目的。养形养神最终是为了在矛盾重重的社会中游刃有余,进而达到“安时而处顺”、合于道德的逍遥游世的理想境界。庄子的这种养生思想虽然与现代体育意义上的养生观念不同,但却能给现代体育养生观一定的启发。
一、庄子的“养生”内涵辨析
“养生”思想源远流长,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养生”概念的理解不同。学术界对庄子的“养生”思想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念认为“养生”即保养身体,如《辞海》解释养生时说:“养生,保养身体。《庄子·养生主》:‘文惠君曰:善载!吾闻疱丁之言,善养生焉。’”[1]2161学术界曾围绕庄子“养生”是否具有体育意义上的养生思想展开争论,有学者认为《庄子》中的“心斋”“坐忘”等养生方法具有现代体育意义的练功方法,因而庄子的养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养生即保养生命的含义[2];另有学者认为养生是“一种人生哲学、处世态度”,因而不具有“体育意义的养生思想”[3]。第二种观点认为养生应该包括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如《辞源》载:“养生,摄养身心,以期延年。《庄子·养生主》:‘吾闻疱丁之言,善养生焉。”[4]1865还有学者认为“庄子所谓的‘生’,实际上是含蓄了高下不同的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自然的形质,属于人的生理层面;其二则是由人的自然生命所开展的精神生命,这属于人的心性层面。而庄子的养生实则是经由自然生命擢升到理想境界的精神活动,反映了心与道相冥合的精神境界。所以庄子的‘养生’实际体现了道的精神义旨。”[5]
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庄子的养生思想的内涵应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庄子认为形与神都由“道”“德”产生,他们共同构成了“生”,因此在理论上身体与精神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从实践角度而言,养形是为避免因“厚生”而短寿,以达到寿终正寝的目的;养神是让人们在心理上摆脱是非、名利对人的不良影响,以达到“安时而处世”的合“道”境界。两者比较,养形是基础,养形比养神更为容易实践,但养神是目的,因而对养神论述较多。然而只有形神兼养,才是庄子意义上的“养生”。
实际上“生”在《庄子》书中有特殊含义。正如徐复观所言:“《庄子》一书,用‘身’字,用‘生’字时,是兼德(性)与形而言,并且多偏在德(性)方面。但他用‘形’字,则常仅指的是外在的官能与形骸(五官百体)所表现的动作。”[6]230徐复观的这种理解非常准确,庄子之所以把“生”“形”做一定意义的区分,这源于他对“生”“形”来源的认识。《庄子·天地》载:“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庄子认为万物由“道”“德”所“命”,并且“形”“性”由“道”“德”所生。庄子对“形”“性”进行了界定。“形”,“所谓物形之是也”[7]239,“大小、长短、修远、殊异而并存者”[8]106,可见《庄子》的“形”,从万物的角度指的是万事万物具备的外在形态,从人的角度而言当然指以五官为代表的身体。“性”,即“形体保神,各有仪则”,指的是“形体之中,还保有精神的作用;而这种精神作用,是有仪有则的”[6]228。《庄子》又认为“生”与“性”密切相关。“性者,生之质也。”(《庄子·庚桑楚》)生命的本质就是性。而《庄子》中“生”多指“性”或“德”,这在《庄子·养生主》中也有体现。《庄子·养生主》载:“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可以保生”中的“生”,即“读为性”[9]95。可见庄子认为从万物起源来看,“形”与“性”都是由“道”“德”产生,他们的地位同等重要。这就决定了庄子的养生思想中形、神并重的特色。
二、庄子的养形思想
庄子非常重视“形”即身体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养形是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很多富贵之人过度注重保养身体,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庄子·达生》载:“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养生固然离不开外物,但社会上却出现物质众多但身体保养不好、形体健康但生命消失的奇怪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众人养生太过。吕惠卿对此解释说:“养形必先之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则凡形不养者以其生生之厚,而不在于物之不足也;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则凡生亡者以其动之死地,而不皆在于形之离生也;则达生之情者,安用夫为形以务乎生之所无以为载!”[7]348通过吕惠卿的解释可以看出:庄子认为形与物的关系非常微妙。人们保养形体离不开饮食、衣服等外物,但如果过度追求外物,反而会伤害身体。社会上的权贵往往会因追求用以养生的外物而不得善终,老子称这种现象为“生生之厚”。《道德经》五十章载:“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生生之厚”,严灵峰解释说:“饱饪烹宰,奢侈淫汰,戕贼性命……”[9]259短短16字,将统治者由长寿走向短命的原因说得一清二楚,即过度地保养形体。
庄子非常反对过度保守形体的作法。《庄子·刻意》载:“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富贵、长寿、好的名声是人人所尊贵的,身安、厚味、美服、美色、妙乐是人人所梦寐以求的。然而富人殚精竭虑追求财货却因此损伤了身体,贵人日以继夜追求禄位而耗精劳神,天下名士为保全名声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些举措或作法对于保养形体来说,都是外在的事物。
庄子养形不仅不止于此,而且还提出形神并重、内外并养的保养方法。《庄子·达生》载:“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庄子》在此举了两类极端的养生例子。一类以鲁国的单豹为代表。他们希望通过“岩居而水”的隐居生活或“吹煦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等种种“导引”(《庄子·刻意》)方法以达到避害、长寿的目的,然而最终被以饿虎为代表的意外之祸所杀;另一种以鲁人张毅代表。他们希望通过对世人恭敬、讲究礼仪等方法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以躲避意外之祸的伤害,然而却被以疾病为代表的内祸所伤害。这两个例子,前者“养其内而虎食其外”,后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庄子·达生》),都不得善终。庄子认为“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庄子·达生》),即善于养生的人应该像牧羊一样,鞭策落后的羊,也就是说,真正懂得养生的人应该内外兼修,形神兼顾,既要养其形,又要养其神,这样才能既避免外来横祸又避免内部疾病伤身害命。
为达到养形的目的,《庄子》甚至提出了“弃世”的观点。《庄子·达生》载:“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并非远离世俗之事,而是特有所指。“弃世”,成玄英解释为“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又说:“夫人之生也,形之妍丑,命之修短,及贫富贵贱,愚智穷通,一豪已上,无非命也。”[10] 632、630通过成玄英的解释可知:庄子认为人们容貌的好丑,寿命的长短,以及贫富贵贱、愚蠢聪明等等都是上天所命的,如果人们对此孜孜以求,即是追求世间分外之事。庄子的“弃世”即是生活在世间,但抛弃人们对贫富、长寿等的过分执著追求。钟泰解释为:“弃世非绝世也,弃夫世俗之见,即上文‘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者。”[11]410—411林希逸解释为:“弃世者,非避世也,处世以无心,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后起……”[12]285钟泰的解释的大意与成玄英的相同,“弃夫世俗之见”即“弃却世间分外之事”,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林希逸的解释则说明了庄子主张的入世心态即没有私心或者说没有成心,这种心态的外在表现即是“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后起”。可知:庄子的“弃世”并非避世隐居,而是身虽参与世俗之事的同时,但内心抛弃了对功名利禄、富贵、长寿等强烈追求。庄子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既使身体避免名利带来的外来横祸的伤害,又使内心避免因富贵贫贱、荣辱等带来的内在疾病的伤害。
其实,庄子追求的长寿并非以战国时期方仙道追求的“不死之药”及长生不死,而是生死自然。《庄子·德充符》载:“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大宗师》则说:“死生,命也。”可见,庄子认为生死存亡属于“德在具体化中所显露出来的‘事之变’”,是“德在实现历程中对于某人某物所分得的限度”即“命”[6]229的运行。《庄子·大宗师》又载:“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块”此处指“自然”或“造物”。而《庄子》中无论“自然”,还是“造物”都是指“道”或“德”。可见庄子认为人们的生死是由“道”或“德”决定的,人们没有必要贪生怕死。具体到养形方面,他主张“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载:“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适来,夫子时也”,郭象注曰:“时自生也”;“适去,夫子顺也”,郭象注曰:“理当死也。”[10]129庄子认为生死都属于自然的事情,人们应该正确看待生死。可见,庄子的养形并非长生不死,而是生死自然;他提倡的长生或长寿是相对于人们因过分追求功名利禄而造成的人为短命。这是庄子养形的最高境界。
三、庄子的养神思想
其实庄子的养生思想中养形与养神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养形之中必有一定的养神内容,养神的内容也涵盖了部分养形的内容。上文养形思想中的张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以及庄子独特的“弃世”观、生死自然观都与养神有一定的联系。只不过前者主要从养形的角度进行论述,后者则主要从养神的角度进行阐释。
庄子的养神思想主要从《庄子》中的《养生主》和《达生》两篇中体现出来。正如学者所言:“《养生主篇》,主旨在说护养生之主——精神,提示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任自然。外篇《达生篇》,通篇发挥养神之理。”[9]93“《养生主》犹言人的生命之自性可养”[13]91,“此篇教人养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16],这些精辟的论述都证明了庄子养生的主旨在于养神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究其原因,正如王夫之所言,“养形之累浅而显,养知之累隐而深”[25],其中的“养知之累”即与养性密切相关。
如何“养神”,即“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吕惠卿注曰:“上不为仁义之行以近名,下不为淫僻之俗以近刑,善恶两遗,而缘于不得已以为经,是乃刳心去智而止其所不知之道也。缘督者,缘于不得已之谓也。[11]”释德清则解释说:“为善无近名之心,为恶无近刑之事。但安心顺天理之自然以为事,而无过求驰逐之心也。”[14]62为善求留名,为恶受严刑,是世人皆知的做事准则。庄子在此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做事准则:做好事不存求名之心,做坏事却不触及法律。而要做得到上述两点,只有心中无“成心”或偏见,即没有从自己利益出发的善恶之心。这就是“缘督”,即顺着中道。《养生主》分别举例说明这三条原则。“疱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名义上赞扬疱丁解牛的技术高超,实则说明“缘督以为经”以养生的巨大利益。正如释德清所言:“疱丁,喻圣人,牛喻世间之事……解牛之技,乃治天下国家,用世之术智也。刀喻本性,即生之主,率性而行,如以刀解牛也。”[14]62庄子以疱丁比例圣人,以牛比喻世间之事;以刀比喻人性。又以大刑、大名、“大善大恶之争”比喻“大軱”[8]32。庄子认为当人们没有体会“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养生道理时,在处理世事时会觉得世间艰辛,就好像疱丁初解牛时满眼都是牛;当他体会并践行上述养生道理时,在处理世事时会顺着事物自然之理而行,丝毫没有争名夺利之心,自然没有伤性害命之实,这和疱丁后来解牛游刃有余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详细说明养神妙理,庄子特举三例加以证明。一是公文轩问右师介足是天生,还是为人为。右师答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庄子·养生主》)我们由右师的回答可以知道:右师独足是先天天生如此,而非后天妄为而成。对此,刘武解释说:“天之所与,即无异天与之以刑也。刑为天与,非由为恶,惟当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已。夫不为恶,且有如右师之受天刑者,更何可为恶,以自近刑乎?此段喻为恶无近刑。”[15]81右师虽不为恶,但乃受天刑“介足”(即一足),这提醒人们庄子所谓的“为恶无近刑”并非真正做坏事而不受刑罚,而是另有所指。《庄子·养生主》载:“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至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刘武解释说:“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是帝之悬解,非同夫世俗之死也。此秦所以失号而不哭。此段再喻为恶者无近刑。盖遁天倍情,过于哀哭,是为恶也;足以伤生损性,近刑也。”[15]83老聃去世,秦失以老聘的朋友的身份前去吊唁,“三号而出”,虽有吊唁之礼却没有悲伤之情。秦失的弟子认为秦失所作所为不合常理,因而询问原因。秦失认为体道者应生死自然,不能因生死而悲伤。因此秦失的吊唁行为从世俗角度来看,是恶的。但从体道者的角度来看,是顺道合德,不会伤生损性。由此可以看出“为恶无近刑”中的“为恶”是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看,如果从“道”生万物的角度,从“性”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这才是“为恶无近刑”的真实内涵。此两例重在说明“为恶无近刑”,庄子又举一例说明“为善无近名”。《庄子·养生主》载:“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刘武解释说:“此段言雉不求畜乎樊中者,以一入樊笼,便受囚拘……何若饮啄泽中,放旷于自得之场?食饮虽艰,而身则适……以喻人有心为善,则必得名,何异雉之求畜乎樊中?盖名,人之樊笼也。此段喻‘为善无近名’。”[15]82庄子此段明论野鸡被畜养笼中,虽饮食无忧,却失去自由,不如他们在野外生活,自由自在,但暗喻世人做善事,处处为名利,这与野鸡被关在笼中同出一辙。从“道”的角度来看,名利是世人的牢笼,人们虽然享受到名利带来的利益,但却被名利牢牢地拴住。老子说:“宠辱若惊……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道德经》第十三章)世人得宠和受辱都会惊惶失措,这生动地描述了世人为名利所困的窘态。因此庄子认为人们做任何事情只有抛弃个人的利益,一切从“道”生万物的无私角度出发,才能“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也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在复杂的世俗事务中,既做到保全性命,又做到顺应自然之理,逍遥游世的合道境界。
由此可以看出庄子的养生思想虽然与现代体育养生思想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对人们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对现代体育养生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庄子的养生思想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庄子的养生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针对当时统治者过度养形、过度求名利等问题提出来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有能力讲究养生之道。但许多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大吃大喝。这种作法不但极大的浪费了资源,而且也极大的伤害了人们的身体,使人们疾病丛生,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庄子形神兼顾、内外兼养的养生理论,身虽参与世俗之事,但内心却抛弃了对功名利禄、富贵、长寿等强烈追求的“弃世”理念,以及生死自然的豁达生死观对于现代人理性保养身体、树立健康的身心观念、正确看待生死观念都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其次,庄子的养神思想有助于人们正确看待名利观念、树立大公无私的理念。名利既是人们生活所需,又是人们的追求对象。很少有人不受名利的影响,但为追求名利而伤身害命却是极不明智的作法。庄子的“为善无近名,为善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养神思想,提醒人们名利只是养生的工具,人们摆脱了狭隘的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善恶观念之后,不但不会被名利樊笼所困损伤性命,而且还会在复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过得自由自在。最后,庄子的养生思想对当代体育具有一定的启迪价值。庄子的养生思想中的“吹煦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的引导之术、形神兼顾的养生理念是中国传统养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现代体育意义的养生有一定的启迪价值。另外庄子的养生思想对于提高体育成绩也有一定的启迪价值。《庄子·达生》载:“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庄子认为用瓦器贱物做赌注,人们全无利害轻重之心,因此能正常乃至超常发挥投注技巧;用带钩做赌注,则心中已有顾惜之意,因而在投注已经影响正常发挥投注技巧;用黄金做赌注,则心中因物太过贵重,患得患失加倍,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投注水平。庄子的言论启示我们:一个人的成绩的好坏除了日常训练水平的高低之外,还有心理负担的轻重。如果心理负担过重必然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庄子养神思想中的“为善无近名,为善无近刑”,提醒人们做任何事情应减少个人利益的影响,以摆脱名利牢笼,对于减轻运动员心理负担,正常发挥训练水平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因此我们应大力挖掘庄子养生思想中的有益成份,以发挥其应有的借鉴价值,为提高当代人们的生活质量,保持身心健康,乃至为当代体育服务。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2]熊晓正.庄子养生思想浅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2,(1)
[3]旷文楠.庄子养生思想的非体育本质答熊晓正同志[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4,(1).
[4]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
[5]吴学琴.庄子养生思想辨析兼评道家支派的养生观[J].社会科学,1993,(1).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吕惠卿.庄子义集校[M].汤君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8]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4.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王厚琛,朱宝昌.庄子三篇疏解[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
[14]释德清.庄子内篇注[M].黄睹辉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5]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张杰)
收稿日期:2014-11-04
作者简介:孟娜(1982-),女,山东德州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史。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6)02-007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