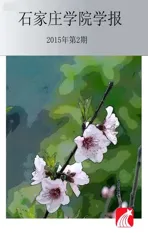“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华”
——《中国的历史》简评
2015-12-24高莹
高莹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华”
——《中国的历史》简评
高莹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共有10卷在2014年被翻译成中文,其作者为来自不同领域的日本知名学者。该套丛书提供了解读中国历史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华”的新角度,以动态视角解读一统时期“天下”的内涵和外延。与趋同性相比,日本学者更多地关注在“一统”下的不同质性。处于中华文化影响下的日本和朝鲜,虽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却呈现出仅停留于表面的政治制度相同性,与作为源头的古代中国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和而不同”是文化中华的重要特征。
和而不同;地理中国;文化中华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为日本讲谈社100周年献礼之作,是由日本学者写就的一流大众史学类历史读本。此套丛书中共有10卷中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作为基本按照断代史编排且时间结点为中华民国的著作,每卷由中国知名学者为之作序,正文内容之后,还附有该时段人物、事件等的注释,为读者展现了不一样的中国历史。该套丛书中译本洋洋洒洒几百万字,千余字的书评必然难以概述其全部,下面仅就贯穿其全套书中的古代中国和中华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进行阐述。
何谓“中国”?对于这个词语的使用,今人处于一种约定俗成的状态。但是在古代却有着多重含义,故而中外学者对古代“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葛兆光先生《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绪说[1]1-33一节,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在此试着在葛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向度、政治向度上,将古代“中国”这一研究实体根据其含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再次细分为“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华”,进而对其进行浅析。
“中国”与“中华”词义虽具有多重性,但一些约定俗成式的使用方式在无形中对两个词语的内涵和外延起到了规定的作用,在这种程度上还是可以对其定义进行归纳总结的。《辞海》中,“中国”一词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二、古时‘中国’含义不一:(1)或指京师为‘中国’;(2)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3)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始专指我国家全部领土,不做他用。三、古地名,即恒河中流一带的中印度。四、日本本州西南部地方名。”[2]1407而“中华”在该书中的解释为:“一、古代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在四夷之中,后世因称其地为中华。其初,但指黄河中下游而言,其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统辖,皆称中华,亦称中国。二、古时对华夏族、汉族的称谓。”[2]1407《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用两页的篇幅对“China中国”[3]160-164这一词条从名称、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与民族、地貌、气候、资源、历史经济、文教卫生进行解释。对中外较为权威的解释进行比较,《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本其China的解释是对《辞海》中第一、二种解释的具体化,同时也是对“中国”和“中华”二词的复合化、简单化处理。该解释对于1768-1771年成书的第一版继承下来多少不得而知,除此之外,由于尚未见到原版,故而只能暂时将这个词条解释看成是中西混合的产物。在中译本的全书中,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和“中华”的使用,其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用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日常生活中更是如此,例如“中国(的)制造”“中国(的)人”,前者强调产品生产的国家、地点,后者强调国籍,“中国”在这两个定中短语中,可以看做是对制造、人的范围和地域的强调,由此可知,“中国”往往含有具体可见或是有明确界限的意思,地域性与国家性、政权性是其标志性特征。与“中国”不同,“中华”之后多与“民族”“文化”等词组合,构成可表明中心语属性的短语。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在语境中更多地是指代有边界、界限、一定地域的具体的范围,直观性是其重要特征。而“中华”一词所修饰之物没有较为严格的边界与界定的地理空间标准,二者各有不同的指称对象,涵盖的范围也有所不同。
一、何谓“天下”
论及天下,首先想到的便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及“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类的俗语,两则俗语前者强调王权范围之广、权威性之强;后者强调天下局势的规律是有迹可循的。“天下”指称什么、统一后的“天下”又指代什么,此处提出或显过分咬文嚼字,但这的确是以往有所忽略的问题。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分裂时期,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若将“天下”这个问题放在分裂的时期,想必古今学者都会慎之又慎地分析其含义,多数人会从“天下”出现的具体文本语境出发,对“天下”的范围加以限定。与之相对,所谓统一时期的“天下”,有时却成为一团乱麻,这样一来纷乱时期的“天下”概念却相对清晰。
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王朝为夏王朝,后面依次为商王朝、周王朝。以往对于三者的普遍印象为,三者都是一统天下的王朝,但此处的“天下”与通常意义上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时的领域差距很大。这也反映了史前历史研究的一个现状,王朝“内部”的研究频率要高于“边缘”的研究。在翻阅中国的史前研究书籍时可以发现,在本应形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王朝”历史链条中,新石器时代与夏王朝间缺少了一个环节,换句话说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政治与后世王朝间的承继关系被忽略了,这固然与中国以往的断代史编写原则有关,使得朝代间联系与承继关系被人为地割裂,而这种割裂在史前的历史中造成了习惯性忽略。但日本学者宫本一夫与平势隆郎敏锐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夏王朝之间的承继关系,后者继而提出“文化地域”的概念。宫本教授以考古学家的眼光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用考古资料说话,成《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4]一书。行文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明并不能涵盖中国所有的古代区域文化。这个观点是极为引人深思的,按照传统,黄河流域的研究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域性文明,但是宫本认为自苏秉琦先生始,对于多元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区域多元性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这一点已经被出土的考古文物所证实。平势隆郎在继承宫本区域多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代的“天下”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地域二者间在部分上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传统观念中认为夏商周三代曾经都是统治天下的王朝,不符合事实,是后世的虚构。他认为,‘天下’包括若干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虽然每个文化地域的范围随着时代变化也多少有些扩大或缩小,但是基本的范围是固定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统治的疆土基本上也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地域而已。虽然也有通过陪都之类的方式将统治区域扩张到其他文化地域的情况,但是基本上一个王朝统治的是一个文化地域”[5]iii。在平势的观点中,夏商周的“天下”范围被缩小为单一的文化地域,即便王朝的统治范围曾经跨出一个文化地域,但王朝内文化类型的趋同性与王朝外部的趋异性仍然是重要特征。现存考古资料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地域多样化,不单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同时也在提醒后世学者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该文化地域上可能会有政权或是国家的存在,夏商周三朝若未能对这些政权或国家实现统治,那么“三代实现一统‘天下’”,这从地缘上看便是一个伪命题。
其他大一统时期的“天下”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是该政权对领土的控制,除去专门史的研究书籍,王朝的版图是如何逐渐扩大,进而达到王朝的顶峰状态,及在此状态下的帝国版图有多大,是普遍历史认知关注点①当然对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和鸦片战争后的清朝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通史类王朝国力衰落期的研究。。在研究王朝如何走到顶峰状态时,学者们都会不自觉地对时间节点投入关注,但是一旦研究对象已经处于一个顶峰状态,除非有震动政权的事件发生,否则王朝的发展就会被默认为停滞的状态直到其灭亡,王朝内部的渐变性被人为忽略。按照杉山正明的观点,以往认为的“大唐三百年天下”只是一个“瞬间大帝国”[6]13,而姚大力也用总章二年(669年)的唐代疆域图在侧面印证了杉山的这一说法。即便在同一个王朝中,“天下”的地理范围也呈现出动态变化,历史地图集上所标注的年代,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统一王朝的“天下”多变,而地理中国的范围也是多变的,不可否认,地理中国的出发点和划分依据多是以王朝为标准,它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圈”形成的地缘基础。统一时期统一王朝的“天下”略等同于地理中国的范围,但其动态发展的趋势也不容忽视。而分裂时期的地理中国,由于牵涉到正统等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各自为阵的状态,有着不同的以自身政权出发的“天下”和“地理中国”。
二、中华文化圈
中华文化圈脱胎于费正清所提及的“圈层式”[7]①“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参见[美]费正清《一种初步的构想》,收于[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外交结构,与地理中国具有相对明确的边界相比,中华文化圈却显得十分飘渺,虽然略显飘渺,但也不能否认中华文化对整个古代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影响作用。而面对中华文化圈的时候,学者更多地注意到文化圈中的同,其异的所在被不自觉地忽略,但是该套丛书中的学者却着重强调了这种不同。
宫本一夫曾提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中国大陆的北方与南方这两条区域社会的文化轴。这两条文化轴各自的特点是,北方时常与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保有交流,而南方的文化轴则呈现出相当保守的状态及缓慢的物质变化。……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4]390-391这两条文化轴因为地域等客观性因素,始终贯穿于中国史。商周文化由于有较多的文字性记载,使得研究大趋势逐渐形成了以 “中原及汉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当然这是由史料存在的客观条件所限,但是不能否认其他没有文字的青铜文化的存在。
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是最早的统一天下王朝,乍看之下此或与上章所写的“以往对于三者(夏商周)的普遍印象为,三者都是一统天下的王朝”有所冲突,但是细细想来,这两句话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天下”的范围和管理方式。夏商周三个王朝,它们的疆域是在一个中心性地带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周朝疆域为例,除了王幾的土地外,还有由功臣等建立的藩屏国家,用以拱卫周天子,秦朝在东西南北方向比周朝都有了地域上的突破,可以说秦朝的统治是超出了一个文化地域的。而从管理方式上,还是以周朝为例,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的出现,使得分封制在实质上已经趋于瓦解,周天子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在统一于周天子的名义下,各个国家之间处于各自为阵的状态。而到了秦朝,郡县制度的出现及各种统一措施的施行,此时的“天下”可能在法律条文和行政上实现了统一。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作为秦朝统一的标志性措施被重复提及,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想也没能力去否定这条措施带给后世的积极影响,但是又想在此咬文嚼字一番,这次的关注点放在“书同文”之上。“书同文”顾名思义是书写的文字的形式,即对汉字“音、义、形”中的形,用政府力量进行了强制性规定。世人往往称道始皇帝在文字上的贡献,但却忽略了在秦统一之前,各个国家,尤其是战国七雄这七个大国内部之间文字的统一,而平势隆郎的文书行政制度恰能补充这个空缺之处。按照平势之说,战国时期的领土国家,中央政权下,法律制度作为支撑,文书行政制度作为有效手段,进而使得官吏统治成为可能。[5]iii不过,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文书行政制度包括秦王朝的“书同文”措施与平民的相关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8]59②日本学者鹤间和幸曾提出“这种改革(度量衡、车轨、文字,笔者注)与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因为百姓并非度量衡、车轨、文字的使用者”的观点。参见[日]鹤间和幸著,马彪译《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基于此,我们可以对秦朝的“书同文”进一步加以分析。众所周知,汉语可以将其细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类,“书同文”很明显的是在书面语文字上有所规定,民会说而不会写,即便是在今天的某些国家或地区也不足为奇,以今观古,识字断句者在秦代所占得比例并不会太高,而就目前所得到的史料看,至少秦代官方并没有对口语的发音有统一的规定,因此文字上实现统一这种说法稍显不妥,严格说来,秦朝只是在书面语上实现了统一而已。尽管古代有雅言和突破了地域的通语作为基础,在今天的口语使用上,仍然形成了全国通行的普通话与七大方言区并存的局面。
之所以花费大量的篇幅去说明“书同文”,因为要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央政权下可实现的“书同文”,对于文字而言是不完全的,即文字的读音是很难划一的,换句话说,文字自产生伊始,便就有了在音上的不统一性,也就是说汉字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自身也有不同一的一面。商周文化与北方青铜器文化,两条轴线并存发展,交织于中国史中的客观现实,其背后也是所谓的夷狄文化交织存在,除较为有特征的划分标准外,很难将二者严格地区分开来,在这一层面上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华文化其实是现代意义上各个民族和文化地域的混合型构成。从明代官修《洪武正韵》中所记“天地生人,即有声音。五方殊习,人人不同,鲜有能一之者。如吴楚伤于轻浮,燕蓟失于重浊,秦陇去声为入,梁益平声似去,江东、河北取韵尤远。欲知何者为正音,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沈约以区区吴音欲一天下之音,难矣。今并正之”[9]2-3可知,语音未统一的问题从秦朝一直延续到了明代,这种四方不能统一的现状,却构成了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一面。由于汉语和儒家文化占有绝对性优势,其构成了中华文化圈的重要部分,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是这种优势汉文化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不同质化。
提及与中国古代时间大致相同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国”或是政权,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和西嶋定生的“东亚册封体制”二者首当其冲。本文并不打算对二者进行论述,只是要说明在可以使用汉字的文化圈下,日本和朝鲜半岛“国”或政权的变异。当然以二者作为研究对象,也不是偶然为之的,这与二者所使用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日本语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两部分,从明治时期政府编定五十音图中可以看出相当多的中文汉字的遗留痕迹,而就发音上五十音图中的あ行与汉语拼音中的元音较为接近。朝鲜半岛上的韩国,现在使用的是一种叫做谚文的文字。“Hankul谚文 ……书写朝鲜语的文字体系,在朝鲜称为朝鲜文字,包括14个辅音、10个元音共24个字母符号。辅音字母由曲线和折角短线构成。元音字母由直线或横线及主线侧的短线构成。据传统说法,谚文字母的发展归功于李朝第4代国王世宗。15世纪40年代中期,世宗颁诏将谚文作为朝鲜语的官方文字系统。因受儒教及汉文化影响,谚文直到1945年日本统治消除前未被学者和朝鲜上层人士采用。”[10]461由这条解释可知,直到通常认可的李朝世宗大王颁行谚文前,朝鲜通用的语言是汉语,现存的《李朝实录》也足以证明汉字在整个王朝系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也在日本和朝鲜传播开来,二者被纳入到了中华文化圈之内,但是纳入不等于隶属和征服,这是在研究中华文化圈时需要注意的,与此同时也需注意到中华文化因时因地在不同地区发生的变异。
豪族、宦官、外戚三股势力构成了东汉的政治舞台,但是在该朝代后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外戚在政权上的活跃程度大大降低,唐明两朝的宦官权利之大达到了让人咂舌的程度。与之相对的日本和朝鲜的朝堂又是怎样呢?金文京对此进行了着重关注,选取了典型性历史事件加以说明,见表1。

表1 明清时期与德川幕府及李朝代表性政治事件对比表
明代宦官的代表有刘瑾、魏忠贤、汪直、冯保等,他们虽然不是都祸乱朝堂,但是能对朝政有益者毕竟少之又少。纵观有明一朝,除万贵妃和郑贵妃外,能干预朝政的后宫也不多,外戚并没有形成很强的势力,这也与明代常选民间女子为后妃有关。而慈禧的掌权却不能算是外戚的产物,奕是她婆家之人,而不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太监安德海、李莲英、张祥斋(小德张)恩宠一时,但与明代相比,宦官的势力大不如前。有鉴于清代宦官肆意妄为程度远低于明朝,上田信为清朝冠之以“自制”[11]17①“宦官在宫外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原因应该包括皇帝出于占少数的满族统治占多数的汉族的必要性而对人民任意行为进行的自制。或许从维持一种高效的行政秩序,即以数千名官僚统治全国数亿人口的必要性层面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参见[日]上田信著,高莹莹译《海与帝国:明清时代》,《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0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之名。
与明清大致同时代的日本幕府的主导力量则是外戚和豪族。先看德川幕府建立时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者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得不借助简图表示,见图1。
织田信长于本能寺之变中丧生,继之而起的是秀吉,而家康曾为丰臣家臣,以浅井江为纽带,德川家与丰臣家和天皇结成姻亲,外戚势力越来越大,此时也是德川家族势力的上升期。大政奉还事件中,萨摩藩岛津家出力不少,而岛津家族是幕府13代将军家定正室天璋院的母家。而李朝也与幕府相似,甲子之祸起于燕山君对其母死因的追查,后宫、皇亲与世族为此事丧命者不在少数。李朝后期,高宗继位之前,安东金氏与丰壤赵氏这两股外戚势力相互较量。其继位之后,作为高宗生父的大院君,为了防止外戚夺势重演,选择了夫人的堂妹失怙的闵氏,但是壬午之乱等仍成了大院君与王妃闵氏家族的争权夺势的重大事件。日本与李朝同样延续使用或是曾经使用过汉字,同处于中华文化圈的政权或是“国家”,在政治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权力表现形式,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也有多有少。上述典型的事例,也印证了金文京提到的“(制度上,笔者注)日中朝三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2]34。
三、结语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的作者展示了一个“和而不同”的中国历史,在古代,“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华”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天下”的范围也不是印象中的范围,夏商周统治下的文化地域是对当时当事“天下”的较为准确的解释。中华文化圈的出现,在客观上强调了其文化的同质性,而忽略了其不同点,对于明清、德川幕府和李朝典型事例的对比,正是延续了打破惯常性思维,求同存异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地理中国”与“文化中华”。

图1 织田家族、德川家族、丰臣家族关系图②浅井江先嫁给丰臣秀胜生女,后又嫁于德川秀忠。
[1]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不列颠百科全书 (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4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4][日]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M]//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日]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M]//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M]//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8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M]//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宋濂.洪武正韵·凡例[Z].四库全书本.
[1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7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11][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M]//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9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日]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M]//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程铁标)
“Geographic China”and“Cultural China”:A Review of A History of China
GAO Ying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en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China 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2014.Their authors are famous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Japan. “Geographic China”and “Cultural China”,which have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al sense,are interpret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With the help of dynamic perspective,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world”are expounded.Compared with the same aspects,Japa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Japan and Korea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al circles.Although they absorb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ir political system which is inherited from China only stays on the surface.This is not the same as the source of ancient China.The thinking of“harmony in diversity”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harmony in diversity;geographic China;cultural China
K207
A
1673-1972(2015)02-0028-06
2015-01-16
高莹(1988-),女,山东淄博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