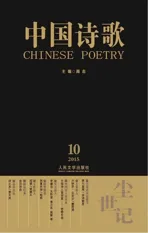诗学观点
2015-11-17李羚瑞
□李羚瑞/辑
诗学观点
□李羚瑞/辑
●杨炼认为读杨政的诗时时常会想起一个词组:“诗歌的原则”。诗歌的原则就是形式,是基于汉字音乐感建立起来的汉语诗歌形式。杨政早期诗歌中已见轻盈把玩语言和操控形式之端倪。形式的限定,不仅没有令诗歌拘泥造作,反而让诗句在流淌中仿佛自动发育出一套规则。诗歌的原则在杨政的诗作中获得了最佳表现:形式,内在于诗作。它使诗凸显出自身的美学性质,而非伤害或减弱。汉字的美学基因,经由表现当代人生经验,激发生成为当代诗学观念。因此,诗歌的原则——形式自觉之原则,绝非简单回顾古典,而是汉语在前瞻全球意义上创造的未来。
(《诗歌的原则——杨政诗歌的形式意识及其他》,《作品》,2015年5月上半月刊)
●周伦佑认为语言不是无所不能的,它有它表达的界限。这样说并不是要取消诗人想象的特权,也不是要取消诗歌的超越性意象,而是说诗歌恰好是在维特根斯坦所划定的两道边界之间并试图实现对两种边界的僭越。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总是力图实现对“世界的语义界限”的打破,同时实现对“语言的表达界限”的打破。这种“打破”或“越界”,在诗人的写作中,通常表现为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正是这种“打破”或“越界”产生了张力,而正是张力使诗成为诗。这提示了诗歌写作的难度,也提示了诗歌写作区别于其他文学体式的主要特征。正是这种“难度”和“特征”,使诗歌成为文学的极致、艺术的最高形式。
(《“诗性张力”或张力的诗意——在北京大学〈现代诗张力论〉讨论会上的发言》,《钟山》,2015年第3期)
●余荣虎认为张志民诗歌语言、句式的口语化、生活化所达到的高度是难以企及的。张志民吸取乡土民间的词汇、俗语、警句,在表达方式上大量运用乡间的文法、句式,真正做到了面向农民。他的两行体叙事诗是为农民而写的,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满足了农民的需要。但张志民又不满足于此,他本身就走在新诗大众化的道路上,又借鉴了古典诗歌大众化语体化的妙处,这就使他的诗歌有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独特的韵味。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独特韵味的艺术形式为传播农民“站起来”的现实和理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农民“站起来”而歌——论张志民的乡土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3期)
●孙晓娅认为《有远方的人》体现出周庆荣一贯秉持的语言风格,即用最简洁凝练平实的词语穿透物表与心识,抵及语言内部,借由词与词的撞击表达创造性写作的意味。读者凭直观就可以感受到这部散文诗集行文间词语铿然敲击的力度,这与周庆荣惯于使用名词动词化,或借用名词的动词意蕴以及词与词的陌生化的搭配不无关联。诗人对语言的处理方式,拓展并深化了词语的意义,它们嵌入生命与时间的流动中,以此抵制那些苍白、漂浮掠现的语言,恰如诗人自己所言“深刻的语言嵌在皱纹里”。
(《当下与远方——评周庆荣散文诗集〈有远方的人〉》,《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杨林认为,从潘桂林的《樱桃》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歌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思路:用形象说话,从形象里抽象出思想,将意象与形象融合,在形象里衍生诗性意味。形象思维是西方诗学“形象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在中国传统古典诗歌中也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精神源头,值得我们吸收和运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形象思维创作的片面化导致思维内在化、系统化和思想观念固化。而诗歌对形象的过度塑造,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形式化的景物。事件描写与诗性拓展的“二元对立”,以及诗歌语言的繁复、散文化倾向,影响了诗歌简洁、凝练的特性,弱化了诗人个体感受、情感、思想的反映,以及诗意的扩张。
(《形具神生——读潘桂林〈樱桃〉》,《湖南文学》,2015年6月号)
●李明
认为城乡一体化时代的乡土小说与打工诗歌固然揭露了社会发展背后的阴暗面,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潮流有泛滥的倾向。底层群体为生活苦于奔波,生活无保障,文学虽然表现出了这一群体的苦难,但由于自身思想体系架构的贫弱,使得这种社会批判显得单调而乏味,千篇一律的感慨有无病呻吟之嫌。在某种程度上,新世纪诗歌过于直白的语言使诗歌失去了诗性的特质,真实性与生活化的强调使诗歌趋向小说叙事化的特点,形式上的“祛诗性”以及驾驭文字上不如小说自由,也使诗歌在表现内容及思想性上越发苍白。
(《喧嚣背后的乡愁——以新世纪乡土小说及诗歌为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月号)
●鲁若迪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应该值得倡导和尊重。作为一个诗人,只有用诗歌这种方式和这个“武器”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一个静态的东西是容易的,维护一个动态的东西则很难。文化作为一个多种形态的东西,去维护它更是难上加难。诗人的“维护”无外乎就是在诗里多些本民族的元素,让更多的人通过诗歌知道诗人的民族,知道其民族的文化。因为别人的“知道”,这种文化可能存活得宽广和久远。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决定着诗歌的多样性。所以为了诗歌的多样性,我们应该通过认识的提高,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多样文化和语言进行合理保护,使之得到传承和利用。
(霍俊明:《作为一种照彻的诗歌——对话鲁若迪基》,《中国作家》,2015年第5期)
●杨玉梅认为诗意和美感产生来自于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想象,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技巧处理。诗歌如果忽略了思想内容而只是一味追求形式,矫揉造作或是精雕细刻,感情没有依托,言之无物,只会使得诗歌变得空洞和虚无。在《汶川羌》里,羊子并不是以小说和史诗叙述故事,以讲述英雄人物传奇的方式追述民族历史,也不借助神话、传说把叙述语境推向古老的过去,而是立足于现实,以现代诗的表达方式通过现实存在的充满文化象征意味的文学意象展开叙述与抒怀,营造一个入情入理的诗意境界。
(《民族诗人的使命与超越——对长诗〈汶川羌〉审美意蕴的阐释》,《当代文坛》,2015年第3期)
●张岩松认为有些语言千百年来被人们不认为是语言,我们在使用这些语言时会认为这些是无能的话,没有意思。语言穿着意思的外套招摇过市,而非意义的语言,我们视同是服装的展览会。诗歌在使用这些垃圾语言时,我们很容易知道此时的诗和这样的语言发生着某种交媾的关系,但诗是诗,这样的语言还是语言,诗意经常跑在这样的语言外面,丢弃它原来的孤零零的样子。语言此刻并不自卑,一些遗忘正浮现在语言本身上面,诗歌也不能伪装好它。
(《关于诗学及艺术的笔记(节选)》,《扬子江》,2015年第3期)
●罗振亚认为作为知识渊博的文化人,临轩很少去经营吓唬人的绝对、抽象之“在”,而多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与情趣中,驰骋诗思,构建自己的形象美学。他的诗始终“走心”,主体的情绪喧哗和感觉舞蹈,很容易将读者引向他设置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可喜的是,他所具备的平素推崇的超拔的直觉力,保证其在对事物观察的过程中,能够穿越客观无为的描摹层面,洞悉、触摸到对象的本质内核,玉成一种智性之思。
(《诗与思的遇合》,《特区文学》,2015年第3期)
●栾纪曾认为,耿林莽之所以在散文诗创作中成绩斐然,正是因为他牢牢抓住了诗学理论的根本和灵魂,因而在各种时髦术语竞相争夺话空间的风潮中沉稳冷静,在实践中更是安如泰山、探索向前。他那些语言的精灵像心灵的溪水,如琴如瑟,清澈透明,不知疲倦地在我们面前跳跃流动,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对读者对生活都是一种美的洗涤,并在洗涤中产生经久不息的身心共鸣。他对诗学和诗歌创作过程的敬畏、认知与不懈的探索精神及对诗性、诗境的不懈追求,同多年来泛滥成灾的语言随意化、自来水化、空洞抽象化、怪异化及后来外文语式化等诗歌生态形成鲜明对照。
(《散文诗是他生命与心灵的样式》,《时代文学》,2015年5月上半月刊)
●梁雪波认为书写的物质性是现代主义诗人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解放了意义对语言的束缚,带来能指的狂欢,但同时又悬置和割裂了写作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堕入一种不免空洞的能指游戏。新世纪以来,重建诗歌与现实的关联,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向度。在卓有成效的写作者那里,“及物”和“不及物”无法截然分割,而是在更高的维度上展开和交汇。沙克《单个的水》第二辑中的“物与词性”,显然就是基于与以上诗学有关的种种考虑。这一组诗有着很好的构思,视角新颖,在表现方式上比较隐微。现代诗的修辞讲究陌生化效果,为此常常需要调动通感、畸联、变形、戏剧化等多种技术手段来达到让人耳目一新的词语拼贴。
(《隐微语义中的“归去来兮”——读沙克诗集〈单个的水〉》,《诗林》,2015年第3期)
●霍俊明认为,“轻型”的诗与“精神体量庞大”的诗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很多专业读者和评论者那里二者很容易被指认为两个截然的阵营。但是邱华栋则刚好通过诗歌完成了这一诗学疑问。在邱华栋这里,他的诗歌几十年来不涉及庞大和宏旨的诗歌主题,也就是在惯常意义上看来是属于“轻体量”的写作——轻小、细微、日常。但是这些诗歌却在多个层次上打通和抵达了“精神体量”的庞大。这实际上也并不是简单的“以小搏大”,而是通过一个个细小的针尖一样的点阵完成了共时体一般的震动与冲击。
(《“吱呀”声中拨动指针——重读邱华栋》,《诗歌月刊》,2015年第6期)
●阿尔芒认为,“成子湖诗歌部落”作品有着显性的特质:简约、随性、朴素而纯粹,对于生命和生活中所有美好的细节,有着超乎寻常的感动,有着与生俱来的热情和眷恋。博大的胸襟是部落作品的情愫之一。诗作带给世界的是无与伦比的美妙之感,另一种苍茫的存在,另一种无垠的意境。悲悯的情结是部落作品的情愫之二。诗作有强烈的感情指向,有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悲悯。炙热的乡愁是部落作品的情愫之三。明朗晓畅,朴素鲜活,形象生动,平实中透出浓厚的生活气息。渴望的期盼是部落作品的情愫之四。飘逸的梦幻是部落作品的情愫之五。
(《蒹葭、渔歌及粼粼诗情——成子湖诗歌部落简介》,《诗潮》,2015年第5期)
●方婷认为李森一直以来都主张带着艺术问题去实现创造,在创作中有效探索语言的奥义。他自觉于纯化自己的诗歌语言,这种语言不同于西方诗歌输出中形成的翻译语言,不同于工具时代的现代汉语,它既是自我心灵的姿态,同时又靠近他理想中的纯正汉语。向纯正汉语靠近,并不意味着对古典汉语元素进行拼贴。尽管李森的诗歌在可见的形式上也有意识地借鉴了古典汉语和古典诗歌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纯正的汉语写作还应该回到汉语产生的情感和精神源头,回到汉语的基本思维和诗性构成中,并尝试着为正在生长中的汉语提供一种向度的可能。
(《风格的洗礼》,《名作欣赏》,2015年第6期)
●边雨认为,作为诗歌、诗论并驾齐驱的写作者卢辉,他的诗歌写作成就了生命的底色、世相的图景以及精神维度。卢辉的诗歌打破了原有事物映入我们眼帘的物理的平面的第一感觉,诗人不仅以清丽奇峻的意象富有悬念地把它简洁地打开,而且为我们拓展了另一层面的空间。它是陌生的灵异的,是我们擦肩而过的未曾结识的人,一次改错的机遇,一种心灵的撞击。短促的句式拉开读者的空间,没有了语言的遮蔽,我们可以赏心悦目地看到更远一些,这也是诗人的玄机。在我们触摸到重建之后的愉悦的同时,发现一首诗的产生,更多是来自词语的刺激。
(《一个地缘诗歌美学部落的“变”与“不变”》,《滇池》,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