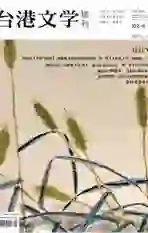侯导、西部刺客、聂隐娘
2015-09-17张全琛
张全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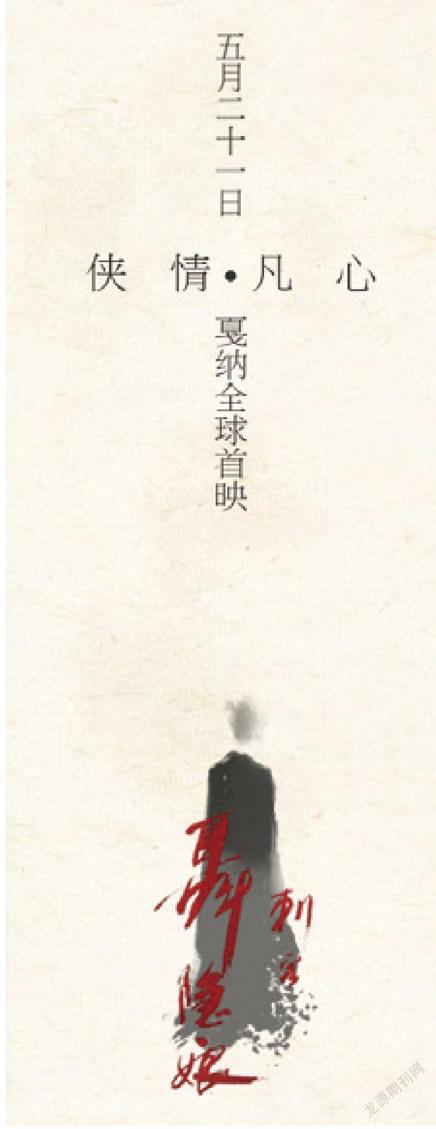

年初在柏林影展,看到Wild Bunch(注:《刺客聂隐娘》的海外销售公司)的promo《刺客聂隐娘》片段时,其实内心是略感不安的,毕竟侯导拍了好久,久到令人无法不期待,而海外自制那张舒淇出拳的海报,以及片尾最后大大的金字,实在让人嗅不出半点侯导的气质(所幸那是片商自行设计),一方面又期待侯导能入围坎城影展,所以心情相当复杂。
直到坎城影展公布竞赛片那天,最初入围的十七部竞赛片其实非常诡异,竟没有近年最夯的中南美洲电影入选,法国片却一口气入围了多部,让人非常好奇今年选片人的标准为何。所幸选片人在记者会上用“大师归来”形容侯导,也让人发现,这次竞赛片的导演当中,侯导是资历最深的重量级导演。
而影展从法国女导演的开幕片《昂首》()开始,仿佛宣布了:这是我们法国的坎城影展。多部竞赛片并非不佳,但只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缺乏灵光,就是不够完整,许多导演更没有突破自己。诸多评论也显得乏力。第一周过去,保罗·索伦提诺语焉不详的《青春》()以及南尼·莫瑞提温和感性的《我的母亲》(),或者是雷声大雨点小,希腊导演尤格·蓝西莫新作《龙虾》()都不太让人心服口服。甚至还出现烂到破表,被Screen杂志评为0.6分(满分4分)——十二年来新低的葛斯·范·桑新作。反而是匈牙利导演拉兹洛·尼梅斯的处女作《索尔之子》()获得满堂彩,该片用声音制造出悬疑,用看不到的猜测角度造成心理想象,被誉为有夺奖可能;陶德·海恩斯的《卡萝》(Carol)以一对女同志的互看角度,观看时代与性别上的生命桎梏,得大奖的呼声最高,双女主角获奖呼声也高。但,都不太像是会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因为这些电影都少了大师的胸襟,独特有余,但论气度或恢宏的内在观点,都不够大器,虽然电影不一定要大器,能瞥见大师手笔是影迷的一种福气。
随着时间逼近,侯导的电影被放到后面才首映,也让大家更期待,金棕榈会不会是《刺客聂隐娘》,而先一步登场的是,“台湾之夜”。
今年的台湾之夜相当有趣,仿佛变成侯导的影迷大会,是枝裕和、河濑直美,贾樟柯等受侯导影响又同时入选坎城的名导们,纷纷现身在台湾之夜。当然也有徐枫跟石隽因为《侠女》而来。当侯导风尘仆仆还没有调好时差(当天抵达),登上台前跟大家问好时,站在我旁边的是枝裕和导演像个小学生一样,踮脚尖引颈看着他心中的偶像,让我忍俊不禁。同样入围竞赛的《山河故人》导演贾樟柯跟妻子赵涛也一同出席祝福侯导,三位竞赛片导演合照时,笑得很开心。金马师徒学院的赵德胤与陈哲艺也一同出席,看着许多深受侯导影响的知名导演们,对于侯导的巨大崇敬,在一旁的我们,仿佛也该更崇敬一点才是。因为台湾之夜很像侯导之夜。
坎城最大的特色就是会有一群小朋友穿着笔挺的西装,手上拿着“求片名XXX的票,感谢”的纸条,乞求人们会施舍电影票一般的奇景,几乎所有竞赛片都会有,而大家也见怪不怪,《刺客聂隐娘》首映日也是。
首映之前,媒体场抢先看的反应跟法国当地影评(包含王派彰翻译的几篇文章),皆惊呼终于出现了一部有大师气度的电影,也是今年坎城最美丽的电影,超越了先前一致被看好、同样评语也几乎完美的《卡萝》。看着这些评语,倒是不禁想着,侯导让法国人如此惊喜地看着古老的唐朝文化与电影艺术,这是何等神奇的魅力,而他们的理解却是比我们更加细微。我们台湾观众对于评鉴艺术的素养,跟对于电影的耐性和追究,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特别喜欢电影最开始的几个镜头,美得出奇,当代电影罕见之美,既像布列松的黑白电影一般,充满着一种森林里的神秘气息,又具有古典电影的气味,这也让人一开始就陷入了故事气氛当中。接着由黑白变为彩色,银幕变宽,也让视野变得更开阔。虽然有观众因为文化的隔阂而离席,但留下来的观众都相当地捧场,掌声如雷。对我而言,这是一部富有西部片精神又兼具黑泽明神采的杰作,侯导的电影很少让人感受到这两点,但全都在《刺客聂隐娘》里看到了。这也是六十八届坎城影展上,我心中的金棕榈电影。从黑泽明的《蜘蛛巢城》到《乱》,宫殿内暗涌的人心角力、感情斗争,宫殿外的打斗跟拜别。隐娘生长时代背景下的牵扯与影响,这种人与时代的关系,更妙似是约翰·福特的电影,那种土地/时局跟人的情感争夺关系,上一代的恩怨情仇遗害到这代人,最后仅能单靠一人去解决。在约翰·福特的电影中通常是约翰·韦恩,而侯导的聂隐娘是舒淇。
不得不惊讶的是,连我们都迷失在侯导的电影对白中,因为讲的是文言文,所以许多对白听不懂,只能跟海外观众一样追逐英文字幕,然而比较好奇的是,外国人懂得“和亲”、“纸人符咒”这些东方概念吗?侯导先是让大家在红色的帘帐后,不断地静静观看着王室宫廷内的谈话与行动,少量的对白,著名的长镜头,让观众静静地凝视出其用心,我们是以聂隐娘的角度去看整个故事,而侯导的镜头是带着一种安全距离的。
西部片的主角常是孤独枪手,个性多半沉默寡言,但杀人迅速确实,毫不手软,果断恩决,有没有觉得这很像聂隐娘?西部片也常出现主角原本要解救守护他人,最后经过一连串的杀戮解救到他人之后,这趟杀戮之旅的意义竟救赎了自己(《原野奇侠》到《搜索者》)。让自己跟孤独同行而又无羁绊。复仇仅成为形而上的哲学。聂隐娘一方面是要刺杀表哥田季安,但最后又放过他,有一身好武功,最后却无法杀人。可为之但不为之,电影的禅意就是在此浮现。全片像是去掉西部片的英雄主义与善恶对立,高手隐姓埋名藏入民间一般。当侯导的电影不再悲情地讲述真实历史,《刺客聂隐娘》这个虚构的唐代传奇小说反而意味更深远,琢磨架构出那些隐藏于外表下的内在情怀。
仇恨消失了吗?那些过往的伤痛隐逝了吗?透过树影炊烟,烛光窗影,高原与林间,贯穿于全剧的精神,竟是某种释然的感情。于是故事不只是唐代,更尝试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脉络下、时代下的悲情男女,如何成全与如何自处,静静观察出一种百态滋味。
“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之后,女性角色在侯导的电影中渐渐地成为故事的主旋律。侯导对于女性的视角,越见锐利。《刺客聂隐娘》更是,即便女主角台词不多,但在舒淇的面无表情中,也能看出某种决绝的心意。对于自己身世及感情的隐忍跟体谅,由刺杀变成保护,或是对于师徒拜别的决心。电影以一种距离,让这种情感相对地淡然处之。于是武艺剑气形同感情,都藏在看不到的体内。
这样深蛰又隐藏的故事讯息下,包含着许多侯导旧有的印记,等待的女性跟朝代更迭的悲剧,少量的对白,沉默的主角们,这应该是侯导理想中的人物。从《悲情城市》中的梁朝伟到不太言语的隐娘,甚至是日本演员妻夫木聪在电影里也只有两三句台词;但不一样的是,没有人有看过这种大量凝视镜头的古装武侠片。杀人仅在一瞬,而放过自己的执念则是一段历程。
“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汝剑术已成,唯不能斩绝人伦之亲。”道姑的这句话,仿佛也替聂隐娘理出了她的人味,她无法因为剑道而成为无情之人,她还是保有为人为情的坚持。道姑在镜头中显得很遥远而且冷静,而聂隐娘也是离意甚坚。鲜少有台湾电影洋溢出如此博大的神秘魅力,那是隐藏在山林峭壁间跟皇廷之中的情感,所以一草一木,一烛一灭,遥远但又亲近,皆具意涵,也都是电影气质的一部分,因为内敛所以有深度,因为隐藏不直言,才能在不经意中传达出写实感,满溢出体谅的深度。
最后的几个镜头更是神来一笔,充满童趣,导演将镜头摆向了小鸡,乡间那种纯真的人情就这样被捕捉出来。守信诺要护送磨镜少年的隐娘从远方回来,少年迎接着他,接着一行人就缓缓地走离了镜头,留下一片景色。
虽然《刺客聂隐娘》呼声很高,但最后柯恩兄弟与评审团仍把金棕榈给了一部呼声与评价都普通的法国片《迪潘》(),它可能是贾克·欧迪亚近年来比较平凡的作品,甚至有一个反高潮的结局。对我而言,《刺客聂隐娘》是一部新世纪的武侠电影,也是侯导再造巅峰之文艺杰作。这远比重复自己的风格及元素,却毫无突破来得有意义。金棕榈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坎城影展每年都会结束,而只有那些具有深意的电影会被留下来。多少的得奖作品最终被浪涛淹没,影迷连个故事都记不得,但我相信《刺客聂隐娘》是会被深刻地记住,因为它有超越奖项意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