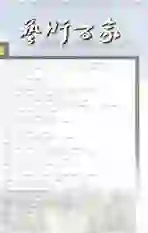舞蹈短论四题
2015-07-07于平
于平
摘要:舞剧是一种舞蹈文化。我们要在当下泛漫化的舞蹈语境中重建舞蹈的文化理想,一是仍要下大力气传承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舞蹈文化,二是要在人民群众的当代社会实践中进行舞蹈文化创造,三是要拓宽传播渠道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舞蹈文化需求,四是要努力培养人民群众成为舞蹈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样,我们的舞蹈就能在极大地发挥工具性能的同时,极大地提升文化品质并实现文化理想。我们要关注舞蹈的生命情调与人文精神。我们同时还要讨伐“舞八股”与优化舞业生态。其中包括爱之深、虑之远讨伐“舞八股”,呼唤“探索规律、追求独创”,创作繁荣中忧思“大晚会综合症”,以及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关键词:舞剧创作;舞蹈文化;文化理想;传承;创造;文化品质;生命情调;人文精神;舞蹈生态
中图分类号:J70文献标识码:A
一、舞剧是一种舞蹈文化
一份很文化的报纸,采访了一些有文化的舞人和非舞人,讨论了一个“乏文化”的问题——舞剧该不该有字幕?这个问题不言自明的前提是,舞剧是不容易看懂的;“该不该有字幕”的设问,那意思是“舞剧还想不想让人看懂”?
包括舞剧在内的艺术产品,是人(被称为各类艺术家的人)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产物。艺术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大概没有谁诚心要让人看不懂。“让人看懂”其实也是心态健康的艺术家的愿景,因为在这之后才谈得上让受众被那些艺术所感染、所感动、所感化——而这也正是心态积极的艺术家的热望。
但是对一个艺术产品的“懂”与“不懂”,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关涉“阐释学”的“理解的命运”的问题。懂,意味着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建立了某种有机有效的联系;而不懂,则说明认知对象对于认知主体的“无意义”,在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出现了某种“短路”。有时候,认知主体理解的“无意义”,可能并不等于认知对象的“无意义”,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对象的意义(至少有一部分)不在主体的解码设定之中。
语言文字是人类居于首位的交流工具。事实上,它也是我们基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工具。作为交流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文字,当然就成了我们“懂”与“不懂”的基本解码设定。问题在于,不同的艺术产品有不同的语义符码,而绝大部分艺术产品的语义符码都不是能用语言文字来解析的。舞剧正属于这类艺术产品。
对于包括舞剧在内的舞台演剧产品,我倾向于认同“非音乐戏剧”和“音乐戏剧”的二分法。“非音乐戏剧”大概只有话剧和哑剧,它的显著特质是语义符码贴近日常生活形态,容易被受众理解。话剧自不在言;哑剧虽非语言文字,但往往惟妙惟肖地再现生活动态。与之有别,“音乐戏剧”的语义符码总是偏离日常生活形态的——无论是戏曲、歌剧、音乐剧还是舞剧,都是如此。相对于戏曲、歌剧、音乐剧还有可以识别的念白、韵白、rap以及唱段,舞剧的语义符码更被认为是“高度偏离日常生活形态”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舞剧该不该有字幕”才成了一个问题。“字幕”在舞台演绎的观赏活动中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无论是看西方舶来的歌剧还是看本国土生的戏曲,没有“字幕”大致是不易看懂(听懂)的。戏曲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声腔体系,在其表意过程中似乎并不在意“意义的表达”,它将“表达的方式”(韵味)视为自身的命脉。歌剧的“宣叙”和“咏叹”也是如此。难怪为了看懂并且仅仅为了看懂的受众,不明白歌剧为什么不能“有话好好说”。
戏曲和歌剧在声腔或唱段出现时配以“字幕”,是为辅助受众在欣赏“表达的方式”时理解“意义的表达”。而事实上,这种辅助理解的“字幕”在以语言为表意手段的电影中已普遍存在,它还更普遍地存在于电视诸多栏目的生活节目中。但即便如此,其语义符码“高度偏离日常生活形态”的舞剧,似乎也难以说要用“字幕”。如果舞剧的疑义都能用文字来说明,我们看到的肯定是一部有问题的舞剧。你能想象交响乐演奏配字幕吗?
舞剧应该让人看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多的人希望舞剧是一种能让人看懂的戏剧,这就需要掰扯掰扯。曾有一位话剧导演大腕对我说,她执导过话剧、歌剧、音乐剧、戏曲(包括京剧和诸多地方戏),想听我讲讲舞剧以便以后也导它一把。我注意到,虽然舞剧也请“刀笔吏”编剧,也有过按编剧的潜台词用哑剧的方式先表意再编舞(比如《小刀会》),还有过让一台话剧导演(当然也是大腕)说一句潜台词然后再由舞蹈编导行动(比如《星海·黄河》)……但绝大部分的舞剧编导都是在小型舞蹈创作中卓有成就者而非其他什么剧种的大腕。年长的舒巧、门文元是如此,中年的张继钢、苏时进是如此,年青的佟睿睿、王舸还是如此。
视“舞剧”为一种戏剧,其实本无可非议的。但鉴于我们当下对于“戏剧”的理解是基于“话剧”的理解,这可能也需要掰扯掰扯。由于汉语言文字确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惯性,在“舞剧”组词的偏正结构中,“剧”成为中心词而“舞”成为其修饰、限定词。当“剧”的内涵已被“话剧”的理解所浸淫,“舞剧”就难免被要求当作“舞蹈的话剧”来看待。也只是在“舞蹈的话剧”的理解设定中,“舞剧该不该有字幕”才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我之所以说“绝大部分舞剧编导都是在小型舞蹈创作中卓有成就者”,意在强调与其视“舞剧”为一种戏剧,莫如视其为一种戏剧冲突和情感张力的舞蹈——“舞剧”的真正涵义,其实应当是以“舞”为中心词的“剧舞”。事实也正是如此。一部舞剧发展史,从诺维尔依托哑剧实现“舞剧”的独立表意,经伊凡诺夫的《天鹅湖》二幕、福金的《仙女们》、格里戈洛维奇的《斯巴达克》、到吉里安的《婚礼》等,“交响编舞”或者说“作曲式编舞”的观念得以确立。“舞剧”作为“剧舞”的确是无法用“字幕”来释义的。
近两年来我看了不少舞剧,但真正值得我为之撰写舞评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林怀民的《九歌》、杨丽萍的《孔雀》、邢时苗的《粉墨春秋》、苏时进的《邹容》、佟睿睿的《一起跳舞吧》、王舸的《红高粱》等。还有一部太过厚重的舞剧《孔子》。要说“该不该有字幕”,比较一下《一起跳舞吧》和《孔子》就能明白。这两部舞剧都用了字幕,前者本可不用,不用也能看懂并有所启迪;后者用得繁缛,但受众仍不明白为什么?也就是说,从制作人生产营销的角度,用用“字幕”未尝不可;但从舞剧编导创作构思的角度,必须摒弃“字幕”思维。
舞剧作为“剧舞”有其表意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舞剧编导的创作构思,基于受众理解的立场,一是借助“前理解”,二是探求“易理解”。所谓借助“前理解”,是指借助受众的知识积累,这体现为我们许多舞剧往往以文学名著(既往)或影视热片(当下)为蓝本,比如前述《红高粱》。所谓探求“易理解”,是上世纪50年代为我国培养舞剧编导的前苏联专家古雪夫就言明了的“特性”:比如表现运动中的形象是舞剧结构的主要规律,舞剧的戏剧结构越简单舞蹈越丰富;比如舞剧中主要人物的数量一般不能超过4个,因为要考虑人物形象能否在发展中展现;比如要按照音乐编舞,独舞的语言设计越复杂越好,群舞则越复杂越糟……
当下舞剧演出中出现“该不该有字幕”的问题,说明我们的舞剧创作从构思到表达都存在一些问题。其一,舞剧为历史名人作传是困难的,比如前述《邹容》和《孔子》。在通过舞剧“看懂”名人的理解上,弄不好我们会出现“名人”和“舞剧”的双重失落。其二,舞剧的让受众看懂不能依赖图解,林怀民的《九歌》和杨丽萍的《孔雀》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九歌》中的“云中君”始终由2位演员肩扛着表演,作者说是“表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孔雀》则在舞台上设计一个硕大的“鸟笼”,来喻说“人生的困境和不自由”。其三,舞剧与其受众的关系,就一种审美实践而言需双向互动、双向建构。借助“前理解”是舞剧顺应受众,探求“易理解”则不能单方面苛求舞剧,受众更应在舞剧的审美实践中逐渐提升解码能力——而 “字幕”只能让这种能力在依赖中沉睡……
二、重建舞蹈的文化理想
这是一个舞蹈无处不在、无处不跳、无处不火的季节。这节那节需要舞蹈,这乐那乐需要舞蹈,这“秀”那“秀”需要舞蹈,甚至这“达人”那“达人”也需要舞蹈……这是狂欢的舞蹈也是舞蹈的狂欢,这是舞蹈的文化却可能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舞蹈。
1.泛漫化的舞蹈成了眼球经济的“百搭牌”
如果你是“驴友”,你可能会在名山大川遭遇“印象”。这“印象”那“印象”,其实是一个个实景演出,是把“一方人文”的典型性格还原到“一方水土”的典型环境之中。你可以挑剔这“印象”的人文不那么深刻,你也可以挑剔这人文的“印象”搅扰了山水的空灵,但对大多数偶尔出游、难得一游的观光客来说,山水的旅游被赋予了文化的积淀,这“印象”还真留下了某些印象。
如果你是“宅人”,你可能会在“大营”、“大道”瞥见“星光”。这“星光”那“星光”,其实是一个个才艺展示,是把孤心苦诣的艰辛求索呈现到大庭广众的开心一笑之中。你可以挑剔这“星光”的才艺不那么精湛,你也可以挑剔这才艺的“星光”抹花了夜空的纯净,但对大多数娱情乐兴、自得其乐的休闲者来说,艺术的神圣被消退了炫目的光环,这“星光”还真荡起了某些念想。
你可能会注意到,无论是“印象”的营造还是“星光”的闪烁,都充实着或镶衬着喜兴、欢愉乃至激越、亢奋的舞蹈。事实上,舞蹈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去公园晨练,你会看到舞蹈的“夕阳红”;去馆所健身,你会投入舞蹈的“音律操”;随手打开电视,不时有舞蹈在晚会上捧场;应邀风情聚餐,也常有舞蹈在席间伴宴……其实舞蹈发挥着远比上述现象更为重要的功能:新近愈演愈红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就有舞蹈的魅力四射,稍早杂技剧《天鹅湖》的载技载艺也多靠舞蹈来支撑,更早些由“团体操”作为开幕式的大型体育赛事则早由以舞蹈为主干的“文艺表演”取而代之了。也就是说,在注重视听感受的“眼球经济”时代,“舞蹈”或者说“泛漫化的舞蹈”成了炙手可热的“百搭牌”,强化着各类艺术或准艺术的观赏性。但在舞蹈不断拓展并强化自己的工具属性时,也不乏职业并且敬业的舞者担心其本体在泛漫中消解。
2.演艺“大制作”的诟病除了舞美就是舞蹈
在当代舞台演艺的创作和制作中,“大制作”是一个颇遭非议的话题。之所以屡遭非议,大抵是认为许多“制作”无助于演艺本体甚至是有害于这一本体,对于重写意理念、重虚拟表现的戏曲艺术尤为如此。演艺(无论是舞台演艺还是影视演艺)需要“创作”也需要“制作”,这是毋庸置疑的。“制作”需要体现“创作”的理念从而引导观众的解读,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电影大片的视觉冲击、豪华剧院的视觉氛围正改变着观众的期待视野,还有某些重大题材、重大庆典的综艺表演也需要“大制作”通过视觉冲击引起心灵震撼——在这里,舞美的“体量谋略”与舞蹈“人海战术”成为工具的首选。
在纽约百老汇看音乐剧,的确能看到不少“大制作”——比如《西贡小姐》中有直升机从天而降,《阿依达》中有游泳池碧波粼粼……但这基本上是一演数载的驻场演出,以至于剧院往往就成为某部剧的专属剧院。我在百老汇所见的《妈妈咪呀》,就其“大制作”的视觉冲击力和感受的震撼力来说,也远非我们“巡演版”的《妈妈咪呀》可同日而语。但那些“大制作”一与豪华剧院无关,二与“人海战术”无关。以舞蹈的“人海战术”来吸引眼球并期待籍此震撼心灵,是我们舞台演艺“大制作”当下独有的特色。
读到过许多抨击“大制作”的文章,大多认为“大制作”一是“烧钱”二是“伤体”——损伤演艺本体,但这好像不影响舞美因自身的本体得到强健而“我行我素”。其实,我们真正够“大”的演艺或综艺“大制作”,一在大型场馆内二在实景“印象”中。这里的舞美制作往往还具有高科技的含量,而“舞蹈”编排(如果还算“舞蹈”的话)则呈现为较低水准的扩张。在许多情况下,服务于“大制作”的舞蹈主要是满场人跑来跑去、成堆成串,舞蹈在其工具属性得到高度发挥时,的确在本体属性上有所困顿。
3.谁是舞蹈明星或怎样成为舞蹈明星
舞蹈界有不少人为刘岩而惋惜而抱憾!这位主演过《瓷魂》《红河谷》《筑城记》和《黄道婆》等4部大型舞剧的女舞者,在“2008奥运开幕式”的连排中因偶发事故而告别舞艺。尽管她是为着一项重要而且光荣的使命,尽管编创团体也有着强化她明星身份的良好愿望,但其实那段只有2分钟左右表演只能展现她艺术才华极为有限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刘岩的悲剧其实折射出舞蹈的悲剧——作为曾经的舞蹈明星,刘岩在4部舞剧中的杰出表演似乎还没有那2分钟的“长绸舞”绚烂。
说到舞蹈明星,当下的大众首先想到的是杨丽萍,想到的是那只充满灵性的孔雀;而在上一辈人的记忆中,这“孔雀”一如白淑湘和她的“白天鹅”。但现在,想如同赵青通过舞剧《宝莲灯》、陈爱莲通过舞剧《鱼美人》、舒巧通过舞剧《小刀会》那样来成为舞蹈明星已不大可能了。这就是为什么杨丽萍要在她的“原生态”歌舞集《云南印象》中,去不断强化大众对那支并非“原生态”的《雀之灵》的印象;也是为什么杨丽萍要在“2012央视春晚”中再度以《雀之恋》亮相,并且还让高科技为雌孔雀也装点了绚烂的尾屏。
借助视频是今日舞者成“星”的一条重要途径。网络达人中,有不少搔首弄姿、扭捏作态的舞者,但这大多与“星”途背道而驰;央视秀场,“星光大道”之侧还有“我要上春晚”助阵,当然每年一度的“央视春晚”最为给力——它甚至使同样每年一度的“央视舞蹈大赛”也相形失色。让我们许多经久难忘的舞蹈基本亮相过“央视春晚”:比如2004年的《俏花旦》、2006年的《俏夕阳》、2007年的《小城雨巷》、2008年的《飞天》等。在此我想特别提一下2005年的《千手观音》。这只舞蹈让大众记住了它的编导张继钢,后来也记住了它的领舞者——聋哑舞星邰丽华。我感到不无遗憾的是,大众在张继钢与《千手观音》之间划上了等号(后来当然还与“奥运”开幕式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划上了连线),而张继钢许多比《千手观音》厚重得多、也辉煌得多的舞蹈创作却如“泥牛入海”了。
4.“萎退的舞蹈”能否重建它的文化理想
莱辛“论诗与画界线”的《拉奥孔》和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的“没有地址的信”,先后都提出过一个论断:即与原始部落的舞蹈相比,现代舞蹈或者说现代人舞蹈是一种“萎退的艺术”。原因在于现代人的运动感知能力在退化,在于曾经在日常交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的“体态语”让位于发达的“声音语言”。但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舞蹈艺术是有过长足进展的。正是由于它与时代、与大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舞蹈在内的歌舞艺术至今仍是最富生机、最有人气、最具活力的舞台演艺。
今天的舞蹈,在其工具属性得到强化并广为泛化之时,也不失有舞人做着重建的努力:我们的大型舞剧创作,尽管不能不受“大歌舞”时风的影响,但毕竟在舞蹈的叙述方法和叙述能力上有明显提升;我们的实验舞蹈创作,已将舞蹈本体的探索和创作主体的思索高度契合,已为当代中国包容和接纳的主体也向当代中国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我们还有许多重新植根乡土沃壤的舞者,在所谓“原生态”的认祖归宗中去焕发舞蹈的情感张力和生命伟力!
舞蹈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尽管它具有自娱、健身、交谊、宣泄等种种非艺术的文化功能,但艺术表现、审美创造肯定是它努力追求的文化理想。即便在文化传播手段不断更新、文艺演出样态不断翻新的今日,舞蹈仍有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和不可取代的优势——比如它的“体态语”表现使它不存在“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比如它的“律动性”节奏使它具有极大的情感穿透力,比如它的直观“动态性”丰富并拓展着“读图时代”的文化理解……在当下泛漫化的舞蹈语境中重建舞蹈的文化理想,一是仍要下大力气传承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舞蹈文化,二是要在人民群众的当代社会实践中进行舞蹈文化创造,三是要拓宽传播渠道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舞蹈文化需求,四是要努力培养人民群众成为舞蹈文化创造的主体……这样,我们的舞蹈就能在极大地发挥工具性能的同时,极大地提升文化品质并实现文化理想。
三、舞蹈的生命情调与人文精神
相信晚饭后去公园或广场散步的人,都能看到一簇簇、一块块展臂踏步、运身转体、摇头晃脑、心悦意得的“舞者”。我之所以称之为带引号的“舞者”,在于他们的“手舞足蹈”既非“情动于中”的艺术表现,也不是“情不自禁”的文化风情;不过他们肯定都自以为是在“舞蹈”,并且自信这“舞蹈”有助于他们康健体魄、愉悦身心,甚至还有助于他们体态袅袅、风姿翩翩!很显然,这是我们当下最具常态性的“群众舞蹈”,我也相信这是我们舞蹈艺术乃至舞蹈文化的群众基础!
大城小镇里公园或广场上的“舞蹈”,其实彰显出“舞蹈”悄无声息的“文化转型”与“自我革命”。这是一个乡村文明日渐式微城镇文明不断昌盛的“转型”。乡村文明中与农耕生产方式相维系的舞蹈活动,以往总是出现在年复一年“春耕秋收闹冬闲”的“冬闲”之中;步入城镇文明后的舞蹈活动,变“闹”的娱乐性功能为“养”的康健性功能,其周期性也由“年复年”变成了“周复周”,在晚饭后,特别是退休人员将活动周期变成了“日复日”。当然,在那些大中城市的舞蹈沙龙里还有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舞蹈”,作为另一类“群众舞蹈”它并不看重康健性功能,它的功能主要在于“社交性”,在于步入一种社交场合、融入一种社交氛围并陶冶一种社交仪态。
谈论“舞蹈”之所以从群众自发的“活动”入手,在于我们关心“舞蹈”其实是关心其“文化”的命运。其实自宋、明以来,文化人基本上就不关心“舞蹈”了——没有了汉魏之际曹植的“拍袒胡舞”,也没有了盛唐李白的“自起舞剑作歌”……文人雅士陶冶情性只谈“琴、棋、书、画”,“修身养性”其实已无“修身”可言了。近代以来关注“舞蹈”的文化人,可能首推激情“说舞”的闻一多。他所著述的《说舞》一文,通过参加一场澳洲原始舞蹈的假想,指出舞蹈的目的是紧紧围绕“生命”来展开的:是以综合性的形态动员生命,以律动性的本质表现生命,以实用性的意义强调生命,以社会性的功能保障生命。因为在闻一多看来,“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
闻一多认为,只有实现“生命情调表现”的“六个最”,才能看到“舞的真面”,才能看到“真正全体生命机能的总动员”。实际上,当舞蹈脱离“生命机能”率性表现的必须而成为一种职业后,它就成了一种失去“真面”的表演。失去“真面”其实并不意味失去“真诚”,比如初民们那些祈丰、求嗣、招魂、驱邪的舞蹈,虽非“真面”却不失“真诚”。随着语言文字的发达及其在人类社会交往中地位的提升,倚重于身体文化的舞蹈无论从生命情调还是从人文精神上都开始滑落。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舞蹈”一个最主要的家园是“女乐”。其品质被清代戏曲大玩家李渔一语道破:“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习声容也。欲其声音婉转,则必使之学歌;学歌即成,则随口发声,皆有燕语莺啼之致……欲其体态轻盈,则必使之学舞;学舞既熟,则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
其实,现在的青少年也不乏通过“学歌舞”来“习声容”者,并且这种欲体态轻盈、欲回身举步“悉带柳翻花笑之容”的身体文化观,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舞蹈”的理解和认证。舞蹈、舞蹈者的身体常常被从“性”的欲念中来解读,而她们之中也的确有混迹那种欲念解读场所者,也的确有(哪怕很少、哪怕不自觉)为某些看客的此种欲念“搔首弄姿”。换言之,对舞蹈“期待视野”的历史积淀,有可能诱导我们的舞蹈误以为那是自身与生俱来的本性。事实上,“舞蹈”既是艺术表现的一种工具,也是“习舞者”把自己变成艺术品的一种方法,如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伊莎多拉·邓肯所说:“只有把舞蹈包括在内的教育才是合理的教育……要把艺术给予人民,要使劳动者获得艺术的观念,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把他们的孩子变成活的艺术品”。这里所说的“活的艺术品”,指的就是“舞蹈”在对人体训练过程中对人体美的陶塑效果。
应《光明日报》编辑同志来谈“舞蹈”,我当然知道主要是谈“舞蹈创作”并且是“职业的舞蹈创作”。但要谈就难免有所褒扬有所批评,这种褒扬、批评需要很“职业”但不能很“小众”,需要很“文化”但不能很“矫情”。我当然知道,舞蹈从业者已经极大地拓展了舞蹈的本体——人们在山水实景游艺中看到舞蹈营造的“印象”,在舞台歌手煽情中看到舞蹈编织的“意象”,在动漫形象设计中看到舞蹈创生的“幻象”……更有诸多TV大敞“精舞门”大开“讲舞堂”:湖南卫视《奇舞飞扬》,贵州卫视《舞艺超群》,浙江卫视《舞动好声音》,成都卫视《舞动嘉年华》,央视既《酷舞先锋》又《舞出我人生》,最甚者莫过于东方卫视《舞林大会》《舞林争霸》《星空舞状元》的全方位出击……
相形之下,我们的这个舞赛那个舞赛、这部舞剧那部舞剧,自身还在“为赋新诗强说愁”,“春眠”过后“却道天凉好个秋”了!的确,“舞蹈”失却了轰动也失却了追捧——上世纪80年代两届全国舞赛后,独舞《水》《春蚕》《海浪》《雀之灵》等广为流传;90年代以来被广为传演的群舞有马跃的《奔腾》、张继钢的《女儿河》、孙颖的《踏歌》和达娃拉姆的《酥油飘香》等;进入新世纪,“舞蹈”的声望不能不借助央视的“春晚”,于是人们记住了刘凌莉的《俏花旦》(2004)、张继钢的《千手观音》(2005)、赵明的《俏夕阳》(2006)、应志琪的《小城雨巷》(2007)……现在不要说小型舞蹈作品,就是大型舞剧也如同“过眼烟云”。
当非职业舞蹈风生水起之时,我们的职业舞者当然不愿随波逐流,那我们该何去何从?能有何作为呢?我想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当然在此不是视其为“执政理念”而是视其为“创作法宝”。深得这一法宝真谛的第一个典型是戴爱莲。她在上世纪40年代深入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不仅传扬了民族风情而且提升自己的创作,一支《荷花舞》至今传扬不朽。深得这一法宝真谛的第二个典型是贾作光。他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扎根内蒙,不仅学习该地区蒙古族、达斡尔族等民族舞蹈,而且将提升后的舞蹈在民众中普及,他不仅有《鄂尔多斯舞》保持本色,而且有《任重道远》《海浪》等开创新篇。深得这一法宝的第三个典型是杨丽萍。她先以《雀之灵》的自编自演为万众瞩目,后又重返红土地编织《云南映象》《云南的响声》等。她不久前编创并主演的舞剧《孔雀》,从语言要素、主题动机、形象设计都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编创理念,成为大众追随“舞蹈”的一大“热点”,体现出最贴近大众的“人文精神”。
毫无疑问,舞剧以其厚重的体量和丰富的承载,成为最可能引人关注的“舞蹈”焦点。新中国的舞剧创作,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舞剧创作,就数量而言在世界稳居首位是毋庸置疑。这其中也不乏包括《红河谷》《红梅赞》《千手观音》《粉墨春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在内的精品力作。但大多数舞剧热衷于舞美的体量谋略和舞蹈的人海战术,一俟“亮相”便偃旗息鼓。立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视点,我特别想推荐编导佟睿睿为上海歌舞团编创的大型舞剧《一起跳舞吧》。这部舞剧不仅表现出都市的世相百态,而且聚焦于让市民们摆脱俗物、超越平庸的活动——在社交舞蹈中放松心情、陶冶性情。是的,这是现时代第一部在表现现实生活时,感悟到大众自己的舞蹈(活动)对自己日常生活超越作用的舞剧。它沟通了大众的舞蹈活动和职业舞者的舞蹈创作,它告诉我们“舞蹈”能够怎样开掘“人文精神”,怎样重新唤起渐趋式微的“生命情调”。
四、讨伐“舞八股”与优化舞业生态
2014年12月9日,资华筠先生在与病魔抗争10年后与世长辞了。想起仅仅还在一个月前的11月5日,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颁奖典礼在苏州举行,荣获“著作类”特等奖的资先生还在同期举办的当代中国文艺论坛上发言,大力倡导文艺批评的“三真”精神。她说:“对评论对象要有真切真实的感受,这是第一个‘真。第二个‘真是对你所得到的感受要有真切生动的表达,使读者和受众跟你有一种共鸣。第三个‘真是在前两个‘真的基础上,追求揭示规律性的探索,这样才能使评论有公信力和前瞻性”。
1.爱之深、虑之远讨伐“舞八股”
我有时会静下来想想资先生“讲真话”的特点,我以为这个特点一是敏捷二是犀利三是通透四是友善。先生曾写过一篇《舞坛不寂寞——95舞坛纵横说》(载《舞艺·舞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厚重舞评。虽是评说1995年的舞事,但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文中有一节专论 《编导“大腕儿”的兴起及讨伐“舞八股”》,指出“‘腕儿级编导有许多施展机会。除个别人有甘于寂寞、积蓄力量的明智之举和少数略见创新之外,大都‘高产而不‘优质,一些作品有明显的‘快餐、‘速冻味道。看似机灵的‘鬼点子,却有雕虫小技之感。如果说‘腕儿级编导有点‘老本儿(生活与艺术的积累)和‘熟能生巧的技法,应付着眼前任务的话;那些盲目的追随者们,却以更蹩脚的方式争相‘复制他们的‘快餐配方,于是频频出现于银屏和舞台的‘舞八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资先生在文中罗列了“舞八股”的“罪状”(资先生语):一是模式化地图解主旋律,二是华丽的包装与舞蹈本体的萎缩,三是假招子代替真功夫,四是“通用粮票”加“风格性装饰”,五是任意杂交的不伦不类,六是人体变形加扭捏作态,七是形体裸露度的无限扩大,八是堆砌技巧的杂技化倾向。“罗列”之后,资先生指出:“‘舞八股纵有诸多表征,总体症状却是造情、矫饰、偷巧和品位低俗,病源则是长期缺乏营养的‘代偿性劳作所致。疗救的前提是正视病体,不讳疾忌医。今日作檄文讨伐,实乃爱之深而虑之远矣”。你看,资先生的“讲真话”就是这样融通着“斗士风采”和“仁者情怀”!
2.呼唤“探索规律、追求独创”
隔了若干年,资先生再次撰文指陈舞蹈创作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篇厚重而深邃的舞论题为《探索规律,追求独创——关于近期舞剧、舞蹈诗创作的思考》(载《舞思》,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资先生指陈的四个问题是:一、“命题”作舞与为舞造情;二、善于“造势”与滥用包装;三、追求“观赏性”的误区;四、借鉴与套用的混淆。关于第一个问题,资先生虽也指出“‘命题未必非得‘造情不可”,但强调“症结往往出在创作准备(生活与艺术积累)不足,命题未能激发起艺术家真实的创作冲动,缺乏命题与创作思维的契合点,力不从心地仓促上马……出现了闭门策划,迷信外援(大腕儿),突击强攻和华丽包装等构成的‘无孕分娩式的创作模式,忽略的恰恰都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关于第二个问题,资先生指出“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舞(情)不够,景来凑。且舞台美术的设计都趋向于大制作、超豪华。有时,作品的内容愈苍白,主体创造愈贫乏,舞台美术愈奢华……也有些基础不错的作品,由于‘包装的品位不高而帮了倒忙。各个剧组间的盲目攀比,互相套用,更助长了艺术的雷同化”。关于第三个问题,资先生认为“首先是脱离具体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片面追求所谓的‘观赏性舞段。如随意设置‘选美、‘宴庆场面,借题发挥地堆砌些花里胡哨的‘表演,游离于主题,干扰了主线,弱化了主体。再就是审美品位的媚俗化——不顾时代背景、作品基调、人物身份,每每都离不开干冰、烟雾,外加彩灯频闪,似乎只有‘美女如云、媚态百出、袒胸露腹外加机关布景才具有‘观赏性,更有甚者以怪诞、刺激取胜吸引观众‘眼球”。关于第四个问题,资先生指出“舞剧创作中的套用现象时有所见,且见怪不怪、愈演愈烈,以致形成了某种趋势。照搬他人之举已无所顾忌,连略微改头换面都懒得去做了……此类问题对于大多数编导来说,主观上并非出于‘抄袭的动机,而是认识——观念上的模糊和创作上的惰性导致求异思维的萎缩”。真是指陈得“鞭辟入里”,剖析得“入木三分”!
3.创作繁荣中忧思“大晚会综合症”
正是基于对舞蹈的“爱之深而虑之远”,资先生又一次发表深邃而厚重的舞论《繁荣中的忧思——舞蹈创作现状的思考》(载《舞思》)。这个“忧思”是什么呢?资先生指出是“‘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大晚会”指的“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图解政治)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关于“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资先生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作替代创作。指的是“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二是“艺术激素”代替创作激情。指的是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三是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指的是“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打飞的”指导;通用性技巧的堆砌和豪华包装滥用,看似“花哨”,却无真货。四是套用、抄袭替代适度鉴赏。五是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四、五两点在《探索规律,追求独创》一文中已充分指陈,这里不再赘述。六是舞蹈本体的萎缩。指的是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舞蹈成为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曲的呈现也未必添色……
4.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既然“忧思”的是“综合症”,资先生提出的“疗救”主张是“优化舞业生态”。她深刻地指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之发展——形成‘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上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制‘形象工程盲目上马;如果‘官员(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制‘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资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艺术评论》创刊号(2003年)上,至今已十年有余了。我在引述先生的“良苦用心”时始终不忍停顿,因为她所说的“生态作用络”、她所希冀的三个“如果”能够实现,我们无疑会有更优质、更美好的繁荣!(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