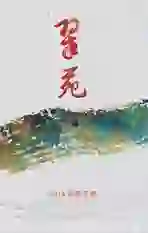林中小屋
2015-06-30许沁
引 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中共满洲省委随后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一些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官兵自发组织抗日义勇军,并接受中共党员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1935年冬,东北军各部开始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一
1935年,初秋,吉林延边山区。早晨,湿湿的浓雾渐渐散去,茂密的栗树林缝隙筛下缕缕慵懒的阳光。
43岁的付卫铭扛着猎枪从林子里钻出来,向山下的木屋走去。林子里露水重,他的裤管完全洇湿,肩上的狩猎袋恹恹地贴着衣服。转了2个多小时,这个早晨仍是空手而归。
木屋门前,大约500米隔着一条小河,河面不宽,现在是枯水期,河里只有一米宽的水,水很浅,而且清得能看到河底的沙石。
木屋又旧又破,门左边有个半人高的鸡棚,鸡棚后面是茂密的栗树林。从高处看,直线距离木屋5公里远的树林里,有个插着太阳旗的建筑群,那是日军设在这里的临时监狱。监狱也是木头搭成的,门岗二层楼高的瞭望棚里,有持枪的日本兵站岗。
木屋里,付卫铭的妻子夏岩芝坐在炕上,看着手里一张照片发呆。照片上是夏岩芝的儿子宝儿,今年19岁。宝儿17岁那年冬天,跟着附近抗日义勇军打游击,已经一年多没回家。
38岁的夏岩芝正怀有8个月身孕。屋里除了土砌灶台、一张旧木桌、一顶裂开口的衣柜和一只旧木箱,再没有值钱的东西。
门推开,付卫铭躬身进来,瞅一眼炕上的夏岩芝,卸下身上的猎枪和狩猎袋挂到墙上,然后一声不吭拿过桌上的旱烟袋和烟丝,蹲到门边往烟锅里装上烟丝,点上。
随着烟锅里兹兹冒烟,付卫铭喉咙里很快呛出一连串的咳嗽。
夏岩芝瞄了瞄丈夫,又扫一眼墙上的猎枪和贴着墙面的狩猎袋,鼻子里软软地滑出两行气,目光又落到照片上。
付卫铭撮嘴吸了两口烟,头转向夏岩芝:“咋又在看宝儿的照片呢?你肚子里怀着娃,别老整一张苦脸!”
夏岩芝头没抬,摸着照片叹了口气:“唉,你说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一年多失去联系了呢?俺家宝儿究竟去哪儿呢?”
付卫铭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也是啊,你说宝儿好好地跟着义勇军打鬼子,过去三五天就有信带回来,现在咋就没音信了呢?按理,就是被小鬼子抓去或者祸害了,也总该打探到消息吧?怎么就一直没信呢?这活要见人,死……”付卫铭说不下去,脸微微背过,不让妻子看见他眼睛托不住泪。
屋外,不时有飞机轰鸣。
付卫铭将燃过的烟丝在门槛上磕掉,然后又押上一锅,点燃,抬眼,眺望门外河对岸的树林:“这栗树叶都快全黄了,真不知道这挨千刀的小鬼子咋会跑到中国土地上害人?这山里的百姓死的死,跑的跑,这日子是没法安生了,要不俺也上哪儿躲一躲?”
夏岩芝斜一眼丈夫:“躲?躲哪儿去?俺说啥也不离开这儿。要是俺走了,日后宝儿找回来摸不到门咋办?”
付卫铭叹气,顿了顿,说:“就依你,不走!”
突然,林子那边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继而隐约有嘈杂的吆喝声从树林深处传来。
付卫铭忙关上门,头颤抖着透过窗户上的薄膜纸洞朝外望。
树林与小河交界处,一个模糊的人影正跑过来,等人影渐渐近了,能看清那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一身褪了色的东北军制服,出了树林,此刻他正慌张地朝小河方向跑来。
到了河边,年轻人停脚犹豫片刻后,警惕地回头看了看。然后飞快趟过河床,冲到了木屋门前,一边焦急地敲门,一边轻声喊:“老乡,请开开门!”
付卫铭脸凑近门缝:“你找谁?”
门外,年轻人脸上的泥和汗水搅在一起,一边说,一边往身后看:“老乡,俺是东北军的,刚从小鬼子监狱逃出来,后面鬼子正在追。现在迷路了,能不能开门找个地方让俺避一避?”
夏岩芝也听清了门外的喊声,见付卫铭迟疑不动,她从炕上挪下身子,走上来推了一下:“你发什么呆呢?现在这东北军也和宝儿他们义勇军一起打鬼子了,快让他进来啊!”说完,夏岩芝开门,拉着年轻人往屋里拽。
年轻人喘着气,一边谢,一边快速闪进屋。
夏岩芝:“宝儿他爹,快帮他藏起来!”
付卫铭猛然醒悟似地:“藏——藏哪?柜子里?”
夏岩芝想了想:“也只有这样了!”
两人手忙脚乱把年轻人塞进柜子,却发现柜子上的大口子一眼就能看到底。
付卫铭着急:“这咋整呢?”
从柜子里拉出年轻人,夫妻俩都愁着眉满屋找地方。
年轻人一眼瞥见炕上的照片,心里一怔:那人国字脸,大眼睛,小平头。他正要开口,夏岩芝说话了:“屋里地方小,藏不住,要不就藏鸡棚里吧,万一有情况,也好从棚后面跑。”
付卫铭:“中!”
两人把年轻人拉到门外,连推带压塞进了门左边的鸡棚。
鸡棚里一阵扑腾后,很快平静下来。
夏岩芝托着肚子,一只腿半跪在鸡棚门口,叮嘱里面的年轻人:“孩子记住,鸡棚后面有块板可以挪,挪开板钻出去,就是栗树林,树林里跑出去50米,就到了南坡,那里林子更密,容易藏人。一会你待在里面别动,如果有情况就逃出去。进了树林一直往东跑,就能跑到山外头。听说那也有打小鬼子的队伍,好像也是东北军的,你跑出去后就找他们。”
年轻人探出头,仰脸感激地看着夏岩芝:“谢谢大叔大婶,你们家炕上照片上那个人……”
一听这话,夏岩芝就迫不及待:“那是俺宝儿,已经一年多没信了。你咋问这?”
年轻人惊讶:“宝儿是你们儿子?”
夏岩芝同样惊讶地看他:“是啊!你认识宝儿?你看见俺宝儿了?”
是的,俺们刚才还在一起,宝儿和俺都关在鬼子监狱里,刚才就是他掩护俺逃出来的。说到这,年轻人的脸突然涨红,眉毛也在下垂。这些,付卫铭、夏岩芝并未察觉,相反,这意外的消息,倒让他俩异口同声地追问起来:“什么,你刚才和宝儿在一起,俺宝儿还活着?”
大叔大婶,你们听俺说:“一年前俺和宝儿被鬼子抓进去,今天才找到了逃出机会……”
年轻人正要说下去,不远处的树林里响起了嘈杂的喊叫声,而且越来越近,明显是冲着这边来的。
尽管夏岩芝和付卫铭的心里,都被刚才从年轻人嘴里意外听到的消息振奋着,牵挂着,但鬼子追击的叫喊声,使他们不得不赶紧打断年轻人。
关上鸡棚门,夫妻俩立即起身回屋,关上木屋门。
二
很快,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叫喊声就在门外响起来,接着是疯狂的拍门声和吆喝声。
付卫铭脸上神经紧绷,站在门边不知咋办。
付卫铭出生于私塾世家,年轻时在延边城里做老师,日本人侵占东北,学校也被强占,成了日本鬼子的兵营,小鬼子到处烧杀抢掠,付卫铭城里待不下去,只得躲回山里跟着猎户学打猎。尽管现在碰到豺狼、豹子,也敢一个人窝在草丛里瞄准、射击,但遇到那些他在城里亲眼目睹过的无恶不作的日本兵,他还是心有余悸。
夏岩芝跟丈夫认过字,也一起出去打过猎,知道丈夫天性怕事,所以就跟在边上陪他开门,一边小声说:“你慌啥?俺陪你!”
付卫铭手刚碰到门栓,门就被踹开了
进来的是肥头大耳的汉奸翻译吴方贵,后面带来3个日本兵,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军官,是驻扎在日本临时监狱的宪兵小队长伊藤井。
这两人,付卫铭和夏岩芝平时就听说过。这一带,他们沆瀣一气,做过很多丧尽天良的坏事,这里好多猎户就因此被逼得远走他乡。
另外两个日本兵,一人刺刀尖上还有一长溜血迹。
这阵势,让付卫铭战战兢兢:“军爷……太君,你们……”
吴方贵点头哈腰地看了一眼伊藤井。伊藤井挺着大肚子,眼睛朝着天。
吴方贵见伊藤井没把自己塞在眼里,便无趣地转身,腰板挺得直直的,拿眼瞪付卫铭:“听着,太君来找一个人, 刚才看见一个当兵的往这儿跑了吗?”
付卫铭眼睛看地上:“没……没看见。”
吴方贵又看了看伊藤井,伊藤井脸上仍无表情,他随即又向付卫铭夫妇喊话:“我可警告你们,如果有一点隐瞒,太君可要不客气了……”
说话时,吴方贵眉毛炸开,左手在付脖子上夸张地做出砍头状。
低着头的付卫铭一阵哆嗦,眼睛余光瞄了一眼手握指挥刀的伊藤井,嗫嚅着答话:“真……真的……没……没看见。”
夏岩芝挺着肚子站在丈夫旁边。
伊藤井向吴方贵耳语,听完,吴方贵转身对着付卫铭,凶神恶煞般地吼:“太君让你看着他眼睛说话,到底有没有看见?太君可没工夫跟你扯嘴皮儿。”
见付卫铭眼神躲闪,吴方贵一手摁住他脖子:“说,有没有看见?”
付卫铭只觉有千吨之力压在颈上,头垂得更低:有……没有。
吴方贵用力摁:“到底有没有?”
付卫铭先是点头,但马上又摇头:“没有,太君,俺可真没看见有什么国军跑过来啊!”
吴方贵眉头突然一闪,当即弯腰看伊藤井反应。伊藤井脸上滑过一丝冷笑,点点头。
吴方贵回头,骄傲地俯视着付卫铭:“怎么?我刚才可没有说那个当兵的是国军哦!”说完,他躬身用日语和伊藤井叽里咕噜了几句。
伊藤井脸上挤出阴森森的笑。
付卫铭额头上汗点更密:“不……这……军爷,太君,俺整天在山里没啥见识,啥都不懂啊?”
伊藤井眼含凶光,嘴里吐出不太标准的中文:“搜!”
付卫铭哆嗦着侧让一旁,夏岩芝用手臂轻轻碰他,示意他镇定。
吴方贵提枪满屋子翻箱倒柜后,一无所获:“报告太君,没有。”
伊藤井一脸不悦:“继续追!”
伊藤井转身。
吴方贵屁颠颠跟着。
伊藤井抬脚刚要跨出门,却突然停下,眼睛盯上了炕上的照片。
见此,付卫铭和夏岩芝直懊恼刚才没把照片藏起来。
伊藤井目光转向付和夏:“这照片上是你们的什么人?”
付卫铭慌不择词:“是……是什么人?”
伊藤井眼睛一瞪,目光刀一般刺向付卫铭:“我的问你!”
夏岩芝忙上来搭话:“哦,太君问照片上的人啊?唉,是俺那傻儿子,经常发羊痫风,已经离开家走失一年多没信了。”
说完,暗暗向丈夫递眼神。
付卫铭当即附和:“是的,太君,是个傻子。”
“八嘎,死了死了的。你的谁是傻子?”伊藤井拔出刺刀,举起来对着付卫铭。
夏岩芝冲上前,身子挡住付卫铭,一个劲地好言哀求:“太君饶命,是俺那儿子傻子,太君的伟大,太君的最伟大!”
伊藤井眼珠转了转,将刀插回套中:“呦西!你们的支那人的大大的傻子!”然后,他表情神秘地继续看照片。
吴方贵也看到了照片,眼睛顿时一条缝地讨好伊藤井:“嘿,我说太君,咱们找了一年多,这义勇军的联络员窝点居然就在皇军的临时监狱旁边呀?真是踏破皮鞋无处找,得来全不费工夫!”
回头,吴方贵看着付卫铭和夏岩芝,一脸奸笑:“大胆狗男女,竟然大白天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告诉你们,照片上的这位一年前就被皇军抓到了,而且,义勇军恐怕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哈哈!”
伊藤井看了看吴方贵,手朝自己鼻子指指:“吴桑,你的过来!”
吴方贵赶紧把脸凑过去,伊藤井在他耳边低语。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鸡叫声。伊藤井一惊,竖起耳朵立即寻找声音来源。听清楚声音来自屋外时,他触电般地转身,命令吴方贵出去搜查,自己则带另一个兵在屋里乱刺、乱捅一气后,转身向外走。
宝儿有了消息,付卫铭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有了着落,见伊藤井正迈脚出门,他脸上绷紧的神经渐渐松开,不料,这一变化全落在突然回头的伊藤井眼里。
伊藤井两眼毒蛇般地盯着付卫铭:“你的,刚才为什么那样害怕?现在,我们的要走,你的又很放松?你的什么的干活?”
付卫铭急忙点头哈腰解释:“太——太君,俺这不是在送你们吗?”
夏岩芝也顺势搭话:“太君们脚大踩四方,俺山里人胆比老鼠小,见了太君自然会紧张。”
伊藤井脸上狡猾地一笑,迟疑片刻,双脚跨出门槛……
门外,吴方贵立马躬身迎上来:“报告太君,就一破鸡棚,没啥!”
伊藤井看了一眼鸡棚,刚挥手想叫大家继续往前追,却又放下了,像想起什么似的,径直向门左边的鸡棚走去。
这时,已经平静下来的鸡棚里,又响起一串鸡叫。
伊藤井狐疑地看一眼鸡棚,脸阴沉着转向付和夏:“你的里面的几只鸡?”
付卫铭慌忙恭敬地回答:“太君,里面就一只鸡。”
伊藤井:“八嘎,一只鸡也能这么热闹?”
伊藤井推开正猫腰朝鸡棚里张望的吴方贵,用刀挑开鸡棚门,然后蹲下身子,脸凑近朝里面看。这时,一只公鸡惊叫着从他头顶飞出,也许惊吓过度,飞过头顶时,公鸡尖利的双爪将他额头的皮划出一长条口子,紧接着是一长溜糖稀排泄物从他鼻尖,一直淋到头发和后衣领。
伊藤井疼得扔下刀,双手去捂受伤的额头。
吴方贵和两个士兵惊得木偶一般僵在那儿。过了一会,吴方贵才叫两个士兵去追公鸡,自己三下五去二脱下褂子,捧在手上跪到伊藤井身边,给他擦脸上和头上的鸡粪,一边扭曲着鼻子躲避臭味。
从脸上松开双手,伊藤井满手是血,他愤怒地推开吴方贵,捂着鼻子蹲下去继续将头探进鸡棚。
鸡棚后面,有个打开的洞口,一块木板斜倒在地,上面沾着厚厚的干鸡粪块,看不出有什么新鲜脚印,但似乎也能猜出,可能有人刚从这里逃出。
伊藤井倏地站起,看着付卫铭和夏岩芝举起刺刀:“八嘎,竟敢欺骗皇军,通通地死了死了的!”
刀将要落到付卫铭脖子上时,突然停在半空。
吴方贵哆嗦着看着付卫铭和夏岩芝。
付卫铭和夏岩芝反而显得很平静。
付卫铭:“太君,俺怎么敢欺骗太君呢,这山上黄狼子多,把这鸡都叼走了,那个挡板就是黄狼子给弄倒的。”
夏岩芝:“是的,太君,本来里面有七八只鸡,让那黄狼子全给偷了,就剩一只了。”
“八嘎,你们的良心大大地坏,黄狼子比人还高吗?”伊藤井一边问,一边目光似两条毒蛇一般,在付卫铭和夏岩芝脸上游来游去。过了一会,眼睛里露出一丝阴森森的寒光,将举着的军刀放下来。
正当付卫铭和夏岩芝以为事情可能快被糊弄过去时,伊藤井突然再次举起刀,一个转身,背对着付卫铭一眼不眨地将刀刺进了付卫铭下腹。
付卫铭当即抽搐倒地,鲜血喷涌而出。
夏岩芝哭喊着扑向丈夫,一个劲地用手帮他捂住流血的肚子……
看着倒地的付卫铭和哭得死去活来的夏岩芝,伊藤井用刀挑起吴方贵的褂子,擦掉脸上的血迹和鸡粪后,又用它擦去刀尖上的血迹,然后扔掉褂子,收刀示意吴方贵过来听他指示。
一番耳语后,吴方贵弯腰连连称赞:“太君高明,太君实在是高啊!”
回头,吴方贵俯视着趴在丈夫身上哭泣的夏岩芝,阴着脸说:“刚才进门就说了,胆敢欺骗太君,一律死了死了的,你们偏要与太君作对。太君说了,刚才你们帮助跑掉的那个当兵的,他可是害死你儿子的仇人。”
夏岩芝一愣,立即停下哭泣,将信将疑地盯着吴方贵:“什么?你……你说是他害死了俺家宝儿?”
吴方贵朝伊藤井献媚一笑,然后继续俯视着夏岩芝:“嗨,你们都说儿子傻,我看还真聪明不到哪儿去。告诉你吧,就是那个东北军告发了你儿子是义勇军的联络员,然后趁我们放松看管才自己逃了出来。要不是他,我们才不会知道你儿子是义勇军呢。好了,我们要去追那个东北军了,你的傻儿子这会还在皇军监狱里。你们好好想明白,今后要是有人来找你儿子,就立即向太君报告,这里下山坡往西10里多地的林子里,就有皇军的监狱,要是再敢骗太君,当心送你们全家地下见!”
伊藤井朝吴方贵满意地点头,紧接着又狡黠地一笑,摇摇头:“你的,太啰唆的不行,快快去追!”
吴方贵领着伊藤井一行,匆匆向树林深处追去。
三
夏岩芝瘫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付卫铭的头,目光呆滞。付卫铭耷拉着头,手脚冰凉,双眼紧闭。
门缝里,中午的太阳穿进来,漏出几缕晕黄的光。
夏岩芝站起来,到灶台边拿出菜刀在石头上磨,一边磨一边泣不成声:“宝儿、宝儿他爹,你们放心,俺要再遇到那个东北军,拼死也要砍掉他的头。可怜的宝儿,你这一走两年多,打打杀杀,又是一年多没信,胖了还是廋了,小鬼子把你怎么了?这下你爹没了,就为掩护那软骨头,你爹死得冤哪……”
木屋外面,满山的栗树被午后的太阳照得处处黄亮亮的。
树林里,年轻的东北军战士一边跑,一边慌张地辨着方向。身后不时传来叫喊声。
前面出现一条河,年轻人跑到河边,放慢了脚步,焦急地自语:“怎么办?鬼子又追过来了,可那份情报究竟掉哪儿了呢?”
沿河边跑了一段路,年轻人又看见了早晨的木屋,眼睛一亮,犹豫着停下来:会不会早晨逃跑时掉在这里了呢?
他环视一下周围,然后快速趟过河床,来到木屋门边,手几次要落到门上,却没有碰。
正在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便冲向鸡棚,一头钻进去。
终于,他从鸡棚倒掉的木板下面找到了早晨逃跑时遗落的情报卷。钻出鸡棚,正要离开,眼前浮现了早晨在木屋里看到的那张照片,于是又回到木屋门边,上前敲门。
屋里,夏岩芝正在给丈夫穿寿衣,一把磨好的菜刀放在桌上。
听到敲门,她立即拿起刀,警觉地躲到门后:谁?
大叔大婶……是俺,早晨你们帮助逃走的东北军。
从门缝里看,夏岩芝确定门外就是早晨逃走的那个东北军,顿时,胸中像是倒进了一大堆石灰块。她举起菜刀刚要开门,心里又犹豫起来。沉默片刻,她朝门外冷冷地说:你这个软骨头,出卖了俺家宝儿,害死了宝儿他爹,现在还敢回来?
站在门边的年轻人一脸惊讶:“什么?大婶,您说俺出卖了宝儿,俺害死了大叔?这是咋回事?大叔他?”
夏岩芝咬着牙,话语石子般从嘴里蹦出:“好吧,就让你这个软骨头死个明白,早晨追你的小鬼子说,俺家宝儿是你告发的。你的心让狼吞了?为了你,宝儿他爹被小鬼子活活刺死,可怜他到死都不知道是你出卖了宝儿。早知你是个没骨气的中国人,当时就该把你交给小鬼子一刀刺死……”
听说付卫铭被鬼子杀害,年轻人的心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扑通”一声跪到门前:“大——大婶,是俺害了大叔,是俺告发了宝儿兄弟。”
“好啊,难得你还敢承认!你摸摸你的良心让狼叼去了吗?你咋就这么没骨气呢?”夏岩芝悲从心来,身子依着门板滑倒在地。
“不,事情不是这样!”年轻人又连忙解释:“婶,早晨你们救俺时,小鬼子追得紧,我没来得及说。可那是宝儿兄弟为了让我逃出来送情报,才故意想出来对付小鬼子的招啊……”
门外年轻人的话,给夏岩芝心里塞进了一团乱麻。她强撑着爬起来靠门站着,将信将疑:“你说是宝儿想出来的招?什么招?俺家宝儿现在咋样了?”
年轻人:“早晨逃跑时,俺不小心把宝儿兄弟交给我赶快送出去的重要情报卷弄丢了,这是专门回来找的。后面鬼子还在追俺,您快开门,俺把宝儿托俺带给你们的信交给您就离开。”
夏岩芝犹豫。
年轻人轻轻地敲门:“快开门吧,婶,俺真有宝儿的信。”
夏岩芝脸色稍缓和:“好吧,看在你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俺再让你进来一次,也好让你给宝儿他爹磕个头,然后再和你算账。说完,她一手拿刀,一手开门。”
年轻人怯怯地进屋,看到地上血肉模糊的付卫铭,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满腹内疚地向付卫铭连磕了三个头,一边磕,一边流着泪不停地自责:“叔、婶,是俺没用,俺早晨真不该来打扰你们。可是,俺真不是叛徒!”
说完,年轻人从贴胸衣袋里摸出一只兔皮做的护身符和一封信,递给夏岩芝:“这是宝儿兄弟让俺带给您的。今天早晨俺到你们家躲避时,看到宝儿照片就想交给你们,结果鬼子追来,没来得及给。在监狱,宝儿兄弟要俺一定要逃出去,等送出情报,就到山里找你们把这些交给你们,还说他以后会想办法逃出来……”
刀从夏岩芝手上滑到地上,她接过护身符和信,然后颤抖着将信摊开:
爹娘:
宝儿让你们惦记了,小鬼子侵略我国土,国家有难,儿也许不能为你们尽孝了。东北军兄弟冯国宝是情报联络员,一年前,咱俩接头时中了鬼子埋伏,现在,义勇军和东北军都不知道俺俩下落,俺怕时间长了双方猜疑,加上在监狱里发现了小鬼子的细菌试验计划。这一年多来,俺整天愁着把情报送出去,却一直没机会,俺只能想招让国宝兄弟脱身送信。俺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千万别难过,只要把小鬼子早一天赶出中国,宝儿死而无憾……
夏岩芝信读了一半,身子一软,又要倒下去,年轻人忙上前扶住。
夏岩芝强撑着站住:“你就是东北军的国宝?真是宝儿让你逃出来的?俺宝儿他咋样了?”
年轻人走过去脸凑到门上,听了听外面暂时没动静后,过来扶夏岩芝坐到炕上。说:“婶,俺叫冯国宝,过去俺东北军的任务是剿灭共产党,现在也开始联合义勇军打鬼子了。营长让俺负责和义勇军的宝儿联系。去年春天,宝儿到延边城里和俺接头,谁知他身边出了奸细,偷偷带小鬼子跟踪他,等俺赶到约定地点刚准备和他说话,一群鬼子冲上来就把俺俩抓了。敌人很快把俺俩从城里弄到这山里的秘密监狱。宝儿说,小鬼子这是使阴招,目的是制造俺俩失踪挑起双方猜忌,从而挑拨离间。宝儿真不愧是共产党员,虽然小俺一岁,却比俺坚强,处处照应俺,鼓励俺。一年多来,无论怎样拷打,俺俩啥都没招。”
夏岩芝看着冯国宝,迫不及待地打断:“这些宝儿信里都说了,你快说宝儿现在咋样了,他这会人在哪儿?”
“婶,宝儿他……”冯国宝欲言又止。
“咋了,俺宝儿咋了?”夏岩芝一脸的期待。
两行泪从冯国宝眼里淌出来,他长叹了口气,犹豫一会,充满敬意地说:“前两天,宝儿放风时意外听到小鬼子要用咱中国活人做细菌试验,为了尽快把情报送出去,他要俺假装向小鬼子告发他是共产党,以便让敌人放松对俺的看管,让俺伺机逃出去。俺不应,他就劝俺,说他身份早被奸细出卖了,而俺的身份鬼子可能还没全掌握。就这样,俺只好答应。今天早晨放风时,宝儿故意和俺打架,然后乘乱让俺逃出来。可俺没逃多远,就听到身后枪响,后来才知是宝儿兄弟为掩护俺逃,不顾一切拼命拖住追俺的敌人……可是……天杀的小鬼子开枪打死了宝儿兄弟……”
没说完,冯国宝已泣不成声了。
夏岩芝将护身符和信紧贴在胸口……早晨瞬间失去丈夫的悲痛还没抚平,此刻再闻儿子的噩耗,她眼睛里已经流不出泪,只觉一片模糊……
四
院子外面,不远处的树林里,叫喊声越来越近。
悲痛欲绝的夏岩芝电击一般清醒过来,看着狼藉的屋子,强撑着站起来,拉过还在哭泣的冯国宝,叫他躲进木柜,又把炕上的棉被抱过来盖到柜子裂口上。
冯国宝:“婶,您……”
夏岩芝:“别说了,俺宝儿做得对,你还有情报要送,还有小鬼子要杀,俺不能看着小鬼子再来祸害你!”
冯国宝:“婶……大叔他?”
一根针刺在夏岩芝心上,但她很快平静下来:走了,宝儿走了,他爹也走了,都是丧尽天良的小鬼子害的。总有一天,中国人会把这些杀人魔王千刀万剐。
冯国宝从柜子里顶起被子,探头哽噎:“婶……俺今天早晨真不该跑到你们这里,不然,大叔他……”
夏岩芝忙将他的头按进柜子,用被子盖上。然后,缓缓坐到炕上。忽然,她看见柜子底下在滴血:“你流血了?”
冯国宝似乎也刚意识到:“哦,早晨从小鬼子监狱里爬窗逃出来时,窗户上的铁刺划伤了腿。刚才跨进柜子时,可能裹伤口的布松了。”
不行,这样鬼子来了会发现的。夏岩芝有些慌:怎么办?
冯国宝掀开被子,再次露出头:“婶,您别管,俺不能再拖累您了,还是让俺走吧!”说着就要往外跳。
夏岩芝连忙将他按下去:“你现在出去是死路一条。你死了,情报谁送?那该死的小鬼子不打了?婶还指着你为宝儿他爷俩报仇呢!”
“可俺藏不住啊!万一鬼子来了,那不又把您拖累了?”
“这是什么话,保你命是为了多杀鬼子,怎么是拖累呢?”夏岩芝想了想,说:“俺有办法了。”
夏岩芝开门,直奔鸡棚抓出那只公鸡,拎回屋,一刀下去,鸡血喷溅。夏岩芝将鸡血淋到了自己的裤子上和柜子上的棉被上,又顺柜子淋到地上。然后,又从水缸里舀一瓢水从头上浇下来。顿时,脸上、身上和头发上血水模糊……
五
吴方贵和脸上裹了纱布的伊藤井带着几个日本兵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树林里追出来,走到山脚,他们沿着小河继续往前找,吴方贵和伊藤井边走边说。
吴方贵:真不知道那个逃兵跑哪儿去了,害得太君追了大半天,要是早晨不上那共产党的圈套,他连溜的门儿都没有!
伊藤井:“哼,愚蠢的支那人,他的跑不远!”
吴方贵:“真应该早点用刀斩了他。吴方贵一边说,一边用手对着自己脖子做出铡人状。”
伊藤井阴险一笑:“难怪说你们支那人是猪。我的要的是他的情报,他的情报不说出来,杀了他又有什么用?”
吴方贵哆嗦着点头:“太君英明,太君英明!”
抬眼,前面出现了小木屋。
吴方贵一愣:“嘿,太君,这林子里真他妈邪门,追了半天,怎么又回到了这里,这户……早晨咱不是已经搜查过了?”
伊藤井眯眼一看,也不解地点头,然后轻蔑地看着吴方贵:“我的知道。那个没用的支那人的还想骗我。”
吴方贵故意作疑惑状:“太君,我有个疑问。”
“嗯?”伊藤井示意吴方贵说下去。
吴方贵:“太君为啥早晨不把那对夫妻一起给咔嚓了呢?只杀了那个男的,这不太仁慈他们了?他们可是窝藏了东北兵呐!”
伊藤井摇头,露出一脸奸笑:“你知道一个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吗?”
吴方贵脱口而出:“这小的明白,就是自己死的时候。”
伊藤井再次摇头,不屑地斜视着吴方贵:“不不不,你的大大的不明白。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的人死在自己面前却无能为力。你的明白,我不是叫你告诉她,说是那个逃跑的中国兵出卖了他儿子吗?如果那个女人再遇到那个中国兵,她的不把他撕碎吃了才怪。皇军的最喜欢的,就是看你们中国人的斗中国人。呦西!”
吴方贵额头直冒汗,一边鞠躬,一边赶快转移话题:“太……太君英明。也不知那个当兵的跑哪儿去了。这么大个林子能藏哪儿?”
伊藤井:“既然来了,你的就进去看看,不过,谅他也没胆再跑进来。”
夏岩芝坐在柜上一个劲呻吟,一阵杂乱的敲门声后,门被踹开。
吴方贵带头闯进来,他眼睛朝天,一脚绊到了躺在地上的付卫铭的遗体,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低头一看,吓得连退两步,但很快又哆嗦着继续往前探。看着满头满脸血水的夏岩芝,他颤抖着问:你……你在干什么?
一脸痛苦的夏岩芝半睁着眼睛,脸上的血水一行行淌下来:“军爷——太君,快救——救救——俺!俺——要要生了……”
看着一脸恐怖的夏岩芝,伊藤井不解地问吴方贵:“她的什么的要生了?”
吴方贵:“当然是早晨被太君刺他丈夫吓破魂了,一紧张就要临产了。真他妈倒霉,一股血腥味,太……太君,咱这里的民俗是,男人如果见了这种事就会犯冲,也就是会沾上晦气,会倒八辈子大霉。您看这?”吴方贵哈着腰,用手扇着血腥味,他的意思是,想赶快离开这里。
伊藤井:“你的什么是犯冲?”
吴方贵:“报告太君,犯冲就……就是太君和我见了这种事,太君的身体,不,太君和小的身体会很快大大的坏,命大大的短。”
伊藤井:“八嘎,你的死了死了的!”
吴方贵连忙扇自己的嘴巴:“唉唉唉,看小的这张臭嘴,是小的命大大的短,身体很快大大的坏,太君的长寿长寿的好!”说完,吴方贵躬身看着伊藤井:那屋里还搜不搜 ?
伊藤井指指他脑袋,摇摇手:“你的这里大大地笨,早晨她亲眼看着丈夫死,现在要生孩子,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短时间遇到两件最痛苦的事,何况那个中国兵还是她仇人,她怎么会再放那个中国兵进来?而且,那个中国兵也不会那么傻,会再跑回来。一定跑别处去了,你的别浪费时间,快快地给我追!”
吴方贵:“是,太君分析的大大的对。那这个女人怎么办?”
伊藤井一声冷笑:“你的不用管,让她自己在痛苦中死去。走!”
伊藤井气势汹汹地跨出木屋,吴方贵弯腰小跑着跟在后面。
一行人继续往河东边树林中追去。
六
门外脚步声远了。
夏岩芝脸色惨白,艰难地将身子挪到炕上,喊柜子里的冯国宝出来。
冯国宝从柜子里出来,朝夏岩芝跪下。
夏岩芝摆了摆手,让他起来。
冯国宝:“婶,您家最后一只鸡……”
夏岩芝:“那畜生该杀,要是早上它不乱叫,说不定你就不会被发现,宝儿他爹就不会死了。”
“婶……”冯国宝大哭
夏岩芝强撑着走过来,扶起冯国宝:“好了,哭什么?小鬼子走了,你快去完成你的任务吧。”
冯国宝目光转向付卫铭的遗体:“大叔他……”
夏岩芝忍着泪,蹲下身去抚摸付卫铭的脸,坚定地说:俺会把他安葬好的。
冯国宝哽咽着扶着夏岩芝。
过了一会,夏岩芝起身:“好了,赶快走吧!万一小鬼子再回来。”
冯国宝:“婶,俺刚才跑的时候仔细琢磨过了,这里出去距离俺东北军营地还真不远,走出这片树林翻两座山就到了,俺队伍里有医生,您生孩子时用得着,等俺把情报送完,就请求营长带人摸上来把您接走……”
夏岩芝:“不用,俺自己能。”
冯国宝:“婶放心,俺看过,鬼子的临时监狱防守力量不强,俺营长当兵前也是山里人,以前跟着老蒋“剿共”没办法,现在俺都加入了抗联专门打鬼子,说不定今晚营长就带人把这里的监狱端掉,给宝儿和大叔报仇。”
夏岩芝:“俺等着,你快送情报吧,这小鬼子多蹦跶一天,就多祸害中国人一天。”
“嗯,您保重!”冯国宝说完,转身要出门。
夏岩芝突然想起什么:“等等,孩子,你叫什么国?”
冯国宝:“俺叫冯国宝,国家的国,宝物的宝。”
夏岩芝:“国宝……和俺宝儿一样,也有个“宝”字。”
夏岩芝转身从柜里找出一件宝儿的褂子,又从口袋里拿出护身符:“这是宝儿的衣服,你穿上,万一遇到鬼子,就说是山上猎户,你那军服脱下来给俺埋掉。这护身符也带上!”
冯国宝:“婶,衣服俺穿,可这宝儿兄弟的护身符俺不能要,您留着也是个念想。”
夏岩芝:“带着吧,战场上生生死死,它兴许还能保你个平安。”
冯国宝接过护身符,放进左胸口袋,向门外走了两步,突然哭着转身跪下:“娘……”
听清是在喊自己,夏岩芝身子一颤,隐约感到腹中一阵绞痛,忙用手去摸腹部,两行泪沿鼻根而下:“孩子,你等一下!”
夏岩芝走到墙边,取下猎枪,又从狩猎袋里拿出一包铁砂弹,递给冯国宝:“这枪和铁沙弹是宝儿他爹平时狩猎用的,豺狼、豹子只要中了铁砂弹,不是眼瞎就是腿瘸。你带上,路上也好有个防护。”
冯国宝跪着,接过枪:“娘,宝儿回到队伍一定带人来接您……”说完,转身朝付卫铭遗体磕了三个头,起身向外走。
七
树林边,夏岩芝一手扶树,一手扶着腹部,眼睛向远处张望。
树林深处小道上,冯国宝噙着泪一边走,一边不时地回头挥手。
望着冯国宝渐渐走远,夏岩芝喃喃自语:“战火——这战火再大,也还是有绿色树叶的……”
作者简介:
许沁,1995年8月生,常州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著有散文集《走过去,一路繁华》《你好,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