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3第五章《两地书》出版与爱情生活
2015-06-01郝庆军
文 郝庆军
鲁迅在1933第五章《两地书》出版与爱情生活
文 郝庆军

作家的爱情生活大都是丰富多样,富有传奇色彩,而且伴有各种传闻,各种花边,离奇古怪,幽明莫辨。有一千个作家就有一千种爱情生活,正如他们的作品,谈恋爱的方式一定是风格独特,绝无雷同。文人本是多情种,爱欲纷争,离离合合,势在必然,不足为奇。但作家和明星不一样,他们大都讨厌聚光灯,喜欢独来独往,秘密行事,对自己的爱情生活绝少愿意披露,更不愿意别人说三道四。许多惊天秘闻,都是作家离世多年之后,由当事人或其后人披露曝光,公诸于世的。很少有作家愿意主动披露自己的爱情秘史,即便无意中曝光了自己的爱情生活,也绝少愿意把私人情书公布出来,且不说要印刷成书,公开出售的了。
但是,鲁迅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仅毫不隐瞒地披露了自己与女学生的婚外爱情生活,而且还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与女学生的情书予以分门别类,精心编辑,出版发行,公之于众。别说普通人物,一般作家都没有如此胆量和魄力,即便如胡适那样的学界领袖,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公布自己的婚外情。胡适与青梅竹马表妹曹诚英,与美国红粉知己韦莲司,与多情美少女徐芳,与可爱女人罗维茨等人的爱情经历,都是谨慎秘密进行,生前绝少公开提及,只是到了他过世之后,才逐渐被历史学者一点点挖出来,逐步丰满了胡适的精神人格。
当然,鲁迅再勇敢,也不会在与许广平恋爱之初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挑战公序良俗,贸然宣布自己的恋情,而是在上海与许广平生活多年,生了海婴之后三年,才公开出版自己与许广平的情书集《两地书》的。
1933年4月,《两地书》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向全国公开发行。这一年,鲁迅52岁,许广平35岁,海婴虚岁4岁。
为什么鲁迅在1933年才印行自己的情书?他出版这本书究竟什么目的?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结合在当时人们的眼里究竟是怎样的?文学圈里的人究竟怎样看待鲁、许的爱情生活?除了许广平之外,鲁迅与其他女性还有没有情感纠葛?如果有,那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透过鲁迅的爱情生活,怎样全面了解鲁迅,怎样客观认识鲁迅的精神内涵?这些问题对我们研究鲁迅和理解鲁迅都至关重要,需要一一剖析。
一
首先要弄清楚《两地书》是怎样一本书。
《两地书》收录了1925年至1929年间,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个人通信135封。全书共有四部分:序言、第一集:北京(1925年3月至7月)、第二集: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第三集:北平——上海(1929年5月至6月)。
第一集收录了在北京时期鲁迅任职教育部和北大、女师大教员期间与许广平的通信35封。这35封信,忠实记录了二人从认识到熟识,以至于发展为热恋的全过程。这些信件充分展现了一个成熟而有魅力的老师与一个求知若渴的女学生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许广平称呼鲁迅为“鲁迅师”、“鲁迅先生”或“鲁迅先生吾师左右”,而鲁迅则称许广平为“广平兄”。
关于“兄”的称谓,许广平与许多读者一样,很是费解:一个比自己大17岁的先生居然称呼自己的女弟子为“兄”,您老人家作何解释?
许广平问:“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绝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
鲁迅回信劈头就回答了为什么称“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有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老哥”的意义。但这些道理,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
鲁迅解释说,这是我自己独创的称谓,凡是老朋友、旧同学、听课的学生,无论大小,不论男女,鲁迅都一律称呼“兄”,这个“兄”字比直接称呼人名稍好一些,略显尊重,但又不像“先生”“太太”“小姐”那样的称呼,显得疏远,客气。总之,鲁迅称“兄”,绝无包含“兄长”“老哥”的意思,而是一种自创的、亲切的、独特的称呼。鲁迅声明,这个“兄”字,当然不是开玩笑的游戏,也不是给许广平单独设立的称呼,其中的意思只有鲁迅自己一个人清楚,难怪许广平费解。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由于名人效应的示范作用,自从鲁迅独创发明“广平兄”一词以来,我国的书信往来中,就多了这样一个称谓:即不论男女老幼,只要关系稍进而融洽,都可称“兄”,尤其是称呼年轻女性为“兄”,不算唐突,而成为一种时尚。
当然,这种称谓中也包含一种调侃和幽默的意味,两人在文字游戏中进一步增进了解和共识。总体来说,北京时期的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探讨的内容比较集中,像一般还未涉及恋爱,但又彼此想恋爱的人那样,无非是谈学习,谈人生,谈理想。都是些大概念,比较抽象,笼统,原则性的东西比较多,即便涉及具体人和事件,也不太直抒胸臆,比较少袒露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因为两人还没有那么熟,没有那么亲密,不可能在信中直接臧否人物,展露心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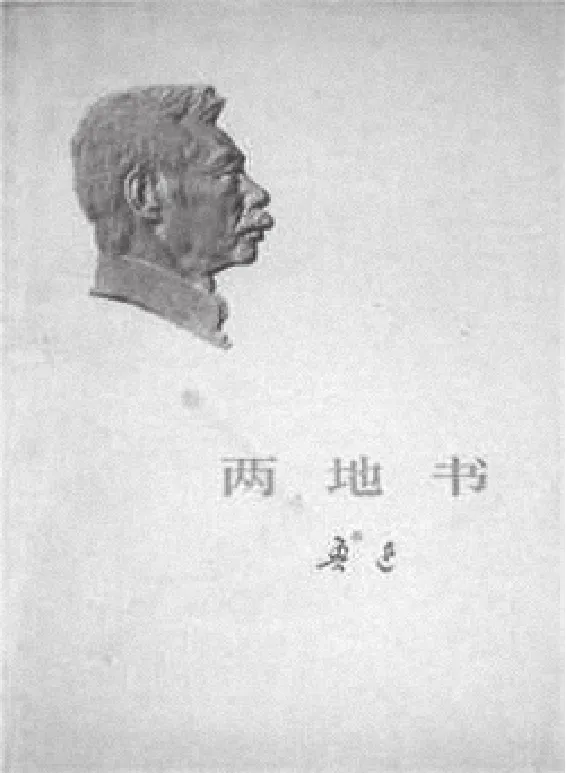
《两地书》书影
相比而言,许广平的来信比较直接,自己有什么想法,尤其是一些不平和困惑,都会一一请教,而鲁迅的回答则虽然也很诚恳,但是有些囫囵,有些笼统,甚至有些滑头。比如,许广平在1925年3月26日的信中问鲁迅,是否真的要“做土匪去”呢?也就是说,鲁迅是否要参加实际的斗争,参与社会活动,许广平并表示,如果鲁迅去做“土匪”,她愿意做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做一个小喽啰,“不妨令他摇几下旗子,而建设和努力,则是学生所十分仰望与先生的。不知先生能鉴谅他么”。
许广平的这些话,很真诚,掏心扒肝,热辣辣的,甚至有些以身相许的味道了。
但鲁迅却有些不敢接茬,显得有些心虚。他说:“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不妨把这些书信来往看作男女之间的攻防游戏,现在看来是不必当真的。信中许广平说,我要做你的马前卒,为你的事业摇旗呐喊,我仰慕你很久了。鲁迅回信说,我哪里是干事业的人呢,我心太敏感,不够凶狠,而且也有些贪生怕死,不愿意牺牲自己,更何况是牺牲别人呢,你还是别跟我了。其实,鲁迅在信中只是示弱,装怂,对许广平的进攻保持守势,只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
为什么说这是鲁迅的托词呢?因为不久鲁迅作为“真的猛士”的形象便展现出来了。那就是著名的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的表现。在这些要掉脑袋的运动中,鲁迅才是个真爷们,铮铮铁汉的形象在“摊上事了”之后方能显现。
女师大学潮的历史功过和是非曲直自有历史学家来评判,在这里暂且搁置其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鲁迅对许广平等人的支持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男朋友,一个男人,鲁迅的表现完全可以打满分。在女师大风潮中,校长和教育部当局无疑是强势一方,他们驱逐许广平等人,擅自撤销女师大,把许广平他们赶出学校,而许广平等人自己组织起来,开展护校、复校活动。鲁迅当时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一方面作为教育部官员,应该维护当局的权威,站在校长杨荫榆和教育部一方,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同时又是女师大的教师,他的激进思想和启蒙精神,使得他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站在学生一方,他坚决支持许广平她们与学校和当局作斗争,身体力行地支持她们复校,起草声讨书,联络教员为复校的学生上课,在声援书上带头签字。为此,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了鲁迅教育部的职务,鲁迅因为许广平丢了饭碗和乌纱帽。撇开鲁迅的进步思想和斗争精神不说,作为一个男朋友,不惜牺牲名誉和职位,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持自己的女朋友,只此一点,便可令许广平值得以身相许。
《两地书》第一集真实地记录了鲁迅和许广平在女师大风潮中,二人如何互相支持,分析时局,制定战略战术,在遇到困难时,互相鼓励,誓死战斗到底的精神,也在纸背暗示了他们如何在困苦中互相支撑,相依相扶,走出困境的。而且,这些书信,没有多少卿卿我我的记录,也没有多少死呀爱呀的山盟海誓,倒是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和人物,成为研究现代史的第一手优质材料。
二
爱情故事到了顶点,自然是鲁迅和许广平双双南下的时期。
第二集收录了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间,鲁迅与许广平分别在厦门和广州期间,异地而处,互相倾吐胸中块垒,记录工作生活境况,发表对时局人事的观点,臧否人物,交流思想的书信77封。这些书信占了《两地书》的一多半,而且发生在鲁迅生活、创作和思想大转折的时期,自然非常重要,历来受到鲁迅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1926年北京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写了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引起全国震惊,当然也受到当局的嫉恨和攻击,他在教育部的职务被免去,随后他上了通缉名单,加上北京学界以胡适、陈源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对鲁迅进行造谣和攻击,公开污蔑他通共通匪、挑动风潮、著作抄袭等,而此时,在厦门大学的林语堂盛情邀请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动了南下的念头。此时的南方,革命潮流日渐高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鲁迅受到感染和鼓舞,加之他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也比较稳固,双双相携南下,另筑爱巢,呼吸新鲜空气,创造新的生活,也是鲁迅下决心南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与许广平同行,途径上海,鲁迅赴厦门任教,许广平去广州老家,一边觅职,一边与鲁迅保持书信联系。


鲁迅到厦门大学后,发现自己上了当。他原本计划至少在厦大住两年,除了教书和著述之外,出版他先前搜集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沉潜下来做点扎实可靠的工作。但是,学校当局对他的工作并不重视,学校并不真心发展学术,而是借鲁迅之名装点门面。更为重要的是,厦门大学的许多教员很多是与胡适、陈源有渊源的人,他们都很排斥鲁迅,或明或暗地抵制鲁迅。
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了这里的情况:“在国学院里,朱山根是胡适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
这里说的朱山根,是指顾颉刚。他是胡适推荐给厦门大学的,胡适与陈源是“现代评论派”的首领,鲁迅与陈源在北京打过笔墨官司,闹得不可开交,顾颉刚到厦门大学,自然对鲁迅有所不敬,引起鲁迅的反感。
在9月25日的信中,他告诉许广平说:“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顷,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白果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在出版《两地书》的时候,当涉及一些批评性文字的人物时,鲁迅都把真名改为化名,以减少对当事人的负面影响。这里除了上述顾颉刚之外,田千顷是指陈万里,辛家本是指潘家洵,白果是指黄坚。尤其这个黄坚,原来在北京任女师大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当时在厦门大学国学院任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他经常故意刁难鲁迅。鲁迅原来住在一个大陈列室里,需要走上百级台阶方可上楼下楼。但是,就这样的地方,黄坚也不让鲁迅住了,但又不给安排新的住处。好不容易安排了一间房子,里面竟然没有任何器具,空屋子一间。鲁迅向他们要器具,他们又是故意刁难,让鲁迅列出账单,签名去领。鲁迅照办之后,还是碰钉子。无奈鲁迅发火,他们才给添置器具。后来他们又捣鬼,拧走了鲁迅房间的一个电灯泡,从一些小事上找茬,故意捉弄他,弄得鲁迅很烦。

鲁迅与许广平
10月21日的信中鲁迅向许广平抱怨说:“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敌却还未知道,将来一知道,就要乐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自做我的事,他们想攻倒我,一时也很难,我在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兴。”
隔了一天,鲁迅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我以为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你看,鲁迅到厦门大学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感受到内部的压迫和排挤,对他自己选择来厦门大学教书的决定有些后悔。而此时,又闹出了高长虹的“月亮风波”,让鲁迅感到人世的悲凉和生活的荒诞。
高长虹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鲁迅在北京编辑《莽原》的时候,为他的成长花费了许多心血,甚至在自己咳血的时候,还为高长虹校对《心得探险》。但是,此人心性高傲,又非常狂妄,取得了一点成绩,就跑到上海开展所谓的狂飙运动,以编辑《狂飙》来树立旗帜。而此时鲁迅已经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教书去了。忽然,高长虹发表了两封信,一封信是《给鲁迅先生》,大骂鲁迅为“世故老人”,说他“头戴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处于“身心交病的状态”。
鲁迅一开始没有回应他,而是在与许广平的信中说出对高长虹的不满。后来,高长虹见鲁迅没有反击,越发来劲,又发表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时代的命运》《我走出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继续攻击鲁迅。无奈,鲁迅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文章回击高长虹,于是,一场笔仗在师徒之间打了起来,文坛又增添了一些是非和热闹。
《两地书》第二集中有二十几封信讨论这场笔墨官司。鲁迅在信中一方面感到悲哀,一方面又对高长虹的攻击进行了分析。而许广平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鲁迅的“傻”。她认为鲁迅在北京的时候那么热心青年的事,费心费力地为青年服务,“傻态可掬”。
她说:“你在北京,拼命帮人,傻态可掬,连我们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其实这样没什么,我的父母一生都是这样傻,以致身后萧条,子女窘迫,然而也有暂致其敬爱,仗义相助的,所以我在外读书,也能到了毕业,天壤间也须有傻子交互发傻,社会才立得住。但长虹的行径,却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他,是尽在人们眼中的,现在仅因小愤,而且并非你直接发生的小愤,就这么嘲笑骂詈,好像有深仇重怨,这真是可说奇妙不可测的世态人心了。你对付就是,但勿介意为要。”
还是许广平看得清楚。鲁迅对青年的热心和帮助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高长虹的此次反目,给鲁迅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他真的有些伤心,甚至愤怒,不惜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鲁迅在回信中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希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竟自以为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
其实,两个人都猜错了。
高长虹之所以攻击鲁迅,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他吃醋了。
高长虹爱慕许广平,许广平则爱慕鲁迅,于是,高长虹攻击鲁迅。这是最普遍的人间喜剧,生活正剧和一切狗血剧的主要桥段。
两个相恋的人,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厦门,猜测上海和北京发生的事情,其实隔着帷幕,幽明莫辨,都是瞎猜。到了1927年1月,二人从韦素园的来信中才知道高长虹辱骂鲁迅的真正原因——于是他们赶紧去查《狂飙》第七期,那上面有一首高长虹作的诗。鲁迅看了一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诗的名字叫《给——》: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看了高长虹的诗,鲁迅释然了。他立刻写信给许广平: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沈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作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鲁迅的这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奔月》,后来收入《故事新编》。鲁迅就是这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毫不退让。高长虹写了一首诗,说鲁迅是黑暗,自己是太阳,鲁迅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写了一篇小说,取材后羿射日的故事:你不是太阳么,我让人把你射下来。这也是鲁迅的可爱之处,在爱情问题上,斤斤计较,像一只好斗的公鸡,捍卫自己对母鸡的权力。你不是说我是黑夜么,那好,我就要拥有月亮,我就要和许广平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月亮风波”。
由第二集中的通讯我们可知,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鲁迅在厦门的教授生活非常艰难,四个月后鲁迅便决定赴广州,因为中山大学伸过手来,要聘任鲁迅为中山大学文科主任。许广平在广州,广州又是革命的策源地,1927 年1月18日,鲁迅毫不犹豫地登船奔赴广州黄埔港,当晚,“黑夜”便见到了思渴已久的“月亮”——许广平。
三
《两地书》第三集收录的是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迁居上海第三年,即1929年5月至6月间,鲁迅前往北平探望母亲,他和许广平之间的通信,一共21封。此时,许广平已经怀孕,走路不便,故此没能跟随鲁迅一同去北平。
在这些书信中,鲁迅向许广平详细通报了他在北平的见闻和经历,而许广平“身子沉重”,在家静养待产,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仔细阅读这些看似平常的信件,我们仍然发现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那种默契和融洽,也能看到鲁迅彼时的心境以及文化界的一些变化。
鲁迅在这些书信中确实爆了不少料。
第一,我们能看到鲁迅的家人对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事是一种什么态度。鲁迅的信中说:“关于咱们的事,闻南北统一后,此地忽然盛传,研究者颇多,但大抵知不确切。我想,这忽然盛传的缘故,大约与小鹿之由沪入京有关的。前日到家,母亲即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即答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鲁迅母亲鲁老太太对许广平的认可与接纳,但鲁迅夫人朱安是什么态度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既然鲁迅母亲问起了许广平,得知她有孕的消息很高兴,这是一个信号,鲁迅在外面“养小”的事实已经成为生米熟饭,老夫人的接纳态度给鲁迅带来的喜悦之气,鲁迅有后的消息让这个家庭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第二,鲁迅到北平的消息在北平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一方面,马幼渔、许寿裳等老友欢迎鲁迅,并与之吃饭畅聊,甚至极力邀请鲁迅留在北平任教。另一方面,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抵制鲁迅的到来,他们对鲁迅的态度前恭后倨。同是五四时代的战友,正在发生分化,有的继续前进,有的渐入颓唐,有的积极钻营。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等的合影
鲁迅敏锐地观察道:“我自从到此以后,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鲁迅又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人拾去了。”
这些感受,令鲁迅深深不安。他发现,原来许多五四时代的斗士开始变化,他们开始走向与他们战斗过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说,原先与黑暗战斗的人,开始化为黑暗了。
第三,鲁迅觉得北平的气氛过于保守和沉静,不利于养成进取的态度,倒十分让人变得颓唐。鲁迅信中说:“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激,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自从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文化重心便从北平转移到广州、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北平文化界逐渐变得保守和落伍,鲁迅的这种感觉是符合实际的。对鲁迅的到来,许多人觉得鲁迅会抢他们的饭碗,于是远远地予以抵制。
所以,在《两地书》中谈及做学问时,鲁迅非常感慨:“北平本来还可以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不响,大家玩玩罢。”
信中还透露了北平的北大、燕大等学校学生几次组织专人到西三条鲁迅家中请求鲁迅演讲,并留在北平教书的事情。这些都说明鲁迅在青年学生心目中具有精神领袖的地位,北平青年界普遍认同鲁迅,热爱鲁迅。
《两地书》毕竟是情书,字里行间夹杂着男女之间的情愫和彼此的牵绊。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因这本书而蜚声海内外,他们之间的各种绯闻和谣言,皆因此书戛然而止。《两地书》成了他们爱情生活的丰碑,一种平淡而绵长的爱情模式,将永远被镌刻着,传颂着,被一代代人咀嚼和分享着。不知这是鲁迅夫妇的幸运,还是一种悲哀呢?
但是,历史事实和世道人心绝不会因为一本书的记录而消磨掉它的复杂性,堂皇的书本和美妙的故事永远也代替不了生命与人性的幽暗与深邃。
我们这里需要简单介绍鲁迅生命中另一个女人,她也姓许,叫许羡苏。在《两地书》第112封信中,鲁迅给许广平开玩笑说:“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学生虐待她。”

许羡苏
这里所说的“令弟”是指许羡苏,因为也姓许,鲁迅戏称为许广平的“令弟”。
许羡苏是作家许钦文的妹妹,系周建人的学生,曾住在八道湾的周宅。鲁迅搬出八道湾后,许羡苏又跟随鲁迅住进西三条,大家都认为许羡苏应该成为鲁迅的女朋友,但是没想到又多出了一个许广平。
鲁迅好友曹聚仁在《鲁迅与我》一文中说:“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和许广平。朋友们的心目中,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而这位许羡苏小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与鲁迅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都不是很好考察。好在许羡苏本人有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会发现她与鲁迅的关系绝非一般。
首先,这位许小姐在鲁迅家住的时间之长令人不可思议。许羡苏前后住在鲁迅家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暑假住在八道湾,第二次是1925年暑假到1925年底,住在西三条的南屋,第三次是1926年暑假至1931年春天,住在西三条的“老虎尾巴”。前后住了五年。她虽然是浙江绍兴人,但她与鲁迅家非亲非故,只是凭她会说绍兴话,获得鲁迅母亲的喜爱这一点,就让她常住鲁宅,这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其次,许羡苏是个性情极其温和又明白事理的女孩,她与鲁宅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关系都非常好,不但老夫人喜欢他,大太太(朱安)、二太太(羽太信子)、三太太(王蕴如)都喜欢她。她是周建人的学生,周作人也教他课程,鲁迅更是喜欢她。鲁迅不仅为她做担保,还为她找工作,不仅给她提供住宿,还为她支付学费。许羡苏记住鲁迅的各种吃饭口味,而且还指挥厨师做出出乎鲁迅预料且非常可口的饭菜。许羡苏知道鲁迅的各种生活习惯,他的睡眠时间,喜欢抽什么牌子的烟,喝什么样的酒,喝多少合适。她知道鲁迅喜欢读哪些书,书在哪个架子上,清楚鲁迅写作时的习惯,知道当鲁迅默不作声躺在躺椅上闭目养神,则是在构思大文章,她便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许羡苏知道鲁迅写作累了不喜欢吃饭,她就指挥下厨房做松软可口的甜食来给鲁迅加强营养。总之,鲁迅的饮食作息,举手投足,喜怒痛痒,许小姐都了如指掌。这样的女人,对鲁迅来说如何不喜欢呢?
第三,更令人称奇的是鲁迅在厦门、广州、上海时期,他都没有停止给许羡苏单独写信,这事,许广平是知道的。几年间,鲁迅一共给许羡苏写了200多封信。《两地书》中共收录135封,还是鲁迅与许广平二人的通信的总和,而鲁迅单独给许羡苏就写了200多封,要是集结成书,那也是很壮观的一本大书了。只不过,这些书信没有保留下来。许羡苏说:“1931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在整理故居的时候,在朱氏的箱内,并没找到。否则可以多一些手稿,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许多事情。”
这“许多事情”,也许包含了鲁迅对许羡苏的感情,或者他们的关系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如果那200多封信在,可能会出版另一部《两地书》吧。
四
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基本都写在这部《两地书》里了。但为什么到了1933年鲁迅决定出版这部书信集,他的用意何在?
在《序言》中,鲁迅已经写得比较清楚:“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了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了,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为纪念,给好友,留孩子,致将来,出版该书的四个目的或理由很清晰,也非常合理。但为什么是在1933年来做这件事情,鲁迅没有明确交代,也没有什么具体说明,这就需要我们联系文学史语境,联系鲁迅思想和生活境况,来做一点探讨性分析。
首先是现实的原因。
1932年8月,未名社成员韦漱园(也叫韦素园)病逝于北平同仁医院,为了纪念他,大家搜集韦漱园的文稿和书信,便求助于鲁迅。鲁迅便翻箱倒柜地找,但是竟没有找到,原因是鲁迅怕被当局抄家的时候搜去信件,从信件中寻找捕杀写信人的证据,他在1927年和1930年两次集中焚毁过朋友的信札。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但是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倒是找出来不少。这些信曾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搁放在家中,经过炮火和枪弹的洗礼,并安然无恙。于是,从1932年夏开始,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把这些信件收集起来,按照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地编辑起来。到了年底,鲁迅将编辑好的这本书取名《两地书》,写了序言,交给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
其次是经济原因。
1931年12月,鲁迅的教育部特别撰述员的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裁撤,每月300元的固定收入也就没有了,鲁迅一下子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鲁迅举家避难,家中遭受枪弹袭击,造成一定损失。还有一条原因,就是在1932年,李小峰的北新书店因为出版《小猪八戒》而引起回民的抗议风潮,当局一度查封了北新书局。而鲁迅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的,他每月从书局支付400元的版税。北新书局遭此一劫,基本断了鲁迅的版税收入。所以鲁迅的经济状况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还有,1932年11月,鲁迅前往北平探望生病母亲,前后二十几天,花费颇多,基本花空了鲁迅的积蓄。所以,一度想北上,离开上海回北平。6 月5日,他给台静农的信中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致白头,前年又生了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在这年的8月17日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谈到他编辑《两地书》的真实想法:“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昨今一看,虽不肉麻,而亦无大意义,故是否编定,亦未决也。”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编辑出版《两地书》主要迫于经济压力,但他也颇为踌躇,因为他觉得“无大意义”。
但是,待到10月20日,鲁迅在致信李小峰的信中似乎下定了决心:“通信正在抄录,尚不到三分之一,全部约当十四五万字,则抄成恐当在年底。成后我当看一遍并作序,也略需时,总之今年恐不能付印了。届时当再奉闻。”也就是说,在1932年的下半年,鲁迅已经做好了出版《两地书》的准备。果然,年底鲁迅夫妇便将书稿全部编定完毕,鲁迅还写了序,于1933年2月将全部书稿交付李小峰,由北新书店假借青光书局之名印行。
第三,市场原因。
既然出版情书集是出于经济考虑,出版书信集是否有市场,是否赚钱,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赔钱,鲁迅出版《两地书》的动机就大打折扣。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市场上,书信集或情书的出版有成功的先例。茅盾的妻弟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印行后,卖得很好。事实上,这部书就收录了鲁迅的书信。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不是普通家书,而是带有浪漫色彩的情书,况且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故事在社会上已经传得纷纷扬扬,大家为弄清楚事实,对这本书肯定有所期待,因此,无论鲁迅本人,还是出版方李小峰,对《两地书》的市场前景都是抱有信心的。
事实上,1933年4月《两地书》一上市,便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极为成功的畅销书。从4月到年底,该书共印刷9次,总印数达6500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惊人的销售量。查《鲁迅日记》,仅仅在1933年,鲁迅因出版该书获得的版税收入高达1625元,极大地缓解了鲁迅窘迫的家庭经济困难。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传记文学》杂志“长篇连载”栏目征稿启事
自2013年《传记文学》杂志创设“长篇连载”栏目以来,先后连载了刘秋菊、蔡元培、冯积岐、鲁迅等人的长篇传记文章,忠实记录了传记人物的鲜明性格、光辉品质和骄人成就,因该栏目容量的丰富性、内容的纪实性、风格的传奇性以及形式活泼、文笔鲜活等特点,在广大读者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为进一步丰富本栏目,增加“长篇连载”的当代性和现实性,本刊公开向海内外征稿。
征稿要求:
1.来稿未在其他正式出版物(包括互联网)发表。
2.字数在10—20万字之间,文从字顺,符合发表要求。
3.内容必须真实、详尽,不可虚构,要叙述生动,可读性强。
4.来稿作者请写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以及身份证号码。
5.来稿三个月后未接到通知者,可自行处理。
6.来稿只接受纸质版,待作者接到刊用通知时,再用电子邮件投递电子版。
7.来稿在信封上请注明“长篇连载”字样。
来稿请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传记文学》杂志社编辑部 邮编:100029
电话:010-64813340 联系人: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