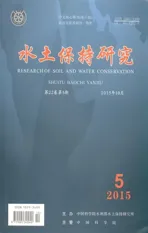LUCC研究进展及其对干旱区生态环境的意义
2015-04-20骈宇哲姜朋辉陈振杰吴洁璇
骈宇哲, 姜朋辉, 陈振杰, 吴洁璇
(南京大学 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23)
LUCC研究进展及其对干旱区生态环境的意义
骈宇哲, 姜朋辉, 陈振杰, 吴洁璇
(南京大学 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23)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变化的主要原因和核心主题之一。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LUCC研究成果,阐述了国际上LUCC研究在信息获取、数据处理、驱动力分析和模型建立等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分析了LUCC研究对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实现的研究意义,介绍了LUCC研究的新趋势,并对研究过程中现存的一些如信息获取过度依赖于3S技术,忽视实地调研等传统信息获取方式与新技术手段的结合、模型功能的欠完善、干旱区土地实现可持续利用缺乏相应的比较全面的科学理论指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健全LUCC研究理论体系,开展相应的理论建设将是未来整个LUCC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趋势。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 干旱区; 生态环境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类通过对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改变地球陆地表面的覆被状况,其环境影响不只局限于当地,而远至于全球。而土地覆被变化对区域水循环、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及陆地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适应能力的影响则更为深刻。20世纪90年代以来,LUCC作为全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日益受到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目前己成为国际上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开发与保护以及生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
LUCC是人类与地球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互作用的重要表现,发生于任何时空尺度[2],它不仅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生产力,客观反映人类改变地球生物化学循环、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产品与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再现了陆地表面的时空变化过程[3]。LUCC已逐渐成为诱发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4]。而全球变化是由一系列过程和现象各异的区域变化所构成,是区域生态与环境危机的集中反映[5],不同区域对全球变化的贡献程度与响应状况差异明显。因此,选择兼具全球意义和区域特色的局地进行个例研究,将有可能最后形成能代表不同区域类型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6],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全球变化的实际应用问题[7],为决策者提供更直接、更具体、更有效的方案,减少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研究意义。
干旱区土地覆盖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干旱区LUCC对全球环境变化具有反馈作用。干旱区LUCC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反馈作用是以累积性变化的方式体现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干旱区域的人类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地表反照率、水分以及养分循环,进而影响到区域和全球的气候变化规模[8]。如果全球范围内干旱区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都向恶劣的方向转化,其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9]。所以,干旱区LUCC研究自然也就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干旱区是地球上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之一。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干旱区域由于自然、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开发利用的强度和规模不断加大。然而,土地利用/覆被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水和土壤的质量以及区域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9]。对于干旱区而言,结构简单,生态功能低下的荒漠植被类型,荒漠化面积大且具有较快的发展速度,生态系统稳定性差,多呈过渡类型的土地类型,高度的依赖于水资源等特征,使干旱区生态系统具备了脆弱生态系统的一切性质,对自然或人为的干扰,尤其是对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干扰极为敏感。任何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都将引起整个区域景观组成和结构发生变化,结果会导致景观发生明显的破碎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干旱区的稳定性,也将限制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10]。因而,开展干旱区的LUCC研究工作能够在保护干旱区生态环境、合理规划干旱区土地利用、实现干旱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多个层面上发挥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
1 LUCC研究现状
LUCC作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关键所在,对其展开相应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国际社会对全球变化影响的认知和理解。因此,过去的几十年间,国内外高校与科研组织对LUCC研究的关注度一直在提升。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数据库与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分别以LUCC为搜索词查询得知,国内外文献库中关于LUCC的文章呈逐年攀升趋势(图1)。本文将从LUCC数据来源和信息的提取及处理、土地利用/覆被分类和LUCC的驱动力分析和模型研究3方面阐述LUCC的研究现状。

图1 以LUCC研究为题的国内外文章发表数量变化趋势
1.1 LUCC数据来源和信息的提取及处理
LUCC研究需要配以一定精度和深度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数据和信息来用于反映LUCC变化的过程与机制,开展LUCC驱动力的分析和影响评价研究。LUCC数据选择主要基于一些诸如政策变动、气候异常等历史事件的记录资料和一些卫星遥感影像。由于资源卫星影像具有成本低、获取相对容易且可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择不同时空尺度的遥感数据等优势,所以当前世界范围内LUCC研究的信息和数据来源大都源于对各类遥感卫星数据、遥感影像的解译。
但是,在对遥感图像解译的过程中,研究者本身图像判读能力、地学知识掌握程度以及图像本身存在的误差,导致单纯的使用遥感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LUCC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化过程和趋势。所以,如果研究过程中数据和信息提取过度依赖于3S技术,忽视实地调研等传统信息获取方式与技术手段的结合将会使得研究结果与实际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近年来国内外的LUCC研究多采用将遥感数据与野外调查数据、统计资料等多数据源复合分析,在图像的处理过程中更加注重了野外调查与室内解译的结合。张飞等[11]先对遥感影像进行预判,制定出野外考察的路线,然后按照指定的路线对研究区域进行调查,结合地形图,运用GPS定位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景观进行采点记录,并确定景观类型。最后在室内应用PCI图象处理系统对影像数据进行解译,得到研究区不同时期的景观类型图,对各景观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最后进一步分析研究区景观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充分体现了多数据源复合分析的思想。闫正龙等[12]以遥感影像数据为背景,结合解译标志库,采用人机交互的方法对土地利用信息进行逐级提取和赋值,同时基于GPS的野外验证方法对解译结果进行修正完善,最终得到符合精度和统一分类的土地利用现状专题图。Ruelland等[13]在马里3个试验区的土地覆被变化模型和驱动力的研究中,同样以卫星遥感数据为基础,运用GPS(±4M)在每个试验区采100个野外观测点记录确定景观类型,在此基础上对卫星遥感影像的解译结果进行修正改善,增强了分析结果的可信度。Tsegaye等[14]通过综合遥感卫星数据、野外观测以及当地居民提供的信息研究埃塞俄比亚北部干旱半干旱区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从而确保了分析结果总体上符合了该地区实际上的LUCC时空变化过程。试验结果表明,野外调查与室内解译能更好地检验遥感判读的正确率,并对判读数据进行室内修正,从而提高分析的精度,准确反映LUCC变化的过程与机制。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搜索库,以LUCC为搜索词查询得知,以遥感为技术支撑的LUCC研究多达103篇文章(图2),占所有文献的比例为25.50%,这表明,遥感作为一种新兴的对地观测技术,其在LUCC的研究中已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图2 基于web of science文献搜索库的不同学科领域内LUCC文章发表数量
1.2 土地利用/覆被分类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划分应遵循相似的社会、环境条件以及产生相似LUCC模式的相似人类驱动力[15]。世界上各干旱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差异导致各干旱区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类型不尽相同。如热带沙漠气候条件下的土地类型多以荒漠为主;热带草原气候条件下的干旱区地表覆被为草、灌木,土地类型多以草地为主;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的干旱区土地类型较为复杂,有耕地、草地、荒漠戈壁等。因此,国际上干旱区域LUCC研究中的土地利用/覆被分类方法比较多样。当前应用较多的土地利用/覆被分类方法仍是一些算法成熟、操作简单的传统分类方法,如目视解译、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相对于传统分类法,近年来出现的新分类方法,如决策树分类法、综合阈值法、专家系统分类法、多特征融合法、神经网络分类法以及基于频谱特征的分类法等,具有能够更准确地提取出目标地物的优点。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传统分类方法通常结合新方法。如Wentz等[16]基于多源数据对干旱城市环境下LUCC的研究中对专家系统法和目视解译法的综合使用。
国内的干旱区LUCC研究中,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划分多采用中科院的土地资源分类系统(将土地利用与覆被分为耕地、林地、水域、草地、城乡工矿居民用地、未利用地6个Ⅰ级类,25个Ⅱ级类以及针叶林地、阔叶林地、针阔混交林地3个Ⅲ级类)和国土资源部的国家级土地利用与覆被分类系统(将土地利用与覆被分为耕地、林地、水域、草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湿地7个Ⅰ级类,26个Ⅱ级类以及针叶林、阔叶林、混生林3个Ⅲ级类)。但是这两种分类系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土地分类系统过分依赖特定的遥感数据源,造成系统的通用性不强;难以适应不同目的的相关研究等。所以,当前的LUCC研究过程中,大部分研究者在采用这两类分类系统的同时多结合研究区域的土地变化状况、景观变化等实际情况。如窦燕等[17]研究和田河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过程中,在采用国家土地利用与覆被分类系统的同时,结合和田河流域草地分布特点,即在高山区或河流旁覆盖度高,荒漠和绿洲带分布有低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覆盖面积很少且典型性不强,容易误分成高覆盖度草地或低覆盖度草地的特点,将草地的二级分类划分为天然牧草地(高覆盖度草地)和荒漠草地(低覆盖度草地),既保证了准确描述地物特征,又保证了分类的精度,充分体现了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划分要结合研究区实际的重要性。
1.3 LUCC的驱动力分析和模型研究
1.3.1 LUCC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动力学研究的核心是驱动力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关系。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驱动力与LUCC的关系来建立经验模型,为定量化预测土地利用变化服务。驱动力是导致土地利用方式和目的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既有自然系统力,也有社会经济系统力。刘纪远等[18]将LUCC时空过程驱动因子总体划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并且认为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累积效应,社会经济因素对LUCC过程的影响相对活跃。这就间接表明了:由于区域性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差异,土地利用/覆盖系统的变化机制的复杂性以及其变化的空间和时间尺度难以把握,因此进行全面综合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十分困难。
近年来,大量的案例与实证研究推动了LUCC过程驱动机理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完善。但是,当前国内外的LUCC驱动力的分析方法总体仍以模型法为主。这些模型方法大体上可以综合为:基于经验的统计模型、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元胞自动机模型、基于Agent模型)、最优模型和综合/混合模型。但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几类模型中没有一种是完美的,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适合解决的问题。学者蔺卿[19]、韩超峰[20]等研究总结认为:基于经验的统计模型能够简化问题,抓住复杂系统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却面临着因变量量化的难题,并且建立的关系并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对于那些有详细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记录的地区,可以考虑使用统计模型。而相对于经验的统计模型而言,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更适于研究土地利用系统对LUCC的原因和结果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混合模型相对于前两者,通过将不同的建模技术综合起来使用,对于不同的问题,综合不同的建模方法,从而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手段。因此,建立综合性模型无论在当前还是以后都将是LUCC驱动力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1.3.2 LUCC模型研究 LUCC研究中,构建LUCC模型有助于深刻理解土地利用系统动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平台,LUCC模型在未来LUCC情景模拟和预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十多年来,众多学者基于不同目的构建了多样化LUCC模型。目前,最常用的LUCC模型可细分为:空间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元胞自动机模型、基于主体的模型以及综合模型等。
唐华俊等[21]认为,近十多年来,LUCC模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还是在实践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理解LUCC变化系统的格局、过程和机制、评估LUCC的综合影响、为政府部分提供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赵睿[22]基于神经网络的元胞自动机支持下的干旱区LUCC模拟研究,以模拟干旱区的复杂土地利用转变为目标,以BP神经网络模拟的单元转变概率代替CA模型的一系列单元转变规则,建立一般意义上的CA模型,对干旱区绿洲LUCC做一空间转变单元的模拟分析,并对该区域未来用地状态做了预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Rouchier等[23]探讨了牧民和农民通过协商在干季找寻适宜牧场问题。随着人们对LUCC模型研究的加深,LUCC模型的功能和作用正呈现多样化趋势,研究不同时空尺度的反馈机制必将是未来LUCC模型的新焦点,人类—环境关系的综合研究仍然是未来土地变化科学中的难点和焦点之一,多尺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将是LUCC模型的新要求,而模型验证则始终是LUCC模型的挑战。当前LUCC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仍是研究LUCC时空变化格局,模型发展正经历从单一的非空间模型向非空间模型和空间模型融合的演进过程,但多数模型只重视空间变化机制研究,而对时间机制考虑不足。此外,利用模型处理土地利用/覆被系统的多尺度特征以及实现模型方法的综合也将是今后模型开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难点和挑战,国外的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很多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Kamusoko等[24]大胆尝试用元细胞自动模型模拟了津巴布韦未来直至2030年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状况;Koch等[25]使用Land SHIFT.R模型模拟了不同的草场管理政策对约旦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等。而相对于国外的研究,我国的模型研究在这些领域内,对全新的理论体系、关键技术和方法仍需要进一步澄清、突破和创新。
2 干旱区LUCC研究意义
2.1 干旱区LUCC变化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LUCC的生态环境效应因研究尺度的不同而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26]。全球尺度的环境效应研究侧重于LUCC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大气成分变化引起的气候变化,主要集中在对生物燃烧、牲畜等释放出CH4、土壤、肥料、生物燃烧释放出N2O等,人类活动使大气中CH4和N2O浓度增加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27];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环境效应研究则侧重于土地退化、水文过程、土壤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效应方面;局地尺度的土地利用环境效应则侧重于地方的生态环境变化[28]。正如邹亚荣等[29]所述:“土地利用变化可以引起许多自然现象和生态过程的变化,如土壤养分和水分的变化、地表径流与侵蚀、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了解区域生态环境乃至全球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干旱区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地表覆被简单、类型单一且质量较差,在人类和自然因素影响下的LUCC变化很容易引起不同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景观破碎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沙尘暴等。杨阳等[30]基于1985年、2000年和2008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对新疆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分析得出,农业开垦是新垦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力因素,草地面积减少是其他土地类型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盐碱地增多和沼泽减少反映了该地区存在因农业开垦而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现象。吉力力·阿不都外力等[31]对中亚地区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土开发,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延迟效应日益凸现,湖泊河流水质恶化,生物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土地盐碱化、沙化日益严重,沙尘暴和盐尘暴频发,农牧业遭到严重损失。陈亚宁等[32]在塔里木河下游断流河道输水的生态效应分析中发现:属大陆性暖温带荒漠干旱气候的塔里木河下游地区,气候干燥,多风沙天气,平均年降水量为17.4~42.0 mm,而平均年蒸发力高达2 500~3 000 mm,在1972年大西海子水库建成后,拦截了塔里木河,致使其下游321 km河道彻底断流,河流尾闾湖泊——罗布泊和台特玛湖分别于1970年、1972年干涸。河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到8~12 m,导致由地下水维系的天然植被极度退化,大面积死亡,土地荒漠化过程加剧,生态系统严重受损,夹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鲁克沙漠间的“绿色走廊”急剧萎缩。同时使得塔里木河下游已成为中国西部干旱区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由此可见,在干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人文、自然等因素作用下的土地类型的改变,很容易引起干旱区内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将限制区域内农业生产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2 LUCC研究与干旱区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目前人类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干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实现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的可持续利用将是干旱区谋求生存的最主要的途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目前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LUCC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干旱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可持续性,而且LUCC研究也关系到区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和行动的有效实施[33]。这一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结构的持续性、土地利用方式与方法的可持续性、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过程的可持续性、实现可持续土地利用的对策与途径等。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西部干旱区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持续攀升,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土地问题[34]。此外,纵观我国加入WTO后的10年,在食物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目标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的驱动机制和未来情景等。这些问题和挑战都必将导致LUCC成为我国西部干旱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可持续发展的焦点。因而在LUCC研究与可持续发展这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开展了很多研究工作。早在21世纪初,陈百明[35]阐述了中国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分区方案的制定,并根据分区基本依据,包括以自然特征和利用状况的相对一致性,注重使所划分的区域之间在重要指标或相同指标的阈值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性,并兼顾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在全面分析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特性、生态环境条件、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利用管理措施等基础上,进行了全国土地利用分区。最终全国共划分出10个土地利用区域,作为制定区域性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分区范围。同一时期,刘彦随等[36]指出LUCC研究目标和内容选择,应围绕“可持续发展重点问题—人类驱动力—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景—可持续发展科学决策”这一主线,并需要区分不同的时空尺度和要点,关键在于揭示人类活动多因子驱动下土地供求关系、程度变化及其效应机制,进而提出在食物、资源和生态安全及其经济持续增长等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约束下的中国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科学决策与综合调控体系。
但目前对于世界范围内干旱区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而言,成果尚少,我国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指标体系的建立方面。多数的LUCC研究中,针对干旱区如何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方面研究的相关工作尚未大规模开展。
3 结 论
(1) 数据获取应注重新技术与传统方法的结合。3S技术的广泛应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的获得,以及各种图像处理软件的开发和应用等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获取的精度和速度。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LUCC研究出现过度依赖于3S技术的现象。但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3S技术在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获取以及信息提取方面难免存在不同情况的错误和误差。因此,仅仅依赖于3S技术未必能准确反映一个区域的LUCC过程。所以,LUCC研究过程中把野外考察、实地访问等传统方法与当前的新技术新手段结合将是今后LUCC研究中的必然选择。
(2)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驱动力与LUCC的关系来建立经验模型,为定量化预测土地利用变化服务。干旱区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研究正是要立足于这一出发点,通过研究,建立模型,指导干旱区正确预测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干旱区土地利用实现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结构的持续性、土地利用方式与方法的可持续性、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过程的可持续性、实现可持续土地利用的对策与途径等可持续发展目标。
(3) 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土地利用系统的尺度依赖性、尺度放大问题以及模型方法对特定学科的依赖性等问题,决定了在LUCC模型研究过程中仍需要注意利用模型处理土地利用/覆被系统的多尺度特征以及实现模型方法的综合。同时这也给未来的模型发展提出了要求与挑战。如前所述,在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型发展中,研究不同时空尺度的反馈机制必将是未来LUCC模型的新焦点,人类—环境关系的综合研究仍然是未来土地变化科学中的难点和焦点之一,多尺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将是LUCC模型的新要求,而模型验证则始终是LUCC模型的挑战。
(4) 目前,LUCC是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前沿的核心问题。世界范围内的干旱区大都面临着落后的经济、脆弱的生态环境等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干旱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对干旱区开展大规模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5) 干旱区LUCC研究缺乏健全的理论体系。对干旱区土地利用开展深入性和综合性的研究需要有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依托。而根植于人地关系理论的LUCC理论,多散见于地理学、农业经济学、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亟需系统归纳和总结,以便于形成统一的理论,指导干旱区的LUCC研究工作推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但就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而言,理论的多样性导致不同研究者出于各自目的对同一地区的研究结果互不相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建立的模型也不能应用于其他地区。导致理论不能解释不同尺度上的LUCC动力机制。随着LUCC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围的不断扩大,健全理论体系、开展理论建设将是未来干旱区LUCC研究乃至整个LUCC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趋势。
[1] GLP. Science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R]. Stockholm: IGBP Secretariat,2005.
[2] Nd T B, Lambin E F, Reenberg A. The emergence of land change scienc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7,104(52):20666-20671.
[3] Foley J A, Defries R, Asner G P, et al. Global consequences of land use[J]. Science,2005,309(5734):570-574.
[4] 周广胜,许振柱,王玉辉.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适应性[J].地球科学进展,2004,19(4):642-649.
[5] 张国平,刘纪远,张增祥.近10年来中国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分析[J].地理学报,2003,58(3):323-332.
[6] 史培军,王静爱,陈婧,等.当代地理学之人地相互作用研究的趋向:全球变化人类行为计划(IHDP)第六届开放会议透视[J].中国学术期刊文摘,2006,61(9):2.
[7] Giupponi C, Ramanzin M, Sturaro E, et al. Climate and land use changes, biodiversity and agri-environmental measures in the Belluno province, Ital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2006,9(2):163-173.
[8] Lioubimtseva E, Cole R, Adams J M, et al. Impacts of climate and land-cover changes in arid lands of Central Asia[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2005,62(2):285-308.
[9] 黄青,孙洪波,王让会,等.干旱区典型山地—绿洲—荒漠系统中绿洲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J].中国沙漠,2007,27(1):76-81.
[10] 李义玲,乔木,杨小林,等.干旱区典型流域近30 a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景观破碎化分析:以玛纳斯河流域为例[J].中国沙漠,2008,28(6):1050-1057.
[11] 张飞,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丁建丽,等. 干旱区绿洲土地利用/覆被及景观格局变化特征:以新疆精河县为例[J]. 生态学报, 2009,29(3):1251-1263.
[12] 闫正龙,黄强,畅建霞,等.基于3S技术的塔里木河干流土地利用动态监测[J].水土保持学报,2008,22(1):190-193.
[13] Ruelland D, Levavasseur F, Tribotté A.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land-cover changes since the 1960s over three experimental areas in Mali[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 Geoinformation,2010,12(S1):11-17.
[14] Tsegaye D, Moe S R, Vedeld P, et al. Land-use/cover dynamics in Northern Afar rangelands, Ethiopia[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2010,139(1/2):174-180.
[15] 刘新卫,陈百明,汪权方.国内LUCC研究进展综述[J].土壤,2003,36(2):132-135.
[16] Wentz E A, Stefanov W L, Gries C, et al.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mapping from diverse data sources for an arid urban environments[J]. Computers Environment & Urban Systems,2006,30(3):320-346.
[17] 窦燕,陈曦,包安明.近40年和田河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J].干旱区地理,2008,31(3):449-455.
[18] 刘纪远,邓祥征.LUCC时空过程研究的方法进展[J].科学通报,2009,54(21):3251-3258.
[19] 蔺卿,罗格平,陈曦.LUCC驱动力模型研究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05,24(5):79-87.
[20] 韩超峰,陈仲新.LUCC驱动力模型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08,24(4):365-368.
[21] 唐华俊,吴文斌,杨鹏,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模型研究进展[J].地理学报,2009,64(4):456-468.
[22] 赵睿,丁建丽,张飞.基于神经网络的元胞自动机支持下的干旱区LUCC模拟研究: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07,14(1):151-154.
[23] Rouchier J, Bousquet F, Requier-Desjardins M, et al. A multi-agent model for describing transhumance in North Cameroon: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rationality to develop a routin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1,25(3/4):527-559.
[24] Kamusoko C, Masamu A, Bongo A, et al. Rural sustainability under threat in Zimbabwe-Simulation of future land use/cover changes in the Bindura district based on the Markov-cellular automata model[J].Applied Geography,2009,29(3):435-447.
[25] Koch J, Schaldach R, Köchy M. Modeling the impacts of grazing land management on land-use change for the Jordan River region[J]. Global & Planetary Change,2008,64(3/4):177-187.
[26] 李锐,杨勤科,温仲明,等.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环境效应研究综述[J].水土保持通报,2002,22(2):65-70.
[27] 赵米金,徐涛.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环境效应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05,12(1):43-46.
[28] 宋乃平,张凤荣,王磊,等.我国土地利用/覆被研究的热点与应用发展问题[J].地球信息科学,2008,10(1):60-66.
[29] 邹亚荣,张增祥,周全斌,等.中国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2):222-227.
[30] 杨阳,张红旗.近20年来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分析[J].资源科学,2009,31(12):2029-2034.
[31] 吉力力·阿不都外力,木巴热克·阿尤普.基于生态足迹的中亚区域生态安全评价[J].地理研究,2008,27(6):1308-1320.
[32] 陈亚宁,张小雷,祝向民,等.新疆塔里木河下游断流河道输水的生态效应分析[J].中国科学,2004,34(5):475-482.
[33] Peng G, Ferräo M, Sedano F. Land cover assessment with MODIS imagery in southern African Miombo ecosystems[J].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2005,98(4):429-441.
[34] 谢余初,巩杰,赵彩霞,等.干旱区绿洲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响应:以甘肃省金塔县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2,19(2):165-170.
[35] 陈百明.基于区域制定土地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的分区方案[J].地理科学进展,2001,20(3):247-253.
[36] 刘彦随,陈百明.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3):324-330.
Review of Research Advances on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Environment in Arid Zone
PIAN Yuzhe, JIANG Penghui, CHEN Zhenjie, WU Jiexuan
(JiangsuProvincialKeyLaboratoryofGeographic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wa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and core subject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UCC research results, we elaborated the latest LUCC research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data processing, driving force analysis and model develop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UCC study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rid regions was analyzed. Then, we introduced the new tendency of LUCC research and pointed out some problems in such process, for instance, excessively relying on 3S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he neglecting union between traditi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ways a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means. Moreover, the imperfect function of LUCC model, the deficiency in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theory to instruct arid area l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etc., also were indicated in this research. We think that theory exploration will be the key to the research of LUCC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its guidance to the direction of LUCC study.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LUCC); arid zo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014-10-16
2014-11-10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2BAH28B02)
骈宇哲(1989—),男,陕西铜川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GIS开发与土地利用。E-mail:bianyuzhe1989@163.com
陈振杰(1974—),男,陕西陇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空间信息处理研究。E-mail:chenzj@nju.edu.cn
F301.24; X17
1005-3409(2015)05-035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