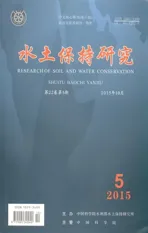耕作与施肥对甘蔗地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2015-04-20何瑞清王百群
何瑞清, 王百群,2, 张 燕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 712100)
耕作与施肥对甘蔗地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何瑞清1, 王百群1,2, 张 燕1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2.中国科学院 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土壤侵蚀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 杨凌 712100)
通过野外调查与室内分析,研究了云南蒲缥甘蔗地赤红壤不同耕作与施肥土壤剖面微生物量碳、氮特征。结果表明:不同耕作与施肥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均有一定影响,其中耕作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较为一致,表现为免耕>翻耕。施肥对0—20 cm土层中微生物量碳的影响表现为翻耕施肥>翻耕,对20—40 cm,40—60 cm土层中微生物量碳的效应呈现为翻耕>翻耕施肥,而施肥对土壤微生物量氮影响则与其对微生物量碳的效应相反。耕作和施肥对各个土层土壤微生物商具有显著的影响(p<0.05),表现为免耕>翻耕,翻耕施肥条件下0—20 cm土层的微生物商稍高于翻耕,而其他土层均为翻耕>翻耕施肥;土壤微生物量氮与全氮的比值与微生物量氮的变化趋势相近。在不同的耕作和施肥条件下,免耕有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量,施肥在一定程度上也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量。
耕作; 施肥; 土壤微生物碳; 土壤微生物氮
土壤微生物量是土壤有机质的活性部分,是土壤中最活跃的成分,虽然只占土壤有机质的3%左右[1],但对养分的供应、转化与循环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其变化可反映土壤耕作制度和土壤肥力的变化以及土壤的污染程度[2-4]。
耕作和施肥影响土壤通气、透水和温度等性质,进而影响土壤微生物量含量及其在土壤中的分布[2,4-7]。Follett等[8]研究了耕作对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西部高平原区土壤微生物量动态的影响,结果表明,耕作降低了土壤微生物量的水平;并且,微生物生长的碳有效性随着耕作强度的增加而降低。Dinesh等[9],Powers[10]的研究也表明耕作会引起土壤物质水平的变化,从而影响土壤微生物活性及其微生物量。张洁等[11]的研究表明,长期耕作导致坡耕地土壤微生物碳、氮具有不同程度的坡下富集现象。免耕能够提高农田系统中土壤微生物的丰富度、增加土壤微生物量含量。Chilima等[12]研究了氮肥的施加和耕作对黑土和红壤中SMBC影响,研究表明氮肥的施加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碳含量。侯化亭等[13]进行田间试验,研究了施肥水平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影响,表明施肥水平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具有显著影响。虽然国内对不同耕作与施肥下微生物量动态等方面的研究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中国亚热带赤红壤生态景观上,对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报道尚少。该研究以云南喀斯特地貌的保山蒲缥为例,通过对典型样区S型采样分析,研究不同耕作及施肥下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以期阐明耕作及施肥对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影响,为科学经营和管理土地,维持和提高亚热带赤红壤地区土壤肥力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选取地处云南喀斯特地貌的保山蒲缥为研究区域,蒲缥位于东经99°02′,北纬24°58′,海拔1 200~1 500 m;年平均气温18.5℃,极端最高温31.7℃,低温-1℃;年日照时数2 300~2 500 h;年降水量1 200.00 mm,土壤类型以赤红壤为主,种植的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甘蔗等。
1.2 样品采集与培养
分别选择长期免耕、翻耕、翻耕施肥的甘蔗地作为样地。每个地块按S型采样法挖取5个60 cm深的剖面,每个剖面分层取样,每20 cm作为一个采样层,即0—20 cm,20—40 cm,40—60 cm三个土层。将各点采取的样品按层次充分混匀并剔除土壤中的植物根系及残体,土壤样品带回实验室风干,一部分土样过2 mm筛,一部分土样过0.25 mm筛备用。
为消除温度与水分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对风干土样进行预培养。称取120 g风干土样加入去离子水,使土壤含水量保持在田间持水量的40%左右,置于恒温箱中25℃下培养7 d。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主要测定指标包括土壤有机碳(SOC)、全氮(TN)、微生物生物量碳(SMBC)和微生物氮(SMBN)。
土壤有机碳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全氮采用半微量开氏法[14],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15-16]。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9.0和Excel 2007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应用Origin 9.0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耕作与施肥下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
不同耕作与施肥处理条件下土壤微生物量碳(SMBC)含量在不同土层都存在差异(图1),显示为20—40 cm>0—20 cm>40—60 cm,每层土壤微生物量皆小于200 mg/kg,0—20 cm土层中SMBC含量变化范围为113.05~133.84 mg/kg,20—40 cm,40—60 cm土层中SMBC含量的变化范围分别是136.71~149.47 mg/kg和95.56~132.49 mg/kg。不同的耕作措施也对其有影响,在0—20 cm土层中,翻耕施肥>免耕>翻耕,免耕对SMBC含量显著(p<0.05)高于翻耕。王晓凌等[17]也曾指出,在免耕条件下SMBC含量高于翻耕条件下SMBC含量。40—60 cm土层中翻耕的土壤SMBC含量显著低于免耕的土壤,而较翻耕施肥的土壤高,这与张洁[11]、牛新胜[18]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翻耕不利于SMBC的保持,翻耕使得土壤浅层微生物暴露于空气中而失去保护作用,并且翻耕后改变了土壤孔性、湿度、温度等条件,从而改变了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的环境,进而影响SMBC含量。

图1 土壤微生物量碳随土层深度的变化
2.2 不同耕作与施肥下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
耕作方式及施肥处理对土壤微生物量氮(SMBN)含量有显著影响(p<0.05)(图2)。0—20 cm,20—40 cm和40—60 cm土层中SMBN含量的变化范围分别是10.69~20.81 mg/kg,13.27~31.28 mg/kg和9.91~16.14 mg/kg,与徐华勤等[19]得出的广东韶关赤红壤表层土壤(0—20 cm)SMBN主要分布在12.15~32.53 mg/kg之间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本试验中各层土壤的SMBN含量均表现为免耕>翻耕,这与张洁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0—20 cm土层中SMBN表现为免耕>翻耕>翻耕施肥;20—40 cm土层中的SMBN为翻耕施肥>免耕>翻耕;40—60 cm土层中的SMBN呈现为免耕>翻耕施肥>翻耕。除翻耕施肥土壤的0—20 cm土层中SMBN低于仅进行翻耕过的土壤之外,翻耕施肥土壤的20—40 cm,40—60 cm土层中SMBN显著高于翻耕的。徐阳春等[20]的研究也表明施用肥料的SMBN含量较施用肥料的高。这可能是免耕使作物残余物在土壤中累积,导致土壤微生物活性和生物量、土壤碳及养分等的增加,改善了土壤水分、结构,并可维持土壤质量。肥料的施加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为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有利条件,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增加SMBN含量。

图2 土壤微生物量氮随土层深度的变化
2.3 不同耕作与施肥下SMBC/SOC,SMBN/TN
SMBC与SOC的比值被称为土壤微生物商。有研究表明,土壤微生物商在0.5%~4.0%之间[3,21]。本研究中,SMBC/SOC为0.9%~1.5%。不同耕作方式之间的SMBC/SOC差异小于SMBC含量的差异。本研究中不同土层的微生物商因耕作、施肥不同而异。就同一土层而言,0—20 cm土层的土壤微生物商是免耕>翻耕施肥>翻耕,这与何莹莹等[22]的研究结果一致;20—40 cm土层的微生物商呈现为翻耕>免耕>翻耕施肥,而40—60 cm土层则表现为免耕>翻耕>翻耕施肥;翻耕施肥的土壤微生物商较免耕均降低。SMBN与全氮的比值(SMBN/TN)与微生物生物量氮的变化趋势相近,与孙凤霞等[23]在长期定位施肥分析中得到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中各层土壤SMBN/TN均为免耕>翻耕,20—40 cm土层的SMBN/TN显著大于仅是翻耕过的。耕作和施肥对土壤微生物商及SMBN/TN的影响可能来源于其改变了土壤环境条件和土壤有机物质的投入,从而使SMBC,SMBN发生变化。

表1 不同耕作与施肥下甘蔗地SMBC/SOC,SMBN/TN %
3 结 论
耕作和施肥影响着土壤微生物量及其他性质。不同耕作与施肥下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特征差异显著,其中耕作对SMBC,SMBN的影响较为一致,均表现为免耕>翻耕。施肥条件下,0—20 cm土层中SMBC的含量表现为翻耕施肥>翻耕,20—40 cm,40—60 cm土层的SMBC的含量表现为翻耕>翻耕施肥。而施肥对SMBN影响则与其对SMBC的效应相反。不同土层的微生物商因耕作、施肥不同而异。与翻耕相比,翻耕施肥条件下,0—20 cm土层的微生物商稍高于翻耕的,其他土层的微生物商均表现为翻耕>翻耕施肥;翻耕的土壤的20—40 cm土层中微生物商稍高于免耕,其他层次表现为免耕>翻耕,翻耕施肥的土壤微生物商较免耕均降低。SMBN/TN与SMBN的变化趋势相近。在不同的耕作和施肥中,免耕有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量,施肥在一定程度上也利于提高土壤微生物量。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减少对土壤耕作及增加向土壤输入有机物质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土壤的生物肥力。
[1] 陶水龙,林启美,赵小蓉.土壤微生物量研究方法进展[J].土壤肥料,1998(5):15-18.
[2] 黄昌勇.土壤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3] 何振立.土壤微生物量及其在养分循环和环境质量评价的意义[J].土壤,1997,29(2):61-69.
[4] 陈国潮,何振立,黄昌勇.红壤微生物生物量C周转及其研究[J].土壤学报,2002,39(2):152-160.
[5] 周桔,雷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影响因素及研究方法的现状与展望[J].生物多样性,2007,15(3):306-311.
[6] 赵先丽,程海涛,吕国红,等.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研究进展[J].气象与环境学报,2006,22(4):68-72.
[7] 孙建,刘苗,李立军,等.不同耕作方式对内蒙古旱作农田土壤微生物量和作物指标的影响[J].生态学杂志,2009,28(11):2279-2285.
[8] Follett R F, Schimel D S. Effect of tillage practices on microbial biomass dynamics[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89,53(4):1091-1096.
[9] Dinesh R, Chandhuri S G, Ganeshamurthy A N, et al. Changes in soil microbial indi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following deforestation and cultivation in wet tropical forests[J]. Applied Soil Ecology,2003,24(1):17-26.
[10] Powers J S. Changes in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after contrasting land-use transitions in northeastern Costa Rica[J]. Ecosystems,2004,7(2):134-146.
[11] 张洁,姚宇卿,金轲,等.保护性耕作对坡耕地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07,21(4):126-129.
[12] Chilima J, Huang C Y, Wu C F.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trends in black and red soils under single straw application: effect of straw placement, mineral N addition and tillage[J]. Pedosphere,2002,12(1):59-72.
[13] 侯化亭,张丛志,张佳宝,等.不同施肥水平及玉米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影响[J].土壤,2012,44(1):163-166.
[14] 鲍士旦.土壤农化分析[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15] 吴金水,林启美,黄巧云,等.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测定方法及其应用[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
[16] 林启美,吴玉光,刘焕龙.熏蒸法测定土壤微生物量碳的改进[J].生态学杂志,1999,18(2):63-66.
[17] 王晓凌,陈明灿,张雷.不同耕作方式对土壤微生物量和土壤酶活性的影响[J].安徽农学通报,2007,13(12):28-30.
[18] 牛新胜,张宏彦,王立刚,等.玉米秸秆覆盖冬小麦免耕播种对土壤微生物量碳的影响[J].中国土壤与肥料,2009(1):64-68,73.
[19] 徐华勤,章家恩,冯丽芳,等.广东省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J].生态学报,2009,29(8):4112-4118.
[20] 徐阳春,沈其荣,冉炜.长期免耕与施用有机肥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磷的影响[J].土壤学报,2002,39(1):89-96.
[21] 何电源.中国南方土壤肥力及栽培作物施肥[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2] 何莹莹,张海林,伍芬琳,等.不同耕作方式对双季稻田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响[C]∥高旺盛,孙占祥.中国农作制度研究进展2008,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329-332.
[23] 孙凤霞,张伟华,徐明岗,等.长期施肥对红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微生物碳源利用的影响[J].应用生态学报,2010,21(11):2792-2798.
[24] 盛浩,周萍,袁红,等.亚热带不同稻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的剖面分布特征[J].环境科学,2013,34(4):1576-1582.
[25] 王小利,苏以荣,黄道友,等.土地利用对亚热带红壤低山区土壤有机碳和微生物碳的影响[J].中国农业科学,2006,39(4):750-757.
[26] 刘守龙,苏以荣,黄道友,等.微生物商对亚热带地区土地利用及施肥制度的响应[J].中国农业科学,2006,39(7):1411-1418.
[27] 张凤荣.土壤地理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8] 张俊民,蔡凤岐,何同康.中国的土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Effects of Tillage and Fertilization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in Sugarcane Field
HE Ruiqing1, WANG Baiqun1,2, ZHANG Yan1
(1.CollegeofNaturalResourcesandEnviron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2.StateKeyLaboratoryofSoilErosionandDrylandFarmingontheLoessPlateau,InstituteofSoilandWaterConservatio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andMinistryofWaterResources,Yangling,Shaanxi712100,China)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SMBC) and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SMBN) in latosolic red soil at Yunnan Pupiao were investigated to determine how they were affected by tillage and ferti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tillage and fertilization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were affected. The effects of tillage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were consistent, and showed no tillage>tillage. The influence of fertilization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in 0—20 cm was tillage fertilization>tillage, 20—40 cm and 40—60 cm were tillage>tillage fertilization, while effect of fertilization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contrasted with the effect of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The quotients of soil microorganism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in different tillage and fertilization and soil depth, and showed no tillage>tillage. Effect of tillage fertilization on soil microbial quotient of the 0—20 cm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illage, and the other soil layers were tillage>tillage fertilization. The ratio of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to total nitrogen was similar to the trend of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In different tillage and fertilization, no tillage would improve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 helpfully, also fertilization could improve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 in a certain extent.
tillage; fertilizati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nitrogen
2015-06-08
2015-07-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330852);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XDA05050504);国家自然科学资助项目(40301024)
何瑞清(1990—),女,云南保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壤有机碳氮循环研究。E-mail:hrqing8990@163.com
王百群(1968—),男,陕西渭南人,博士,副研究员,从事土壤有机碳氮循环研究。E-mail:bqwang@ms.iswc.ac.cn
S154.3;S158.3
1005-3409(2015)05-01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