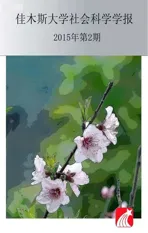偶然与生命
——沈从文小说生命意识形态的分析
2015-04-15武斌斌
武斌斌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偶然与生命
——沈从文小说生命意识形态的分析
武斌斌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鲁迅与沈从文是现代文学作家里少有的将生命意识上升到哲学高度的人,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复杂既表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生活”与“生命”的差异,也表现在以原始生命为基础的对生命美即神性的追求。面对这“不大会思索也不容许思索的生命”,本文着意从偶然、死亡、爱与死相邻的角度出发,分析沈从文生命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其中原始生命形态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为研究沈从文作品乡村与都市的二元对立形态提供一个道德评判角度外的新的视角。
沈从文;生活;生命;偶然
沈从文在《黑魇》、《水云》中分别提到:“‘生活’失去了人作为人的自己,也失去了生命力,人生便恢恢无生气。”,“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与情感乘除而来”[1];“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你后天的命运”,“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2]要理解沈从文关于生命意识的这些思考有必要对沈从文的自身经历,即其生命形态在其作品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和梳理。
一、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储存、觉醒和建立
在平凡的人生里书写传奇。探索沈从文的生命意识有必要对其自身生命意识的储存、觉醒与建立进行一番梳理:
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储存是从人性负面的角度开始进行启迪的,由于身处湘西边地,以及苗民的特殊历史地位,沈从文从小就看惯了苗民的随意被杀,抽签决定生死的行为更为其自在生命状态增添了宿命论的色彩,这种生命屠戮记忆的储存为其以后生命自主状态的实现储存了原始性的材料,也对“其一生对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投下了浓厚的阴影,并在此潜藏了对生命原始或自在状态中下宿命论的思考。
家族“再来一个将军”的梦想让破产后的沈家做出了让沈从文投身行伍的决定,而又由于年龄较小,与老残官兵留守辰州的军令让他免于全军被灭的惨剧。但这些偶然性因素的参与并没有让沈从文有死里逃生的惊骇,也没有唤起他对隐藏在这种偶然性因素中的社会变迁之大势的思考,对他来说这只是属于运气沉浮的范畴。沈从文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得益于姓 文的秘书的《辞源》、熊希龄家的书籍启蒙,以及在陈渠珍身边担任秘书的经历,也正是由于先前社会经验的积累与对不合理事情的观察、怀疑、独立判断,让他在对比中发现了“知识”即理性的价值。沈从文的一生都主张知识的获得必须要经过“大书”与“书本”的比较参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沈从文建立起了自己对生命意识形态的终极追求:对生命“神性”的思考与追求,具体到文学作品里即为爱与死共存、相融合的一种生命状态。
二、沈从文的生命形态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3]。分析沈从文生命形态的层次,我们一般只注意到其对“人性”的追求,一种生命由原始到自在再到自为的上升趋势,却容易忽略在这一上升趋势里“生命的原始状态”作为基础的重要性:“选山地为地基,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结合沈从文的作品进行分析,能够看到其对生命原始状态美好保留的回忆也能看到生命自在状态下社会性因素对生命原始纯真的破坏与对生命“神性”建立的期待。
(一)原始生命形态的美好回忆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乡村尤其是湘西边地总是给人人性美好的感觉,这得益于湘西环境的封闭和原始生命形态保存的完整。在这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居的山寨内”,仍保持者原始的部落氏族制度与原始习俗。原始生命的活力重点表现在爱的自由,沈从文深深地为这种爱所陶醉:在《神巫之爱》、《龙珠》、《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中,沈从文都有这种对原始生命的活力,都给与了赞扬与充分的美好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爱与死相邻”的观点。
但对这种原始的生命形态,沈从文并不取认同的态度,“虽不为人生琐细所激发,无失亦无得,然而‘其生若浮,其死则休’,虽近生命本来,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3]这种单调又终若不能忍受的原始生命形态由于没有“知识性的参与”或“理性判断的甑别”,而终究保留了许多不合理的因素:《渔》中家族仇杀的表现以及《月下小景》中“与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的野蛮风俗,让这种原始生命形态的美好参进了暴力性与悲剧性。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的出现并不影响沈从文对原始生命形态基础性作用的重视,在生命的原始状态里有着人之为人的自由,有人性未受污染的本来存在方式,正是这种人性之真的存在让沈从文的生命形态在上升阶段具有了抵御或消解人性异质力量的作用,并为生命自为状态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生命自在状态的印象式书写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自在生命的觉醒是伴随着对原始生命形态的破坏而进行的,具体表现为两种形态:一,原始复仇情绪的发泄;二,自在生命社会性思考的出现。原始复仇的发泄如《贵生》中的贵生放火后逃走,《生》里上演了十年的王九打到赵四的玩木傀儡戏。虽然表现出来复仇的不同形态,有消极有积极,但都是一种生命自在状态下的非理性的抉择。真正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与作者对社会性人为性的思考相结合的:《牛》描写了一个老农因牛伤腿后延医给牛治病,请人代工的焦急复杂心理,但等牛伤好后,正当老人对秋收充满喜悦之情时,牛却被官府征用,拉倒不知何处去。《菜园》中的菜农以种菜为生,去北京读书的儿子带着媳妇回家探亲却被官府请去当做共党杀害,双双陈尸校场,其母也耐不住孤独而悬梁自尽。正是由于作者将这种对自在生命状态的思考置入了社会性历史存在中,这种偶然才具有了意识性的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4]
与原始生命形态相比较,生命自在状态下“爱与死相邻”一则表现出了作者对偶然与死亡的关注,以及对此种状态下严肃生存的同情;二则强调了人为性的破坏对生命美感意识的消除,这种生命的美的压抑将在生命自为状态的理性思考中再次绽放。
(三)生命自为状态的呈现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因素都是由无穷多个社会因素制约、影响,都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愿望所从事的历史活动的结果,是由从事历史活动的各个人、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
沈从文的《边城》正可以体现这种单个意志相互冲突所形成的合力作用,从作家创作的角度出发,通过文学作品理想化状态下力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三种生命形态在这篇作品中的共存,连续与上升的姿态。生命原始状态的力的综合表现在傩送——翠翠——天保这组关系中:理想化状态下的合力表现为傩送与天保亲情之力的抵消,傩送对翠翠以及天保对翠翠爱情之力的抵消,综合的结果即表现为翠翠对傩送的爱情。而在天保出走遇到激流死去后出现了死亡的空缺的力,这种死与爱的结合实现了原始生命“爱与死相邻”的状态,似乎作品到此已经可以结尾,翠翠的等待已经具有了原生态的为“爱与死”的价值。但正是基于对原始形态的“爱与死为邻”的价值意义的否定,沈从文在此基础上植入了异质性的因素,形成了生命自在状态的破坏性趋势,即团总女儿的出现。在翠翠——傩送——团总女儿三者的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力的合力作用倾向于翠翠,但此时由于傩送对老船夫的误会(偶然性)以及船总顺顺的态度(想要碾坊)使得这种合力出现了复杂性的因素,这种生命自在状态的复杂表现出了人为性因素对“人性”(爱)的破坏。这种破坏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与甄别才能实现生命状态的上升和释放。傩送的出走既有死亡之力的助推,更有对异质性因素的反抗,所以具有了理性抉择的意义,而生命自为状态的实现表现为一种爱与死的融合,正是在此意义上翠翠的等待才获得了理性的自为的意义,即一种生命意志的理想状态,“爱与死为邻”到此已不重结局而只重呈现,这种生命形式的实现只是想“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生命的原始状态表现为“爱与死相邻”的无意识表达,而生命自在状态下的爱则由于受到人为性因素的破坏而处于被动状态,那么只有到了生命的自为状态才能表现出爱与死的交融的状态。
而对都市作品的表达沈从文强调的是自在到自为的无法实现,这又表现为两类:一,《八骏图》类的上层知识分子由于缺乏生命的原始性本真而无法实现生命意识的自为,对此作者予以嘲讽的态度。二,对自在向自为上升受挫之后向原始的回归。《都市一妇人》中的将军遗孀有生命自在状态下“复仇的满足”,也有生命自为意识的觉醒,但这种觉醒却表现为一种破坏性因素(弄瞎了爱人的眼睛),但即便如此在返回老家的途中他们还是因轮船失事而双双葬身水底,而他们朋友的评论是“死了也好,这收场不坏。”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是寄予一定程度肯定与同情的。
总而言之,沈从文对乡村生命状态的言说呈现为一种上升趋势,表现为原始——自在——自为的过渡,原始生命形态作为其建立人性小庙的根基不可或缺。而在都市生活表达中,沈从文对生命意识形态的表达却表现为自在——自为的无法实现,或自为受挫后对原始回归的肯定。沈从文在此似乎暗示着生命从自在上升到自为的过程中必须以生命的原始形态为根基。
[1]沈从文.绿魇[M]//沈从文散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沈从文.水云[M]//沈从文散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沈从文.沈从文习作选代序[M]// 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4]刘曙光.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J].湖湘论坛,2009(3).
[责任编辑:黄儒敏]
2015-02-03
武斌斌(1989-),男,山西吕梁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6
A
1007-9882(2015)02-01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