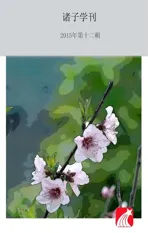《文選》李注所引《莊子》及《莊子》注研究
2015-02-07劉濤
劉 濤
《文選》李注所引《莊子》及《莊子》注研究
劉 濤
《文選》李善注引用了大量的《莊子》原文和諸家注釋,雖然他對原文進行了删節改造,但仍具有校勘、輯佚價值,且這些佚文對探究五十二篇本《莊子》原貌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在諸家注釋中,司馬彪注保留最多,經過與《經典釋文》相關部分所引用的注釋的對比,發現二者有很大不同,這可能涉及司馬彪注的兩個版本,且其注釋風格也不似《經典釋文》所展現的那樣幾乎完全是文字訓詁,在李善注所引用的注釋中,體現了他重視解釋《莊子》義理的一面。
關鍵詞 《文選》李善注 《莊子》 司馬彪《莊子注》 版本 義理
中圖分類號 B2
《文選》李善注世稱賅博,其所徵引之書多達一千六百餘種,但流存至今的十不一二。大量的古書逸注,後人唯有通過此書方可上越千年,窺見一鱗半爪,李注文獻價值之大,於此可知。而據筆者統計,李善注稱引《莊子》即有七百餘處,其中不少逸出今本三十三篇之外,除了提供一些較早的校勘材料,對輯佚也有很大的幫助;另外還大量保存了司馬彪、郭象、向秀、徐邈、李頤、李軌等諸家注釋,尤以司馬彪注最多最富價值。據有關文獻記載,唐前注《莊》之作多達數十種,除郭象注完整流傳而外,其餘多賴陸德明《莊子音義》之引録而得以部分保存。《文選》李注雖然不像《莊子音義》是專門為《莊子》而作,但它所保留的諸家注釋條目之多卻僅次於《莊子音義》。雖然就絶對數量來講,李善注中的《莊子》注釋與後者不可同日而語,但由於二書宗旨不同,取捨自然相異,最後呈現出的面貌也就不一樣。而李善注所展現的這一别樣的面貌,對於研究魏晉六朝莊子學意義匪淺。下面主要就李注所反映出的莊子學做一些闡述。
一、 李注所引《莊子》原文之校勘價值
《文選》李善注稱引《莊子》之處如此衆多,但並不能完全忠實於《莊子》原文,若要資以校勘,需要予以小心考辨。撇開一些明顯錯誤的條目不論,注文對《莊子》原文常常截取縮略加以整合,以就所注之文。有時所引内容相同,而具體文字則有所不同,對此須倍加謹慎。
如張衡《東京賦》末云“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兹”,李善注:“《莊子》曰: 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第68頁。以下所引《文選》及李注,如無特殊説明,皆據此本。李善引此句注釋“大庭氏”三字,典出《莊子·胠篋》,而今本原文為:“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96年影印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第162頁。以下所引《莊子》及郭象注,如無特殊説明,皆據此本。兩相比較,即可看出李善注的特點與用意,如此多的上古君王,無須全部羅列,於上古時代的具體描述亦不須徵引,只截取了結論“若此之時,則至治已”,因為對於理解《東京賦》文句的意義只須知道大庭氏之時乃“至治”之世即可。李善此注甚是精當,可謂善注釋者。
又如班固《東都賦》“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李善注:“《莊子》曰: 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尚富貴也。”而張衡《東京賦》“藏金於山,扺璧於谷”句下李注則作:“《莊子》曰: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兩處注釋所引用的是同一句話,但《東都賦》注作“捐”而《東京賦》注作“藏”,且都與所釋正文一致,這就不免産生了一些問題。今本《莊子》作“藏”,王叔岷《莊子校詮》引述《東都賦》李注後云:“古人引書,往往隨正文改字,未可盡信。”*王叔岷《莊子校詮》,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17頁。所言甚是,然未必適用於此處,否則為何只改第一字為“捐”,不改第二字為“沉”以隨正文呢?這豈非扞格不通?那麽可能是李善所用的古本就作“捐”,他並没有作任何改動?據陳景元《南華真經闕誤》記載,當時他所見的九種古本中,張君房本作“沉珠”*陳景元《南華真經闕誤》,收入方勇主編《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一六册,據明正統《道藏》本影印,第430頁。,但並没有作“捐金”的。而且,陸德明《莊子音義》也未記載有異文“捐金”,今存衆本也不見有作“捐金”的。那麽,有古本作“捐”這種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因此,也就不可據以校勘今本。
再如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懷湘娥”,李善注:“《莊子》曰: 馮夷得道,以潜大川。”至謝惠連《雪賦》“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句下李注則為:“《莊子》曰: 夫道,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這兩處要點在於注出馮夷與河川之關係,而《莊子》原文意在突出道之於馮夷的重要性,如果徑直照録原文“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就會使人不得要旨,故而需要加以處理。而兩處的處理方式竟然不同,單獨看都很合理,但考慮到是出自一人之手,就不免有隨意之嫌。且後半句一作“潜”,一作“遊”,這就不是隨意二字所能解釋得了的,可能涉及版本問題。如果是版本不同,那就需要解釋為何要用不同版本。而況今存衆本包括宋元諸本此處皆作“遊”,只有《淮南子·齊俗訓》作“馮夷得道,以潜大川”,可以作為某一古本作“潜”的旁證。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古本,那麽李善《西京賦》注所用的版本應該就是出自這一系統。而李善注文竟與《淮南子》此句絲毫不差,其出自《淮南子》而誤記為《莊子》也不無可能。考李善對《大宗師》此段類似語句的改造還有兩處,分别作:“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宫”(揚雄《羽獵賦》注),“夫道,傅説得之,以相武丁”(賈誼《鵩鳥賦》注)。與《雪賦》注手法如出一轍。如此看來,《西京賦》注應該出自《淮南子》,李善誤以為《莊子》,並非對原文改造是否一致的問題,也就没有版本不同、存在異文的問題了。
總之,李善注並非十分嚴謹,甚至有錯誤,用作校勘材料時尤須嚴格甄别。日本斯波六郎早就注意到李善注略字徵引、改動原文、顛倒順序的現象,而仍堅持認為李善“絶不改動引文文字”,並舉數例以説明,其理由是李善有見到古本的可能,且今本李善注已然經過後人篡改,並非最初模樣*[日本] 斯波六郎撰,權赫子、曹虹譯《李善〈文選〉注引文義例考》,《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四輯)》2011年6月。。本文的目的不在討論李善注的原本如何,而在其引文是否具有校勘價值,所以與斯波氏所論並無衝突,何況他的觀點本身就有些自我矛盾呢!
披沙揀金,偶或見寶,雖然李善注存在上述問題,但是不能説一點價值没有。江淹《雜體詩·謝光禄莊(郊遊)》云:“静默鏡綿野,四睇亂曾岑。”李善注:“《莊子》曰: 静默可以補病。”此語出於《莊子·外物》,今本作“静然可以補病”,“静然”二字不通,古今多有學者指出“然”字之誤,如宋代林自云:“然,當是默字之誤。”*禇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收入方勇主編《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二七册,據明正統《道藏》本影印,第160頁。陶崇道《拜環堂莊子印》也如此推測,宣穎《南華經解》及劉鳳苞《南華雪心編》則徑直改作“默”,但都止於推測,並没有確鑿的文獻證據。直到清末奚侗找到這條李善注作為證據,據以改正,馬其昶《莊子故》、錢穆《莊子纂箋》及王叔岷《莊子校詮》也都以為當作“默”。雖然江文通原詩作“静默”,此處李注乍看似有為遷就原文而改字之嫌,然而實際並非如此。“静”字自身即表示一種狀態,“然”字在“静”字下也是表示狀態,顯然重複,且習慣上也不見這種搭配組合;而《莊子》原文下句作“眥可以休老”,“眥”通“搣”,二字同是“摩”的意思*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據經韻樓原刻影印,第599頁。,反觀“静默”,義亦相近,“静默可以補病”,意謂安静沉默有益於疾病之調理,與下句按摩有助於延緩衰老同為一般的養生方法。“默”、“然”二字因為字形相近,所以導致訛謬。
魏文帝曹丕《與吴質書》有云:“年一過往,何可攀援?”李善注:“《莊子》: 北海若曰: 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虚,終則又始。”而今本作“年不可舉”,郭象注云:“欲舉之令去而不能。”可知郭本作“舉”,但這個解釋實際是不通的,何謂“舉之令去”?王叔岷也以為郭注未得“舉”字之真義,而以“與”釋之,云:“舉、與古通,《論語·陽貨篇》之‘歲不我與’,皇疏:‘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蓋釋與為待。《後漢書·馮衍傳》‘壽冉冉其不與’,注:‘與猶待也。’‘年不可與’,猶言‘年不可待’耳。”*王叔岷《莊子校詮》,第607頁。初看似乎信然,仔細分析,就會發現裏面存在嚴重的問題。其所舉二例中,“與”確為“待”之義,全句意謂時不我待,時間不等人,但套到“年不可待”上則主客顛倒,意謂“我不可等時間”,謬誤一目瞭然。《莊子》原文無論作“舉”抑或作“攀”,都是時不我待、歲不我與之意,作“年不可待”則於文意有悖。若作“攀”,則魏文帝此句正可反過來為莊書此句作注,攀援之,可使止,可使反,均與下句“止”字相契合。“攀”、“舉”二字字形也相近,極易致訛。馬融《長笛賦》李注有云:“熊經,若熊之舉樹而引氣也。”《莊子音義》則作“攀”,即同此例。因此,此處不無因《與吴質書》正文致訛甚至故意改字之可能,且作“攀”者只此一處,並無其他文獻可以互相驗證,所以一時未敢斷言原文必為“攀”,但以“攀”來解釋顯然更勝一籌,所以不敢不表而彰之,以俟來者。
二、 李注所引《莊子》佚文對探究郭象“以意去取”之價值
據《漢書·藝文志》及《經典釋文·序録》記載,《莊子》原有五十二篇,司馬遷《史記》云有十餘萬言。郭象刊落十九篇以成今本,由於其注“特會莊生之旨”,書成之日,即被奉為經典,大行於世,那些完本如司馬彪注本、孟氏注本反而逐漸退出人們的視界,最終失傳。然而幸運的是,斷圭碎璧,時時可見,晉唐古注、韻書類書之中尚有零星保存,異常寶貴。南宋王應麟始輯佚之,雖然只有三十九條,遠遠稱不上完備,但首開先河的貢獻不可泯滅。其後,有清一代,閻若璩、翁元圻等加功覆簣,以注釋的形式對王氏所輯進行補充;孫馮翼、茆泮林等繼其踵武,開始全面系統地進行佚文搜集。至民國,馬叙倫、王叔岷也都屬意於此,所獲大大超過前人,而以王叔岷晚年重新董理的一百七十六條最為大觀。這之中,就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文選》李善注。據筆者統計,李善注所保留的《莊子》佚文多達四十一條*其中有幾條王叔岷以為不當歸入《莊子》,詳見下文辨析。,去其重複尚有二十八條,約占王叔岷所輯佚文的六分之一;其中獨見於此書的則有十三條,可見李善注對保存《莊子》原文的貢獻之巨。
《莊子》之文,謬悠荒唐,洸洋自恣,常藉古帝先哲之口傳達自己的“莊語”,通過神話寓言表現自己的深意。佚文雖然只是隻言片語,也仍然具有這一特色。如左思《魏都賦》“備法駕,理秋御”句下李善即引了《莊子》中的一個故事,注曰:“《莊子》曰: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 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這段佚文又見於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文字稍有不同。若將之與《吕氏春秋·博志》《淮南子·道應訓》中的相關内容對照一下,即可知原文還未結束,李善是節引的。《吕氏春秋》下文作:“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許維遹《吕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55頁。《淮南子》略同。單就這段文字來看,故事頗為神奇,尹需學習法駕,過了三年老師都不教他,為此他十分苦惱,這一點李善注省略了,《淮南子》云:“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吕氏春秋》亦云:“苦痛之。”最後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他竟然在夢裏學會了法駕。正面説是瓌瑋神奇,反面説就是謬悠荒唐,這樣的故事出自《莊子》是再自然不過的,但為何被删呢?日本高山寺藏古鈔本後有一段跋文云:“然莊子閎才命世,誠多英文偉詞,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暢其弘旨,而妄竄奇説,若《閼亦(弈)》《意脩》之首,《尾(危)言》《遊易(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若此之類,十分有三,或牽之令近,或迂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夢書,或出《淮南》,或辯形名,而參之高韻,龍蛇並御,且辭氣鄙背,竟無深澳(奥),而徒難知,以因(困)後蒙,令沈滯失乎(平)流,豈所(以)求莊子之意哉?故略而不存。”*《日本高山寺藏莊子古鈔本》,收入嚴靈峰編《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五四册,臺灣成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148頁。括號中釋文參考了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及業師方勇《莊子學史》相關部分。跋文未交代作者,但《經典釋文·序録》則明言“一曲之才,妄竄奇説,若《閼弈》《意脩》之首,《危言》《遊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乃郭象所説*陸德明《經典釋文》,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以下所引《序録》及《莊子音義》,皆據此本。,則跋文作者定為郭象無疑。郭象認為五十二篇本《莊子》摻雜了後人的作品,這些作品發展了《莊子》恢詭譎怪的特點,更加離奇不經,但無甚深意,與《莊子》弘旨相去太遠,所以他以意去取,删去十分之三。對照郭象所言,“尹需學御”一段之所以遭到删棄,大概就是因為“或似夢書”吧。
在現存佚文中,似《山海經》者也能找到。左思《吴都賦》“瓊枝抗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瓏”句下,李善注:“《莊子》曰: 南方積石千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這一段關於瓊枝的佚文還見於李善注的另外三處,分别是謝惠連《雪賦》“庭列瑶階,林挺瓊樹”句下,嵇康《琴賦》“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句下,江淹《雜體詩·嵇中散康(言志)》“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句下,而以最後一處江淹詩注最為詳盡:“《莊子》: 老子歎曰: 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前三處所釋為瓊枝,此處所釋則為靈鳳、琅玕,重點不一樣,詳略也就隨之不同,正可驗證本文第一部分所云李善注截取縮略以就原文的情況。然而即便這最後一條,也不完整。《藝文類聚》卷九十云:“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顔回為仁,子張為式(《太平御覽》作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1558頁。巧合的是,在《山海經·海内西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下,郭璞注也節引了《莊子》這段文字為注:“莊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玗琪子。’謂此人也。”*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64頁。郝懿行云:“以此參校郭注所引,‘與玗琪子’四字,蓋衍誤焉。”可見《莊子》部分内容與《山海經》的關係已經不僅僅是“似”了,而是根本相同,可以互相印證,所以古人早就將二者拿來互作注釋了。因此,郭象以意去取,將這些荒唐無稽的故事都排除在外。
乍看起來,以上兩例似乎證明郭象所言不虚。然而仔細分析一番,便知實則不然。尹需一心向學,感夢通神,其重點絶不在感夢,而是藉助這一神奇的事件表現愛好、專注學御達到的效果,主旨與痀僂承蜩、梓慶造鐻的故事相近,以“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來形容最貼切。《吕氏春秋·博志》在故事結束後云:“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許維遹《吕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55頁。《淮南子·道應訓》則與同篇其他段落一致,引用《老子》十六章作結:“故老子曰:‘致虚極,守静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895頁。《吕氏春秋·博志》從外部揭示去除干擾,才能專注於學的道理,《淮南子·道應訓》則就内在探討致虚守静,方可用心一志的途徑。二書之發揮雖有不同,但對這個故事都是認同的,並以為有深意在焉,與郭象所云“辭氣鄙背,竟無深澳(奥),而徒難知,以因(困)後蒙”迥然不同。第二例也是如此。文中與《山海經·海内西經》相同的是“一人三頭”三句,通觀全文可知,這只是鳳鳥神話的一部分,而鳳鳥神話又是老子的一個比喻,只是全文的一部分,“一人三頭”占全文的比重可知。且故事重點在孔子帶領五個弟子,每個弟子代表一種德行,而老子把孔子比作鳳鳥,鳳鳥之文可與其弟子及各弟子所代表的德行相應。引文到此戛然而止,但按照現存《莊子》中的孔老對話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下面應該還有老子對孔子的批評指點。但與現存的幾段對話相比,明顯更加形象,更有文學意味,更富象徵性,其實是更符合《莊子》的特點。而且,以鳳鳥比孔子,與《德充符》接輿“鳳兮鳳兮”之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再聯繫《莊子》寓言、重言、巵言的寫法,這一段兼有寓言和重言兩種意味。所以無論如何,郭象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或者至少是自相矛盾的。《山海經》占夢書雖稀奇古怪,但未必没有深意,或者未必不可藉以闡發深意。如此看來,陸德明説郭象“以意去取”,這個“意”究竟是什麽還要費一番探究,不能偏聽偏信郭象的一面之詞。
三、 李注所引《莊子》佚文對探究古本《莊子》篇目的價值
郭象跋文雖然不可盡信,但仍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它保留了五十二篇本《莊子》的部分篇名: 《閼弈》《意脩》《危言》《遊鳧》《子胥》。除去以上五篇,今天能够知道的還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提到的《畏累虚》《亢桑子》二篇,《北齊書·杜弼傳》透露的《惠施》篇,《南史·何子朗傳》言及的《馬捶》篇,《文選》李善注引用的《莊子略要》《莊子後解》二篇。其中《亢桑子》一般認為就是《庚桑楚》,《馬捶》則是指《至樂》篇“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一段,並非單獨的一篇。如此算下來,能够確定的只有九篇,較諸郭象删去的十九篇,將近一半。
在這九個篇名中,《莊子略要》《莊子後解》較為特殊,其他篇目都是文獻明確記載的,這兩篇則是引用時只標明了篇名,並未明言其屬於《莊子》,因而還有一些疑議。《莊子略要》在《文選》注中共出現四次,分别為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注、江淹《雜體詩·許徵君詢(自序)》注、陶淵明《歸去來》注、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注云:“淮南王《莊子略要》曰: 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 獨往自然,不復顧世。”*此處據謝靈運詩注,其他三處文字略有不同。《歸去來》注胡刻本作“淮南子要略”,“要略”、“略要”義同。茆泮林纂輯《莊子逸語》即未敢收録,而置於《莊子司馬注疑義》中,並云:“案,《選》注凡四引,俱作‘淮南王莊子略要’,並有彪注。《略要》,未審何書,附録於此。”*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收入方勇主編《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一一三册,據道光十四年《梅瑞軒十種古逸書》本影印,第497頁。王叔岷以為:“《莊子略要》,乃淮南王外書之逸篇(《淮南子》今僅存内書二十一篇,外書已亡),以概論《莊子》者,非《莊子》五十二篇本中有此篇也。司馬彪注云云,僅可證司馬彪有淮南王《莊子略要》注,不能確定五十二篇本中有淮南王《莊子略要》。”*王叔岷《莊學管闚》,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51頁。其説貌似嚴謹確鑿,然而經不起推敲。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所言司馬彪注五十二篇包含“解説三篇”,《莊子後解》《莊子略要》應該就是這三篇中的兩篇。李善注所引《莊子後解》“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争財相鬥者,庚市子毁玉於其間,而鬥者止也”,乃是為《莊子》“庚市子肩之毁玉也”作注,這是從微觀角度對具體典故的解説。現存《淮南子》末篇也是《要略》,即從宏觀方面用簡短數語對各篇要旨的解説,《莊子略要》應當也是對各篇的簡要概括,細審其文,恰好與《刻意》篇開頭部分相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首尾兩種人性質相近,皆為隱士,故可概括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當然這只是《刻意》篇略要的一部分,還不完整。但《莊子略要》作為“解説”是無可懷疑的了。況且還有司馬彪注,歷史上並無司馬彪為《淮南子》作過注釋的記載,如果有,那為何僅此一處,而且是丢失的外書?内書皇皇巨著為何不見司馬彪注?可見,將《莊子略要》《莊子後解》在五十二篇之内這種看法更為合理。孫馮翼所云“彪固注《莊》,未注《淮南》也”、“自屬《莊子》逸篇”*孫馮翼輯《司馬彪莊子注》,收入方勇主編《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一一一册,據嘉慶二至七年承德孫氏刊《問經堂叢書》本影印,第4頁。,實是高見。清人俞正燮、日本武内義雄、今人江世榮及業師方勇也都讚同此説。
《莊子略要》《莊子後解》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不僅保存了篇名,而且保存了相關的内容。上文已經徵引,並對其解説特點略有分析,從其内容來看,已經突破戰國諸子和漢代辭賦家、經學家、醫學家對莊子的闡釋活動,並非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對《莊子》中的思想資料加以援引和改造,而是“把《莊子》完全當做一個直接的研究對象,從而揭開了我國歷史上獨立研究《莊子》的新篇章,其意義相當重大”*方勇《莊子學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頁。。另外七篇則只有篇名,具體内容不得而知。有人認為,今本《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當屬《惠施》篇,其餘諸篇,在今本《莊子》中則無明顯線索。然而在佚文中,卻有諸多發現。顔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云:“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李善注:“《莊子》曰: 閼弈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 元天,山名也。”顯然,這應當屬於《閼弈》篇,而且是開頭部分,《閼弈》之名即是取自起首二字。據王叔岷所輯,此段又見於《白帖》《天中記》,而《白帖》晚於李善注一百餘年,《天中記》要遲至明朝才出現。李善此注的地位不待多言。劉孝標《廣絶交論》云:“瞑目東粤,歸骸洛浦。”李善注:“《莊子》曰: 夫差瞑目東粤。”此條佚文王叔岷疏漏未收。筆者以為,此條佚文當屬《子胥》篇。伍子胥事迹見於《史記》《吴越春秋》,其後半段即與夫差休戚相關。夫差為報父仇,大敗越國,勾踐請和,夫差應允,子胥苦諫不聽,最後身死國滅。“夫差瞑目東粤”,放在結尾部分若合符節。馬叙倫亦“疑此為《音義》所謂《子胥》篇文”*馬叙倫《莊子義證》,收入方勇主編《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一五三册,據民國十九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影印,第660頁。。另外《遊鳧》篇也有一條佚文存世,見於《玉燭寶典》《藝文類聚》《白帖》《太平御覽》《記纂淵海》等多處*見王叔岷《莊學管闚》附録二《莊子佚文》,第231頁。,因非本文所論重點,故不徵引。可以看到,《莊子》逸篇十九,現在能够知道的篇名有九條,其中兩條來自《文選》李善注;這九篇之中有内容可尋的有六篇,其中四篇也是出於李善注,李善注對我們探究五十二篇本《莊子》真是功不可没!
四、 李注所引司馬彪《莊子注》之價值
司馬彪注《莊子》五十二篇,最擅文字訓詁,所以陸德明《莊子音義》引用最多,據黄華珍統計,達749項*黄華珍《莊子音義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74頁。。但由於郭象注“特會莊生之旨”,廣受推崇,相形之下,司馬彪本漸於唐代失傳。有清一代,孫馮翼、茆泮林相繼進行輯佚,今人王叔岷又有補正,對《文選》李善注、《藝文類聚》《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等典籍鈎沉索隱,可稱完備。據筆者統計,《文選》李善注所引用司馬彪注,去除重複後仍達八十餘條,其中不少為《莊子音義》所無,郭慶藩在《莊子集釋》中已基本補入相應位置,並以“釋文闕”三字標識。除了補闕的價值,將部分條目與《莊子音義》相應部分對比之後,還會發現兩個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文字訓詁的。《秋水》篇云:“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莊子音義》“反衍”條下云:“如字。又以戰反。崔云: 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 猶漫衍合為一家。”左思《蜀都賦》“累轂疊迹,叛衍相傾”句下李注云:“司馬彪注云: 叛衍,猶漫衍也。”*《文選》,第79頁。唐鈔本《文選集注》亦作“叛”,可見並非是流傳過程産生的問題。司馬彪注被李注包含在内,陸德明將之忽略不提並無不妥,但他對司馬彪本出現的異文不置一詞,顯與體例相悖。《經典釋文·序録》叙述其校勘體例云:“余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别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言之鑿鑿,無論是哪種情況,只要司馬本作“叛”,與《莊子音義》不同,就應該收録。況且在同一條目下,交代了一個異文,而將司馬彪本異文忽略,這種强烈對比不能不讓讀者産生質疑。又如《逍遥遊》篇“逕庭”,《莊子音義》云:“逕,徐古定反,司馬本作莖。庭,勑定反。李云: 逕庭,謂激過也。”劉孝標《辯命論》李善注所引司馬彪注云:“徑廷,激過之辭也。”此處不僅“逕”的異文與《莊子音義》所示不同,“庭”也存在異文,而且,李注與司馬彪注相同,為何没有用“司馬、李云”的形式將二者放到一起呢?《養生主》篇“緣督以為經”,《莊子音義》云:“李云: 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司馬彪曰: 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也。”從中可以知道司馬彪對於“經”的解釋也是“常”,為何没把司馬跟郭、崔放到一起呢?《徐无鬼》篇“今余病少痊”,《莊子音義》於“少痊”下注云:“七全反。李云: 除也。”然而李善注兩次引用皆作:“司馬彪曰: 痊,除也。”(潘岳《閒居賦》李注、張景陽《七命》李注)與《莊子音義》所引李注一字不差,陸德明卻隻字不提。從以上數例來看,有兩個問題比較集中: 第一,李善注所引司馬彪注所顯示的《莊子》原文與陸德明所出示條目所顯示的《莊子》原文有異文存在,但陸德明並未提及其所用司馬彪《莊子注》與其所用底本郭象注本有異文;第二,李善注所引用的司馬彪注與陸德明所引用的李注注釋内容基本相同,但陸德明卻只引李注,對司馬彪注置若罔聞。郭慶藩從李善注中輯出這四條,置於相應之處,但都僅綴“釋文闕”三字予以説明,並未注意到《莊子音義》尤其是其中的李注與司馬彪注的複雜關係,自然也没能對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做進一步的思考。由於目前資料有限,筆者在此也只是提出問題,做一些合理推測,並不能給出確切的答案。首先,可以排除陸德明所用司馬彪注非完本的情況,因為在上述諸例前後都引用了司馬彪注,如“逕庭”前“無當”條下即有司馬彪注云“言語宏大無隱當也”,“緣督以為經”後“文惠君”條即作:“崔、司馬云: 梁惠王也。”而且,也可以排除陸德明和李善有張冠李戴的情況。原因有二: 一,問題不是只有一處兩處,説明不是偶然性的;二,二書所引用的司馬彪注有相當部分是相合的。如《逍遥遊》篇“海運”之“運”、“旁礴”,《大宗師》篇“以襲氣母”之“襲”,《山木》篇“假人”之“假”,《徐无鬼》篇“以賓寡人”之“賓”等,解釋完全相同,還有一些條目解釋詳略稍有不同,或文字略異而意思一致。這都表明陸德明和李善不存在把别家注釋錯當成司馬彪注或反過來把司馬彪注當成别家注的情況。那麽,就只有兩種可能了,一種是陸德明自相矛盾,體例不一,不能嚴格執行自定的標準,一種就是陸德明和李善所用的是不同的版本。若真是由於版本不同造成上述現象,那麽這兩個版本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因為司馬彪注本是五十二篇本,其字數在十萬以上,而李善注引用的不足一百條,問題就有這麽多,全書的差别之巨可以想見。
第二個問題則是關於義理的。司馬彪《莊子注》雖然自清代孫馮翼、茆泮林就開始有輯佚,王叔岷又使之漸趨完善,但還算不上真正的研究,直到業師方勇教授的《莊子學史》才開始對它的特點、優劣及在整個莊子學史上的地位有了較為全面的研究。業師認為,司馬彪雖然也有超越禮法名教的思想,但並非崇尚玄學之人,而且,身為歷史學家,富有强烈的求實精神,所以,“從總體上看,他的《莊子注》並不像當時一般玄學家的注《莊》之作那樣重在闡發義理,而是以訓釋字句見長。”*方勇《莊子學史》,第359頁。若著眼於其注釋特點,此誠不刊之論,但若從全面性來看,則有所不足。我們知道,陸德明《莊子音義》目的在於注音釋義,而不在義理,這就決定了他對前人注釋的取捨删改的傾向性,也決定了後人所能看到的前人注釋尤其是散佚注釋的面貌。所以,《莊子音義》雖然以郭象本為底本,但所引郭象注數量卻排在第五位,排在前面的正是音字釋義的司馬彪注、李氏注、崔譔注、徐氏音。而且,以義理著稱的郭象注,如果只看《莊子音義》,恐怕我們得出的結論會是它是一部訓詁著作,其義理方面完全被忽略掉了。司馬彪注也是如此,今存司馬彪注主要從《莊子音義》中輯出,可以説《莊子音義》大體決定了我們對司馬彪注的認識。但幸而不是全部,李善注所引司馬彪注就有明顯不同。
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句李善注云:
《莊子》曰: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攄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 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
李善對《莊子·逍遥遊》有關章節進行了節引,單就這一部分看,《莊子音義》出示了一些條目,其中“魏王”、“而實五石”、“則瓠”、“落”、“掊之”、“不慮以為大樽”等六條引用了司馬彪之注,可見李善、《莊子音義》所引司馬彪注互相交叉,但都没有全部引用。郭慶藩《莊子集釋》録畢李善注後云:“較《釋文》引為詳。”實在是没有認真比較。而“枵”、“攄”、“罇”三字,《莊子音義》作“呺”、“慮”、“樽”,但没有出示此三字之異文,這就為上文所述問題又添一新證。而此處更為關鍵的是,李善注所引司馬彪注多出二句“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此章莊子、惠子二人就大瓠之有用無用展開辯論,但並非表面的就事論事,而是另有深意,司馬彪即指出大瓠是比喻莊子之言,惠子掊擊大瓠意在批評莊子之言大而無用,可以説司馬彪對本章主旨的揭示真是一針見血。相對之下,善於談玄的郭象只簡單地説:“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遥也。”莊子反駁惠子,要點在於大瓠的空虚、無用,正可以作逍遥之用,郭象就在空虚、無用如何有逍遥之用的作用機制上作文章,將空虚、無用作為萬千途徑中的其中一種,從中抽象出“得其宜”則能致逍遥的原理,而在《莊子》中,空虚、無用其實是唯一的,郭象注顯然背離了莊子之意。且莊子確實是藉此事以辯其言的,下章惠子所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即揭明其指,而本章與下章又是接續上一章“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的接輿之言的,前後一貫,宛如長蛇,郭象無視於此,粗暴地比附他發明的“適性逍遥”,實際上是不如司馬彪注簡明而扼要的。可見,司馬彪不僅對文章義理有分析,而且極有見地。只是,在《莊子音義》中限於其體例,他的重義理的這一面很難被認識到。
在李善注所引的八十餘條司馬彪注中,像這樣涉及《莊子》義理的還有數條。如《逍遥遊》篇“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箋》李注引)《齊物論》篇“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李注引)《齊物論》篇“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栝之發。”(鮑照《苦熱行》李注引)《大宗師》篇“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江淹《雜體詩·謝僕射混(遊覽)》李注引)《大宗師》篇“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賈誼《鵩鳥賦》李注引)《秋水》篇“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孫綽《遊天台山賦》李注引)從這幾條綜合看來,司馬彪對義理的分析,基本是緊貼原文,稍作補充,加以解説闡發,有時也引入新的概念,如上引前兩條分别引入“自然”來解釋“神人無功”、引入“性”來解釋“使其自已”。甚至只是將原文换一種表達,如《秋水》篇那條。水平參差不齊,整體上可能不高。而且不像郭象那樣,他似乎並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系統的理論,也没有理論化的表述方式,這就與談玄論道者的口味南轅北轍,那麽司馬彪注逐漸被淘汰就是勢所必至的了。
一般認為,内篇是莊周本人的作品,内篇題名頗為獨特,以三字概括全篇大意,而非像外雜篇或其他子書那樣,取篇首二三字為題,這在整個先秦都是極為罕見的。這個現象得到非同尋常的關注,表現在諸多注家為之所作的題解上。以郭象注來説,内篇皆有題解,外雜篇無,因為内篇是《莊子》義理的淵藪,就是在對内篇的題解當中,郭象開宗明義提出了他的逍遥觀:“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莊子音義》也是如此,外雜篇只在題下注曰“以事名篇”、“以義名篇”、“以人名篇”字樣,内篇則有題解*内七篇獨《齊物論》篇没有題解,不知為何。,或出己意,如《逍遥遊》篇的“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或直接引用前人題解,如《德充符》篇引用崔譔的“此遺形棄知,以德實之驗也”。《大宗師》《應帝王》也都是引用崔譔的題解,可見這似是當時的慣例,歸根到底是緣於對内篇義理的重視。那麽司馬彪呢?潘岳《秋興賦》“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下李注云:“莊子有《逍遥遊》篇,司馬彪曰: 言逍遥無為者,能遊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 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現在僅能找到司馬彪對這兩篇的題解,藉此可窺一斑。司馬彪以無為解逍遥,還是很契合《莊子》之意的,從許由的不越俎代庖,到藐姑射神人的不以天下為事,再到五石之瓠的大而無用,都可歸於無為,以此遊於大道,而非人間俗世,充分展現了逍遥遊的超拔境界。《人間世》之要旨在於虚心處世,所謂“虚者心齋也”,司馬彪解作“無心而不自用”,正是此意。所以這段題解被郭象完全承襲,只將疑問語氣的“何足累”變為陳述式的“不荷其累也”,流播千古。這既表現了司馬彪對《人間世》篇把握之精到,也體現了郭象對司馬彪的讚同。同時,也加深了我們對郭象注的認識,郭象固然是天縱英才,自成一家,但還是離不開對前人成果的繼承,除了衆所周知的對向秀注的“述而廣之”,還有此處對司馬彪注的因襲,不僅是義理,還有文字訓詁,《莊子音義》中就有不少郭、司馬相同的注。應該説郭象是一個集大成者。
綜上所述,司馬彪不僅關注一般文句涉及的義理,還特别重視對全篇尤其是内七篇大旨的把握,其對義理的分析雖然不够玄遠,但大體仍然是契合《莊子》之意的。固然,從總體來講,文字訓詁是主要的,也最有價值,但是其義理方面的努力和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
李善注引用最多的是司馬彪注,其次為郭象注,另外還有向秀注兩條、李頤注四條、李軌注一條、郭璞注三條、張湛注一條、徐邈注一條、《七賢音義》一條、《莊子音義》三條。但其中問題頗多,如劉孝標《辯命論》李注引所謂張湛注“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其實是《列子·黄帝》注;孫綽《遊天台山賦》李注、賈誼《鵩鳥賦》李注引所謂郭璞注實則是郭象注,左思《吴都賦》李注所引另一條則疑竇叢生,不可遽定是郭璞《莊子注》。其他幾家注則又過於零星瑣碎,故略作交代,不一一具論。
[作者簡介] 劉濤(1988— ),男,江蘇沛縣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先秦諸子學研究,已發表學術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