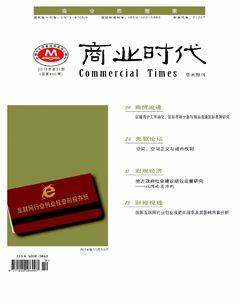劳动参与率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探讨
2014-11-12陈玲
陈玲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国 1982-2010年人口普查和人均GDP数据,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方法对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同时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关键词:劳动参与率 经济增长 格兰杰检验
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之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面对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终结的讨论,很多学者也在关注劳动参与率变化对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田成诗、盖美,2005)。《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指出,目前仅从总体数量上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仍然比较充裕,但是人口结构和劳动参与率都有所变化。都阳认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都阳,2007)。同时,蔡提出劳动参与率的扩大能够减缓人口红利减弱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蔡,2010)。因此,研究劳动参与率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郭琳、车士义,2011)。我国劳动参与率的状况到底如何?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利用我国 1982-2010年的人口普查和人均GDP 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分析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率,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10年我国16岁以上劳动参与率为70.96%,属于较高水平。从整个六次人口普查来看(见表1),多年平均劳动参与率为77.28%,但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年平均下降0.36%,且与年份序列的相关系数达到0.83。其中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参与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年平均下降率为0.59%,为整个人口普查年份劳动参与率年平均下降率的1.64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在80年代出现短暂的增长,90年代以后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在2000年前后下降幅度最大。尽管如此,还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劳动参与率水平。
(一)劳动参与率年龄曲线
劳动参与率年龄曲线是指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所形成的曲线,反映了不同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它表达了人口生命周期中劳动就业变动规律(王金营、蔺丽莉,2006)。无论1982年还是2010年,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呈现倒“U”型曲线。劳动参与率从15岁开始逐渐上升,20-25岁仍处于上升态势,在25岁达到高峰并且平稳的持续到45岁,在45岁后劳动参与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不断降低。因而,虽然年份各有不同,但是劳动参与率的整体趋势符合人的生命周期规律,由于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的实行(彭秀健,2006),加快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由图1可知,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模式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低龄组(15-24岁)和高龄组(50岁以上)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值得注意。
(二)分性别低龄组与高龄组劳动参与率
由表2可知,15-19岁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普遍高于男性,但这个差值由1982年的7.55%变化为2000年的2.64%,到2010年出现男性劳动参与率略高于女性。在20-24岁年龄段,男性劳动参与率高于女性,且这个差值呈现周期性变化,基本上在5%范围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低龄组劳动参与率均变小,且15-19岁年龄段的减小幅度远大于20-24岁年龄段。上述表明,教育改革和义务教育使得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开始渐渐变大,女性接受教育时间也开始渐渐变长。
高龄组人口包括50-54岁、55-59岁和60-64岁三个年龄段。 50-54岁和60-64岁的男性劳动参与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1990年时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年份,55-59岁的男性劳动参与率从1982年的82.96%上升至1990年的92.30%,在2000年后稳定在80.3%左右。然而,女性劳动参与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50-54岁年龄段女性1982年劳动参与率为50.90%,1990年和2000年保持在67%左右,2010年有小幅度的回落。55-59和60-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基本处于上升状态,60-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由1982年的16.87%上升到2010年的40.58%。
经济增长变化趋势分析
从上述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主要由低龄组和高龄组两个年龄组别引起,并且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改变连带着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曲线。关于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较多,本文采用GDP衡量经济指标,用历年的通货膨胀率将各年的GDP转化为1980年的不变价格,同时加入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微单元经济增长,作为一个辅助变量,以分辨出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国GDP基本上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多年平均增长率为2211.1亿元/年。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由经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趋势明显。在1992年前(不含1992年),经济增长速度较缓,平均增长率为68.10亿元/年,其中1988年和1989年略微下降;在1992年后(含1992年),经济增长迅速,平均增长率为3570.50亿元/年。
我国人均收入基本上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多年平均增长率为109.65元/年。为保持GDP分析一致,将1992年作为转折点。在1992年前(不含1992年),城镇人均收入增长较缓,平均增长率为37.38元/年,其中1988年和1989年呈现下降,分别减少了5.8元和10.8元;在1992年后(含1992年),人均收入增长迅速,平均增长率为166.64元/年。在各时段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比GDP增长趋势显著。endprint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思想是:如果A是B的原因,则A先于B出现,在加入A滞后项的回归模型中,A滞后项的系数应该统计显著,并能够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毛洪涛、马丹,2004)。采用Eviews软件,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辅助变量,进行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检验,其中R表示劳动参与率,G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I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表3可知, R不是G的格兰杰原因,而G是R的格兰杰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发展优先于教育发展,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导致了15-24岁劳动参与率降低,从而引起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在因先果后的假设前提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了经济增长是劳动参与率原因这一结论,而否定了劳动参与率变动先于经济变动这一命题。R是I在10%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因,而I是R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因,二者彼此互为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变动必然导致人均收入的改变,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变化,必然改变人的生活观念,导致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检验
大多数经济数据是非平稳数据,不能直接用来建立回归模型。如果用非平稳数据建模,极容易产生“虚假回归”问题。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揭示变量之间真实关系,必须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刘舜佳,2008)。
(一)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
由表4可知,劳动参与率离差较小,其次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与偏度和峰度关系是一致的。
(二)平稳性检验
采用Eviews软件,利用AIC和SC准则,G、R和I的ADF检验方法均为滞后一期,按照从无约束到逐步增加约束条件的顺序,利用不同形式的检验方程,对三个指标加以检验。由表5可知, G、R和I均为1阶单整,即都是I (1)过程。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通过对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增长趋势分析,利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平衡性检验来实证劳动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自由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活力与技术革新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互为因果关系。劳动参与率增加导致城镇化进程加快,增加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
面对我国“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争论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不争的事实,如何能够释放二次红利,使得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制定劳动力政策提供有益启示。首先,通过缩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职业化教育,使得劳动力的初次就业年龄变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其次,实行梯度渐进的办法推迟退休年龄,稳定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再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整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为显著,调节女性劳动参与率,适时应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参考文献:
1.田成诗,盖美.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7(2)
2.张璐.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1)
3.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B/OL]. 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
5.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6.彭秀健.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4)
7.毛洪涛,马丹.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财经学,2004(1)
8.刘舜佳.国际贸易、FDI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基于1952-2006年面板数据的DEA和协整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9.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与实现更加充分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化分析[J].关注,2011endprint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思想是:如果A是B的原因,则A先于B出现,在加入A滞后项的回归模型中,A滞后项的系数应该统计显著,并能够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毛洪涛、马丹,2004)。采用Eviews软件,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辅助变量,进行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检验,其中R表示劳动参与率,G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I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表3可知, R不是G的格兰杰原因,而G是R的格兰杰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发展优先于教育发展,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导致了15-24岁劳动参与率降低,从而引起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在因先果后的假设前提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了经济增长是劳动参与率原因这一结论,而否定了劳动参与率变动先于经济变动这一命题。R是I在10%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因,而I是R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因,二者彼此互为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变动必然导致人均收入的改变,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变化,必然改变人的生活观念,导致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检验
大多数经济数据是非平稳数据,不能直接用来建立回归模型。如果用非平稳数据建模,极容易产生“虚假回归”问题。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揭示变量之间真实关系,必须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刘舜佳,2008)。
(一)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
由表4可知,劳动参与率离差较小,其次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与偏度和峰度关系是一致的。
(二)平稳性检验
采用Eviews软件,利用AIC和SC准则,G、R和I的ADF检验方法均为滞后一期,按照从无约束到逐步增加约束条件的顺序,利用不同形式的检验方程,对三个指标加以检验。由表5可知, G、R和I均为1阶单整,即都是I (1)过程。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通过对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增长趋势分析,利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平衡性检验来实证劳动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自由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活力与技术革新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互为因果关系。劳动参与率增加导致城镇化进程加快,增加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
面对我国“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争论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不争的事实,如何能够释放二次红利,使得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制定劳动力政策提供有益启示。首先,通过缩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职业化教育,使得劳动力的初次就业年龄变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其次,实行梯度渐进的办法推迟退休年龄,稳定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再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整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为显著,调节女性劳动参与率,适时应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参考文献:
1.田成诗,盖美.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7(2)
2.张璐.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1)
3.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B/OL]. 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
5.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6.彭秀健.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4)
7.毛洪涛,马丹.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财经学,2004(1)
8.刘舜佳.国际贸易、FDI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基于1952-2006年面板数据的DEA和协整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9.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与实现更加充分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化分析[J].关注,2011endprint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思想是:如果A是B的原因,则A先于B出现,在加入A滞后项的回归模型中,A滞后项的系数应该统计显著,并能够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毛洪涛、马丹,2004)。采用Eviews软件,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辅助变量,进行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检验,其中R表示劳动参与率,G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I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表3可知, R不是G的格兰杰原因,而G是R的格兰杰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经济发展优先于教育发展,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的教育,导致了15-24岁劳动参与率降低,从而引起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在因先果后的假设前提下,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了经济增长是劳动参与率原因这一结论,而否定了劳动参与率变动先于经济变动这一命题。R是I在10%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因,而I是R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原因,二者彼此互为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变动必然导致人均收入的改变,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变化,必然改变人的生活观念,导致劳动参与率的变动。
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检验
大多数经济数据是非平稳数据,不能直接用来建立回归模型。如果用非平稳数据建模,极容易产生“虚假回归”问题。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揭示变量之间真实关系,必须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刘舜佳,2008)。
(一)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
由表4可知,劳动参与率离差较小,其次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与偏度和峰度关系是一致的。
(二)平稳性检验
采用Eviews软件,利用AIC和SC准则,G、R和I的ADF检验方法均为滞后一期,按照从无约束到逐步增加约束条件的顺序,利用不同形式的检验方程,对三个指标加以检验。由表5可知, G、R和I均为1阶单整,即都是I (1)过程。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通过对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增长趋势分析,利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平衡性检验来实证劳动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开始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自由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活力与技术革新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互为因果关系。劳动参与率增加导致城镇化进程加快,增加了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
面对我国“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争论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不争的事实,如何能够释放二次红利,使得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制定劳动力政策提供有益启示。首先,通过缩减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职业化教育,使得劳动力的初次就业年龄变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其次,实行梯度渐进的办法推迟退休年龄,稳定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再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整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较为显著,调节女性劳动参与率,适时应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最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参考文献:
1.田成诗,盖美.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7(2)
2.张璐.中国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1)
3.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B/OL]. http://data.bls.gov/pdq/SurveyOutputServlet
5.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6.彭秀健.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4)
7.毛洪涛,马丹.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财经学,2004(1)
8.刘舜佳.国际贸易、FDI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基于1952-2006年面板数据的DEA和协整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
9.劳动力供给变化趋势与实现更加充分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化分析[J].关注,20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