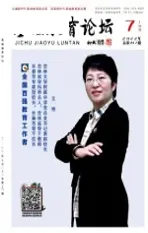拒绝当标准产品
2014-10-22董月玲
董月玲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选自《云南教育》2014-1~2)

2013年高考刚放榜,7月7日一清早,我就收了条短信:“我女儿陶雨晴,已被香港浸会大学录取,应该是写作特长起了作用。老陶。”
收到短信后,我回了一条,祝贺他们父女俩在激烈的高考大战中获胜。
老陶很快回复道:“不能说胜利吧?只是在这个教育制度下挣扎而已,分数只有560,在对付高考方面只能算及格。我觉得有个问题值得探讨:孩子的天赋,到底有多少值得维护发展的价值,家长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和体制的矛盾。”
“一上学,她再也没有快乐过”
陶雨晴是个单眼皮的女孩,人长得挺瘦,胳膊细细的,刘海有些长,一低头,能盖住上眼皮。
采访是在陶雨晴的房间里,屋里有张单人床、一张长条大书桌和书柜。桌上堆放着《梭罗集》、《史怀泽传》等书,书柜里没有一本关于高考的书,大部分是自然和生物方面的。在书桌前坐了一小会儿,陶雨晴就抱了本书,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去了,撂下我和老陶。
谈话时,老陶时不时地要喊上一嗓子:“陶雨晴,这事我能说吗?”
“你说吧!”靠在沙发上看书的陶雨晴,不情愿地回一声,老陶这才接着往下讲。
说起陶雨晴最大的特点,老陶认为是好奇心重,有点语言天赋。
“小时候,就爱看书,老是抱本书跟在大人身后,嚷着给她念、念、念。认点字后,就自己看。每天晚上都得给她念故事,不念不睡,我困得不行,睁不开眼,她就来扒我的眼睛。”
“从小,她就喜欢动物,去农村的奶奶家,什么虫子都敢抓,连蛇也不怕。村里每次来卖小鸡的,她都缠着大人买。结果,一共抓回来59只。”陶雨晴还饲养过一只大肉虫子,看动画片时,就把虫子搁在沙发上,两个人一起看。
“一上学,就完了,她再也没快乐过。”老陶讲。
“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分或特长,可惜小芽还没长大就给掐掉。但有的小孩比较倔,顽强地生长着。”老陶说自己的女儿就属于这种,不温顺。
基建工程是一项庞大而繁杂的工程,它不仅历时较长,耗资巨大,而且在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单位、人员也比较多,所需专业面也非常广。基建档案作为工程项目建设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为企业各环节的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减少资源浪费现象,有效维护企业权益,促进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老陶分析道,主要矛盾就是时间问题。学校希望学生啥也别干,一心一意学习,奔了中考奔高考。一天差不多12个小时,全上课、写作业,没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应该说,老师没做错什么,是按学校规定做的。”老陶始终这么认为。知道陶雨晴有点天分,老师甚至对她还有些照顾。“在小学,到后来,校长也挺无奈地说过:陶雨晴这孩子,只要她不影响别人,不要管她!”“现在的老师有升学压力,没有办法管学生有没有特长,只管你守不守纪律。”老陶说。像初中,每天有几项指标:交没交作业、听不听课、迟不迟到、上课说不说话、打不打架等等,由班干部每天填,陶雨晴就属于经常被填上的主儿。
说到这,陶雨晴气呼呼地说:“我们学校也分好班和差班,老师让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讲学习经验,给好班请的,都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给我们找的,都是上语言学院之类的。这就是把人分了等级,凭什么呀!”“她老提这事,觉得不公道。”老陶坐在一旁讲。“咱们这个教育制度不公平,大家交的学费是一样的,但学校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资源,都用在好学生身上了。”老陶的观察是:学校的思想教育,是让小孩虚伪化的过程,好多道德标准要求很高,根本就做不到。教育者假装在教育别人,被教育者也假装在听,大家都心照不宣。心里想的跟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而陶雨晴呢,就属于虚伪化过程没完成,不太成功的,所以,她才处处碰壁,较劲儿。“她的痛苦在于,不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想什么就表现出什么。也许有的学生想得比她还严重,但人家不表现出来,表面上规规矩矩的。”“别人都能顺从,你也就随大流呗?”我问陶雨晴。
“可我心里不舒服。”
直到现在,老陶也觉得:老师的话要听,但也不能全听,因为家长才知道自己孩子是啥个性。“像陶雨晴这种孩子,逼急了,弄崩了,出了事怎么办?我可不想冒那个险。强迫孩子老老实实听话,考个高分,结果把孩子心理弄扭曲了,精神不健康,划不来。”
“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陶雨晴说。中考完的暑假里,陶雨晴写了一篇文章,叫《永州之野》。老陶看了,觉得奇怪:“这是我孩子写的吗?”拿给当记者的朋友们看,大家也都挺惊讶:这哪像个初中生写的,文字这么老道。大家都鼓励她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获奖后,小陶挺高兴的,把荣誉证书拿到了学校。班上有个体育生,看了后怪稀奇。“哎呀!这是全国的奖啊!”他带着小陶和一大帮同学,浩浩荡荡开到老师办公室,问老师:这个高考能加分不?老师瞅了一眼说:不能!一群人只好悻悻地回去了。
“作文好,但她不按要求写,跟高考没关系,就是没用。”老陶一度挺矛盾,平常还行,到了高考,老师得考虑分数。
“我就是个投降派!”老陶这么说自己。肯不肯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妥协?虽然痛苦挣扎过,但他说自己还是投降了。“应该说,好多小孩都不适应这种教育制度,但最后都服了,怎么办呢?你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呗!”
“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
一考完,父女俩就把有关高考的书全卖了,差不多有100公斤。陶雨晴说自己还举行了一个仪式,拿出其中一本,烧掉。
“哪本?”
“讲高考状元的那本。”
中国的童话,陶雨晴评价最高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她还说自己的好多价值观,是从动画片里得来的:“就是人性的解放,人与人要平等,我们都是—样的。”
接着,她又说道:“生命是最宝贵的,应该尊重生命,不能一味地鼓励和歌颂牺牲,这是不人道的。”老陶的朋友给他支招:“你闺女不适合咱国内的教育,让她出去。”可是,陶雨晴喜欢的是中文写作,总不能跑美国学中文吧。“去香港啊!”朋友说,“人家的大学比咱的活泛,没准她的写作特长能管用,说不定还能破格录取呢。”
老陶父女也试着参加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自主招生。“那也得考,参加学校自己组织的面试、笔试,也是按分录,分低还是进不去。那所学校只招60多人,陶雨晴的考试成绩排到了100多名,没戏。”
高考要填志愿,老陶上网查了半天,最后选中了香港浸会大学。据说这所大学,在香港排名第五,而且重视文学创作。但去年,人家在北京的文科平均录取线是628分。
在网上报名时,老陶把陶雨晴出版过的书、得过的奖全填上了。陶雨晴今年考了560分,只超过一本线28分。没料到,香港浸会大学来了面试通知。去面试时,爷俩也没敢抱多大希望,因为内地有3000多号人报名,录取名额只有140个。
没想到,才隔了一天,浸大就来电话,说陶雨晴被录取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问是否愿意。
“能不愿意吗?从小学到现在,她一直受压抑,从没高兴过。这次拿到浸大通知书,是她自上学以来最高兴的事了。尤其是她的写作,能够被人承认,这点,最让她感到愉快。”
毕竟,陶雨晴分数挺低,真上了浸大,学习上会不会有压力?小陶讲不会。“再枯燥的知识,只要它是知识,我就不怕,逻辑学也是很美的。但问题是,高考学的知识,好多是假知识。真的知识,有道理之美,简洁之美。”几天后,我收到老陶发来的一封邮件,谈了他的“一点想法”。虽然只有几百字,但我反复读了好多遍,越读越心酸:
“陶雨晴的经历,实际上就是在这么一条路上挣扎的过程,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天分很高的精英的故事,而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高考轧路机下面的小草的经历。在她的经历中,没有人有什么错,学校、老师都没有,甚至对她比一般学生还要宽容一些。而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在学校、老师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学生这样地不快乐。”
“至于浸大的录取……可以作为一个相声中的包袱,原来以为打不开的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