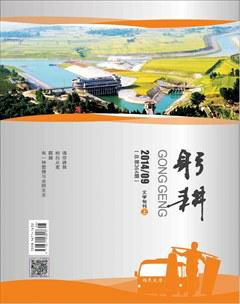陌路
2014-10-09黄绍祝
黄绍祝
要不,你们离婚吧。
这句话她虽然想了很久,可是说出来还是有些后悔,毕竟母亲快65岁了,在这样的年纪,谁还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呢。
她偷偷地把目光向母亲瞭去,不想也正碰上母亲瞭过来的目光,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瞬,她们都明白了,其实这个问题,无论是母亲,还是她,都已经考虑很久了。
母亲的头发都白了,就是这两年刚刚白起来的。在父亲没有出现婚外恋之前,母亲的头发一直是家里的骄傲。原来,母亲的头发光亮润泽,60多岁的人了也没有一根白发。而她的头发则稀疏干涩,还有些发黄,尤其这两年那些黄演变成了一种黄白,看上去让人厌恶。有时候,她跟母亲开玩笑,说自己不是亲生的,要不头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母亲笑着说,别昧了良心说话,亲生的怎么了,不是亲生的又怎么了,老娘对你不好吗?母亲的话让她无法辩驳,从小到大,母亲对她的爱都是无懈可击的。
她原来不相信精神对一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可是自从跟杨少华离婚之后,她就深切地体会到了精神的打击对一个人是具有毁灭性的。她是这样,母亲也是这样。这两年母亲的头发不仅仅白了,精神头也没有了,无论说话,还是走路,都让她有了一种胆战心惊的感觉,尤其像刚才的话,她真怕母亲一时承受不住,而轰然倒塌下来。
母亲看看她,半天没有说话。整个空间瞬时凝固下来,她听得见母亲的呼吸和自己的呼吸,她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她不知道说些什么才能把刚才的话收回来。离婚,对母亲那一代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接受的事情。
半响儿,母亲才悠悠地说,这个问题其实我早就想过了,可是,你刚刚离婚,我再离婚,让别人怎么看啊?
只是短暂的沉默,她在心里就流泪了。在这样的时刻,母亲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她。
她说,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一味地让着他吧。
他便是父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把原来的“爸爸”换成“他”了,不是不想喊爸爸,而是喊不出了。
是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样的变化了呢?她还真没有留意过。原来的母亲和父亲,虽然说不上有多么恩爱,可大矛盾是没有的。从小,她跟母亲生活在农村,父亲一个人在外面过着单身的生活。这样的情况在那时的中国并不鲜见,两地分居似乎是那一代人固有的特色。母亲属于那种很能吃苦的女性。在那时的农村,家里没有男劳力往往会给生活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是母亲都克服过来了。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大冬天浇地,因为垄沟跑水,母亲就双脚踩进冰冷的泥水里,那样的温度,弄不好,腿脚就冻伤了。可是母亲说,没办法,别人能吃的苦,咱也能吃。母亲的腰疼,风湿病,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印记。直到现在一逢阴雨天,母亲的两腿都微微的酸痛。但是母亲从没叫过苦,甚至一点都没有埋怨过父亲。
父亲是当兵出去的,转业后因为三线建设,就跟随大部队来到了这家钢铁企业。在她的眼里,父亲是威武英俊的。关于母亲和父亲认识的过程,她曾向母亲求证过,母亲说自己的哥哥和父亲是同学,他们的事情是在父亲回家探亲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提出来的。至于是谁先提起的,母亲说她并不知道。母亲小父亲三岁,似乎是最佳的年龄搭配了。她看过父母年轻时的一张合影,父亲是一身英武的军装,母亲长发,系着一条长长的围脖。如果不明就里的人看到那张照片,脱口而出的肯定是“才子佳人”,但实际上父亲并没有多少文化,如果不是到部队,恐怕连小学的水平都没有。
她儿时眼里的父亲是和蔼可亲的,虽然父亲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并不多,可是每次回来,给她买的礼物都是最多的。那时她最喜欢父亲拉着她的手在大街上走过。父亲的手是温暖的,当然最温暖的还是那些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羡慕的眼神。有一个在外地挣工资的父亲在那时的乡村是并不多见的。她很依赖父亲,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父亲也并不厌烦,说她是跟屁虫。她用尖尖的指甲掐父亲的手指。父亲的手指很粗糙,她掐不动,有一次就咬了一口。父亲没急,反而说我的丫头馋肉了。父亲每次离家,都是趁她睡着了,否则她会抱住父亲的大腿,谁劝也不松开。
那时候很多的孩子都羡慕她,其实她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大人羡慕母亲。隔壁的三婶每次来串门都对母亲说你烧哪柱高香了,怎么我就遇不到这样的男人?大人们的话她不懂,可是从母亲的笑容里,她还是感受到父亲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荣誉和快乐。
她没有弟弟,也没有哥哥,直到现在她都很疑惑,那时的父亲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一个那时代的男人做到这一点,是很不简单的。倒是母亲会时不时地叹口气说,要是有个男孩,这个家庭就美满了。那是母亲的心病,对于她来说,并不会强烈的感觉到。倒是自己在有了一个女儿之后,杨少华的态度让她强烈地感觉到了,重男轻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并不会因为一代人两代人的改变而改变。
十七岁的时候,她初中毕业了,因为没考上高中,就只有务农的命了。这样的归宿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农村大多数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宿命。那时的教育条件就这样,老师教的不好,学生学的也不好,两个不好遇到一块,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在她垂头丧气的时候,父亲的工厂却传来了招工的信息。她跟着父亲远走高飞了,却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农村。
她很不舍,毕竟跟母亲生活了十七年。父亲说,别急,你先去,等条件成熟了,你娘再去。
父亲所在的钢铁企业虽然挣钱不多,可是工人和农民的区别毕竟是巨大的。不再披星戴月了,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次发工资,她清楚的记得是39元。长那么大,她还没见过那么多的钱,装在口袋里,她的手一刻都没有离开过,好像那些钱会自己飞走似的。直到交给父亲,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父亲说,你自己攒着吧。她说,不行。父亲说,那你留一半,爸爸给你攒一半。方案就这样定了,她拿着那19块钱,跑去了商店。她给父亲买了一个刮胡刀,又给母亲买了一副漂亮的毛绒手套。面对崭新的刮胡刀,父亲夸她长大了。她很高兴,她觉得那一段时光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
原来在农村,她以为父亲天天在外面吃食堂,不会做饭什么的。可是在一起生活了,她才知道,父亲做的饭菜一点也不比母亲差。她爱睡懒觉,父亲就早早地做好饭等她起床。有时候她下班晚了,父亲还会骑上自行车去单位接她。在她眼里,父亲是那样的慈爱有加。她想要是母亲也搬来了,一家人该多么幸福。endprint
那时父亲什么都好,唯一让她牵挂的就是父亲的周六外出。父亲有技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到附近的乡村挣点外快。父亲每次出门,她都把嘴撅得高高的表示抗议,她总怕父亲在山路上摔倒了,或者遇到什么野兽。
母亲搬来的时候是在五年之后了。那时候企业里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解决了大批两地分居职工的户口问题,当然父亲也在其列。
一家人团圆了,真让人高兴啊。可是看看父母都是年近50岁的人了,这样的团聚多少让人有些唏嘘。
母亲来了,矛盾也开始多起来。
父亲让母亲刷牙,母亲说受不了牙膏的气味,父亲就生气。母亲嫌父亲不吃剩菜剩饭,说他不知道节约,父亲说一个人多年的习惯不好改了。
母亲刚来,没什么活干,对于已经在地里劳累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父亲对母亲的表现很不以为然。父亲说,在家里呆着有什么不好,我还不想上班呢。话是这样说,其实父亲也没什么办法,因为那时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除非去给人家做保姆。母亲说,如果天天干耗着,我还不如回老家。父亲说,你在家做饭不是活儿吗?你就不能面对一下现实?
那一段时间,她觉得是母亲最难熬的阶段了。有好几次,她看见母亲一个人跑到居民楼的护坡上,看着远方的庄稼地出神。她也劝过母亲,没事就陪在母亲身边,好在母亲不是那种转不过弯来的女人,很快就适应了做家庭妇女的角色。
真正让母亲不容的是父亲的周六外出。母亲来了,按说父亲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陪母亲上,可是每到周六,父亲依旧像原来那样要去附近的乡村挣外快。母亲说,你是真的去挣外快吗?父亲反问道,我不是挣外快是干什么!母亲说,干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并说,下次我跟你一块去。父亲说,别没事找事了,一个女人家不方便。母亲则说,带我去当然不方便了。每逢这时她就劝母亲,并说周六周日自己可以陪母亲。
可能是为了减少母亲的牢骚,也可能为了摆脱与母亲的争吵,没过多久,父亲还真给母亲找到了一份打扫楼道的工作。父亲说,你要是不怕丢人,就去。母亲说,这有什么丢人的,我脸皮比别人厚。母亲的话很噎人,父亲没再吭声,事儿就这么定了。
那时节,父亲买了一辆嘉陵牌的摩托车。他说,这样出去就不那么辛苦了。尽管母亲和她从安全的角度都反对,可是父亲很固执,并说就这么一个女儿,攒钱也没什么用。
父亲说攒钱,其实也没有攒下多少钱。这是母亲有一天告诉她的。开始她不相信,说即便前些年她交给父亲的工资也应该有很多了,可是母亲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她想父亲肯定是藏私房钱了。可是让她纳闷的是父亲藏私房钱有什么用呢?
父亲把他的自行车卖给了一个老乡。那天来推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子眉清目秀,看见她们很拘谨的样子。父亲介绍说,是一个他外出挣外快时的一个房东的儿子。她没往心里去,可是母亲却看了那个小伙子很久。
小伙子走了之后,趁父亲不在,母亲忽然悄悄地对她说,你看那个小伙子像谁?母亲不说,她也没怎么留意,可是经母亲一说,她还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母亲说,像不像你爸爸?她惊讶地看着母亲,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层面上来,母亲太多心了。她说,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母亲反问道,世上的事情什么都有可能,我早就怀疑你父亲了。她没再敢接母亲的话,她知道接下去,只有无穷无尽的怀疑。
母亲还想跟她说什么,她借口有事离开了。她觉得父亲不会去做那样荒唐的事情,而她也不会凭空多出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来。
那一段时间,她恋爱了,对象是父亲一个工友的儿子。父亲说,那家人都挺实在的,我看那小伙子也不错。父亲看得并没走眼,杨少华最初给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老实的大男孩,腼腆,不爱说话,似乎不坏的样子。母亲也点头认可,亲事就这么定下来。在没生女儿之前,他们婚后的生活一直一帆风顺,公公婆婆对她也知疼知热的,给她的感觉真是找对人家了。但在生完女儿之后,所有的事情却都改变了。在这之前,杨少华上面的两个哥哥家都生了女孩,所以公公婆婆包括杨少华在内都把生男孩的希望寄托她身上,可是她也没完成任务,公公婆婆的脸色就开始不好看,说话也没原来那么中听了。以她的脾气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现状,再说了生男生女关键在男方,他们凭什么给她脸色看。她还之颜色,时间一久,杨少华就不愿意了。有一次因为争吵,杨少华打了她一个耳光,她当然也不示弱,回敬了杨少华两道抓痕,并把家里砸了个乱七八糟。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次数多了两个人的态度就敌对起来,直到离婚的地步。
父母都劝过她,尤其母亲说,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能轻易离婚的。她说,就这样过下去?母亲说,怎么杨少华的哥嫂没离婚?她说,那是他的两个哥哥做得好。母亲说,仅仅是做得好吗?女人,有些事总要低头的。她说,凭什么我要低头?错误又不在我。母亲说,在家庭琐事上,谁能分得清对错。她说,你那是老思想,现在的婚姻生活,想一块过就过,过不了就离,简单得很。母亲说,你是简单了,可是孩子呢?她说,孩子我自己养活。
父亲也曾委婉地劝过她,父亲说,你要慎重,要是真过不到一块,也没必要勉强自己。父亲还说,现在离婚也不像原来那样是件多么丢人的事了,自己拿主意,不后悔就行。她觉得还是父亲比母亲更了解她。但在父亲的婚外恋暴露之后,她才觉得,父亲的委婉似乎是在为自己的出轨做注脚。
婚离得很痛快,杨少华净身出户,好像,他比她更厌倦他们的婚姻。
虽然她说孩子自己养活,可是离婚之后,她才知道事情并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的。她把孩子交给了母亲,那一刻,母亲说,我真是前世欠你们的。
因为要看孩子,又要打扫楼道,母亲一时忙乱起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干脆搬到了父母家。
父亲天天不着家,即便不出门也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打电话,她一直怀疑,退休之后的父亲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电话?偶尔她也想悄悄地听上几次,可是父亲很敏感,每次都及时敏锐地发觉了。她什么也没有捕捉到。endprint
父亲向她借过几次钱,说是借,其实根本就没说过还。第一次是1000元,第二次就2000了。第三次的时候她忍不住问道,你的退休金不够花吗?父亲摇摇头,退休金不是你娘拿着嘛。那一刻她有些可怜父亲,老了老了,连零花钱都没有了。
她开始劝母亲不要把钱管得太紧。母亲开始还有些糊涂,等明白她的所指时勃然大怒,说,他的退休金从来就没给过我。她困惑了,不知道父母是谁说了谎话。
父亲再跟她借钱时,她就拒绝了。她说,你老借钱,有什么事吗?父亲没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反而问道,你是我的女儿,我跟你借点钱花还不行了?她说,不是不行,我想知道你借钱干什么,你的退休金足够你花销了。这次父亲没再把借口往母亲身上推,直说到,我做生意用了。
她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她觉得多年的父亲一下子在自己眼前模糊起来。父亲竟然在做生意,打死她也不相信。
她一直也没敢把父亲跟她借钱的事情告诉母亲,她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关于父亲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这时候传进她的耳朵里的。说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而且不是一个。开始她不信,后来听多了她就起了疑心。有一天,一个单位的同事无意中对她说,你父亲对你真不错。她有些莫名其妙,反问道,怎么不错了?那个同事说,上个礼拜天,我在县城的商场里看到你父亲买了一件女士大衣,他说给你买的。她心里咯噔了一下,不过还是稳住自己的情绪。她说,是给我买的。那个同事说,你爸爸真好。她笑了笑,却再也坐不住了。
她开始观察父亲,这一观察还真不要紧,父亲果然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父亲很注意自己的容貌了,每次出门,胡子必刮,头发必梳,这显然是不同于以前的。而洗衣做饭什么的家务活,简直都成了母亲一个人的专利,即便是能帮忙的时候,父亲也袖手旁观了。有时候父亲外出归来,就埋头大睡,好像多疲劳似的。她惊诧于父亲的变化,这次不是模糊,而是陌生了。有一次她委婉地提到那件大衣,开始父亲愣了一下,但马上就否认了。父亲说,你那个同事肯定是看花眼了。她没再跟那个同事核实,因为她已经都清楚了。
但她始终也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她变了,还是这个世界变了?
她决定跟母亲挑明。毕竟她眼里揉不进沙子,不管这个沙子是杨少华,还是自己的父亲。
本以为母亲会大吵大闹,可是等她把自己的怀疑跟母亲一五一十说完的时候,母亲只是淡淡地说,我早就知道了。
这下轮到她惊讶了,她说,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母亲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你还记得我不愿意他周六的外出吗?他那时根本不是出去挣外快,而是在外面有女人了。啊?她睁大了眼睛,原来在平静的家庭生活下面早就有了波澜,只不过她一点都没觉察到。母亲又说,开始我还不相信,可是有一次当我把他和一个女人堵在家里的时候,我相信了。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她质疑道。说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母亲说,家丑不可外扬,况且我们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他后来改了吗?她说。改不改你现在应该清楚,母亲说,你还记得买咱们自行车的那个小青年吗?她点点头。母亲说,他是你爸爸的儿子。什么!她把手里的东西掼在地上。是真的,都是真的,那一次他什么都跟我坦白了,他说要么这样过下去,要么离婚。
你就这样忍了?她简直不敢相信母亲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
不忍又能怎么样?母亲看看她说,你看我的头发,为什么这两年忽然白了?
她背着母亲气冲冲地找到父亲,好像从那个时候起,她就不喊他爸爸了。她说,你怎么能这样?父亲低着头躲开了她咄咄逼人的目光。父亲说,那么多年的单身生活,一个人是很苦闷的,这些你们都不会懂的。她说,那你就到外面生儿子?父亲苦涩地笑了笑,也是误打误撞,实在没办法的事。是没办法吗?你看你这些年变成什么样子了?什么样子?父亲反唇相讥,我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你那是幸福吗?我和母亲没给你幸福吗?父亲摇摇头,幸福和幸福有时候是不一样的,这些你都不懂。
是我不懂,还是你不负责任?她开始哭起来,多年父亲美好的形象一下子倒塌下来,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父亲不再跟她解释,也许,沉默能避免更多的风暴。
她以为和父亲摊了牌,父亲就会收敛的,可是父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回家了。他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在外面租了房子,过上了夫妻生活。
这是她不能容忍的,她去跟父亲要钱。她说,把借我的钱都还给我。父亲说,我没钱。她说,把你的退休金卡拿给我。父亲说,我不生活了吗?再说了你那个弟弟还要成家。他是谁弟弟?她打断父亲的话,你们的事情我不管!父亲说,你能不管吗?我是你爸爸,你有赡养我的义务。她说,那也要看我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次她气愤至极,冲动之下砸烂了父亲出租屋里的玻璃。
母亲一直也没有闹,即便是在父亲拿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折之后,母亲也没有一丝的慌乱。母亲说,人在做,天在看,他会后悔的。
她还是劝母亲离婚。她说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恋头?母亲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说,你知道前楼那个刚去世的马大娘吧?她说知道。
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吗?她看着母亲摇摇头。
她是被老头气死的,他们前脚刚刚离婚,后脚她就走了。
这怎么可能?她睁大了困惑的眼睛。那个马大爷,她是知道的。那个老头曾是某个单位的一把手,当一把手时,身边的女人就不断。退休后好像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把一个女人带回家过起了一夫二妻的生活。她很早以前就听说马大娘要跟他离婚,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局
母亲说,我不想死,更不想被他气死,我要好好地活着,因为有你,还有孩子。
就这样便宜了他?她心有不甘。
人离了谁都能活,大不了我回老家种地去。
她看着母亲的白发和疲惫的神情,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觉得母亲的隐忍已经让所有的事情都平淡如水了。
活一天就少一天了,谁爱折腾谁折腾吧,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就是死了,也不会走到一起的。母亲又说,他是你父亲,你该怎样对他就怎样对他,别让人家笑话你不孝。
她大声地拒绝,说,我做不到!
她觉得父亲已经死了,即便是没死,和她,和母亲,也没有关系了。
父亲搬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即便是偶尔在马路上相遇,也像陌生人那样,瞅一眼后各奔西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