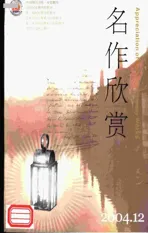论《花园茶会》中的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
2014-07-14姜风华菏泽学院外国语系山东菏泽274015
⊙姜风华[菏泽学院外国语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作 者:姜风华,菏泽学院外国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花园茶会》是英国著名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后期的优秀作品之一。故事聚焦正值豆蔻年华的小主人公萝拉,展示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内心成长的历程。正如曼斯菲尔德1922年在给威廉姆·格哈地的信中所讲,她在这个故事中想要竭力表现的是“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我们如何试图适应一切,包括死亡”①。而评论家帕特里克·D.莫罗也曾提到,《花园茶会》这个故事的创作正是基于生命和死亡的二元对立。②另外,该小说从头至尾还流露出一种极为强烈的阶级意识,并暗示出阶级偏见和阶级对立主题。在小说里,曼氏“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冷漠和傲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攻击”③,从而使她的阶级观和人生观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故事中的薛立丹太太,也就是萝拉的母亲,和萝拉的那些姐姐们都一样。她们那种充满稚气的漫不经心的言行举止之下,其实隐藏着中产阶层人士所特有的冷酷无情的性格,她们也正是借用这种拙劣而愚蠢的方式来试图掩盖自己残忍、自私的一面。
“亲爱的孩子,不用问我……别想着我是你们母亲,就把我当作贵客好了。”④当孩子们在为晚上将要举办的花园茶会做准备、问她们的母亲薛太太该把帐篷搭建在哪里时,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后来,花店的人给薛家送来了一大盆盛开着的百合花,不知情的萝拉认为是他们搞错了,谁知薛太太却说是她订的花,而较真的萝拉有些不满地分辩说她不该干预她们的事,薛太太又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亲爱的孩子,你不会喜欢一个一板一眼的母亲的,你会吗?’”其实不光是萝拉的母亲,她的那些姐姐们也都是自私虚伪的人,她们只关心自己的事和利益,对其他的人和事都持有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
与空虚无聊而又严格遵循资产阶级传统思想观念的姐姐们不同,萝拉是独立的、崇尚自由的,她乐意管事。在母亲的派遣下,她去监督工人们搭帐篷。但是面对着这些“下等人”,她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以什么样的身份跟他们交流和相处。一开始她模仿着母亲傲慢的声调跟他们打招呼,但是听起来非常矫揉造作,她有些害羞地又改为这样问候着:“噢——呃——你们来——是搭棚的事吗?”一个高个子工人微笑着回答了她的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和严格的阶级等第观的萝拉在心里这样思量着:“他有多么可爱的眼睛……他们也都在微笑。‘高高兴兴的,我们不会咬人。’他们的微笑似乎在说。工人多么可爱!”这里从萝拉天真的视角读者能体会到她身为一个中产阶层的富家小姐颇为傲慢的态度,也就是说,曼氏较为客观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思想尚未成熟的小女孩形象:一方面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另一方面她又向往着跨越阶级之间的鸿沟。当那个高个子工人闻了闻手上的薰衣草香味时,萝拉感到很惊奇,因为她们这个阶层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甚至一度有了这样违反常规的想法:“工人们真是可爱得出奇,她想。为什么她不能有工人朋友呢?他比那些和她跳舞,每个星期天夜晚来吃晚饭的傻头傻脑的青年们强多了。”对于萝拉来说,她蔑视自己的阶级,甚至有些憎恨那“悖情悖理的阶级差别”。当她听到有一个人称呼另一个人“伙伴儿”时,为了让高个子看看她是多么蔑视愚蠢的习俗,她“大大地咬了一口黄油面包。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女工”。在这里叙事视角的转换凸显了小主人公内心对这种强加在她身上的社会和阶级规范的矛盾的态度。
说到这个小说所要表达的阶级意识这一主题,我们不能不提萝拉的姐姐乔丝,她可以说是极具资产阶级本质的人:势利、傲慢而冷漠。比如,她总爱向仆人们发号施令,而他们也乐于听从她。她弹唱着一首忧郁而悲情的歌曲,但是脸上却绽开了一个“光彩焕发,毫无同情心”的微笑。当萝拉把在厨房里听到的那个工人阶层的邻居在车祸中丧生的消息告诉乔丝,并提议取消花园茶会时,立即遭到了乔丝的强烈反对,并且她还认为萝拉有这样的想法太不可思议了,为此感到很吃惊:“‘不举行茶会?亲爱的萝拉,别这样矫情。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做。没人指望我们这么做。别太过分了。’”而固执的萝拉仍坚持己见,乔丝起初还假惺惺地说着自己其实和萝拉一样难过和同情,但接着“她的目光变得冷酷了……‘感伤不会使一个喝醉的工人复生。’她柔和地说”。在她看来,别人的死活、别人的痛苦与否都与她们无关,尤其是这样一个低级的下层人。这里暴露了乔丝的冷酷无情和强烈的阶级对立观。
在乔丝那里得不到认可,萝拉又跑到楼上去找母亲,然而令她失望的是母亲的反应竟同乔丝如出一辙。当得知并不是在自己家的花园里死了人时,母亲“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而当萝拉提出取消宴会以示他们的宽容和尊敬时,令萝拉惊异的是,她的母亲似乎觉得她说的话有点可笑,更表达了对于那些下层人的蔑视和阶级偏见:“‘我简直不懂他们怎么能在那些小破窟窿里活着。’”萝拉坚持认为她们这样做太狠心了,这一次薛太太终于失去耐心了:“‘你很不通情理,萝拉。’她冷冷地说。‘那样的人并不指望我们牺牲什么。’”说着把手中的帽子戴在了萝拉头上,还夸她有多么漂亮,以此来转移她的注意力。从母女俩的交谈,我们能清晰地体会到薛太太根深蒂固的阶级等第观。
看着镜中戴着那顶漂亮的帽子的妩媚可爱的自己,萝拉的世界观有些动摇了,不知该相信权威的母亲说的话,还是该信自己的判断,不过最后她决定等宴会过后再去想这个问题,这一点暗示了萝拉已经受到了母亲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影响。
茶会进行得很成功,后来薛先生提到了那个死讯,薛太太心里觉得他说这些话很不得体、很不明智,不过随即她有了一个出色的念头:把宴会剩下的吃的东西给那家人送去。这一次萝拉又有了质疑,她认为拿些残渣剩屑送给那可怜的女人有些不妥。不过最终她还是提着一篮子剩饭给差遣到那儿去了,走在路上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对那家人家里躺着个死人这件事不能理解。当她走进那些工人阶级住的胡同、看到他们贫困的生活时,她有了极强的自我意识:“她的衣服多耀眼!还有那垂着丝绒飘带的大帽子。要是戴了另一顶帽子就好了。人们在看她吗?他们一定会的。不该来。她一直知道这是个错误。”后来她被那个悲伤的寡妇领进了厨房,她站在寡妇的立场审视着自己:“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陌生人提着个篮子站在厨房里?”这时的萝拉已然和故事开头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不一样了,起码不再那么傲慢了,甚至有了仁爱之心。而后她走进卧室,看到了那个死者,她觉得有些羞愧,面对着死亡这个现实,突然间她感到自己琐碎的生活是多么荒唐。萝拉隐约意识到生活当中并不只有花园茶会和花边衣服,除了生命和快乐,还有死亡和忧伤。第一次接触到死亡这个现实,萝拉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同时也暗示着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不知所措的她发出了孩子般的一声哭泣,说了一句“原谅我的帽子”就逃走了。
小说的最后一幕是萝拉和哥哥劳利之间的对话,备感困惑和茫然的萝拉竭力想向哥哥表达她从这次与死亡的邂逅所领悟到的人生的意义:“‘人生是不是——’她期期艾艾,‘人生是不是——’但是人生是什么,她没法说明白。没有关系。他很明白。‘不是么?亲爱的,’劳利说。”
在死亡这一现实侵扰她的生活之前,萝拉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和快乐的童话般的世界里,她从未近距离地目睹穷人的生活状况,也从未感受过死亡会带给人什么样的影响。但就在这短短一天中,萝拉去除了之前的稚气而变得愈加成熟,彻底完成了内心思想的成长历程。她先是享受了花园茶会带给她的快乐,而后又体会了死亡带给她的焦虑。从光明到黑暗,从富有到贫穷,从生命到死亡,从大喜到大悲,这样的经历使她领悟到了生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她似乎理解了却无法用一个更为贴切的词来概括人生的真谛,是“好”还是“坏”,是“丑”还是“美”,是“悲伤”还是“快乐”?尽管她没有说明白,但是萝拉的顿悟“暗示着她作为一个少女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同时,也预示着她快乐生活的终结”⑤。她的困惑意味着她仍然被传统的社会角色和阶级观念所束缚。尽管她隐约领悟到了生活的本质并获得片刻的自我意识,一直以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影响的她却又不愿直面残酷的现实,而想着要逃避它,并最终也没能获得那种纯粹的阶级认同,继续生活在自我欺骗的幻觉里享受着阶级特权。
综上所述,在《花园茶会》里,读者的确能深切体会到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而这一点则通过曼氏对人物言行举止,尤其是心理活动的生动描写得以充分凸显。这不仅暗示了小说旨在说明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使我们透视到曼氏的创作思想并领略到其表现主题的精湛的叙事艺术。
①[英]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陈家宁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② 参见Patrick D.Morrow,Katherine Mansfield’s Fiction.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1993:74.
③⑤ 赵文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第25页。
④[英]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陈良廷、郑启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以下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