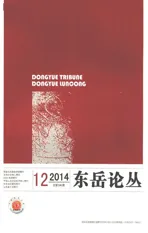香港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概况与困难
2014-06-16郭俭罗金义
郭俭,罗金义
(1.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香港999077;2.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香港999077)
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基本理念
香港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七百多万居住人口有93.6%是华裔。根据2011年的人口统计,香港有451,183非华裔居民,占总人口的6.4%。本文探讨在港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焦点放在这6.4%非华裔人士,尤其是当中比较弱势的南亚裔族群和外籍家务工人。
所谓政治参与,这里可以先从比较传统的定义开始:经过设计的行动去影响政府决策。与选举有关的行动无疑是最典型的一种政治参与,但Huntington & Nelson提醒大家,“政治参与可能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有组织的或者自发的,持续的或者偶然的,和平的或者暴力的,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有效的或者无效的”(1976:3),政治参与的多样性可以陈列在宽广的光谱上,包括利益团体的活动,小区当中的倡议活动,政治教育,甚至是个人串连等。
Leighley & Vedlitz(1999)将有关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主流理论模式归纳为五大种:社会经济地位,心理资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s),社会连系性,群体身分/意识,群体冲突。Amy Freedman(2000)则归纳为四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跟Leighley & Vedlitz的提法相似;文化适应和族群进路,跟Leighley & Vedlitz提的群体身分/意识模式有颇多可以互为参照的理念;Freedman提出的模式当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主义。笼统而言,社经地位(例如收入、职业地位)较高的少数族裔会有较强烈的动机去参与政治;很多研究确定他们比社经地位较低的少数族裔参与更多的选举、组织和运动(Leighley,1995)。不过,近数十年来也有好些研究发现,身处较高社经地位的人士的收入不断增加,但投票行为反而愈见冷漠。要解释这种吊诡的现象,需要考虑到人们更多的心理取向,例如政治利益和效力,对政府的信任,公民责任感等等(Rosenstone & Hansen,1993)。反之,当人们感到自己与大众社会的连系性是疏离、异化、偏见、冷感,政治参与自然下降。要了解社会连系性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些学者关注到少数族群的组织参与,例如在北美社会,人们看到黑人受宗教组织影响和政治动员的现象十分显著(Harris,1994;Putnam,1995)。Freedman(2000)的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路的发挥,它涵盖的是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团体,以及在地社会的整个制度体系。后者关注的是制度体系中是否有各种条件致使或是阻碍少数族群参与政治活动的条件,这也称为政治机会结构。这种思路的另一面,就是具备意识认同的族群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历史的也好,当下的也好,有实际利益或是文化价值也好,都会透过制度体制的里里外外不同的条件和方式影响少数族群的政治参与。
早期的种族关系和政治参与
殖民地时代早期,在香港居住的非华人主要是英国人和南亚裔族群。英国人是殖民地统治者,而跟随着英国人来香港的是印度人。他们大多数是服务于警察部门和英国军队。另外一批在香港定居的印度人是从事贸易的商人,是社会中、上流的精英(White 1994)。英国统治者不愿意跟华人接触,更制定法律禁止华人接近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休闲活动,居住分布或者是政治参与,种族隔离的情况处处可见(Sautman and Kneehans,2002)。
虽然英国在殖民地时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港英政府还是有限度地吸纳了非英国人进入香港的政治体制中。就在1880年和1881年,伍廷芳和庇理罗士(Belilios)先后被委任为立法局的首位华人和犹太裔印度人议员。然而,这种政治吸纳并不是为了达到种族平等或是促进政治代表性,而是为了安抚本地华人群众的情绪和确保统治的稳定性,也让港英政府能够与本地的商界以及专业人士保持联系,得以在香港获取最大的利益。获委任的一般都是商界精英或是专业人士,他们能操流利英语,很多都跟英国有生意往来,而且对香港社会的公共建设功不可没(White 1994)。
被吸纳的有华人和印度人,都是接受了西方教育,认同西方种族与文化优越性的社会精英,在议会或是不同的咨询架构里可以做到与英国人异口同声,支持政府的政策和维护英国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吸纳不同种族的人进港英政治体制的做法,不但没有带来种族和谐与平等,相当程度上反而强化了香港社会的分化,这是一种以种族和阶级作为隔离的分化,而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Baig,2010:33-34)。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接收了数以十万计的移民,包括来自中国内地的华人,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家务佣工,以及为港英政府服务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人的家属和后裔。这使香港社会的整体人口分布发生了不少变化,比如从1981到1991这十年间,香港的非华裔人口翻了一倍。英国人减少了,然而南亚裔和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就迅速加倍(见表一)。少数被港英政府委任的印度裔上层精英已经不能再代表香港广大少数族群人口的利益,其被委任的意义大不如前。

表一 香港居住人口分
回归以后少数族裔的议会政治参与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整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立法会取消了委任制度,使一些在港的非华人的政治参与没有过往“方便”;然而,议会开放直接选举却为他们提供了另一个政治参与的途径。1999年的区议会选举只有两位少数族裔参选人,但是自2003年以来,参选人的背景就趋向多元化。正如议会直接选举的目的是要让市民选出代表他们利益的代议士,少数族裔参选人也不再纯粹来自商界,而是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见表二)。
九七前后有少数族裔背景的区议会议员有加利、马力和罗友圣。加利是印度裔,自1970年代开始落脚于尖沙咀,1985开始参选区议会,当了十多年的独立民选区议员,直到2003年竞选连任不果为止。马力来自巴基斯坦,有民建联政党背景,受政府委任为区议员。加利之后,尽管不乏南亚裔参选人,包括他自己在香港长大的儿子,然而就再也没有人当选区议会议员了。罗友圣是意大利背景的民选区议员,直到2007年退任时,他一共当了23年东区区议员。荷兰背景的公民党党员司马文在2011年的区议会竞选中胜出,成为薄扶林区的民选代表。
少数族裔在区议会里的代表寥寥无几,而在今天的立法会里更加踪影全无。虽然2008年和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都有少数族裔参选人,不过都没有成功当选(见表三)。相对而言,立法会选区比较大,参选人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少数族裔候选人缺乏政治参与经验以及小区网络,如果再没有得到政党的人力和财政支持,成功当选的机会甚微。
尽管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不尽人意,议会制度的开放毕竟为香港市民提供了直接参选与投票的途径。作为香港市民的少数族裔人士,本来应该跟所有本地华人一样拥有同等议会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然而,碍于种种因素,他们的政治参与却受到很大的限制。

表二 少数族裔人士参选区议

数据源:选举管理委员会(2003、2007、2011):区议会选举结果

表三 少数族裔人士参选立法会
中国化与本地化背景下的困难
香港的回归除了是殖民统治的结束,也标示着中国化或者“大陆化”(Lo 2007)的开始。香港人“重新聚集,重新创造和重新发现香港和大陆的历史和文化的纽带”(Ma and Fung 1999:500-1),无论是在政策或是社会经济上,香港人都越来越接近祖国。与此同时,香港人也在回归后产生一股强烈的本地化或本土化情绪,积极寻找香港华人的集体身份认同(Ma and Fung 2007)。在这大背景之下,香港的少数族裔变成了被忽略和被排斥的一群“外来人”。
首先,尽管在香港有一群土生土长的少数族群,他们也拥有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Right of Abode),但根据中国国籍法,中国并不承认他们是中国公民,这妨碍了他们获取香港特区护照,令他们前往外地旅游、工作或升学时构成不便(South China Morning Post,09.12.1996)。即使后来中国当局的态度软化了,允许香港的少数族群申请中国国籍,政府官员却一再重申:“入籍并不是一种权利,是要通过审批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5.12.2002)。这意味着中国国籍法不会让所有香港出生或是已经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少数族群人士得到国籍。在2012-2013年间,有几起少数族裔申请归化中国国籍被拒绝的个案,再次引起香港社会关注,也说明了有关准则含糊而且不合理(明报,14.08.2012;东方日报,30.04.2013)。这种把少数族群公民政治权利排除在外的做法,大大地打击了他们的政治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在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处境下,香港少数族裔在政治参与方面最让他们步履维艰的是语言。在殖民时期英语环境中长期生活或是长大的少数族裔人士,很多都不会说流利的广东话,即使会说,也看不懂中文字。这对于参选人和选民都造成信息和沟通方面的障碍。其中Komal于2008年选战新界东的立法会议席,他表示选举辩论时自己只听懂一半内容,也因此没有选民向他提问。而于2011当选区议员的司马文,就一直觉得自己讲广东话很尴尬(《星岛日报》,2011年8月24日;《星岛日报》,2008年7月31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8年9月14日)。此外,政府在竞选安排方面也忽略了少数族裔的需要,比如说宣传选民登记时往往只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也没有在少数族裔小区里多做推广,使许多符合资格而不谙中英文的南亚裔选民失去投票的机会,也使少数族裔的候选人无法获得到更多同族人的支持(《太阳报》,2003年11月2日;《明报》,2011年7月4日)。
2004年Roger Nissim竞逐立法会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功能组别议席的故事也许能说明“中国化”对少数族裔参政的另一种影响:Nissim是英国人,曾于港府任职,官至地政署助理署长,后转任新鸿基地产高层。他参选时表示自己在港定居超过30年,早已认定自己是本地人,承诺当选后会专注本港事务,又相信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的都是专业人士,英文了得,他不善广东话和普通话不会是大问题。但当时不止一份报章的选情分析都指出,业内人士希望自己的代表能多与中方沟通,帮助业界争取向内地发展,选出一位“外籍”代表不利于这种取向。结果Nissim落败,在六位参选人中仅及第四名,得票数不及当选人刘秀成的一半。看来即使在精英层面,“中国化”也为少数族裔参政添加不小的阻碍(《大公报》,2004年9月4日;《香港经济日报》,2004年9月9日)。
其二是政治团体的支持。大部分少数族裔参选人缺乏本地有实力的政党的支持,这意味着资金和网络方面比较势孤力弱,难以与其他候选人竞争。近年来本地政治团体已经逐渐意识到有需要争取少数族裔人士的支持,而个别政党也成立了少数族裔委员会或是关注组,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苹果日报》,2012年2月7日;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然而,除了荷兰裔的现任区议员司马文曾经获得公民党的支持参加选举之外,还没有出现第二位少数族裔参选人是有政党推选而令之有足够争雄竞逐之力,更遑论是南亚裔的参选人。南方民主同盟成立于2004,靠不足一万元经费创立,是香港首个以南亚裔人士为主的政党,主席是香港华人龙纬汶,历届选举都有积极推举南亚裔参选人,可惜政党经费有限,关注的课题又未能获得社会大众认同,至今还没有发展成一个比较全面和稳定的政党。
议会以外的政治参与
在议会政治以外,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一般活跃于工会组织、压力团体和社团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也被学者称为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摇篮(Martiniello 2005)。它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代表少数族群成员向主流社会的政治团体和大众表达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关心的议题。殖民地时代,少数族裔团体有与宗教相关的,也有以发展专业或是提供休闲联谊活动为宗旨的,更多的是以少数族裔移民的祖籍作为结聚的小区性社团(Vaid 1972),类似华人的同乡会。二战前后,比较有规模的南亚族群团体要算是印度人协会和香港巴基斯坦人协会,他们至今还活跃于香港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社群中。
在去政治化和非民主的殖民时代,少数族裔社团将精力较多放在为成员提供休闲联谊活动,政治要求和倡议性的工作比较少。他们第一次公开地向港英政府争取权益和向香港主流社会表达要求,要算是在回归前有关国籍争议的课题上。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备忘录,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在回归以后失效,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公民海外护照。然而英国公民海外护照(BNO)只是旅游证件而不是正式的英国国籍,持有人也不会自动获得英国居留权。联合声明也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香港的华裔居民能够在九七回归以后自动获得中国国籍,然而对于非华裔居民却只字不提。这意味着有许多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非华裔居民将会变成无国籍人士。当时大概有8000人的南亚社群对前途忧心忡忡,包括在港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及尼泊尔人,他们大部分是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持有人,当中很多已经放弃了原有国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07.02.198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2.02.1986)。1985年,代表6000名英国属土公民护照持有人的印度社团首先向立法局呈递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正式的英国居留权和领事保护。从那时候开始,印度人代表在香港和英国的政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游说工作,费时十多年,不仅获得来自两地不同官员、政党、人权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支持,还引起联合国组织的关注。最后,在各方压力下,英国政府于1997年初宣布向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的少数族裔人士给予具有居英权的英国公民身份(Baig,2010:103-114)。
在国籍争议中有一些活跃的少数族裔团体冒起,其中一个是印度资源组。为了让大众关注香港的种族歧视问题,印度资源组联合了一些本地华人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回教团体和家务劳工团体等,在1999年组成一个名为香港反对种族歧视的联盟,争取通过立法和教育来保障少数族裔的权益和减低种族歧视。香港的《种族歧视条例》立法过程费事旷日,直到2008年通过,2009年才正式全面生效。过程中少数族裔社团一直在背后推动,对于立法成功他们功不可抹(Baig,2010:43-44)。
少数族裔劳工的政治参与
香港目前有大约三十万的外来劳工,大部分是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女性家务佣工。家务佣工的身份限制了她们取得香港的公民身份,因而不能得到居留权,享用本地教育医疗等福利,以及政治参与权利。作为基层移民工,她们不但公民权利不被承认,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还面对工作上的剥削和欺压,其命运跟中产移民有天渊之别(Sim,2007;Constable,2009)。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一些少数族裔家务佣工在过去二十年积极组织社团、工会,联合本地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熬心费力地为争取劳工权益和改善工作条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抗争。由天主教教会支持的菲律宾人组织是香港少数族裔劳工团体和政治抗争的先锋部队(Sim,2007)。最早的一次抗争行动可以追溯至上世纪的80年代初。1982年,菲律宾政府颁布了第857号行政命令,规定所有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合同工必须把至少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汇返菲律宾,而且只能通过菲律宾政府认可的银行,这被民间称为强迫汇款。在港的菲律宾家务佣工于1984联合了11个菲律宾人组织,成立了团结菲律宾人反对强迫汇款的一个社会行动组织。组织收集签名,举行集会,组织抗议等抗争活动,形成其中一鼓强大的压力,迫使菲律宾政府于1985年撤消该行政命令(Law 2002;UNIFIL-HK)。
如果说以上例子说明的是少数族裔劳工如何在香港进行跨国式的抗争以影响原住国政策,那么以下的例子展示的就是少数族裔家务佣工如何影响香港的政策决定。亚洲移居人士联盟成立于1996年,是首个由亚洲不同国家移民和其基层移民团体联合而成,成员包括有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移民劳工组织。1998年香港经济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有议员建议把外籍家务佣工的最低工资降低百分之二十,亚洲移居人士联盟是最早向香港政府提出反对减薪的团体。他们的响应包括在当年的国际人权日组织游行,向当局表达反对意见。香港政府最后同意只降低工资的百分之五。2001年,香港劳工处建议增设外佣税,每位有雇用外籍家务工人的雇主,都要多付400元港币的税,其目的是要将之用作培训项目经费,再培训有志当家务佣工的本地人。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强烈反对,后来劳工处撤回建议。同年,香港政府以增加税务收益的理由再次提出减薪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建议,亚洲移居人士联盟举行记者招待会,号召大约5000名的支持者从铜锣湾游行至中环抗议。香港政府最后同意只冻结而不扣减工资(Hsia,2009)。
2005年12月,香港主办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工人、农民、反对世贸组织和反全球化等人士齐集香港,进行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近年来,少数族裔家务佣工团体获得更多本地政党的关注和工会组织的支持。有学者指出,能够在香港见证外籍家务佣工高姿态地在公共空间出现,进行集会、参加游行、抗议原住国和移居地的政策,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香港政府给予的有限度政治空间。在其他的亚洲城市如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和中东国家,尽管有不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家务佣工的足迹,但这种有限度的政治空间是难以想象的(Constable,2009)。
讨论及小结
少数族裔劳工在本港的选举中没有参选或投票权,主要是透过相关利益团体所组织的社会行动来争取劳工权益;而南亚族裔港人对参与选举、议会政治也欠积极,跟相关理论的整体认识有可以相互参照之处。例如,他们的社经地位都处于社会低层:2011年,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劳动人口平均月薪低于一万元的占47%左右,明显高于全港整体数字(不足40%);同年,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劳动人口任职于最底层的非技术性工人行列的比例分别是36%和42%,远高于全港的整体数字(不足20%);根据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2011),2006年专上程度的少数族裔学生百分比约为总学生人数的0.59%而已,他们在教育阶梯的劣势值得严肃正视。从而可思过半的是他们的心理取向,应该是缺乏动机参与政治,对于参与议会政治的效力、对政府的信任等非常单薄。以2008年立法会通过《种族歧视条例》为例,香港基督徒学会在立法会表决条例前夕,做了问卷调查,发现45%被访的少数族裔人士没有听过该条例草案,而36%则认为条例通过后会令他们生活变差(《明报》,2008年6月10日)。他们对议会政治的心理取向可见一斑。
再者,香港缺乏对提升少数族裔的社会联系性和政治参能够发挥长足作用的组织。与南亚族群相关的宗教组织并不热衷于动员信众参与本地政治,一些与南亚族群相关的利益、压力团体会就个别社会行动组织成员参与,但远远未能孕育出参与政治的规范或模式。本地主要政党对支持南亚族裔人士参政亦是心力不足,民建联运用影响力令巴基斯坦裔的马力得到政府委任为油尖旺区(香港最多南亚裔人士聚居的地区)的区议员,算是异例,但亦为时甚短。马力曾经埋怨说,他加入民建联之前尝试过申请加入某民主派政党,但对方以没有英文表格为由拒绝他,多年来他接触过的政党都让他的要求吃闭门羹(《文汇报》,2004年8月31日)。2007年区议会选举,一些泛民政党在南亚裔人士聚居的尖东选区竞逐席位,虽然以“济弱扶倾”为竞选口号,但却将所谓“印巴籍”和“本地人”清楚分野,埋怨前者投票比后者踊跃而令致自己败选(《成报》,2007年11月19日:A05),对南亚裔港人施加的“他者”标签,令人沮丧。
2007年区议会选举尖东席位结果由民建联成员胜取。民建联相信是动员少数族裔人士起步最早、最有组织、投入资源最多的政党,而在多次选举中也得助于此而获益,包括2012年立法会选举在新界西的佳绩(《香港商报》,2012年9月2日)。事实上,十年前早有从政者估算,最多南亚裔港人聚居的九龙西和新界西,就有超过五万人符合选民资格,票源怎能忽视?九七回归以前,在区议会选举中反而可以有加利、罗友圣等人稳胜议席多年,以少数族裔身分亲自代议;但当“中国化”、“本地化”愈见深入,少数族裔只能在背后支持带有丰厚政党资源的华人走到台前,希冀他们当选后确实实践承诺为他们谋求福祉。当然,最值得深思和继续考察的是,这种社会联系性和政治参与的关系,是不是一种良性互动,抑或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龙纬汶多年前曾说:“本地政党都只视南亚族裔人士为‘蛋糕’,争取选票后却无为对方解决民生问题。”(《星岛日报》,2004年2月2日:A11)这番评论,“不幸地”历久弥新。
[注释]
①Baig,R.B.(2010).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Race Relations in the Legislation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PhD 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②Constable,N.(2009).“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any states of protest in Hong Kong”,Critical Asian Studies,41(1):143-164.
③Freedman,A.(2000).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New York:Routledge.
④Harris,F.(1994).“Something Within:Religion as a Mobilizer of African-American Political Activism,”Journal of Politics,56(1):42-68.
⑤Hsia,H.C.2009.“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Grassroots Migrant Movement,”Critical Asian Studies,41(1):113-141.
⑥Huntington,S. & Nelson,J.(1976).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⑦Law,L.(2002).“Sites of transnational activism:Filipin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In B.S.A.Yeoh,P.Teo and S.Huang,eds.Gender politic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p.205-222.
⑧Leighley,J. & Vedlitz,A.(1999).“Race,Ethnicity,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Competing Models and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The Journal of Politics,61(4):1092-1114.
⑨Leighley,J.(1995).“Attitudes,Opportunities,and Incentives:A Field Essay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48(1):181-209.
⑩Lo,S.(2007).“The mainland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A triumph of convergence over divergence with Mainland China”.In J.Y.S Cheng ed.The Hong Kong Speic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in Its First Decade.Hong Kong: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pp.179-232.
⑪Ma,E.and Fung,A.(1999).“Resinicization,Nationalism and the Hong Kong Identity,”In C.So and J.Chan eds.,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Case studies from 1967 to 1997.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pp.497-528.
⑫Ma,E.and Fung,A.(2007)."Negotiating Local & National Identifications:Hong Kong Identity Survey 1996-2006,"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2):172-185.
⑬ Martiniello,M.(2005).“Political participation,mobilisation,and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offspring in Europe,”in: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Legal Status,Rights,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tate of the Art Report for the IMISCOE Cluster B3.
⑭Olsen,M.(1970).“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Black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5(4):682-697.
⑮Putnam,R.(1995).“Turning In,Turning Out: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PS,28:664-683.
⑯Rosenstone,S.and Hansen,J.(1993).Mobilization,Participation,and Democracy in America.NY.:Macmillan.
⑰Sautman,B.and Kneehans,E.(2002).The politic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Baltimore,Md.:School of Law,University of Maryland.
⑱Sim,A.(2007).“Women in Transition:Indonesia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PhD thesis,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⑲Vaid,K.N.(1972).The overseas Indian community in Hong Kong.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⑳White,B.S.(1994).Turbans and traders:Hong Kong’s Indian communit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㉑《明报》,《数十南亚裔登记选民,不熟投票,倡增宣传》,2011年7月4日。
㉒《明报》,《香港仔巴汉申特区护照被拒》,2012年8月14日。
㉓《成报》,《社民连首次出征无人识》,2007年11月19日:A05。
㉔《成报》,《落区助选,陈太称遭“包围”报警》,2007年11月19日:A03。
㉕《星岛日报》,《“南方民主同盟”成立》,2004年2月2日
㉖《星岛日报》,《司马文怕丑唔讲广东话》,2008年7月31日。
㉗《星岛日报》,《公民党有印籍主任》,2011年8月24日。
㉘《东方日报》,《少数族裔抗议入籍审理不公》,2013年4月30日
㉙《大公报》,《测量师对碰建筑师得益》,2004年9月4日。
㉚《太阳报》,《外籍候选人政纲印六种语言》,2003年11月2日。
㉛《文汇报》,《少数族裔全力支持民建联》,2004年8月31日。
㉜《香港经济日报》,《六人混战两刘格斗》,2004年9月9日。
㉝《香港商报》,《梁志祥陈恒镔团队齐告急》,2012年9月2日。
㉞选举管理委员会(2000),(2004),(2008),(2012),(2003),(2007),(2013):立法会选举结果,检自http://www.elections.gov.hk/elections/legco2000/update/result/index_e.htm,浏览日期:2013年9月2日。
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11):《2011人口普查主题性报告:少数族裔人士》,检自http://www.census2011.gov.hk/pdf/EM.pdf,浏览日期:200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