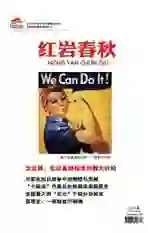“十袋米”月薪从伦敦聘来英国医生
2014-04-21刘重来
刘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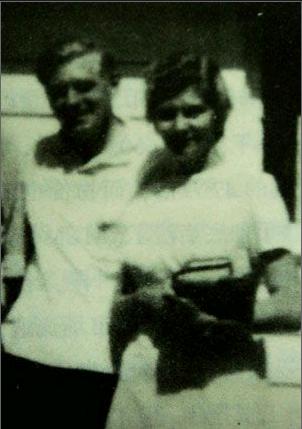

北碚是个自治实验区,在行政系统上是独立的。区主任卢子英先生,乃川中实业巨子卢作孚先生之介弟。他年富力强,剃光头,穿布衣,赤足穿着草鞋,说话做事十足的朴实无华。
这是文学大师梁实秋1979年7月在美国写的一篇题为《北碚旧游》的文章中谈到40年前初见卢子英时的印象。对于北碚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和兄长卢作孚一样,卢子英可谓倾尽心血。正如有人所言:“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而卢作孚为北碚所设计的蓝图,大都是通过卢子英之手来实现的。因此,卢子英当之无愧是北碚的奠基人。”
抗战胜利后,为了发展北碚的现代医药卫生事业,卢子英写信至万里之外,聘请英国医生到北碚医院工作。在他热诚的感召下,英国医生德尔(Dr. Donald Dale)一家欣然接受邀请,远渡重洋,历经艰险,从伦敦来到北碚医院,为重庆医药卫生发展史留下一段佳话,也成为卢氏兄弟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珍贵见证。
一封来自中国的信
1947年秋的一个早上,住在伦敦柏孟塞(Bermondsey)的英国医生德尔(到中国后取名“丁晓亮”,人称“丁大夫”)夫妇突然收到一封异国信件。德尔夫妇虽然不识中文,但通过信封上除英文外的方块汉字和贴的邮票断定,此信来自中国。德尔一家都很吃惊,他们并不认识任何中国人,怎么会有人从万里之遥的中国给他们写信呢?德尔急忙拆开信封,抽出信笺,但上面书写的是自己完全不认识的汉字。
德尔医生夫妇虽然暂时不知信的内容是什么,但拿着这封来自遥远中国的信,作为基督徒,他们却有一种预感:这是一封“即将改变我们一生的信”。夫妻二人“彼此望着说:‘这是我们前往中国之路。……我们心中没有一丝怀疑地确信,它已经把门打开了”。
几天后,德尔夫妇在本地教会一位中国朋友的帮助下,终于知道了这封信件的具体内容。德尔夫人(Penelope Dale,到中国后取名“丁桂贞”)后来回忆道:
晓亮把信递给她(教会的那位中国朋友——编者注)时说:“这是我们去中国之路。”当她读的时候,我们紧盯着她的脸,然后她看着我们说:“真的吗?”我们向她一再保证。她告诉我们,这封信是中国西部,一个名叫北碚的小镇镇长卢子英先生寄来的,他请我们到那儿新建的市立医院去工作。他要我们尽快地去,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说我们可以自由地分享我们所信的,他也为我们提供住宿。
很显然,这是卢子英为发展北碚的现代医药卫生事业向英国医生德尔发来的一封盛情邀请信。
当时的北碚,并不像那位读信人所翻译的只是一个“小镇”,卢子英也不是什么小镇的“镇长”。自1936年划江北、璧山、巴县的二镇三乡成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后,北碚即为一等县的地方行政机构。1942年改为北碚管理局,仍为一等县设置。卢子英当时是北碚管理局局长。
卢子英为什么要从英国聘请医生来北碚工作呢?德尔夫妇来到北碚后,也多少知道了卢氏兄弟为北碚现代化建设的良苦用心。德尔夫人是这样说的:
一九四九年春天的北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卢镇长的哥哥就是民生船运公司的老板,正和他的弟弟合作,要把北碚镇现代化。哥哥提供大部分的资金,弟弟监督各项革新建设,例如柏油马路、路灯、食物干净的市场等等。
从这一段话来看,作为刚到北碚的外国人,对北碚的建设历史知之不多,讲述得虽然不够确切,但对卢氏兄弟“要把北碚镇现代化”的努力印象深刻。而发展北碚现代医药卫生事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但卢子英又是怎么知道德尔医生并向他发出邀请函的呢?这与北碚基督教会有很大关系。
基督教于1920年左右传入北碚,最初信徒很少,也无神职人员驻北碚,仅有教士巡回布道而已。1938年抗战爆发后,不少基督徒随着南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来到后方小城北碚,北碚基督教徒大大增加,于是“北碚基督教会”正式成立,并公推兼善中学校长张博和等7人为执事,管理教会事务。1942年,基督教“华西灵工团”(West China Evangelical Band)应邀从广汉迁来北碚传教,并于1944年在朝阳新村建福音堂,其总执事为英国牧师董宜笃(Archdeacon Donnithorne),北碚基督教会的规模更大了。
卢子英作为地方长官,不仅对北碚的宗教活动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而且与当地宗教界代表人士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他与董宜笃及夫人董英兰就很熟悉,彼此经常来往。据卢子英的女儿卢国模回忆,每逢圣诞节,董宜笃夫妇“还会给家里送来亲手烘烤的蛋糕”。德尔医生来北碚,就是董宜笃夫妇向卢子英介绍的。
德尔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前在伦敦时结识了董宜笃夫妇。有意思的是,德尔医生有着特别的中国情结——他“是诞生在中国的一对英国宣教士夫妇的儿子,常以自称‘白华人为荣,比正宗的华人更爱中国”,他十分向往到中国来工作。正因为如此,当卢子英在一次宴请董宜笃夫妇的酒席上,请他们推荐一位英国医生来北碚医院工作时,董宜笃夫妇马上就想到了热爱中国的德尔夫妇,并郑重地向卢子英作了推荐。德尔夫人记述了这次推荐的过程:
有一天,北碚市卢镇长请他们(指董宜笃夫妇——笔者注)吃饭,通常在中国,这表示做东的要请你帮个忙。饭后镇长问道:“您认不认识任何英国或美国医生,愿意到我们北碚新的医院来工作?”董宜笃夫妇答应把我们的名字和地址给他。
就这样,卢子英知道德尔医生可能愿意来中国工作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发出了一封邀请信。诚如德尔夫人所说,卢子英的这封信,不是一封普通的邀请信,而是一封改了他们一生命运的信。
令人费解的“十袋米”月薪
卢子英在信中告知,他承诺给德尔医生每月的薪俸是“十袋米”,这使德尔一家百思不得其解:薪金一般是用该国和该地流通的货币来支付,而卢子英怎么会提到用大米呢?德尔夫人回忆说:“虽然,当时每个人(包括我们)都不大清楚,每个月十袋米能做什么,在我们到达北碚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原来,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因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而出现的畸形现象。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统一使用的货币——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过14亿余元,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自然灾害等原因,物价暴涨,法币贬值,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总发行量已达5千亿元。到了1948年,更达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法币总发行量的47万倍,而物价也随之上涨了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了。
在这种情况下,和全国一样,当时北碚的民众“已不相信任何纸币,北碚市场流通多用银元。商业活动多以实物计价交易,拒用纸币”。而大米,作为生活必需品,则成了商品交易、工资报酬、经济往来计价的通货。
老舍在1946年所写的《在北碚》一文中谈到,他的夫人胡絜青抗战期间在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工作,其薪酬是“月间拿一石平价米”。因此,当德尔医生一家来到北碚后,才知晓月薪“十袋米”的真相。德尔夫人后来写道:
在我们到达北碚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米是那儿真正的“货”币,那时钱币一夜之间可以贬值一半……镇长答应给晓亮一个月十袋米的薪资,事实上是主给我们一家奇妙的预备。纸币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当我们于一九四九年五月飞往香港之前,买卖已经得用银元,而米仍然是一种价值稳定的通货。
对于德尔医生一家,这“十袋米”的月薪给他们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几十年后,德尔夫人撰写了一部回忆中国之行的书,书名就叫《十袋米——往中国的福音之路》。
漫长而惊险的跨洋之旅
当年德尔医生一家前往中国,可以说是一次漫长而艰险之旅。在20世纪40年代,交通不发达,英国还没有通往中国的班机,德尔医生只能选择坐轮船前往中国。卢子英在信中也告知了他们的旅途,德尔夫人回忆道:
那封信继续说,我们必须自己前往上海,卢镇长的哥哥卢作孚先生是民生航运公司的负责人,他将关照我们乘船逆长江而上,前往重庆,他们会在那里接我们,搭半天的车子到北碚去。
卢子英对聘请英国医生来北碚一事,不仅十分重视,还考虑得十分细致。1948年12月4日,他专门给其兄卢作孚写了一封信,对德尔夫妇到上海后的接站、取行李、送暂住地、支付零花钱、购买至重庆的船票等等,作了周密安排:
英国德尔医生已自英国转美,乘S.S.RHEXENOR Blue Funnel Line首途来华,即将于十二月廿日左右到沪,请兄赐助三事:“一、请兄派员并用汽车到轮船码头接他,代为照料在海关提取行李,护送到新闸路一五三一号内地会暂住。二、请由申公司付给德尔医生相当现金作彼零星用费,账拨渝总公司转北碚文建会归还。三、请由申公司代德尔医生夫妇购申渝二等舱船票二张(直航更好),票价可否请照五折优待?账拨渝总公司转北碚文建会归垫,并请派员照护上船。”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坐轮船从英国到上海,是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程,更何况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之中。这对德尔医生一家来说,困难更大:他们的大儿子安得烈·柯林(Andrew Colin)才3岁,而小儿子彼得·若宾(Peter Robin)才3个月,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所以,当德尔夫妇同意卢子英的邀请,要到遥远的中国西部北碚医院工作时,德尔夫妇的亲朋好友都惊呆了。德尔夫人回忆道:
我们的朋友和家人都以为我们疯了,但是我们确信主在对我们说:“不要靠你们自己的想法,不要为自己想办法,只要完全的信靠我,我必定引导你们。”
不管别人怎么劝说,德尔夫妇去中国的决心已定。1948年10月9日晚,出发的日子到了,德尔夫妇带着两个儿子从伦敦乘火车向港口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进发,开始了一段艰辛的旅程。一大群教会的朋友聚集在伦敦火车站,一起唱诗祈祷,为他们送行。第二天一早,又有一群基督徒到格拉斯哥火车站来迎接。
当天下午,德尔医生一家登上了一艘只能搭乘12名旅客的小货轮“瑞克斯那”(Rhexenor)号。这艘小小的货轮要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沿途停靠纽约、温哥华、马尼拉等地,还要装卸货物,最后才将德尔医生一家送到上海。
大西洋的巨大风暴使这艘小货轮在惊涛骇浪中颠簸,险象环生。德尔夫人回忆道:
大海似乎无意平静下来,现在船虽然不怎么左右摇摆,却前后颠簸得厉害。夜里当船摇摆得特别严重时,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吓的事。我们被一个惊人的碰撞声吵醒,开了灯后,发现彼得和他的婴儿床已经从五斗柜上滑了下来。这本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五斗柜的上端边缘很高,婴儿床在上面是不应当会移动的。在这么大的风暴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彼得被抛出了婴儿床,他的睡衣被钩在暖气管的水龙头上,婴儿床已经摔坏在地上。他倒挂于暖气管上摇摇晃晃,有些吓着,却完全没有受伤。
经过不少惊险,终于在1949年新年第一天的早上,小货轮到达了上海。从英国到上海,整个航程近3个月。
当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后,按照卢子英的嘱托,卢作孚已安排民生公司的人员上船来迎接德尔医生一家了。德尔夫人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元旦一大早,检疫与移民官员们就上了船。上午十一点半前,船已停靠了候此(Holts)码头。三位中国绅士来接我们,唐先生为我们停留上海的期间作了所有安排,王医生预定陪我们搭江轮前往北碚,王医生的一位朋友也加入这个行列,尽量帮我们的忙。他们都留在船上,直到我们的行李被放上了一艘汽艇,然后我们随着他们上了另一艘属于民生船运公司的汽艇,到上海外滩登了岸……接下来的一天,晓亮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海关。民生船运公司提供了一位深谙海关作业的资深专家陪着晓亮,因为有一位传译员对他是十分必要的。
终于到达目的地北碚
然而,当德尔医生一家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上海之后,从上海去北碚也并非通途。这是因为,就在他们航行于大海的3个月时间里,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德尔一家到达上海20天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不得不宣告下野。
由于战争形势的突变,长江航线被切断,民生公司由上海开往重庆的航班已被迫停开,德尔医生一家不得不滞留上海1个多月。直到2月4日,他们才搭乘一架教会的小飞机“圣保罗”号,飞行6个小时,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卢子英和北碚医院院长唐永松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陪同他们前往北碚。
卢子英虽为北碚管理局局长,并没有自己的专车。因此,只能陪德尔一家乘坐公共汽车去北碚。自1946年起,从重庆至北碚有了往返的班车,行车路线是从重庆市中心的七星岗,经红岩村、歌乐山、青木关,到北碚中山路。然而在那个年代,从重庆到北碚的公路还只是一条用碎石泥土铺成的凹凸不平的土路,而公共汽车则是由美国道奇车改装而成,座位是一排排横跨车厢的木条凳。这让德尔一家十分吃惊,德尔夫人是这样描述他们这段最后行程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星期天,我们抵达了期盼已久的目的地(北碚)。但是,即使在这最后一天的行程中也有意想不到的经验。和那些搬运我们的行李上车的苦力们讨价还价之后,大家终于到了所谓的公共汽车站。在我们上车之前,又发生了两件差错:首先,巴士爆了一个轮胎;其次,一个工作人员把水当汽油加进了油箱。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才开始上车。就连上车本身都是件特殊的经验,那些木头座椅横跨整个车身,所有坐在后座的人必须爬过那些座椅。在所有的人都爬了进去以后,前头的两个座位给了我们。我抱着彼得靠着司机而坐,晓亮和安得烈挤在司机后面,市长(指卢子英)和医院监督坐在晓亮的旁边。从重庆到北碚一路风景秀丽,公路工程相当不易,沿途有许多U形急转弯,有一两处公路盘桓爬升到至少海拔一千五百英尺。我们到达时已经天黑了。
德尔一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北碚。从1948年10月9日自英国伦敦启程,到1949年2月6日到达中国北碚,整个行程竟花了4个月时间,个中滋味令德尔夫妇感慨万千。
在德尔一家到达北碚的当天晚上,卢子英虽也十分疲劳,但他和夫人邓文媛仍在兼善公寓为德尔一家设宴洗尘,并让他们与董宜笃夫妇见了面。
细心的卢子英将德尔医生一家安排在北碚民众会堂对面的蓝公馆居住。这是四川军阀蓝文彬之弟的住所,也是当时北碚最好的房子。德尔夫人回忆说,他住的“是一栋当时北碚最大的楼房之一,它下层有五个房间。我们要住在那儿,直到新居建好。这里非常方便,因为离董宜笃家以及晓亮每天早上要去的诊所都很近”。
在《十袋米》一书中,德尔夫人专辟一章并用《终于到了北碚》作为标题来叙述北碚之旅,可见从英国伦敦到中国北碚,旅途中的艰难险阻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快乐却短暂的北碚时光
德尔医生携家人到达北碚后,非常兴奋,想安下心来在北碚工作个七八年,诚如德尔夫人所写的那样:“到了北碚的第一晚,我和晓亮(德尔)彼此说:‘能到这我们将停留至少七年的地方真好,这段期间不需要再旅行了。”德尔医生马上投入到北碚医院的工作中,且很快适应了北碚的生活,德尔夫人回忆道:
我们每天的活动似乎很快就上了轨道。晓亮(德尔)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而我则照顾小孩。中午我们和董宜笃夫妇一起用正餐,这使得我们每天都能见面,也和一些教会的会友接触。从他们身上,我们很快地学到了一些中国的习俗,并且也得以享受到一些道地的中国菜。我们又开始了常规的语言课程,却很快地发现那是得花一辈子工夫去学的!但是我们努力地坚持下去,每当能说一点新的只字片语,就开心得不得了。
德尔一家不仅很快安顿下来,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且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也立即参加了北碚的基督教会活动。德尔医生的到来,在偏僻小城北碚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据卢子英的女儿卢国模回忆,每当德尔夫妇走在北碚小街上,都会引来不少人的注目:“当时居民都很注意这对年轻漂亮、衣着靓丽的外国夫妇,偶尔见他们带着小孩上街,更是引起人们的注意,都喜欢那乖巧逗人爱的洋娃娃,人们都知道北碚住着这些外国人。”
对于初到中国的德尔夫妇来说,中国是陌生的,是神秘的,也是十分新奇的。中国人认为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却让德尔夫妇大为吃惊。如他们雇用了一名女工在家做杂务,这位女工用搓衣板洗衣,用石磨辗米、磨花生米,用土法熬糖等都让他们十分惊奇。德尔夫人记下了令她难忘的几件事:
在我们到达以前,董宜笃的太太董英兰找了一位愿意来替我们帮忙的女管家,每月工资相当于一元美金。我想她一定是做些扫地及清理房间之类的事,然而五十几年以后,还有三件事清楚地记在我的心头。头一件是她在一块木板上,用冷水搓洗我们的衣服,我就不明白这样衣服怎么洗得干净,要不就是洗完一次之后,衣服会成了千疮百孔,但是它们似乎完好如初。我还记得她把花生放在两块大石当中去磨,直到那有点像花生酱一般的东西从石头缝中渗了出来,看着她把那酱刮下,放入一个容器里,使我一辈子都不想吃花生酱了。相反地,晓亮和安得烈却很喜欢把这酱涂在又硬又干的面包上一起吃。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是那“洁净食糖”的绝活:首先把糖摆进一个像炖锅的容器里,将锅放在露天的炭火上煮滚,女管家还得不停地搅拌;煮滚时,她用木杓把浮在面上的杂质清出扔掉,这样好几回。当大部分的杂质都被清干净之后,就把那煮滚的大锅从火上挪开;她继续不断地搅拌,直到糖再一次结晶出来……我们真感激有这样一位助手,她确实比我们每月付给她美金一元的工资要有价值的太多。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4月底,德尔的两个儿子可能由于气候不适和水土不服,均得了肺炎,不得不到位于重庆南岸的加拿大宣教医院医治。正在医治期间,战争形势又发生了更大变化,解放大军逼近四川边境。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德尔一家不得不再次搭上“圣保罗”号飞机离开了重庆。
临行前,德尔夫妇将一床新的英国毛毯送给卢子英,又将自己孩子骑的三轮车送给卢子英的孩子。2012年6月,在北碚卢作孚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卢子英的女儿卢国模将德尔夫妇赠送的毛毯捐予纪念馆,作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
德尔夫妇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为了到北碚从事医疗服务,他们放弃了在英国的舒适生活,经受了旅途中种种艰险的考验。虽然他们只待了短短的3个月时间,但北碚已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记忆。1995年9月,德尔夫妇回到北碚旧地重游,还和曾在他们家帮忙的那位女工见了面,当他们得知这位女工也成了基督徒后非常高兴。
卢子英不远万里诚邀英国医生来北碚工作,与卢作孚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开发大西南的理想有极大关系。除热情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外,卢作孚还极力主张要促成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来四川。他说:
我们除运动外省人到四川来以后,更还要促起世界上的人都到四川来,或来考察,或来游历,使世界上的科学家都到四川来,世界上的工程师都到四川来,世界上的金融界或实业界有力量的人都一齐欢迎到四川来。什么时候可以来呢?这就看我们去做这个运动的力量如何,如果是我们下大决心去做,那么,我们要想他们哪一年来,就可以使他们哪一年来,这纯全视我们用力的程度以为转移了。
卢作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1928年他主持修建北川铁路之时,就曾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出任北川铁路总工程师,还请其参与了北碚城市的设计和规划。1930年卢作孚在创建中国西部科学院时,又聘请了德国生物学家傅德利负责带领少年义勇队去川边考察、采集标本,并请他到生物研究所主持昆虫研究。
卢子英也正是因为秉承其兄卢作孚的思想,才聘请万里之外的英国医生到北碚医院工作。从卢子英的盛情邀请、周密安排,到卢作孚指示民生公司的热诚接待,可以看出兄弟二人志同道合、合作默契。正如卢子英在《怀念二哥卢作孚》一文中所说:
我同二哥的关系,不仅是手足兄弟,还是师生。他把我从小培养到大,我进入社会,又把我带在一起去北碚工作,先培养我为他的助手,后把建设北碚的担子又交给我……我们之间,既有骨肉之亲,又有师生之情;既有上下之属,又有同志之谊。从小共患难,长大同命运……我们相处的几十年间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非常融洽,从没面红耳赤地争吵过。
二人的这份亲密与默契,正是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效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的努力,为偏僻小城北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本文作者系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图片来源:除注明出处外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吴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