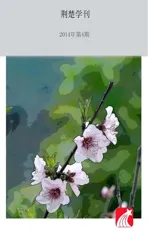荆楚文化与文化开放
2014-04-16王小玫
王小玫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荆楚文化与文化开放
王小玫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荆楚文化作为南方地域性文化的代表,在中华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开放兼容是文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规律,在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亦呈现出开放性与兼容性,体现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融、社会风俗文化的融合等。特殊的地理位置、移民浪潮的影响、荆楚人自身的包容性,使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更加突出,也使荆楚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荆楚文化;开放性;兼容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形态等因素不同,中华文明又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色,如以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和以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各有千秋,各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1]导言荆楚文化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开放兼容是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荆楚地区有着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长于此地区的荆楚文化,亦呈现出开放性与兼容性,这使荆楚文化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一、荆楚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元素
任何文化构架,都会在自己原有的传统基础上,不断与外部文化发生撞击与交流;某一文化如果仅仅封闭地自我发展,那它终将成为供人凭吊的遗迹。文化得以发展绵延就需要开放。何谓“开放”?开放是指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度打开门户,与外地、异族、外邦发生文化互动和人员交往,在工具器物、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乃至价值系统诸层面,进行深度不等的沟通,呈现文化传播上较为顺利、流畅的局面,达到传出与接受、影响与涵化、冲突与整合的对立统一[2]。开放性与兼容性使荆楚文化中有较多的外来文化元素。
(一)荆楚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从考古出土文物中,我们能发现中原文化对荆楚文化影响深远。集中分布于江汉平原的屈家岭、云梦的胡家岗的文化遗址就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有密切关系。“这些遗存的陶系,以泥质红陶为多;其次为泥质黑陶和磨光黑陶,有少量的灰陶和橙黄陶;纹饰以素面为多,其次以剔纹、弦纹、戳印纹、划纹、附加堆纹,以及少量兰纹,并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片;类似仰韶文化的器形有:鼎足,鼎足有尖锥形和圆柱形两种,均为夹砂红陶,红顶盆、钵、碗、红陶缸形器。这里的鼎足,足身较长,有的足上端饰有按窝纹,这种鼎足与后岗类型鼎足十分近似。”[3]
在湖北境内出土的青铜器也有中原文化的元素,如车马器的车、乐器的编钟和兵器的戈等。发生在楚地的三次大规模南迁,对荆楚文化亦有重要的影响。黄陂的盘龙城等都具有明显的中原特色。
(二)荆楚文化中的巴蜀文化元素
从出土的漆器来看,早期的巴蜀文化对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蜀漆早在三星堆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考古发现的雕花漆木器是其典型代表,而此时楚文化还未发展成熟。直到春秋战国之际,蜀楚两地出现大量漆器制成品。楚地发现了较多的漆器,如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雨台山楚墓群、江陵望山楚墓、当阳赵家湖楚墓群等。就时间而言,三星堆文化要早于荆楚文化,蜀漆也比楚漆要早一些。通过水路陆路,早期的蜀漆工艺传播到楚国境内,楚人将漆器发展壮大。
在青铜器铸造方面,楚人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学习模仿巴地的兵器。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楚国青铜器是熊渠所用的一件铜戈,它就是仿巴蜀三角无胡戈而成。1975年在湖北江陵发现两把巴式剑,其形状为柳叶形长剑,并铸有虎形图案,这与巴地出土器物的虎形图案颇为相似[4]243。这些都得益于荆楚文化的开放兼容精神。
从墓葬方面亦能看出巴蜀文化的踪影。湖北江陵地区出现过巴人的墓葬,如当阳的赵家湖就曾经发现带有巴人墓葬特质的墓葬。巴人的墓葬多为西向墓,而在楚国此类墓葬形式较为少见,可见这一地区两种文化的交融。
另外,在楚国的木雕、丝绣中亦能看到巴地器物上常见的虎形图案等,如虎座风架鼓,不论图案还是造型设计都带有巴文化的痕迹。
(三)荆楚文化中的吴越文化元素
从考古出土文物来看,越文化对荆楚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上。
根据考古资料看,铜绿山古铜矿的早期开发者为扬越先民。在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中,发现有越文化特征的陶器残片。以铜绿山为中心,北至英山,南至通城,西至武昌,东至黄梅、阳新和江西九江,发现了数十处古文化遗址,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春秋战国,从文化内涵上看,应为越文化遗存[4]244。出土于湖北江陵、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被视为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越王勾践剑,至今不生锈且锋利,从侧面反映了越国高超的冶炼铸剑技术。楚王曾经专门派铸剑师风胡子等前往吴国、越国求教铸剑技术。在目前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剑中大部分为楚剑。如果说吴越善于铸剑,那么荆楚儿女将这一技术广泛应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越式鼎是越地出土文物的典型代表,其特征是上部鼎口立耳比较小,底部为圆形腹较浅,但也出现过少数的腹部较深、三足细高且向外伸展器形。这种鼎在楚地屡有出土,如在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雨台山之东九店楚墓、湖北宜城雷家坡楚墓中都有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式鼎。在众多出土文物中,一种有盖、附耳敛口、细高足外斜的鼎,与其他越式鼎相比形制更加地接近楚式鼎,是经过楚化了的越式鼎。靴形钺是一种典型的越地器物,在荆楚大地亦有发现,在湖北江陵拍马山25号楚墓和湖北秭归官庄坪等遗址都出现类似的兵器[5]。这些正是楚、越两地文化交流的体现,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越文化得以传播的关键。
(四)荆楚文化中的群舒文化元素
群舒位于今安徽江淮地区,是先秦时期的古方国,有着500多年的历史,对早期江淮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与荆楚地区也有文化上的交流。
从出土的青铜器看,群舒文化对荆楚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矩形钮盖鼎,是群舒文化青铜器的代表。其主要特征为平盖,盖顶中心为一环形钮或扁平状方环钮,盖周分别有三个矩形钮,两耳附于鼎腹或口沿下,敛口多呈子母口,弧腹略鼓,亦见卵形腹者。此器形在楚鼎中亦可见,如淅川下寺楚墓M7:6鼎。戳印圆点纹和旋纹组合为群舒典型的纹饰,在湖北枝江出土的余大子鼎耳部也可见到这种纹饰,可能是通过战争等途径传入。小口鼎在楚地也有出现,不仅出土数量最多,而且自春秋中期一直流行至战国中晚期,在楚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6]。这些考古文物的出现正说明了荆楚文化与群舒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五)荆楚文化中的他国文化元素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100多颗玻璃佩珠,被称为“蜻蜓眼”。“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别称,发源于西亚或印度,这些地区相信眼睛有辟邪的功能。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记载了曾侯乙墓的玻璃珠的材质:“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7]此后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一直没有定论。近日,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运用现代科技对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进行检测,成功测试出了玻璃佩珠的主要化学成分和物理特征。结果表明,这些“蜻蜓眼”的材质具有西方常用玻璃的化学成分和特征,是西方的玻璃制作工艺的代表,与我国战国时期兴盛的玻璃工艺在材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此外,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173颗“蜻蜓眼”,标本检测断定是西方制造的;装饰在越王勾践剑柄部的淡绿色玻璃,也被检测证明是从南亚或西方进口的[4]248。这些“蜻蜓眼”是什么时候传入荆楚大地的?专家认为,公元前552年至公元前506年这段时期,彩色玻璃珠传入楚国的时间就在这一时期,属于春秋晚期,这比陆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更早,可见楚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不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还是吴越文化、群舒文化、百濮文化,甚至外域文化都可以在荆楚文化中看到,这是荆楚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最好的物质层面的印证。
二、荆楚文化与地域文化
荆楚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还体现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联系交融上。在古代时,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融合,到了近代,与西方文化碰撞,这些都彰显了荆楚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一)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对荆楚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了荆楚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自夏初至战国中期,以祝融后裔芈姓部落为主的中原人(楚人的先民)三次大规模南迁,移居荆楚地区:第一次发生在夏初禹征三苗部落后,芈姓楚先祖南迁荆楚,居住在丹水、汉水之间和汉水下游以西地区;第二次发生在商代中期,中原移民“居国南乡”,楚人先祖鬻熊、熊丽、熊绎等以丹淅流域的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汉水流域逐步向南开拓,最后入主汉水东部,建立盘龙城(今武汉黄陂区)等据点;第三次是在西周时期,中原移民移居荆楚,在汉水流域建立随国、曾国等“汉阳诸姬”[8]。北方部落的不断南迁,也将其文化带入了荆楚大地,与荆楚原有文化融合、转化。芈姓楚祖迁入后,与荆楚原著民不断地融合,形成了楚民族,建立了楚国。但这时期的荆楚文化初露锋芒,特色还不多,水平还不高,几乎无足称道[1]导言。之后,楚人不断开拓疆土,使中原文化、原始部落文化和农业文化、荆楚蛮夷文化糅合,形成了成熟的荆楚文化。成熟型的楚文化,是以萌芽型的楚文化为本源,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多,在楚国的集权统治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蛮夷文化为助力,在这些文化交流、化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64。
先进的中原文化对荆楚大地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楚人学习中原文化的风气十分兴盛,贵族更甚。《左传·哀公六年》载:“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濉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9]楚昭王的做法与民间相反,同时得到了中原儒家文化代表孔子的认可,可见楚国贵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楚墓出土的竹简,主要内容包括儒家经典和道家经典两部分。儒家典籍有《成之为之》《淄衣》等十四篇,道家经典有《老子》。儒家典籍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诗》《书》的内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郭店楚墓在楚国都城纪南城周围,地点与仓山楚墓基本相同,下葬时间可以确定为楚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郭店楚墓出土了这样多儒家典籍,它让我们了解了楚国贵族的精神生活,其不但对巫筮重视,也热衷于儒家的经典典籍。
《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曾命大夫上塞为太子师,为了更好地使太子受教,他请教贤大夫申叔时,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0]从申叔时的言辞中,我们可知其早已熟读过这些经典,其中《诗》《世》《乐》《春秋》等,都是中原周王朝的典籍,同时将这些经典列入太子学习的课程中,可见楚人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和重视。
不同地区人员的流动,交流与融合必不可少,语言在这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的传播是以人为基准的。据西汉扬雄《方言》统计,在楚国疆域内,南楚、陈蔡、吴越之间相同的方言有30余条,而楚与北方中原地区相同的方言亦有30余条。这正是两个区域文化长期交融的结果,它对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丰富了两地的区域文化,使之呈现出更多的特色。
(二)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源于长江上游,荆楚文化源于长江中游,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两地文化交流频繁。古代的楚国人进入巴蜀有两条路:一是从汉中大巴山进入巴,然后到蜀;另一条是走水路,经夔门和巫峡到达四川。要想从蜀地到达楚,可以从长江顺流而下,几天就能到达楚国的郢都。如果从巴国的汉中到楚,坐几天的船也可以到达楚都郢[11]。便捷的水路、陆路交通为两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
在艺术领域,巴文化中的音乐对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巴人的音乐高亢悠扬,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宋玉对楚王问》载有“曲高和寡”的故事,提到了“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等楚国歌曲[12]。“下里巴人”是楚人、巴人杂居之地流行的歌曲,一唱而应者数千,可见其影响力。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楚人都很喜爱,楚人对音乐的这种热爱,更展现了楚人的开阔胸襟和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
“万舞”,亦称“武舞”“象舞”,源自巴人的“武舞”。巴人的“武舞”出现在战士阵前,可鼓舞士兵的士气。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3]巴人“武舞”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楚国的“万舞”,因其以干戚作道具,又称“干戚舞”或者“大武之乐”。1960年,湖北荆门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一件大铜戚,上有“大武辟兵”的铭文,应该是演出“武舞”时所用的道具[4]242。舞蹈形式的融合,正是荆楚文化开放性与兼容性的体现。
巫在荆楚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巫起源于巴蜀地区,后出三峡,沿江而下传入楚地,对楚人的民风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书·地理志》记载:“江汉信巫鬼,重淫祀。”无疑就是受到巴文化的影响。楚人引以为傲的楚辞更是融入了巫的元素。楚辞的“鼻祖”屈原,在《楚辞》《九歌》《天问》中多次提到巫,其中《九歌》很大部分源于当地祭祀神灵的乐曲,《天问》的问话体例则采自《盘天歌》,《招魂》所述更是与现代土家族地区巫师招魂的基本程序类似,据考证土家族先民正是古代巴人。宋玉在《高唐赋》中记述了楚襄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该故事明显也因巫文化的吸引流露出对巫山神女的无限思慕[14]。荆楚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使其不断地与巴蜀文化交融,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三)吴越文化
吴国和越国是长江中下游两个重要的国家。吴越文化则是长江下游最主要的地域文化。先秦时期,随着楚国的不断发展壮大,荆楚文化对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先秦时期是楚越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
首先体现在文学方面。作为荆楚文化文学的突出代表——《楚辞》,是楚越文化交流的写照,也是荆楚文化开放性与兼容性的具体体现。刘向《说苑》记载有鄂君子皙叫人翻译“越人歌”的故事[15],朱自清认为,经楚人译过的《越人歌》是见于典籍的中国第一首翻译作品,这表明了楚越在语言上的互通。同时《说苑》完整记录了《越人歌》的内容,从中体现出了在文学创作方面《越人歌》对《楚辞》的影响,如《越人歌》中多处用到了“兮”,“兮”作为语气词使用,在屈原《九歌》《离骚》等作品中多能看到,《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的比兴手法也明显受《越人歌》的影响。《离骚》中也涉及了越地的地名和植物等,如“朝发韧于苍梧”中的“苍梧”就在越境内,“纫秋兰以为佩”中的“兰”等。《楚辞》的其他篇目中也有越文化的影响。越文化在楚人的文学发展之路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对越文化的吸收更多的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特别是越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楚人在与越人的交往过程中,学习了越人先进的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不断地推陈出新,促进了楚国自身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上文已述,此不赘言。
另外,在社会生活方面,荆楚文化也吸收越文化。解放前湖南长沙出土的楚俑中,有所谓“黥面”女俑,此即越民族的文身之习;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女俑和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上妇女的发式,颇似越人的“椎髻”[4]246。
由于对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直至近代西方文化等都采取积极的吸纳态度,在不断的融合发展中,荆楚文化丰富了自身文化内涵。
三、荆楚文化开放性与兼容性之成因
作为中国中部地域性文化的代表,荆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文化,形成开放性与兼容性的品格,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移民文化因素和楚人主观诉求等。
(一)地理环境因素
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决定人们的气质和性格,进而对人类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产生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荆楚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对荆楚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荆楚地区处于我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之间,地形多样,有平原、丘陵和山地,其四周群山环绕,中间为有着“鱼米之乡”之称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地貌整体呈现出盆地形状。
荆楚地区有发达的水系交通,武汉有着“九省通衢”的美誉。湖北境内除长江、汉江干流外,其他河流河长在5公里以上的有4 228条,河流总长5.92万公里,其中河长在100公里以上的有41条。湖北湖泊众多,水资源丰富。湖泊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上,面积达到百亩以上的有800余个,总面积共计2 983.5平方公里,因此,湖北省被称为“千湖之省”。近代以来,荆楚陆路交通纵贯南北,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这些地理环境因素促进了荆楚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使荆楚文化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移民文化因素
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正如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所述:“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使文化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表现出强烈的地理特征。人们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16]不同的文化在移民浪潮的作用下相互融合,使原有的地方文化不断地丰富发展。
荆楚地区是一个居民比较复杂的地区。居民的复杂性,是由于移民众多。如前文所述,三苗的流徙、芈姓楚人的入主、“楚蛮”与“汉阳诸姬”等的流动,对早期荆楚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后,秦汉时期、六朝时期、唐宋明清时期的移民都对荆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北人纷纷南下,逃避战祸。南迁的路线有三条,其中中线主要流入荆楚地区。中线移民主要来自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河南地区人们出“义阳三关”,经过大别山,进入随枣走廊东部,有时稍东渡淮出弋阳路,经过大别山东麓的英霍山地,南下到今鄂东地区。三省人们还通过武关路出关中或经方城隘道到南阳,最后集中在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游,有部分进一步南下,到达荆湘两广[17]83。移民主要有三次高潮,东晋时期最盛。在这个时期,移民及其后代所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并不大,但移民中多有高门望族、官僚、文人学士,其在文化水平、经济实力等方面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在荆楚地区所起的作用与其所占的人口比重呈负相关。东晋中后期至南朝,以南来北人为主体、由低等士族所控制的襄阳武力集团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在政治方面,如梁武帝的兴起,就是仰仗雍州兵力;江陵成为南朝与建康齐驱的文化中心,也与这些高门望族汇集江陵有关[17]87。移民的进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据《隋书·地理志下》记载:“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仪经籍焉,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18]
隋唐五代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北人南迁,随着人员往来的增加,荆楚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继续融合。这期间伴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荆楚大地的经济中心也向南部和东部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文化发展,逐渐形成了襄阳、荆州、鄂州、长沙、朗州(今湖北襄阳、江陵、武汉、湖南长沙、常德)等经济和文化中心。文化的根基是文化得以更好发展的基础,其中襄阳和荆州两地因有着良好的经济和历史文化基础,显得最为繁盛,其中有襄阳本地的大文人杜甫、孟浩然等,也吸引了大批别地文人骚客至此,从而带动了这些地方乃至荆楚地区市民的习文之风。据《酉阳杂俎》记载:“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虽然其中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荆州、襄阳二地文化的繁盛,两地文化的繁荣也带动荆楚文化的发展。
到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攻,百姓流离失所,在新建立南宋政权的推动下,大批北人南下,形成了又一次移民高潮。这次移民运动,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范围、规模、人数更甚。在北人南下的大背景下,加之经济社会的发展,荆楚地区文化风气兴盛,在兴学、读书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需求。两宋之际,官学、书院在荆楚地区大范围内出现,兴办书院、讲学风气在湖北盛行,便是例证。
明清之际,“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对荆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方言为例,现代湘语分布在湖南的湘江和资水流域,大致以长沙为界,长沙及其以北地区称为新湘语,以南地区称为老湘语。老湘语比较保守,古全浊音声母字一般仍念浊声母,新湘语区则一般已念为清声母音字。赣方言语音的最大特点是无全浊声母,这正是新老湘语差别的关键。明初江西移民在改变了长沙地区人口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长沙地区的方言体系,即赣方言,但长沙地区周围依然是湘语区,以后逐渐侵蚀这一赣语区,终于形成没有浊声母的新湘语。湖北也有类似的情况。今鄂东南至今仍是赣方言区。新编《武昌县志·方言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认为,武昌县南部的江西方言属于南昌方言系统[17]100-101。
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对荆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人是文化的主体,移民浪潮的涌入使得荆楚地区原有的文化受到了冲击,多种文化不断地融合、发展,带来了文化上的多样性和融合性。
(三)楚人的主观诉求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为的选择因素对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荆楚地区人们的主观诉求也是荆楚文化开放性与兼容性的重要因素。不论是统治者贵族,还是下层民众对先进的外来文化,都有极大的包容态度。楚文化得以成长、发展与统治者开放的政策分不开。楚国在长达530多年的对外扩张中,总共灭掉了61个国家,楚国对这些小国的民族政策较为开明,尽可能摈弃民族偏见,《左传·襄公十三年》称之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4]238。
另外,楚人追新逐奇的开拓进取精神,也促使楚人不断地将其他文化消化吸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例如在青铜铸造方面,楚人吸收百越民族的冶炼工艺和中原诸夏的铸造技术,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需求,或发挥,或改造,大胆创新,形成了楚人的铸造专利——熔模法,使得楚国的青铜冶铸,成为“支撑楚文化美仑美奂高堂邃宇的六大支柱之一”[1]导言。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将熔模铸造技术推向高峰之作[4]229。
荆楚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造就了荆楚文化开放兼容的气魄。地理位置的原因、移民浪潮的影响、自身的积极进取使荆楚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1]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冯天瑜.中华开放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5.
[3]周原强.对孝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点认识[C]//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
[4]王生铁.楚文化概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5]朱燕华.从考古资料看楚、越文化关系[D].厦门:厦门大学,2007.
[6]孙振.群舒青铜器初步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
[7][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6.
[8]江凌.试论荆楚文化的流变、分期与近代转型[J].史学集刊,2011,(5):73-79.
[9]李梦生.左传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08.
[10]国语[M].[吴]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8.
[11]林军,张瑞涵.巴蜀文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14.
[12][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宋玉对楚王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626.
[13]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2.
[14]张明杰.互动中的巴文化:巴文化的开放性体系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15][汉]刘向.说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09.
[1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2.
[17]罗运环.荆楚文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18][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79.
[责任编辑:陈如毅]
G127
A
1672-0758(2014)04-0022-06
2014-07-08
王小玫(1989-),女,辽宁大连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