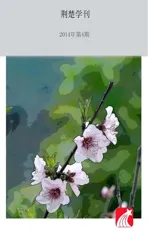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荆楚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2014-04-16梁桂莲
梁桂莲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荆楚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
梁桂莲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等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元丰富和博大精深;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又与中原文化和而不同,显现出其“独处南方”的独特地域文化气质。以地缘文化角度视之,荆楚文化的发生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生成的某些规律,而且其发展、演变,也反映了地域文化打破地域、种族、制度差异,参与民族文化构建,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必然。
地缘文化;荆楚文化;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文化
作为中国文明史早期在楚民族区域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荆楚文化确有着南方文化的一般特征,足以代表南方文化,但同时荆楚文化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动态演变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它不断融合其他文化,最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同构体;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丰富,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化,因此,只有以动态的眼光,才能描摹荆楚文化这一突破地域、时间、民族局限的文化的丰富可能性和发展性。本文即以地缘文化为视角,试图从荆楚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来揭示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生成的一般规律,以及地域文化参与中华民族文化建构、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必然和时代趋势。
一、地缘文化的概念与荆楚文化的形成
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自然因素(地理、位置、气候等)和人文因素(制度、宗教、习俗)共同作用的结果。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创立了环境地理学,提出要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考察范围的观点。之后,黑格尔又对地理环境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认为一个“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在“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缔造形成的关联上,人们又提出了“地缘文化”的概念。相比于“地理环境”,“地缘文化”更具有统摄性和包容性,是指在同一空间区域内,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族群,因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在历史、语言、信仰、道德、风俗、艺术、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层面上或隐或显地呈类同性、趋近性的文化现象[1]。地缘文化包括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风俗、地域文化性格三个层面,其中,文化景观作为物态文化,是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文化风俗则指各种社会规范和习俗;文化性格,则反映了一个区域的意识形态和审美情绪、思维方式等,是文化的核心和根本。
荆楚文化作为活跃于江汉之滨的地缘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性格和文化思维,并日益沉淀,成为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分析,荆楚文化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山林未启的自然环境是形成荆楚文化神秘莫测、精彩绝伦的文化形态的基础
人类聚居地的环境、土壤、气候的差异,是影响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环境、土壤、气候,统称为物质环境,是最先作用于人并形成人类环境感知的基本因素。作为一种基础且行之有效的认知模式,环境感知不仅支配着人们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方式,而且也影响着人们对世界、自我的认知和判断,并进而影响人们对社会结构、社会习俗等一系列精神世界的建构。因此,地有南北,人分东西,地域环境的复杂性,形成了人类对世界、社会认识建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令尹子革对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僻处南方、水网密布的地理位置,三面环山、奇骏诡秘的地形地貌,虫蛇出没、水害频繁的生存环境,不仅形成了楚人对原始、神秘的自然环境的敬畏,而且也形成了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宗白华在论及钟鼎镜盘的境界时就说:“当时人尚系在山泽原野中与天地的大气流衍及自然界奇禽异兽的活泼生命相接触,且对之有神魔的感觉(《楚辞》中所表现的境界)。他们从深心里感觉万物有神魔的生命和力量。”[2]洪亮吉在《春秋十论》中认为,“楚之山川风物,足以发抒人之性情”。在与自然、宇宙接触的过程中,楚人应物斯感,不仅体验到山川风物的谲怪奇伟,而且“记楚地、名楚物”,睹物兴感、随物赋形,借艺术表现自然景物的奇峻伟丽、灵动秀美,创造出原始神秘的歌舞、响绝伟辞的词赋,以及造型奇特、制作精巧的青铜器、漆器、壁画等。这些都浸透了楚人对天地山川的热爱、敬畏以及借艺术表征自然、创造美感的精神追求。
(二)夷夏融合的民族政策造就了荆楚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性格
从已有的出土资料来看,楚文化是一支融合了中原文化、三苗文化、巴文化、越文化、淮夷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文化形态。这种多元融合的文化形态一方面与楚地“立乎东西南北之中,介乎华夏、蛮夷之间,可以说是非夏非夷”[3]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楚国夷夏融合的治国之策和民族结构有关。楚先民由中原南徙至江汉蛮荒之地,栖身于土著荆蛮之间,为了生存发展,楚人与当地及周边的蛮夷友好相处,建立了和睦的关系。与中原诸夏严格的“夷夏之辨”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即采取了尊重各民族习惯、保留各民族文化的政策,由此“蛮夷皆率服”。在此过程中,楚国不仅在政治上、民族上结夷夏为一体,而且还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在吸收夷夏文化之所长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张正明先生指出:“楚文化之所以能迅速成长,主要就是因为楚王国长期奉行了一条混一夷夏的路线。”[4]如楚式鬲对苗式鬲、中原鬲的改造、创新,楚语对巴语的吸收、楚文学对龙的表现,楚人对越人青铜冶铸技术的学习等。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融汇夷夏文化的基础上,楚文化才后来居上,创造出灿烂辉煌,体现当时南方文化最高成就的楚文化。
(三)尚巫重神的社会风俗造就了楚人浪漫飞扬、玄思冥想的文化气质
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地,其俗信巫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舞以乐诸神。”虽然在中国古代,祭祀鬼神的传统由来已久,三代以前便有了巫、祝、史,专主神道,但西周以来,理性精神大增,周人一变殷人“先鬼而后礼”的做法,转而“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制定了一套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制度。而在楚国,由于未开化的自然环境,以及源远流长的巫文化传统,楚地很大程度上仍被巫风笼罩,上自君王,下至庶民,都信巫好祠。《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桓谭《新论》曰:“昔楚灵王矫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由此可见荆楚文化巫风之盛。
这种弥漫于宫廷与民间的神巫之风,不仅成为楚人的宗教信仰,形成楚民族稳定的心理结构,而且也造就了楚人浪漫飞扬、玄思冥想的审美情趣和充满想象、瑰丽多姿的神话传说。在楚人看来,天地山川、风物走兽,无物不神,无物不灵,既能上天入地,又能神游八极。受巫风浸渍,楚人不仅把这种对山川风物的想象带进了艺术作品,如祭祀歌舞中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而穿戴的精美的服饰、妆扮成的至善至美的神灵形象,出土的文物中对神奇诡异的禽兽和飘渺灵动的云气的表现,以及以繁复艳丽的龙、凤形象等,而且还大力发展了玄思冥想、心游万仞的精神气质,如屈原“驾飞龙”“麾蛟龙使梁津”,庄子言鲲鹏,不知几千几万里等。表面看,这种超凡的想象力是楚地巫风巫教浸淫的结果,但实质却反映了楚人对生活的美化和对自然、宇宙的无穷美妙遐想,以及日益发达的审美能力。
(四)奋发图强的国家心态造就了荆楚文化不拘礼法、尚独求新的文化思维
地处尚未开发的荒僻的江汉之滨的楚民族,历史上一直被视为“蛮夷”,受到中原诸夏的歧视和侵伐。到战国时代,孟子还称其为“南蛮鴂舌之人”。特殊的地理位置、备受歧视的处境,不仅形成了楚人桀骜不驯、彪悍刚烈的民族性格,而且也激发了他们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因此,楚先王虽以子男之爵立国,却并不满足于偏安一隅,而是奋发图强,积极争取与诸夏同等的地位。公元前705年,楚伐随,要求周“王室尊吾号”,在遭到拒绝之后,随即“自尊为王”。这种奋发图强、不甘落后乃至“僭号称王”的举动,虽然在当时显得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但却充分显示出楚人的自信和大无畏精神,反映到文化上,即形成了楚人不拘礼法、卓然不屈的文化思维。因此,楚人虽积极向中原文化学习,却又并不为其所缚,而是结合自己经济、政治、民族、宗教、习俗等社会实际,在吸收夷夏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与中原文化受农耕文明影响,推崇理性,排斥个性、异己,不善创造不同,楚文化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不服周”的国家心态,在学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挑战精神和创造精神,既不受理性教条和习俗礼法的束缚,又张扬生命、尊重个性独创,率性而为,任性而歌,将自己的民族特性和审美创造发挥到了极致。
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环境、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作为中国远古时期南方文化的代表,荆楚文化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因素。正是在自然环境、社会习俗、民族政策、国家心态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荆楚文化才不拘一格,发展成具有独特审美创造和艺术价值的文化体系。
二、荆楚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荆楚文化自然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楚之立国到楚国灭亡,八百年的历史,不仅见证了楚先民开拓进取的伟大功业,而且也见证了荆楚文化绚丽至极、繁盛一时的辉煌。之后,由于秦汉王朝的统一,荆楚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和周边区域文化融合,发展演变成湖湘文化、江汉文化和江淮文化[5]。近代以来,荆楚文化在民族、国家的理念追求下,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关注现实、人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发展。
大体而言,荆楚文化在近代的转型与分化,大致有以下路向:
(一)从崇武卫疆、忠君爱国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爱国精神发展
与中原华夏诸族相比,楚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深重的灾难,不仅磨砺了楚人剽悍勇猛的性格,而且也培养了他们崇武卫疆、忠君爱国的民族情怀。从楚国平民保家卫国,“相率而为致勇之寇”到屈原“忠而见疑,自沉于江”的忠君爱国,千百年来,楚文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早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并激励着一代代革命志士为之奋斗、牺牲。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爱国民主运动随之高涨。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救亡变法到“五四”爱国运动,从戊戌六君子的慷慨赴义到武昌首义战争,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战争,中华大地上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救亡图存、富强兴民的爱国运动,涌现出一大批精忠报国、慷慨赴义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与楚国“崇武卫疆”、忠君报国的朴素爱国思想相比,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入人心,“爱国精神”的内容和实质有了很大的改变,更富有现代色彩。
其一是爱国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就是“中国”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古代的“中国”是指“中央之国”,即中原地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则指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统一体。古代的爱国,爱的是自己的城邦,如屈原之爱楚国。现代的爱国,爱的是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文化传统等。其二是爱国的精神、实质发生了变化。古代的爱国,表现为守土、守人、忠君;现代的爱国,则是为了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打破封建主义专制制度,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富强就成为现代“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包含着对祖国不受欺凌和人民不受压迫的反抗,同时也体现为对新的国家理想的追求和实践。
(二)从追新逐奇向革故鼎新、尚新求智发展
荆楚文化自先秦时代起,就有容纳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传统,这种创新不只体现在某一方面,而是政治(首创县制、积极变法)、经济(量入修赋、开渠筑陂)、军事(发明连弩)、科技(天文历法、青铜铸造)、人文艺术(骚体、浪漫主义诗歌)等领域的全方位创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儿女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创新精神,并以其经世致用、鼎故革新的实践致力于近代文化转型。
如在湖北,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积极学习西方技术,创办各种工商实业、发展军事、改革教育、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等,由此促进了湖北的近代化进程。在湖南,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一系列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措施和举措。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也大力鼓吹民智,倡导西学,创办实业,在改变湖南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革命的青年才俊。湘潭人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主张,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荆楚文化不仅赋予了两湖人民敢于争先的品质,而且也涵养了他们创造、创新的潜能。在列强入侵、山河破碎的时代,两湖人民开风气之先,或鼓吹民智,为民族崛起而呐喊;或献计献策,为革新政治而绸缪;或投身革命,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近代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实现了民族伟大富强的光荣梦想,荆楚文化也由此发扬光大,实现了现代转型和持续发展。
(三)从忧国忧民向关注现实人生发展
“楚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韧不拔的使命感。《左传》经常出现楚国君主和执政重臣告诫宗戚文武不得忘记熊绎、若敖和蚧冒三代君主的艰苦创业。”[6]所处时代的不安、动荡,险恶的地理位置,使得楚人的忧患意识几乎与生俱来。屈原是荆楚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承袭了荆楚文化的忧患意识,并发展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民生关怀。屈原之后,这种忧患意识和民本思想,就一直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作家、诗人。
近现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民生”思想的深入,荆楚文化“忧国忧民”的内容、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是从不忘先祖遗训发展为对人文精神、民族之根失落的忧虑,如寻根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等。其二是从国家无望、人民无路可走的忧愁发展为对国家、政治、人民前途的关怀思考,如政治讽刺诗、归来的诗等。其三是从民生多艰的关怀发展为对现实社会、底层人生的关注、思考,如乡土诗、乡土小说、新写实等。
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繁衍地,其作家自然也继承了荆楚文化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从闻一多的《死水》《洗衣歌》等到胡风、绿原、冀汸等的七月诗派,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熊召政的《张居正》,从方方、池莉的新写实小说到刘醒龙、陈应松等关注山区底层人民的书写……湖北作家始终以现实人生为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承担着对民族、历史、现实的反思之责。从其作品中,我们既可看到他们勇于担当、心系民众的济世情怀,又能看到荆楚文化匡世济民思想的闪光。
(四)继承浪漫飞扬精神,专注于对人的本性的发掘和被压抑层面的关注
浪漫精神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屈原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注重对自我情感的抒发和张扬,开创了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在此之后,李白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将诗歌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明代后期,湖北公安三袁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因袭主义,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作家作文写诗要解放思想、张扬个性,由此推动了诗文革新。
“五四”以来,随着民主、自由、科学观念的兴起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提倡,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的强音,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主张,得到进一步肯定。与现实主义关注现实人生、注重客观不同,浪漫主义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如郁达夫《沉沦》对自我灵肉的剖析、袒露,郭沫若《女神》对新我的塑造和对个性、解放的呼吁等。因此,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浪漫主义实带有张扬生命、放飞想象的情感纾解性质。
“五四”之后,浪漫主义文学退潮。受荆楚文化浸润的作家沈从文在吸收浪漫主义、道家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对都市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行批判,关注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侵蚀,提出了建构“人性小庙”的文学理想。在这方面,沈从文不仅是荆楚文化的承继者,而且也以其作品实现了荆楚文化在现代的转化和回响,他的《边城》《三三》《凤子》等一大批作品都以沅湘流域为背景,不仅再现了古老的荆楚文化的原始、神秘,而且也以其赤诚、大胆的人性描写,再现了荆楚文化人与自然谐和、物我统一的优美化境。
作为一个自成特色,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荆楚文化的转化和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内容和特质也会体现在现代文化、文明的方方面面,因此,以上所举的四个转化路向,只是择其要者而论之,并不能包涵全部的荆楚文化的内容。但透过这四个路向,我们认为,荆楚文化并没有过时,也没有消亡,它不仅参与着现代文化、文明的构成,而且还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荆楚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认同。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多元共生共存终至一元演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民族都会在自己的族群之外,不断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碰撞、交流,自我更新、演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生长繁衍于中华大地的华夏民族的子民,每个民族都会基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而突破地缘文化、种族文化的限制,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构建和文化认同。
荆楚文化作为中国文明史早期形成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其自身内部经历了楚、巴、苗、越等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演进,是多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和结合体;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荆楚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又不断受到来自“华夏文化”的引力,有着从边地向中心、从蛮夷向华夏融合、演进的诉求。因此,在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进程中,荆楚文化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不仅以其灿若星河的文明,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主体,而且也在发展、演变中积极参与着现代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价值信仰的构造和创新。
首先,荆楚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楚国是周朝时期由华夏族在中国南方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因此,楚国自产生之日起,就接触到先进的中原文化,感受到中原文化的魅力,并在其后的发展中,自始至终坚持学习中原文化。
其次,荆楚文化是融夷夏为一体的文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楚人在发展壮大后,通过征战、民族融合,不仅实现了政治统一,而且还主动学习华夏文化和其他各民族文化,丰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楚国积极贯彻“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国家政策和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原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表面上看,这段话称颂了楚国的赫赫武功,但深层地看,楚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属诸夏”,华夏化和建立华夏化的国家。因此,在武力征服各蛮夷后,楚国还通过安抚的方式,使之与楚民族融合进而试图建立统一的华夏化国家。
再次,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荆楚文化日益打破地域、民族限制,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楚亡后,秦汉王朝建立,荆楚文化随楚地一起,被纳入秦汉王朝的历史版图,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之后,荆楚文化历经秦汉王朝的汉化、三国时期的战乱、北方移民的南迁等,而不断与中原文化和周边区域文化融合,获得了创新发展,如原属楚地江淮一带的荆楚文化与淮南文化融合,发展成江淮文化,南宋时,荆楚文化又析出湖湘文化。但不管如何演变,楚地作为中华民族领土的一部分,始终没有逸出中国历史的版图,荆楚文化作为重要的地域文化,虽影响深远,余音不绝,但也始终没有超出华夏文明的阈限,相反,随着秦汉文化的统一和传播、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儒学逐渐在荆楚大地占据主导地位,影响改变着荆楚文化的风格与面貌,如宋代的湖湘学派、晚明的鄂东泰州学派等,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主张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由此推动了儒学在晚明乃至近代的转型。
不仅如此,荆楚文化在“华夏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批文化名人,他们的出现,不仅带动了荆楚文化的发展和文化风气的兴盛,而且也促进了荆楚文化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影响、交流。文学方面:《楚辞》作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影响了一批文人如宋玉、景差、王逸等竞相模仿,而且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研究。《楚辞》之后,有李白激情昂扬的诗篇、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公安三袁的性灵文学,近代以来闻一多的诗歌、曹禺的戏剧等。哲学方面:有义理精深的道家学说,宋代的湖湘学派、晚明鄂东泰州学派等。此外,艺术、政治、军事等方面,也是人才济济,成就斐然。概而言之,从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到闻一多追求自由、争取独立的爱国民族精神,从言微旨远的老庄学说到近世体用合一的改革变法,从辛亥首义第一枪到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从戊戌六君子慷慨赴义到近现代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荆楚文化以其独有的魅力,不仅激励了众多学者、文人、革命志士的实践和阐扬,而且也在其绵延不绝的传承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化,从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支柱。
近年来,学界对荆楚文化的认定,即是从这方面入手的。目前较为学界认可的荆楚文化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取义成仁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谐精神[7]。仔细推敲,这五种精神虽然都可以说是荆楚文化的特质,却并不是独有的特质:一是这几种精神在每个民族、每个诸侯国中都存在,是共性而非个性;二是荆楚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古代、近世、当代的时序概念,其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早已从远古楚地发展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三是这几种精神是现代人对荆楚文化的总结,现代中国人作为华夏炎黄子孙,在文化上、心理上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其对荆楚文化的认定,不可避免带有建立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共同体这一文化诉求。因此,荆楚文化的五种精神,既是楚民族适者生存、谋求发展的文化体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战胜自然,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精神写照和执着追求。这由此也表明,荆楚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超越了地域、种族、时间之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参与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实践创新,并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精神信念和价值取向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民族融合和各地域文化的广泛参与,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也就是承认多元、容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一方面来自于各民族、地域文化对“中国”这一政治主权和文化意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涵容性和包容性,即在承认中国主权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允许各民族按照自己的社会模式、宗教习俗、生活习惯生活,在这一前提下,各地域、民族必然会基于共同的民族归属和文化认同,突破时间、空间、地域条件的限制,汇聚形成大的中华文化的统一体和综合体。
历史地看,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建立在华夏文化的基础上的。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华夏文化通过其影响力和辐射力,带动周边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成为各少数民族共同认可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信仰。近代以来,由于共同的历史遭遇,各民族同仇敌忾,奋勇抗敌,缔结了共同的使命感和国家观念。当今世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深入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包括海峡两岸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社会价值理念,成为凝聚亿万人民造福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共同精神信仰!
[1]杨艺.从中国地缘文化看中国人“和为贵”的平和心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6): 256-263.
[2]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M]//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4.
[3]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J].民族研究,1983,(5):1-12.
[4]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4.
[5]江陵.试论荆楚文化的流变、分期与近代转型[J].史学集刊,2011,(5):73-79.
[6]陈金川.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489.
[7]刘纪兴.荆楚文化的内涵及其创新特质简论[J].文化建设,2007,(2):41-43.
[责任编辑:卢红学]
G127
A
1672-0758(2014)04-0016-06
2014-05-09
梁桂莲(1981-),女,湖北当阳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湖北文学、荆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