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诸城市的亚文化与青少年的心理
——动漫、轻小说、cosplay以及村上春树
2014-04-13千野拓政
〔日〕千野拓政
东吴讲堂
东亚诸城市的亚文化与青少年的心理
——动漫、轻小说、cosplay以及村上春树
〔日〕千野拓政
周宏(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日本朋友千野拓政教授来给我们奉献一道美味的精神佳肴。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千野拓政教授,千野拓政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生于日本大阪,一九七九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中文系,在东京督立大学中文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一九八九年在日本流通经济学部担任讲师。后历任日本明星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现在是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千野拓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普通话研究,同时,他还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艺批评,翻译介绍等工作。千野拓政工作的特点很明显。他把文学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致力于对现代文化生活进行理论阐述,这一点是很可贵的。在我看来,学者不应把自己套在一个所谓学术世界的封闭空间悠然自得,学者的使命就是要运用自己已经获得的理论来解释世界和牵引世界,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要义无反顾地把自己获得的真理奉献给人们,帮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升华,我感到千野拓政直面现实、引导现实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千野拓政主要的作品有《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对文学感到现代的瞬间》、《我们跑到哪里去》等。近年来,千野拓政在我国许多高校都作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千野拓政教授给我们作讲座。
一、问题的所在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特别是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纷纷说起文学的边缘化。当中经常涉及青少年离开文字、不看文学作品的现象,而且说这个现象不只是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在整个东亚的城市都能看到。
可说实在的,目前受年轻人欢迎的文学作品并不少。比方说,在日本,二〇〇九年出版的村上春树的长篇《1Q84》第一、二、三卷一共卖出四百多万册,二〇一二年出版文库本以后又卖出四百万册。在中国,余华的《兄弟》卖出三十五万册(我觉得这个数字也相当好)。别提纯文学,在轻小说(lightnovel)和漫画等亚文化的领域,比村上春树还畅销的作家有的是。比如,在日本,谷川流的轻小说《凉宫春日》系列一共卖出两千多万册,尾田荣一郎的漫画《航海王》(One Piece)每一卷初版打印二百五十多万册。在中国,郭敬明的《幻城》销售二百万册,《小时代》每一卷一百万册。还有ver.1.5,2.5等漫画版,销量也不错。爱看如上作品的读者主要是青少年。(有些统计表示目前村上春树的读者当中中学生不多,主要读者是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但支持村上的读者仍然可以说是青少年。)这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抛弃文学,相当爱好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说,爱好广义的文艺作品。只是他们的兴趣已经不在传统的纯文学,好像开始迁移到亚文化或另类文学方面去。那么,人家感到的文学的边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为什么在整个东亚城市能看到如上现象?
在我看来,这密切地相关于文艺文本阅读方式的变化,以及它带来的读者和文学的关系的变化。而且其背后存在着青少年在社会上的位置的变化,以及它带来的青少年对社会的感受的变化。
现在,部分年轻的读者阅读轻小说等文本的方式显然跟以前的文学阅读不一样。最简单地说能看到如下变化:如果可以说以前的读者看作品时欣赏故事情节、思想和文体等,现在的部分青少年读者讲究的是作品里的角色的形象(character)。他们可以离开作品的世界,单独地欣赏这些character。当然,他们不是完全忽视作品的故事情节和思想,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这样阅读作品。其实,对部分读者,阅读作品时character已经成为跟故事情节和作品的思想同样或比它们更重要的因素,而且这样阅读文本的读者越来越多。这种倾向在动漫、轻小说(即lightnovel,在中国大陆相当于校园小说或青春小说)、yaoi(也称作boys love,是女生看的男生同性恋的故事)小说等领域特别明显。
而且,如上文本阅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读者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的变化。到了现代以后,我们看文学作品时,相信作品里的世界和我们精神上的世界沟通,并且读者期待着通过作品的世界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某种真实。至少我们认为,能让读者感受接触到真实的作品才算优秀的文学。对这一点,文学不外是给每个读者启示更大的世界的东西。我们看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的部分年轻读者对作品的寻求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爱好如上亚文化或另类文学作品的青少年有他们的圈子或者共同体。他们在圈子里的活动很活跃,不只是欣赏作品,也有参与创作等生产行为。他们经常跟其他爱好者交流,有时候在网上,有时候碰面,在共同体里面聊天,分享喜怒哀乐。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活动和交流当中,他们得到某种现实感或跟人或社会接轨的感觉,换句话说,获得成就感或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好像同好之间的交流跟通过作品接触到真实一样重要(有时候比它还重要)。如果可以这样说,读者群对作品寻求的东西的变化确是很大。
更重要的是如下一点:出现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青少年的某种无聊、孤独或闭塞感。更正确地说,他们对社会带有某种隔阂的感觉。加上,这种现象不是惟在日本,而是几乎所有的东亚城市都能看到。那么阅读文本方式的变化(着重character)和读者对作品的需求的变化(跟同好交流为主)和青少年的心理变化有何关系?
从如上问题意识出发,我在东亚的五个城市(北京、上海、台湾、香港、新加坡)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分为问卷调查和访谈两个部分。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大学生,问的是有关村上春树的接受,动漫、轻小说的接受,参与同人活动的情况等。访谈的对象是轻小说作家、漫画家,同人写手,同人活动的策划人、参与者等,问的是他们活动的情况和他们的想法。在此根据调查的结果,初步探讨上述问题。
二、东亚城市的青年文化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当下东亚城市出现的共通现象。
二〇〇二年三月,日本有名的广告公司“博报堂”亚洲生活者研究小组出版了一本书,《从这儿开始亚洲销售战略》(博報堂アジア生活者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アジア·マーケティングをここからはじめよう』PHP研究所,二〇〇二,東京)。这本书的内容是如下三点:第一,在东京、台北、香港、上海、北京、汉城、新加坡、吉隆坡、曼谷、胡志明,十个亚洲城市进行的青年消费生活调查的结果。第二,通过调查所了解到的跨境消费情况。第三,从如上调查归纳的向亚洲青年的销售战略。这些都是为了推销日本产品,和我的文化研究没太有关系。
其实,这本书所收录的在十个城市的街上所拍摄的年轻人的照片颇有参考价值。看这些照片时,如果不注意背后牌子上的文字——是片假名还是汉字(其中还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区别),是罗马字还是韩国字母,是泰国文还是越南文——你肯定看不出他们是哪个城市的小伙子或小姑娘。因为包括服装、头发、化妆在内,他们的整个面貌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个事实证实着,虽然文化、历史、社会背景都不一样,当代亚洲青少年的消费生活,无论在哪个城市都非常相似。
说实在的,不仅仅是消费生活,当代东亚城市青少年的文化趣味也有不少共通的地方。举一个例子,读者们是否知道如下作品:《名侦探柯南》(原题:名探偵コナン)、《新世纪福音战士》(原题:新世紀エヴァンゲリオン)、《灌篮高手》(原题:スラムダンク)、《逮捕令》(原题:逮捕しちゃうぞ)、《侍魂》(原题:侍スピリッツ)、《心跳回忆》(原题: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这都是几年前在东亚城市的青少年当中非常流行的作品。前两个从动画出发,后来扩大到漫画、小说、游戏、模型等领域。中间的两个从漫画,最后两个从电子游戏出发,后来同样出现其他领域的作品。
如上作品都是日本原创。一九八〇到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的漫画和动画片席卷亚洲城市。其实,到了二十一世纪,各城市的年轻人开始享受亚洲各地的作品,双向的流行成为普遍的现象。比方说,本来在韩国的网上流行的卡通形象“mashimaro”,后来到中国大陆被叫作“流氓兔”,风靡一时,在东南亚地区也受欢迎。就我的经验来说,在曼谷能买到“流氓兔”的布娃娃,去柬埔寨旅行的时候,当地的导游小姐所带的皮包上也有“流氓兔”的图画。
以前在亚洲,看漫画的主要是小孩子。除了报纸和时事杂志的讽刺漫画以外,成人基本上不看漫画。成人(包括年轻人在内)看漫画的习惯从六十年代的日本开始,渐渐扩展到亚洲各地。现在东亚城市的大多数年轻人好像自古以来的传统似地看漫画。①1959年3月创刊了两种周刊漫画杂志,是《少年サンデー》和《少年マガジン》,这是很重要的变化。以前的漫画杂志差不多都是月刊,价钱比较贵,一般的小孩子买不起,算是只有请求父母才能买到的东西。所以,万一父母情绪不好,孩子们就读不到漫画。跟它相反,上述周刊杂志不算贵,每一本30块和40块日元。当时每天的零用钱一般10块日元,存了三四天的零用钱就能买到一本,并且跟朋友交换,两种杂志都能读到。就这样,日本的大多数小孩子开始习惯性地看漫画。几年以后为了女孩子的周刊漫画杂志创刊,再过几年,上中学到了不想看小学生的漫画的年龄,创刊了为中学生的漫画杂志。后来,也创刊了实验艺术的漫画杂志、黄色的漫画杂志,这些显然是为成人的漫画杂志。这意味着,当时长大以后继续看漫画的人已经不少。在60年代日本,大人看漫画的习惯是这样形成的。所以,在日本60岁以下的人当中还在看漫画的不少。
除了动漫以外,其他领域的情况也差不多。关于流行音乐,现在亚洲的青少年听日本歌曲成为普遍的事情,比如宇多田光、安室奈美惠、AKB48等歌手很受欢迎。(我在中国买的宇多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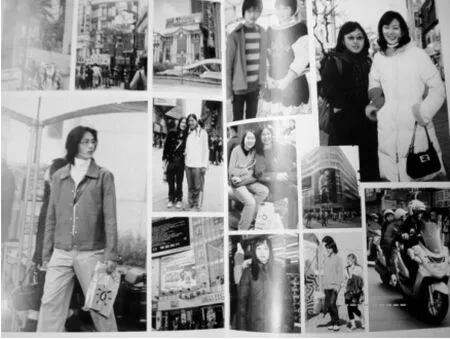
图1 哪里的青少年?
在中国,开始翻译日本漫画是在1980年代初,可能1981年的《铁臂阿童木》最早,以后陆续出版《森林大帝》等作品,都受欢迎。只是这些漫画用连环画的形式出版,影响也有局限。最早用日本漫画书的形式出版的漫画可能是1990年的《圣斗士星矢》,之后漫画开始流行发生很大的影响。出现中国原创的漫画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跟日本一样,部分爱好这种漫画的人成长以后继续看漫画。所以在中国,看漫画的人基本上是40岁以下。东亚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差不多。光的CD是福建制造的,不是盗版而是引进版。)与此同时,香港、台湾、韩国的不少歌手进入日本的歌坛,受青少年的欢迎,这样的倾向近几年特别明显。这意味着,东亚城市的青少年共同享受同样的流行音乐。(比方说,香港的张国荣、刘德华、梁朝伟,台湾的飞轮海,韩国的少女时代、东方神起等明星几乎都在所有的东亚城市受欢迎。)
电视剧和电影的情况也同样。众所周知,九十年代日本的电视剧和电影受到亚洲城市观众的热烈欢迎,你肯定还记得日本的电视连续剧《东京爱情故事》(原题:東京ラブストーリー)或电影《七夜怪谈》(原题:リング)等多么流行过。后来,“韩流”过来,韩国的电视剧和电影席卷整个亚洲城市。典型的例子是《冬天奏鸣曲》(日文题名:冬のソナタ)、《我的野蛮女友》(日文题名:猟奇的な彼女)。中国的电影也在整个亚洲普遍流行。比方说,中港合作的《英雄》,李安的《色·戒》等作品风靡一时,另外,不少香港、台湾、韩国的演员在日本制造的电视剧或电影上演出,受大家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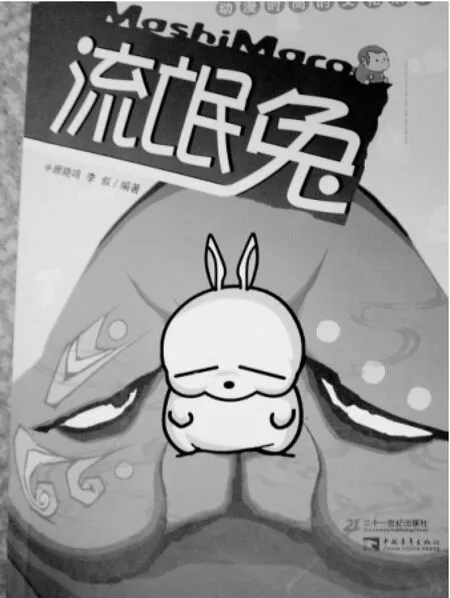
图2 mashimaro

图3 在柬埔寨看到m iashima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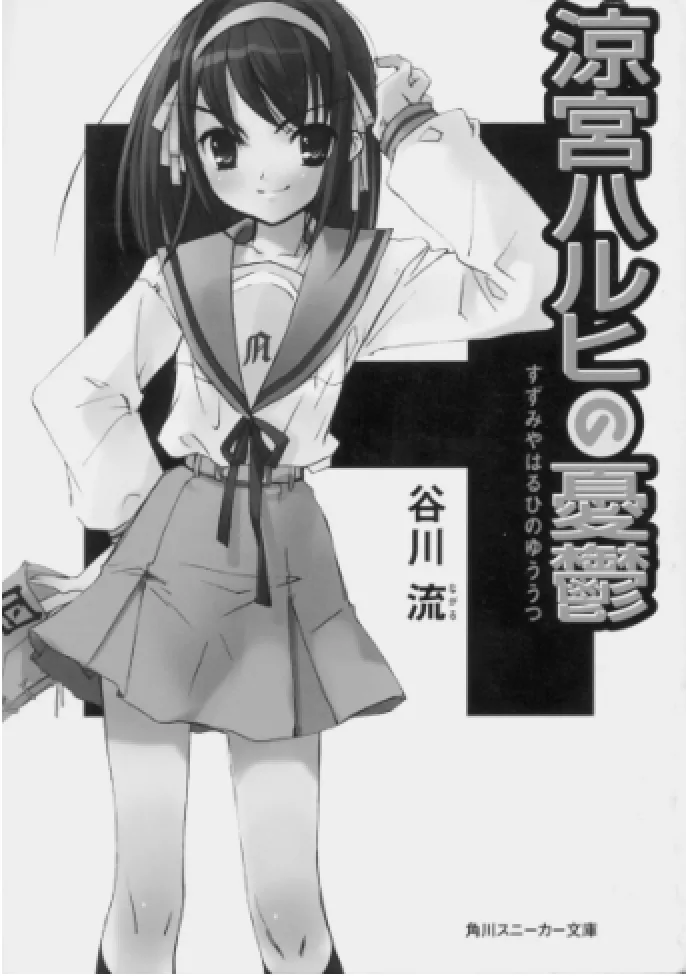
图4 日本的轻小说《凉宫春日的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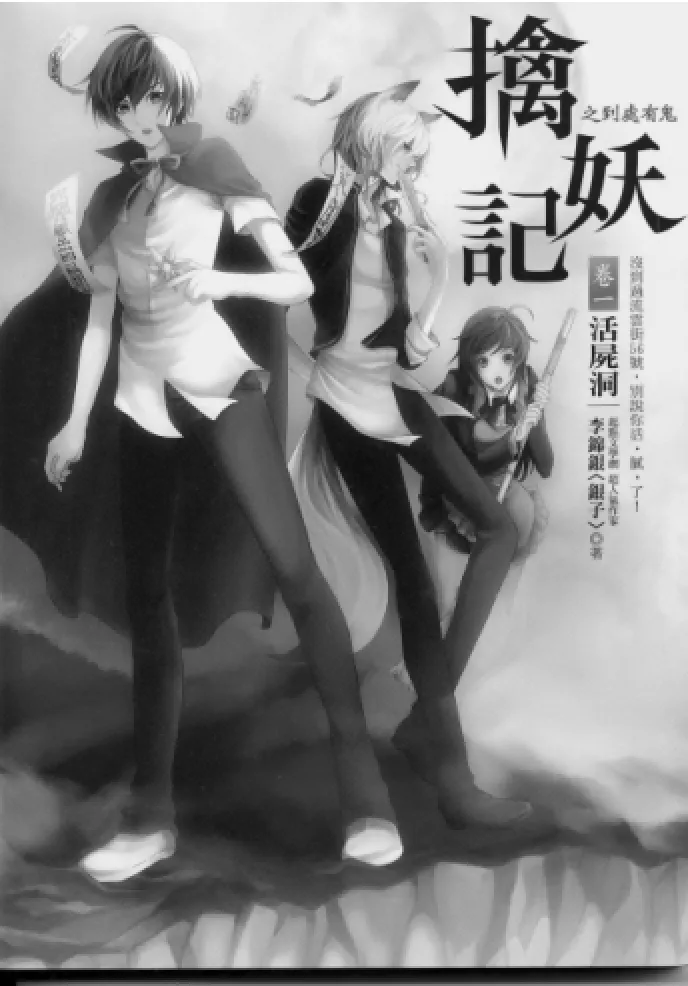
图5 台湾的轻小说《擒妖记》
在文学的领域也发生共通的文化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轻小说”的流行。“轻小说”这个称呼是一九九○年在日本开始使用。也就是以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要读者的小型本小说(日本把它称为“文库”或“新书”),内容非常多样,也有科幻或幻想的作品,也有所谓“世界系”小说(描述普普通通的学生突然被卷入左右地球或世界存亡的大事件的故事),还有描述学生的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的所谓“日常系(或空气系)”小说等等,不能简单地概括。只是在书店里一拿到这种书,就明白跟其他通俗或类型小说有所不同。举个例子,封面和插图多用漫画,作者也是年龄跟读者差不多的青少年。它们有角川sneaker文库、电击文库等不少品牌,并出了不少非常畅销的书,其中几个作品的销售量超过村上春树,比如,谷川流的《凉宫春日》系列(角川sneaker文库,二〇〇三),西尾维新的《戏言》系列(讲谈社novels,二〇〇二-二〇〇九)等。这些作品除了爱好者以外,开始受到日本整个社会的关注,比方说,文艺评论杂志EURECA分别编“《凉宫春日》系列”和“西尾维新”的特辑,冲方丁的Mardock Scramble三部曲获得二〇〇三年的日本科幻大奖。
轻小说不只是日本国内,在东亚各城市也受青少年的欢迎。在台湾,除了进口日本的轻小说以外,当地原创的作品也不少,有台湾角川轻小说大奖等文学奖,不少人投稿。在中国大陆说“轻小说”主要指日本进口的作品。但也有原创的类似轻小说的作品,就是所谓“青春小说”、“校园小说”之类。举一个例子,郭敬明的《幻城》初版或再版时封面和插图都是漫画,明显模仿日本的轻小说。在香港和新加坡,说轻小说主要是日本和台湾的作品,因为市场规模很小,当地原创的小说不多,其内容也是描述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喜剧或描述青春苦恼的少年小说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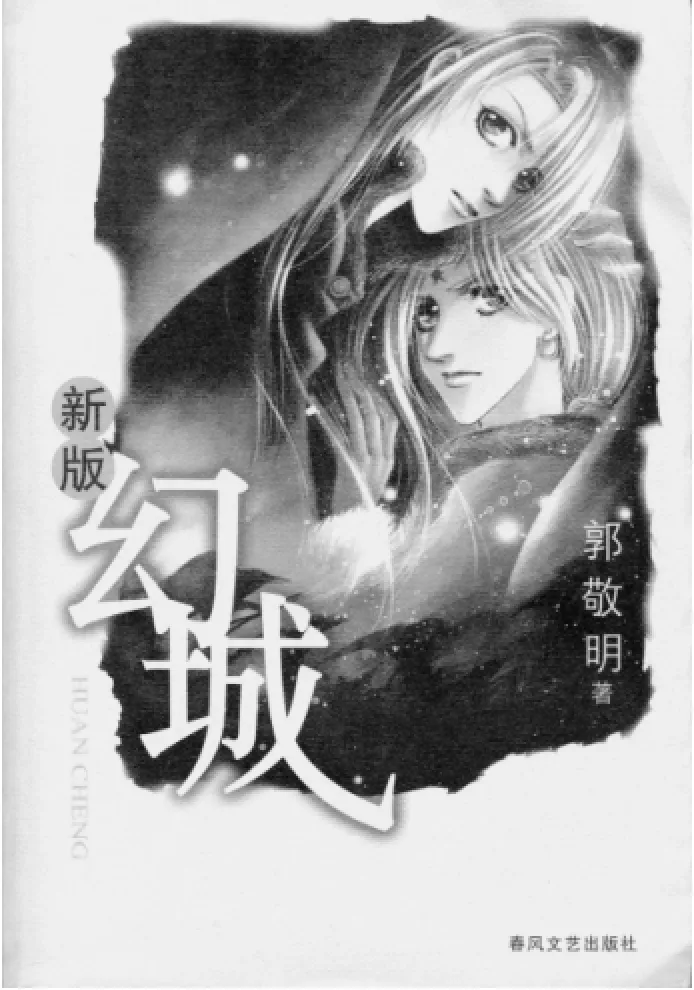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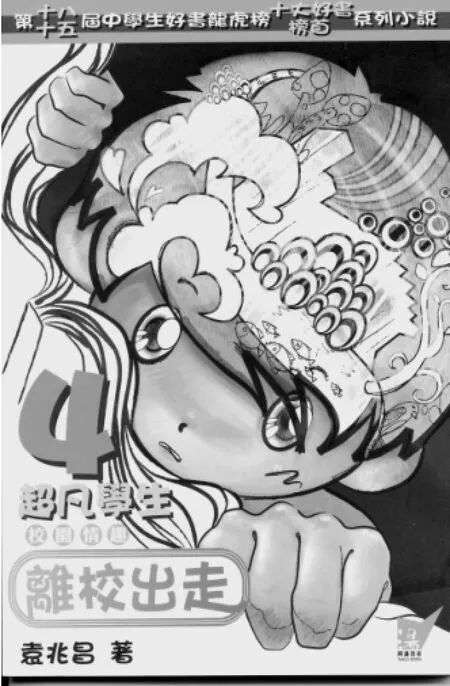
图7 香港的轻小说《超凡学生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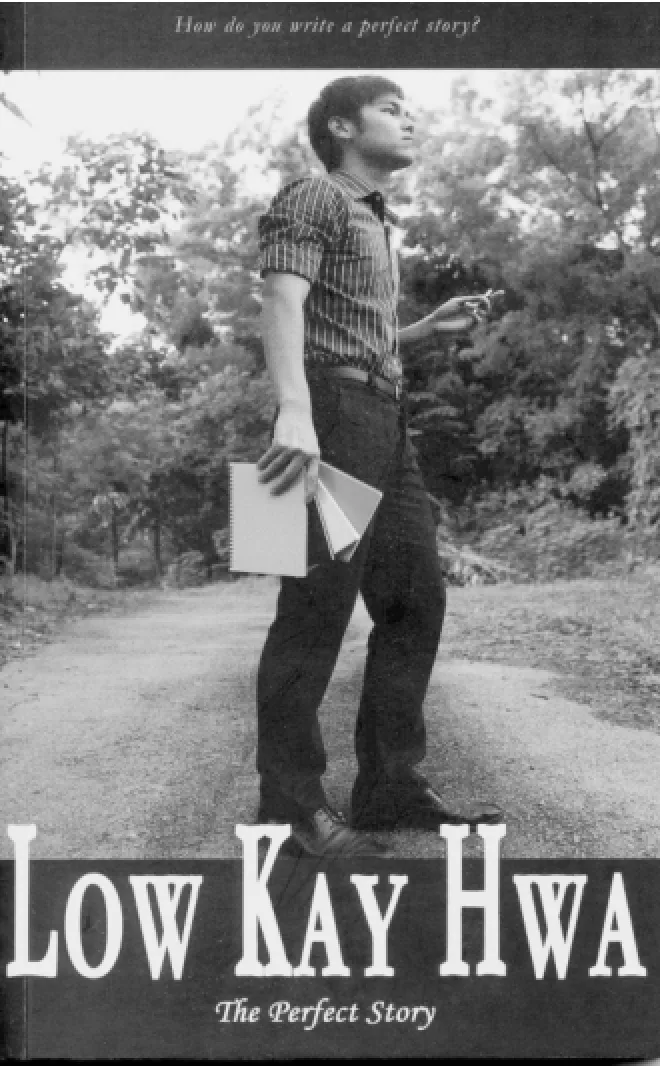
图8 新加坡的轻小说Low Kay Hwa The PerfectStory
BL(另称“耽美”)也受青少年的欢迎,就是女生喜欢看的男生同性恋的小说(动漫也有)。在日本每个大书店都有专用书架,爱好者很多。台湾的情况跟日本差不多,同样很有人气,而且除了从日本进口以外,也有当地原创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新加坡,这一类作品几乎没有商业性的出版,但是作为同人活动的一部分有爱好者写作,跟港台的爱好者进行交流。
另外,在日本一段时期非常流行手机文学,就是支付会员费手机上看小说或动漫的服务,有些公司拥有几万客户。当中有卖出一百万册并被拍成电影的《恋空》(美嘉,魔法iland,二〇〇五)等畅销作品。还有搜集BBS上贴的文章而编的《电车男》(中野独人,新潮社,二〇〇四)等作品。在中国大陆、港台、新加坡,手机文学没有日本那么流行,但网络文学很发达。有很多文学网站,读者向它投稿,并阅读登载的作品,如“榕树下”、“晋江文学城”等网页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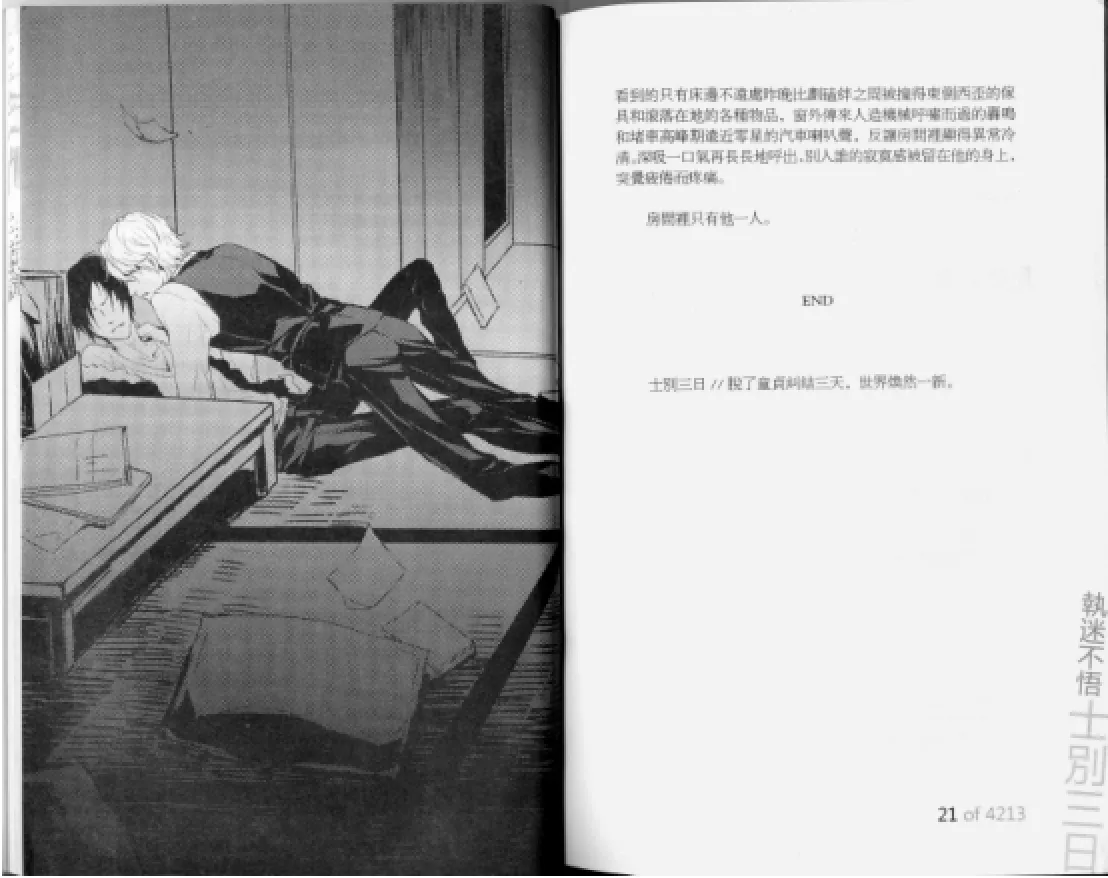
图9 上海的BL(同人创作)《执迷不悟》

图10 上海的com icmarket1

图11 上海的com icmarket2
如上文学的流行跟青少年的同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起源是九十年代以来在日本非常流行的同人文化。他们的活动包括发行同人杂志、参加或组织cosplay大会、制作电子游戏、一起搜集模型(figure),等等,又多样又活跃。杂志上登载的作品大部分是二次创作,也就是说,不是原创,而是借用某些作品的character当作自己作品的角色而重新创作的作品。除了漫画以外,小说、评论、影像什么都有。它们跟原作几乎没有关系,大多数是yaoi(boys love)或美少女pornography之类的作品。其实当中也有好作品。日本获得芥川文学奖、直木文学奖的部分作家,以及受欢迎的部分著名漫画家是同人写作出身。登载这种作品的同人杂志和书籍在爱好者的书市(叫做comicmarket)或网络上交换并销售。比方说,日本每年夏季和冬季在东京最大的展览馆分别召开两次comicmarket,这个书市是日本最大的活动之一,世界各国的爱好者来参加,有些杂志一天能卖出上万册。这意味着,参加这些活动的同人很多,而且不是同人而去参加comic market的人,换句话说,对如上活动感兴趣或支持它的人更多,社会上的影响很大。不待而言,中国大陆、台港和其他东亚城市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Cosplay和收集figure很流行,社团和同人杂志以及动漫节不断地增加。每个亚洲城市每年召开几次comicmarket,参加这些活动的青少年不少,而且越来越多。
我已经说过,在如上爱好者当中,享受作品的方式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着重character。那么,阅读文本方式的变化真面目如何?

图12 台北的com icmarket1

图13 台北的com icmarket2
三、阅读方式的变化——从story到character
下面的数据是二〇一〇年在东亚五个城市(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对大学生进行的有关轻小说和动漫的问卷调查的结果。问的是“你喜欢轻小说/动漫的哪些部分?”(可以复数选择,回答者限于看过轻小说或动漫的人)。
在北京,关于轻小说的项目,回答者九十二人当中最多的回答是“可读性比较强”四十一人,第二名是“故事情节很好”三十七人,第三名是“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三十六人。其次是“感到某种治愈、安慰或救济”三十一人。关于动漫的喜好项目,回答者九十六人当中回答“故事情节很好”的人最多,有六十九人;第二名是回答“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的人,有六十人;其次是“感到某种治愈、安慰或救济”三十八人。
在台湾,轻小说和动漫的调查当中回答最多的是“故事情节很好”和“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关于轻小说,回答者二百八十七人当中前者是二百四十一人,后者是二百四十人。关于动漫,回答者三百三十四人当中前者是二百九十三人,后者是二百七十八人。
香港也差不多。关于轻小说,回答者八十六人当中回答“故事情节很好”的有四十八人,回答“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的有三十人。关于动漫,回答者八十二人当中回答“故事情节很好”的有五十五人,回答“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的有三十八人,都位于第一和第二名。
新加坡的结果稍微不同。关于轻小说,回答者四十五人当中第一到第三名的回答如下:“故事情节很好”二十二人,“感到某种治愈、安慰或救济”二十一人,“可读性比较强”十九人。关于动漫,回答者四十八人当中回答“故事情节很好”的最多,有三十七人,其次是“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三十四人,都是第一和第二名。
虽然每个城市“故事情节很好”都占领第一名,与之同时“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的位置也相当高。如果一九八〇年代做同样的调查,回答“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有魅力”的人肯定少得多。由此可见,现在的年轻读者如何重视character。

图14 新加坡的com icmarket1

图15 新加坡的com icmarket2
然后,从各城市采访的结果也表示读者如何重视character。比方说,上海动漫节的策划人F女士这样说:“中国的年轻的受众也更可能受到形象(character)的影响。三十岁以上会更喜欢重视文本。但郭敬明的小说比较注重人物的架构,文学性很弱,但青少年很喜欢。那种风格很红。所以可能年级低一些的受众,更容易接受人物的形象吧。”(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采访。)另外,北京大学的学生、轻小说的写手山崎晴矢也说:“好的角色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二〇一一年二月,在北京大学采访。)台湾也有同样的反应。轻小说的写手花月ASKA说:“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爱好角色。但我是剧情角色并重。”(二〇一一年二月,在台湾大学附近的咖啡店采访。)
这种讲究character的阅读方式从一九七〇年代后半期从漫画的领域开始。当时在日本出现叫做mediamix的现象。也就是出版漫画的同时,上映动画,卖出模型,把作品里的角色的形象作为巧克力、糖果之类商品的附属品卖出等,即所谓跨领域的复合性销售方式。有人说六十年代早就有同样的销售。《铁臂阿童木》、《铁人二十八号》都把漫画拍成动画在电视上播送,并利用作品的character卖出模型、巧克力等。只是当时先有漫画作品的流行,然后才有如上商品的销售。但是《宇宙战舰大和》、《银河铁道999》等七十年代后半期的作品不一样,漫画已经不一定是核心。这些作品在动漫、小说、模型等好几个领域同时或连续上市。后来,同一个作品在动画、漫画、小说、游戏、模型等多数领域平行展开成为普遍的推销法。
这些mediamix的作品有一个特征,每个领域都加入自己的特色,各作品世界在细节上跟其他领域有一点出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动画里还活着的人物在小说里已经死掉,等等。这种特点带来了几个新的效果。比方说,每个领域的产品互相成为其他领域的广告。因为爱好者对不同领域的不同的故事感兴趣,被吸引复数领域的商品。另一个特点是,虽然每个领域有出入,但所有的领域带有共通的因素,也就是作品里的人物的角色(character)。所以爱好者能把这些作品看作一个有系统的有机作品群。就这样,读者单独地欣赏作品里的character的基础逐渐形成。
到了九十年代左右,在阅读漫画的方式上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漫画评论家伊藤刚把它称作“chara的自律化”(《手冢已经死了(Tezuka isdead)》(原题:テヅカイズデッド,NTT出版社,二〇〇五)。他以漫画《bonobono》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变化为例,说;“从漫画的‘故事’带来的快乐,到观看chara的游戏而感到亲切的快乐,这算是《bonobono》的变化。这个作品的chara从“故事”平缓地离开,可以个别游戏。”换句话说,以前漫画的读者先读漫画的故事情节,然后欣赏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但是从这时期开始,相当多数的读者离开作品的故事,单独地欣赏作品里的character。为了跟以前的character区别开来,他把这种角色称作chara。因为跟故事情节没有关系,欣赏的对象没必要是主要的角色。如果他们对作品里无名的小动物、小摆设感兴趣,也会欣赏它说“很好的chara,kawaii(可爱)”。
他的分析符合当下动漫的接受情况。典型的例子是cosplay和收集figure(模型)的流行。这些东西的爱好者欣赏的显然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作品里的chara。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创作(包括所为“恶搞”)。它们主要是借用原作的角色重新创作的作品。
如上有关漫画的消费(即阅读)和再生产(即第二次创作)的变化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也发生影响。轻小说是其典型的例子。
轻小说本来跟漫画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轻小说的封面和插图都是漫画。而且它们的创作跟漫画一样,从设定角色的形象(character)开始。另外,character在读者的阅读也成为很重要的因素。比方说,每年出版的《今年轻小说排行榜》(このライトノベルがすごい,宝岛社)等书里,除了作品和作家的排行榜以外,还有插图画家和character的排行榜。
轻小说的另一个来源是table role-playing game,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创造故事的游戏。参加游戏的人当中一个人扮演叙事者,提供背景的世界和故事梗概。其他的人扮演作品里的角色(比如,勇士、魔术师、贤者,等等)。大家按照叙事人描述的故事和背景的框架,发表自己扮演的角色的行动,集体地完成一个故事(发生战斗的时候,掷色子决定输赢)。不待而言,把这个游戏搬到电脑上就变成电子游戏,而把它改为小说就变成轻小说。轻小说初期的代表作《罗德岛战记》(角川sneaker文库,一九八八-)在序文里说明,这本书把他们玩儿的TRPG改编为小说。这种table role-playinggame当然以character为中心。结果,轻小说也着重character。电子游戏(比如美少女game等)也一样。
除了轻小说以外,叫作yaoi或boys love(BL,另称耽美)的小说、漫画也跟character有密切关系。BL是女生喜欢看的男生同性恋的作品。它的来源是日本一九七〇年代的少女漫画。那以前的少女漫画是又可爱又浪漫的简单的故事。可是一九七〇年竹宫惠子画的《在日光室》(《别册少女comic》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号)描述美少年的性爱故事,对当时的读者给予很大的冲击。以后类似的漫画受少女读者的欢迎,比如,竹宫惠子的长篇漫画《风与树木之诗》(小学馆flower comics,一九七六)描写十九世纪末欧洲学生宿舍里的美少年同性恋爱,风靡一时。它们受欢迎也有理由。这些漫画提供思考恋爱和性爱的机会,这以后的少女漫画的确比以前深得多,受到青春期对恋爱和性爱感兴趣的读者的欢迎。另外,因为描述的是男生之间的恋爱,对女生来说是百分之百想象上的东西。所以女生在完全想象的世界里能自由地思考恋爱和性爱。(如果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免不了联想到自己,这样的想象可能有点过激。)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创刊了少女小说杂志《JUNE》,①正确地说,1978到1979年刊行《comic jun》,然后,1981到1996年刊行《JUNE》。另外,1982到2001年刊行《小说JUNE》。里面设有叫作“小说道场”的读者投稿栏。在这个栏目里,著名的作家栗本薰公开修改读者写的BL小说,如果写得好登载全文,成为很有人气的栏目。另外,这个杂志有一期翻译登载法国新发现的BL小说并附作者小传和解说。其实这都是栗本薰自己编写的。通过如上活动和这种宣传,BL小说爱好者逐渐增加,并随着comicmarket的发展,写手和作家也培养出来,现在已经成为同人活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作品也有变化,目前的BL以character为主,爱好者一起欣赏并评论美少年character,或者借用喜欢的character重新创作(所谓二次创作)。小说、漫画都有。
在台港和其他东亚地区,BL也都很流行。在中国大陆,一般的出版社没被许可出版yaoi和boys love之类的书,但在同人活动里已经有不少类似作品。而且有的作品在台湾和香港的comicmarket里出售,跨国的交流早已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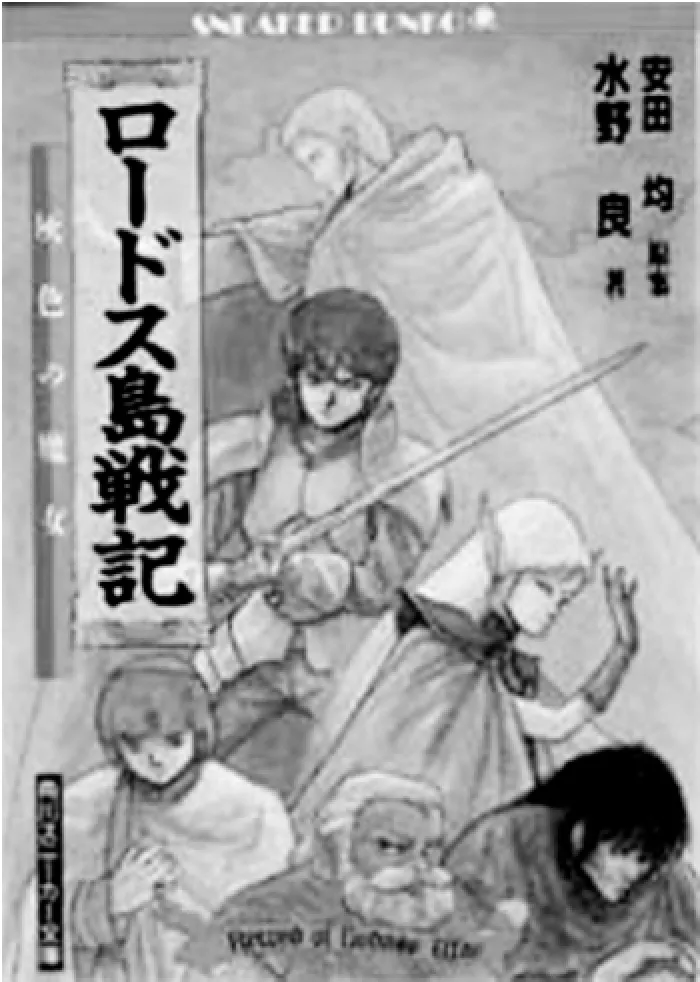
图16 《罗德岛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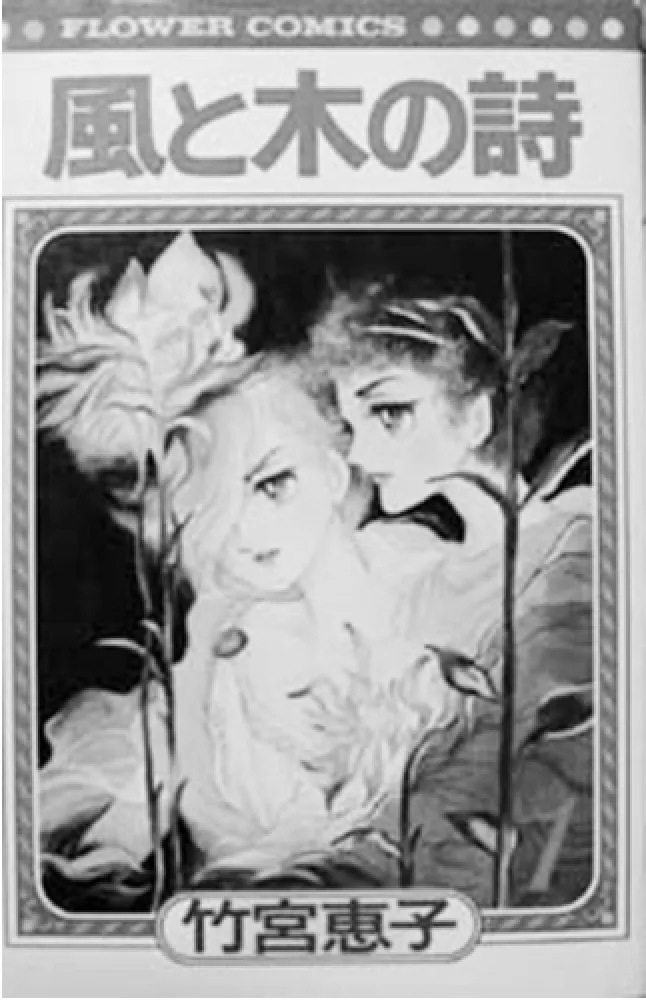
图17 《风与树木之诗》
手机小说跟如上领域稍微不同。读者讲究的好像不是character,而是故事情节的类型,或构成那些类型的各种要素。手机小说的来源之一不外是一九九○年代的少女杂志,比如《pop teen》(富士见书房,一九八○年始,一九九四年以后由角川春树事务所出版)等。它们设有读者投稿栏,不少女中学生投稿告白自己被强奸、怀孕、被同学虐待等经验。当时的编辑说,写的内容几乎都是假的。在一个座谈会上他们这样说:
铃木谦介:“我也比较投入。脑子里理解几乎都是假的,至少不是事实。可不由得读起来。”
中村航:“第一次读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被吸引住。我读到高中时代。”
——《文学界》二○○八年一月号
当时的读者知道写的几乎都是假的,可是把它当作真实的经验来阅读。换句话说,这些文章是用某种游戏的感觉写作,并作为某种游戏阅读,而且读者会产生共鸣。把这些类型的告白改为小说,就成为手机小说,手机小说受欢迎的理由之一可能在这儿。在上述座谈会上,中村航这样说:
我觉得,年轻人想看这种东西。可不知道去哪儿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手机小说”可能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出现。
手机小说有叫作“七个大罪”的要素,是嘲笑说,几乎所有的手机小说由“卖淫、强奸、怀孕、毒药、无法治的病、自杀、真实的爱”这七个因素组合而成。我觉得说得相当对。手机小说的爱好者可能欣赏这种要素或组合各要素而构成的故事类型。换句话说,这些要素或类型代替其他领域character的功能。给东亚城市的青少年介绍如上“七个大罪”时,他们都暗笑。好像他们也感到要素的存在和组合要素的故事类型的效果。
不待而言,其他同人活动也都讲究character。Cosplay、搜集模型和借用character重新写作的二次创作都讲究character。由此可见,从日本开始的character文化已经普遍于东亚城市的青少年人群中。那么,他们欣赏作品的方式为何有这样的特点?
四、对作品寻求何事?——从追求真实到跟同好交流
如上领域作品的爱好者除了讲究character以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少爱好者不只单独欣赏作品,还要通过作品互相交流。Cosplay、二次创作、网络上的聊天等都是实现这个需求的方法。他们当然不是忽视欣赏作品,日本和其他东亚城市的青少年都寻求有趣的作品。上述问卷调查当中,无论轻小说还是动漫,对故事情节的关心位于第一名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要求。只是,同时要注意不少回答者强调跟同好聊天的快乐的事实。各城市的采访当中也有不少同样的发言。
比方说,北京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里,分别有如下发言:“(同人活动——引用者)很温暖,一些本来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像大家庭,自由参与,不管水平是好是差,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并接受他人‘吐槽’,是很好的群体交流方式。”“同人活动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是寻找有共同语言的伙伴的好方式。它能使人增加很多能力,如组织协调能力,动手能力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人的性格,比如使人变得更加开朗并善于交流。”
在上海,参加同人活动的Y女士对“如何开始创作?”的问题回答如下:“是因为有了想法,有表达的需求,比如,寂寞的、想发泄的感觉,需要通过想象来解脱,从而通过写作来寻求,把这种情绪记录、分享,如果有认同更好。”(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复宣酒店大堂咖啡厅里的采访。)由此可见爱好者如何寻求能交流的同好。
这种心情台湾也一样。从如下采访的回答,我们能看到爱好者同样的心理。同人杂志的写手水月流转说:“比起轻小说创作,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给我更大的吸引力。”(二〇一一年二月,在台湾大学附近的咖啡馆采访。)业余轻小说写手宇宙油王也说:“轻小说是提供一个动机。我最初的动机是我要写小说,我要去投稿,可是当这个动机在某一个程度之后,他会发酵,我可能不再只是为了写小说,而是我写小说使我认识很多人,那我认识了更多人去接触到更多意外的活动,进而再去把一个一个连在一起,再回归到轻小说本质上……就是可能我只是写小说,但我不见得只是写小说,我可以认识到一样是喜欢这个小说的人,或是他专程只是喜欢这个小说的人物,所以他去装扮这些人物的cosplay参与者,他带来一个串联性,一个联结性。”(二〇一一年二月,在台湾大学附近的咖啡店采访。)
通过它们的发言,我们能理解轻小说或动漫成为跟同好交流的重要工具,而同人活动是实现这个交流的场所。
在新加坡,关于同人活动的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栏上也有同样的回答:“同人活动是让有共同嗜好的人聚在一起分享心得和看法,互相切磋的好机会。”“它也渐渐地成为了社会中非主流文化的强力体现,有时甚至取代了个人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例如家庭活动、社交活动等)。”从此也能看到跟同好的交流成为参与同人活动的爱好者的一个目的。
如上爱好者不但欣赏作品,而且参与创作的理由之一在于轻小说或动漫的创作比纯文学比较容易入手。因为轻小说由几个要素组合而形成,比方说,角色(character)、世界观、武器等道具(item)、故事情节,等等。轻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冲方丁在《冲方丁的轻小说创作讲座》(原题:冲方丁のライトノベルの書き方講座,宝岛社,二〇〇八)一书里很仔细地说明创作过程,先决定角色,然后决定世界观、道具、故事情节等。中国也有类似的书,比如《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积木工作室,长江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对读者来说,写纯文学比较难,应该有文采。可是轻小说的话,如果把握这几个要素的规则,写作品并不难,自己也能做到。至少比纯文学门槛低得多。所以不少爱好者参与轻小说的创作。当然漫画也一样。
如上作品的爱好者或同人活动的参与者在他们的活动当中,有时候通过网络有时候碰面,经常跟同好聊天并分享感受。如果自己发表的意见或作品好的话,即时有巨大的反应,他们从中能获得找到自己位置的感觉。所以,对他们来说,通过作品跟同好交流和对作品感动(即接触到人的或社会的真实)同样重要,有时好像比它还重要。这说明二次创作对他们的意义。如果他们写(画)原创作品的话,因为它是原创,没人看过他的作品,有可能同好们不认同。可是二次创作因为借用原作的角色而写作,同好们都知道作品里的角色,跟他们沟通并不难。
另外,大多数爱好者不是欣赏唯一一个领域,而是倾向于爱好复数领域的作品。这也表示爱好者如何着重跟同好的交流。如果只要欣赏作品,爱好一个领域就够了。可要跟同好交流,爱好的领域越多越好,这样能跟更多的同好们交流,聊天会更热闹。而且着重character的话,跨领域不成大问题。利用自己喜欢的character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进行交流就行。由此可见,跟同好交流的寻求支持轻小说和动漫的流行,并推动二次创作、cosplay等同人活动。这不外是意味着,读者对作品的寻求,换句话说,读者和文艺作品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背后存在着青少年怎样的心理?
五、形象(character)阅读与青少年的绝望
爱好轻小说或动漫、BL、游戏,或参与cosplay、二次作创等同人活动,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娱乐。在各城市的问卷调查当中,问“喜欢同人活动的哪些地方”的时候,最多的回答是“就是一种消遣”。在北京,参与过同人活动的回答者四十九人当中三十三人,在台北,三百三十八人当中二百九十三人这样回答。其实,那么多的青少年为了这些娱乐下那么大的功夫,肯定存在着推动他们爱好的理由。换句话说,现象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他们对今天的社会、现在的文化的想法。那么,如上爱好者对社会和文学文化又如何感受?
在日本,近年来围绕青少年的社会情况不好,很难找到光明的一面。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相信我们都属于“中产阶级”。但一九九〇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两极化。过了二〇〇〇年,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根据二〇〇八年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人民的平均年收入大概是三十万人民币左右,跟以前相比变化不大,算是稳定(拿工资的人,不包括自营、农家等)。其实,这是两极化的结果。一方面收入超过七十万的人增加到百分之七(比五十万、六十万的人还多),一方面收入不到二十万的人达到百分之四十。将两者平均成为三十万,年轻人当然属于后者,并且这十年收入逐渐下降。二十到二十九岁的青少年的平均收入十七万,比十年前减少三万元。加上,能找到正式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据二〇〇六年的统计〔收录于《雇佣多样化的变迁》(雇用の多様化の変遷)〕,十五岁到三十四岁的青少年当中非正式雇佣者(打零工,当作派遣职员等人)已经达到25%(不包括学生)。而且按照该书一九九四年的统计,非正式雇佣者不到10%,这十年之间增加到二点五倍。当然这些非正式雇佣者的收入比正式职员的收入少得多。比如,刚才提到的平均年收入三十万是正式职员的收入。非正式职员的平均收入是二十二万左右。二十到二十九岁的非正式职员收入更低,为十五到十七万。数字上他们的收入跟同岁的正式职员差不多。其实,他们没有升级、升工资的机会,也没有第二年能继续工作的保证,几乎体验不到安全感。
评论家雨宫处凛针对如上青少年的情况这样说:
二〇〇〇年代的年轻人事先被注定“失去”。但不知道自己何时失去了何物。只是觉察到失去的时候,切实感受到会有的选择无疑减少。也就是说,不知为什么活下去如此困难的皮肤感觉。经过九十年代,在“国际竞争”、“全球化”等口号之下沉默的时候,不少年轻人被划为“一次性劳动力”……亲眼看到“进入社会”的朋友都满身创伤,一个接一个地伤害身心。这样不少青少年从“劳动市场”撤退出去。
《漫画描述青年残酷的“现实”》(漫画が描き出す若者の残酷な「現実」)——《小说tripper》二〇〇八年autumn
她说,当下的青少年对自己的前景没有希望,不得不感到无聊、孤独或闭塞感(换句话说是某种绝望感)。
可是,当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绝望。不能把所有的青少年概括为只有一个趋向。举一个例子,是这四十年日本内阁府每年进行的《有关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问卷里面有“您是否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幸福”一问。据二〇一〇年的统计,二十到二十九岁的青年当中回答“满足现在的生活”的人,男性65.9%,女性75.2%。这是四十年的调查当中最高的比率。这是否意味着现在的青少年比以前幸福得多?
目前社会学家的分析不肯定他们的幸福。比如,青年社会学者古市宪寿在《绝望国家的幸福青年》(原题:絶望の国の幸福な若者たち,讲谈社,二〇〇一)一书里,根据大泽真幸的看法说:
将来还留下可能性的人,或者对以后的人生还感到“希望”的人回答“现在我不幸福”,不算否定自己……反过来说,当感到自己不会更幸福的时候,人只好回答“现在我幸福”。
支持这个推论的事实确实存在。老人对如上问题往往回答“现在我幸福”。因为他们剩下的时间不长,觉得将来不能改变情况,结果不敢说“现在我不幸福”。古市说:“像住在小村的居民,年轻人跟‘伙伴’一起在‘小世界’混日子。这就是他们感到幸福的根本原因。”(同上书)由此可见,青少年的回答不是意味着他们感到幸福,而是意味着对未来没有信心。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日本内阁府的《有关社会意的舆论调查》。问卷里面有“您重视个人生活的充实还是重视对国家社会的关心”一问。据二〇一〇年的统计,二十到二十九岁的青年当中,回答应该对国家社会关心的人55.0%,回答应该重视个人充实的人36.2%。感到应该关心国家社会的人在历年调查当中最多。这是否意味着现在的青少年对社会充满希望和责任感?
古市说:“他们几乎找不到能打破日常生活闭塞感的有魅力而不复杂的‘出路’。”他们虽然回答应该关心社会问题,但是实际参加义务活动等人并不多。结果,据古市的说法,他们“想做点什么,不想保持现状。不过,不知道做什么好”。(《绝望国家的幸福青年》)
这些例子说明,在日本不是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绝望,但他们并不是感到幸福或满足。
如上青少年的情况不是日本惟有,中国的年轻人也抱有同样的无聊、孤独或闭塞感。他们几乎都是独生子,生下来就注定孤独。在学校和家里一直受应试教育,万一没考上大学一辈子都受影响,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跟朋友交往的时间显然比以前减少。幸运考上大学也难减少压力,毕业时找工作非常难。幸运找到了工作,后面还有买房子的压力。加上中国的社会缺少老百姓参与决定社会上的重要问题的机会和权利,那么,他们跟日本的青少年一样,对自己的前景不抱信心也不奇怪。他们可能觉得现在的社会所有的事情都被固定,自己生活的社会圈越来越缩小,而感不到能参与社会、能打开出路的希望。台港以及其他的东亚城市的青年的情况也差不多。
那么,如上青少年的失望和阅读character到底是什么关系?评论家宇野常宽这样分析二〇〇〇年以后青少年的心理:
把过日常生活的小共同体(家庭、同班同学、朋友等)当作一种“故事”,并且把在那儿被分配到的(相对的)自己的位置当作一种“角色(character)”而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渗透到广泛的人。
……像故事里面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一样,被分配到的角色在那儿(小共同体)决定一切。——《零年代的想象力》(ゼロ年代の想象力,早川书房,二〇〇八)
他认为,对今天的年轻人,看文本时讲究character是非常亲切的阅读方法。有学者说,青少年所经历的学生生活也有原因。年轻的教育学家铃木翔在《教室里的种姓》(教室内カースト,光文社新書,二〇一二)一书里说,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初中以后,每个学生都属于一个小集团,并给它取名,互相把握集团之间的‘地位之差’”,并且“学生的分类好像每个人稍微有区别。比方说,有一个女生分‘洋鬼系’、‘微质素系’、‘极质素系’,一个男生分‘酷系’、‘非酷系’,另一个女生分‘过激派’、‘中心派’、‘稳健派’、‘清静系’等等,种类无限”。重要的是这些分类给学生带来的结果。铃木说,现在的学生“虽然跟自己的心情不同,扮演别人需求的‘角色’”。他说,学生该扮演自己所属的小集团的character。
另一个教育学家土井隆义在《角色化/被角色化的孩子》(キャラ化する/される子どもたち,岩波ブックレット,二〇〇九)一书里分析如上学生的心理说,“今天的年轻一代把握自己的人格时,不是采用类似‘自我认同’等话语表示的固定的概念,而是采用类似‘角色’等话语表示的汇集片断要素的概念”。并且“学生为了回避破绽复杂化的人际关系,而给它赋予明确性和稳定性,互相推动扮演角色”。
土井说,作为如上情况普遍化的结果,“九十年代以后,相信‘努力带来成功’的学生和感到‘任何努力无用’的学生都增加,两极化”。意思就是现在的学生认为“有的学生必然成功,有的学生必然失败”,“人生的方向事先固定”。
根据如上几个人的说法概括起来,今天青少年的感觉如下:现在的社会所有的事情早已都被固定,而自己生活的社会圈越来越缩小,自己在这样狭窄的圈子里被分配角色,扮演它而生活。当中很难感到将来能参与社会,打开出路,并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希望。
目前,如上提到的小集团的例子唯在日本看到,好像在东亚城市还没出现。只是我觉得,虽然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在其他东亚城市的不少学生也可能带有类似的心情。
如果可以这样说,我觉得,青少年对纯文学的兴趣远远不如对轻小说、动漫、电子游戏的兴趣是理所当然的。轻小说突出character,给他们提供更亲切的世界。而且,他们在网上找出有同样爱好的粉丝们,通过共同体里面的聊天分享喜怒哀乐,从中能获得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这样的圈子可能让他们感到现实感和充实感,以及跟人或社会接轨的感觉。
六、村上春树与共鸣孤独、闭塞
如上探讨的是今天在东亚诸城市的青少年所能看到的共通的现象。他们对文本的阅读方法有变化,并且这个变化带有读者对作品寻求的东西的变化。加上,其背后存在着青少年心理的变化。这都是围绕亚文化所发生的问题。其实,如上阅读方式的变化,以及对作品寻求的东西的变化在纯文学的阅读上也能看到。其背后也存在着青少年读者同样的心理状态。我觉得,村上春树的爱好者阅读他的作品的方式是典型的例子。为什么呢?
村上春树在海外当然通过翻译接受。每个语言的翻译都有不少出入。比方说,中文当中,大陆的林少华、施小炜和台湾的赖明珠译文多么不同。英文和其他的语言的差别不待而言。可是通过几个城市的调查,对“你喜欢村上春树的哪些部分”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城市的回答当中“共鸣人物的孤独感”、“共鸣作品的虚无感”最多。①回答“共鸣人物的孤独感”的村上春树的爱好者(问卷上回答喜欢或比较喜欢村上春树的人),在上海126人当中95人,在北京96人当中63人,在台北102人当中80人,在香港65人当中25人,在新加坡45人当中20人,都是第一名。回答“共鸣作品的虚无感”的爱好者,上海64人,北京41人,台北68人,香港24人,都是第二名。在新加坡占第二名的回答是“思想有深度”16人,回答“共鸣作品的虚无感”的有6人。虽然译文不同,但读者的感受都相似。这好像意味着,除了村上春树的作品本身以外,读者的心里也存在推动如上读法的因素。
不少人早已谈到过村上春树的作品带有虚无感和孤独感。其实,这跟他的气质有关系。他本人带有浓厚的孤独感,也算是自闭症spectrum的倾向。在此应该说明,我并不是说村上春树是自闭症的病人。自闭症spectrum是为了把握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而产生的新话语。简单地说,它指的是“不擅长于临机的人际关系,而本能地强烈欲望优先自己的关系、做法,或者保持自己的节奏的倾向”(本田秀夫《自闭症spectrum》,softbank新书,二○一三)。当中包括,症状比较重、不太适合社会活动而该治疗的人(所谓障碍性自闭症spectrum)。也包括能跟社会适合不用治疗的人(所谓非障碍性自闭症spectrum)。后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病”,说某种气质也可以。精神科医生本田秀夫说,现代社会的百分之十的人属于这个spectrum。只是他们往往某种程度上感到人际关系的困难,并带有某种孤独感。
以前所谓的亚斯伯格症候群也是类似的东西。这个症候群现在分类上被自闭症spectrum吸收,成为它的一部分。根据一般的说法,亚斯伯格症候群有如下三个特点:社交困难(social deficit),沟通困难(communicatiaon deficit),以及固执或狭窄兴趣(rigidity or restricted interest)。这些当然也是自闭症spectrum的特点。他们智能很高,跟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学者当中也有不少亚斯伯格症候群的人。他们当中也有障碍性的人,也有非障碍性的人。说实在的,所有的人大小都有如上气质,只是它到了不合适于社会的程度,该开始治疗,这时才算某种“病”。这意味着社会上不善于人际交往、爱孤独的人很多。举一个例子,医生如何判断你是自闭症spectrum,就是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所定的问卷DSM-Ⅴ问诊,万一A到C的每个栏目里有两项以上符合的项目,判为自闭症spectrum。这意味着,有符合的项目但没达到每栏两项的地步的人多得多。他们并不是病,但又爱孤独,有不善于跟人交往的倾向。
我只是觉得村上春树本人,以及不少他作品里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问题在于这些孤独的因素和阅读文本的方式的变化,以及读者对文学的寻求的变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首先要确认,村上春树本人有喜欢孤独(社交困难)的倾向。他自己说: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过日子的性格”,“结婚以后慢慢习惯跟别人一起生活”。(《当我跑步时谈些什么》)而且他不喜欢跟别人一起运动,只喜欢一个人游泳或跑步。这些可以说是自闭症spectrum倾向的表现。他还说:“我觉得写小说在很多部分是某种治疗自己的行为。”(《村上春树拜访河上隼雄》)另外,小说里面也有同样的说法,“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疗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且听风吟》)有可能他自己已经察觉出自己的倾向。
结果,他的小说里面也有不少带有自闭症spectrum倾向的描写。在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自传的因素比较强的作品《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的几个描写:
我开始跑图书馆,一本接一本看那里的书。一旦翻开书页,中途便再也停不下。书对于我简直如毒品一般,吃饭时看,电车上看,被窝里看,看到天亮,课堂上也偷偷看。——第二章,主人公的独白
主人公“我”的读书行为表示主人公“固执或狭窄兴趣”的气质。他好像带有自闭症spectrum的倾向。下面的例子也一样:
你肯定喜欢一个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不大喜欢被人窥看。这也许因为你是独生子的关系。你习惯于独自考虑和处理各种事情,只要自己一个人明白就行了。——第三章,女朋友泉对主人公说的话
女朋友泉批评主人公带有的“社交困难”,换句话说是自闭症spectrum的倾向。而且主人公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下面举一个例子:
我比过去还要深地卷缩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去游泳池,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和看电影。习惯以后,也不怎么觉得寂寞或不好受。——第五章,主人公的独白
这个部分也表示主人公不习惯社会,算是“社交困难”的倾向。如上例子都说明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如何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爱孤独。
下面是另一部小说《挪威森林》里的例子:
“喜欢什么?”
“徒步旅行,游泳,看书。”
“喜欢一个人做事吗?”
“嗯——或许。”我说,“以前我就同别人配合的活动不起兴致。那类活动,无论哪样我都沉不下心,觉得怎么都无所谓。”——第六章,我和玲子的对话
这个部分描述不能习惯社会的孤独的主人公。算表示“社交困难”的倾向。这部小说除了他以外,还出现不少带有自闭症spectrum倾向的人物。下面三个例子都描写这样的人物:
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专长……——第六章,玲子对我说的话
这是女主人公直子给主人公“我”介绍住院的人的情况时的会话。说明住院的人们虽然仅身上带有病,但是智能很高。
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第六章,我的感想
这个部分是主人公对主演的人的感想。也表示着住院的人们带有“社交困难”的样子。
我们企图通过你来努力使自己同化到外部世界去,结果却未能如愿以偿。——第六章,直子对我说的话
这个部分是女主人公直子对男主人公“我”说的话。同样表示着她的“社交困难”。
如上三个例子都描述主人公直子和住院的人们都带有自闭症spectrum的倾向。对这一点来说,《挪威森林》与其说是恋爱小说,不如说是描述治愈心理伤害过程的小说。
《舞!舞!舞!》里面也有不少同样的例子:
“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你我两人在一起,但并不乐意从早到晚都守在一起。怎么回事呢?”
“唔。”
“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感到心烦,只是恍惚觉得空气变得稀薄起来,简直像在月球上似的。”
……
“反正我有时觉得空气变得像在月球上一样稀薄,和你在一起。”
“不是月球上空气稀薄,”我指出,“月球表面压根儿就没有空气。所以……”——第一章,主人公和女朋友的对话
女朋友说:“空气变得像在月球上一样稀薄”意味着,跟你在一起感到某种隔阂。但主人公回答说:“不是月球上空气稀薄,月球表面压根儿就没有空气。”他不能理解她的言外之意,只能了解文字上的意思。这也是自闭症spectrum的特征之一——交往困难。
这样表示孤独的描写在村上春树的作品里数不清。村上春树描述的孤独和闭塞不外是不善于人际关系、不能习惯社会的人的苦楚。我说它带有自闭症spectrum的倾向的意思就在这里。重要的是村上的爱好者共鸣如上作品里的人物的孤独,以及故事情节不走向圆满的结局的虚无感。这个倾向,日本和其他东亚的城市没有区别。
七、村上春树与疗愈、救济的感觉
有关阅读方式的分析,村上春树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村上春树一边描述带有孤独和闭塞感的人物,一边发信“这样也可以”、“你被允许”。比如,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里有如下描写:
在她(主人公的女朋友岛本同学——引用者)面前,我往往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说什么好,无从判断。我想冷静,想开动脑筋,但都做不成。感觉上自己总对她说错话做错事,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都浮现出仿佛将所有感情吞噬一尽的迷人微笑看着我,就好像在说“没关系,这样可以的”。——第十二章,主人公的独白
村上的爱好者大概对这样的部分感到“疗愈”或“救济”。这样的描述从他处启动作品一直存在。下面是处女作《且听风吟》里的句子:
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第一章,主人公的独白
译文上的“解脱”,原文就是“救济”。村上的这种“疗愈”或“救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不是鼓励说拼命努力,而是肯定现在的状况说,你不用拼命,有时候应该等待着。另一个是,他说最后说不定成功,其实输了也没问题,这样允许你。下面举两个例子。
……那就在那里,我想,那就在那里,在那里等待我伸出手。需花多长时间我不知道,需花多大力气我也不知道,但我必须停住脚步,必须设法向那个世界伸出手。那时该做的。必须等待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本田先生说。——《奇鸟行状录》第二部,预言鸟篇
……我或许败北,或许迷失自己,或许哪里也抵达不了,或许我已失墟灰烬,唯我一人蒙在鼓里,或许这里没有任何人把赌注下在我身上。“无所谓。”我以轻微然而果断的声音对那里的某个人说道,“有一点是明确的:至少我有值得等待有值得寻求的东西。”——《奇鸟行状录》第二部,预言鸟篇
另外,学者小森阳一也在分析《海边的卡夫卡》的时候承认说,读者对村上春树的作品感到“疗愈”或“救济”。
小说家角田光代对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感到“暴力的无意志的意志”。反而非常畅销的这部小说的大多数读者,不知为什么感到“治愈”与“救济”。——《村上春树论——细读〈海边的卡夫卡〉》,平凡社新书,二〇〇六
在五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当中,问“你喜欢村上春树的哪些部分?”时,回答“感到某种治愈,安慰或救济”的人不是最多。在上海,回答者一百二十六人当中四十人(第六名),在北京九十六人当中三十人(第三名,另外有两个人数相同的回答),在台北一百零二人当中四十七人(第四名),在香港六十五人当中六人(第八名),在新加坡四十五人当中四人(第八名)。虽然每个城市都有出入,但人数基本上跟回答“故事情节好”、“思想有深度”、“气氛很酷(cool)”、“对话、举措很潇洒”的差不多。只是在自由记述栏里的回答和采访里的发言,提到“救济”和“疗愈”的人不少。下面是其中一些例子:
在其特有氛围之中,你能感到也许这小说只是为你而写,直达你的心,却又无法告诉你该如何。所以,结局变成了“就这样吧”。——上海,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
有关心灵的文字。构建一个时空,让人能够看到、读到自己,抑或知道有所陪伴的东西或事情。——上海,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
作品讲述的情节也许并不复杂,但通篇给人纯粹、窒息般的感觉,让人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主人公的心境里,也有着相同的体验,所以每次合上书页回到现实中的时候都会有种浮出水面的鲜活感,进而像具有某种治愈系功效,深感快慰。——北京,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
“村上春树的书安慰了我的心。书中男主角那带着困惑,却不害怕,淡泊无为中却自有一番坚决的态度,使我感到,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看完他小说我心里会很平静。所以我很喜欢这样子。”——台北,采访时的发言
令人心安。——香港,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
当然不能简单地概括如上回答。只是我觉得,如上回答呼应“孤独感”或“虚无感”的共鸣。这可能因为村上的作品不是提示绝望,而是描述今天的社会而表示不能简单地找到出路的缘故。在找不到出路的彷徨里,村上春树肯定主人公说“这样也可以”,“输了也没问题,能允许你”。这样的描述对读者虽然不能成为“出路”或“希望”,但可能成为某种“疗愈”或“救济”。这种找不到出路的自己的描述可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如下回答好像暗示如上读者的心理。
“在踏入社会以后,难免会感受到理想和现实激烈碰撞以后所产生的虚无感,村上的小说教会人们与这种虚无感、孤独感和平相处。教会人在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里有尊严地活下去,而不是走向彻底的颓废和沉沦。”
“心很静,更加明白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读后自己会有很奇怪的满足感。里面的对白很有启示性;人生虚空。”——上海,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
实话说,我并不是能对村上春树的小说读得很懂,但是在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主人公有过的迷茫和怅惘,我们仿佛也有过,也曾迷茫过,经历过。——北京,问卷调查的自由回答
包括日本在内,不少东亚城市的读者确实对他作品里的“孤独”和“虚无”产生了共鸣,并对类似“这样也可以”向你伸出扶手的描述感到“疗愈”或“救济”。他们喜欢村上的理由好像在这里。我在上面说过,现代以来纯文学的读者一直期待着通过作品接触到人的活社会的真实。那么,村上春树爱好者的阅读文本的方式跟以前文学作品的读者多么不一样。读者群好像已经开始变化。村上春树可能是能适应如上读者群变化的极少数作家之一。也许,这是他在全世界受欢迎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八、文学跑到哪里去?
在上面,我们看到青少年对动漫、电子游戏和轻小说的爱好和文艺文本阅读的方式的变化。然后探讨在这个变化里面所存在的对文艺的寻求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跟青少年对社会的隔阂感有关系的事实。村上春树爱好者的阅读方式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其实,进一步说,我觉得如上阅读方式的变化和对作品的寻求的变化可能彻底地改变文学和读者的关系。为什么呢?
到了现代以后,我们看文学作品时,能相信作品里的世界和自己的精神世界沟通,并能期待着通过作品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某种真实。至少认为能感到这些真实的作品就是优秀的文学。(这个“真实”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主观的“真实感”。)对这一点,文学不外是给每个读者启示更大的世界的东西。但是对现在的青少年,文学不太能启示这样的世界。世界已经固定,而在所属的狭窄的共同体里,自己的位置或角色(character)被分配下来,很难感到自己能参与并能改变的余地。对他们来说,传统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某种假设的故事,可能很难发生跟自己的精神世界沟通的感觉,不太能产生真实感。他们讲究的是作品里的角色(character)。当然他们也讲究故事情节、作品的思想、文体等,但character跟那种真实感同样重要。如果他们对作品有希求的话,那不是接触到人的或社会的真实,而是通过作品感到“共鸣”、“疗愈”或“救济”。村上春树的流行暗示着如上变化。然后,他们欣赏作品的同时,在网上跟同好们交往,寻求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他们也许在此才能感到某种真实感。对他们来说,这种交往跟作品本身同样,或者比他们还重要。我觉得部分轻小说或漫画能卖出几百万、几千万册的背景,可能存在着这种青少年人的感性变化。
我不觉得轻小说或动漫能简单地取代现当代文学。我相信包括青少年读者还需求感到真实、给自己启示更大的世界的作品。只是觉得,我们一直信仰的现当代文学可能对现在的青少年逐渐丧失以前所有的那么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现当代文学可能慢慢代表不了读者群的希求。其深层存在着文本阅读方式的变化,以及它带来的读者和文学的关系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真的跟青少年对社会感到的隔阂有关,那问题的根很深。现代文学形成以来已经过了一百多年(西方两百年,日本一百多年,中国一百年),文学现在可能面临着空前的大转折,那么我们跑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在变化的旋涡当中,还看不清这个转折的整个面貌,但是已经感到某种预兆或端绪。这样看,动漫、轻小说等亚文化给我们提出不少重要的问题。
周宏:十分感谢千野拓政教授,千野拓政教授在他的讲座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信息,以及他的文学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我谈谈听了以后的一些感受,还请千野先生批评指正。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关键词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区域概念,比如说是东亚,东亚城市。第二个是他的文化主要指的是亚文化。第三个是青少年。千野拓政先生在空间的维度上提出了东亚城市亚文化和青少年的一种同质化倾向。同时又在时间这个维度上提出了东亚城市亚文化与青少年的一种断裂化倾向。当然在这里,千野拓政先生是从文学的层面上探讨其原因的。在聆听千野拓政先生的讲座以后,我感到全球化的推力可以说不是主要但应该是重要的,现代化道路的同质模式使人类面对相似的社会问题,产生相似的精神感受,同时,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细细品味文化和反思自己思想成为一种奢侈,而追求精神上的娱乐则成为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就有一种目的,就是消除精神上的疲劳。从刚才的讲座里面我体会到一种显性的也是没有刻意把它突出的概念——孤独,就是说当代或者说八十年代以来突出的一个心理问题就是孤独。它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时间上来讲都和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交融、同质化和断裂的同时存在,说明人们的交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交往扩大化,另一方面交往又难以深化,我有很多朋友,但是我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人走向孤独是必须的。于是自闭、孤芳自赏、做白日梦、写不可公开的日记、制造一个封闭的世界,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那一块不可侵犯的世界就成了现代青少年的时尚。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千野拓政教授讲的这些行为,它们既是孤独的原因也是一些孤独的症状。千野拓政教授是从文学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则从哲学的层面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一切文化问题的根源必然在现实中,文化问题的解决必须在现实中来实现,孤独是一种时代病,它既使人具有一种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又使人比较痛苦。那么人何以走出孤独呢?这个问题在千野教授的讲座中是一个问题,叫文学。如果我们从人的层面上讲,那么我们青少年如何走出孤独问题的答案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难以做出统一的答案,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答案,就是有一个哲人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于是我告别了孤独。谢谢。
(录音整理:窦悦朗肖佳萍)
千野拓政,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