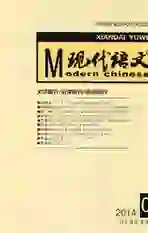试论张可久的咏史怀古散曲
2014-04-09张晓晓
摘 要:在元代的咏史怀古散曲中,张可久自成一家。其作品以历史上归隐的高人或隐士为抒写对象;以怀才不遇之士或贤才遇“知音”为主题;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并对其进行评价。本文在全面探讨张可久咏史怀古之作的同时,还试图发掘他与其他散曲家咏史怀古散曲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
关键词:元散曲 张可久 咏史怀古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咏史怀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班固首先“咏史”标目,自产生后一直延续不断。到了元代又发展成为咏史怀古散曲。元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士大夫投入到散曲的创作之中,也是咏史怀古类作品较多的一个朝代。
一
张可久生于书香门第,贯云石称“小山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是深具传统气质的文人。一生积极入世,希望走一条传统文人入仕的道路,却始终壮志未酬。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沉抑下僚,一直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全元散曲》中所收集的张可久的作品数量为元人第一,其散曲多为写景言情、唱和、游记之作。咏史怀古散曲①数量虽然不多,却也自成一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1]
据笔者粗略统计,张可久现存作品中咏史怀古散曲有七八十首。根据这些散曲所表现内容的不同,可将其大致分为三类②:
(一)以历史上归隐的高人或隐士为抒写对象
他们不贪恋名利,于纷扰喧嚣的世界之外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净土,因此,他们就成为文人士大夫崇拜向往的楷模。这之中以邵平、严子陵、陶渊明、范蠡最多。如“青门外芸瓜邵平。白云边垂钓严陵。”([双调·折桂令]《读史有感》)“瓜田邵平,草堂杜陵,五柳庄彭泽令。”([中吕·朝天子]《野景亭》)同时写这些隐士的怡然自得,读书风流,“杨柳村中卖瓜,蒺藜沙上看花。生计无多,陶令琴书,杜曲桑麻。”([双调·折桂令]《幽居》)这样悠闲自得、诗酒自娱、隐居山野的生活是张可久所向往、追求的,因此欲“罢手,去休”却“已落在渊明后”。([中吕·朝天子]《山中杂书》)仕途的不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使张可久想要一种“投身老农家”“老向林泉”的闲适,但又充满着矛盾的心情;向往严子陵那样的垂钓隐居生活,但不具备放达隐逸的条件。生活的艰辛使他不能放弃世间的物质追求,又希望精神上有所寄托,所以就时隐时仕。用闲适的隐居生活来逃避现实,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人生自由,回复到一个传统文人宁静雅致的精神境界,完成精神的追求和人格的自我塑造。
元代社会现实的黑暗使大多数文人士大夫都有隐居林泉的思想。比张可久早一些的马致远,做的也是小吏,人生经历相似,不能够飞黄腾达实现抱负,不得不隐居山水田园,将它们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2]这样无奈的选择和精神的苦闷,在张可久的散曲中也得到反复的抒写。甚至像贯云石、张养浩这样的为官得意之人也高唱着归隐之歌,只是他们想要避祸全身,是与张可久、马致远般处于社会下层、抱负难以实现的文人士大夫们所不同的一种对归隐的向往。相同的是,那种清闲平淡、无是无非、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是他们最好的心灵避难所和精神栖息地。在山水田园中,心灵超越现实的痛苦,陶醉于自然之中,享受心自由的舒适和愉悦。
(二)以历史上怀才不遇之士或贤才遇“知音”为主题
传统文人的入世思想对张可久来说,是深挚而坚定的。在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下,和当时的文人士子一样,他也希望能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因此积极入世,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终不被元朝统治者所重用。他的咏史怀古散曲中就有大量的作品来抒写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江湖漂泊的愁苦。如“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误……人传梁甫吟,自献长门赋,谁三顾茅庐。”([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生活在元朝,即使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济世之才也没有三顾茅庐之人;即使像司马相如那样有赋在手,亦无可献之路,思量起来,感叹自己“枉被儒冠误”。另外还有“剑空弹月下高歌,说到知音,自古无多。白发萧疏,青灯寂寞,老子婆娑。故纸上前贤坎坷,醉乡中壮士磨跎。富贵由他,谩想廉颇,谁效常何。”([双调·折桂令]《读史有感》)借冯谖、廉颇等英雄被弃的命运,来哀叹自己被埋没的伤感。同时从历史上怀才不遇之士的例子中找到安慰,想到他们也曾有功名,尚且命运坎坷,自己又何必太过悲伤呢?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与古人产生共鸣,抒发“知音无多”、识才者难遇的感慨。这也是身处元代的文人士子的通感。当遭遇挫折、仕途不顺、壮志难酬之时,就借古人来宽慰自己,抒发愤懑之情,或借历史暗喻己见,表达对社会的不满。马致远就愤慨地唱出“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男儿未济中”“恨无上天梯”([南吕·金子经])的心声。
(三)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对其进行评价
这类咏史怀古诗中有感叹光阴易逝的“人生可怜。流光一瞬。华表千年。”([中吕·满庭芳]《山中杂兴》)看一切繁华都是过眼云烟的“铜雀台边破瓦。金鱼池上残花。谁见繁华”([双调·水仙子]《湖上怀古次疏学士韻》)有对古代英雄贤士的评价“立功名只不如闲。李翰林身何在。许将军血未干。播高风千古严滩。([双调·水仙子]《乐闲》)“菊老青松在。生前酒一杯。死后名千载。淮阴侯不如彭泽宰。”([双调·清江引]《张子坚运判席上》)
在作者看来,不管是曾经兴盛繁华的王朝,还是建功立业的贤才将相,虽然当时业绩辉煌,然而终究摆脱不了失败、失意和被历史淘汰的命运,最后终将是“浪淘尽千古风流”。这种历史观和人生观在元代绝非是个别散曲家的偶然流露,而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共同倾向。[1]如马谦斋《楚汉遗事》描写楚汉相争的历史风云,“龙争虎斗。争强争弱”,最后也只是“江山空寂寞。宫殿久荒凉。”雄风已去,霸业成空,正如虚无缥缈的南柯一梦。在“空寂寞”“久荒凉”“一枕梦黄粱”等字眼里,作者的态度是鲜明的。从对历史的关照中,彻悟人生虚幻,一切都幻化如泡影。
怀古之情怀,多起于登高临水之际,见古迹,思古人,元散曲中就有很多以地点直接为题的散曲。多以帝王曾建都的地方为伤悼中心,如姑苏、咸阳、长安、洛阳、金陵、汴京、临安等,也有曾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如骊山、赤壁、马嵬坡、华清宫等。张可久有[黄钟·人月圆]《会稽怀古》《吴门怀古》。其他的散曲家如卢挚就有[双调·蟾宫曲]《洛阳怀古》《咸阳怀古》等十几首。咏史怀古以朝代论,怀古多为春秋战国、六朝、隋代、安史之乱、南唐等,重在感伤或痛责君主荒淫,从而导致国破家亡。[3]张可久的散曲中以“安史之乱”为题材的有[双调·水仙子]《天宝补遗》、[双调·落梅风]《天宝补遗》、[双调·折桂令]《观天宝补遗》等。
二
元散曲中诸多怀古之作或咏叹古人,或凭吊古迹,其共同的基调则是借思古之幽情,悟世态之变化和人生之虚幻。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4]一书中提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一原则在理论上是后世儒家知识人所共同接受的,尽管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我们可以将这个观点适用于本文。
元代散曲家,他们大都是文人出身,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大批的文人仕进无路,沦落下层,被抛至社会的边缘。文人阶层社会地位的失落,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失去了依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就对这个“无道”的社会加以批评。在他们的笔下,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功名利禄、圣人贤才、伦理道德,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一切都是荒诞的,都是应当被嘲弄的。例如薛昂夫[中吕·朝天曲]二十二首,就对历代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隐士平民,从诗人到道士,无不受到讽刺戏谑。
“借史咏怀”,摆出历史,其最终指向是映照现实。从历史中,更加深刻地感到儒家规定的士人传统进取人生观的不可取。[5]殚精竭虑建立的事业和功绩不存在“不朽”的意义,到头来都只是一场梦,既然如此,建功立业、积极进取似乎已没有多大意义,那么又何必为此而“苦奔竞”呢?
相比较而言,从张可久的咏史怀古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与前期散曲家所不同的心理和清雅的文人情趣。前期散曲通常以“古”之悲剧映衬“今”之社会,张可久的怀古,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传统的伤感文人形象,这与前代散曲家的形象是不大相同的。[6]虽然内心充满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但他没有像前期和同时代的很多散曲家那样以放浪的方式玩世,极度的抨击社会,并给予无情的嘲弄,以示与传统价值取向的决裂。仕途失意,为了生活不得不沉抑下僚,强颜事人,使张可久有时也不免会有些牢骚,如[双调·庆东原]《次马致远先辈韻》就着实发了一些牢骚。但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那种愤世嫉俗、金刚怒目式的愤懑,表现出的只是含而不露,怨而不哀的情感。他登临怀古也只是低徊微叹,不像马致远、张养浩那样心情激荡。例如同样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为题材,马致远[南吕·四块玉]《马嵬坡》就写出了唐明皇的贪色、荒淫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安史之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唐明皇和杨贵妃所代表的最高统治者,而张可久的散曲相对而言就比较含蓄了。
可以说,张可久的散曲体现了一种对传统儒家观念的执著信念,以及不能实现传统儒家人生理想的悲哀。因此,其怀古之作的主题,虽然常包涵着对现实的伤感,但更追求一种传统文人宁静雅致的精神境界,与前期的咏史怀古之作相比,张可久作品的蕴藉含蓄是很明显的。
内文注释:
①咏史怀古散曲所选题材大都是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通过“借史咏怀”的形式,以古讽今,劝诫统治者,揭露社会黑暗,感叹朝代兴衰,表露作者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之情。可以说咏史怀古就是“以史写心”,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味。
②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本文是根据张可久咏史怀古散曲所写的内容不同而划分的。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散曲所写到的人物,如隐士,同时也是怀才不遇之人,因此,划分的类别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线。
引文注释:
[1]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罗忼烈:《两小山斋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3]莎白,王立:《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怀古主题》,江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
[6]朱万曙:《元散曲隐逸主题再认识》,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张晓晓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一中 713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