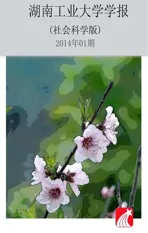关于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探讨*
2014-03-31甘智林
甘智林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关于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探讨*
甘智林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属于普通语言学范畴,过分强调具体语言的特性和对特定语言的解释性是对其学科性质产生认识误区的原因。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内容是从共性的角度讨论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展”。
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认识误区;学科内容
“语言学概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从学科体系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语言学(代码为740)与文学(代码为750)是并列的一级学科,其学科重要性毋庸置疑。1994年,伍铁平教授出版了专著《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论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论述了语言学科的领先性。彭泽润(1999)阐述了“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发展对策。[1]然而,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效果却不太理想,这在当前实际教学中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课程地位与教学效果的巨大反差的根源还在于对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学科性质认识上的任何偏差对课程建设、课程教学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与探讨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学科性质
(一)语言学概论学科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
1.引进阶段
我国第一部语言学概论教材是乐嗣炳(1901-1984)的《语言学大意》,由上海中华书局作为“国语讲义第九种”于1923年出版。全书大约2万字左右,共有九讲,涉及语言学的定义、研究方法、语言变迁、语言分类等问题,书中提到了英籍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MaxMüller,1823-1900)和德国梵语专家弗朗兹·葆朴(Franz Bopp,1791-1867)等西方语言学家,主要目的是引进和介绍西方语言学,正如作者在《例言》中所说:“跟世界语言学家互相提携,这是语言学界最所希望、所欣幸的一件事了。”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暨南大学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主要是根据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的《语言研究导论》为蓝本编写而成,内容较为充实。值得注意的是,张世禄先生在《例言》中指出:“本书编制的目的,在使读者明了语言的性质,并关于构造、组织、发生、变化种种的原理,以为各种语言学专门研究的准备”,这对我们今天认识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学科性质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张世禄先生后来对该书进行了修订,改名为《语言学概论》于193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以“语言学概论”为名的语言学概论教材。
2.苏联模式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斯大林语言学说”的浪潮中,“语言学引论”课程列为高等学校中外语言文学各系科的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以契科巴瓦编的《语言学概论》一书为框架,中国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批教材:“朱星(语言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年),宋振华、王今峥《语言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编的《语言学引论》(时代出版社1958年),都属于前苏联的模式。再后来出现的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是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2]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接受和模仿苏联的语言学说,西方语言学理论成了批判对象,内容主要是“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的阶级性问题”等,语言研究逐渐僵化封闭。最后一段时间各大学甚至取消了语言学概论课程。
3.发展与创新阶段
随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1980年“语言学概论”课程正式列入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计划。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语言学概论教材。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是这一时期发行量较大且至今仍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教材。这部教材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为蓝本,奠定了“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展”三大块内容的基本格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教材在“语言的发展”部分把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汉藏语系,对语言发展规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普通语言学。此后,徐通锵、李宇明、王德春、彭泽润、李葆嘉等学者有在各自的教材中增加了字本位理论、语用学、语言规划等理论,体现出发展与创新的特点。
(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
无论是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模仿苏联,还是发展创新,语言学概论都是对人类的全部语言作整体上的把握的一门学问,是探索语言本质的科学。考察现行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如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的《语言学纲要》、岑运强主编的《语言学基础理论》、余志鸿、黄国营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张世禄主编的《语言学原理》、骆小所主编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等,尽管名称各异,但这些教材论述的都是人类语言的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属于普通语言学性质。叶蜚声、徐通锵在《语言学纲要》1980版序言中指出:语言学概论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为学习各门语言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也为以后学习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岑运强《语言学基础理论》2004年版前言中指出:“语言学概论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是从理论上对全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进行研究的学问”。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和学者对此也有类似的论述,如彭泽润、陈长旭、吴葵(2007)指出:“语言学概论是站在全世界所有语言的基础上,强调的是语言最基础、最普遍的规律”,[3]聂志平(2010)指出:“语言学概论是语言学理论的入门课,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从共性角度讲述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运用、变异以及发展演变规律”等。[4]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就是普通语言学(或一般语言学)。对此,教育部在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大纲里作了明确说明:该课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阐明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起源及发展等基本理论,通过教学,要求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三)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逐步深入,语言学概论教材建设不断推陈出新,语言研究者对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更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理清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对语言学概论学科建设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普通语言学诞生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出现并空前繁荣之后,毋庸讳言,普通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诸语系诸语言的研究之上的,当时包括索绪尔在内的西方的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藏语系诸语言都谈不上深入的了解。陈望道先生曾指出:“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5]的确,这一现象不仅使学生感觉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远离汉语实际,也增添了教师教学的畏难心理。甚至有人因此认为西方的普通语言学是“不普通的”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的建立基于以下两个理论前提:一、人类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二、以人类所有的语言为研究对象并总结出一般规律是可能的。中国绝大多数语言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前提并不怀疑。上个世纪赵元任、朱德熙等先生等运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汉语语音、方言、语法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探索,其研究方法与成果对当今的汉语研究仍具有范式与指导意义,也证明了西方普通语言学对人类语言的一般解释力。王力先生甚至认为:“可以这样说,最近50年来,中国语言学各个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就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6]王希杰在总结一百年来中国理论语言学历史时指出:“流行的西方色彩浓厚的普通语言学的确是比较地科学的,它的缺点是还不够普通,这也是有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本当具有更广阔的心胸,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上来建立更加普通的普通语言学。”[7]因此,中国学者应不仅有汉语自身的眼光,也要熟悉世界各民族及国内少数民族语言,要以一个语言类型学的眼光把汉藏语的研究融入普通语言学,丰富普通语言学,发展和完善普通语言学。这既是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也是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及教材建设所应遵循的原则。
二 对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认识误区
如前所述,语言学概论是对人类的全部语言作整体上的把握的一门学问,其语言研究的角度和立足点是“求同”。如果偏离了“求同”这一根本立足点,着眼于语言的“异”和具体特点,对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的就会出现似是而非的认识,甚至将语言学概论与语言的其他研究领域混淆起来。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应该处理好以下两类关系:
(一)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与语言文化属性的关系
申小龙(2004)认为:“高等院校中文学科的基础课程‘语言学概论’,是一门讲述普通语言学基础理论的课程。以往,这一课程全部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语言学。这一‘习惯’做法,隐含着两个语言学假设:其一,语言不属于文化范畴,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是相同的。西方语言学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二,语言学理论不属于文化范畴,人类各民族的语言理论中,西方语言学理论是唯一科学的。”[8]这段话中提出的两个“语言学假设”逻辑含混,第一个假设中包含两个似是而非的论断:一、因为普通语言学认为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是相同的,而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有特点的,所以语言不属于文化范畴;反之,承认语言的文化属性,则必须承认人类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规律是不相同的。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概论学科的人类语言“共性”性质与文化对语言的特定影响对立起来了。我们认为:语言在更高的层次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属于文化范畴,但语言的文化属性并不能否定作为共同物种的人类的语言不能具有相同的基本规律,人类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律恰恰是普通语言学得以建立的理论前提。二、语言学概论这一课程全部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语言学,西方语言学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认为:普通语言学从理论上对全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进行研究,能揭示人类语言一般规律的,不管某种是来自西方还是中国,都是科学的,都属于普通语言学。如前文所述,上个世纪赵元任、朱德熙等先生等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音、方言、语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证明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人类语言的一般解释力,是普通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反过来,如果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人类语言一般规律的高度,对西方和世界其他民族语言具有解释力,也就在普通语言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普通语言学的组成成分了。
(二)语言学概论学科性质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关系
语言学概论的教材和教学要结合我国语言研究和教学的实际,但在具体实践中应处理好“一般规律”与“特定语言现象”的关系。汉语语言学研究包括现代汉语与方言研究,属于具体语言学,如果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过分强调具体语言特点,则背离了课程的学科性质。
马学良、瞿霭堂(1997)指出:“我们认为中国的普通语言学教学首先应该本土化,即中国化,以中国的语言学理论为主导,中国的语言现象和资料为基础,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为目的”。[9]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普通语言学研究和注重的是人类语言共性和一般规律,不是微观地研究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更不能仅仅以“中国的语言现象和资料为基础”,也不可能有所谓本土化和中国化。
谢奇勇(2010)指出:“现行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其理论部分的内容较多的是借鉴或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如何在语言学概论中占有一席之地?”[10]这里涉及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国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概论3个概念,我们认为,在语言学概论学科中,不应存在国外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理论之分。如上文所述,能揭示人类语言一般规律的,不管这种理论是来自西方还是中国,都属于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的语言识别和方言研究”、“中国的双语现象和双语研究”、“中国的文字问题”等具有中国语言研究实践和理论当然可以出现在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内容中,但必须从人类语言共性和一般规律角度进行研究和阐释,不能只强调其特性而不注重其一般性,否则那就是汉语语言学了。
总之,语言学概论的学科性质要求我们着眼于人类语言的“同”,而不能过分强调具体语言的特性和对特定语言的解释性。
三 语言学概论学科的内容
根据关彦庆(2010)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内容上大都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既有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又有言语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编者的自主创新意识”,“彭泽润、李葆嘉的《语言文字原理》(1995)增加了语言规划理论。王德春的《语言学概论》(1997)介绍了边缘学科。李宇明的《理论语言学教程》(1997)介绍了语言运用和语言学习理论。徐通锵的《基础语言学教程》(2001)重视字本位研究视角,体现汉语研究成果。岑运强的《语言学概论》(2004)重视言语的语言学研究。”[11]上述教材的出现既是语言学概论内容改革的一个良好探索,但也反映了编者对语言学概论学科内容的不同理解。
曾毅平(2001)认为:“近几十年来,西方语言学发展迅速,但当代语言学甚至现代语言学的重大成果没能得到应有的反映”。[12]但正如陈青松、张先亮、聂志平(2012)指出的那样:“尽管现在国内高校使用的课程教材多种多样,侧重和创新多有变化,……“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展”三大块内容都是课程的主体。而这三大块内容基本理论观点都基本上统一在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框架内。有学者和教师对课程的教学内容多有批判,但往往批判的东西又在批判者的教材和课堂中出现。”[13]
我们认为,语言学概论学科的内容就是从共性的角度讨论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发展”,这种基本一致性归根结底是由其学科性质决定的,而不仅是因为多年的学术传统和教学实践。语言学概论阐明人类语言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后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影响较大的语言学理论不属于普通语言学,它们只不过是新的语言研究方法对某些具体语言的特定方面进行研究,其创新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而不是语言结构和语言发展规律的创新,其对人类语言共性和规律的阐释还没有达到颠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程度。我们可以在语言本质论部分增加相关的介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能处理成语言学流派讲座,只能就这些流派的语言本质观对结构主义语言本质论进行对比分析;二是在后面的语言结构论和语言规律论中要能有机穿插这些语言学理论,真正起到开阔理论视野、促进普通语言学理论建设的作用。
字本位理论、语用学、语言规划理论等能不能纳入语言学概论内容?这在目前还处于实践探索过程。谢奇勇(2010)指出:“语用学应该纳入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内容,并且是在‘理论’(即普遍规律)的层面纳入”,[14]因此,上述理论和内容在多大意义和层面上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就是一个值得慎重研究的问题了。
最后附带一个与语言学概论课程学科性质紧密相关问题,即教学目的。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语言学概论的普通语言学性质,决定了它是一门用以指导各类语言的学习和研究的基础理论课,所这里所分析的“语言”不应该仅仅只是现代汉语,而是应该包括汉语方言、英语等其他语言。当前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目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应该引起重视。
[1]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J].语文建设,1999(2):49-53.
[2][7]王希杰.一百年来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的道路[J].平顶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1-8.
[3]彭泽润,陈长旭,吴葵.“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协调改革发展[J].云梦学刊,2007(4):135 -138.
[4]聂志平.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问题探讨——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7-81.
[5]陈望道.文法简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6]王力.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J].中国语文,1957(3):38-45.
[8]申小龙.论高校“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理论创新[J].辽宁师专学报,2004(5):8-11.
[9]马学良,瞿霭堂.普通语言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前言.
[10][14]谢奇勇.关于“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国大学教学,2010(1):52-55.
[11]关彦庆.关于“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思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3):6-8.
[12]曾毅平.“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若干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1):70-74.
[13]陈青松,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用例选择和使用的原则[J].中国大学教学,2012(6):45 -51.
责任编辑:李 珂
Discussion on the Discipline Nature of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
GAN Zhi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 Hunan 415000,China)
The discipline nature of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 belongs to the general linguistics category.Itoveremphasizes the characteristic,and explanation of specific language is the reason for themisunderstanding of its discipline nature.The discipline contentof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 is discussing about“the language essence”,“the language structure”,as well as“the language development”from the angle of general characters.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discipline nature;misunderstanding;discipline content
H0-05
A
1674-117X(2014)01-0153-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29
2013-05-03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模式的多维构建——‘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研究”湘教通〔2010〕243
甘智林(1971-),男,湖南津市市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