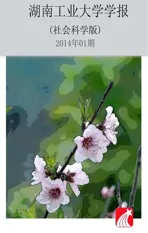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
——以“启蒙”为中心考察
2014-03-31刘长华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0081)
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
——以“启蒙”为中心考察
刘长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0081)
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除了源于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和传统诗学用典意识的积淀等之外,“启蒙”使命更是关键因素。促成这两者联姻最重要的契机就是类比诗性思维,这表现在新诗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质来类比中国现代“启蒙”文化,而类比思维恰恰又是中国神话的鲜明精神结构和国人的思维个性、文化特征。
类比思维;神话诗歌;民族神话;启蒙文化
无论承认与否,启蒙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它作为鲜活的实践,承载过知识界的“光荣与梦想”,也凝结过他们的“苦乐年华”。它的形象姿态就在于高扛着“理性”的猎猎旗纛。殊不知,正是在“启蒙”这样一个滚滚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常以“非理性”“荒诞”等面孔出现的神话、传说获得了从历史漩涡中泛起的更大势能。自不待言,当民族神话、传说在有“时代晴暑表”之谓的诗歌中汩汩上冒时,这也正好折射出启蒙的高歌猛进、腾挪跌宕。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也是大力发掘希腊等神话资源,智性、人性等是它所倚重的,而中国神话则以德行、神性为主脑,与“启蒙”内蕴上颇为方枘圆凿。所以,造成这种“相向”而又汇流的局面,与受到“文艺复兴”的历史启示联系不甚紧密。在我们看来,其根由应在于类比诗性思维的根深蒂固。众所周知,诗性思维是意大利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一种以“想象”“情感”等为主导的主体性活动与客体的高度融合的精神生存把握方式,是一种思维智慧和创作性思维,是人类初级阶段的思维特征。而类比诗性思维则是“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分析与表达的目的”。[1]很多文化学者认为,类比诗性思维典型性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理个性、文化特征。不过,需提醒的是,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神话的精神结构又是“孪生”的,两者互为表里地成为后世诸多精神现象的泉源。那么,类比诗性思维究竟如何促进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蕴与“启蒙”文化两者结为姻缘的,并聚集在中国诗歌进而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运动麾下,便是问题要讨论的关键之所在。
一 “混沌”类比启蒙之初的社会生态
在人类文明的首页翻开之前,是“混沌”主宰世间一切,它是中西创世神话的共有意象。在中国,“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庄子·应帝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天问》,郭沫若将其译为:那是混混沌沌,谁能够弄清?);畲族的《盘古歌》中也说:“天地混沌,先有盘古”,等等。在西方,“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旧约全书》);“万物之先有浑沌,然后才产生了宽胸的大地”(《神谱》);“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空间都消逝不见”(参见卡西尔《人论》),诸如之类。不管中西文化语境之下的“混沌”一语于具体指涉上有何区别,但它都应是人类自我意识萌芽、理性开启之前的整个生存形态的精到概括。不过,最大的区别也就在这里,西方视域之下的“混沌”正是孕育着生机与可能的象征,是后世各要素得以成长的母基,《圣经》中所包含的叙述语态就充满着“向后看”的希望与欣喜,其本身就以否定性的姿态出现;而中国意义图景之下的“混沌”在后世主要是表现出一种美学境界上的追求,“天人合一”“浑融”等范畴正由其派生而来,表达的是静止、“返回”的精神,其本身在内蕴上有着自我肯定的诉求。对传统意识的反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最撼人的举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混沌”一词在语义上要为新文化运动者所择取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神话之概念界内的,惟其如此才成为批判的靶子。就先知先觉者而言,他们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哺育,是以反思、质疑为精髓的现代理性拥有者。所以,在这些人眼里,“礼制”文化经过几千年风雨的浸洗,趋于成为心灵的“盐碱地”,广大百姓生存于其上被教化、奴化、钝化,他们完全是理性的缺席者,不存清明之气,就是升级版的“人之初”,历史上演了一曲轮回者的悲剧。“混沌”在传统文化语境就是蠕动在鲁迅等人笔下的“铁屋子”“鲁镇”“茶馆”中的那些群体;就是乡土小说中那些麻木不仁、自我丢弃的父老乡亲……当然,这种直觉感受早在陈天华、梁启超时就诞生了,《狮子吼》的楔子中以“混沌国”隐喻中国,后者的《呵旁观者文》中4万万国民就是混沌一团。基于中国历史情状,鲁迅不禁疾言感愤:“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东方学》中有言:“理性为东方的偏激和过度所削弱,那些具有神秘的吸引的东西与自认为正常的价值相左。”[3],此言有所差矣,被理学所阉割过的国民是无从予偏激、过度以形诸的。闻一多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绝非夸张之辞。与之同时,就在这片被传统所板结的土地上,从清末以降很长一段时间内,混战不歇,思潮蜂拥,乱象环生,风云变幻,天地玄黄。“五四”之际,蔡元培曾以“风雨如晦”来黾勉学生及同仁“鸡鸣不已”。
和这种整体文化环境一致的是,新诗就常以“混沌”来描述诗人对生存世界的感受。闻一多在《南海之神》中写到:“百尺朱门关闭了五千年;/黑色的苔藓侵蚀了雕梁画栋,/野蜂在兽环口里作了巢,/屋脊上的飞鱼,鸱枭、铜雀,宝瓶……/都狼籍在臭秽的壕沟里。/宇宙乘除了五千个春秋,/积尘瘗没了浮鏂钉,百尺朱门依然没有人来开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侯”。闻一多的这幅“工笔画”与人们印象之中的“混沌”图像——整个世界没有生灵、云水翻滚、烟雾茫茫、一派氤氲等颇有出入,但是这正“吊诡性”地说明了此“丑学”视野下的“混沌”属于中国范畴的,理由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正也是在这么一个语义结构之中,诗中就以孙中山类比“第二个盘古”,前后之间于整体上构成了逻辑统一。在闻氏之前的郭沫若,他的诗歌人生正是从神话、传说中开启的。众所周知,诗剧《女神之再生》中就是直接以原始神话为抒写题材,诗歌写到“共工”与“颛顼”酣战之时,颛顼抵挡不住来犯,无力回天时哀号不止:“天诛快……咿呀!咿呀!怎么了?/天在飞砂走石,地在动摇,山在爆,/啊啊啊啊!浑沌!浑沌!怎么了?怎么了”。此中的“浑沌”可以理解为《神异经》中嗜恶如命、残害忠良的怪物,当然更可视为本文上面所指之“象”。因为这与后文所写:“——雷霆住了声了!/——电火已经消灭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已经罢了!/——倦了的太阳呢?/——被胁迫到天外去了!/——天体终竟破了吗?”构成衔接;更是为后文的道白:“诸君!你们在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当中怕已经坐倦了吧!怕在渴慕看光明了吧!”做出了铺垫。诗人以“混沌”为文化运动的箭镞,其矢的就直奔“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魂兮,归来”,同时人们也不再满足从政治层面对“史无前例”的伤痛进行抚慰和反思,而是希冀从文化切口对这满目疮痍、因袭负累的民族精神世界寻根溯源、一勘究竟,两者激情相遇、相得益彰。民族神话、传说因此再次纷纷“粉墨登场”。韩少功小说《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就是意指混沌时空。应该说有了“寻根”这条导火线,当代一些诗人的灵感得到了擦亮和点燃,他们拟从史前文明和原始精神出发,抱着理性与浪漫,并融入现代哲学对存在、对自由等命题的思考以及人类批判工业文明的思想成果,对民族文化以至于东方文化进行发掘和重造,构架神话体系与西方史诗对话。杨炼的《诺日朗》、海子的《太阳·断头篇》、北岛的《古寺》、彭燕郊的《混沌初开》等作品相继面世。这些作品中依然描述了“混沌”场景,作为原色背景来烘托生命的出场,进而赋予生命形而上的思考。这依然是启蒙,不过已是建立反思科技或工具理性层面之上。
二 “开天辟地”的文化英雄类比启蒙姿态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界就突破了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从内部对启蒙在中国的是非曲直展开巡检和反思,有人曾经说:“‘五四’启蒙主体膨胀了的文化优越感也好,咄咄逼人为我所是的‘霸气’也罢,通通来自启蒙主体扮演的掌握了话语优先权和专有权的身份、角色,以及由此决定的启蒙主体在言说过程中对启蒙意图的理性阐释和激情发挥。”[4]这是比较准确地道出了“五四”启蒙情状的一种真实,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所流露出作者的情感倾向、写作姿态等对此可谓有着充分的印证。确乎,作为知识和理性即“道”的既得者,作为外出阅历过世界的行者,这些“知识层”自然就会怀揣着比“引车卖浆流”多出几份的优越与自信;同时,在多灾多难的近现代中国,在现代公共空间走向历史舞台之际,儒家文化强调个体对社会承担的“死灵魂”在这特定时空之下得以最大程度地复活,因此这些“知识层”都是带着几分“真心英雄”的自许,气壮山河,力争打破转型期文化上的“混沌”,充任“盘古”在文化疆壤上“开天辟地”,创造出新的纪元。创世神话令他们心迷神醉,在新诗中这类神话、传说无疑是投射了作者们浓郁的主体意识的。当然,这些启蒙者抱着“开天辟地”的比附性遐想及其雄心壮志,一者是激进主义思潮累积而成的必然喷薄;二者这种雄心壮志实则扼腕之痛,更是映衬了在世界文化赛道上中国落伍之巨;再者也是人文主义对“人”的高扬的客观表现。
正如后人将诗集《女神》历史定位为“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5],它里面的诗作不是最早的,却成了新诗的“开天辟地”之作。或许这就是奇缘,作者在内容里面正好表达了“开天辟地”的主题,诗风与主题构成了格式塔式的同质。《女神之再生》中“女神”们复命历史的就是重新“开天辟地”,共工与颛顼两相“争帝”而最终同归于尽的题材中寄寓了作者对帝制、对权力、对上层统治甚至对男性的厌弃,从而表达了对民主、自由和“地母”即生命力的讴歌,非常契合时人“大破坏大建设”的精神气概和文化策略。其中的“女神”和“这幕诗剧的诗人”是合二为一的,作者的身影按捺不住,“这幕诗剧的诗人做到这儿便停了笔,他真正逃到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心气高远的郭沫若跃然纸上,传达了一代人的心声。在《湘累》中,主人公屈原自白:“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出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这种自白其实也是郭沫若的自况。《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华美蜕变,光风霁月,宇宙为之一新。这依然是对先前诗歌中“开天辟地”主题的接力。闻一多的《南海之神》中对“中山先生”诞生的咏叹,文章的结构方式本身就遵循着中国神话思维模式,像“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史记·帝王世纪》);“登,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于裳羊山”(《史记·帝王世纪》);“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史记·帝王世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夏本纪》),等等,这些都极富想象性地描述了中国“圣人”们与众不同的出身,充满了神玄谶纬色彩,摄人心魄。整个诗篇的思想基调、艺术氛围都围绕在挽悼、歌唱中山先生“开天辟地”式丰功伟业之上,抒发了对文化创造精神的神往。在《长城下的哀歌》中,诗人热烈呼唤“哦,鸿蒙的远祖——神农,黄帝!”饶有兴味的是,被孔子称为圣人的“尧舜”们,在新诗中被激活,不过伦理道德不再是他们的身份符号,无所畏惧、勇于开辟的文化创造精神才是这些诗歌所要择取的。
新时期对长期以来的“左倾”思想予以了清算,笼罩、纠结在人们头脑上的阴霾终于被拨开了,一切似乎是重见天日,给人同样有种革故鼎新、新纪元横空出世的意味。昌耀的诗歌《划呀,划呀,父亲们!——献给新时期的船夫》,以类神话的叙述结构,表达了“开天辟地”的追求和气概,“我们昂奋地划呀……哈哈……划呀/……哈哈……划呀……/是从冰川划过了洪水期。/是从赤道风划过了火山灰。/划过了泥石流。划过了/原始公社的残骸,和/生物遗体的沉积层……/我们原是从荒蛮的纪元划来,/我们造就了一个大禹,/他已是水边的神。/而那个烈女变作了填海的精卫鸟”,意境浑融而元气淋漓,改造世界、洇渡过去的英雄群体亦将主宰未来。杨炼的《诺日朗》:“我是瀑布的神,我是雪山的神/高大、雄健、主宰新月/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我来到的每个地方,没有阴影/触摸过的每颗草莓化作辉煌的星辰/在世界中央升起/占有你们,我,真正的男人”,俨然当年的郭沫若神采转世而来。这种对强力的炽热呐喊让人看到更多的是一种类似“弥赛亚”的豪情,但是这种“弥赛亚”是属于中国的,因为它在启蒙身姿上难以觅见自我救赎的情结,这应是中国启蒙最终消歇下去的又一个重要内因,当然这是另话,不必展开。
三 “渎神”类比对传统圣明的解构
勃兰兑斯在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对浪漫主义的兴起有过精辟论析:“直接反对的是十八世纪的某些思想特征,它那枯燥的理性主义,它对感情和幻想的种种禁忌,它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它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视,它对大自然索然无味的看法和它对宗教的错误概念,认为它是有意识的欺骗。”[6]中国启蒙文学并非能削足适履合乎这个论断,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启蒙文学似乎对西方的逻各斯主义、经验主义张冠李戴式的移植过于严重,“超验性”在价值天平上明显下跌,忘记或忌讳文学本身就具有超验性一面。所以从理论上讲,尽管不少舆论为神话、传说护过法,正面阐扬过它的价值,但是对于“神”或“神圣”之类的采取娱乐、亵渎的心态也就是在所难免甚至家常便饭,挑战了权威又顺乎了科学,也实现了对人、对人性的张扬和彰显了平民百姓的力量,“民心”“天理”俱获,整体上切合启蒙主义的价值路线。这一切皆因在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正是对神性最大的应诺和追求,帝王将相不惜神化自我、扮成圣明,经书典籍被士大夫奉若神明……自然,这种解构与封建时代士大夫耻于言及神话、传说的不可同日而语了。“耻于”是奚落、潜压,而“解构”是批判、是攻击,却也是将其从历史的冰封中推向了现实前台,获得了面世、被关注的可能。与之同时,在这个过程之中,反讽的是启蒙对神话、传说这些所谓“超验”文化现象予以解构,它自身对理性的绝对权威进行了树立和确认,也就制造出了目前已被学界所批判的“启蒙神话”。同样,20世纪中国尽管有过波诡云谲、风雨苍黄,总体上却是其天翻地覆、今非昔比,历史的进步可谓风行电掣、夸父再世,在心存感恩、感怀的人们看来这本身又是最大的神话传奇。出于对历史和自我的礼赞,民族神话、传说往往又成了载体,但是其中往往蕴含着一个价值预设——传统是可以超越的,人类是可以超越“神”的。所以,启蒙愈是高举“理性”,社会愈是呈现“进步”标识,神话、传说在被解构、被祛魅中就越有生存机会,“渎神”也就成了对传统“圣明化”的解构、超拔的精神符码,主体再次以类比的体验博获了对启蒙的认同。启蒙本身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未完成的工程”,是不断超越的事业。
应该说祛魅“神话”的序幕是鲁迅揭开的,不过在《故事新篇》里鲁迅显然不是举打着理性主义之光对民族神话、传说作常规意义的口诛笔伐。反之,这与他对神话终其一生的珍爱相互龃龉。于此,鲁迅恰恰敏感地揭橥了作为启蒙者其自我所设定的“神圣”姿态不免会坍塌,他对启蒙的实践及其意义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思考深度,与其“一切都要由‘我’自己决定,‘我’别无选择”[7]的思想精髓前后贯通,不信任任何“神圣”的这份清新与冷静或许只属于鲁迅式的“最后的”理性者。“情圣”徐志摩在《雷锋塔》中写白素贞:“到今朝已有千百年的光景,/可怜她被镇压在雷锋塔底,——”,坟头斜阳荒草,寺院晚钟远去。作者显然对白娘子的“多情”是同情惋叹的。但诗中的弦外之音,就是“划船的”这类平民百姓对白素贞“为了多情,反而受苦”表示摇头,难以理解,似乎表现出了少有的理性思维。换言之,“情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无法想象的奢侈,“爱情神话”终究倾圯。诗人与“划船的”进行了一次价值观的无声对谈,“划船的”不执信“爱情神话”或许令他激醒。作为文化人徐志摩马上自置于心理高台,对“划船的”言论表示并不认同,因此他又从这桩神话中获得了救赎,仍旧诗意盎然地相信爱情神话;而“划船的”自以为是的,去解构神话、传说反倒印证这个被启蒙者亟待现代价值理性的灌输,因为他们过于拘泥于实用与现实。“白蛇传”这桩神话馈赠过徐志摩,他对“情感”的理性化感悟是强烈的,所以他还写过《月下雷峰影片》《再不见雷峰》等相关的诗作。
对理性的高度张扬,莫过于对与“科学”相关的这一精神与意象的书写。神话、传说就其产生而言,原是包涵着先民努力地解释世界,是原始“理性”的最大化,但在现代视域之下,就捉襟见肘、荒诞不经了。不过,新诗人又用民族神话、传说承载着对现代科技的歌咏,郭沫若笔下“天狗”意象承担现代科学意蕴已是尽人皆知,科普杂志《科学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性地刊发一些文言诗歌来介绍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其中不少就用到神话、传说等意象。30年代初,卞之琳在《大车》一诗中以“骡子大车”来象征着老大中国缺乏科学动力的引擎而步履蹒跚,与夕阳为伍,作者对现代交通、现代科技的强烈而不着痕迹的愿望寓含其中,这种意愿就转化成对神话、传说的比附:“古代传下来的神话里的英雄/腾云驾雾去不可知的远方——”。20世纪80年代初,卞老身心解禁,有了领略域外文化的机会,现代化科技让他再度心潮澎湃,“月球上肉眼看到的建筑/还惟有东西横亘的长城——/却多承宇航员带来了消息。/嫦娥把孤凄只留给自家,织布、牵牛,就不会通电话——”神话与科技两相比照中给科技赋魅。显然,这些诗歌的背后都是隐含着现代科技对神话、传说的胜出,对历史的胜出。
立足社会进步、创造历史的角度,民族神话、传说成为人们咏叹今必胜昔、人定胜天等一些理念的载体也是不乏其例。毛泽东时常将其伟人气魄融入古典诗词,是这方面创作的典型之一。“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诗歌也有这种写作习惯。冯至先生在建国后的一些创作《韩波砍柴》《宜君县哭泉》《人皮鼓》等中有意识地遵从一些神话、传说只属于过去那些过去岁月,而新社会人民把神话、传说改写成了最美好现实的创作指导思想。
四 “神巫”仪式类比启蒙的诗性想象
启蒙过程之中是类比实现了神话仪式感的诗性践行。“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凭依,故谓之曰灵”[8]。王国维从中指出一种仪式感是“灵”之存在的必然因素,也是其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源泉之一。当然仪式感也常常是充满诗性,正如弗雷泽有所谓的“模仿性巫术”和“交感性巫术”两类,前者是充溢着游戏精神、童年心态、狂欢意气,后者表现出人与物、身与心浑然交融的境界,套用狄尔泰对诗的解释,这种“交感”“将灵魂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同时又向灵魂显示现实的意义”[9]。所以,这种仪式感是对诗性想象一种践行,而“诗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诗人是明察生活含义的目击者”[10]。所以,最初的巫师就是最本真的诗人。现代启蒙所展示出的仪式化过程在某种意义就是对原始巫术传魅通灵的这个原型的复现,启蒙者也就是巫师的“投胎转世”。从理论上而言,启蒙者本身应该也是浑身洋溢着诗意,诠释着诗性的内涵,但20世纪中国启蒙者是“慷慨悲歌”的,终以悲剧的方式落幕,这是令人不胜遗憾的。
纯粹的神话、传说作为语言的表象,它们本身难有仪式感可言。仪式感何其而来?这时神话、传说的传播往往依托正如上文所引王国维的“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不过,由于北方位居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瞽叟、大巫这类职者被史官化,像左丘明等即是代表,口传文化不再得到重视,这本身也是导致中国神话不够体系化的原因,所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口传神话的大家巨人,有的话也只能淹没消弭在边村远寨、街头巷尾之中。所以,屈原虽位列贵胄,但身受楚风浸染,口传的丰神在其笔下灼然可现。《天问》让人依稀地看到一个峨冠博带的巫师仰面昊天,向宇宙发问、对话,俨然通灵者的角色。《招魂》更是以楚地所保留的“人死后让灵魂回家”的迷魅习俗为诗人灵感着火点,通篇笼罩一派浓郁的巫觋气氛,直接活脱出“招魂”的场面,“招魂”因仪式感而实至名归。不过,在我们看来,这里面还包含一个层面的“招魂”,那就是屈原一直哀叹“举世混浊”“众芳污秽”,其中也包括楚王的昏聩无能,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魂魄放佚”,因此屈原不仅是在为亡者悼挽,而且是在唤醒行尸走肉的所谓生者“灵魂还乡”,这才是真正的哀国之音。在这一点上,启蒙者、巫师和诗人身份在屈原身上汇聚成了真正的“三位一体”。
以神话的仪式感来传达启蒙意向在中国新诗史上是屡见不鲜的。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的《群鸟歌》一反“百鸟朝凤”的模式而成“百鸟嘲凤”,但这种模式所带来仪式化氛围并未削减,被启蒙者吃掉启蒙者的悲剧感由是得到了深度呈现。闻一多在《南海之神》中为颂扬孙中山的神异,以充满仪式感的山河场景:“于是宇宙万物尽他们所有的,/都献给他作为庆贺的仪程了”为陪衬、为渲染,其对这华丽壮观的出场描写更是不吝笔墨。在这颂扬的背后,无疑是离不开如前文所说对启蒙者自身的礼赞,让人领略到启蒙者的姿态并不简单。就上文所提的“招魂”主题而言,撇开战时一些对阵亡英雄的悼念作品之外,郭沫若、饶孟侃、孙大雨、朱自清、朱湘等人都涉足过,其中的确有出于对逝去的亲朋好友一寄哀思的,甚至其中的意象并不完全是对典型意义上的神话、传说的袭用,但是无论是饶孟侃的吊亡友杨子惠,朱自清对友人的“招魂”,还是孙大雨对徐志摩的追怀,都已经超过了一般概念上对生命永逝、阴阳两隔、亲情斩断的悲恸,更多的是融入了作者的主体性情感体验——寂寞而充满了诗性色彩与神秘主义,表现出心灵沟通强烈的欲求,无不隐现着当年屈原上下求索却无路而通过“招魂”方式间接地倾诉衷肠的影子,这些作者都是将自己和亡友摆放着“独醒者”的人格姿态之上。这种姿态就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启蒙者姿态,这种“招魂”可以视为文化的“招魂”、人格“招魂”,让我们看到了身处中西文化碰撞之下中国历史嬗变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虑让灵魂何处安家的惶惑,这是早知早觉者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征象、必然诉求以及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更是在为广大活在“混沌”之中的百姓“招魂”。总之,在这种“招魂”的过程之中,诗人实现了与自我与自然的心灵对话,依稀复现了通灵者的丰韵。
综上所述,“启蒙”虽然在20世纪中国开展得并不彻底与深入,但是它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文化的大观与时代的核心征象,在我们看来,国人深层次的思维结构之作用是居功至伟的。类比思维让不少启蒙者体验到了几千年前的神话意识,所以他们就以民族神话、传说来建筑启蒙工程,事实上类比诗性思维又正是民族神话、传说在思维结构上最本质的特点之一,两者是互为表里的。自然,这一过程之中也就有意无意地增强了新诗的民族性,譬如诗歌的生成方式,譬如表达的题材,譬如诗歌意象的营构等。但是,在通常看来,新诗运用民族神话、传说就是诗人在表达着浪漫主义诗风。浪漫主义作为西方的概念,不少诗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或者一些现代派诗人对此都是大加摒弃的,但这又不妨碍他们使用民族神话、传说作为写作材料。所以,立足于民族神话、传说本身的特征来展开新诗的民族性分析,应该是一条不俗的路径,能推动中国新诗与中国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为新诗在未来文化全球化的局势下之建设提供启示意义。
[1]王 宁.中国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6.
[2]鲁 迅.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5.
[3]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7:72.
[4]倪婷婷.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J].江苏社会科学,2004(1):204-209.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
[6]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4.
[7]汪 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7.
[8]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52.
[9]毛 峰.神秘主义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65.
[10]刘小枫.诗化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3.
责任编辑:黄声波
Analogical Poetic Thinking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M ythological Poetry——W ith“En lightenm ent”as the Center of Investigation
LIU Chang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 China)
About the rise ofmodern Chinesemythological poetry,in addition to originating from the accretion of translatingmythological theorie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using allusions in traditional poetics,themission of enlightenment is a key factor.Analogical poetic thinking is themost important juncture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marriage of these two aspects.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authors of new-style poetry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make use of nationalmyths,legendary imagery or essence as an analogy tomodern Chinese Enlightenment culture.And analogical thinking is indeed the distinctive spiritual structure of Chinesemythology and the individual thinking feature,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eople.
analogical thinking;mythological poetry;nationalmyths;Enlightenment culture
I207.25
A
1674-117X(2014)01-0121-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22
2013-04-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族神话、传说意象与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建构之研究”(11YJC75104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神话、传说对中国新诗民族性的影响研究”(2010YB244)
刘长华(197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