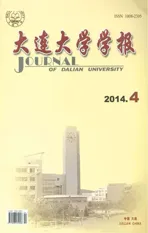武则天故事与宋元文人心态
2014-03-23韩林
韩 林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622)
武则天在中国古代帝王系列中的特殊位置,使她难以淡出人们的视线,无论哪个朝代,武则天都是人们谈论不衰的话题之一。武则天故事是从历史移位到文学中来的。囿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唐五代的武则天故事比较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宋元时期的武则天故事则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无论是史书、政论、诗歌、戏曲还是小说中,对武则天的记录不再局限于故事本身,而是成为作者的传声简,人们通过武则天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一、北宋:借反对武则天以警示后妃执政
北宋时期对武则天故事的研究与重写,与当时女性参政的现实密切相关。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他认为武则天“虽刑罚枉滥”,但“终不杀狄仁杰”,在用人方面还是有独到之处的。此后,由于北宋后宫“垂帘听政”出现的频次较多,文人士大夫为防止后宫威胁王权做出很多努力,这也是宋朝没有出现“女皇帝”的原因之一。通过武则天含沙射影,是他们的惯用手法。
北宋的文人士大夫通过史书的撰写为后妃敲警钟。《新唐书》是在刘太后去世不久开始编撰的,难免有敲山震虎之意。《新唐书》作于1044-1060年,是宋仁宗当政时期。宋仁宗年幼继位(1023),由太后刘娥(968-1033)垂帘听政。刘太后是宋真宗赵恒的皇后。天禧四年二月(1020)真宗患病,朝廷大事多由她裁决。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刘祯继位,真宗遗诏尊刘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这就给刘后参与政治提供了依据。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直到过世。这时刘祯已经22岁。此前,刘祯早已成年,但刘太后迟迟不肯归政。刘娥并非没有僭越之心,但迫于现实无法实现。她当政时,方仲弓曾上书,请求按照武后的办法,立刘氏庙,刘娥没有照做。程琳呈献《武后临朝图》,刘后掷图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宋史·后妃列传上》),这都是做给别人看的,虽然刘娥表面上拒绝做武后第二,但她内心很想学武则天。她以自己的生日为长宁节,规格与皇帝的乾元节相同;刘后与年幼的宋仁宗一同外出时,乘坐大安辇并要走在皇帝的前面。有一次刘后谒太庙时,竟然穿衮服。曾慥《类说》载,刘后曾经拱手瞻礼称赞武则天是真圣人,鲁宗道立刻反对,认为武后几乎要危害到唐朝的社稷天下,是李唐的罪人,太后沉默了许久。鲁宗道还用“夫死从子”来劝说刘后不要逾矩。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宋朝大臣可以说紧紧盯着刘后,赵匡胤所立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使文人有胆量说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时时提醒她不要越轨。仁宗初亲政的前十年,只不过是在朝堂之上陪坐的小皇帝,生活在刘后的阴影之下。刘后的行为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恐慌,生怕武周故事重演。《新唐书》是在刘后去世的十一年后开始编撰的,刘后在这些大臣心里留下的余悸还没有完全消失。《新唐书》中载武则天“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逐嗣帝,改国号,有莫大之罪”。宋祁、欧阳修等人充分发挥了史家的“春秋”笔意,警示来者。
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表达了对女主干政的担忧。司马光编史的目的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编撰时正值曹后、高后掌权时期,这种意识自然而然渗于其中。《资治通鉴》编书的18年(1066-1084年)间,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仁宗无子,传位给侄子赵曙(英宗)。英宗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就大病一场,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他亲政不久于治平四年去世,传位于神宗,时年20岁。神宗即位后,任命王安石推行变法(熙宁变法),受到了以太皇太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反对。因为英宗、神宗非仁宗嫡系,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都有较大的威慑力量。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哲宗继位,因哲宗年幼,高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听政。《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武则天执政时的一些弊端大费笔墨,不无敲山震虎之意。
宋代的执政太后对武则天相当敏感,生怕别人拿自己与武则天相比。高太后垂帘时,左仆射蔡确被贬官期间,曾作绝句十首,被吴处厚抓住把柄,说有五篇涉及讥讽,其中之一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古人不见清风在,叹息思公俯碧湾”(《车盖亭诗》)。郝甑山指郝处俊,曾被封为甑山公,上元三年,唐高宗欲逊位于武后,郝处俊上疏谏阻此事。吴处厚与蔡确不和,言此诗是蔡确以武则天比高太后。当时高太后垂帘,遵循刘后故事,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被人说自己僭越。此诗令高太后大怒,蔡确又难以自圆其说,最后被贬新州。《资治通鉴》写作期间所经历的三位皇帝,都没有摆脱后宫的影响。虽然高后非常欣赏司马光,一掌权就把司马光召回京师,但司马光本人是一个正统的封建士大夫,他不至于因知遇之恩而放弃原则,故对武则天的描写不能排除警示之意。
二、南宋及元:借反对武则天以反对异族
国家分裂及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令士大夫十分重视正统问题。有宋一代,边疆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南宋偏安一隅,丢失的北方一直是封建士大夫的终生耻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恰是这种心态的表达。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文人士大夫特别强调“华夷之变”。南宋陈亮在《酌古论》中说“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南宋文人在诗文中用武则天做文章,借反对异性以反对异族。郑思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郑思肖(1241-1318)生活于宋末元初,宋亡之后改名思肖,“肖”是繁体“趙”的组成部分,即思念赵宋的意思。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都要向南背北。堂扁名为“本穴世界”,“本”字可以拆为“大”和“十”二字,“十”置于“穴”下为“宋”,合为大宋。曾著《大无工十空经》一卷,“空”字去“工”加“十”为宋,即《大宋经》。擅长画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意为宋土已被元人所夺。他曾经为所画菊题为“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临终前嘱咐其友在其牌位上书写“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可见郑思肖的整个人生都沉溺于亡国的痛苦之中。元军南侵时,他曾向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终身遗恨。
郑思肖强调正统观念,不仅否定武则天的帝王地位,甚至连她的皇后地位也一并否定。郑思肖认为正统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黄帝,夏后氏之后;二、必须是天子所封;三、男性统治。在他眼里,只有黄帝及夏后氏的后代才是华夏正统,北朝因与中国抗衡,故北史应黜为“胡史”。南朝虽地处一隅,但是中国一脉所系,故应尊崇为“四朝正史”。隋代杨坚因为是异族,故应黜其国名、年号,直书其姓名及甲子。唐代的统治者本是夷狄,但因为享国久盛,姑且列于中国,但仍不应该以正统对待,如遇到与帝王相关的行为如诏、封禅、郊祀、太庙等事,应直书“某僭行某事”。在提到女性执政时,认为“吕后称制八年,武后称制廿一年,牝鸡之晨,俱恶逆事,书法同前;但仍书曰吕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当以后书之”。[1]吕后、武后因为是妇人,所以连‘僭’和‘逆’都不够资格。“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王莽、曹操为汉臣,逆也;普六茹坚乃夷狄,吕后、武后乃妇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俱僭也,非天明命也。……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1]。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他的正统观又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
元人借反对武则天来表达反对民族统治的愿望。南宋虽丢失山河,但还有立锥之地,元代人则没有这么幸运,所以这种民族感情更加强烈。因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元代人不敢公开叫板,故武则天就成了现成的言说对象。他们认为“妇人不可加于男子如夷狄不可加于中国也”[2],把正统性与民族性问题合为一体。陆文圭(约1256-1340)南宋咸淳年间考中乡试,南宋亡国之后,隐居城东,人称“墙东先生”。元代延祐年间恢复科举,他被强令参加,再中乡举。朝廷多次征召,他都没有应聘。他有一首诗《戏狄怀英》:“花样精神月样妆,妖魂不以近忠良。如何凰阁平章老,欲事宫中妩媚娘”[3]。怀英是狄仁杰的字,狄怀英即狄仁杰。狄仁杰一直都是被当作李氏王朝的中流砥柱来塑造的,但这首诗歌竟然调侃狄仁杰。一个“戏”字体现出作者游戏人生的态度。“妖魂”两字,把武则天视为祸国殃民的妖孽。“凰阁平章老”指狄仁杰,作者还特意使用“宫中”二字,以示与“朝中”之不同。第一句是说武则天这个妖孽主动接近忠良之臣,第二句则是反问,武则天这样也就罢了,为什么像狄仁杰这样的“忠良”,却要为她做事呢?
陆文圭由宋入元,可以说是前朝遗老。国家败亡,进入新朝,新朝又是“异族”。亡于“异族”之手与正常的朝代更替对于士人来讲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当于在“亡国”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亡族”的意味,这种心灵上的打击令他们不堪重负。陆文圭入元以后屡召不应,其原因不言而喻。此时他戏狄怀英,即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加以自嘲,同时表达自己不仕贰朝的决心。由于当时处于元蒙统治之下,人们不敢公开反对,只好采取这种曲折的表达方式来表示这种对抗情绪。
三、宋元文人心态
宋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北宋与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对峙之势,“靖康之变”使宋人体会到了深切的“国耻”和“族耻”;南宋先后与辽国、金国处于胶着状态;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统治华夏。整个这段时期,可以说都是笼罩在民族矛盾之下。北宋初期,封建士大夫从正统性的角度指责武则天“牝鸡司晨”。当民族矛盾激化,受制于现实又不敢公开反对时,武则天成为一个指桑骂槐的靶子,成为人们表达自己观点的万花简。
首先,文人士大夫的正统观念。古人的正统观念特别强是。“中国古代君主集权的皇位继承性表现为帝位的终身制和皇统的世袭制,是把帝位看作皇室家族的私产,父子相传,他姓不容染指,刘邦所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就表明了皇权的不可外移和皇位的不可转移。因此,皇位的继承问题就成为皇帝制度中又一重要内容。……太子是国家的嗣君。”[4]他姓而王是不符合正统的,武则天可以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可以以母亲的身份辅佐幼主,但绝不允许以异姓皇帝的身份继承大统。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5]武则天的行为“名不正,言不顺”,结果将是国家败亡,所以文人士大夫会不遗余力地为国尽忠。
宋代类书收录武则天的类别表达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态度。《册府元龟》“帝王部”是宋代以前关于帝王事迹的分类记载。但所有“帝王”的类别中,没有收录武则天的事迹,即使这件事武则天的确做过,如“封禅”类。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表明自己文治武功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条件举行这样盛大的活动。据司马迁确认,曾在泰山封禅的远古帝王有十二位。秦汉以后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等。唐高宗时曾封禅泰山,武则天于万岁登封元年(695)封禅嵩山。这是历史事实,难以抹杀。但在《册府元龟》“帝王部封禅”类中,高宗封禅之后紧接着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封禅,武则天的行为被遗漏忽略,这决不是马虎,而是有意为之。其它类别也是这种情况。如关于武则天改唐为周的事实在书中没有专门记载,只是在高宗、中宗、睿宗三人的记录中提到。如“帝系”类中,描写中宗时说“太后遂革命称周,凡十五年,复以庐陵王为太子,寻即皇帝位,是为中宗,在位六年”[6]。“继统”类在叙述中宗时提到“天后临朝”。其它类别如“诞圣”、“名讳”、“睦亲”、“文学”、“仁慈”等类中都是按照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的顺序依次排列,没提到武则天。“继统”类记录帝王传袭情况,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类别,应该包括每位帝王,但仍没有武则天的位置。其它非连续性的类别如“好文”、“崇儒术”、“命相”等类中,更看不到武则天的影子。“奇表”类中,写得是帝王具有与众不同的“奇表”,唐代只写了高祖和太宗。如唐太宗四岁时,相者认为他将来必会济世安民。袁天纲给武则天相面的故事流传很广,却没有列入其中。
其次,文人士大夫的性别观念。宋代士大夫把武则天视为“女祸”,横加指责。程颐在解释坤卦时说“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为柔顺,或为文明,或为暗弱;在坤,则为居尊位。阴者臣道也,妇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犹可言也。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废兴,理之常也;以阴居尊位,非常之变也”。[7]与君相比,臣属阴,与男性相比,女属阴,应该居卑位,君主、男性属阳,应居于尊位。人臣如后羿、王莽越居尊位属于大逆不道,但还算可以接受。女性越居尊位,则无法接受。以下犯上是谋反的大罪,但与女子为君相比,男性宁愿接受前者,也不愿意处于女性统治之下。宋代史书收录武则天的类别曲折的反应了文人士大夫的性别观。武则天当女皇帝,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是“错乱阴阳”的行为。武则天“以女、以妻、以阴、以地的命定属性,却打破这样的命定属性,而敢于直取以男、以夫、以阳、以天的命定属性才能占据的地位”[8],对男权文化体系形成强烈冲击。在男性掌握话语的社会,必然要对武则天进行打压。宋代的类书《彤管懿范》由王钦若等人于大中祥符元年诏编,被称之为“女《册府元龟》”。体例应该与《册府元龟》相似,只是记妇人之事。其中,后妃事迹七十卷,其中应该有关于武则天的内容,却没有保存到今天。唯一一部关于女性的类书失传,与男权文化的霸权地位不无关系。
官修实录的失传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唐人所作的《则天实录》早已不存。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写到《唐则天实录》时说“陈氏曰:按《志》魏元忠等撰,刘知几、吴兢删正,今惟题兢撰。武氏罪大恶极,固不应复入唐庙,而题主犹有圣帝之称,至开元中,礼官有言,乃去之。武氏不应有实录,犹正史之不应有本纪,皆沿袭《史》、《汉》吕后例,惟沈既济之论为正,而范氏《唐鉴》用之”。[9]从中可见,《则天实录》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很难保存。《旧唐书》中,《则天皇后本纪》列于《高宗本纪》和《中宗睿宗本纪》之间,与《史记》及《汉书》中把吕后列入本纪中一样,武则天被列为本纪而非后妃列传中。从中可以看出,唐及五代时,史家虽不承认武周王朝,但承认她是唐室帝王谱系中的一个环节,肯定她的执政行为。《新唐书》中,《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与中宗合为一卷,列入《高宗本纪》之后,睿宗与玄宗本纪合卷之前。但在后妃列传中又列入《则天武皇后》,体现了史家的矛盾心理。如果仅把武则天列入后妃列传不符合史实,仅列于帝王本纪类又觉得她不够资格,于是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两部分都列有武则天。《资治通鉴》在帝王纪年中列《则天顺圣皇后》,位于《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与《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之间,承认武则天的帝王身份。这三部史书虽然把武则天放入帝王之列,但没有庙号,仅称谥号,并且以“皇后”的称谓强调她身份的特殊。
再次,文人士大夫的道德观念。武则天的面首是深受人诟病的问题之一。武则天的行为对传统道德观念形成强烈冲击,文人士大夫便抓住武则天的缺点加以放大。由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定位,攻击一个女性最佳的方法就是在私生活上做文章,为了败坏武则天的形象,她的私生活因此受到了高度关注,武则天被描述成扰乱宫闱的淫妇。元代刘将孙《养吾斋集》中的《约略杂诗》中载:“但疑女君羡,皇识武媚娘”,“莲花张六郎,老武八十一。”[10]武氏之祸是唐太宗自己酿成的,屈杀李君羡而留下武媚娘,嘲笑武则天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养面首,“老武”这是称呼是第一次出现,一个“老”字表达出作者的嘲讽意味。《全元散曲》中载薛昂夫的[中吕朝天曲]中有“则天,改元,雌鸟长朝殿。昌宗出入二十年,怀义阴功健。四海淫风,满朝窑变,《关睢》无此篇。弄权,妒贤,却听梁公劝”。[11]对于则天朝的张昌宗、薛怀义等人出入宫禁,以至于淫风弥漫加以批判,对武则天的私生活全面否定。
妻妾杀害主母,是武则天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罪状之一。宋元时期的许多作品描述的是武则天残害王皇后,萧淑妃的故事。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佚名金院本《武则天》,关汉卿的杂剧《武则天肉醉王皇后》(简名《王皇后》)都是这方面题材,后两个剧本已经失传。
元代杨维桢《武后》诗云:“忠良斩刈若刍荛,乳虎苍鹰积满朝。可是唐臣无杜伯,危心只忌六宫猫”。[12]诗中指责武则天残害忠良、任用奸佞、残杀王皇后与萧淑妃。文人士大夫利用这个题材,把武则天写得毒辣无比,把武则天歪曲成一个狠如蛇蝎的恶妇。
武则天故事在宋元时期的流变,早已脱离了故事本身的内容。特殊的现实环境,使武则天成为士人阐扬“华夷之辨”的最佳素材。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文人士大夫的矛盾心态。
[1][宋]郑思肖著.郑思肖集[M].陈福康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32
[2][明]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4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M](第7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4599
[4]李孔怀.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49
[5]张须.通鉴学[M].上海:开明书店,1975:91-92
[6][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C].北京:中华书局,1960:14
[7][宋]程颐,郑汝谐著.伊川易传·易翼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
[8]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51
[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41
[10][元]刘将孙.养吾斋集[M].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别集.文渊阁影印本
[11]隋树森.全元散曲[M].中华书局,1964:703
[12][元]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M](卷第十四).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常熟瞿氏藏明成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