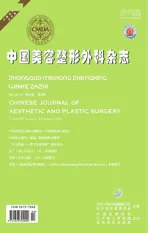隐性唇裂修复术术式回顾
2014-01-21童海洲赵振民
童海洲, 赵振民
综 述
隐性唇裂修复术术式回顾
童海洲, 赵振民
隐性唇裂; 口轮匝肌; 人中嵴
隐性唇裂是先天性单侧唇裂畸形中最轻的一种类型,也称为顿挫型、微小型、先天自愈型或伪匿型唇裂。目前,国内外对于隐性唇裂的概念尚没有完全标准化。1938年,V Veau首次按照单侧唇裂的严重程度,从完全性唇裂到微小型唇裂进行描述,并将第一类称作为隐性唇裂。虽然他也认识到,唇裂同时存在齿槽弓及鼻部的畸形,但描述重点仍放在唇部软组织的缺损上。BF Brown于1964年,SJ Stenstroem和BL Thilander于1965年,共描述了3例存在类似唇裂鼻畸形,却未患有唇裂的患者。1976年,JA Jr Lehman和JS Artz对隐性唇裂的畸形组成作了系统的描述,并提出修复目标应包括重获上唇及鼻部美观和恢复口轮匝肌连续性及功能。同年,FR Heckler等注意到,上唇上部垂直沟痕处皱缩可能是口轮匝肌纤维错乱的表现。1982年,T Onizuka等根据形态学特征,对唇腭裂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并将其中的第一、二类定义为为隐性唇裂。1986年,R Ranta对患有唇腭裂畸形儿童的牙齿发育形成进行了研究,将齿槽弓及切牙的微小畸形称为隐性唇裂的一种。Kim等[1]建议将鼻畸形、自红唇缘到鼻底的沟痕和红唇与表皮交界处白线中断,3种畸形作为隐性唇裂必须的诊断特征。Weinberg和Brandon[2]通过对单纯腭裂患者的上唇进行超声检查,发现部分患者存在着上唇口轮匝肌连续性的中断,并从病因学上对唇腭裂的发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指出,口轮匝肌连续性应当作为隐性唇裂最基本的解剖特征。无论对隐性唇裂如何划分,目前人们对于单侧隐性唇裂的畸形特点描述,可总结为以下7点:①黏膜边缘凹陷;②内侧红唇组织偏薄;③内侧唇峰上移;④人中嵴处浅的沟痕;⑤口轮匝肌连续性中断;⑥微小鼻部畸形;⑦侧切牙处骨质缺失。然而,并不是每一个隐性唇裂患儿都存在以上全部畸形。隐性唇裂修复术的目的,是消除红唇部的凹陷,对齐唇弓,矫正鼻翼塌陷,在瘢痕最小化的前提下,恢复口轮匝肌连续性和再造人中嵴[3-4]。现笔者就隐性唇裂修复术术式综述如下。
1 早期传统开放性手术
1938年,V Veau采用Rose-Thompson法将裂隙处皮肤去掉,对齐红唇及黏膜高度后,直线缝合切口,修复一种所谓“simple”的单侧唇裂。1979年,RL Harding采用改良的Rose-Thompson法,将外侧小三角瓣插入近中侧红唇与皮肤交界处斜行松弛切口来修复。1964年,RH Musgrave对2例患者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1例采取Rose-Thompson的直线法,使用梭形切口及黏膜处Z字改形;1例则采取旋转推进法,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梭形切口设计,一直沿用至今[5]。1962年,AB LeMesurier采取矩形瓣修复所谓的轻度红唇凹陷。改良的Tension三角瓣法,也被应用于隐性唇裂[6]。我国整形外科医师宋儒耀也采取鼻小柱侧面皮瓣法来修复单侧隐性唇裂[7]。实际上,大部分的医师都推崇Millard提出的方法来修复隐性唇裂,即采取上唇部开放性手术,利用旋转-推进原理进行修复[8]。1985年,HG Thompson和W Delpero通过对旋转推进和下三角瓣法进行对比发现,二者术后效果无明显差异。虽然以上修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畸形,但仍停留在修复单侧完全性唇裂的术式上,且多采取上唇开放性切口,明显的手术切口瘢痕可能会使术后外观较术前更差,从而极大地影响手术效果。
2 向皮内入路手术过渡阶段
由于隐性唇裂本身为唇裂畸形中最轻微的一种,而开放式的手术往往会造成更加难看的手术瘢痕。因此,越来越多的整形医师开始追求在瘢痕最小化的前提下修复畸形。
实际临床中,隐性唇裂患者通常只存在其中一种或几种畸形,故修复手术需要根据患者实际存在的畸形情况而采取单一或联合方案。Akita等通过对传统直线切口下三角瓣法与鼻底及红唇处Z形切口(类似于Onizuka方法)两种术式进行对比发现,虽然最后手术效果可以接受,但前者会遗留明显的上唇术后瘢痕,后者鼻孔不对称则更加突出[9]。
1995年,TH Buyn和KI Uhm将隐性唇裂分为3类:Ⅰ类,仅有轻度鼻畸形或上唇过短;Ⅱ类,轻度上唇畸形伴唇峰模糊、红唇凹陷及皮肤浅沟痕;Ⅲ类,轻度上唇畸形伴唇峰交错偏离。并根据其分类,分别提出了修复方法:Ⅰ类采取Z改形术来缩窄鼻孔及丰满鼻底;Ⅱ类采取小三角瓣矫正唇峰畸形;Ⅲ类采用改良的Onizuka法修复。同时亦可以利用填充物,如远位的筋膜组织、皮下脂肪或人工真皮组织等来填充凹陷的人中,以再造人中嵴,但它们都存在被吸收的可能。吕金陵[10]是较早在国内开展隐性唇裂皮下修复术的,其做法是在皮下将口轮匝肌从异常附着处分离并恢复连续性,同时重建鼻翼软骨。
显然,这一阶段的手术方式虽然具有瘢痕较小的优点,但对畸形修复观念,仍停留在畸形的表面,而对畸形的本质问题并没有解决。隐性唇裂虽然不如完全性唇裂那样有着严重组织缺损及移位,但仍存在口轮匝肌连续性的破坏和鼻翼软骨的移位。因此,想要获得满意且持久的手术效果,就必须从解剖学上入手,恢复口轮匝肌的连续性和重建人中嵴,并将鼻翼软骨复位。
3 多元化、个性化修复阶段
随着对口轮匝肌及人中嵴解剖结构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解剖学要素在隐性唇裂修复术中的重要性。口轮匝肌在唇部动静态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1968年,M Fara曾描述,即使是最微小的唇裂,都存在着肌肉的断裂,其外在的畸形是由于口轮匝肌的非连续性造成的。组织切片观察发现,人中沟痕处主要为胶原纤维的渗入,仅伴有少量散在的肌纤维。Neiswanger等[11]提出,交错的口轮匝肌中断,应该作为不完全性唇裂的一个表型。Kim等[1]发现,隐性唇裂肌肉超微结构的损害,与完全唇裂一样。1962年,IW Monie和A Cacciatore通过观察胚胎唇部切片,认为人中是由结蹄组织聚集而成,皮肤与口轮匝肌之间的结缔组织在人中窝处较人中嵴处密集。而1976年,RA Latham和TG Deaton通过对人中嵴的解剖研究发现,口轮匝肌的浅层来源于面部表情肌,并可分为上束(鼻束)和下束(鼻唇束)。其下束又可分为长短纤维,短纤维止于同侧皮肤,形成人中嵴,而长纤维在中线交叉后,止于对侧人中嵴。1981年,J Briedis和IT Jackson也证实,浅层肌肉相互交错并插入真皮层,而深层纤维跨越中线相互连续,并认为真皮内的胶原是构成人中结构的要素。与之前研究相反的是,Namnoum等[12]通过对3个月胎儿的上唇组织切片进行观察发现,人中嵴是由增厚的真皮和真皮下组织构成,并且注意到,有上唇提肌纤维从侧方插入。因此,口轮匝肌的功能重建及人中嵴解剖结构复原,在隐性唇裂修复过程中最为关键[3-4,9,13]。与此同时,各种唇裂术后继发唇鼻畸形的修复术也被引入到隐性唇裂的修复中,使隐性唇裂修复术式变得多样化,手术切口也开始向口腔黏膜侧转变。
Cho[14]通过对口轮匝肌及人中嵴解剖结构的深刻理解,提出了经口内切口行口轮匝肌垂直交错缝合来修复隐性唇裂。他在皮肤浅沟正对的口腔黏膜侧做垂直切口,将口轮匝肌显露,并劈开分成两瓣,外侧上叶肌肉瓣固定缝合于人中窝处真皮下,然后将内侧上叶肌瓣放在其下,下方肌肉垂直交错缝合,以此来增加人中嵴厚度及恢复口轮匝肌的连续性,且同时矫正了鼻底部塌陷。对于鼻畸形修复,则采取改良的鼻翼缘倒“U”形切口及末端“V”形回切[15],同时红唇部畸形则采取局部“Z”改形矫正。但在长期随访过程中发现,该法存在着以下问题:①幼儿口轮匝肌过于薄弱,无法劈开形成上下两叶肌肉瓣;②肌肉瓣的交错缝合导致红唇缘膨隆,影响美观;③再造人中厚度降低且形态圆钝。
Mulliken[3]提出采取两个单臂的Z改形术来修复隐性唇裂。在患侧红唇凹陷处设计两个单臂Z改形合并上唇部垂直切口,以去掉上唇部无毛发的皮肤,并达到矫正红唇凹陷及下降唇峰的目的。同时经过切口行皮下口轮匝肌分离,纵行剖开后,两端行垂直褥式缝合,并取耳后真皮组织置于肌肉缝合线上,恢复口轮匝肌连续性并丰满人中。另外,视鼻翼基底外移的程度,可分别设计鼻底梭形切口,配合肌肉悬吊,或行Y-V推进并向鼻腔内旋转,以修复鼻畸形。与Cho不同的是,Mulliken在对隐性唇裂人中嵴再造时,同时强调肌肉与真皮。虽然真皮组织有被吸收的可能,但可以等患儿成长后,再次行真皮组织移植修复术。Yuzuriha和Mulliken[4]将单侧不完全性唇裂,按照其畸形程度分为Minor-Form、Microform和Mini-Microform,其分类依据是双侧唇峰至鼻小柱底部中点的高度差。高度差大于3 mm,则为Minor-From;小于3 mm,则为Microform;若双侧唇峰位于同一平面,则为Mini-Microform。并根据分类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①Minor-Form cleft lip。作者认为,垂直切口联合下方单臂Z改形术下降唇峰的极限为3 mm,若大于3 mm,则上方的切口必然延伸,那么遗留的切口则类似于三角瓣法。因此,采取标准的旋转-推进法联合红唇部单臂Z改形术,但切口及手术范围可适当减小。国内学者成铤等[16]也认为,对于隐性唇裂白唇隐裂切迹部位的表面组织类似于黏膜,并且患侧唇高度较健侧短的患者,适合采用改进的Millard-Ⅱ式法;②Microform cleft lip。由于双侧高度差小于3 mm,采取两个单臂的Z改形术即可矫正,并使用真皮组织移植再造人中;③Mini-Microform cleft lip。这类患儿往往红唇部畸形较轻,采用梭行切口垂直关闭即可。对于鼻畸形相对明显患儿,采用鼻底部梭行切口或“Y-V”推进法修复鼻畸形。而关于口轮匝肌重建,则待患儿长大后,确认有人中处沟槽之后再行手术修复。通过以上分类及术式划分,对隐性唇裂的个性化修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Desrosiers等[17]重点强调了口轮匝肌重建在隐性唇裂畸形修复中的重要性。他将Seagle和Furlow[18]、Mulliken[3]和Cutting[19]提出的方法进行改良,通过红唇部的Z形切口,在皮下分离口轮匝肌,同时行闭合性的鼻翼软骨的分离及鼻翼基底复位,并按Furlow所描述的方法,行口轮匝肌交错缝合,再造人中嵴并丰满红唇缘。此法综合了各家之长,术后口轮匝肌功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但其关于人中嵴再造的理念及术后长期效果,则有待观察。近两年,国内的学者们也开始将隐性唇裂修复的重点转移到口轮匝肌功能重建及人中嵴再造上来,并结合他们所设计的唇部辅助切口,一次性实现恢复口轮匝肌连续性、人中再造及鼻畸形矫正,并获得了良好效果,值得借鉴[20-21]。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前唇部的切口设计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李盛等[22]曾对唇裂形态进行研究,提出了上唇“W”形态理论,并遵循该理论进行切口设计,以矫正唇峰上移和中线偏离畸形,恢复“W”形态。之后,刘强等[23]借鉴了Mulliken的经验,为了尽可能保留未受累的皮肤,分别采用局部Rose法切口和倒“V”形切口附加皮肤小三角瓣切口进行修复。与Mulliken法不同的是,其松弛切口不是沿着裂隙近中侧唇红缘切开,而是尽可能偏向唇红缘,这样既可以隐蔽三角瓣下边线切口,又可防止误将唇红缘切断。另外,皮肤三角瓣的高度设计为两侧唇峰高度差值的2/3,不足部分由倒“V”字切口对位缝合后补足,这样可以避免因三角瓣的插入而导致裂隙侧唇峰过低的缺点。Chen等[24]的切口设计与Koh相类似,根据旋转-推进原则,将传统裂隙侧唇峰3、9点向内侧移位,在裂隙两侧做曲线切口,并认为此法可以更好地下降唇峰,减少附加切口瘢痕,获得对称唇弓形态。Oyama等[25]着重强调了患侧唇峰点定位及其在唇弓形态恢复中的重要性,并将Koh与Mulliken在唇峰处切口的设计进行完美的融合,从而获得更佳的唇弓形态,但同时,上唇部皮肤的切开,势必也遗留了瘢痕。
综上所述,隐性唇裂的手术切口从早期的上唇开放性切口,转向红唇部及口腔黏膜侧切口,消除了上唇手术瘢痕对美观的影响。通过口腔侧切口在皮下行口轮匝肌分离,重建口轮匝肌功能,模拟人中嵴解剖结构再造人中,已成为隐性唇裂修复手术的重点。同时,多种唇裂继发唇鼻畸形的手术方式应用于隐性唇裂红唇部及鼻部畸形矫正,使得修复手段变得多样化、个性化。以上所提及到的各种修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良好的术后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有关隐性唇裂的概念仍停留在形态学表现上,是否需要从组织病理及解剖学特征上再次进行标准化,为实际手术方法的选择提供更确切的理论依据;其次,在口轮匝肌修复及人中嵴再造上,Onizuka通过中间肌肉瓣填充再造人中,显然不符合正常解剖。Cho和Desrosiers通过对人中嵴解剖结构的理解,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修复方法,且获得了满意效果。但在患儿菲薄的肌肉上实际操作较为困难,只有经验丰富的医师才能把握住分寸,再造出理想的人中嵴轮廓。另外,考虑到上唇运动可导致局部肌肉体积减小,故人中嵴维持还有待观察。至于Mulliken提出的用组织移植的方法来重建人中,存在着组织吸收的问题。有关鼻畸形修复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赞同在同期进行鼻翼软骨的分离和复位。另外,对于一些亚解剖单位,如鼻槛、唇珠、唇峰等结构的精细修复,也值得关注。目前,关于隐性唇裂修复术式呈多样化发展,尚无统一标准,具体采取何种术式,则需要根据患儿的实际畸形程度及术者经验综合考虑后决定。正如AO Whipple所说的,“Fit the operation to the patient and not the patient to the operation”。
[1] Kim EK, Khang SK, Lee TJ,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microform cleft lip and the ultra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bicularis oris muscle[J]. Cleft Palate Craniofac J, 2010,47(3):297-302.
[2] Weinberg SM, Brandon CA. Rethinking isolated cleft palate:evidence of occult lip defects in a subset of cases[J]. Am J Med Genet A, 2008,146A(13):1670-1675.
[3] Mulliken JB. Double unilimb Z-plastic repair of microform cleft lip[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5,116(6):1623-32.
[4] Yuzuriha S, Mulliken JB. Minor-form, Microform, and Mini-Microform cleft lip: anatomical features, operative techniques, and revisions[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8,122(5):1485-1493.
[5] Carstens MH. The spectrum of minimal clefting:process-oriented cleft manag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an intact alveolus[J]. J Craniofac Surg, 2000,11(3):270-274.
[6] Wang MK. A modified LeMesurier-Tension technique in unilateral cleft lip repair[J]. Plast Reconstr Surg Transplant Bull, 1960,26(2):190-198.
[7] 宋儒耀, 柳春明. 唇裂与腭裂的修复[M]. 4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189-195.
[8] Millard DR. Cleft craft:the evolution of its surgery[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7:23-25;303-304.
[9] Akita S, Hiraro A. Surgical modifications for microform cleft lip repairs[J]. J Craniofac Surg, 2005,16(6):1106-1110.
[10] 吕金陵. 隐性唇裂皮下整复术[J]. 中华医学美容杂志, 1997,3(3):134-136.
[11] Neiswanger K, Weinberg SM, Rogers CR, et al. Orbicularisoris muscle defects as an expanded phenotypic feature in nonsyndromic cleft lip with or without cleft palate[J]. Am J Med Genet A, 2007,143A(11):1143-1149.
[12] Namnoum JD, Hisley KC, Graepel S, et al.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fetal philtrum[J]. Ann Plast Surg, 1997,38(3):202-208.
[13] Tosun Z, Hosnuter M, Senturk S,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microform cleft lip[J]. Scand J Plast Reconstr Surg Hand Surg, 2003,37(4):232-235.
[14] Cho BC. Newtechinique for correction of the microform cleft lip using vertical interdigitation of the orbicularis oris muscle through the intraoral incision[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4,114(5):1032-1041.
[15] Cho BC, Baik BS. Correction of cleft lip nasal deformity in Orientals using a refined reverse-U incision and V-Y plasty[J]. Br J Plast Surg, 2001,54(7):588-596.
[16] 成 铤, 刘 坤, 赵 敏, 等. 用改进的Millard Ⅱ式法修复隐性唇裂10例[J]. 中国美容医学, 2006,15(5):557-558.
[17] Desrosiers AE 3rd, Kawamoto HK, Katchikian HV, et al. Microform cleft lip repair with intraoral muscle interdigitation[J]. Ann Plast Surg, 2009,62(6):640-644.
[18] Seagle MB, Furlow LT Jr. Muscle reconstruction in cleft lip repair[J]. Plast Reconstr Surg, 2004,113(6):1537-1547.
[19] Cutting CB. Secondary cleft lip nasal reconstruction:state of the art[J]. Cleft Palate Craniofac J, 2000,37(6):538-541.
[20] 金邵华, 李一民, 吕 洁, 等. 单侧隐性唇裂整复方法的研究[J]. 口腔医学研究, 2010,26(2):291-292.
[21] 孙秀英, 李家锋, 韩建国, 等. 口内入路法功能性修复唇隐裂[J]. 中国美容医学, 2012,21(13):1745-1747.
[22] 李 盛, 石 冰, 郑 谦, 等. 微小型唇裂整复方法的探讨[J].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2006,22(3):193-195.
[23] 刘 强, 李增健, 郭永峰, 等. 单侧微小唇裂的个性化修复术[J].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2008,19(4):246-249.
[24] Chen J, Shen W, Jie C. Mild incomplete cleft lip repair[J]. J Craniofac Surg, 2012,23(4):1131-1132.
[25] Oyama A, Funayama E, Furukawa H, et al. Minor-Form/Microform cleft lip repair: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fi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pid bow peak on the lateral lip[J]. Ann Plast Surg, 2014,72(1):47-49.
2014-11-19)
100144 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整形一科
童海洲(1989-),男,湖北咸宁人,医师,硕士研究生.
赵振民,100144,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整形一科,电子信箱:zhaozhenmin0098@vip.sina.com
10.3969/j.issn.1673-7040.2014.0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