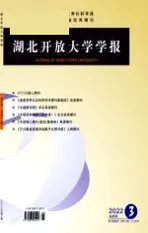从《大双心河》看海明威生态观的矛盾性
2013-08-15杨丽
杨 丽
(新乡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0)
《大双心河》是海明威著名的带有半自传性质的短篇故事。文中没有悬念十足,扣人心弦的曲折情节,只是以平淡的语调讲述了主人公在大二心河河畔宿营及垂钓的过程。小说中亦没有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的人物角色,尼克是故事中唯一的人物。尼克在战场中饱受创伤,试图皈依自然,在与自然的融合中找到慰藉,他沉醉在宁静迷人的自然美景中并逐渐找回了曾经的活力。然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并不是文中的主旋律,尼克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主宰自然的欲望。其实书中的尼克即是海明威的写照。他对自然时而依恋时而控制的态度折射出了作者生态观的矛盾性。
一、皈依自然的生态情怀
美国自然作家特里.威廉斯曾说:“海明威提醒我们注意,我们不是自然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的热爱者”(戴桂玉,2009)。海明威的成长经历和自然密切相关,作品中也洋溢中浓厚的绿色气息。海明威对自然的依恋和热爱在《大双心河》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尼克在战争中心灵和身体备受摧残,于是想要远离世事纷扰,回到少年时代常去的钓鱼之地大双心河去寻找精神的慰藉。大双心河是一片自然的净土,尼克在河边的宿营垂钓之行就是一段与自然亲密交融,在自然中寻找寄托的回归之旅。
小说以尼克从战场归来,乘坐火车回到塞内镇而开篇,尼克渴望看到家乡的青山碧水以抚慰受伤的身心。而出乎意料的是映入眼前的是一片破败不堪,萧瑟冷清的景象:“这里已没有镇子,什么也没有,只有铁轨和被火烧过的土地。沿着塞内阵唯一的街道曾有十三家酒馆,现在已经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广厦旅馆的屋基撅出在地面上。基石被火烧得破碎迸裂了。塞内镇就剩下这些了。连土地的表层也给烧毁了。”(陈良廷,2011)寥寥数语即表达了作者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无奈和惋惜之情。失望万分的尼克顺着铁轨继续走,所幸的是河还在那里,他感到一丝安慰,心里的阴霾也随之淡化了,那涌动的河水,跳跃的鳟鱼和飞翔的翠鸟成了他眼中一道道亮丽的景色。自然原始宁静的美景让尼克逐渐地恢复了活力,他顺着大路往前走,尽管山路弯曲,背包沉重,可他依然心情愉快。到达山顶时,尼克极目远眺,那一望无际的平原,潺潺流动的河水,若隐若现的青山,茂密黝黑的松林组成了一幅妙不可言的美丽画卷。
当尼克走下山坡时,他踩着沙地,穿过田野,闻着香蕨木的飘香,伴着簇簇短叶松,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唤起了他的激情,也使他受创压抑的身心完全复苏,他感到心旷神怡,四下都是一片生气了。此时的尼克感受着大自然的活力,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带来的这份难得清静和安宁。到了晚上天黑时,尼克支起了帐篷,“在帐篷里,天光通过棕色帆布渗透进来。有一股好闻的帆布气味。已经带有一些神秘而像家的气氛了。尼克爬进帐篷时,心里很快活。”(陈良廷,2011)尼克独自在荒野中,忘记了尘世的喧嚣和梦魇般的苦痛,他在和自然的亲密融合中找到了家的感觉,于他而言,自然就是他的精神家园。海明威认为“荒野具有某种“正确的”东西,某种我们未尝得到东西。在荒野,我们能找到慰藉”。(戴桂玉,2009)尼克对自然的皈依也反映出了海明威对自然的眷恋。
尼克不仅沉浸在充满生机而又和谐宁静的自然美景中,对非人类生命也充满着同情和关爱之心。生态批评认为偌大的自然界其实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万物皆兄弟。法国伦理学家施韦兹提出了著名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他认为生命没有等级贵贱之分,自然界里所有的生命有机体都是平等的,值得敬重的,人类与其他所有创造物亲如一家。尼克的身上即体现了海明威的生态伦理思想,把道德关怀扩大到每一个物种。当看到一只蚱蜢颜色都已变成黑色时,他立刻“认识到它们是因为生活在这片被烧遍的土地上才全都变成黑色的”(陈良廷,2011)他不禁小心地伸下手去抓住蚱蜢的翅膀并仔细打量它,然后尼克说出了他自来到大双心河的第一句话:“继续飞吧,蚱蜢”,“飞到别处去吧。”(陈良廷,2011)尼克在蚱蜢这个弱小的动物面前没有人类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是对其充满理解和怜爱,并给予它去寻找更好的家园的自由,彰显了其对非人类生命的尊重。文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尼克钓到了一条鳟鱼,他特意弄湿了手才去摸它。因为“如果用干手去摸鳟鱼,那摊被弄掉黏液的地方就会被一种白色真菌所感染”( 陈良廷,2011)多年前曾亲眼目睹被白色真菌致死的鳟鱼的惨状在他心中依然记忆犹新,所以当他身临其境时,他用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显示了对生命的尊重。
二、驾驭自然的强者情结
海明威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生态的热爱和关注,但与此同时,他对自然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冲突对立,他既热爱赞美,又乐于征服控制。著名学者安.普特南曾指出:“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总是呈现出一种自我分裂的趋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田园冲动总是与征服自然的悲剧性冲动相冲突。”(黄兰,2009)
尼克与自然交融的乐趣并未贯穿整个垂钓过程,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流露出了征服自然的悲剧情结。对尼克来说,自然是“某种必须被征服,被控制的东西;它不是根据它自己而是根据尼克的需要来定义的”(戴桂玉,2009)。尼克初次看到蚱蜢时,想到自己和蚱蜢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把蚱蜢引为同类,倍加爱惜,然而当他钓鱼需要用蚱蜢做钓饵时,曾经对蚱蜢的怜爱和尊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触目惊心的残忍:“尼克一把抓住它的头,捏着它,把细钓钩穿过它的下巴,一直刺透咽喉直到它肚子最下部的那几个环节。蚱蜢用前脚攥住了钓钩,朝它吐烟油般的唾液。”(陈良廷,2011)此时的蚱蜢在尼克的眼中不过是一个任他恣意蹂躏的诱饵。尼克对蚱蜢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完全决定于自身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了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于尼克而言,大自然不仅是心灵的栖息地,更是一个必须被征服的对象。他放走了已捕获的小鳟鱼,是因为他觉得对手太弱小,没有强烈的挑战性和征服感。他需要更强劲的对手来证明个人的价值,于是他继续寻找可以和他抗衡的猎物,当一条大的鳟鱼出现时,尼克表现得很兴奋,他和大鳟鱼反复搏斗体验着征服的紧张刺激,最终由于钩绳突然断裂大鳟鱼乘机溜走了,尼克感到非常失望,但内心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并没有减弱,他继续前行寻找深水潭。当河道愈来愈窄,河水愈加汹涌时,他深知在沼地里钓鱼是一桩冒险行动,但对自然的征服意念又让他不愿意就此停下,一番心理的纠结挣扎过后,他决定不沿着下游继续前行了,可内心的不甘使他一次次地回头望,并想着以后还有机会来这里继续钓鱼。尼克决定中止前行并不是停止了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而是把念想留给了以后。
三、结语
尼克从战场归来直奔大双心河,他欲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在整个露营垂钓行程中,他突出自然生态,淡化人类个体,尊重非人类生命,然而与此同时又企图通过征服自然来证明个人的强大。尼克对自然的双重态度反映了海明威生态观的矛盾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1]海明威. 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M]. 陈良廷,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戴桂玉. 后现代语境下海明威的生态观和性属观[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黄兰. 海明威生态意识中的悖论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