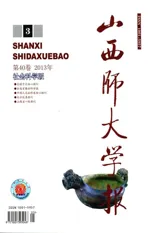论戏剧家曹禺的主体建构与文体选择
2013-04-11王俊虎
王 俊 虎
(延安大学 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主体是指具有思维能力并运用一定物质和精神手段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人,从这个意义来说,曹禺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是偏重于用精神手段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在这一认识和改造过程中,就存在着主体自身建构的问题和方法。当然这一建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和主体认识的不断加深,随时调整和改变方向,以使主体更有效地对外在世界提供符合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曹禺作为现代文化人和作家,“固然都有一生的本性难移意义上的‘自我’,但也都有一个自我发展变化的‘变量’,体现着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这种‘变量’可以在知识结构方面展开,也可以在人格结构方面展开,或者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为‘世界观’方面的发展变化”[1]174。的确,对于任何一个鲜活的社会人来说,主体建构都是一个复杂流动的变化过程。虽然来自母体的基因遗传深刻烙印于每一次主体的重建序列当中,但流动于社会和生活中的“变量”常常会打破固有秩序,促使主体奔向新的建构序列和目标。对于精神世界缤纷五彩、情感生活细腻复杂的文人作家们来说,主体的建构往往在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发展过程后,才会逐渐成熟和趋于稳定。
出身于富贵家庭的曹禺,童年的物质生活极为丰裕,但他精神世界并不愉悦。父亲万德尊脾气暴躁,后来由于官场失意、郁郁不得志,更是性格乖戾,有精神时对家人和仆人大发雷霆,没精神时靠吸食鸦片麻醉神经。曹禺后来回忆童年的家庭生活氛围像坟墓一样阴森沉寂,父亲万德尊生气的时候曾将自己的长子万家修的腿打断,给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幼年曹禺养成了胆怯怕事的性格特征。万德尊对这个表面怯懦但却喜欢读书的孩子珍爱有加,把光宗耀祖的重任寄托在这个神态忧郁但不失机巧聪慧的小儿子身上,他虽然留学海外,但并不主张曹禺过早地进入洋学堂,而是在家开设私塾,聘请国学功底较深的塾师给曹禺讲经论典,《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诗经》、《左传》、《史记》虽然枯燥无味,但是家庭教育培养了曹禺浓厚的文学兴趣,也奠定了他较深的国学根底。继母薛咏南嗜爱戏曲,曹禺才三岁的时候就在她怀中开始接受戏剧教育启蒙,京剧、河北梆子、昆曲,以及各种曲艺,曹禺小时候都欣赏过,有时看戏回来,曹禺竟然和小朋友们模仿戏剧名角演戏。生活条件的优越,使得曹禺在幼年不会为生计担忧,自然也不会过早萌生比较务实的人生理想,而是全凭兴趣来生活学习。
1922年,年仅12岁的曹禺报考了著名的南开中学,开始了他人生历程中最具纪念意义的一段求学生涯。进入中学后不久,曹禺便迷恋上了新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学主将的文学作品他都认真习读,他后来回忆说:“我13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还有后来收入《彷徨》的《祝福》就给我以深深地感染。……读《阿Q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却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人民。”“《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或者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2]23因此,承受五四新文学熏陶的少年曹禺迷上了新文学,开始了他人生历程的第一次人生建构,他决心做一名“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呼唤自由”的文学家,至于选择哪种文体作为创作的主阵地,曹禺并没有确定的目标。1925年3月,曹禺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1926年,曹禺和同学创办了《玄背》的文学副刊,表达同学们对郁达夫的共同崇拜。据田本相考证,以戏剧名世的大戏剧家曹禺的第一篇创作并不是戏剧,而是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发表于1926年9月出版的《玄背》第6—10期上,并第一次署名“曹禺”。小说创作之余,曹禺还涉猎了杂感、诗歌等文体,他在《杂感》短序中写道:“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的造出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3]他在《偶像孔子》中还大胆断言:“在偶像势力的积威下,常产生一种积极相反的潜势力;待时机一至,便爆发成为火山的裂罅,经历了千年的偶像,立刻陷堕其中,焚成灰烬。”[4]文章中的这些话语,既是对文学家挑战习俗勇气的积极肯定,也是对自己后来文学创作中激扬的强烈叛逆情感的夫子自道。从性格来说,曹禺不是坚强之人,曹禺家人在多次场合毫不隐讳地提到他的怯懦,但曹禺文学作品中洋溢着的决绝反抗精神却是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的,这可能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缘故吧?曹禺童年受到家长威严的管制,在温顺听话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几乎同一时期,曹禺迷恋上了新诗,1926年10月发表于《玄背》第13期上的两首诗《林中》和《“菊”、“酒”、“西风”》洋溢着忧伤的调子。1928年上半年,曹禺先后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不久长》等诗歌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苦苦思索,是时代苦闷和精神抑郁在文学世界中的爆发和排遣。
可见,以小说、杂感、诗歌创作开始自己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生涯,证明曹禺第一次人生主体建构绝非明确把自己定位为戏剧作家。从文体学角度来看,小说与杂感这两类文体与曹禺的个性气质、思维特征并不十分契合。小说这种文体需要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理智冷静的思维,而就曹禺个人来说,富家少爷的生活大大限制了他与社会的交往和互动,段妈告诉曹禺穷苦人的生活片断是无法与生活在大杂院和胡同中的同时代作家老舍相比拟的,曹禺从家庭、私塾再到学校,一切是那样自然、平稳,根本不存在为读书发愁的那种担忧和惧怕。从个性气质上来说,曹禺偏于激情冲动,这种个性气质并不利于小说叙事,因为激情和冲动容易激起写作杂感的动机和愿望,但杂感这种文体需要透彻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这对感性极强的曹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再说要成为大作家,很少有人以杂感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阵地。就诗歌的文体来说,与曹禺的个性气质倒是十分契合,他自幼忧郁孤寂、沉思冥想,具有诗人的气质和风范,但是曹禺最终并没有选择诗歌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阵地,而是选择了话剧,不过在他后来的戏剧创作生涯中,不难看出曹禺戏剧创作的诗化倾向。
曹禺之所以最终选择话剧作为自己文学创作主阵地,开始自己人生最为重要的第二次主体建构,有这样一些原因:其一,对戏剧有着浓烈的兴趣。受继母影响,曹禺童年就喜欢看戏并模仿演员演戏,进入南开中学以后,浓烈的演剧校园文化深深吸引了曹禺,在戏剧家张彭春的栽培和器重下,曹禺独自担纲扮演话剧主角,受到同学和观众的好评,极大地刺激了曹禺对话剧的关注和喜爱。其二,话剧1907年正式传入中国,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话剧界出现了各种戏剧社团和刊物。关于戏剧问题的理论探讨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但真正成熟的话剧剧本并不多或者根本没有出现,因此从事话剧创作既是挑战也是奠基。而话剧在中国电影业刚刚起步、尚未普遍流行时期,无论对观众还是作者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纯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的活跃分子,不同于家境贫困孩子求学时期的务实观点,他有条件也有能力把精力投注到话剧这一颇为时尚的文艺形式上面,大量老舍式的穷孩子们固然也有文学才能,但是他们为了以后的生计,不得不看重学业成绩,压抑自己其他方面的爱好。其三,话剧是舶来品,真正的话剧精神来自于欧洲,曹禺的父亲虽然早年留学日本,但是日本流行的西方文化气息自然会被万德尊带回,给曹禺提供了潜移默化的西学家庭背景,使他能够在艺术气质上与话剧这种高雅艺术相契合。其四,曹禺初涉文坛,尝试写作小说、杂感、诗歌等文体,均未获得令人满意的文学效应,这些作品仅发表于《玄背》、《南中周刊》、《南开双周》等自办刊物或者校刊,与其他现代作家初尝小说便发表于国内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等相比,自然打击了曹禺从事小说创作的积极性,而话剧舞台演出的极大成功吸引曹禺把文学眼光投向有待开垦的中国话剧园地,处女作《雷雨》发表后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轰动效应强有力地证明了曹禺的正确抉择。
现在很难推断曹禺将自己定位为话剧作家,开始自己人生第二次主体建构的具体时间,但是可以肯定并不是写作《雷雨》的1933年,而应该在此之前,即《雷雨》的构思时期。曹禺后来说:“《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5]南开中学后期,曹禺先后成功扮演易卜生话剧名作《国民公敌》中的裴特拉、《娜拉》中的娜拉,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曹禺的同学鲁韧后来回忆说:“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影响很大。……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到现在,这样好的艺术境界、艺术效果是很难找到的。”[2]32当时的南中校刊对演出盛况也作了报道:“新剧团公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观客极众,几无插足之地。”“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2]32这两次话剧演出使万家宝名声大振,同学们都亲昵地称他为“咱们的家宝”,曹禺被誉为“南开五虎”之一。南开成功的演剧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声誉和影响无疑激起血气方刚的青年曹禺对话剧的由衷热爱。1929年南开校庆,张彭春邀请曹禺合作改编英国戏剧家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曹禺初涉话剧创作,为以后的《雷雨》创作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尽管曹禺在1928年南开中学毕业之时,已经对戏剧发生浓烈的兴趣,但是他却阴差阳错、令人费解地报考协和医学院,因数理化成绩差没有被录取,后来又转报南开大学政治系并被录取。医学和政治学专业与戏剧文学相差甚远,曹禺对之应该说均无兴趣,那么何以有如此选择?只有一个原因,来自父亲的威压!官场失意的万德尊把光宗耀祖的重任一直压在万家宝身上,名为军人实为文人的万德尊并不想让儿子再做自己那样的无聊文人,而是首先考虑能够振兴家业的实用专业——医学,根本没有考虑孩子的兴趣和特长,以至于曹禺落榜,退而求其次又强令其选择报考南开大学政治系,对于文学艺术之类的专业是根本不予考虑的。进入南开大学的曹禺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毫无兴趣,备感厌恶和无聊。恰在此时,曹禺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1929年大年三十,从南开大学回家探亲的曹禺陪父亲洗澡理发途中,父亲突发急症、暴病而亡。父亲死后,曹禺尽管悲痛万分,饱尝世态炎凉,但终于迎来自由,摆脱束缚,像奋飞的鸟儿终于能够展开翅膀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奋斗,他冒着巨大的学业风险(考不上也不回南开)向南开大学提出报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终获成功。
进入清华园的青年曹禺如饥似渴地攻读西方戏剧文学理论与经典名著,厚积薄发,终于在23岁的时候,以话剧《雷雨》一鸣惊人,完成了中国话剧最终成熟的这一重大文学转折。曹禺话剧融合中西文化精髓,远离阶级斗争和革命尘嚣,始终追问人生困境,关怀疗救人性弱点,远远超越了一般的社会问题剧,主题意蕴辽远深奥,汲取西方话剧结构特长但却能扎根民族土壤之上,深受中国和异国读者或观众的喜爱。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原野》和《北京人》,曹禺话剧几乎篇篇创新、部部精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剧坛最高峰的历史地位。而正当曹禺话剧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肆侵略中国,国内矛盾急剧变化,曹禺和大多数现代作家一样,无一例外地被席卷进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尽管曹禺没有接收系统的革命理论,更对中国革命前景缺乏清晰的判断和分析,但是“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建设,建设也包含着革命。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人们不得不去面对生疏、难以把握的生活磨难和动荡时代的生命蹉跎”[6]。不熟悉中国革命、长期游离于中国革命阵营之外、作品经常被革命作家误解甚至非议的“民主”、“进步”作家曹禺最终还是难逃被中国革命、政治所重建的历史宿命,开始了自己第三次人生主体建构的艰难“蜕变”过程。当然不是每次主体建构都对个人人生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有时主体的建构或者重建也会出现失误,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被中国革命所重建的曹禺面对汹涌澎湃的中国革命和政治热情,不得不重新反思弥漫在自己早期剧作中的神秘氛围和历来为革命权威文艺理论家们所诟病的“宿命”立场,进而追求明朗、火红,能够预兆中国革命必胜的艺术效应,从《蜕变》到《黑字二十八》再到《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显示了曹禺由艺术至上的民主作家向政治第一的党员作家艰难“蜕变”过程,逐渐丧失了支撑早期话剧艺术伟大成就的“通灵宝玉”,创作才华趋于钝化。步入晚年的曹禺虽曾极力追寻早期戏剧创作的灵感与诗意,但终因主客观方面各种复杂难言的因素未能遂愿,陷入巨大的痛苦不能自拔,未能完成自己人生的第四次主体建构,给自己也给中国话剧留下了巨大而难以估量的损失和遗憾。
[1] 李继凯.鲁迅与茅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 田本相.曹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 曹禺.杂感[J].南中周刊,1927,(20).
[4] 曹禺.偶像孔子[J].南中周刊,1927,(25).
[5] 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J].剧本,1982,(10).
[6] 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J].文学评论,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