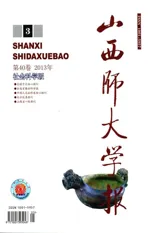“新童话观”背后的启蒙
——重读鲁迅译本《小约翰》
2013-04-11陈芸
陈 芸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1926年七八月间,鲁迅先生与友人齐宗颐合作,首次将荷兰作家拂来特力克5望5蔼覃(Frederik van Eeden)的童话《小约翰》翻译成了中文。在书的序言中,鲁迅特意交代翻译此书的缘起:1906年,他在文学杂志《文学的反响》上看到此书,只看到此书的第五章,就“非常神往”,找了几个书店都买不到,特意让朋友到德国订购。此书发表于1887年,弹指一瞬,此书翻成德文,再由鲁迅转译成中文,已是四十年之后的事。
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何鲁迅对此书情有独钟,甚至在外语实力不足而被“学者”、“正人君子”围攻的情况下,仍执意翻译此书?此书到底有何魅力?荷兰批评家波勒5兑5蒙德对此书的评论值得玩味。虽然他坦言自己不太懂这本书,然而却说这部书易被有文学修养的人误读。因为此书的好处,“绝不是因了它的高尚的艺术形式,也不是因了在里面说及的哲学的纯粹,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诗,其中并非叙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如现在已经长大的约翰,当他在一个满是人类的悲痛的大都市中,择定了他的住所之后,在那里经历着哀愁的道路,由哀愁与爱,得了他自己的性格的清净,这两者是使他成为明洁的,遐想的纯觉的人。”[1]122在蒙德看来,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容易看重“艺术形式”和“哲学意涵”,而忽略了其“象征底散文诗”的意义,这种误读无异于买椟还珠。而他所看重的“象征散文诗”,是不是一种新的内涵需要认真分辨呢?在百年之后重新面对《小约翰》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再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
若从感性的阅读出发,《小约翰》里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对于爱和哭泣的强调,使得整个童话在幸运与不幸、喜剧与悲剧之间跌宕起伏。这种起伏与其他童话存在着天然的差别。一般而言,写给儿童看的故事人物形象较脸谱化,善恶鲜明,没有过分强度的情感,也以皆大欢喜的结局为多。而《小约翰》却始终穿梭着悲与喜、哀与怒,而最能表现这一特色的便是让鲁迅神往的第五章。 一开篇,叙述者“我”告知读者不可向小约翰提及此事,暗示了这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然而在前四章的叙述节奏和风格上却大体上呈现出明快喜悦的色彩。小约翰和父亲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他睡前祈祷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果然,有一天奇迹发生了,他遇上了像蓝色水蜻蜓的精灵旋儿。在第五章中,小约翰在旋儿的带领下漫游初秋的森林,他们一起造访形体各异的蘑菇们,一起造访树精灵小鬼头“将知”。将知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精灵,他保管着精灵的圣书,一切的知识都可以从这个圣书而来。将知告诉小约翰,人类一直都没有这样的“大书”,因为这本真理之书,能够给人大幸福和大太平,它告诉人们为什么每样事物应该是那个样子。总之,它能回答一切问题。这触发约翰寻找“大书”的兴趣。但旋儿却告诫约翰,不要像将知那样相信可以寻找到这本书,虽然这本书的确存在,但它就像影子一样,“你怎样地飞跑,你怎样地四顾着想攫取,也总不能抓住或拿回。而且你终于决定,你是在寻觅自己”。遗憾的是,约翰没有听从旋儿的告诫,而是陷入了对大书的寻找,可以说正是在第五章的时候出现全书的转折,为旋儿与约翰的分离埋下了伏笔。
不仅如此,此处出现了“寻书”这个关键词。小约翰到底能否寻找这样的书,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书,成了贯穿全书的红线,也吊起了读者的胃口。那么按着童话的常有的套路,寻书如寻宝,小约翰应该走上了一条探险之路。然而故事的发展出乎意料,旋儿没有带领约翰寻书,反而不满约翰变得和人一样,所提的问题没有答案,没有满足,像所有和将知谈过话的人一样,牺牲了一切,“像寻找炼金术一样满怀热情地四处寻找那本书”,对眼前的自然不屑一顾,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只专注于寻找大书,却忘记了目标和方向,变成可怜的老糊涂。而旋儿希望约翰只爱他,这样就能与自然作伴,知道更多,享受真正的宁静和祥和。然而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得约翰并没有真正理解旋儿的话,而是又继续找回将知。也正因如此,约翰失去了旋儿这个朋友,走上独自寻找大书的道路。
至此可以略微窥见全书的主旨,所谓“成人的童话”,并不只是用童话的视角和语言来表现成人的世界,也不只是孩子、成人都适宜看的童话,而是用童话的形式巧妙地承载了童话思维与哲学思维之间的张力,展现了从童年世界向成人世界过渡的不可避免的孤独和忧伤。
旋儿最初能与约翰为伴,因为约翰热爱自然,童心未泯,能够相信奇迹。然而和将知谈话之后,约翰已经不满足欣赏自然,他渴望知道更多答案,得到一个简单清楚的解释,之后,“为了知道事物本来的样子”,他开始跟随另一个精灵“穿凿”,穿凿如同《浮士德》中梅菲斯特,代替了旋儿,担当起教育约翰的责任。之后,约翰还成为“号码博士”的学生,拿兔子做起实验。但约翰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寻找,可能南辕北辙。世界里有太多的秘密,一些秘密需要隐藏,没有必要知道所有的答案。爱这样的秘密,比知道所有的秘密更加重要。过分清晰的答案,只能解构那些秘密,解构人对自然的敬畏。约翰无法意识到他此时已经享有宁静和祥和,而一旦走上寻找之路,首先就是破坏宁静祥和,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成长,开始从童年世界向成人世界的过渡。从这个角度看,《小约翰》类似一部成长小说,或是德国式的教育小说。
鲁迅翻译此书,最初的意图是不是在此呢?鲁迅曾引用日本儿童作家桢本楠郎的话来论说:“旧的作品中, 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 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 来观察和倾听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 却是没有的。为了新的孩子们, 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 不断地发荣滋长的。”[2]395他常感叹中国人没有童话,没有成长小说,文化都太过于成熟,没有合适小孩子看的书。而让孩子有一个从童年走向青年的过渡,显然也是他努力的一个目标。故孙郁先生在《一个童话》的书评中提及《小约翰》催生《朝花夕拾》,也不是空穴来风,大可从这个角度理解之。[3]222
二
事实上,若从《小约翰》创作的时间和主题出发,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童话(或称诗化小说)《奥夫特尔丁根》,同样是成长和寻找的主题,在《奥夫特尔丁根》中寻找的是“兰花”,兰花预表世界最深的秘密,也许正是那本“大书”的另一个名字。以诺瓦利斯的作品作为潜在的互文文本,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小约翰》的文类特征——在“童话”与“非童话”之间,它与传统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样都有奇幻的经历、超自然的景象,然而从叙述的方式上显出了差别,使得文本从外在形式上就显出了“非童话”的特征。在《小约翰》的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一个讲述者“我”:
我要对你们讲一点小约翰。我的故事,那韵调好像一篇童话,然而一切全是曾经实现的,设使你们不再相信了,你们就无须看下去,因为那就是我并非为你们所作。倘或你们遇见了小约翰了,你们对他也不可提起这件事,因为这使他痛苦,而且我便要后悔,向你们讲说这一切了。
我大概还要给你们讲一回小约翰,然而那就不再像一篇童话了。
以“我”作为第一人称的讲述者,一方面为小约翰的经历定性为“童话”,一方面又坦言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这样的告白使得文本一开始便具有了悖谬的色彩,因为按照常识,童话应有强烈的虚构性、夸张性,这正与真实背道而驰。不仅如此,“我”还请不相信这件事的读者就不必往下读了,并且和读者约定,见到小约翰的时候不能提这件事,否则小约翰会痛苦,而“我”也会后悔。这一系列的要求,显然不像在讲童话,而是表明“我”讲的是小约翰的不幸,并且有意造成读者阅读期待的某种“逆转”,因为听童话的时候,读者往往期待读到一个美好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的不幸。
再看结尾,“我”再次强调了之前所讲的是童话,但若再“讲一回”,是继续讲小约翰的故事,还是重新讲这讲过的故事,就不再是童话呢?结尾显然并没有清楚地表达,而是暗含着两种可能性,进而也暗含着每一位读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遍可能读的是童话,而再读一遍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已经不是童话了。而对此时的笔者而言,它就已经不是童话,隐藏着更深的秘密。那么此时的笔者,是不是也成了小约翰?当我们试图对眼前的“书”开始寻找探究时,我们就面临着某种对“自然”的背离?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必然成为“小约翰”,但也许只有成了小约翰,我们才能更明白《小约翰》。
继续探索这种“非童话”,它更明显地体现在不少对于世界最根本问题的思考上。如对于人类、上帝、死亡、爱的说法,都远远超出了童话的范畴。例如小约翰要寻找的书到底是什么书?小约翰自己也茫然不知,只是好奇去寻找,直到借着穿凿的口,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具有“最高的智慧,给万有立一个根基”的书。这本书其实就是哲学,正是哲学试图为万物找一个根基,任何科学的探究、对理性强调都是建立在哲学之上。由此,才解开造成旋儿和小约翰根本分歧的正是“自然”与“哲学”的对立,这种对立并不是简单的观点的差异,而是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自然的生活强调爱、顺从、信赖,而哲学的生活则充满了好奇、怀疑、刨根问底,质疑宗教,轻视自然,甚至要改造自然。这两种世界观的差异造成了旋儿不得不离开小约翰。
再如旋儿对世界本源的描述,也带有强烈的“非童话”的色彩。他要求小约翰忘记自己是人类,因为“生在人类里,是一个恶劣的开端”,小约翰必须学习忘记人间生活,过去的记忆只能使他像一只在幽暗中徒然逃跑的小金虫一样无所适从。而作为太阳的孩子,旋儿虽未见过耀眼的太阳父亲,确有“一种不知不觉的记忆,向往着发光的一切”。而人类却只能“带着不可解的,不能抗的冲动”,“向着警起他们而他们所不识的大光的幻象那里去”。[4]47—48这段看似荒诞的描述,却可看作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洞穴比喻”的重新阐发和颠覆。由于无法直视太阳,人的眼睛容易去看那些“光的幻象”,而对光的幻象的追求是人的爱欲的表现,对智慧的追求,可能将人引入歧途,而忘记更加重要的发光源“太阳”。 那么,“这个太阳是上帝吗?小约翰战战兢兢地询问道”。不,也不是。在旋儿看来,“上帝”只是一个“可笑的幻象”,“是一盏大的煤油灯,成千上百的飞虫儿在那上面无助地紧粘着”。当小约翰向周围的人讲述这个观点,讲述自己曾听懂过花卉、动物的话,周围的人就以为他读过了安徒生,并提醒他应该多学习安徒生对上帝的敬畏[4]73,不要说渎神的话。因为小约翰不愿承认《圣经》就是那本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大人们便不让他继续与新认识的女孩荣儿继续往来。
此处一笔带过地提及了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显出此书虽延续了安徒生童话的思维,但根本立论与安徒生并不相同。与安徒生虔敬的基督信仰不同,此书不少地方都有对基督教的批评,对祈祷的重新诠释。但就此也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反基督教立场或是无神论的观点,而是需看到它否定的是基督教过分形式化的仪式,常人对宗教过分刻板的态度,但在内在精神上并没有否定基督教。尤其是在全书的结束处,小约翰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眼睛像旋儿,含着“无穷的温和的悲痛”的人,“他背着晃耀的乘具,在火路上慢慢漂远”。看到他的时候,小约翰一下子想到耶稣。这个联想表明小约翰重新回到信仰的起点,回到了基督教耶稣的苦弱形象。然而那人却让他不要称呼这些名字,“因为之前,它们是纯洁而神圣如教士的法衣,贵重如养人的粒食”,如今变成了“傻子的呆衣饰”,成为世人的嘲笑对象。那他到底是谁,“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是那个“那使你为人们哭的,虽然你不能领会你的眼泪,将爱注入你的胸中的,当你没有懂得你的爱的时候,和你同在,而你却看不见的,触动你灵魂,而你却不认识的”[4]119那一位。这不正与耶稣的训导相合吗?这个上帝正是与你一起哭泣,一起欢笑,与你同在,你却浑然不知的上帝。这种对于上帝的认知,从某种程度上讲,暗合着20世纪初欧洲思想界对于“上帝之死”的讨论。小约翰从否定上帝走向自然,又回到了重新认识上帝的路上。虽然他没有最终确认那个上帝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但最后,小约翰沿着他的路继续行走着,拉着他的手,和他的伙伴们“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这样的场景,不由让人联想到基督徒们背着十字架的朝圣之路,而这正是小约翰的朝圣之路,成长之路。
这些“非童话”的部分大大加深了文本的阅读难度,然而它们并没有流于说理教化,而是仍然依附在“童话”之上。童话、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是古代人揭示意义、创造意义的活动,它们最好地保留了原始的诗意思维,保留了神话的内在结构,童话中的象征功能构成丰富的寓意系统,这些都是其他文体形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从童话、神话到诗歌、散文、小说是一个人成长阅读的次序进路,也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发展成熟的过程。而对于浪漫派诗人而言,由于启蒙以来的科学精神摧毁了原来由神话、童话提供的幻境,使得原有得以依靠的信仰无本可依,诗歌的生存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重新使用童话、神话这样的文本形式,一方面就是对过分理性化、清晰化的现实世界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对理想人格的某种补充。例如诺瓦利斯在《塞斯的弟子们》中所用的夏青特和洛森罗蒂的童话,就是以童话的形式补充了“严肃的人”所缺乏的东西,并使得文本形成了从童话世界向小说世界的过渡。[5]176可见,作为浪漫派诗人杰出代表,诺瓦利斯是有意识地使用童话形式的。
蔼覃使用“童话”,显然同样有所寄托。童话这件“外衣”对于他要讲述的故事也相当重要。强调“童话”,一是给了小约翰一个充满奇异幻想的开端,符合孩子童年生活的图景,同时它又预言了孩子的成长之路。二是对于文本中间出现的启蒙理性精神、科学精神采取了调侃和颠覆。当小约翰被“将知”吸引时,表明启蒙的初步胜利,表明在小约翰从童年期向成人期的发展过程中,童话思维不敌哲学思维的处境。然而即使如此,“童话”并没有就此败北,因为整个的叙述框架仍统摄在“童话”之下,“童话”便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对科学精神进行报复和解构。如对“将知”、“穿凿”、“号码博士”的形象塑造,就无不透露出反讽的效果。三是童话的形式带有怀旧追忆的意味。对于已经成人的读者而言,重读童话,便是返回自己的童年,召唤自己的成长记忆,寻思自己是从何时开始从“自然之子”转向了“人之子”,是从何时开始失落了童真,进入了悲哀的生活。由此可见,童话与非童话之间微妙的张力,正是《小约翰》独特的魅力之一。
三
结合对《小约翰》内在结构的解读,让我们重返鲁迅先生的翻译。从翻译的童话内容出发,已有多位学者指出鲁迅翻译童话,不同于传统童话宣扬的善恶观,因果报应,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和启蒙功用。如《小彼得》反映的阶级压迫意识,《俄罗斯的童话》中荒诞的俄罗斯现状。鲁迅的启蒙旨在“抵抗一个缺乏本真、真爱、童心的现代社会”,所谓“成人的童话,便是成人用稚童的语言、稚童的心态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尝试,一种背着童话皮的成人教谕”[6]181。
若从这些童话的形式出发,可以进一步发现鲁迅所偏好的文类是处于“童话与非童话”之间。这种“新童话”(或“象征的散文诗”、“诗化小说”)作为文类形式的意义,对鲁迅而言也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种“新童话观”正构成了鲁迅启蒙观的一部分。其中“非童话”的部分承载着对人类命运、历史、社会、人性、宗教、哲学的思考,承担着启蒙教化的功用;“童话”的部分则保留着想象、神话、诗意的空间,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弊端。此二者之间的相生相克,使得鲁迅不同于只强调理性、知识万能论的法国式启蒙主义者。法国式的启蒙者往往轻视童话,认为它们只是人类理智不成熟的阶段性产物,而用普遍人性论的哲学教化取代童话的教化。这种取代一方面符合人的理性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对于童话本身具有的教化功用的忽视。
相反,德国的启蒙者更加重视童话的作用,正如本雅明所言:“童话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至今也是孩子们的第一位导师。童话始终暗暗存在于故事之中。第一个真正的讲故事的人是讲童话的人,将来也依旧是。无论何时,童话总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忠告;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童话的忠告都是极有助益的。”[7]309童话的背后往往渗透着最朴素、实用的伦理观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理念都会因为哲学教化的介入而造成混乱和破坏,就如同小约翰离开了旋儿、离开了自然,久久找不到幸福。“寻觅、思想、观察”是哲学、科学研究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并没有带领人真正接近世界的真相,而是将一切还原为号码和数字。看似追求光明和真理,却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但又不能就此简单否定哲学教化的意义,而应看到它如同梅菲斯特的“恶”,从另一方面同样推动了历史和个人的进步。正如“永终”所告诉约翰的,“穿凿”能够把他变成好人。“恶”也能引向“善”,但必须经过最后的一跃,自我的超越才可能最终实现。若没有那么一跃,约翰可能就此消沉抑郁而亡。正是最后的一搏,约翰得到了真正的自我救赎。
而结尾处那个人告诉约翰,“必须许多眼泪来弄亮见我的眼睛,不但为你自己,也必须为我哭,那么,我于你就出现,你也又认识我如一个老朋友”。则表明了认识自己与认识神的过程是同步的,只是通过泪水才能净化心灵,通达神性。这个过程如此艰难漫长,必须通过“自然的教育、哲学的教育、泪水的教育”三步曲之后才最终完成。
鲁迅一针见血地概括为“在自身中看见神”,说明了鲁迅是蔼覃心心相契的真知己,蔼覃是鲁迅的同时代人。与鲁迅原来学医的身份相似,蔼覃也是医生,日后还成了著名的心理学医生。他们面对自己国家积弱的处境,都以文学、文化的革新来挽救国民的命运。可见从医还是从文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疗救青年,思索人的走向。在这一点上,他们呼应了德国浪漫派强调“个体精神与宇宙精神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融合”,呼应了对人的教育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
而数年前,《小约翰》由胡剑虹先生重译。因从英文版译出,流畅浅白了许多,更符合儿童的阅读习惯。胡先生似乎努力将《小约翰》还原为“童话”,但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种还原的努力也可能从教化的层面削减了文本形式蕴含的丰富性,大大消解了“童话”与“非童话”之间的张力,使得《小约翰》仅仅成了“儿童的童话”,而非“成人的童话”。
也正如不少读者最直接的阅读体验,新译本不如鲁迅译本有“神韵”。这种神韵到底从何而来?它恐怕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文白相杂,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怀旧情结,更多还是因为鲁迅更切近原作者的初衷,鲁迅译文精心营造出来的更具纵深感的形式味儿蕴育了“神韵”。而若对此视而不见,也无异于买椟还珠,成了蒙德所谓有文学修养的人的误读。
[1] 波勒5兑5蒙德,拂来特力克5望5蔼覃[M].鲁迅译文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7.
[2] 鲁迅全集:第1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弗雷德里克·凡·伊登.小约翰[M].胡剑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4] 鲁迅译文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2007.
[5] 诺瓦利斯.大革命与诗化小说[M].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6]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7] 瓦尔特5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