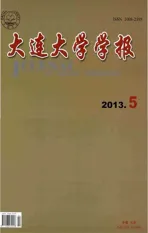试论二战后日本在领土处理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托管冲绳(二)
2013-03-22安成日李金波
安成日,李金波
(1.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编辑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试论二战后日本在领土处理问题上的态度与美国托管冲绳(二)
安成日1,李金波2
(1.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编辑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二战后美苏矛盾不断激化,东西冷战的乌云迅速蔓延东亚的形势下,掌握对日占领主导权的美国,为使日本尽快成为“东亚防共防波堤”,高唱对日“宽大的媾和”,致使日本置喙媾和问题的机会陡然增加。在东西冷战迅速蔓延的形势下,安全保障问题和与之相联系的日本周边岛屿的处置问题,成了日本能否谋求与同盟国尽早实现媾和的关键。最终日本吉田茂政府接受美军继续驻扎日本本土;牺牲冲绳人民的利益,同意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托管琉球(冲绳),日本只保留“潜在主权(或‘残存主权’)”的有限恢复主权的方式实现了同西方阵营的“多数媾和”——即事实上的“片面媾和”。
二战后;领土处理问题;日本;美国;托管冲绳
为了弄清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并继续推进对日媾和,1950年12月8日,杜勒斯在递交给国务卿艾奇逊的备忘录中表达了近期准备访问日本意向。1950年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对日媾和问题做出了“不管苏联参加与否,美英两国不妨与日本继续推进媾和条约交涉”[1]的决断,从而正式确立了对日单独媾和方针。杜勒斯访日前夕,1951年1月15日和20日,占领军总司令部政治顾问西博尔德,向华盛顿传递了两份备忘录。其中,在1月15日的备忘录中西博尔德称:日本的各政党要求恢复领土主权,并建议在媾和条约表述中承认日本对琉球(冲绳)的最终主权。在第二份1月20日的备忘录中,西博尔德又称:吉田茂首相曾非正式来访,表达了日本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媾和愿望。吉田茂希望“如果实行托管统治,不管其内容多么稀薄,希望留下某种主权的痕迹”。西博尔德还称:吉田茂希望在东京就领土问题同杜勒斯直接交换意见[2]。不仅如此,1月25日,吉田茂还直接派遣心腹白洲次郎到华盛顿,转达了日本方面的上述愿望。
1951年1月25日,美国对日媾和特使杜勒斯第二次访日。1月29日、31日和2月7日,杜勒斯先后3次与吉田茂首相举行了会谈。1月29日吉田茂同杜勒斯举行会谈之后,30日日本政府向以杜勒斯为首的美国使团递交了有关日方对媾和问题的备忘录——《我方见解》。该备忘录由(一)“领土”、(二)“安全保障”、(三)“重整军备”、(四)“人权等”、(五)“文化关系”、(六)“国际上的福祉”等内容构成。在该备忘录中,日本政府就有关领土问题阐述了如下见解:“(一)现在琉球以及小笠原群岛被提议置于以美国为施政国的联合国的托管统治之下。日本愿意响应美国提出的任何军事上的要求,并且也可同意接受‘百慕大式’的租界方式,但是为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恳请美方对此次[日方]提议予以慎重考虑。(二)为了日美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要请对以下各点予以考虑。①有朝一日若无需对琉球、小笠原群岛进行托管统治,期望立即把它归还日本。②允许这些岛屿的居民保留日本国籍。③日本与美国拥有共同权限(joint authority);④允许战争中由日本当局或战后由美国当局指使移居日本本土的8000名小笠原群岛及硫磺岛居民返回各自的家乡岛屿。”[3]在31日的会谈中,吉田茂首先谈到领土问题,称:“希望不要剥夺冲绳、小笠原两个群岛的领土主权和居民的日本国籍”。对此,杜勒斯态度十分干脆,他以“冷峻、冷酷”的语气表示:日方“提出领土问题是极为不妥当”。此时杜勒斯至少在表面上还以《波茨坦公告》中已明文规定日本的领土仅限于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及“盟国指定的周边岛屿”为由,坚持在领土问题上不容日本置喙的态度[4],他对日方置喙领土问题感到不悦,但也注意到这是日本国内的普遍愿望,感到有重新予以考虑的必要性。2月10日,杜勒斯把有关媾和条约的“日美谅解备忘录”和访日成果加以汇总形成书面材料呈送至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艾奇逊。此后,杜勒斯继续其亚太之行,相继访问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月26日返回华盛顿。此次亚太之行以后,杜勒斯在琉球、小笠原群岛战略托管统治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杜勒斯对外仍继续坚持对琉球、小笠原群岛进行战略托管统治的原则立场,但是与之同时他开始暗示托管统治并不意味着使日本彻底放弃对琉球、小笠原群岛的主权,并开始摸索实施托管统治的同时以某种形式保留日本对琉球、小笠原群岛主权的方法。
总之,1950年秋到1951年初日本政府在琉球、小笠原群岛地位问题的对美交涉中的基本方针是:尽量避免出现对琉球、小笠原群岛实行联合国托管的局面,并尽可能保留日本对上述岛屿的“哪怕是稀薄的主权痕迹”。日方上述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对日和平条约》与琉球(冲绳)、小笠原群岛的“残存主权”
杜勒斯返回华盛顿以后,美国为了同英国协调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立场,结合此次访问亚太各国的成果,加紧了新的对日和平条约草案的起草工作。3月12日,英国政府通过其驻美代理大使向美国转交了阐述英国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备忘录。从该备忘录上看,美英之间的分歧主要出现在媾和会议上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媾和后对日本造船业的限制问题、南桦太岛(南萨哈林岛)及千岛群岛的处理问题等方面。
1951年3月23日,美国国务院终于完成了新的《对日和平条约草案》(即“3月草案”)起草工作。美国“3月草案”在琉球、小笠原群岛托管统治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总体上看“3月草案”基本沿袭了美国“9月草案”和“对日媾和七原则”基本内容,但在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安排和表述中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美国的“9月草案”是在其第四章第六条中规定了有关南太平洋诸岛的战略托管统治和琉球、小笠原群岛的托管统治问题。然而“3月草案”则与之不同,在其第3条中规定了有关朝鲜的独立问题和南太平洋诸岛的战略托管统治问题,并明确表明日本放弃对上述地区主权,而有关琉球、小笠原群岛等的战略托管统治问题则放在在第4条中,且在此并没有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上述地区的主权。也就是说,“3月草案”有意识地把日本需要放弃主权的领土和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小笠原群岛进行了区分。美国“3月草案”,在条约条款上的上述微妙的调整和变化,为后来的冲绳、小笠原“残存(潜在)主权论”提供了依据。因为,“3月草案”领土部分后经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就成了提交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的“对日和平条约最终案”的领土条款。
“3月草案”出台以后,杜勒斯携该案同英方展开了“对日和平条约最终方案”的交涉。在这一过程中,4月9日,英国向美国提出了由89项条款构成的“对日和平条约”英方草案(起草日期落款为4月7日)。该草案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对琉球、小笠原群岛的主权[5]。正当杜勒斯在华盛顿围绕美英两国方案同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Shewell Franks)折冲之际,发生了足以影响对日媾和进程重大事件。4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罢免了盟国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麦克阿瑟是“对日尽早媾和论”的重要支持者,他的解职无论是对杜勒斯还是日本的吉田茂政府都产生了强烈冲击。杜勒斯对尽快实现对日媾和几乎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辞去国务院顾问和对日媾和全权代表职务,不再过问对日媾和问题的想法。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允许杜勒斯辞职。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杜勒斯,要求杜勒斯立即飞往东京向日本政府说明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不变立场的同时,与麦克阿瑟的后任、新任命的盟军总司令官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中将协商相关后续事宜。
1951年4月16日,杜勒斯第3次访日。访日期间杜勒斯向日方阐明美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媾和立场的同时,就英国提出的媾和条约草案同日方交换了意见。4月20日,日本政府向杜勒斯递交了题为《关于对日和平条约英国草案之考察》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日方认为英国的草案带有某种强迫媾和味道,相比之下日方更愿意接受美方的草案。日本政府罗列英国草案中令日方难以接受的内容的同时,希望把英方草案中日方能够接受的内容揉和到美国草案中去[6]1003。4月25日杜勒斯结束访日返回华盛顿。同一天,英国外交部派遣的以日本处处长查尔斯·H·约翰斯顿为首的英国对日媾和条约交涉代表团也抵达华盛顿,同杜勒斯的特别助手艾利逊(J.M.Allison)为首的美方就对日媾和问题展开事务级磋商。美英以美方的“3月草案”和英方的4月7日草案为基础进行磋商,开始了美英共同草案的起草工作。5月4日,美英完成事务级别的折中,共同起草完成了“对日媾和条约草案”。
美英“共同草案”由“前言”和“第一章和平”、“第二章领土”、“第三章安全保障”、“第四章政治·经济条款”、“第五章请求权与财产”、“第六章纷争之解决”、“第七章最终条款”组成。在有关领土条款中,有关台湾、澎湖列岛问题,英方对美方主张的“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和请求权”的规定,采取了有所保留的态度。有关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问题,原来美方在其草案中规定“日本向苏联归还南萨哈林岛及其附属岛屿,向苏联移交千岛群岛。”美英共同草案则改为“日本向苏联割让由日本过去行使主权的千岛群岛、南萨哈林岛及其附属岛屿”。至于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小笠原群岛的处理问题则全盘接纳了美国“3月草案”的方案。但是,美英外交当局的事务级磋商依然未能解决美英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上分歧。
为了进一步协调对日媾和问题上的美英立场,杜勒斯感到了近期访英的必要性。杜勒斯本打算5月21日至26日访英,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内部就对日媾和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应英方的要求只好推迟访英,6月2日杜勒斯携其特别助手艾利逊等飞抵伦敦。杜勒斯抵达英国以后6月4日首先同英国外相赫伯特·摩里逊(Herbert Morrison)、6月5日同杨格、继而6月8日同英国首相艾德礼等举行会谈,继续调整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美英分歧。6月1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在“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上最终确定了不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对日媾和会议的方针,接受了实现对日媾和以后由日本选择认为合适的中国政府签订和平条约的美方妥协案。
1951年6月14日,美英最终完成了“对日和平条约美英共同草案”(以下简称“美英6月草案”)的起草工作。6月24日,美国为了向日方通报美英交涉经过,派遣杜勒斯的特别助手原美国国务院东北亚处处长艾利逊公使访日。艾利逊到达东京以后6月25日同日本外务省次官井口贞夫、外务省条约局局局长西村熊雄等举行会谈,6月28日又举行了同日本政要的第二次会谈。在第二次会谈中日本首相吉田茂就联合国托管琉球、小笠原群岛的问题提出了“琉球、小笠原群岛被托管的情况下,居民的国籍问题将会如何处理?在经济方面,是否继续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等问题。吉田茂希望“在经济方面,对上述地区的人民给予[日本]内国民待遇。”对此,艾利逊答复称:美方“对上述问题早已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将来的琉球问题,尽管取决于联合国的决定,但在细节问题上,美国很乐意接受日方的提案。”艾利逊称:如果吉田首相或吉田首相的专家“愿意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我愿意聆听高见。”[6]1162-1163
1951年7月2日,日本政府经井口贞夫之手向艾利逊公使递交了最终表明日方对美英共同草案意见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日方称:冲绳等将置于以美国为施政权国家的联合国的托管之下。同占领时期一样,事实上由美国掌握主权的托管地区和日本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方面,希望美国在具体问题上给予关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试图修正和平条约中定的各项原则,也不是在提出类似的修正要求。”[6]1171-1173(1951年7月2日井口贞夫-艾利逊会谈内容)急于实现媾和的日本政府生怕日方对琉球、小笠原群岛的主权要求影响对日媾和进程,所以在备忘录中附加了,日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修改媾和原则”、也不意味着“提出类似修改要求”的“但书”。日本政府将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了美国的“善意”安排上。
艾利逊访日期间,杜勒斯为了进一步协调同五角大楼的意见,于6月26日同国防部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将军就对日媾和条约草案的内容问题举行了会谈。同马歇尔进行会谈之前,为说服五角大楼接受“美英6月草案”,杜勒斯还特意准备了一份“关于琉球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杜勒斯明确表达了不应迫使日本放弃对琉球群岛的主权的立场,并作为其理由提出了以下三点:“(一)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家宣言中,美国宣布了不扩大领土的原则,基于这一点美国本身也不谋求对冲绳的主权。(二)如果日本向非特定的国家放弃主权,可能会使国际情势陷入混乱。特别是在这种情势下,联合国有可能否决[美国对冲绳的]托管统治。那样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三)美国将通过对日和平条约从日本那里获得对琉球实施托管的全权,但是如果迫使日本放弃对琉球的主权,那么美国将从无资格者那里获得有关托管权限的认可”[6]1152-1153。“关于琉球的备忘录”表明,在日方的再三要求之下,杜勒斯和美国国务院都感到了以某种形式把日本与琉球、小笠原群岛等托管的统治区域加以联结起来的必要性,而这一想法在对日和平条约草案中则以迫使日本接受对琉球、小笠原群岛的托管统治,但是并不要求其放弃对上述地区主权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即所谓保留日本对上述托管地区的“潜在主权”的形式体现了出来。杜勒斯准备“关于琉球的备忘录”目的在于生怕美国军方反对在对日和平条约草案中由国务院精心设计的日本保留对琉球、小笠原群岛的“潜在主权”托管条款。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勒斯的担心是多余的。杜勒斯—马歇尔会谈之后,6月28日,马歇尔致函杜勒斯的一封信。在该信中,作为美国军方的意见,马歇尔附上了起草日期为6月26日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英6月草案”的见解。上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见解对“美英6月草案”中的琉球、小笠原群岛的托管规定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把原来的“以美国为施政当局”的词句改为“以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6]1161。
这时期,美国方面尽管对日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的“希望保留琉球、小笠原群岛居民的日本国籍等”保留“潜在(残存)主权”的要求没有进行明确的正面表态,但在“以某种方式给日本留下上述地区的主权依据”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已基本达成了共识[3]253。
1951年7月3日,美英完成了“对日和平条约草案”的最后修订工作。1951年7月12日,美英两国把7月3日两国共同起草完成的“对日和平条约草案”作为盟国的对日媾和条约草案予以公布。有关琉球、小笠原群岛处置问题的第三条规定,只增加了“以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的“唯一”二字。
与之同时,美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对日媾和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多方考虑,美英最终敲定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并开始向有关国家发出了与会邀请。1951年7月20日,日本政府也收到了美国政府通过西博尔德之手转交过来的正式约请日本派遣全权代表参加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的致吉田茂首相的公函。1951年8月16日,美英正式公布了准备提交对日媾和会议的《对日和平条约最终草案》。
1951年9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48个国家在旧金山同日本缔结了《对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对日媾和条约”的领土条款第三条规定:“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之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其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7]同一天,日美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军继续驻扎日本本土。
美国通过《对日和平条约》第三条的规定获得了对琉球、小笠原群岛行使排他性的行政、立法、司法之权利的依据,从而继续不受他国干扰地、自由地对琉球、小笠原群岛实施所谓的战略性托管统治。在琉球、小笠原群岛的托管问题上,鉴于美国继续保有冲绳的强烈愿望,急于结束占领、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吉田茂政权,无奈地接受了美国的安排。但是,对吉田茂政府的这一决策,当时很多日本人都是不愿接受、甚至是反对的,这对广大冲绳人民而言,更是意味着战后继续为日本本土的安全与繁荣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实际上,“《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以及日后日本的繁荣是以牺牲冲绳为代价”[8]得以实现的。
在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对日和平条约》第三条的酝酿过程做了如下说明。杜勒斯称:“[《对日媾和条约》]第三条主要涉及琉球群岛、日本以南以及东南诸岛的处理。这些岛屿的行政权自日本投降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若干盟国极力主张,为了美国本条约应规定日本放弃这些群岛的主权。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则提议,应将这些岛屿完全交还给日本。面对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美国感到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岛屿置于以美国为施政者的联合国的托管之下,并允许日本保留残存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9]所谓“保留残存主权”被解释为日本拥有对上述领土的最终处理权。
在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上,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吉田茂首相在接受《对日和平条约》的演说中称:“对于把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根据和平条约第三条被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的北纬29度以南之诸岛的主权保留给日本的美国全权代表和英国全权代表发言,我谨代表日本国民并以喜悦的心情予以接受。我期望能够尽快确立世界及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并期待这些岛屿尽早返回到日本的行政权管辖之下”[10]。
二战后日本为尽早结束被盟国占领的状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依照当初《芦田备忘录》和《天皇口信》的构想,选择了与美结盟,允许美军继续驻扎日本本土,并将冲绳置于美国单独托管下的方式,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实现了所谓的“多数媾和”——即事实上的“片面媾和”。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1952年2月28日签署的《日美行政协定》,构成了二战后延续至今的日美安保体制基本框架。美国依据上述条约获得了在日本继续驻军和建设基地的权利。日本通过向美国提供基地以获得美国的保护,美国则通过在日本驻扎军队达到了“冷战”时期控制远东地区、防范苏联和中国之目的。“就美国而言,驻日美军是其在亚太地区建立基地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其推行侵略远东政策的基石。就日本而言,《日美安全条约》提供了事时上的安全保障,用最低限度的军费开支来保障经济大国化目标的实现。”[11]
冲绳的美军的基地是基于日本政府于美国政府间缔结的安全保障条约而设置的,曾任日本防卫厅防卫局局长的久保卓也指出,“冲绳的美军基地是日美安保条约的枢纽。若无此基地即无法维持安保体制。因此,日本政府负有维持冲绳基地机能之责任”。[12]因此,二战后冲绳行政权归还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始终被置于日美安保体制允许的框架之内。
[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50,vol.6,1131.
[2]“Telegraph,No.1405,from W.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 20,1951,RG59,NA.
[3][日]石丸和人.戦後日本外交史(Ⅰ)——米国支配下の日本[M].東京:三省堂,1983.
[4][日]三浦陽一.吉田茂と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下][M].東京:大月書店,1996:162.
[5][日]河野康子.沖縄返還をめぐる政治と外交―日米関係史の文脈[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52.
[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51,vol.VI.
[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335—336.
[8][日]石丸和人.戦後日本外交史[III]━発展する日米関係[M].東京:三省堂,1985:225.
[9][日]入江通雅.戦後日本外交史(増補版)[M].京都:嵯峨野書院,1983:148.
[10][日]外務省戦後外交史研究会編.日本外交三十年——戦後の軌跡と展望(1952——1982)[M],東京:世界の動き社,1982,50;なお吉田茂.回想十年(3)[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104.
[11]冯昭奎.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1.
[12][日]新崎盛暉.沖縄現代史[M].東京:岩波書店,1996:28-29.
Discussion on Japan's Attitude toward the Territory after World War II and Okinawa under U.S Trust(II)
AN Cheng-ri1,LI Jin-bo2
(1.College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2.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Heilongjiang Education,Harbin 150080,China)
After World War II,US-Soviet Union contradiction became intensifed,and the dark clouds of the Cold War spread in East Asia;the USA who had the dominant right over the occupation of Japan,in order to make Japan an”East Asia breakwater against the Communist”,singed a”lenient peacemaking”over Japan,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hat Japan could join the discussion of peacemaking abruptly.Under the situation of a rapid spreading of the Cold War,security issue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posal problems of surrounding islands of Japan became the key to making peace with the allies.Finally,Shigeru Yoshida government accepted the continuation of deployment of U.S army and agreed U.S to trust Okinawa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Nations by sacrif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Okinawa,and in the way of retaining the potential sovereignty(or 'residual sovereignty'),and limited restoration of sovereignty to realize the peacemaking with the majority of western camp,that is,a de facto”one-sided peacemaking”.
After World War II;Japan;U.S;Trust Okinawa
D819
:A
:1008-2395(2013)05-0022-05
2013-04-22
安成日(1964-),男,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行政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国学院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东亚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李金波(1965-),女,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编辑,工商管理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管理学研究。
基金课题:2007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522087);南开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研究项目(2009JJD77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