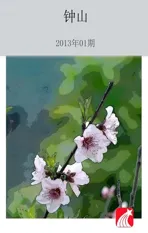读孙频记
2013-02-26何平
何 平
本来题目叫《看孙记》,因为孙频一直心念对张爱玲的欢喜,也想戏仿下“张迷”们的“张看”和“看张”写篇《看孙记》。张爱玲对孙频影响非常大,她说:“我十几岁第一次读她的小说时就喜欢上她了。不仅是喜欢她文字的苍凉与精致,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那个人。说实话,至今,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会一遍遍看她的书,原因很简单,读她的文字的时候我感觉我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很孤单的。是那种致命的苍凉的孤独。”也确实如此,读孙频的小说,不时感到张爱玲的“幽灵”和“鬼影”。但我们应该知道,张爱玲之后,学“张”者甚众,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多了去,所以有人说:“若拘泥于表面的文字姿态和人物戏剧,也就容易变成‘学张者死’了。”那么,在张爱玲玩熟了的套路上孙频是驾轻就熟还是别出新径?是“学张死”还是“学张生”?都是值得细细辨察的问题,先按下不表,容后细说。

一
拿到孙频的作品目录,看到她三四年攒下了的一百多万字已经发表的小说,虽然不算少,但比起动辄千万字成名已久的作家,这只是个小数目,我想当然地以为作一篇她的作家论不会费时费事,这也是一开始就应承下这个活的理由。及至读她的小说,我发现事实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一个秋天就在读她的小说中过去了,可感觉还是漂的,有的东西还是没有想透。这一方面,因为如果我们粗疏地分类,其实有的作家是有明确的观念统驭写作的,因此也更容易被抽绎和概括,而有的作家观念藏掖着,可能更适合阅读和体味。对于后一类作家,你如果要抽绎和概括就会涉及篇篇殊异的繁琐文本细读。孙频也许就是这后一类作家,因为孙频的写作关乎的是“单数”生命个体茫然无序的日常生活和一团乱麻的内心。面对世俗庸常的人事,孙频没有我们习见的居高临下的教训者嘴脸,而是平等尊重体恤地将心比心地入乎那些她虚构的人事。就像一个演员,孙频属于那种很容易入戏,现场感很强的作家。另一方面,孙频这样一个写作年龄不长的作家一开始所必然的四面出击乱打乱撞的“芜杂”也使得对她写作的走向很难把握。她还没有“风格化”,她的写作才刚刚开始,未来还在眺望中,她还要通过不断的调整和变动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所以针对这种对象的批评要理出头绪作出一个概括性判断是很难的。
我注意到已有可数的几篇对孙频的研究,几乎都是把她作为一个“女性写作”的样本来考察的,但是不是只要我们确定了一个写作者的性别属性,就可以径直动用文学的性别尺度来框定?一定程度上,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性别视角”已经成为女性作家研究的另一种“政治正确”。但文学不是生理学,文学的魅力很多时候恰恰是“安能辨他(她)是雄雌”的混沌、暧昧。我也注意到,将孙频纳入到“女性写作”来观察的研究几乎都是通过对她的文本做减法来实现的,研究者有意减去了她“不女性”的部分,而那些所谓“女性”的充分则是用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尺子量下来的。那么,这种做减法所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可靠就很是让人怀疑了。我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孙频的写作中客观上存在 《车中的父亲》、《月夜行》、《九渡》等以男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我当然亦知道所谓的“女性写作”不仅仅关心你写的是男是女,而是一种有意的视角和立场。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迄今为止,我认为孙频并没有明确地用 “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视角和立场来约束自己的文字。孙频有比“性别”更辽阔的尺度,那就是能够把“女性”涵容其中的“人性”尺度。孙频认为:“我一直以为写作应该是深刻的,应该是触及人性的,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苦难和疾病的产物。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不应该失去对生命光辉的深意诠释,他其实是在争取人的更高的尊严和意义。正是这种类似于宗教的情结使文学滋养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就是这些思想使我一直在小说中探究人的命运,尤其是女人的命运,可能是对女人更了解的原因。在写作过程中我其实是在不停地向世界和自身提出问题与困惑,然后,我再在虚构的故事中自己将它解答。我喜欢触及到人性深处时的那种质感,虽然不免带着点鲜血淋漓,但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却也不失为一种活着的动力。”
退一步说,就算仅仅作为“女性写作”,孙频的写作也已经不是在我们熟悉的刻意强调的与男性中心主义的对抗中展开的。很长时间里,女性的写作被我们描述为一种压抑和反抗的书写。压抑和反抗所针对的是一个男性的想象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差异性背景下,女性的性别特征成为文学的书写对象,也成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识别标志。因此,我们想象中的女性写作者应该抱负着一种针对男性世界挑战和反抗的“烈士”情怀。她们昼伏夜出,不是战士,至少也是刺客。但我们应该看到“斗争哲学”左右下的女性写作和研究其实构成了对女性写作最深的遮蔽。像孙频的小说《凌波渡》,“男女”其实可以是作为独异者的彼此欣赏。王林和陈芳园,“他和她是一个部落里的人。”“在这所大学里,在密密麻麻的学生当中,只有这个人是她真正的族人。他们血管里流的是同一种浓度的血液。她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部落里可能只有她和他两个人。在这个校园里,他们不是农夫,不是猎人,不是逐水草而生的牧民,他们只是一个稀有而孤独的部落。”小说写陈芬园“十八岁中师一毕业就当老师了,在一个县中学里当了一年老师,如果一直当老师我现在教龄也好几年了,估计连婚都结了,说不定连孩子都有了。可是我过不下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你知道那一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是一天一天扳着指头数过来的。到了春天我就看着窗外的杨树叶想,杨树叶变绿了,夏天快来了,半年要过去了。到秋天的时候我看着树上掉下的落叶想,又是秋天了,一年又要过去了。我却还在这个地方困着。我没有一天把心放在那里,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有一天我肯定要离开的。我就一辈子呆在那么小的地方?过这种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生活,然后就困在这个地方死在这个地方?那种生活会把我默无声息地吞噬掉的,连骨头都不留。”孙频喜欢死犟、不低头的女性。死犟、不低头不是要和假想中的男性世界对抗,而是双手互搏样的幻想和现实的较劲。陈芬园想“用十年考个大学,就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她不是不反思,但拒绝回头,就算识得过去的好也不回头。“我经常问自己,我怎么就一步一步走到这步来了?我要是安分守己地去当中学老师,我现在教龄也应该有好几年了吧,大概已经结婚了,过着最安稳最踏实的生活。虽然平庸,可那是人间的。可是我原谅不了自己,我不允许自己过那种平庸的凡俗的生活,我就那么一点骄傲,我一定要拼死去保护它。为了保护这点骄傲,我都可以去死。我是宁可战死沙场都不愿平庸活着的。于是我就走到了现在。我问自己那个最开始的源头究竟是哪里?我也回答不了自己,只要错开一步,后面整个就面目全非了。我以为千辛万苦来到这所大学是圆了自己的梦,是捍卫了我的骄傲,一切都可以重新活过了,我想给自己机会重新活过。我让自己远离凡俗,远离平庸,却不知道那其实是走在水面上的,其实不过是凌波虚步,一脚踩下去,下面就是空的。”“我陈芬园心高气傲了这么多年,就白高傲了吗?最后的下场就是被一个都不爱我的人收留掉?我还要去找的,我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找,我就不信这世上没有一个能真正明白我是怎么回事的男人。”陈芬园孤绝的反抗和沉没,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以为是针对男性主宰的世界的挑战。小说写“陈芬园却不止一次有意无意地对王林说,我怎么就连你的性别也无视了,你在我眼里现在根本没有性别。我只觉得你是我的战友,是我的同盟,我根本不管你的性别是男是女”。小说最后,“陈芬园是在大三的第二学期突然退学的,退学前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王林。她办好退学手续后就在一个黄昏悄悄离开学校了。系里的老师一直不知道她为什么退学,她很突然地就决定了,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如果陈芬园是一个失败者,也不仅仅是“性别”的失败,而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作为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陈芬园的骄傲和独立并不是在和男性对抗中确立起来的,就像《碛口渡》的陈佩行,“全镇都知道了,她的心气儿忒高了,压根儿觉得自个儿就不是这个镇上的人。两年过去了,陈佩行还是一个人。”
安吉拉·默克罗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当代妇女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和‘普通’妇女及女孩相关?”安吉拉·默克罗比举男性社会学家施恩于他们的工人阶级对象的方式来说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隔阂:“通常是在研究的名义之下,他们构造出了极端浪漫化,甚至是奇妙化的描述,但是却远离了‘田野’,在他们身后留下的只有混乱、心怀疑虑,抑或直接就是陷入困惑。”安吉拉·默克罗比进而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关注生活中的人类主体,已经寻找出了颠覆这一学院派作风的道路。与学院派不同的是,我们努力以尊敬和平等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对象’。进入‘她们’的文化,浅尝辄止后向外在世界描述它,将其当作投机倒把的 ‘对象’,这是我们勉力避免的。女性主义让我们将我们自身的经历和经验放入我们可能询问的问题中,以便我们能与我们研究的女性有共同的感觉。所以我们自己的自尊也运用于我们和妇女及女孩间的调查关系之中,同时也运用于其他从事田野调查的女性身上。这就是说,女性主义不应被当作一种开门密码,如果那样,将会把全体女性放在单纯的性别背景上,建立起错误的‘统一’观念。 ”事实上,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针对汉语世界的“女性写作”和“女性写作”研究而提出。相对于“‘普通’妇女及女孩相关”的“田野”,其实,男女对抗只是关系之一种,孙频的小说迷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是简单的“男女”对抗,而是更缠绕,就像《合欢》中写到的,“在这个世界上,一旦有了关系就永远有了关系罢。所以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出招表示出要修葺的愿望时,另一个必须马上接招。他们之间已经是一盆炭火,吹一吹炭会变红,不吹就剩下了灰色的余烬。”而这种“变红”或者“剩下了灰色的余烬”的过程是孙频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小说的叙述路径和结构。
孙频小说的“女”对“男”不仅仅不反抗,甚至是顺应、迎合、妥协和屈服。就像张爱玲所说的:“西洋有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哀的。”(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像《醉长安》,“这混乱到了没有任何章法的男人。可是她还是舍不得他,她还是不愿意离开他,难道真的爱一个人就是什么都可以原谅可以容忍?她爱的究竟是他,还是她假想中的最后一次爱情?而她又为什么会有这假想中的最后一次爱情?她真的是为了去爱他,还是她想为自己赎罪,在她潜意识里,她三十岁以前的不忠诚就是她的原罪。”像《玻璃唇》,“她(林成宝)后来对姑妈说,她和霍明树那次见面始终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她觉得他一直在告诉她,如果我们不在一起,那还有什么意思?男人和女人之间可能就是那一眼两眼的事情,没办法,只一眼,她就从一个男人身边跨到了另一个男人身边,就那么一眼。”像《鱼吻》,“她(韩光)知道这样也许不对,她还是决定这么做,给他钱。尽管他根本没有提出来过。她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她会更深的陷进去,除了精神,还有经济上的陷进去。更彻底更致命的陷。”孙频无意让她小说的女人们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而是诚实地在“女人”们的“田野”里做一个勘探者和记录者。
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女性”的性别是不是只有在“男女”中才能呈现?比如孙频的《琴瑟无端》、《天堂倒影》显然就是一种“女女”式的性别呈现方式。小说对当下女性与婚姻、女性与爱情、女权与男权,以及剩女心理的一种思考。思考感情与性,爱与生存,妥协与算计,悲伤与理性。两个女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得到她们想要的感情的,也不可能得到她们想要的生活,真是得到了,小说去表达这种圆满也毫无意义,所以孙频只能安排她们在爱的缺失状态下选择去爱同类,同类的女人让她们更温暖更安全。孙频的“女女”之间的女性呈现,甚至可以是男性隐匿的,比如《同屋记》。“女女”之间的女性呈现并只是当下现实,《红妆》就是一段前朝旧事。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孙频也写到“男男”之间的男性呈现,比如《月夜行》。因此,如果孙频也可以作为“女性写作”的案例,显然不是建立在想象中的“女性写作”的“统一”观念之上的,而是具体情境和细节之下丰富的毛茸茸的“关系”——“这个女人,这样的女人,怎么就和自己有了关系?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何况,她们两个女人也是互相充当着彼此的观众、知己和敌人。惺惺相惜着,又冷眼旁观着,喜欢着又厌恶着,甚至,她们看到对方的伤口和隐痛时也是带着嗜血的快感吧。那她还能为什么,只能是为自己了”以及“关系”对人生理和心理的影响。“观众、知己和敌人”不只是“男女”,也可能是“男男”、“女女”,也可能是男男女女和他(她)们所置身的世界。
二
在同龄的作家中孙频起步不算早,如她说:“我最早写作是在2004年,上大二的时候,发过两个比较尖利的小说,此后一直没有再写,大学毕业后过了段四处辗转的日子,后来2008年来了太原才又开始写。”2004 年开始,2008 年续上。我没有查到2004年 “两个比较尖利的小说”,不知道这2008年才又开始写的是不是后来发表在《黄河文学》上的《追债》。《追债》确实不“尖利”,有点像记者按照线人爆料进行的社会新闻的调查,严苛地说堪称“平庸”。这样写小说的做派,孙频后来还会偶然为之,比如《菩提井》。能够看得出孙频在写《追债》的时候想说的东西很多,但都没有想透彻,所以夹缠粘着在一起。但应该看到孙频未来的写作是有能力将这篇小说中混乱错杂的那些因素自我澄清的,这也是衡量孙频作为一个有才情的年轻小说家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事实上,后来孙频果断地把《追债》中朱良和李桑之间都市男女的暧昧情感、母亲和春雨秋水姐弟破敝凋败之家的局促生活以及秋水这样的乡村或小县城知识女性孤傲与无望的挣扎,切割开来,各自发展成富有生机的部分,能合则合,当分则分。而这三个方面到目前为止几乎也是孙频小说的主要三个生长点。在第一方面,孙频写出了《醉长安》、《天堂倒影》、《鱼吻》、《隐形的女人》、《美人》、《合欢》等;第二个方面有《铅笔债》、《玻璃唇》、《血镯》等;第三个方面则有 《凌波渡》、《祛魅》、《夜无眠》等。
从2008年到现在也才四年,但孙频的写作对我们的许多文学经验和想象都构成了挑战,除了前面论及的“女性写作”,其中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如何重新看待“80后”。放在“80后”里,孙频绝对是个异数,她几乎从来不写抑郁孤独的青春期,几乎不用第一人称。“80后”里和她差不多的可能是甫跃辉和郑小驴。孙频的写作世界和她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镜像式的“仿写”,而是建立在更深层的精神关系之上的。如果要探讨孙频和她生活世界的关系我们现在还缺少实证。“很普通的家庭,很淳朴的父母,他们很爱我。但是,父母性格差异太大,所以我小时候也算是受过家庭创伤的人。这与后来对爱情和婚姻的怀疑,以及多年后提笔开始写作都有一定的关系。”“我是个性格比较分裂的人,可能是双鱼座的原因,一面朝上一面朝下,我是八零后的人,骨子里的很多东西却是七零后的,所思考的东西也是偏于七零后的,内心严肃,并不前卫,真的。我的一部分小说写的都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故事,当然都是听来的故事,放在我家乡的县城背景下。因为我对我长大的那个北方县城万分熟悉,我知道它的质感,这个县城离贾樟柯的汾阳很近,就是那样的质感,我写这些早已远去的故事的时候竟觉得是亲切的。”虽然她在和郑小驴的访谈中谈了自己的家庭、父母、星座、出生地等等,但要对孙频的小说进行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研究仅仅靠这些闪烁其词、影影绰绰的信息还不够,所以对这个相当有意义的话题暂时无法展开。而回到孙频开始写作的原点,看她和“80后”之间,思考“单数”的她和“复数”他们的关系,有些问题能够看清楚,也很有意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孙频其实提供了一个“80后”文学青年成长的样本。
虽然“80后”文学青年的成长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但2004年在“80后”文艺青年成长史上是绝对重要的一年。正是这一年孙频发表了两个“尖利”的小说。我们不知道这种“尖利”具体所指,但估计不是这种清浅的孤独和忧伤。“2004年,吉本芭娜娜的《厨房》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我们阅读太多的孤独的文字,却并未真的尝到孤独的滋味。我们未被留在孤独的操场,也未被直接抛进社会的洪流,在短暂的时间里,我们依然留存在青春期的尾巴上,不按时起床,每天什么都不做,糟蹋时光,任性伤感,毫不惋惜。 ”同年,张悦然在《花城》、《上海文学》、《小说界》推出三个小说专辑,并分别在春风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 《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红鞋》和《十爱》。笛安继 2003 年在《收获》发表小说《姐姐的丛林》,2004年《收获长篇小说专号》又刊登了她的长篇小说《告别天堂》。已出版《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郭敬明成立“岛”工作室,出版《岛》书系列。如果是指激越和愤怒,那2004年倒是“80后”彰显愤怒的一个年份。2004年6月,已发表出版《北京娃娃》、《抬头望见北斗星》和《长安街少年和玩火》的春树,成为《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人物,此前2月2日,《时代》周刊亚洲版也以春树作为封面人物,该期杂志的封面标题是“BREAKING OUT”,内文则以 《新激进分子》(The New Radicals)为题,将春树、韩寒、满舟、李扬等“80后”与美国“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是年,韩寒出版小说《长安乱》和文集《韩寒五年文集》。
她的阅读史不是“那些阅读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片山恭一的时光恍恍而过”,她的写作史也没有“新概念作文”的显赫前史,孙频让我们知道我们对“80后”作家的研究是多么不充分。“80后”作家中可数的几个公众人物和更为广阔的“80后”作家之间也有着很大距离的。在可数的几个公众人物高倍的聚光之下,其他的“80后”作家有可能成为“灯下黑”的被掩盖的一群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80后”作家中几个公众人物,比如韩寒、比如春树、比如郭敬明、比如张悦然、比如蒋方舟等等,分析他们的成长史成名史,就会发现他们的出道和成名彰显,往往都是从文学之外借力。而且一旦他们羽翼渐丰,他们手中将会握有更丰沛的资源,比如韩寒在网络上“可支配”的粉丝,比如郭敬明《最小说》的庞大读者影响力,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代人中的“大声说话”者。这些人“大声说话”的结果是,只要他们说了或者写了,不管他们说了或者写了什么,都不会缺少拥趸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频提供了一种和传媒、和资本运作没有关系的成长模式。和她的同龄人比较起来,孙频的写作史是“老派”的,当她的同龄人在大众传媒聒噪的时候,她却消失了,等她复出的时候,她还是诚实地从传统文学纸媒上,从 《满族文学》、《黄河文学》、《山西文学》、《章回小说》等一些名头不彰的“地方刊物”一步一步写出来。
当下正炽的“80后”作家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并没有被充分揭示,就是“80后”作家成长和上海之间的关系。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很少有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集结了这么多 “80后”作家,他们有的是来自外省的“沪漂”的文艺青年,有的是城区或郊区读中学时从“作文”转身到“文学”的年轻的资深作家,有的则是边写作边经营的作家兼商人。讨论上海和“80后”作家成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造星神话,《萌芽》、《小说界》、《收获》《上海文学》对新作家的提举,复旦大学写作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作家协会的“上海新锐作家文库”的连续出版,韩寒、郭敬明巨大的粉丝聚合力等等,而且《独唱团》、《鲤》、《文艺风赏》、《最小说》、《zero零》这些“80后”作家主编的刊物也都和上海或深或浅地有着渊源,但这些可能都是表面现象。往深处想,“80后”年轻作者的写作从它在世纪之交出现伊始,其实就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而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天然地对青年文化中的叛逆、夸饰、矫情等异端品质有着包容性。有一个流传甚广似乎从来不需要证明的看法是上海这个城市是最排外的。但事实上,近现代中国,上海这个城市市民的保守性、逐利者的商业性和城市精神气质中与生俱来的先锋性往往是并行不悖的。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会屡次成为先锋文学的策源地,也不难理解新世纪上海会成为“80后”作家的聚集地。
如果还从粗糙的代际来描述,作为一个所谓的文学群落,“80后”作家肯定已经是当下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构成,其人数之众、写作量之大和前面任何一代作家相比毫不逊色。但应该看到的是,“80后”作家在当下中国文学中的显赫地位,一部分当然由于“80后”作家早熟的写作才华所奠定;而另一部分则更多的是因为大众传媒和商业资本参与其间的塑造和自我塑造。一定意义上,“80后”作家的文学生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整体上并不景气的文学出版中的支柱产业。因此,自然而然,一些“80后”作家成就的不是文学天才的神话而是迅速致富的商业神话。当然这样说我并不否认任何一代作家中都不乏掘金客和投机者,只是“80后”作家在他们青涩的时代就躬逢商业和网络盛世,他们轻捷地就跨越了前几代作家漫长磨砺的学徒期。孙频“非京”“非沪”“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长史对于我们考察今天的文学生态和作家成长史有着另一种典型意义。
所以,讨论所谓的“80后”作家群落,一个重要的事实首先必须被追问:当我们谈论“80后”作家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谁?当我们谈论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文学吗?简单地说,“80后”作家个体书写的差异性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要复杂得多,而且这种差异性往往从他们写作的学徒期,从他们写作的起点就开始了。因此,在我们对“80后”作家缺少针对个体的普查式的文本细读和作家研究之前,就以某几个曝光率比较高的所谓代表作家作为样本,以一总多地去描述这一代或者这一群作家,其局限性和片面性是明显的。
三
现在该谈谈孙频和张爱玲的关系了。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张爱玲在今天的语境下也格式化了,就像也斯说的:“这么多年,各种言谈把她放置在流行小说、美元文化、经典作品、学院研究的种种阵营中,她写的东西好像跟这些标签都拉得上一点关系,读仔细点,又好像这些说法都未能真正说出她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即使不从也斯说的这些宏大上赋义,张爱玲的对世俗生活的萃取和转换的法术经过“张迷”们的反复演练也褪去了神奇的光影,比如下面这些片段就曾经被“张迷”们不断把玩:“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
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着的火光。”(张爱玲:《道路以目》)“街上的店铺全都黑沉沉地,惟有一家新开的木器店,虽然拉上了铁栅栏,橱窗里还是灯火辉煌,两个伙计立在一张镜面油漆大床的两边,拉开了鹅黄锦缎绣花床罩,整顿里面的两只并排的枕头。难得让人看见的——专门摆样的一张床,原来也有铺床叠被的时候。”“南宫在玻璃窗外立了一会,然后继续往前走,很有点掉眼泪的意思,可是已经到家了。”(张爱玲:《散戏》)“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是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更衣记》)除了这种俗世萃取转换术,如许子东说张爱玲好用“大量琐碎奇绝杂色质感的物化意象”,
张爱玲语言的修辞术也被许多人津津乐道。应该说,在语言的技术、修辞层面,孙频和张爱玲的亲缘关系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这种亲缘关系甚至是腔调和气息上的。孙频是张爱玲的识得者,语言的技术和修辞只是她和张爱玲的跳板,孙频最后要抵达的是张爱玲最核心的东西。“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就是苍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张爱玲小说的底色与我这种心理无疑是契合的,那是一条通道。”“绝望”、“苍冷”、“齿啮与痛苦”、“最冷最暗的地方”,这是孙频和张爱玲心有戚戚握手言欢的地方,只是一定意义上,孙频比张爱玲甚至更狠更坐实,因为在张爱玲所谓的“苍凉”是:“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张爱玲:《〈传奇〉再版序》)不管是真相,还是虚晃一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流离不安大厦将倾总是张爱玲“苍凉”的底子,所以你可以说张爱玲琐细,但张爱玲自有她的宏大布景。而孙频很少给小说摆设一个时代的宏大布景。不知道是兴趣使然,还是干脆和时代没有深刻的遇合,除了《红妆》这极个别的小说,孙频的小说差不多都把具体的时代抽空。但孙频的抽空不是张爱玲式的把人写成 “扁平的小纸人”(张爱玲:《我看苏青》),而让人和人在最简单的关系上缠斗,最终把“最冷最暗的地方”逼出来。
孙频小说的苍凉感,哪怕仅仅看她小说“苍凉”这个频频出现的词所栖身的场景和意象也能够感受到。所谓“苍凉”是无法摆脱的灰败日常生活的 “苍凉”:“窗户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灯泡,蜡黄色的油腻的灯光厚厚地涂满了整间厨房,四十多岁的姑妈正蓬着头在窗前炒菜。她看着这窗户就像看着一张陈年的油画,烟熏火燎的,散发着油哈气,像一个很深的梦里藏着的气息,即使是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她也能准确地闻到,是它。这过分的熟稔让她突然觉得无比苍凉,恍如隔世。”(《玻璃唇》)是“劫后余生的苍凉和温暖”:“她把头发当手帕擦了擦眼睛,这头头发被她养得像一只手一样柔软,仿佛是她身体上长出的另一只手,这只手带着劫后余生的苍凉和温暖抚摸着她。她这些头发可真是野火烧不尽啊,它们像地里的野瓜蔓一样顽强地爬了多少年,才爬到了今天的长度?她怜爱地抚摸着它们,像抚摸着一群逃出牢笼的囚徒。”(《骨节》)是亦华丽亦苍凉:“她一个人站在两根柱子的中间高声唱起来,唱《含嫣》,唱《打金枝》、《卖画劈门》。苍凉华丽的晋剧在空旷的戏台子上左冲右撞,最后袅袅地落在了地上。据说这戏台下面埋着两口大瓮,修建的时候结构十分严密,青砖之间不留一丝缝隙,捉音效果极好。平日里不唱戏的时候,这戏台就荒凉着,不见人迹。只有陈佩行隔两三天就要来一次。然后一个人在夜色中走回去。”(《碛口渡》)而如果把那层稀薄的温暖和华丽剥去,看到的是“苍凉”残酷的底色:“不知道是夜里几点了,竟是满月,就在当空,月光照在半透明的纱窗上,被筛的千疮百孔,然后像雪花一样落在了她们的被子上,脸上。月光的寒凉让她们在一瞬间觉得自己像河底的石子,白天所有叽叽喳喳的浮在空中的愉悦突然停止了,一瞬间是苍凉的安静,那么深那么苍凉的安静。两个人看着月光的眼睛都有些潮湿起来。似乎与岁月深处那些最深最暗的东西迎面遇上了,清晰、残酷而荒凉。两个人都觉得在这月光下有些溺水的感觉。也是在那一瞬间,她们知道她们之间终于有了一点通道,借着这一点通道,她们即使举着蜡烛也可以从这个身体到达那个身体里。”(《同屋记》)孙频小说人物的生命轨迹几乎可以用张爱玲的话来概括:“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一边是“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的人生匆促;一边是躲也躲不了的生命磨损,怎么可能不让人心生“苍凉”?因此,孙频小说的“苍凉”本质上心源上是绝望和虚无。在绝望和虚无的视镜下,人会逼仄到渺小,我注意到孙频除了喜欢用“苍凉”这个词,另外一个爱用的词是“浩大”。“她又低头看着地板,棕色的涂着清漆的木地板,她看着自己在地板上的倒影,像站在一片浩大的水面上。有风正从窗户里吹进。窗帘膨胀了起来,像里面站满了人。她又看了看周围。走在这老房子里,似乎到处是眼睛,到处是耳朵。”(《琴瑟无端》)“她掉头骑着自行车追前面的贾建华,贾建华走着,步子快而慌乱,近于逃生的脚步,没走几步就被后面的自行车追上了。她先用绝望的目光看了看前面,这才偷偷瞅了邵向美一眼。又是这偷偷摸摸的目光,就好像她刚偷了邵向美什么东西被邵向美当场抓到了一样。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血液一般在她们中间涌动着,穿过她的身体,又穿过她的身体,浩大的血腥的气息包裹着她们。她们被包在了最里面,都逃生不得。”(《鹊桥渡》)“当初三个人搬进这三室一厅的房子时,都大大惊讶了一番客厅的空旷浩大。这屋子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三间卧室一间比一间小,唯独客厅大的可以当足球场。加上租来的房子本身就没摆多少家具,所以,即使在白天,走在客厅里都能听到自己脚步悠远清冷的回声,像广寒宫似的。加上地板是白色的瓷砖,走在上面都能看到人影,就像走在一片浩大无边的水面上,一低头,自己清冽的倒影已触手可及,似乎伸手就能把自己捞出来。”(《同屋记》)我很难知道在孙频的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让她总是停驻在人内心深处 “最冷最暗的地方”,“浩大”——虚无空洞而又苍茫无助。
“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皮相上看,孙频很多小说都写到近三十,或三十郎当的女性何处安放自己,何处是归处的焦虑和算计,这几乎是《倾城之恋》白流苏的还魂,就像苏童说的,“张爱玲的心境出自一份古老的情怀,张爱玲笔下的女主人公通常是林黛玉式的纤弱,多愁善感,命运不济,但她们是新型的林黛玉,也许琴棋书画比不上林黛玉,但在现实较量与男性下棋的过程中,她们常常能胜出,尽管有时险胜,有时是惨胜。”但孙频很少像张爱玲那样散播琐碎的世俗气,她领受的张爱玲遗产是细致的心理分析,她摒弃的是张爱玲“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在孙频的小说中,虚无是一个迟早会到来的结果,她并不急着赶着奔向那个结果,而是耐心、步步为营地追问并回答虚无从何而来?因何而生?就像《祛魅》让李林燕不断萌生的现世幻想掐灭,“在方山中学一窝就是十年,十年可以让多少东西灰飞烟灭,一个三十二岁的单身女人能逃到哪里?”不只是三十二岁,再给十年的四十二岁,小说同样不给李林燕一点希望。“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至此,从“学张”开始的孙频,正在逃出张爱玲的阴影。
2012年11月15日随园西山
注释:
(1)(6)(7)(12)孙频:《内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2)(10) 也斯:《反墓志铭》,《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
(3) 孙频:《用文字和世界对话》,《山西文学》2010年第6期。
(4)(5)安吉拉·默克罗比:《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张岩冰、彭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8)周嘉宁:《扶桑岛上的青春札记》,张悦然主编《鲤·孤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页。
(9)张悦然主编《鲤·孤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页。
(11)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13)(15)(16)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见《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14)苏童:《张爱玲让我想起林黛玉》,见《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19-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