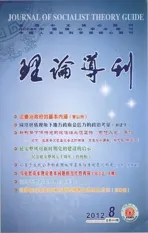环境治理策略之审视三题
2012-12-23杨华锋
杨华锋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环境治理策略之审视三题
杨华锋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基于经济理性主义而生的市场自决、基于行政干预主义发展而来的政府主导和由民主实用主义催化而来的社区自治,是环境治理策略的三种基本类型。就其实践进程而言,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市场机制中所承认与建构的实体都必然包含着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因而对环境问题的应对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手段;其次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积极干预有着现实的土壤;再次因为行政干预主义视角下的行政垄断所带来的弊端,政府失灵频现,因而也滋生着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期待。
环境治理;经济理性主义;行政干预主义;民主实用主义
基于经济理性主义而生的市场自决、基于行政干预主义发展而来的政府主导和由民主实用主义催化而来的社区自治,是环境治理策略的三种基本类型。
就国家机制而言,其在自然灾害、社会群体内部冲突、市场失灵以及外部威胁方面扮演着关键性角色,通过必要的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来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并结合必要的行政强制力,建构社会主导价值观,实施社会公共工程。当市场供给无力,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下,这种治理机制体现出高效、回应与积极主动性。不过国家治理机制在制度层面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与缺陷,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制度适用过程中的选择性与自由裁量,往往会诱发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的治理危机。
就市场机制而言,其通过市场分工的深化、资本的激励与经济理性的培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政治权力的过度干预,体现“看不见的手”的积极意义,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因此,市场治理机制在应对资源配置失衡和经济行为不当方面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不过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比较苛刻,而不完全信息市场的现实往往体现为投机行为的泛滥、垄断行为的盛行、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等。
就社会治理机制而言,志愿合作与积极行动是积极公民的集中体现,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公民行为具有典型的自治与他治统一的特性,其对政治权力和市场行为均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只是在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其发展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碎片化和随机性,令其难以充当有效治理的主体,反而可能被某些政治力量或利益集团所控制,走向民主参与、社会治理的反面。
一、经济理性主义与市场自决策略的审视
首先,经济理性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人类社会和广阔的环境世界应当服从于经济利益,而不是经济应当被组织起来服从于人类与环境的利益。[1]在经济理性主义者看来,市场机制能否对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对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是否清晰。而“产权是个人和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们使所有者能够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或承担在这些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与亏损”。[2]不过,这种基于产权而衍生的一系列环境治理手段,已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如William Mitchell和Randy Simmonms所言,环境难题应当更多地被理解为政府划定私有权的失败,而不是私人利润追逐的失败。[3]在经济理性主义中,政府也是作为类似于一种经济个体的集合而存在的,公民是明显缺失的,集中关注的是消费者。这就在本质上承认了污染权是可以交易的,事实上也就践踏了基本的环境人权。
其次,经济理性主义向环境政策实践扩散的速度极其缓慢。就制度创设而言,经济理性主义的影响力远远落后于行政理性主义,同时经济理性主义关于市场取向的政策工具论点植根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它与现实世界是大不相同的。[4]这就造成经济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市场自决型治理策略往往难以解决环境问题,反而还会加重治理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理性主义机械式地关注理性生产者与消费者,而忽略公民的存在。正如安德鲁·多布森所认为的那样,经济激励本身不太会导致一个可持续社会所要求的实质性的和多方面的行为变化。[5]并且这种激励行为往往会削弱环境领域中的公民权,其只看重生产者与消费者偏好,而忽略公民偏好。事实上,公民偏好往往与生产者与消费者偏好存在显著的差异。
再者,市场机制下的经济激励措施往往会导致一种集中化的结果。因为只要社会中存在着等级,那么经济财富的集中也总是与政治、军事等权力集中在精英集团手中一样具有伴生性,并且这种集中性往往还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恰恰也就是资源禀赋日益分化的源头。同时,经济理性主义所关涉的“理性”也将导致非常恶劣的市场效果,就环境事务而言,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理性自我主义者,那么,公共物品将总是被滥用,污染者将继续制造外部性,而政府将绝对不可能力挽狂澜。显而易见,经济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对环境事务的应对是不合适的。[6]经济理性主义视野中的理想产权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对环境问题的治理缺乏充分的治理性,而徒具破坏性。尤其是当这种经济理性与地方政府、企业集团或者其他行动者结合起来时,其破坏力是相当大的。
最后,需要反思的是,在亚当·斯密阐述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时,他认为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和习俗都会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对个体行为进行制约。这种从前工业社会或曰前资本主义时代继承而来的社会道德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遗憾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当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的信条,那些社会价值与伦理规范也就失去了规约的能力。在疯狂的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驱使下,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严重畸形。尽管我们不能浪漫地、不切实际地幻想前工业社会时代的道德高度,但是却不得不展开对工业文明体系的反思。因为只有对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予以适当的反思与追问,才可能寻找到绿色经济、生态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价值观的调节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组织的调节,更有赖于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和调试。因而,在市场机制作用之下,如何扭转市场经济行为的非道德化,为可持续发展与道德经济提供必要的、宽泛的自然观,继而来调和市场社会关系,就意味着一场旨在改善社会活动与政治体系的自组织化运动的开展,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治理模式有汲取国家机制与市场机制教训,并予以改善的责任与义务。
二、行政干预主义与政府主导策略的反思
行政理性主义强调专家而不是公民或生产者/消费者在社会问题解决中的角色,也强调等级制而非平等或竞争的社会关系的作用。[4]在行政理性主义视野中,环境事务中的公共利益的发现和应用本身往往成为一种技术性的过程。行政理性主义将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现状视为理所当然。在不改变现行结构的条件下,它利用结合进官僚制系统并被公共利益所激发的科技专长来解决环境问题。[4]而官僚制是20世纪人类社会组织的超级理性形式,借助官僚化组织而提高的社会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7]因此理性主义往往是与官僚制相吻合的,“行政理性主义”也就意味着基于专家意见的等级制,存在着集中于顶点的权力和知识。但是,任何复杂性的难题都会向这种中央集权提出挑战:所有人——包括专家,都不可能做到对一个议题的各个方面都有足够的了解。正如卡尔·波普尔和冯·哈耶克所论证的,知识总是分散和零碎的。而行政理性主义所具有的封闭性的、层级性的风格,采取一种简单化的、以命令与控制为主的行政行为来实现治理目标,往往难以有效地实现信息的整合。
在面对具体现实环境问题时,政府主导型策略具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环境治理效果的可预期性与可确定性。由于政府行为的强制性,因而其被施予的对象必须严格服从相应制度规制,从而有助于环境目标的确定。二是有利于处理突发性的环境事件。突发性的环境事件往往具有紧迫性与扩散性,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当会引发更大范围的不稳定事件,因此由政府主导通过便捷的行政行为来协调环境矛盾,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三是公共服务的优势。良好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在提供此类公共产品时具有先天性优势。政府直控型环境政策有其合理性和实际效益,它的优势领域是那些公共性和总体性强、需要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事务,即在创造和维护人与人就环境权益进行合理交易所需的“秩序”方面。[8]
然而由于信息障碍、腐败、寻租以及官员个体行政能力差异等方面因素的存在,环境治理领域中也存在着政府失灵。政府主导型策略不可避免的具有以下缺陷:一是政府依靠威权主义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实施对环境事务的管理,政府主导行为造成了社会的不足;二是政府管理带有强烈的道德主义特征,由于距离悖论的存在,公众总是会倾向于认为更高级的官员拥有更高的“善”与“德”,从而对中央政府抱有并不现实的期待。在这一导向下,政府干预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如政府行政暴力的滥用、对既有正式与非正式规则的践踏等。
政府主导型策略无法回避权力集中化趋势。“行政主导的政治传统造就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结构和行政化法律形态,不是权利制衡权力,而是权力支配权利,法律不但不具有制衡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的法治功能,反而成为侵害公民权的工具。整个社会对行政权的依赖,导致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的缺失。”[9]在环境治理实践过程中,“即使地方政府更能回应民主参与,而集权的歪曲效果反使国家政府看起来似乎比地方政府更能对环境问题做出反应。”[10]这种效应的存在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催化权力的集中化,最终必然酿成治理体系内部熵值效应的极大化,致使权力系统有效性下降并出现紊乱化特征。权力集中和民主的削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权力如果持续性地集中,必然导致民主的削弱;反之,民主的削弱也催化了权力的集中。在环境事务领域,一方面,无穷地追求权力必然导致权力主体对人文关怀、对生态意识的漠视;另一方面,集权化的趋势往往会使民众致力于保护与复原环境的仁义之举失去用武之地。在现实中所呈现出来的“行政国家”现象,意味着“权力集中构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构,这个历史过程以等级制社会结构的确立为起点,蕴涵了人对人、人对自然进行统治的意识形态”。[11]
在这种行政国家现象的视域中,国家往往遭到“执行赤字”的质疑,即立法与高层执行决定宣称要达到的和现实生活中实际达到的之间的一个巨大鸿沟。[12]一个有助于解释行政理性主义下“执行赤字”的直观理由是对政策制定顺从的难题。这种顺从体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最基层官员必须遵循上级的期望;第二,排污者、开发者和资源使用者必须遵从行政机构发出的指示。中央制定的政策对于最基层的官僚制所处的当地环境并不敏感,因此作为环境治理最大责任主体的政府也往往是自然环境最大的破坏者,其治理责任与破坏行为的距离在实践进程中展示为行政主导策略下的“执行赤字”问题。
三、民主实用主义与社区治理困顿的检视
相对于市场自决型而言,社区治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对自然生态的道德性关怀。在社区内,环境资源是可贵的、珍贵的,而不是用金钱衡量的。它的价值体现为人们对它的珍惜而不是无度的耗用上。社区与环境可以被看成是一对“互惠的伙伴”,一方面社区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另一方面,环境也因此成为社区形成的最重要的促成因素之一。相对于政府主导而言,社区治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参与民主的诉求。参与式民主体现在民众可以更大程度地进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范畴,在那些传统的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能范围之内的事情上影响政策的制定、参与政策的执行等等。伴随社区治理的拓展,当社区公众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普通社区居民可以享有必要的“自卫”权力。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共权利的彰显,市民社会的发展为社区自组织行为提供了施展的平台。社区“自组织”的机理就在于,在社区利益共同体内居民之间进行自主合作,通过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来实现持久性的共同利益,有效地保护社区的生态环境。社区治理相较于市场治理与政府主导的策略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优势,不过该优势之实现仰赖于以下四项基本条件:一是社区自主治理的规模必须足够小。社区规模的大小决定着行动者行为策略的偏好。可以想象如果规模过于庞大,那么基于传统社区而来的经验也就失去了效力,其约束群体边界过于宽广,也就失去了规约能力;二是社区内部的个体界限必须清晰。只有清晰的界限才能实现对社区成员身份的全面描绘,社区成员会倾向于选择信任与合作行为,从而催生自发秩序的产生;三是互动行为的可重复性。解决囚徒困境的关键,就在于多次重复博弈行为。倘若是一次性博弈,且该博弈行为不可重复,那么必然滋生投机行为。只有当人们知道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需要与他人继续交往时,才会考虑自己的名声好坏;四是必须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存在。任何一种合作化行为,其先决条件都是需要一套社区群体成员都奉行的基本规范。
在看到其优点之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社区治理也面临着许多局限性。首先,社区治理往往缺乏必要的透明性。通过社区内个人间的反复交往而发展起来的非正式规范,必然缺乏透明度,在社区边界之外的人看来尤其如此。这种封闭性往往会破坏信任与合作的发展,使得社区外部成员难以融入该社区。而在法治环境下所形成的正式性规范或制度约束则容易实现更大范围的信任与合作;其次,缺乏透明性的体系难以保证权力运行的公正性。在许多传统社区,其成员接受的许多内部规范未必符合公正性,这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往往反映出一个群体的能力,通过其丰富的财富、权力、文化吸收力、智能或赤裸裸的暴力与威逼,去支配另一个群体,必然导致公正性的缺失。这种状况自然是与封闭性的环境密不可分的;再者,社区自主治理制度框架下容易滋生错误选择的持续性。在社区中个体行为选择与组织的选择往往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惯性,即便是一种错误性的选择,也会持续性地发生;最后,自主治理框架结构最终往往被等级制所取代。自主治理的框架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组合的形式,但是这种组织化的方式在事实上往往会发展成为等级制的样态。尽管我们在市民社会与网络治理的引导下,希望实现自治与他治的同构,希望“中心-边缘”结构的消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等级制仍然是组织形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我们不能认为网络和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不存在网络的地方,等级制度就是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其二,一个组织要实现其目标,等级制度往往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三,人们天生就喜欢以等级制形式将自己组织起来。”[13]
社区自治局限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民主实用主义的取向。环顾当今世界,我们会发现,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国家都是民主实用主义最普遍的国家。然而它也面临极大的困局,那就是政治权力的天然性存在和社会民主存量的稀缺。实际情况往往是,那些经济资源雄厚的利益团体极力使政策辩论和决策制定过程的结果偏向有利于它们的方向。[14]因此这种民主文化的结果,往往与民主与公正无关。而现实市民社会发展的羸弱与生态公民权的缺失,使社区自组织化行为的基本条件难以满足。社区政治理性的期待往往与行政理性主义的期许存在难以填平的鸿沟,从而造成政治理性上的尴尬。诚如德赖泽克所言,“民主实用主义承认公民是基本的实体和公民间平等的自然的关系。但这种平等的理性辩论的形象被权力和策略的广泛使用和政府维持经济信心的主导性需要所严重扭曲了。”[4]因此,社区治理策略也往往难逃治理失灵的窘境。
[1][英]简·汉考克.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M].李隼,译.重庆出版社,2007.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0.
[3]William C.Mitchell and Randy T.Simmonms.Beyond Politics:Markets,Welfare,and the Failure of Bureaucracy[M].Boulder,Colo.:Westview,1994.
[4][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蔺学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5]And rewDobson.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6]John S.Dryzek.“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 alpolitical economy:The search for homo ecologicus?”[M].New Political Economy,1.1996.
[7]H.H.Gerth and Mills C.Wright.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8.
[8]夏光.论环境治道变革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
[9]周祖成.论行政主导对我国走向法治的影响[J].社会主义研究,2002,(6).
[10][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1][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当代多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M].李宏,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12]Albert Weale.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13][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刘榜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George A,Gonz le.Corporate Pover and the Environm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Environment Policy[M].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1.
D035
A
1002-7408(2012)08-0050-03
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KYF-2011-T57)。
杨华锋(1982-),男,山东冠县人,管理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理论与政府创新。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