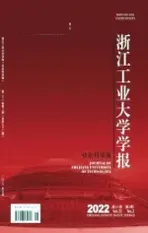协商民主理论述评
2012-08-15王河江陈国营
王河江,陈国营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杭州310024)
协商民主理论述评
王河江,陈国营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杭州310024)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代议制民主有背离民主本质的倾向和局限。因此,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协商民主在西方兴起。协商民主强调平等、自由、理性地沟通和对话,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发展和丰富了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协商民主对于完善中国政治协商、促进基层民主、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诸多启示价值。但要注意的是,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在中国既要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选举民主,实现二者的互促互进。
协商民主;代议制民主;民主政治
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民主是极其重要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在西方兴起,逐渐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民主理论和政治实践。探究西方协商民主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脉络与主张及其现实实践,借鉴其合理的成分,并结合中国的政治协商传统和政治制度环境,对于完善中国的政治协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推进基层民主,提高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进一步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协商民主的历史与现实
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态,协商民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探究协商民主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回顾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协商民主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民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时代。“民主理论是由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个论说主流形成的”[1]。雅典民主是一种公民直接参与的直接民主,被视为现代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历史源头。随着国家规模和人口数量的扩大,分工逐步细化,公民利益与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直接民主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最终,公民参与的直接民主没有落下好的名声并走向了衰落。18、19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大众参与和精英统治相结合的产物,“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利上,公民投完票后便退居一旁,国家事务任由‘代表’们决定,对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是间接的”[2]。政治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实际权力主要由公民选举产生,并以公民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政治家和议员)来行使。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间接民主,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取向的民主、精英主义民主或保护性民主。这种民主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地位开始确立起来,也长期被视为民主的正统。
但是,当代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取向的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罗伯特·古丁等人指出,“如果民主制度仅仅允许公民为远离现实的政治机构选举代表,以及保证这些公民不受政治滥用权力的影响,那么民主制度就是一套空洞的制度。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意味着人们能够作为公民参与在所有的主要机构中行动”[3]。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自由主义取向的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的理论与现实的不满,新的民主形态——协商民主被提出来,并迅速得到极大的关注而开始复兴。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最早于1980年提出了协商民主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分别于1987年和1989年阐述了协商民主理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学者纷纷积极倡导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协商民主被视为西方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主理论的核心”[4]。
协商民主对代议制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官僚主义、精英的傲慢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公民主要通过定期选举参与政治,政治权力和决策权主要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政治家行使,政策执行权主要由常任的文官行使。定期的选举和选举中的政治操纵,政治家、议员的承诺常常跳票,主权在民只是在选举层面得到体现,公民实际上很难对政治和公共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同时,随着参与人口规模的扩大,单个个人的选票显得无足轻重,加大部分公民不参与政治的倾向,这既恶化了政治不平等,也加剧精英对公民个体的轻视。二是由于性别、种族和政治的复杂性、信息获取等方面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政治生活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抽象概念上的公民权利平等,但代议制民主和选举民主存在大量事实的不平等。如种族歧视从法律上已被废除,但种族身份问题依然阻碍政治的平等。现代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日趋复杂,政治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政治信息的不对称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生活的不平等。三是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文化导致无法进行真实的对话和沟通。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更趋于多元化。基于性别、种族、信仰、阶层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现有的代议制民主体制、媒介体制使得不同的群体更难以进行真实、有效的沟通和对话,反而可能进一步固化各自的观点并扩大分歧。四是代议制民主过于局限于选举民主和政治过程宏观层面带来的局限。代议制民主主要限于选举等政治过程,对行政民主和公共政策民主缺乏足够的重视。在现代国家,三权分立中的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急剧膨胀,而代议制民主对公民参与行政和政策过程不重视的局限显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主要关注的是宏观的政治领域,对于社区等层面的公共事务和微观层面的民主重视不够,而社区等微观的民主与公民的生活却又最直接相关。
代议制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政治和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而这种同意通过定期的选举进行表达,民主被视为一种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统治者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民主过程中的人——普通公民和政治人物——都是基于自利动机采取行动,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达成公共决策。
协商民主对民主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代议制民主的消极自由和消极的公民资格进行了批判,更加强调平等,它试图复兴古老的激进民主——直接民主,只是其方式主要是诉诸于公共讨论、协商、推理和包容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协商民主中的参与者不是基于理性自利的计算,而是在协商过程中追求和达成“共同的善”(common good),关注的侧重点不是“谁来统治”的问题而是“如何统治”的问题,或者说不是“谁来讨论”的问题,而是“如何讨论”的问题。现代丰富的公民社团生活、网络媒体、公共论坛、公共舆论以及超越国家层面的欧盟协商实践为民主协商提供了现实的制度、基础设施、实践活动等呈现形式。
二、协商民主理论的表述与评价
英文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国内有许多不同的译法和解读,诸如协商民主、审议民主、商议民主等,总计竟有10种之多[5]。西方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对协商民主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总结起来,关于何谓协商民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观点:
一是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机制和方式。古特曼、汤普逊等认为,协商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各方的意见在公共论坛中互相交流,使各方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6]。从决策机制和方式的角度是协商民主最为普遍的观点,它认为所有受到公共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自由、平等地参与决策过程,通过自由的交流、对话和沟通,弥合歧见,相互理解和谅解,最终达成共识,实现决策民主。
二是将协商民主看成是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库克认为,“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7]。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8]。协商民主是集体协商、沟通和对话,公民能够有效参与其中,并对公民的需求作出及时的回应,实现民主的治理。
三是将协商民主视为社团的自主治理模式。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社团。这种社团的价值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仅仅是可以根据某方面的平等或公正价值来解释的衍生性理想”[9]。组织中的成员都有其独立自身的偏好、信念和信仰,并且大家彼此相信,具有理性协商和交流的意愿和能力,协商程序是组织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协商民主是社团组织的一种自治性协商和自我治理方式。
四是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话语民主。约翰· S·德雷泽克等人认为协商民主就是话语民主[4]。协商强调在公共领域、公共生活中的普通公民能够平等参与其中,进行理性、理想的话语交流。哈贝马斯为此提出了“公共领域”的理论,反对精英的自言自语和自娱自乐,强调对话的真实性、有效性和理性。协商民主是政治个体发展的对话本质的政治产物,通过构建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参与,彰显出民主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讨论的社会。
在研究取向上,主要包括两种取向:一是将协商民主并入共和主义的民主形式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形式,认为协商民主是在自由、平等的宪政制度框架中,通过公民间协商讨论参与决策、达成共识或一致的民主形式;另一种取向是将协商民主视为与选举投票的民主形式相并列,但协商民主并非简单的决策前的投票过程,而是协商讨论下的理性思辨过程,是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统一[10]。
作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和模式,协商民主被认为可以促进政治信任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高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化水平,推动积极的公民权。库克认为,支持协商民主的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缘由:(1)公共协商过程的教育作用,协商过程对公民具有有益的教育作用;(2)公共协商过程形成具有共同体的力量;(3)公共协商程序能够促进公正的民主结果;(4)公共协商结果能建设性地促进民主结果的实践理性;(5)协商民主表述的政治理想与“我们是谁”具有一致性[11]。
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阐述协商民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协商民主。概括起来,协商民主就是指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和审议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政治过程和公共决策,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通过包容性、理性和真诚的协商,在多元复杂的公共生活中达成共识,实现公共利益。协商民主回答的是具有差异性和不同利益的公民能否是某种意义上确认“共同的善”,核心任务是要发现和构思公共决策的方法,通过公开的集体讨论来解决集体选择的问题。协商的前提是承认不同公民之间存在合理的差异,公民社会是多元化的,是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基于自由、平等、公开原则进行真诚的对话交流,自由地表达意见,愿意倾听并考虑不同的观点,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它是解决冲突和集体问题的实践理性形式,参与者要承担通过合作和寻求公正解决公共问题的责任。
对于西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评判都需要基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背景,将其置于西方民主理论传统和民主理论发展脉络中。协商民主是对西方主流代议制民主和选举民主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的修正而不是取代,试图复兴古典直接民主的积极、能动的公民资格和追求共同的善以及对公共政策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代议制民主在现代社会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包括代议制民主在内的西方宪政框架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实践空间。
三、协商民主的未来与中国特色
产生于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当代西方重要的一种民主理论。中国建国后的宏观政治层面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加之地方诸如温岭民主恳谈会等基层的民主实践,使得协商民主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
国内外学者认为协商民主对中国发展民主是可能的较好选择。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发展协商民主与现阶段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政治社会现实相适应。詹姆斯·博曼认为,“许多国家,也许还包括中国,都处于这种创造性的民主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是各种层面的要求,而且这样做也要求公民在新背景中创造新的试验性协商实践和形式”[12]。
在国内,陈剩勇认为,鉴于作为国家或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同时缺乏民主传统,中国现阶段引入和倡导协商民主,可避免动员型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弊端,激发良好的意见表述,提升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并详细分析了协商民主形式在浙江省基层的五种实践形式[6]。林尚立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偏好民主的效率而不是政治多元化和竞争性民主;协商民主满足和符合中国民主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和现实条件来看,从民主的程序与过程入手更为有效[13]。朱勤军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多元化利益结构、公民和社会拥有的越来越强大的社会资源、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与信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分别提供了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体制资源、文化背景和科学基础[14]。燕继荣认为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参与性以及不同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协商,而不仅仅局限于自由选举,深化和拓展了对民主的认识[15]。何包钢认为协商民主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是中国人可以发展和改进地方民主的一个新领域;在有些情况下,协商制度初始动机可能是用来增强专制统治,但随着协商制度的不断实践,开始的限制可能会被突破,导致结构性变化,为地方民主开辟一条道路[16]。
探讨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适应性及未来,挖掘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我们需要将西方的协商民主和中国的政治协商进行比较,并结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实际需要。西方协商民主是建立在西方比较成熟的宪政制度和框架基础之上的一种民主模式,强调的是普通公民参与政治和决策的自由、平等地位,进行真实、诚恳的理性沟通、讨论和对话,以达成共识,是对西方古希腊直接民主的一种复兴,其目的是克服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提高公民参与和决策的合法性。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不是在一种竞争性的选举代议制民主下展开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一种民主制度,各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协商和决策的地位不是对等的。政治协商是协商,而不是决策;协商是精英、小范围内的协商,而不是普通公民可以参与其中的决策协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保障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由此可知,西方协商民主和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框架完全不同,发展的理论历史资源、兴起的缘由、兴趣点和关切点迥异,发展阶段不同。但西方协商民主对于中国发展民主政治依然具有诸多启示价值,而且中国的协商政治制度对于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形态和可能性。西方提出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和选举民主的修正、补充和完善,是对民主本质的巩固、深化和拓展。
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没有照搬西方多元政党政治和竞争性选举的制度框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民主协商制度的基础上展开的。就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包括两个层面:高层的政治协商和基层协商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制度安排。研究和发展协商民主,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对话、沟通,培育包容、互信、理性和责任精神,发展党内民主和民主政治,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在基层公共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吸纳不同阶层、群体和大众的广泛参与,加强自由交流、沟通和对话,可以更好地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畅通参与渠道,化解利益矛盾,推进基层民主,提高地方公共治理绩效。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理论,也是一种政治实践,已经取得普世的价值地位。协商民主是在对主流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契合了新的历史背景和对民主本质的时代呼唤,与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脉络相衔接。协商民主要求公民不仅有参与政治过程和公共生活的自由,而且应该有能力、能够确实参与其中,实质性地影响公共政策,在多元的社会中通过协商、对话、讨论和审议,达成共识,实现公共利益。协商民主唤起了人们对于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公民自治、公共生活以及践行“共同的善”的理想。但在一个多元主义事实不断强化,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们是否能够并有意愿进行理性沟通和协商,需要打一个问号。就此而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协商民主并不能治愈西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弊病,而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修补。
对中国而言,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协商民主是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发展协商民主可以推进民主实践,提高参与意识,增进公共理性,培育民主精神,促进互利互惠互信和公民参与网络的发育。通过发展协商民主,可以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同时,中国在发展协商民主过程中,要克服现民主协商局限于小范围的精英主义取向弊端,尤其在高层政治,促进公民协商的平等,大力发展公民社团,畅通公共舆论表达和公共论坛渠道。尤其要注意的是,发展协商民主并非意味着要取代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否则协商民主会走入死胡同。相反,中国现有的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没有健全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将缺乏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实践支撑基础。要通过选举民主来发展协商民主;通过协商民主来推动选举民主,用民主的方法救治民主的弊端,用民主的方法发展民主,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民主政治。
[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3.
[2]陈国营.公民参与研究述评:理论演变与焦点转移[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1):49-55.
[3]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科学新手册(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2006.686.
[4]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
[5]杨守涛.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22-27.
[6]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J].浙江社会科学,2005,(1):28-32.
[7]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39.15.
[8]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3.
[9]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50.
[10]韩东梅.西方协商民主的概念与特征分析[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09,(1):35-39
[11]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5-25.
[12]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4.
[13]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4):19-25.
[14]朱勤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探析[J].政治学研究,2004,(3):58-67.
[15]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6,(6):28-31.
[16]何包钢.中国协商民主制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13-21.
On the Review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ANG He-jiang,CHEN Guo-ying
(Zhijiang College,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4,Chin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s the mainstream of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and practice,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has a deviation from the democratic nature of the tendencies.Therefore,as a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he west has been rising.Deliberative democracy emphasizes equality,freedom,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consensus and collective action,and it develops and enrich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Given the reality of China’s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socio-economic reality,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s much inspiration value to improve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and promote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But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 complement and perfection to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democracy,but not a substitute;otherwise you will misunderstand.It is necessary to vigorously develop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further improve electoral democracy in China,thus promoting each other.
deliberative democracy;representative democracy;democratic politics
book=6,ebook=61
D0-02
A
1006-4303(2012)02-0160-05
(责任编辑:金一超)
2012-04-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IA810025)、(09YJC810042)
王河江(1962-),男,江苏盐城人,教授,从事政策分析研究;陈国营(1977-),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博士,从事网络治理与制度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