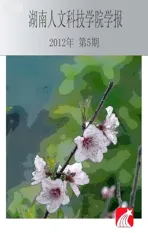男性的权威与女性的异化
——读《马桥词典》
2012-04-07曾雪阳
曾雪阳
(海南省委党校 文史教研部,海南 海口571100)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1]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使得二者在进化中逐渐变为女性从外部的空间转移到内部的空间,经济活动的范围缩小。男性却是相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得更大。经济活动空间的大小,也就是生存技能的大小的无形标准。经济地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地位,妇女沦为家庭的奴隶,男女不平等现象也随之产生,性别压迫也随之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柔弱,以及随之而来的强权下的奴化,而奴化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于是,男性霸权让女性奴化而最终导致女性异化的因果链,形成了一个导致女性主体意识丧失、地位沦落的恶性循环。在韩少功先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反反复复地刻画和展现了这样一群异化了的女性形象。
一 价值取向的异化
女性在马桥是男人们歇息时最感兴趣的谈资,往往与“吃”联系在一起。女人的婚姻是与一口锅紧密联系在一起,婚姻的存续并不是由情感来维系,而是做饭的“锅”。“锅”在婚姻在,“锅”走婚姻散,简单而脆弱得经不起任何冲撞,却又被马桥男女天经地义地践行着。女性对男人世界的价值评判标准之顺从与屈服甚至荒诞到一群闹洞房的男子的喜好就可以左右一桩婚姻。女性在马桥是卑贱而廉价的。
另外,男性一面为女性的美着迷,称之为“诱惑的象征”,一面又视女性为弱者,“不吉的象征”[2]。这种由男权文化而定的变态和畸形的“审美”感受,使马桥有了很多与女性相关的忌讳。词条“不和气”就是“漂亮”的避讳说法,这种异化里隐藏着一种马桥人心照不宣的结论:“美是一种邪恶,好是一种危险,美好之物必会带来纷争和仇恨,带来不和气。”在马桥男人看来,女人最好的是屁股大能生娃崽,再就是满足一下生理需求,除此,就不要再去惹她们了。
当思想和话语的条款是由男人设定时,女人们永远也不会轻松自如。所以,不懂得掩饰自己反而卓尔不群的漂亮女人是注定不会有好前途的,比如聪明、美丽、仗义的铁香就客死他乡,死无完尸。
在生存资料是第一追求的环境中,寻求劳动力就是第一需要。而漂亮女人的脂粉气和柔弱的体质就是劳动高效率的制约因素,漂亮女人作为劳动力的缺陷显而易见。所以,年轻美貌、娇柔多情的铁香在马桥人眼里并没有多大价值,当然在她丈夫本义的眼里更是如此,只当是属于他的一件摆设而已,拥有或失去都不是太在意。
贫困的马桥需要劳动力,而异化了的女性正符合了需要。她们是在男性无法完成社会要求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完成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诊释之后,她的性别诊释却在劳动中悄无声息地融化了。在这里,生育是女人最重要的用处,比贞洁的道德操守重要得多。男人选择一个具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是择偶的第一要务,在这一点上与选择一头身体健康、繁殖能力强的母牛或母猪意义差别不大。因此,会唱戏的长得漂亮的水水在马桥在丈夫志煌的眼里并不会比其他村妇高贵:从劳动力的价值角度来衡量,从小远离农活的唱戏的水水在干练与利索上也许远不及一个在农活中锻造出来的膀粗腰圆的脸黑如炭的却样样农活都在行的女人;同时唱戏的容貌与身段,从生殖能力角度衡量,也不是最佳选择,相反只会引来丈夫对水水不忠的猜测。当水水因为失去唯一的儿子过度伤悲而罹患精神疾病,终于变得毫无价值,所以自然而然地被丈夫遗弃。
二 服饰的异化
男女两性生理特征有明显的区别,服装是区别和规范男女行为的工具之一。服饰的审美功能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女性的服饰要体现女性柔美的特征。
而在马桥,女性不是通过服饰来展现女性的柔美,而是借助服饰来掩盖女性的特征。她们“总是把胸束得平平的,把腿夹得紧紧的,目光总是怯怯低垂落向檐阶或小草,对女人的身分深感恐慌或惭愧。”“她们很少有干净的脸和手,很少有鲜艳的色彩,总是藏在男性化的着装里,用肥大的大统裤或者僵硬粗糙的棉袄,掩盖自己女性的线条。”女人穿着清一色的平淡、死气沉沉。连女干部来马桥也将身体裹在旧军装里,黑长发藏在棉帽子里,为的是让自己干练得像男人,显得有男人一样的威力。马桥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所以会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把有“男性气质”当成是一种荣耀。女性不仅要掩饰其女性特征,而且对于个人所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男女服饰的混淆,也是女性独立人格的丧失。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物质的匮乏,女人必须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在此种生存条件下,马桥女人往往遗忘与忽略了自我的性别特征,一味关注她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自然成员应具备的特征、应担负的责任。她们因过分在乎男人们的标准而拼命去适应这个标准,在“削足适履”中丧失了女性特征。
水水也是一个异化的典型。婚前的水水“戏唱得好”“貌艺双全”,婚后却“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脸上黑花花的,大襟口没什么时候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一个匆忙起床的样子”。一个有名的花旦不可能没有美与丑、干净与邋遢的判断标准的,那么,她何以变得如此落魄却浑然不觉呢?当然是马桥独特的审美判断,让婚后的水水自觉地以一个依附于丈夫的劳动力同时兼生育工具而存在,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女人而存在。
三 语言的异化
语言具有社会性,社会对语言存在着制约,语言的发展、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对社会的反作用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制约。《马桥词典》从女性语言的失落方面为读者展现了处在马桥底层的女人,如何主动隐藏了女性的特点,在这个男权社会中扮演着与男性同样的角色。比如在“△煞”这一词条中,年轻的女干部万部长为了在男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威严和展现自己的“格”,很少出声说话,顶多点点头,笑一笑,大多情况下将“脸板得木瓜一样”,需要说话时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发出简短的指示。这也是借助代表男性权威的话语特点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另外,在“小哥”的词条中,作者讲到马桥的流行语之中缺乏女性的亲系称谓,称呼女性多半是在男性称谓之前冠以一个“小”字,例如“小哥”指姐姐,“小弟”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指姑姑,“小舅”指姨妈,如此等等。女性的无名化毋宁说是女性的男名化,女性性别的被抹去,势必会对其性心理甚至性生理产生影响,她们“大多数习惯于粗门大嗓”,甚至“打架骂娘”,她们渴望像男人一样生活,一样主宰“她们”,一样没有恼人的“例假”。因为男人的世界中没有为女人的月经留出应有的位置,这在马桥世界是毫无用处、毫无意义的麻烦。在马桥的价值尺度中,也没有专门为女人的特殊性留出位置,女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像男人一样去评判,甚至完全遗忘自我。
四 劳动的异化
在“马桥”,从劳动方式及行为方式上,女性也同样被异化着。男女有着生理上的明显区别。男性在力量上是优越于女性的,所以才有了男耕女织的农业传统。耕地,干农活,是对力量的挑战:织布,整理家务,是对耐心的考验。这是由生理特征而形成的经济分工。女性如果为了证明男人能干的事自己也能干,要跟男性争个高低,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只要女人还在挣扎着去蜕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造者。”[3]只要女人还在为男女之间的差异而自惭形秽,并奋力挣扎着去扮演男人的角色,那她将永远不能挣脱男权的樊篱。
在《马桥词典》“老表”这一词条中,作者写到在人民公社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大家都饿得眼珠发绿,但还要踏着冰雪去修水库,“妇女也被迫光着上身,奶子吊吊地担土,配合着红旗、锣鼓、标语牌以示不畏严寒的革命干劲。”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鼓舞人心的但也是酸楚至极的一段历史的回眸,这是男女生理与身体差异被严重忽视的体现。这也是对女性极大地伤害。在这里,妇女走出家庭,不是以女性的身份;妇女追求两性的平等,不是以自身为参照物,而是在以女性突破自身的生理限制,麻木追求两性所谓的体力平衡下的平等,以女性在他性为标准的情况下的“解放”。
女性参加并不适合自己的劳动,异化自己的劳动,只为了从狭小的空间里找到自己可以自由呼吸的,找到为妇女解放可借的理由。在劳动中透支体力,“丧失了触感,羞涩和矜持全部抽象为气喘吁吁”,使性别在劳动中消失。
劳动的异化在马桥世界还体现在马桥人对“懒”的不同诠释上。在马桥,“懒”是男人的“一枚勋章,被他们竞相抢夺,往自己胸前佩戴”,他们为自己的“懒”而炫耀、自豪,认为那是强者的证明、是强者的特权;但是却深恶痛绝女人的“懒”,女人的不懒,才是保证男人“懒”的源泉。扶老携幼的责任毫无疑问的由“懒”男人的女人承担,女人的地位和价值仅仅如此而已。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1.
[2]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阿图塞.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127-186.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李掖平.现代作家新论.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