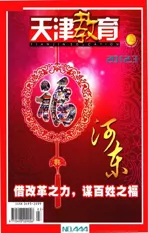在“天堂”读书——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2012-02-15朱永新
■朱永新
1978年年初,我背着一个自制的小木箱,从苏北的一个小镇,来到了苏州,来到了这所当时叫做江苏师范学院的学校。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个城市、这所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读的是政史系,100多人的班。不久,政史系又分为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两个系,但是,班上的同学已经感情深笃,不再分离。同学中许多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经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地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经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中学基本上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一段时间疯狂地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英语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试着翻译。记得当时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地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从此不再惧怕学习外语,后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个高干子弟,他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但是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书,与图书馆的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给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就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是,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就是从那时养成的。今天,我成为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全民阅读的推动者,应该说与当时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记得当时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并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
那个时候,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范小青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文系有个才女写小说了。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的荀德麟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当然,大部分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从此喜欢上了读诗,喜欢诗意与激情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还是个狂热的体育运动爱好者。且不说中学时就专门拜师学习武术,进了大学,越发对体育运动痴迷,开始效仿某位伟人,把体育运动变成每天的必修课。清晨,先是迎着晨曦在400米的跑道上跑10圈,然后回到宿舍洗一个冷水澡。神清气爽,然后去教室自习。在这样的状态下背外语单词,学习的效率特别高。傍晚,一般是与同学们一起打篮球,水平很臭但是乐此不疲。
我的运动水平很一般,但是每天早晨的跑步还是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连说带拽把我拖进了学校的长跑队。后来我才知道,老师看重的其实是我的意志力。
其实,体育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体现了人类意志力的能量。无论是课堂上的训练,还是竞技场上的比赛,它都要求学生或运动员挑战自己的体能、挑战自己的过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要求学生或运动员咬紧牙关,与对手抗衡,坚持到最后一刻。“两强相遇勇者胜”,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往往是意志力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一段日子的磨砺,让耐心与坚韧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一点点充盈。慢慢地从一个懵懂的农村孩子,开始向往新的生活,思考未来的天空。
这个时候,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深造。一下子几百名学生报名。我有幸过关斩将,成为其中一员。
在新的大学,我又交到了新的朋友,袁振国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堪称我学术朋友中的“青梅竹马”。
振国比我小一岁,应该是我的老弟了。我们在大学三年级分别从苏州和扬州来到上海师范大学,他瘦长的个子与我肥胖的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朋友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不仅合作写文章,而且可以搭伴说相声。
振国最初给大家的印象是扬州才子。到底是中文系出身,那优美的文笔让我们羡慕不已。学习的时间不长,他的一篇关于灵感研究的论文就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我不太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于是,有了我们频繁的讨论和“争吵”,有了我的商榷文章。而我们的友谊,也就在这讨论和“争吵”中萌芽与成长。
那时,我们可以说是无所畏惧、豪气满怀。记得有一次,我对振国说,总有一天,我们要让自己的著作像弗洛伊德的著作一样,走进每个人的书架!于是,我们疯狂地读书,疯狂地写作。我们以两个人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和《南京日报》等报刊开设了专栏,我们在《心理学探新》、《苏州大学学报》等刊物联合发表论文,我们的第一本书《心理世界窥探》也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当时我们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为能赶上振国这位中文系的才子,我也只好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精雕细琢,用心打磨。通过一系列“小文章”的撰写,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现在很多朋友说喜欢我的文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训练。
我和振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约定:两家一起寄情于山水,把自己交付给大自然。可是这些年来,我们都把自己交付给了教育,寄情于工作,不知振国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我的确是幸运的,就这样顺利地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准教师”。我更大的幸运是人生路上,遇到了那么多授业恩师。
用不着努力地从记忆中去搜寻,一张张慈祥的面庞、一幕幕感人的往事就不断浮现于我眼前、回映在我脑际。
我似乎看到初中时教语文的徐鸣凤老师。在那个并不重视知识的年代,她将藏书一本一本借给我阅读,她对我那双如饥似渴的眼睛所给予的微笑,远远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更美。
我似乎看到高中时教物理的林象云老师。他用那特有的宁波口音,把深奥抽象的物理知识说得那么清晰、那么明白,我不仅学会了“三机一泵”,也把探究自然的兴趣扎根于心中。
我似乎看到大学时教哲学的吴建国教授。一个留学苏联的哲学博士,在他家里评论我的一篇论文,他未在原稿上作任何记号,竟然能将某处的标点、某处的别字、某处的史实、某处的观点解析得淋漓尽致。我从此知道,什么是做学问。
我似乎看到读博士时的沈荣芳教授。为了指导我的论文,经常乘火车到苏州“送教上门”,当我推着自行车和老师在大学校园里边走边谈的时候,我早已忘记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长者。
我似乎看到做博士后研究时的苏东水教授。这位享誉海内外的管理学大师,冒着酷暑,为我的新书《中华管理智慧》撰写前言,为我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写推荐书。
…………
师恩重于山,师情长于江。在我忙中得闲的时候,在我小获成功的时候,在我与学生相聚其乐融融的时候……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他们。
而这一次,我的思绪却“定格”于燕国材教授。
那是1980年9月,我通过考试被选送到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那是“文革”后心理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派出了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当时,一批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已经张开双臂拥抱即将到来的“科学的春天”。其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燕国材先生。
一天,教室里来了一位个子不高但气度不凡的中年人。上课铃一响,他就健步登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八个大字。后来,我们知道,这就是学术界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燕国材教授(我称其为“燕师”)。燕师博学多才,这八个大字就是他倡导的治学方法,激起我们的创造冲动;他反对“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主张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遗产,并身体力行,他的《先秦心理学思想研究》等一批专著先后出版,引发我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激情。他把“创新”作为治学的灵魂,也作为对弟子的期待。后来,他确实用这种精神把我们带进了心理学园地。
燕师1930年12月29日出生在湖南省美丽的桃花源边,17岁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20岁考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是正宗的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的个人专著《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正式出版,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让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离开了心爱的教学岗位,先是劳动改造,再到图书馆搬书。上个世纪80年代初,燕师差不多与我们一起走进了课堂。
他给我们开设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三门课。有一次,他用“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去邻家”开始了他对中国心理史课程的讲授。这句也许不太经典的诗,却激起了一个年轻学子的强烈冲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破译中国人心灵的密码!于是,有了我们师徒间的长期合作,有了中国心理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的第一篇习作《朱熹心理思想研究》被燕师带到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向潘菽、高觉敷教授等大力推荐,很快收录在两位老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文集中。
我的第二篇习作《二程心理思想研究》被燕师推荐到权威核心期刊《心理学报》,很快变成了铅字。
我被推荐破格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纂工作,没想到撰写的条目被出版社编辑作为“样板”条目供其他作者参考,还闹出了责任编辑张人骏教授到苏州大学来寻找“朱老先生”的笑话。
这些,对一个刚刚走上教学科研道路的年轻人来说,是多大的激励!
在燕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第一本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参加了全国心理学史的第一套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第一本辞典的编写工作……可以说,我参与了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的全过程。
后来,我又同燕师合作撰写了一些著作与论文,如《非智力因素与学习》、《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心理学纵横论》、《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学史》、《刘邵〈天才性理〉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等,他从不以先生的口吻教训我,而总是以朋友的方式与我沟通。
后来,燕师又鼓励我独自放飞,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犯罪心理学史、中国管理心理学史,当我有新著出版的时候,当我获得一个个国内外科学研究基金时,他总是为我喝彩、为我加油。
在我所知道的学术前辈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勤奋,60岁以后,他差不多每年至少还要有一部个人专著问世,数十篇论文发表。他不仅用他那四卷本著作奠定了在中国心理学史中的地位,而且在非智力因素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等方面,都独具慧眼、自成一家。
在我的印象中,燕师似乎是不老的,他的心近乎明代李贽所说的“童心”。燕师虽然学富五车,讲演时口若悬河、声音宏亮,在生活中却是一个不太擅长交际的人。他只顾耕耘,不计收获;他淡泊名利,不计得失。这种个性也使他失去了一些本来应当属于他的东西,然而他不在乎,依然乐呵呵地向前走。
燕师已经年过七旬了。本来我和几个同学说好在苏州为他祝寿的,没想到闸北八中的刘京海校长等捷足先登,在上海为他举行了庆祝活动。前年,和他相濡以沫的师母因病去世,燕师在家乡为她购置了墓地,师母的灵魂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安息了,而燕师在哀恸之后又像往常那样默默投入了另一本新著的写作之中。
去年五一节,燕师家乡的一所名校——桃源一中邀我去讲学,我不假思考地应允了,为了那一方水土,为了那恩师之情,也为了拜谒师母之灵。这一去,我也与“桃源”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一年的八月酷暑,温州的“苍南”让我为全市校长作一个报告。为此,他们打了数十次电话,我实在太忙,不敢应承。结果,他们搬来了燕师,要我们师徒同去。于是,我顿时没有了拒绝的勇气。因为,与老师多说几句话、多呆几分钟也正是我所渴求的。与其说我成全了“苍南”,不如说是“苍南”满足了我。
可是,这么多年,燕师从来没有要我做过什么。他给我的是大海,我回报他一滴水的机会都没有。我拿什么报答您?我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