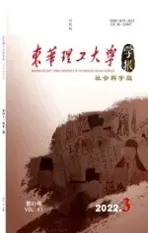元代后期流寓江南杂剧作家作品中的“变奏”现象论略——以《倩女离魂》、《东堂老》为例
2011-08-15王子文
王子文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江西南昌330029)
元代后期流寓江南杂剧作家作品中的“变奏”现象论略
——以《倩女离魂》、《东堂老》为例
王子文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江西南昌330029)
文章以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秦简夫的《东堂老》为例,探求元代后期流寓作家作品中“变奏”现象。突出两个亮点:(1)冲破传统封锁,“幻化”追求真爱;(2)商人形象突围,彰显人性之美。并归纳了流寓与变奏的关系。
流寓;变奏;幻化;突围
“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戏曲史的角度来说,元代杂剧作家流寓江南和北曲南移,都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它不仅至深地影响着南戏和后来明清传奇的发展,而且其自身也发生着许多嬗变”[1]。“南方文学传统的妩媚轻柔风格也开始侵入曲坛,杂剧和散曲的创作表现出‘南方化’的倾向”[2]。元代后期流寓江南的杂剧作家们在既有的题材中重复着老调子,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能否同中求异,呈现新的变奏是他们能够成就不朽的关键之一。传统的老题材,因多人写作而显得“疲软”,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从传统中变奏,才有可能延续杂剧的生命。
就元代后期的杂剧创作总体情况而言,无论是从战斗性、思想性还是舞台性,都难以与前期相媲美,时代嘹亮的战斗强音已经难以找寻,加之战乱的频仍和元廷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以及科举的“梅开二度”,作家们大多有和元廷合作与妥协倾向,很多作品无法避免要代表江南地主阶级利益、愿望,宣传伦理道德的剧作大量出现。
后期虽没有里程碑式的作家和作品产生,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精品的存在,作家如郑光祖、乔吉、宫大用、杨梓、秦简夫等,作品如《倩女离魂》、《东堂老》等。流寓江南确实使作家某方面灵感或经验突出,加之各地方言不断对北杂剧发生影响,在声腔上也不断产生变化,且与南戏的直接交流与竞争,甚至一些杂剧演员兼职演南戏的情况,也使得北调用南腔来演唱(按:笔者拟专门著文论述,此不赘言)而出现新的“变奏”。由于元杂剧北曲传统的唱法已经失传,些许只能从“昆曲化”的元杂剧演唱中得知其遗响之片羽,故而我们这里就从文学性、思想性角度以郑光祖《倩女离魂》、秦简夫《东堂老》为例,探求“变奏”的地方。
1 冲破传统封锁,“幻化”追求真爱
郑光祖《倩女离魂》故事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前贤时彦对其研究不乏大大开拓我们的视野之作,如邵生《郑光祖杂剧中儒士文化的心态剖析》、曾远鸿《论郑光祖杂剧的思想价值》、《郑光祖杂剧艺术成就探微》、马涛《郑光祖在〈倩女离魂〉中对相思之苦的发掘》、王刘纯《郑光祖杂剧文化意蕴心解》等。我们这里从“变奏”的角度来审视剧作本身,作者采用单线条结构方式的同时还运用了“幻化”与写实相结合的结构方法。抒写了一个冲破封建社会各种束缚和封锁,大胆追求自己真爱的具有新思想、新行动的女性。
单线条叙述是指:张倩女和王文举早有婚约,他们初见便一见钟情——王文举辞行、倩女长亭送行——倩女“魂灵出窍”追王生,并与之在京过了三年生活——倩女之身则长病在床——王生高中携倩女(魂)归家,魂身合一,完婚。
“幻化”是“疲软中变奏”的成功尝试,是一种本质的自我深化,它与神仙道化剧中的“点化”有着相当的不同。
作者采用的“幻化”手段,可谓是展现张倩女风风火火追求爱情幸福的新女性特征的最佳手段,不激烈而且很和谐地展现了倩女的少女人性化情怀。这种“幻化”也是使本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幻化”可以理解为对现实困难和痛苦的一种超越。本剧的“幻化”表现为倩女的“魂灵出窍”、婚追文举、人魂生活、魂体合一。
爱情至上,是倩女离魂的出发点和归宿。她的离魂,代表了女性对爱情婚姻的渴望与追求,代表了妇女内在的欲望和感情的力量。倩女深爱王文举,在王文举离去后,便不顾一切地追赶,以至于生活中现实的倩女因相思而成疾、一病不起、魂灵出窍、魂追文举。对此第二折写得比较充分。
【越调·斗鹌鹑】人去阳台,云归楚峡。不争他江渚停舟,几时得门庭过马?悄悄冥冥,潇潇洒洒。我这里踏岸沙,步月华;我觑这万水千山,都只在一时半霎。
【紫花儿序】想倩女心间离恨,赶王生柳外兰舟,似盼张骞天上浮槎。汗溶溶琼珠莹脸,乱松松云髻堆鸦,走的我筋力疲乏。你莫不夜泊秦淮卖酒家?向断桥西下,疏剌剌秋水菰蒲,冷清清明月芦花。
【小桃红】我蓦听得马嘶人语喧哗,掩映在垂杨下,唬的我心头丕丕那惊怕,原来是响珰珰鸣榔板捕鱼虾。我这里须风悄悄听沉罢,趁着这厌厌露华,对着这澄澄月下,惊的那呀呀呀寒雁起平沙。
【调笑令】向沙堤款踏,莎草带霜滑;掠湿湘裙翡翠纱,抵多少苍苔露冷凌波袜。看江上晚来堪画,玩冰壶潋滟天上下,似一片碧玉无瑕。[3]
以上写张倩女魂追王文举的感受和艰辛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悄悄冥冥,潇潇洒洒”,就是倩女脱离了沉重的躯壳后在冥冥夜晚中飘逸轻扬但又心惊胆怯魂魄的特征;“汗溶溶琼珠莹脸,乱松松云髻堆鸦,走的我筋力疲乏”,写出了匆匆赶路的神态;“你莫不夜泊秦淮卖酒家?”道出了寻觅不得后的疑问;“向断桥西下,疏剌剌秋水菰蒲,冷清清明月芦花”则以凄清之景来衬孤寂之情;【小桃红】写出了魂临江边内心的各种变化,担惊受怕;【调笑令】继续写赶路的辛苦,并且写出了在囚笼般闺房所未见过的景象——“看江上晚来堪画,玩冰壶潋滟天上下,似一片碧玉无瑕。”
真情未必一帆风顺,挫折亦是在所难免,当倩女之魂追到王文举后,立即遭到王文举的斥责:
(正末做怒科,云)古人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老夫人许了亲事,待小生得官回来,谐两姓之好,却不名正言顺!你袅私自赶来,有玷风化,是何道理?
“常言道做着不怕!”(第二折【越调·洛丝娘】)男女私奔,在古代是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而女子私奔,面临的压力和威胁更大。当压力来自所熟悉的情人时,那更是真正严峻的考验。但是,倩女心中只有一个“爱”字,所以,她打定了跟王文举上京赴试的主意,那些封建传统的伦理观念全不放在她眼里,并且还表示了同甘共苦的意愿:
……你若不中呵,妾身荆钗裙布,愿同甘苦。
【越调·拙鲁速】你若是似贾谊困在长沙,我敢似孟光般显贤达。休想我半星儿意差,一分儿抹搭。我情愿举案齐眉傍书榻,任粗粝,淡薄生涯,遮莫戴荆钗,穿布麻。
爱,是无价的;但追求真爱,却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
因为爱,所以对爱的感受也就更加敏感,更会担心情人的“变心”。倩女不在乎王文举有无功名,担心的倒是文举高中后别娶高门。她对爱情的追求是真挚、热烈的并始终有一种比较清醒的认识,总提防男子的“变心”。对王生的应举,倩女并不十分在乎:“也不指望驷马高车显荣耀”(第一折【仙吕·赚煞】),大有《西厢记》中“但得一个并头莲,强煞如状元及第”之感。送别王文举赴京应试,她顾不上少女之羞涩,殷勤叮嘱就要远行的恋人:“若得了官时,想必休别了丝鞭者 !”(长亭送别的旁白、叮嘱)“你休有上梢没下梢”(第一折【仙吕·元和令】)、“你身去休教心去了”(第一折【仙吕·胜葫芦】)。王文举走后,她一再担心他会因金榜题名而结亲权门,“辜负了碧桃花下凤鸾交”(第一折【仙吕·赚煞】),所以魂身分离,追赶上王文举,且坦言相告来意:“秀才,赶你不为别的,我只防你一个”,“你若是御宴琼林罢,媒人每拦住马,高挑起染渲佳人丹画,卖弄他生长在王侯宰相家,你恋着那奢华,敢新婚燕尔在他门下?”(第二折【越调·东原乐】)
她一直担心男方的“变心”,并采取了主动稳妥的做魂随王生,寸步不离,这样,就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里。相比之下,崔莺莺在长亭送别后对自己的婚姻就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只好整日以泪洗面,长吁短叹,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表现了封建时代丧失了婚姻主动权的妇女的悲惨命运。而张倩女为改变命运作出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理想的胜利。
这里有激烈交锋的和刚柔并济的几“斥”几“怨”,并且都是跟爱恨情思交织在一起的,还涉及到了人物形象的“性别颠倒”和复归的问题[4]。
有人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这里就有了有力的反驳,更明显的应该是女性的自我启蒙、自我解放。这种“幻化”以及其表达的个性解放思想在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再次得到确证。
2 商人形象突围,彰显人性之美
前贤时彦对秦简夫《东堂老》的理解主要集中在财产继承问题和道德问题上,如季国平《略论元杂剧〈东堂老〉的思想意义》、王平《论秦简夫的“伦理道德剧”》等。我们认为,要对秦简夫作品立体化理解,首先必须回归到人性本质上,我们暂且舍弃人性“娱乐”的一面,从“美”的角度做出开掘,在“疲软”的写作与研究中,我们需求一种新的“变奏”。
这种“变奏”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对商人形象的“纠正”与“救赎”来实现的。同时也把商人归还为人,进而彰显了人性之美。
《东堂老》故事虽没有刘备临终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那么“壮烈”,但东堂老李实身上却体现了诸葛亮一样诚信的神圣。东堂老事在人为的理念、艰苦创业的精神、为富亦仁的人格、诚信讲义的品质,是《东堂老》之所以弥久恒新的人性魅力所在。
但这个“诚信”不是直线流露出来的,而是通过故事一步一步发展,最后才拨开迷雾点出来的,这种方式很像法国作家莫泊桑《项链》结尾的结构。这种诚信感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个体的影响,而是群体的影响。剧中扬州奴沦为乞丐前的样子很像《项链》中玛蒂尔德在舞会上的表现,出尽了风头;不同的是,玛蒂尔德向往的是“美”,是对下层生活的不满和对上流生活的向往;而扬州奴向往的是“恶”,是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和对自身价格的亵渎。正是这种“恶”的种种表现,东堂老出于对晚辈的关心、对朋友的信义,暗中教导着他一步一步成人。
东堂老对扬州奴的教育和关心同样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激将和询问的方式加以指导的。如,第三折扬州奴沦为乞丐后的营生中,东堂老与其对话:
询问如:
……(正末云)我不信扬州奴做甚么买卖来。(扬州奴云)您孩儿里卖炭,如今卖菜。(正末云)你卖炭呵,人说甚么来?(扬州奴云)有人说来:扬州奴卖炭,苦恼也。他有钱时。火焰也似起。如今无钱,弄塌了也。(正末云)甚么塌了?(扬州奴云)炭塌了,(正末云)你看这斯。(扬州奴云)扬州奴卖菜,……(正末云)你这菜担儿,是人担,自担?(扬州奴云)叔叔,你怎么说这等话?有偌大本钱,敢托别人担?倘或他担别处去了,我那里寻他去?(正末云)你往前街去也,往那后巷去?(扬州奴云)我前街后巷都走。(正末云)你担着担,口里可叫么?(扬州奴云)若不叫呵,人家怎么知道有卖菜的。……
这里东堂老其实把营生的经验间接而具体地传授给了扬州奴:营生要放下架子(特别是读了点书的人)、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如亲自挑担)、要有分清是非曲直的能力(如看清两个无赖一类人面目)等。
激将如:
……(正末唱)你就着这五百钱,买些杂面你便还窑上去。那油盐酱旋买也可足零沽?(扬州奴云)甚么肚肠,又敢吃油盐酱哩?(正末唱)哎!儿也,就着这卖不了残剩的菜蔬,(扬州奴云)吃了就伤本钱,着些凉水儿洒洒,还要卖哩。(正末唱)则你那五脏神也不到今日开屠。(云)扬州奴,你只买些烧羊吃波?(扬州奴云)我不敢吃。(正末云)你买些鱼吃?(扬州奴云)叔叔,有多少本钱,又敢买鱼吃?(正末云)你买些肉吃?(扬州奴云)也都不敢买吃。(正末云)你都不敢买吃,你可吃些甚么?(扬州奴云)叔权,我买将那仓小米儿来,又不敢舂,恐怕折耗了。只拣那卖不去的菜叶儿,将来煨熟了,又不要蘸盐搠酱,只吃一碗淡粥。……
这里东堂老用扬州奴以前的挥霍浪费为背景来点醒扬州奴,真正的营生是要加倍地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这两段引文中,扬州奴答话的内容其实就是东堂老平时生意经的一个方面。他并没有将自己艰苦奋斗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古董”而加以珍藏,而是慷慨地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这种“寓教于问”的方式,一改以前的伦理教条式教育方式,充满生活气息,生活本色化的语言也较容易接受。所以学者有称“在秦简夫的作品中,似可隐约见到北方杂剧依旧保持着初期杂剧本色当行的一些迹象”[5]。
现实生活的残酷、人情世态的炎凉深深地使扬州奴认识了自己,东堂老的教育也使得扬州奴不断地改变自己。这些都共同谈到了经商的苦楚悲辛:
如第二折:
……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善能货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
【正官·端正好】我则理会有钱的是咱能,那无钱的非关命。咱人也须要个干运的这经营。虽然道贫穷富贵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稳坐的安然等?
【滚绣球】想来我幼年时血气猛,为蝇头努力去争。哎哟,使的我到今来一身残病。我去那虎狼窝不顾残生,我可也问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场往来奔竞,那里也有一日的安宁?投至得十年五载我这般松宽的有,也是我万苦千辛积儹成。往事堪惊!
这里谈到的商人事在人为理念、艰苦创业的精神,有一改前人认为商人是奸诈渔利、贪得无厌、不劳而获形象之功,可谓是一种对商人形象的“拨乱反正”。它所表现的,不是“重义轻利”的士大夫道德,而是更具有真实性的、与追求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商人道德。“东堂老这一连串的自白,实际上否定了贫富穷通皆由命的观念,肯定了商人阶层注重实际、刻苦耐劳的人生态度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了元代社会日益活跃的商人和手工业主的人生观和道德观。”[6]
传统的农本经济滋生的“重农抑商”观念和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商人的态度。
虽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赞扬范蠡“富好行其德”(《史记》卷一二九),但在后来,这种人本的思想却湮没了。两汉以来,“重农抑商”定为国策更是如此了。以至于很少发现商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影子,即使有也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自从白居易《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句的出现,更多文人对商人更是采取一种鄙夷的态度了,总认为商人只有眼中的钱而没有心中的情,是重利无情之徒。唐代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思想的活跃,曾一度使商人题材解冻,但毕竟是零星的。宋元时期,“重农抑商思想,一直到南宋的叶适才首先予以批判”[7]。
虽然元杂剧也有对商人形象的贬抑,如商人财主,要么像郑廷玉《看钱奴》那样被描绘得贪婪吝啬,要么像《贩茶船》中的冯魁那样,重利轻情,夺人所爱。这类作品揭露金钱的罪恶和商人的弱点,固然有其真实性,但也多少反映出人们轻视商品经济的传统观念;以及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视求取功名为正途的狭隘心态。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观念的变化,秦简夫的《东堂老》中东堂老的形象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对受贬抑的商人形象的突围。
“秦简夫的《东堂老》,第一次正面塑造了李实这样一个见财不昧,有情义、重言诺、诚恳可信的商人形象。它肯定了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对商人经营的艰辛深表同情。这种违背传统意识而与近代进步思潮更接近的观念,很值得读者注意。”[6]这一形象的出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综合考察“流寓”与“变奏”之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两点:
第一,地域性的差异使“流寓”赋予杂剧“变奏”的灵魂。
杂剧作家流寓江南后所创作的戏曲带有明显的“南方性”,其题材和思想与前期北杂剧有明显的不同。《西厢记》和《倩女离魂》同是写文人士子爱情,但《西厢记》中表露的思想就是要比《倩女离魂》中表现的要正统,《倩女离魂》中更多的是“反叛”——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女性主义的觉醒”,更多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大胆追求。
《东堂老》剧中也明显有这种北方正统、南方开放的思想倾向。北杂剧商人多被贬抑;流寓作家南来之后,看到南方经济的富庶和繁荣,以及经济对人生的一种思想投射,开放的思想明显超越北方正统观念和对商人“为富不仁”的“经验”式偏见。
倘若没有这种“流寓”,杂剧手法和思想的“变奏”也许会在黑暗中摸行很长的路。
第二,“变奏”使“流寓”作家的作品顺应了南方戏曲环境,促进了戏曲形态自身的嬗变。
“南北合套”是戏曲“流寓”的必然结果之一,也是“变奏”的结果之一。大家之所以能记住“熟悉”的事物,就是因为“变奏”中提供了新的东西和新的亮点吸引了注意产生了记忆。“北调南腔”中创作手法互为借用现象酝酿出了新亮点就是很好的例子。作家在流寓过程中,与南方戏曲圈子的作家不断交流和学习,也促使南戏吸收了很多杂剧的优点而不断发展,最终完成了戏曲形态的逐步嬗变:杂剧(南戏)——南戏——传奇。由于后期文化理学氛围的加浓,杂剧和南戏都有“律化”和“戏教”倾向,杂剧呈现出“幽梦难回”趋势,虽与“流寓”有关,但那是另当别论的事。
[1]胡久江,王子文.元代流寓江南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创作研究综述[J].飞天,2010(8):85-86.
[2]郭英德,尚学锋,过常宝.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25.
[3]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181.
[5]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66.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33.
[7]兰寿春.古代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嬗变[J].龙岩师专学报,1996(2):30-33.
The Discussion on Variation Phenomena in Zaju Works of Writers Migrating to the South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WANG Zi-wen
(Department of the Humanities,Nanchang Teachers College,Nanchang330029,China)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variation phenomenon in Zaju works of writers migrating to the South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by Qiannvlihun of ZhengGuanzu and Dongtanglao of QinJianfu.Then it highlights two bright spots: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blocks by the diversification from body to ghost and combination,and making known the beauty of human nature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businessmen’s images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s.And it summa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tion phenomena and the writers’migration to the South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migrate;variation phenomena;diversification;breakthrough
I207.41
A
1674-3512(2011)01-0045-05
2010-12-06
2010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课题《元代后期流寓江南的杂剧作家及其创作研究》(ZGW1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王子文(1981—),男,江西瑞昌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元代)、戏曲文化、书法艺术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