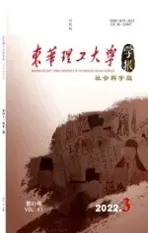元小说创作模式较之于传统小说创作模式
2011-08-15崔媛媛方加胜
崔媛媛, 方加胜
(1.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抚州344000;2.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210024)
元小说创作模式较之于传统小说创作模式
崔媛媛1, 方加胜2
(1.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 抚州344000;2.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210024)
传统小说创作模式中存在的承认小说是作者虚构的产物与元小说创作模式对小说虚构本质的不断揭露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进一步通过对现代元小说与含虚构因素的传统小说的比较更加深入地理解元小说。
元小说概念;虚构因素;现代元小说文本;传统小说
元小说创作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循着自己的轨迹,遵守自己独特的创作原则和创作理念,通过不断大胆地挑战传统创作规范、创作模式,坚持不懈地为寻找小说新的叙事方式的可能性而努力。传统小说创作都是作家先创作,作品出来以后,评论家、读者进行阅读并批评鉴赏。在整个作品创作过程中,作家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没有作家,就不会有作品。而元小说则是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中,经常邀请读者参与进来,经常能听到作者在征求读者的意见,和读者商讨如何安排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在元小说创作中,读者的地位得到了大大地提高。这些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在传统小说中是不可能有的。
1 元小说的概念及其理论来源
帕特里夏·沃说:“所谓元小说就是指这样一种小说,它为了对虚构和现实的关系提出疑问,便一贯地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工制品的自身的位置上。这种小说对小说本身加以评判,它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1]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有一个更简洁的说明:“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2]元小说早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斯泰恩的作品《项狄传》中就出现过,而且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因此戴维·洛奇视它为“最早的元小说”,并指出其特点是“采用叙述者和想象的读者间对话的形式”[3]。
元小说理论来源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及其“小说性对话理论”。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其作品“创造的不是无言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他们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起而与之抗争”[4]。也就是说,被叙述者可以与叙述者处于平等地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有权反对作者对其命运的安排。
元小说不断揭露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虚构性,说到底,是文学求真进取的体现。文学是不断追求社会、心灵、表象、幻象,以及人的存在的真实性的。元小说既然能回归本原的虚构性上,其实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求真呢?
2 传统小说创作模式中的虚构因素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也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发现了元小说手法的运用。如杨义、高辛勇等认为,《红楼梦》、《西游补》、《聊斋志异》、《拍案惊奇》等作品中都有元小说因素(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诚然,在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确实能够发现元小说因素的大量存在。如《红楼梦》中,开篇作者就承认自己的作品是他虚构的产物,但他的这种承认虚构和元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对虚构的不断揭露在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红楼梦》在引子中说自己的作品是满纸荒唐言,但到了具体正文部分又回到了客观叙述上,作者本人保持不介入的姿态。而元小说文本则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作者出场,提醒读者注意作者是在进行虚构创作。
虽然早在明代《西游补》这样的传统小说中就已经出现了元小说的因素,但由于数量少,而且小说在中国古代地位低下,小说理论不发达。因而,对元小说相关的理论研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只是具有元小说因素的传统小说,其典型的叙述方式仍然是客观叙述,跟真正意义上的元小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韦恩·布斯经过细密的考察已经指出,即使在客观叙述中也还有一个置于场景之后的“隐含作者”,但巴特还是强调“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头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作者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同这部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5]但是马原却偏偏要打破这个成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场,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作为真实作者的身份。其元小说《虚构》,开头就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种叙述方式受中国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明显。”在文言小说中,叙述者有时也直接使用作者的名字。李朝威在《柳毅传》中说:“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 愚义之,为斯文。”李朝威的“叹”显然带有评价色彩,但首先,这种评价在小说中只是偶尔出现的,叙事主体多是单一的;其次,这种评价并非他的主要意图,他的主要意图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故事是真实的,以提高读者的信任感;还有,这种评价较明显,一个“义”字,叙述者的倾向便显现出来。而马原的小说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是叙述者经常从故事中跳出来而叙述生活中的马原如何如何,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小说中的马原有时候真的就是生活中的马原。叙事主体产生了分化。二是真实作者有时直接取代叙述者。三是这种貌似明显的评价只是作者的随感,对整个故事的进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样,叙事主体便用表面明显的评价来掩盖实际上隐晦的评价,惟其如此,这种评价才隐藏得更深。
3 现代元小说与含虚构因素的传统小说的比较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巴赫金指出:陀氏“创造的不是无言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他们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起而与之抗争”[4]。元小说也实践了这一理论思想,在现代元小说文本中,作家、人物、读者的角色已经淡化,是元小说文本的作者有意为之。以往的传统小说,有叙述者而且也经常边述边评,特别是章回体小说,如《红楼梦》,叙述过程中,常见到这样的情况:针对一个人做的事情,作者不直接发表看法,而是通过“有诗为证”等等之类的形式来加以评论。这是形式上的差异。在话剧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话剧演着演着,有演员也许会突然背对着其他演员,对观众说:“这个家伙,来路可不一般啊,我才不认为怎样怎样。”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心理活动,甚至发表评论。其实,这些都是不同文学体裁所适用的形式不同决定的。元小说文本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大胆突破传统创作规范,把人物和读者的地位上升到与作者同等重要的位置。元小说不仅仅限于边述边评,并不把确认叙述者身份当作己任,而恰恰是着力于扰乱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界限。和传统小说中处于权威地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同,元小说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处于平等交流的地位。元小说中的主人公再也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人,能够与作者平等交流,发出与作者不同的声音,甚至反对他。
元小说文本中,作者的主体地位是被消解的。约翰·查尔斯评论到:“现在,小说家仍旧是神仙,因为他可以创造一切(即便是有幸成为现代小说先驱的作品,也没能完全排除作者的意向)。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经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所想象的无所不知、发号施令的神仙;我们成了新的神学形象,即以自由而不是权威为首要原则……我想让你知道,我无法完全驾驭我脑海中的人物。”[6]
因此,我们常常在元小说中看到作者和读者讨论该如何开始或结束一个故事,作品已经不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例如,约翰·巴思就在《漂浮的歌剧院》的第一章里大谈特谈要不要开始讲他的故事;例如《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不停地问主人公查尔斯:“我现在可以利用你吗?我现在拿你怎么办呢?”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元小说中作者、创作者、评论者是同时存在的。元小说中作者的声音都不再是唯一的独白的声音,而是和其他声音共存。在作者失去权威地位的同时,元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传统小说中任人摆布的“无声的奴隶”,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独立体。他们在文本中崛起,成为一种抗衡作者权威的不同声音存在。例如,元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会说谎、夸夸其谈、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会与作者争辩,甚至反对作者的决定。主人公再也不是作者意志的“传声筒”,他一旦出现于作品当中,就具有了自我意识,作者不能违背主人公的意志而强行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作者本身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元小说不再是作者独自控制的天下,而是充满了各种不同声音的杂语世界。
在元小说文本中,淡化作者主体地位的同时,无形中也提高了读者的地位。传统小说中,读者在文本形成过程中,是一个不在场者,是后知者;而元小说中,读者显然参与了元小说故事情节的创作过程,变成了在场者。由以前的被动地位变成创作主体之一。如,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约翰·福尔斯干脆提出几个结尾给读者自己选择。作者也常常不知道该拿主人公怎么办,有时甚至在书中和读者讨论起来。再如,意大利作家阿·贝维拉夸的《和家俱杂物共度八月节》这篇元小说,小说的副题是《一篇需与读者合作的小说》,从其题目中就可以看出元小说中读者地位是提高了。元小说的作者似乎变得相当谦虚,他们的作品需要听到不同的建议,因为他知道,作品总是需要读者欣赏才有价值,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总而言之,含虚构因素的传统小说与现代元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含有虚构性要素,多是以虚构写其梦境、幻觉。如,《红楼梦》中,写实性主导时空,把虚构性要素放入其中。而后者是本源性虚构,虚构是作为主导背景出现的,局部细节、片段上写实。而这种本源性虚构又存在两点:一是,作者直接介入或颠覆文本。这在元小说作品中屡见不鲜。如《冈底斯的诱惑》,它在叙述过程中便出现“作者注”、“作者又注”的字样,这种“注”,是直接针对叙述者的叙述而发的议论,评价的味道很浓。二是,反复暴露文学虚构特征。这正是元小说“反对现实,反对传统的文学成规”的地方。可见,元小说的这种揭露虚构是彻底的,而具有元小说因素的传统小说承认自己创作是在虚构,只是在行文时构建一个大背景的虚构,增加作品的神秘色彩,进一步吸引读者读下去。所以,我们也只能称其为“具有元小说因素的小说”,而不能称其为元小说。
[1]金圣坤.关于后现代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J].国外社会科学,1988(2).
[2]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30.
[3]王又平.元小说:暴露虚构的话语策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63-70.
[4]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
[5]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K].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6]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M].陈安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The Comparison of Metifiction Mode and Traditional Novel Mode
CUI Yuan-yuan1,FANG Jia-sheng2
(1.College of Chinese Law and Arts,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Fuzhou344000,China;2.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24,China)
In traditional novel-writing mode,that the novel is a product of fiction is admitted.However,in metafition mode,the nature of fiction is constantly disclosed.The author makes a further comparison between modern metafiction and traditional novels with fiction elements so a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etafiction.
The concept of metafiction;fiction elements;modern metafiction text;traditional fiction
I207.41
A
1674-3512(2011)01-0042-03
2010-11-14
崔媛媛(1985—),女,安徽寿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20世纪小说理论与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