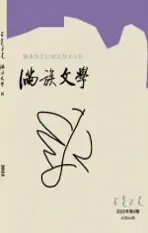身体里的棋局
2011-08-15满族
〔满族〕北 野
之一:如果是一次搏弈
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体里摆开棋局。一个人同时被自己暗杀。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但肚子烂了还会剩下牙齿。这可以让你正确评估一小块骨头的价值和硬度,从而开始变得蔑视自己和肉体。
我从一只苍蝇的飞行高度上推断人类哲学的虚伪。我假装和大家一起厌恶苍蝇,但我心里依然对它悄悄地赞美,包括被它传播到一定层次的疾病。高度,意味着厚颜无耻,同时也意味着被人担心和敬畏。
我们偶然来到这个社会,用喜怒哀乐消遣我们所遇到的事情,用七情六欲对付我们所钟情的男女;得意者当官,失意者出家,伤心者病死,流浪者隐匿,学会写诗的人痴痴傻傻,患了精神病的大都是笃学深厚的艺术家;许多人连生活都没弄懂,就恬不知耻地死了;像梦游的人,抱着一团巨大的棉花,终生都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放下。
这个时候,我就想:身体和灵魂到底谁更大些?这个问题搅扰得我彻夜不安,那些疯疯癫癫的身影是灵魂的庙堂和家吗?其实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和瘠薄啊,一张纸也可以把它的脖颈割裂,一片树叶也可以把它的头顶砸破;一副身体或者就是一个假人的宝座,用风声可以把它掀翻,用雨水可以把它浸塌,用情歌也可以把它焚毁;上帝啊,是谁在我们的灵魂以外涂了这层四面漏风的泥巴?!
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因为重新回到身体而被自己吓得昏死过去。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总是长吁一口气,慢慢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像又一次回到树荫下纳凉的人,幸福地眯起眼睛。
之二:童年记忆
一个经常沉浸在童年回忆中的人肯定是接近了人生迟暮,比如我。这和反省是两码事。回忆不同于反省,但更近似忏悔,它有否认现实幸福的意思。纸里包不住火,雪里也不能埋下孩子,但回忆常常需要一个人突然的沉默。水往下流,云往上升,时间的面具依然黑白分明,但过去的生活死死地埋伏在心里,我却一样也无法说出。
爬上山就遇到了《山海经》里的野猪,下到河就可以捉到《水经注》中的白泥鳅;只有那片老林子过于复杂,令人望而生畏,有獐狍虎豹和野鸡,也有逃婚不归的哑女,我一直在林子边向里张望,始终不曾与她(它)们相遇;这是不是意味着,漂亮的哑女已经主动做了老虎的白骨夫人?反正一桩婚姻到此戛然而止,这让我少年时代暖洋洋的心里突然冒出寒气。
蓝格英英的土豆花美丽的像罂粟,但绿皮子的土豆果却要吃上四季。大人们举着语录本警惕地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孩子们却笑着喊“土豆烧牛肉,不许放屁”。地震和饥荒挨着个来,连麻雀都羞愧自己成了四害,惊慌地自杀在胡麻地里。一把镰刀磨了三年,依然挂在南墙上,好庄稼都被冻死在坝上的霜冻里;这个时候土地上最多的就是蝗虫和盗贼,贫下中农开始羞涩地盗窃着社会主义,贫下中农饿啊!继父从饲养处偷回的牲口料,成了我们改善生活的奢侈品,我困惑地看着大人们流着泪把它吞下去,他们呜咽着说:粮食,要珍惜粮食!
而现在的幸福生活,已经把我变得萎靡和颓废,就像在春天呆久了,反倒多了一份对冬天的怀疑,我总是在心里回过头寻找自己。我抚摸着自己的脸颊,它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疲惫而空虚;但它一旦安静下来,就像个影子一样地鼓起来。其实隐私是不能公开的,而沉默反倒经常会使自己脸红。身体中的财富已经被大把地消耗光了,剩下的就只有对时间的记忆。
其实也只有时间中的记忆,才能不使自己的身体被再次利用。
之三:真实
太真实了,反而变得虚假。真实像一副墨镜,它把你自己描述得傲慢而荒谬;所以你需要躲在人群里,像个发烧的小人物,捂着两腮尖叫,竭力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患者,因为无辜,你才有可能被更多的精明人所疏忽。
即使狐狸也懂得这个道理。在漆黑的夜晚出行,连狐狸的心灵也拖着一条阴影。所幸狐狸的眼泪和巧嘴令人动容,为此每一个白面书生都相信自己在荒郊野外遭遇了美女,缘分天赐,纸醉金迷。狐狸是幽灵中的白领丽人,不是狐夹子上那个哭泣的弱女,即使在此刻我伪装成猎人,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情欲;这一点,在商周时代就被一只飞翔在朝歌的动物看破了。
我梦见自己死于花下,又在泥里复活。而泥是化粪池,需要捏着鼻子才能啼哭,需要倒提双腿才能控出藏在肚子里的花心,需要猛拍后背才能咳尽肮脏的前生;最后我被人扔进洗澡盆里,摔得鼻青脸肿,接生婆险恶地说:小子,出水才见两腿泥呢!
如果用森林的眼光看木匠,那木匠必须被一根大木楔钉死在树桩上;然后挖开胸腹,掏出带血的斧锯和恶毒的心肠。木匠是森林的克星,木匠的尸体必须被鹰叼到树冠上,让每一根枝条都狠狠地抽打他十次,让他血肉横飞,一块骨头也不剩下,还要让站在楼顶上的城里人看到木匠的下场,直到他们和森林成为亲密的同谋,直到他们把站在街头招揽生意的木匠的后代也一起赶出城来,森林才会收起城头的沙尘暴和呜呜的风声。
如果把教堂里的唱诗班降到千米之下的深渊,在云头上偷听的上帝会不会突然掉下来?落入地狱的上帝,肯定让一群嚎啕的聚餐小鬼兴奋不已。问题是小鬼们根本就没有去过天堂,所以落在手里的上帝就和穷命鬼是一个命运,并被小鬼手里的催命符所威吓,上帝被装在垃圾车上垂头丧气,即使你拥有亿万星辰,在此刻,也必须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
鸟在半夜发出诅咒:“上帝早晚要死于他的仆人之手”。上帝居住在高处,上帝并不影响我的生活,而我只向自己身边一切普通的事物致敬,并且毫无悔意地爱、恨和沉默。
之四:夜游者
如果我们一直把一个素食主义者的胆结石当成佛舍利,那么肯定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大地的屋顶上,亡灵夜夜在飞。只有人浑然不知,人在梦中思考和睡觉。人在梦中不假思索地说:“我们这一世啊,从来没有人照应!”暗夜里有多少双耳朵听见了这话,有多少双眼睛看清了你的底细,又有多少颗心在沉默?
痛苦已经形成。痛苦像铜号再次吹响:城市在半夜突然断裂,动物园和学校一起下沉。孩子在废墟里惊叫。未诞生的儿女通过母亲的嘴在大声祈祷。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风吹雨打的生活,我哭着喊:这是敲诈,是谁诱导了那些纯洁的死者?
但夜晚再深,也从不把死亡的秘密埋没。豹子滑下山坡的时候,在河边碰见赤裸的百兽和水面上迷路的幽灵,豹子首先用脏衣裙把自己的身体裹起来,然后说:黑夜宜于忧伤,但不暴露道德。死亡的身影恰好可以把每一片荫翳利用起来,但它们从不利用坟茔。而那些贫穷的死者却围成一圈,等着一块乌云刮到头顶。
除开都城以外,城市索性就用树叶建造吧,甚至教堂和乡村;这样一来,让一阵风就可以轻易掀开生活的屋顶。我们只把豹子的家安于山涧,让熊猫的家安于风景,让老鼠背着它的家四处逃生。我们已经习惯了风吹雨打,我们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一只乌鸦背负着黄昏飞进深夜。一只乌鸦傲慢的叫声甚过一百只猫头鹰。
我在半夜打开窗子,空出座位,用一杯酒邀请黑暗中的人。我说:“幸福是一场运动,她的价值需要被重估。”黑暗中没有人回应。此时,我发现,我的心与黑暗的夜色相等,而我的双肩松弛下来,是不是得到了安抚?像贴着墙根逃命的小偷,侥幸和苟且也会被当做快乐的人生。
那么,如果一天即一生,我耻辱的生活还要被复制多久?
之五:蚂蚁与大象的烈士生活
一头大象为两只蚂蚁所解剖。而两只蚂蚁高举草叶的解剖刀,最终累死在大象辽阔的尸体里。这说明,再小的成功也意味着要有伟大的支持,那怕是死亡的接引。没有人承认的死亡就是一种抛弃。所以人需要集体,需要两个以上或更大的群体来互相陪衬,这和精神中的孤立无关,这是生存之需,这容易使一切不应获得的荣誉被赋予充足的理由,这同时也使面临颓败的人生在暗中多了一份对未来的窃喜。而此时,蚂蚁在大象的血管里像游泳一样沉浮,它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来收拾这个残局。
我渴望自己像骑士一样在时间里冲锋陷阵,同时用最快的速度把风车挑落在擂台上,然后把英雄的花环佩戴在众多的懦夫胸前,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个英雄的集体,而我心中却为自己的个人主义洋洋得意。生活习惯教育我必须如此,名声和鲜花之下,我是个谨慎而寂寞的英雄。我是懦夫们的情敌。我在天上。我坐在大象宽阔的脊背上正虚构自己。
插上翅膀的蚂蚁就是蜻蜓。或者就是现代生活里的直升飞机。即使它们牙齿松动,满面尘泥,蒙受了一生的艰辛和羞辱,蒙受了一路风雨,我依然会记住这一切,并且珍惜它们死亡之前挂在树桩上的空巢和大地之中的巢卵,记得它们短暂的生活和酸涩的命运。我拣出大象尚未被蛀空的骨头,等着蚂蚁们孤注一掷的队伍陆续钻透纸背,这是它们闻风而来的后代么?它们来得多么快!像一片阴影迅速淹过了我的脚踵。
之六:生存从无胜利可言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机会并不多。长久以来就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有定数。每一种定数都预先经过了计量,幸福与灾难,诞生与死亡,这些信息都由一个命运的黑匣子盛装,然后被安放在我们身体中某个隐秘的地方,只是我们一直从无知晓。这不是唯心,其实如果唯心至上,我们就会更早知道这些,起码早就洞悉人类的真相,与我们的生存尽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解;我们生存的背景那么深,那么广大,又那么迷茫;她到底珍藏了什么玄机?一直让我们百思不解,迷恋又忧伤。
地震停息了。大自然在一瞬间向她看中的地方发出吼叫,这吼叫过于残酷和庞大。用尽了自然界一切可怕的手段和声响,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而人像碎片一样漂泊,被迫献出生命和肢体;我们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痛哭失声,但大自然毫无声息,她一下子又消失了,甚至具象成了瓦砾和虚墟,具象成了洪荒时代的一片苍茫;其实这灾难是给整个人类的,她决不是因为人类罪孽深重,而是对世界文明快速泛滥的一种疼痛抵抗。灾难的阴影中,人和人都一样,没有崇高与卑下,没有百姓与将相,只有本能地抗拒才能共同获得一线生机,此时人和其它动物是一致的:掩埋好痛失的伙伴,然后逃亡,勇敢的生存才能继续追问死亡的因果。
在大自然面前,其实“人定胜天”一直是个假象。人肉体脆弱,但意志坚强,这是造物主提前赋予的生存秉性,用以应对自然界的雷电风霜、劳动与战争;用以衔接一个物种的繁衍重任并且教化四方;生不能长生,生则必死,这个法则必须被执行,这样才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人类艰难地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生存理想,并且用文字记下未了的心愿(这文字奇妙而富有重量),供来者继承和分享;而肉体则要化做烟尘,紧紧跟在你的身旁。我在此时则对灵魂一说深信不疑,我相信空气里飘满了她们欢乐而匆忙的身影;而坐在树荫里喃喃自语的人,谁说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我甚至猜测,他就是一个预言家,他在与灵魂彻夜长谈之时而拥有了先知的身份和光荣。
我曾表达过我的惧怕。我写过一篇《文明与恐惧》的文章;我提出了那些尖端文明所带来的速度和恶果,那些东西几乎让我们目不暇接和忘乎所以,我们被幸福感占据的大脑像一个核武器,每天都在裂变中上下求索;我们吃光了应该属于身后十代或几十代后来者的文明财产,像败家子一样超前享用了他们的幸福时光,却还在愚昧地洋洋自得。现在我才知道,地震算什么!海啸和飓风又算什么!人类自己所掌握的秘密武器就足够把地球毁灭十几遍;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就像炸药一样堆在我们身边,“世界已使生活雪上加霜”,为此,和谐生存与人为善,让一切都慢下来显得多么重要;敬畏自然像孝敬父亲一样,接受它和平的风景,也接受它愤怒的风暴,品尝它所给与的赏赐也献出她应当获得的贡果。每当黄昏来临,我们匆忙走在回家的路上,淹没在钢筋混凝土所构筑的城市之中,我就心神不宁,这座人体的囚笼,这架夸大了的绞肉机,它要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旋转,把我们全部吐出来,一起交还给缓慢的世界和平静的郊外,交还给朴素的生活和艰辛的时代?
而对那些汹涌而来的文明成果,我们不要轻言胜利。其实人生一世,根本就没有胜利可言。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个问题。文明的盛宴不是人类必须的要求,它们对于我们的生存几乎构不成完美的结合,它只是一种破坏和分裂,包括对人性的可耻引诱;它很长时间都不能让我们在纯粹的生活中恢复过来,并且很快就让我们放弃了自己已有的美德,而加入到无休止的掠夺和肉搏;森林变成了工具,开始吐纳工业废气;动物被拉进食物链,在刺激着我们贪婪的食欲;植物们遭遇了基因的惊扰,成了每一场风沙中暴怒的异类。这恐怖的世界,已经让我们心灰意冷。而人类却还要坚持躲在断墙下,无力地看着大自然用它安排的暴乱吞噬着我们遮风挡雨的家园,我们用来温暖心灵的蜃景破灭了,肉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蔑,数千年来安居在心中的人群被赶出了历史的山脉;苦难之日,连上帝和佛陀都不在场,只有记忆可以作证,只有记忆在不断追查着我们突然散落在民间的生存烟火。
每一个到来的白天或夜晚,我们都需要珍惜,我们都需要用她来涵养道德和力气;而尊敬自然,接纳一切迎面而来的恶意和善意,都是对我们的锻炼和洗礼;大浪淘沙,纤尘毕现,而我们的身体里只应剩下干净的历史、心灵和自然;至于胜负,我们暂不提起,以免巨大的现实又把我们当做对手。生活再次开始的时候,我是那么地厌恶极端世界里的一切文明成果;我只想简单而愚蠢地生活在大地的草木之中,以便让普遍的自然之力盖住我灰暗的身影,让我逐渐恢复的人性之光,慢慢地适应生死和命运的距离,让我平静地送走逝者,迎接来者,深情地挚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她们都是为我而来,她们是上帝所赐;在人类幸福的广场上,人与人相遇是多么珍贵而稀疏。
生存,从无胜利可言。但生存依旧充满了失败的欢欣和乐趣。
之七:沉默的陷阱与巅峰
种一棵树让它开花结果,和种一棵树让它长到吊死自己的年龄,用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在它面前,一个思想家可能等不到结局,而一个农民却可以平静地等到最后。那么,可以这样说:收拾残局的人往往置身局外,但他们一直遭到局内人的轻视。
我在白天遇到的人和我在梦中遇到的人,他们是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如果是,而我想遇到的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在这个世上?而我将在哪一场梦中才能和他相遇?这样的假设是不是要使我的生命变得遥遥无期?而我要找的人他真的存在吗?我发现我在梦中一直捂着嘴哭泣,这和我在白天保持沉默的习惯几乎是一致的。
用刀子吃饭的人是不是比用筷子吃饭的人更文明一些?这需要让一个谙熟炼金术的人来回答。首先要弄清楚刀子出现的目的,把稻谷和动物的碎肉用刀子搅来搅去,然后吃掉它,这离屠杀和行凶有着比较近的距离,一个新的概念在字面上掩盖了刀子的本意。而筷子被随手插在土里,长出绿叶,有着靠近树林的决心。
之八:在一堵墙上照见自己
站在一百层高楼的顶部,我们也不能摸到上帝的脚趾。或者我们用尽一生的力气,再加高一百层,上帝依然无影无踪。而此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不能全身而退了。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在自己虚构的天空里变得老态龙钟。在这一点上,神仙要比人聪明,神仙不登高楼而是驾云飞行,所以神仙和上帝是一伙。而人类只能在上帝的背后望风扑影。神仙遭遇膜拜还要发出窃笑,人类一直不解上帝的窃笑到底是什么意图!
怀孕的大象有资格和野猪高谈阔论。而野猪假装谦恭,低着头从不在大象面前暴露自己的怯懦。野猪像窃贼一样逃出象群的领地之后,站在另一个山涧大喊:大象你是破鞋,你怀了俺们猪的野种。大象恼羞成怒,跳崖自尽。山坡上发出野猪的笑声。从此象群一旦有怀孕的,就要在道德上首先检讨自己,大象以此来清除身体中的罪名。而大象心中的阴影一直不为我们所见。
用一面镜子和一堵墙都能照见自己。我们甚至可以从镜子上看见逃逸的幽灵。而一堵墙更容易使一个人自我批评和自我辩论。墙是中药铺里的药剂师。是赌场中的恶棍。是吞糖豆自杀的服毒者。是被小心保护下来的分裂成两个人的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骑在墙头上,心里有飞升的冲动和燥热。
我在梦里发财,富有四海。我在梦里成了黄金中的狂人。然后驱赶那些曾经被我轻蔑的富人为奴仆,打他们耳光,揪他们头发,审问他们灌满钱币的良心,把他们抢劫财富的双手折下来喂狗,把他们美丽的妻子据为己有。梦醒之后,我依然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知道,如果现实需要靠梦操纵,我已经成了生活中的暴徒。
我始终对命运存有疑问。对大地上的风景迷惑不解。我不知道自己将为此遭到什么样的处罚或奖赏。这样设想的人肯定不多,不然每个夜晚又会有多少人从梦中惊醒。我不能为此而说出这些疑问,正如我不能说出我暗自吞下了多少苦果一样。而苦果是身体中一个寂寞的挖井人,他把我的心挖得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