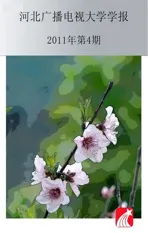近代涉县申氏契约文书探析
2011-04-08朱文通
朱文通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近代涉县申氏契约文书探析
朱文通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51)
随着近年来徽州文书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契约文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也明显存在着对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华北契约文书重视不够的倾向。近代华北契约文书的研究,一方面应该大量搜集资料,一方面应该借鉴古代历史文书研究的经验。近代涉县申氏契约文书的命名、分类、特点及学术价值的研究,对传承无序的契约文书的研究将会有所裨益。
近代;文书学;涉县;土地;契约文书
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念景廷宾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10月22日在河北省广宗县宾馆召开,笔者有幸与会。会议召开当日午餐后,笔者和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吕坚先生一起外出散步,在县城新华书店门前冷清的地摊上,偶然购得契约文书9件、“粮簿”1册,后经研究可以确定为近代涉县申氏契约文书。目前学术界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华北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还比较少见①本文写于2009年8月,曾经提交当年9月18—20日在冀州市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2009年年会,笔者到会后又因伯母逝世而离会,未能参加会议交流。嗣后陆续修改补充,并于2011年6月定稿。,更遑论邯郸地区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了。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华北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不同地区契约文书比较研究的重视,以期促进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探索,引起学术界对近代传承无序的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的高度重视。兹按时间顺序将笔者搜集到的申氏土地契约文书公诸同好,并略加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录文
1.立典契人申进武,因为不便,今将自己祖业道西地一段陆亩,其地四至不一,水流行道,依旧往来。今情愿出典与北水村王建庚名下,承为典业,同房地行言明典价大钱三十五千文,其钱笔下交足不欠,自限三年,茬下回赎。两家情愿,并无反覆。恐口不凭,立典契存证。
上带本地原粮壹斗贰升正
光绪贰拾贰年五月初九日 立典契人申进武(押)
(加盖房地行“正堂王-南庄□□□□-孙怀新戳记”)
2.立合同人申进文,因与胞弟分居后,又有祖上所遗地地名白尖、道西,地二段六亩;小窑坡地一处;南脑地一处,典当在外,未承均分。今同人方同祥将南脑地一处分与侄子暖心永为己业,小窑坡地分与进文永为己业;至于白尖、道西地,作大钱壹百五十千,除典价两股均分,暖心得钱五十八千,地归进文己业。恐口无凭,立合同存证。(此件未署年月——笔者注)
3.立典契人申德居,因为不便,今将自己祖业地名腰色腰,计地壹处一亩,本地大小根条一切在内,其地四至不开,水流行道,依旧往来。今情愿出典与申进文名下,承为典业。同房地行言明典价大钱肆拾千文,其钱笔下交足不欠,自限种满五年不到回赎。两家情愿,并无反覆。恐口不凭,立典契存证。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立典契人申德居(押)
后批本地原粮壹斗贰升正 同人申德邻
(加盖房地行“知事王-支发行所记-神头村申正瑞”戳记)
同人王乃成(押)
5.立卖契人李安义,因为不便,今将自己祖业地名蛟凹被一处,东至赵文广、赵廷美,西至赵成璧,南至路,北至赵文广,四至开明,各照原界;又有交凹地一段,井坡地一处,大小根条在内,水流人行,依旧往来。今情愿出卖与赵和璧名下承为己业,同勘丈员人言明卖价大洋叁十五元整,当下交足不欠。上带原粮贰升正,价足粮明,随收过割。两家情愿,并不反覆。恐后无凭,立卖契文为证。
民国二十年 立卖契人李安义(押)
同中人申乃田(押)、赵廷珍(押)
(由“西第六区勘查申国正”加盖“无隐无漏”戳记,并签名,戳记上的时间是“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刊发”)
6.立卖契人赵廷美,因为不便,今将自己祖业地名井坡根地一处,东至赵浮校,南至路,北至路,西至河,各取四至开明,水流行道,依旧往来。今情愿出卖与□□□(原留空白——笔者注)名下承为己业,同产行地房卖价大洋贰拾陆元整,其钱笔下交足不欠,两家情愿,并无反覆,恐口不凭,立字为证。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 立卖契人赵廷美(押)
上伐本地原粮壹合正
7.立卖契人申子芳,因为不便,今将自己祖业地名后院地,计地一段三亩,本地大小根条一切在内,其地四至开明,东至申连惠,西至郝丕承,北至路,南至河,各取四至明白。土木相连,水流行道,依旧往来。今情愿出卖与申子元名下承为死业,同勘丈员言明卖价大洋伍拾元整,其钱笔下交足不欠。上带本地原粮壹斗二升正,价足粮明,随收过割。两家情愿,并无反覆,恐口不凭,立卖契存证。
民国二十三年十贰月廿日 立卖死契人申子芳(押)
同中人申谭(押)、申子正(押)
(加盖“涉县契□经理□第十一区勘丈员”和“勿隐勿漏”戳记)
8.立借约人申清书,今借到赵六顺名下大洋十五元,言明年月一分五厘行利,自限来年本利清还。若要还办不到,情愿有场后地一处二亩,押与保人,得业佃还。恐口不凭,立借约为证。
民国廿六年二月初九日 立借约人申清书(押)
后批本地粮食每亩五分正
同中保人王庄则(押)、郝丕谟(押)
9.立卖死契人李安义,因为不便,今将自己祖业地名交凹被坡地一处,大小根条在内,其地四至开明,东至赵文广、赵廷美,西至赵成璧,南至路,北至赵文广,四至明白;交凹地一段一处、井坡根地一处,大小根条在内,四至开明,水流行道,依旧往来;今情愿出卖于赵和璧名下,承为死业,同勘丈员死卖价大洋肆拾捌元,其洋笔下交足不欠。两家情愿,并无反覆。恐口不凭,立字为证。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立卖契人李安义(押)
后批本地原粮贰升正
同中人申乃田(押)、赵廷珍(押)
二、文书命名
因为上述契约文书是从广宗县购得的,所以笔者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广宗当地的契约文书。及至阅览,从文书7经公戳记标明“涉县”字样和这些契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或关联性来看,其实应该是“涉县申氏契约文书”。然而,申氏准确的居住地并未明确记载,当系在文书中出现的村名北水村、南庄、神头村(另外,和上述地名有关的还有“西第六区”、“第十一区”等,大概是上述村庄所属的区,不过有可能不同时期所属区不同而已)附近,从文书内容来看,北水村显然不是申氏的居住地。又,从文书3经公戳记加盖房地行“知事王-支发行所记-神头村申正瑞”来看,申正瑞是神头人,因而申氏的居住地很有可能属于涉县神头村(现为神头乡)。又查,在神头村几乎是正南方、距神头村三里多有申家庄,在神头村和申家庄之间略微偏东,恰好有北水村。因此可以断定,笔者在广宗县购买的申氏契约文书,应出自涉县神头乡申家庄。神头海拔约300米,申家庄附近海拔约500米,位于涉县西南部,已经是太行山的深山区了,再往西约12里就是著名的响堂铺(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发生著名的响堂铺战役),响堂铺向西约1里就是河北、山西的分界线。南庄出现在契约1房地行的戳记中,在涉县县城和神头村之间偏东,离县城4里,在光绪年间神头村、申家庄等地的房地交易大概属于南庄管理。
上述契约文书持有人,或者涉及的人员,以申氏为核心,他们居住在同一区域之内,在发生经济关系时,签定契约,互为保人、中人、地邻等。从契约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区域社会生活共同体。文书 1、2、3、4、7、8均为涉县申氏家族文书,没有任何疑问。契约5、9在签约时间上虽然相差7年,卖方都是李安义,买方都是赵和璧,中人相同,其中之一是申乃田,契约5经公勘查为申国正,应该说和申氏有一定关联,或为本家;而有关的其他人,和申氏或有亲戚关系,也未可知。而契约6(赵廷美卖地契)和申氏在字面上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从赵廷美、赵廷珍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契约5和9中,这些契约的内在关联不言自明。因为契约6只有卖方姓名,没有买方姓名,或许因为地域狭小,一时难以找到买主,没有发生交易;如果发生交易,买方很有可能也是申氏。而究竟是否找到了买主,不得而知。这9份契约文书,也许原来就在一起,也许是古董小贩在申家庄不同人家收购的。但是这些契约文书均出自申家庄,并且以申氏为主,或与申氏有一定关联,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因此,我们命名这些契约文书为涉县申氏契约文书。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契约2实际上还暗含着另一个土地买卖过程,“至于白尖、道西地,作大钱壹百五十千,除典价两股均分,暖心得钱五十八千,地归进文己业”。也就是说,白尖、道西两块土地回赎除典价两股均摊外,土地回赎后,暖心以五十八千钱将应分土地卖给了申进文。
涉县申氏契约文书中时间最早的是契约1,光绪贰拾贰年(1896年)五月初九日申进武当地契,最晚的是契约9,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初一日李安义死卖契。其中,契约2没有标明时间,但是从内容来看应该在光绪贰拾贰年(1896年)五月以后。因为从文书内容来看,契约1立典契人申进武和契约2立合同人申进文应该是同胞兄弟,契约1立典契人申进武在光绪贰拾贰年(1896年)就已经单独立契约,可见他们已经分家,各立门户了。从契约2来看,这次分家应该属于第二次分家析产,但是一定是在光绪贰拾贰年(1896年)后。此外,除契约2外,只有契约4是申心并且是和申喜元一起于民国十六年签立的一份契约。契约1、2、3使用大钱或钱,契约3的确立时间是民国十二年,其余契约签定时间均在此后,全部使用大洋,而契约2使用大钱或钱。因此笔者认为,契约2确立的时间应该在契约4之前,而从契3可知,申进文1923年还与人签定了5年回赎的承当合同,说明1923年申进文仍然健在,这说明契约2很有可能就产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和民国十六年(1927年)之间。据著名金融史专家戴建兵先生告知,清末民初为使用大钱和大洋的分界线,而在远离城市的地区改变起来可能要晚一些。居住在太行山深山区的涉县申氏在土地买卖中使用货币情况的变化,恰好反映了这个特点。
三、文书种类与特点
涉县申氏契约文书虽然很少,但是形式多样,种类较多,有卖契(包括顺约、绝卖)、典契、借约、合同(分家析产文书)等。
1.典契
契约1、3为典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契约1有“上带本地原粮壹斗贰升正”、契约3有“后批本地原粮(可能是新开垦的土地,后来才纳税——笔者注)壹斗贰升正”字样。此外 ,契约 4、5、6、7、8、9 都有类似的字样。有的是“上带原粮贰升正”,有的是“上伐本地原粮壹合正”,各有不同,缴纳的数量大概和土地开垦的时间、数量以及贫瘠、肥沃有关。也就是说,除契约2是分家析产文书外,其他都带有“本地原粮”。“本地原粮”是指什么?笔者曾经撰写《有清以来沧州地契文书的几点研究》①《河北学刊》,1989年第1期。一文。其中,谈到清末沧州土地典契过程中有典当土地上带小租若干文(每亩百文)一事,沧州土地典契过程中的“小租”是指什么?笔者一直存疑,查阅资料之外,也请教过一些专家学者,未能得到圆满解答。2010年春节期间,笔者采访了有关文书当事人的后人,一位91岁的长者。据这位长者说:小租实际上就是土地税。笔者觉得此说有一定道理,可以聊备一说。由此联想到涉县申氏契约文书中的“本地原粮”,笔者认为“本地原粮”应该也是土地税,就是民间所说的“皇粮国税”。所不同的是,“本地原粮”缴纳的主要是实物,只有一份是缴纳货币——“后批本地粮食每亩五分正”,而沧州小租缴纳的均为货币。关于这一点,还可以证之其他契约文书,比如《,乾隆至咸丰年间王永德家买地契约汇集》②参见:戴建兵等《河北省近代土地契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217-234页。收录文书56张,大多都在文书的相同位置写明“二五过税”“、二五过粮”、“二五过拨”,有的则为“二六”、“二七”,有的则具体言明总数或者每亩数量等,既有实物形式的,也有货币形式的。光绪十五年、民国十四年直隶省(河北省)唐县卖地契及验契纸也有曾写明“随带唐县粮”①参见:戴建兵等《河北省近代土地契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66-167、198-199页。的。这种情况,在直隶省、山西省等地文书中可以得到很多证明②参见:戴建兵等《河北省近代土地契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62-216页;安介生、李钟《:乾隆初期晋中田契“契尾”释例》《,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不再一一例举。
2.析产
契约2为分家合同,即分家析产文书。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知什么时间,申进文和申进武分过家(不知为何未见到文书),我们称之为第一次分家析产。不知道什么缘故,家产并没有彻底分净,这在分家中并非普遍现象③确实也有约定一些家产不分的,如邯郸永年申氏家族申涵光在《岵园记》中曾说“:与两弟约,此园永不分析,长房主之。”《(聪山诗文集》,申涵光著,邓子平、李世琦点校,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39页)当然,时间长了,倘若境况不好的话,也许就会分析。按:岵园即南园,明末由申涵光之父河南杞县县令中佳胤购置,在永年县韩家屯滏阳河以南,河朔派诗人所组织的观社等时常在此活动,申涵光等人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南园。;立这份合同文书时,申进武已经去世,所以立合同人是申进文和他的侄子即申进武之子暖心。二是典当出去的土地,也在分家的财产中,这一点倒是符合惯例;但是,典当出去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暖心的一部分经过作价后,全部给了申进文。也就是说,这份分家析产文书实际上暗含了一次土地买卖过程,并且是买卖的典当出去的土地所有权。至于,典当出去的土地所有权的价格和正常土地买卖的价格有没有差异,值得关注。
3.卖契
契约 4、5、6、7、9 为卖契。其中 ,契约 4,名为顺约,实际上也是卖契。民间卖地,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里顺字可能是为了回避“卖”字吧。契约7先后两次写明为“卖契”,最后签字时又特别写上“卖死契”,契约9开始就标明为“卖死契”,最后签字时仅仅写卖契,没有特别强调死卖。“卖死契”,就是死卖、绝卖。绝卖又称死卖、卖断,在北方这样写的并不很普遍,只是比一般卖契更强调卖主不得以任何方式回赎或加价而已。然而在南方,写明“绝卖”的契约比较常见,但是却又经常发生“绝卖”后加价的情况,而北方的土地契约文书虽然大多并未写明死卖或绝卖,但是实际上就是绝卖,只有在荒年皇帝下令后可以加价、找价外,卖后又加价的极为罕见,这可谓南方和北方地权关系和经济关系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南方的社会经济关系相对复杂,北方则相对简单一些。
另外,从签定契约双方关系来看,无论是典当,还是买卖,当地都遵循了先本家,后同族,其次亲戚,再后就是地邻,最后才能卖与其他人的惯例。这一点在涉县申氏契约文书中比较明显,不再具体分析。
再有值得注意的是,除分家析产或丈夫去世、孩子幼小这种情况下立文书可以有多个当事人(兄弟或母子)具名外,其他一般是双方各有一个当事人具名,而契约4,申心、申喜元共同具名,似为兄弟联名。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4.借贷
契约8为借贷文书,名为借约。清末到民国时期,高利贷利息低的大多在1—2分之间,高的一般都是3—4分,极个别也有高达7分的。契约8民国廿六年申清书借约年月“一分五厘行利”,应该说不高。此外,该文书的抵押方式也值得注意,一般土地典当中抵押土地都是直接抵押给债权人,该文书可能是借贷数额较小,所以抵押的土地也较少,是2亩;抵押方式不是直接抵押给债权人,而是由中间人负责管理抵押的土地,以便“得业佃还”,比较独特。
四、涉县申氏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村落社会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状况
1.涉县申氏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实际情况
一是文书中错字、别字、白字,几乎通篇满纸,难以卒读,以致笔者实在无法完全按照原文再加注释过录,只好径改;契约加盖的戳记中难以辨认的字和有意留出的空白,则用□代替。二是文书书写潦草凌乱不说,重要的是不够规范,内容严重缺项,如契约2没有写明立合同时间和地亩数;契约5民国二十年李安义卖契没有写明月日和地亩数,契约9民国二十七年李安义死卖契,提到所卖地三块,既没有说明每一块的名称、地亩数量,也没有总数。契约5和契约9,二者文字几乎相同,几乎只是钱数不同而已;契约8民国廿六年申清书借约没有明确写清还款的具体日期,只说“来年”,一般按照习惯“来年”当为一周年,此或为当地以习惯法为主之遗绪;契约6民国二十一年赵廷美卖契没有写明买主姓名,好像是想卖地,又没有找到买主;等等。9件文书中,有5件内容缺项,不够规范,这说明当地文化水平明显落后,法律意识淡薄,似乎以习惯法为主;文书中有个别错字、别字、白字,还可以理解,错别字奇多,而且在内容上严重缺项,就极不正常。一方面,这不符合官方的有关明文规定,另一方面也容易诱发纠纷,而事实上一旦发生纠纷,就难以处理。这在笔者30多年来所见各地契约文书中是唯一的,可谓绝无仅有。
2.所有买卖或典当的土地全部写明应该缴纳的粮税,其中办理手续虽然经公率比较高,但是官方管理仍然不到位
9份文书当中,除一份分家文书外,其余8份为买卖或典当土地,全部注明应纳税数目,而这种完税的情况,在平原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契约文书中一般并不反映。此外,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有4份经公即房地行,经公较高,但是又没有用官颁契纸,也没有粘连契尾,交易过程中的纳税情况均未反映出来,这说明官方对这里的土地买卖和典当管理还不到位,即管理不力。笔者所见沧州、安国、辛集、衡水、石家庄等地契约文书,不税契者较多,倘若税契,大多都用地契官纸,并于完税后在官纸和契尾粘连处加盖印章成为红契。民国初年,税契或者验契明显增多,亦多用地契官纸,有的则粘连契尾。解放区的土地买卖大多都用地契“官纸”或“经验费”,这说明社会控制越来越强。涉县申氏契约文书虽然完税,但是又不用地契官纸,也没有粘连契尾,确实颇具地方特色。
3.土地状况
由于文书比较少,目前一时还难以比较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从地名、四至和文书内容来看,买卖或典当的土地多属于丘陵山地或河滩地段,一般地块比较小,最大的有两块6亩的,其他为1—3亩。有数块地只写地名,没有地亩数量,大概是因为地块零碎,难以丈量,无法写清楚,不是书写无意中遗漏;有的没有开列四至,也许是孤地,不存在四至问题;有的也许确实是书写不够规范所致。有五份契约写明“大小根条在内”、“大小根条一切在内”,说明当地可能较多种植果木林树等,反映出丘陵山区的种植或者植被特点。
五、关于“粮簿”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粮簿”册的情况。笔者曾经搜集多本账册,但是搜集到“粮簿”册还是第一次。该“粮簿”,宣纸,共计14页,长26厘米,宽13厘米,毛笔书写,右侧用宣纸纸捻分为四孔装订,纸捻较长,折叠后仍然突出册页之外。封面左侧上角书“粮簿”二字,右侧下角书“副四甲”字样。这说明当时当地实行保甲制。而保甲制能够推行到这样的深山区,可见当时社会控制比较有力。“粮簿”册的内容自然主要是“完粮”的记录,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依次如下:
1.付款
“八、十六,付洋叁块(在数字处加盖‘王壹’二字)。”
“九、廿九,付洋伍元(在数字处加盖印章一枚,模糊不清)。”
“十一、十八,付钱壹千(在数字处加盖印章一枚,模糊不清);付钱壹千九百五十三(在数字处加盖‘王壹’二字);完。”
“二、十七,付洋壹元(在数字处加盖‘王壹’二字);付钱一千(在数字处加盖‘王壹’二字);完。”
上述共计四笔六次付款,三次付洋,三次付钱,从钱洋并用及后面银钱并用这一情况来看,“粮簿”册似乎写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究竟为什么付款,不得而知。笔者猜测,很有可能是付给雇工的工钱,也有可能是购买物品的支出。其中的时间,按照惯例,应该是阴历。“粮簿”册上付款加盖印章比较奇怪,印章当为“粮簿”册主人的名号或者堂号之类。
2.收款
收款系该“粮簿”册的主体内容,依次记载赵福、赵文毓等15人(这些人名在上述契约文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完粮”的情况,银两数目除用汉字书字外,均另用苏州码子书写,其中13个数目字用苏州码子书写后又用墨笔圈掉重新书写。具体内容如下:
赵 福,银叁分六厘,250(圈掉,笔者注,下同),264。
赵文成,银八分四厘,588(圈掉),607。
赵文太,银六钱一分叁厘,4 291(圈掉),4 431。
赵文和,银壹两贰钱六分六厘,收洋四块,8 862(圈掉),9 058。
赵文春,银叁分贰厘,224(圈掉),239。
赵世香,银贰钱九分四厘,2 058(圈掉),2 108。
赵文举,银贰钱贰分三厘,1 581。
赵 义,银乙(即一,笔者注,下同)钱叁分九厘,973(圈掉),1千。
学 场,银贰分八厘。
赵 禧,银贰钱七分三厘,1 911(圈掉),2 098。
赵世斌,银贰钱六分六厘,1 862(圈掉),1 908。
赵文隆,银乙(即一)钱0九厘,763(圈掉),785。
赵良弼,银乙(即一)钱六分八厘,1 171(圈掉),1 207。
赵文毓,银乙(即一)分六厘,112(圈掉),120
赵文兴,银四分七厘,329(圈掉),342。
共银:3两5钱9分4厘(用苏州码子书写,笔者注)。
从赵文和名下明确写有“收洋四块”来看,此应为收款记录,应该为佃户完粮情况的记录,对于“粮薄”册主人来说就是地租收入,且系货币地租,而非实物地租,并且货币地租主要是用银结算,只有一例辅助少量大洋。由于没有租种土地的亩数,故无法计算地亩和租银之间的比例。然而,从佃户所交银两数目比较零碎来看,佃户租种的土地也应该比较零碎,这恰好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涉县山区土地比较零碎的特点。考虑到山区土地稀少,虽然有15人完粮,但是主人最多也就是一个中小地主。
苏州码子所写不知其确切含义,很可能是银两折算大钱的数量,而圈掉的数目,大概是折算比例有变化所至。倘若如此,那么,银3两5钱9分4厘共折合大钱25 748文,银一两折合铜元约为7 164.16文;圈掉的数目则为23 394文,一两折合大钱则约为6 509.18文。7 164.16比较接近这个时期大致通行的7 200的折算比例,6 509.18则表明银更贵一些,银贵钱贱的情况比较明显,也说明了银钱折算的比价随时变化。
3.付使唤钱
收款记录后,还有一笔另外的付款记录,记载为“九、廿九,付使唤钱六百文”。从数额较小来看,可能是“粮簿”册主人家中临时短期雇人的费用支出。
4.又一个总计数字
在“粮簿”册的封底上,主人用苏州码子记载“共4 972”一组数字,不知其确切的含义,或许是按照银和铜元的折算比例进行折算得出的一个结果。如果是折合当十的铜元,每两银子折合铜元约为138枚,也比较正常,符合当时的基本情况。但是,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而已。
清末以来,随着中国历史资料的六次大发现①即甲骨文、简牍文书、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文书、徽州文书、黑水城文书的发现和刊布。,文书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实际上已经悄然兴起。契约文书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徽州文书研究为典型代表之一,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也明显存在着对近代特别是民国以来华北契约文书重视不够的倾向。近代华北契约文书的研究,一方面应该大量搜集资料,一方面应该借鉴古代历史文书研究的经验。国内关于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是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定县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中涉及有关问题②参见:李景汉等《定县社会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481页;冯华德、李陵《: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4卷第4期。,随后是傅衣凌关于福建契约文书的研究③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为躲避日机的轰炸,曾经在距永安城十多里的黄历乡居住,在所居住的老屋里无意中发现了一大箱民间契约文书,自明嘉靖年间以迄民国有数百张之多。他对这些契约进行整理和研究,陆续完成三篇论文,后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于1944年由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该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也是傅衣凌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华北或者河北省契约文书的研究,起步在国内应该说还算是比较早的,但是一直没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令人惋惜,由此导致在学科建设方面也比较落后。希望各界朋友特别是年轻学者能够更多地关注华北的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工作,从我们身边做起,努力搜集有关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不断地有所进步。
Analytical Study of Shen’s Contract Documents in Shexian County in Modern Times
ZHU Went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ijiazhuang,Hebei 050051,China)
With the recent rise of the studyof Huizhou contract documents as a subject,the studyof contract documents has become a school of learning.But clearly there exists a tendency of inadequate attention to the contract documents in North China of the Modern Times,especially since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study should,on the one hand,collect a lot of data;on the other hand,learnfrom the experience of ancient historical documents research.The studyof Shen’s contract documentsin Shexian Countyon its naming,classific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will be useful to the study of the disorderly heritage of the contract documents.
modern times;study of contract documents;Shexian County;land;contract documents
K263
A
1008-469X(2011)04-0006-06
2011-06-24
朱文通(1964-),男,河北沧县人,研究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李大钊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