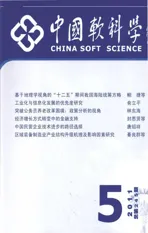我国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援助的探索与挑战
2011-02-19刘正奎吴坎坎
刘正奎,吴坎坎,张 侃
(1.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我国是灾难多发的国家。1908年至2008年的一百年间,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十大重大自然灾害中,我国占有四起[1]。仅从2008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我国重大的自然灾害就达八起。其中,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树大地震和8.8舟曲特大泥石流不仅导致人民重大生命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而且也给灾难的幸存者留下了巨大的个体、家庭和集体的心理创伤。
我国的心理援助工作最早始于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2003年非典疫情中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逐渐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2004年,浙江和上海还先后成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2007年,浙江颁布《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行动预案》。在国家层面,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2002年-2010年工作规划》和卫生部的《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中都提及心理援助服务。但是,对于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心理援助工作基本上是零散的、自发的或被动的,在国家的整体救灾方案之中也几乎没有心理援助的位置。“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灾难带给人民的巨大个体、家庭和集体的心理创伤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高度的关注。由政府部门、部队、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等组织的大批心理援助队伍进入地震灾区。据估计,在5.12大地震发生后的一年时间里,超过4000人的专业心理学工作者前往灾区或坚守在本职岗位上,开展实施灾后心理援助工作[2]。目前,仍有大批的专业心理学工作者在四川灾区开展持续的灾后心理援助。因此,5.12汶川大地震使得灾后心理援助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开始被纳入我国灾后重建计划。2010年,我国又发生了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重视和规范。我国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开始走向科学、有序和可持续的道路。
一、心理援助是重大自然灾害后救援体系和行动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因灾死亡或受害的人数都大幅增加。根据国际灾难数据库(EM-DAT)的统计报告,1999-2009年间,全球共发生重大自然灾害3886起,比1980-1989十年间发生的1690起,增长了一倍多[3]。而且由于全球气象变化可能会导致未来灾难进一步增加[4]。因此,建立并完善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准备和灾后重建计划是各国政府必要的任务。
重大自然灾害不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而且由于灾难造成的多米诺效应会在短期之内在整个地区甚至国家范围内引起心理恐慌,随着营救工作的展开、生产生活的恢复,灾难造成的恐慌会逐渐缩小,但是灾难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或创伤会在灾害受难者心中留下长久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1992年就曾就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心理影响做出报告,其中对灾难进行了如下定义:“一种大大超过个人和社会应对能力的、生态和心理方面的严重干扰”[5]。一直以来,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灾行动主要在生命救援,以及满足住所、食品、卫生和流行病免疫基本需要的物质援助。近年来,自然灾难的援助策略和模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已开始认识到,自然灾难对人类的心理具有非常深刻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他们的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难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6]。我国对5.12汶川大地震后受灾群众的心理疾患发病情况的系列调查发现,受灾人群的心理疾患的发病率较高,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项的发病率往往都在10%以上,有些人群甚至高达45.5%[7-15]。因此,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需要对受灾人群提供心理援助和社会性的关怀,以帮助他们恢复到正常的健康水平,并最终实现心灵的重建。
实际上,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灾难的援助模式和行动中非常重视心理援助,并将心理援助纳入整体援助战略计划中。比如,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WHO与受灾国出台了旨在满足心理社会需求及防治心理疾病的战略计划。世界银行和土耳其政府达成的灾后重建协议中规定,援助总经费的1%将被用于心理健康的恢复项目。而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也不断在重大灾难之后,对于其国家紧急事件计划进行了调整,以突显心理援助在灾后重建中的地位。因此,心理援助与生命营救、物质救援一样,已成为灾难救援体系和行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我国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援助主要工作
在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树大地震和8.8舟曲特大泥石流发生后,我国的灾后心理援助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包括:开设心理援助热线,进行灾后心理援助人员的培训,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灾后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派遣专业人员奔赴灾区,对家在灾区的学生、灾区转移到非灾区的学生和其他受灾人群开展心理援助,开展系列灾后心理创伤研究等。
(一)政府出台灾后心理援助相关政策,在专业机构的支持下,发挥主导作用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于2008年6月8日发布的第526号国务院令《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都提到心理援助工作,使灾后心理重建工作有法可循。同年7月,国家教育部颁了《关于地震灾区中小学开展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纲要》,以具体指导地震灾区中小学生进行科学、有序、持续的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4.14玉树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专业支持下,科学规划,推动了灾后心理援助纳入灾后重建整体规划,在《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第九章第一节中心理援助工作正式作为重建工作的一部分。
我国的心理学专业工作者积极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作用,通过向各级政府提供专业的建议,支持政府实施灾后心理安抚的科学决策。仅中科院心理所在512汶川地震和414玉树地震后就向党和国家递交政策性建议22份,其中11份被中办和国办刊物采用,5份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此外递交人大提案1份、政协提案2份,并且向四川省各级政府递交政策性建议7份。这些建议为政府参与主导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海玉树地震后心理援助工作中,中科院心理所通过与青海省委宣传部的合作,成立了青海省心理援助领导小组,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牵头,参加部门包括青海省教育厅、卫生厅、民政厅等,在中华慈善总会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专业技术支持下,统一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使得玉树地震后心理援助工作完全纳入了政府重建体系中。
(二)灾后心理援助的管理和工作模式探索
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我国心理学工作者一直在灾区开展持续的心理援助工作,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出我国的灾后心理援助的管理和工作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在4.14玉树大地震和8.8舟曲特大泥石流后的心理援助工作中均得到很好运用,发挥重要作用。
1.灾后心理援助的二维管理模式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幸存者的心理应激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从时间维度上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对应着心理援助的三个阶段:警戒期(应激阶段)、抵抗期(冲击阶段)、衰竭期(重建阶段)。从5.12大地震后的研究结果来看,我国国民在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后,其心理变化也符合这三个时期。同时,灾难发生后,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上给人们心理带来的负性影响不同。我国研究者发现灾难发生后民众在空间上的心理感受长期遵循“心理台风眼”(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效应,即在空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16-17]。依此可以从空间上将心理援助分为三个部分:灾难中心、灾难的周边地带、外围区(即非灾区)。依据不同的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我国的学者构建了心理援助的工作框架,形成了灾后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程度的受灾地区采取不同的心理援助行动的二维的管理模式[18]。灾后心理援助的二维管理模式便于组织者快速地制定目标,明确区分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实施的任务,也为长期开展灾后心理援助架构了框架。
2.灾后心理援助的工作模式
迄今我国尚没有建立灾后心理援助的体系。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为了开展长期的心理援助工作,各专业机构和民间团体对灾后心理援助的工作模式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中科院心理所自5.12大地震后在当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先后在四川成立了7个工作站,分别为绵竹工作站、德阳人民医院工作站、北川中学工作站、什邡工作站、绵阳工作站、东汽工作站和四川司法警官学校工作站。4.14玉树地震和8.8舟曲特大泥石流发生后,心理援助站的工作模式进一步在两个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中得到运用和发展,分别建立了玉树、西宁、舟曲三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北京师范大学与德阳市教育系统密切合作,在当地受灾严重的10所中小学建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基地”,对学生和教师开展系统的心理援助工作;北京大学心理系在彭州市新兴学校设立了心理辅导站,成为在彭州的示范校,同样以学校为中心,学生和教师为直接干预对象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也在北川中学建立了“心灵花园”北川工作站,以沙盘为辅助工具,对该校的师生开展了长期的灾后心理援助;“妈妈之家”作为一个纯民间的社工组织,以社工的方式在都江堰的社区开展长期的社会支持性工作,被媒体称之为“民间的自我疗伤组织”等。
在众多尝试和和探索中,在本地建立心理援助工作站是目前最为持久而有效的工作模式。心理援助站工作目标:1)对灾后民众进行心理援助,并预防重大精神疾病的产生和大规模爆发。2)在灾难发生之后对民众心理受影响程度进行评估。3)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探索一套适合我国的灾害心理援助的模式和程序。4)关注灾后受到影响较大的重点人群。心理援助工作人员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心理辅导员和社会义工等。通过三年多的实践,逐步建立了基于心理援助站的“一线两网三级服务”的体系。“一线”是指心理援助热线,即在灾区联合当地的移动公司,开通各自的心理援助热线,并有专职的、经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接听热线,进行线上心理援助服务。例如,在四川灾区开通的“100865‘我要爱’减压热线”,自2008年12月正式开通以来,受到了灾区群众和各界的好评;“两网”是指灾后心理援助队伍网和互联网,即依靠各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在三年里为各个灾区培养了一大批有针对性、实际操作能力强的心理辅导教师,覆盖北川、绵竹、什邡、德阳、玉树、西宁和舟曲等的几乎所有中小学,建立了应对灾后心理创伤康复的队伍网络;同时,我国的心理学研究者研发基于移动互联网平台的系统软件——“移动心理服务系统”,通过手机就可以协助心理专业人员对受助对象进行评估和干预,并即刻反馈结果,提供专家建议和专业解决方案[19]。此外,我国的心理学爱好者还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建立“本土心理联盟”,使非灾区心理专业志愿者通过互联网帮助灾区心理辅导教师及网上求助者,目前这一联盟有4800多名心理学志愿者,成为一支分布广泛的民间心理援助队伍;“三级”是指学校、社区心理咨询室-心理援助工作站-精神卫生中心的一套针对不同的心理创伤的严重程度形成的体系,一级机构主要解决一般心理问题,开展群体心理健康教育、团体辅导活动、学校心理课等,遇到复杂困难个案转介到心理援助工作站,心理援助工作站还可以对一级机构进行督导和培训,此外,遇到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或者需要药物治疗者则转介到三级精神卫生中心。因此,三级体系可以基本覆盖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
心理援助工作站根据与当地不同部分的合作,形成了基于社区、基于学校、基于医疗卫生系统和综合模式的灾后心理援助具体工作模式。在基于学校的教育模式方面,依据校长-班主任-骨干教师-学生的思路,逐步渗透,多管齐下,覆盖教育系统各个层面,以帮助灾区学生、教师、乃至家长舒缓情绪、获得情感支持;在社区模式方面,通过“调研-培训-评估”程序,围绕地方政府灾后重建的中心任务(如维护社会稳定、加快永久性住房建设),为当地政府和受灾群众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并通过社区农村干部心理辅导培训工作,在社区干部中培养心理辅导员;在医疗模式方面,在地方医院,依据“评估-诊断-干预”的程序对社区群众和教师群体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建立高危人群心理档案,开展心理治疗;同时也在灾难深重的地区(北川、绵竹和什邡等县)选择重点乡镇和社区(北川县曲山镇、绵竹市汉旺镇、什邡市方亭社区),长期、稳定的开展灾后心理重建综合模式的探索与实施,并建立覆盖整个灾区(德阳、绵阳、玉树和舟曲等)的心理服务热线及计算机网络服务体系,培训了一支以当地教师和咨询师为主的线上和线下服务队伍,成为各个灾区灾后心理援助的有力保障[18]。据调查,四川绵竹心理援助工作站在5.12汶川大地震两周年时,对曾经来接受心理咨询的91名来访者进行的回访,发现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平均改善程度达到了81.9%,折射出心理援助工作站模式在灾后心理援助中的成效。
3.灾后心理援助枢纽人群的培训,建立当地的心理援助队伍
灾后枢纽人群主要是指在灾后重建中担负重要角色的工作人员,包括基层干部、医务人员、教师等。他们不仅受到了灾难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心理创伤,而且,他们是灾后重建的本地主要力量,要承担艰巨而繁重的重建任务,他们本身的心理健康状况或康复程度,不仅关联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因为他们生活、工作并服务于当地最广大的各个领域的人群,从而影响着灾后的重建。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使其能够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运用好心理学知识为群众服务,同时可以更广泛、全面的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特别是在专业人员极其缺乏而又主要分布于大城市这样现实条件下,通过对枢纽人群的系统培训,可以促进灾后心理援助可持续地进行下去。据统计,到5.12大地震周年,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先后在四川当地系统地培训枢纽人群共6000余人,包括基层干部、医务人员、教师等,其中,通过选拔与培训相结合,培养了238名专业的心理援助志愿者,为四川部分灾区建立起了自己强大的心理援助队伍。目前,经过两年多的系统培养,已为北川县、安县和绵竹市建立了一支稳定的开展灾后心理援助的本地力量。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绵竹市和北川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已走在全国的前列,并在全国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评比中多次获奖。
(三)灾后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
5.12汶川大地震后,灾难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造成了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和心理创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缺乏,因此,进行灾后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是灾后心理援助工作重要的环节。我国几乎所有省市的心理学会和主要的心理学机构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参与了卫生部、教育部、中国科协分头组织的有关灾后心理援助的指南和手册的编制。如《灾后心理援助100问》、《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地震后青少年心理援助教师、家长辅导手册》、《<我们一起度过>中小学生心理援助手册》、《危机心理咨询的实施》、《四川灾后心理救助手册》、《四川灾区心理应急指南》、《心理自助》、《心理自救互救宣传手册》、《创伤后应激障碍宣传手册》、《地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地震灾后心理防护与干预手册》、《社会集体事件心理辅导手册》等,内容丰富、数量庞大、面对人群广,编制速度快,令海内外同仁称赞。其中,山东心理学会于5月14日就制作了《一线官兵心理自我救助手册》,在第一时间发往抗震救灾一线,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表扬,同时,5月19日中科院心理所制作的《灾后亲子心理自助手册》《灾后救助者心理自助手册》《灾后救援官兵心理自助手册》《灾后成人心理自助手册》在灾区共发放了7.5万册,受灾群众评价“很有用”;5月24日由中国心理学会、中科院心理所、中科院成都分院共同编写的《灾后心理援助100问》对灾区群众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心理援助建议;6月1日为了帮助灾区少年儿童早日走出地震带来的心理阴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和上海增爱基金会共同发起针对灾区少年儿童进行心理干预的“我要爱”动漫心理援助活动,并决定根据专家建议,将心理援助的相关知识与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相结合,制作对儿童有心理辅导功能的漫画和动画短片,对灾区少年儿童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理辅导。
此外,在光明日报、人民网、北京晚报、科学时报、CCTV、网易等媒体和各心理学机构的官方网站进行灾后心理健康知识的讲座和文章撰稿,并根据已有的心理援助的经验规范媒体的宣传,宣传灾后各级人群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通过心理学界在汶川地震灾区、玉树地震灾区和舟曲泥石流灾区的共同努力,灾区的政府公务员、医院的医生和病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最广大的受灾群众对心理援助和心理学都有了全新的认识,甚至通过媒体的传播,社会大众对心理学也具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心理学也借助心理援助非常好的完成了科学传播的工作,走出了实验室,走向大众,走进大众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
三、我国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援助的问题与对策
5.12大地震发生后,心理援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大批志愿者以心理援助的名义不断涌向灾区。这说明整个社会对灾后心理援助在救灾行动中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但是,由于心理援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同时,我国在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的组织管理经验积累不足,人才储备也缺少。因此,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也凸显出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重大灾害后心理援助的法规不健全,缺乏立法保障,需要通过政府立法,保障灾后实施心理援助的地位。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心理卫生或心理健康的法律条文,而灾后的心理援助长期在国家紧急事件处理草案中受到忽视。5.12汶川大地震后,灾后心理援助得到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但是,如果缺乏健全的法规和国家立法保障,灾后心理援助工作未来很难有可持续性。在国家立法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美国,1978年,NIMH出台了《灾难援助心理辅导手册》,这是第一本由政府颁布的心理援助指南,且官方灾难后心理援助或心理服务被列入联邦紧急事务应急预案(FRP),在发生国家紧急事件时,启动国家紧急事件管理系统(NIMS)进行灾后管理重建工作[20]。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了国家应急行为管理系统,为经受灾难的人群提供医疗及心理服务。日本早在1961年就出台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对《灾害对策基本法》做了修订,之后陆续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构成了完整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其中明确规定了心理援助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21]。
我国于2008年6月8日发布的第526号国务院令《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第二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五条都提到心理援助工作,为灾后心理援助立法奠定了基础。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灾后心理援助的法规,通过政府立法,保障灾后实施心理援助的地位,制定《国家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预案》,将其纳入国家的应急预案法律系统,从法律上保证灾后心理援助的有序和高效运行[22]。
其次,灾后心理援助管理与协调机制缺乏,需要建立统一的组织及执行机构。5.12汶川大地震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灾后心理援助管理体系。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涉及的对象不仅是心理疾病患者,更重要是面对绝大部分的正常人群开展心理安抚工作;工作范围包括专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群体心理健康促进到社会文化活动的开展。这使得5.12汶川大地震后,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在管理上出现混乱局面。不同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团体从各自的角度涌向灾区,各自为阵,开展心理援助,有的甚至给灾区群众带来很大的困扰。因此,建立我国统一的组织和执行机构是科学、有序开展灾后心理援助的必要条件。
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很多国家灾害心理援助体系已日趋完善和成熟,也为预防灾害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法律,明确了灾难心理援助的组织和执行机构。例如,美国设立负责防灾救灾的中央机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机构(FEMA)。此部门直属白宫,从事指挥、协调管理相关工作以应对各种紧急国家事件,同时,对防灾及减灾项目进行支持,提供相关的培训。目前,全美有超过82000项政府项目进行与灾害管理相关的心理服务[20]。澳大利亚设有紧急事务管理局(AEMI),它是澳大利亚国家紧急事务管理的中心机构。针对各种灾难,AEMI制定了极为完备的应对指南,包括实施灾后心理援助[23]。
我国近几年实践中,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组织也做了很多探索。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四川、青海玉树和甘肃舟曲灾区建立的十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在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是一种成功的心理援助基层组织模式。其中,由青海省宣传部牵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提供专业支持,联合省卫生厅、民政厅、教育厅和妇联等多家单位,成立联合灾后心理援助组织机构,是一种典型的省级建立统一的灾后心理援助组织模式。建议在吸收这些成功的灾后心理援助组织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从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灾后心理援助常备的机构和组织,协调各方力量,使灾后心理援助能够快速、高效地开展。
第三,灾后心理援助队伍的专业水平和规模较低,需要大力推进心理援助专业人才培养,并建立专业人才储备网络,以应对灾难发生后的巨大的心理援助需求。灾后心理援助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她需要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心理援助技术、危机干预技术等专业知识和技能。没有足够的专业水平准备,不仅不能帮助灾难中幸存者摆脱痛苦,而且还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二次创伤。因此,建立一定规模的专业水平队伍是灾后心理援助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心理援助体系成熟的美国,重大灾难及危机心理援助系统具备比较完善的辅助支持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建设一直受到政府及各专业组织的重视,这些机构均组建了专门的灾难心理援助专业人员数据库,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定了组织管理人员职责、临床工作人员遴选标准与职责、专业人员培训计划等等[24]。对于心理救助队员,美国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NCPTSD)有明确的规定:具有心理健康医生执照;接到通知后能够马上提供10-14天的服务;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包括能够承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够给幸存者和志愿者以及社区组织提供教育服务、在美国红十字会接受过灾害心理健康志愿者培训等[24]。由于大规模的灾难并非经常发生,往往带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这就决定了志愿者在灾后心理援助中的特殊作用。为此,必须在平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建立数据库,以便在需要时能及时调动并迅速到位。美国红十字会设立了灾难服务的人力资源系统,存留和追踪救灾人员资料,通过该系统进行志愿者招募,以应对大灾难。红十字会还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美国心理协会、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美国婚姻和家庭治疗协会等签署备忘录,以促进机构间合作。美国红十字会与美国心理学会合作建立了灾难应对联盟(Disaster Response Network,缩写DRN)。这个志愿组织包括近2500名注册心理学家,这些心理学家都需要完成关于灾后援助的标准课程。灾后援助课程对于有执照的心理健康及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是完全免费的,只有完成相关课程并加入美国红十字会的灾后援助机构,才可以开展心理援助工作[25]。
我国持证从业的心理咨询师已达数万人,他们是我国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工作重要的后备力量,但是心理咨询师队伍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而且绝大数没有进行系统的灾后心理援助理论与技能的培训。同时,我国灾后需要心理援助或心理安抚的人群往往数量众多,即使全部从事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也无法满足需求。因此,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队伍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上都需要极大的提升,需要大力推进心理援助专业人才培养,并建立专业人才储备网络,以应对灾难发生后巨大的心理援助需求。
第四,社会和地方的心理援助力量的引导不够,需要整合政府与社会、当地的心理援助资源,形成共同援助局面。5.12汶川大地震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社会各个阶层对这次灾难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灾后心理援助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5.12大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参加心理援助的个体志愿者人数就达3000人,各种机构也达几百之众,至今仍有大批的心理援助志愿者在艰苦地工作。由于我国政府对灾后心理援助的应对不足,曾出现灾后心理援助中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各自为阵的问题。
实际上,世界各国也都极其重视融合民间力量,以期最有效地开展心理援助。日本最近20年来在应对地震灾害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不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自卫队援助的“公救”,社会力量或民间团体也要团结起来,互助“共救”。在美国,非政府组织是灾后心理援助的主要力量。很多非营利机构也积极参与灾后的心理服务,包括美国红十字会、各大学的医学院、心理学系、社会工作系以及教会组织、慈善机构等。
受灾地区当地的心理援助力量是长期开展灾后心理援助的关键。一方面,灾后心理援助需评估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了解文化基础和当地困难间的关系;明确文化和社区的特点,发现高危群体,如精神病患,和其他有需要的人群等,以便采用更适合的应对方法。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当地力量,从当地招募重建人员。应该先确认当地有能力的人员,并了解地方资源,包括当地的医生及其他资源(比如牧师、巫师等),总之,利用当地资源,需要识别当地心理援助资源的优势和局限[26]。
我国2008年以来三次伤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发生在比较偏僻的山区,当地政府、群众对于心理援助的了解和支持是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开展的关键。缺乏当政府和群众支持和理解的地方,心理援助工作明显地难以开展而且非常缓慢,从而严重耽误了灾后心理援助的最佳时机。此外,长期的、持久的心理援助工作也需要在当地培养出心理援助队伍,做到自给自足,因此,持续开展灾后心理援助,需要政府整合各方心理援助力量,共同实施灾后心理援助,从而让灾后心理援助变成灾后的常态事件。
[1]UDOMRATN P.Mental Health and the Psychosocial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in Asi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2008,20(5):441-444.
[2]张侃,张建新.5.12灾后心理援助行动纪实——服务与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7-8.
[3]EM-DAT.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DB].http://www.emdat.be/2010.
[4]UNESCAP&UNISDR.Protecting Development Gains:Reducing Disaster Vulnerablity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R].Thailand,2010.
[5]WHO.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after Disaster[R].Geneva:WHO,1992.
[6]SAXENA S.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Crisis Situation[R].Geneva:WHO,2005.
[7]KUN Peng,CHEN X,HAN S,et al.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Sichuan Province,China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J].Public Health,2009,123(11):703-707.
[8]KUN Peng,HAN Shu Cheng,CHEN Xun Chui,et al.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A Cross-Sectional Study among Survivors of the Wenchuan 2008 Earthquake in China[J].Depression and Anxiety,2009,26(12):1134-1140.
[9]WANG Li,ZHANG Yu Qing,WANG Wen Zhong,et al.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Adult Survivors Three Months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J].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2009,22(5):444-450.
[10]WANG Li,ZHANG Yu Qing,SHI Zhan Biao,et al.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Adult Survivors Two Months after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Psychological Reports,2009,105(3):879-885.
[11]JIA Zhao Bao,TIAN Wen Hua,HE Xiang,et al.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Survey among Child Survivors of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J].Quality of Life Research,2010,19(9):1381-1391.
[12]JIA Zhao Bao,Tian Wen Hua,Liu Wei Zhi,et al.Are the Elderly More Vulnerable to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A Population-Based Survey of Adult Survivors of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J].BMC Public Health,2010,10(1):172.
[13]LIU Zhi Yue,YANG Yan Fang,YE Yun Li,et al.One-Year Follow-up Stud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mong Adolescents Follow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J].Bioscience trends,2010,4(3):96-102.
[14]YU Xiao Nan,Joseph T F L,ZHANG Jian Xin,et al.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Reduce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t Month 1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10,123(1):327-331.
[15] FAN Fang,ZHANG Ying,YANG YanYun,et al.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Depression,and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 Following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J].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2011:in press.
[16]LI Shu,RAO Li Lin,REN Xiao Peng,et al.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J].PLoS ONE,2009,4(3):e4964.
[17]LI Shu,RAO Li Lin,BAI Xin Wen,et al.Progression of the“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PLoS ONE,2010,5(3):e9727.
[18]陈雪峰,王日出,刘正奎.灾后心理援助的组织与实施[J]. 心理科学进展,2009,17(3):499-504.
[19]黄飞,祝卓宏,王文忠,等.手机与纸笔测验的心理测量学等值性:以儿童版事件冲击量表为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1):31-33.
[20]张黎黎,钱铭怡.美国重大灾难及危机的国家心理卫生服务系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6):395-397.
[21]张侃.国外开展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一些做法[J].求是[J].2008,16:59-61.
[22]张侃,王日出.灾后心理援助与心理重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23(4):304-310.
[23]崔秋文.国外紧急救援管理工作简介[M].成都:2006.
[24]YOUNG B H,FORD J D,RUZEK J I,et al.Disaster Mental Health Services:A Guidebook for Clinicians and Administrators[M].Menlo Park,California:National Center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1998.
[25]APA.Helping Communities in Times of Crisis[M].APA.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9.
[26]WEISS M,SARACENO B,SAXENA S,et al.Mental Health in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s: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J].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2003,191(9):61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