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篇小说《大势》的对话
2010-11-04陈希我廖述务
/陈希我 廖述务
关于长篇小说《大势》的对话
/陈希我 廖述务
好作品就要达到象征的境界
廖述务:先说说书名吧。小说《大势》的诞生比十月怀胎还艰难。所幸,它没有流产,要给萎靡文坛一个惊喜。诞生往往意味着选择的丧失。这时,尤有必要追怀一下那两个近乎注定流产的书名——《中国》与《操》。这种放弃,差不多是复杂文化语境伏击的必然结果。想必,您和读者都会怀抱遗憾与惋惜。不过,在我看来,尽管“大势”二字有些折中和避让的味道,但也更令人叫绝,其语义相当丰富,几乎包含了前两个书名的全部内涵:对国族的反省与身体文化政治学的考察,以及对两者暧昧关联的追索。
陈希我:我很欣赏你说的,诞生往往意味着选择的丧失,我每部作品被印成铅字后的感觉就可以证明,很索然。这也许是因为我的过分苛刻,我承认我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似乎还谈不上完美不完美,因为我的作品,无论长的短的,哪怕是一篇随笔,都几乎不可能按原来的面目诞生。所以所谓的诞生,毋宁是被阉割的完成。当然这还不包括我在写时的自我阉割,我说写作是“冒犯”,我的作品常被认为把世界写得太不堪,但实际上我在写的时候,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阉割了。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是不一样的,我为自己写和为别人写是不一样的。我也是如此。所谓表达,在我,只是说真话和说谎话之间的挣扎。只不过我常会忍不住,任性了。
《操》是在我脑子里冒出的最初的题目,自己也觉得不可能用,一部名叫《操》的小说是不可能被出版的,于是就改换成《中国》。在出版的时候,我又想改成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女娲》。问题不在于是否用人名,而是其中的象征意味。哪怕是人名,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以至后来,我仍然想到的是个有象征意味的书名《势》,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大势》。阐释为中华民族走向大国的“大势所趋”,但是探讨的却是,在这种“大势”之下我们的“势能”。当然,这个书名的象征意味并不止这些,包括另一个人物的名字:王国民。我认为好作品就要达到象征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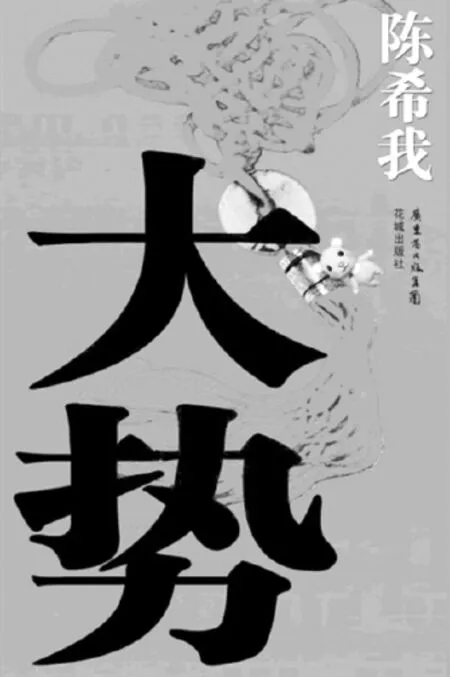
陈希我:《大势》,花城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29.00元
廖述务:确实,女娲、王中国、王国民等人名都具有隐喻色彩。这当中,“女娲”的命名值得深究。我们只要稍稍结合性别意识形态,就可以发现,其名字具有戏仿效果,寓示了一种文明形态,一种阴性、内敛、易被欺凌的农耕文明。女娲造人是我们的创世神话,是整个民族在神话学意义上的源头。整个民族之柔弱与坚韧,恰似一个静态、温雅的女子。对此,我们不由得会想起有关《河殇》的激进表述。不过,在《大势》中,柔弱(黄色文明)并不是一无是处,所谓怀柔四方倒是在“顺势”时体现了出来。这正是您反思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入口。
陈希我:“顺势”、“以弱克强”是弱者的策略,如果真是强势,就没有必要这样。从中国的武术和西方的拳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人不强,所以讲究顺势借力,讲究谋略。这是我们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谁叫我们弱嘛!关于女娲,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就是“补天”。小说中的女娲所以叫女娲,也就因为她的父亲企图“补”,她最后和她的男友佐佐木闹翻,佐佐木强暴她时,也一边说她身体有缺口,本来就是给男人填的。当然佐佐木是借用日本女神伊邪那美命的传说,在日本,女人有缺口,就要认这个“缺”。
中国人是不认,所以我们不甘的时候,就更加激进。你发现没有,对列强,我们更看重用外在的拳头来解决,比如义和团,李瀚祥的《火烧圆明园》里,僧格尔沁用拳头跟西方外交官巴夏礼比胜负。郁达夫在《沉沦》喊:“我一定要复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它本来也是弱者。所以在《大势》里,有日本学者菅野跟王中国的对话,他似乎比王中国更参透“顺势”。这是日本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是知弱,但不认(从好的方面说,也可以说是不屈),日本人则是知弱而服弱,从而让自己强起来。日本人是服从强者的,所以当中国强大时,它恭恭敬敬学中国,当美国占领了它,它服服帖帖学美国,所以他们的“国骂”不是“操”,是“马鹿野郎”。在中国,“指鹿为马”是一个关于道义的故事,但是在日本,则只是一个关于认知的故事:你认不认得鹿?
“势能”与国族
廖述务:对于“势”,人们的理解肯定是多层面的。“顺势”就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我对这个字做了语义考辨,“势”亦作“睾丸”的别称。《古今医鉴·脏气各殊论》中说:“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从这个含义来看,“势”是男根的代称,寓示一种雄性的力量,一种理性的无坚不摧。去势是阉割、宰制的形象代称,对男性而言无疑是奇耻大辱。这种文化心理,包含一种挥之不去的性别压抑关系——女性天然无势,因此如同宦人,是被歧视和凌辱的对象。这种解读,应该可算做是进入您这个长篇的一个可能的秘密通道吧。
陈希我:是的,势,指的就是“睾丸”,也就是男根,它体现了男人的性能力。小说中写到了书法中“势”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势”的概念在许多领域都存在,但其源头就是性能力。太监被阉割,于是“去势”,于是成了废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性,表面上看只是为了生殖需要,传宗接代,实际上这不是主要的。小说中的王中国因为生了女儿而沮丧,如果说是在农村,女性不能成为劳动力,女儿最终要出嫁,可以成为理由,那么在城市,已经不存在靠儿子养老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当今城市,女儿往往比儿子对父母照顾得更周到),传宗接代观念也日渐淡薄了,为什么他还有沮丧?其实是失败感。失败在哪里?因为你没本事,生了女孩了。据说生男生女还真的跟男方的性能力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把打开中国人心结的钥匙,那些不着边际的解释,应该重新审视。
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总有失败感,因为被外族欺侮了,我们失去了“势能”。而且,这种被欺侮在性上表现得更突出。《火烧圆明园》里,外国军队侵入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最刺激人的就是那个强奸中国妇女的场景。在列举日本侵华罪行时,一定会提到强奸,并且特别强调,比如“下到8岁女孩、上到80岁老太太都不放过”。性的屈辱,是最大的屈辱。也因此,遭受性屈辱者也负有了雪耻的责任。《火烧圆明园》里,那个被强奸了的女人,只能去跳井,边上一个老者对大家喊:“不要拉她,让她死了干净!”一个民族受难,首先是女性的受难。女性是弱者,更何况在中国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一直被歧视。但是吊诡的却是,女性在战争中又被赋予过于沉重的责任。一个民族要侮辱另一个民族,首先是侮辱它的女性,而被侮辱了的女性,不只代表了自己被侮辱,且代表了整个民族被侮辱。更可怕的是,女人还是母亲,这个被玷污的身体还可能繁殖后代,所以最好她自决,“死了干净”。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小说中那些中国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福建人,福建是被中原汉人征服的土地,汉人攻占了福建,把男人杀死,把女人赶进森林,脚上系上绳子,让征服者牵,牵上谁就是谁的妻子。王中国、王国民们就是这样的母亲的后代,所以其屈辱感跟普通中国人又是不一样的。
廖述务:确实是这样。不过我也注意到主体的变异,女娲不再是《火烧圆明园》中那个跳井的女人。在某些层面,她甚至是天真烂漫的哈日一族。在萨义德看来,主体“丧失”与精神“沦陷”,是后殖民时代的典型症候。这是一种遭人诟病的“遗忘”。饶有趣味的是,王中国、王国民等人因自身强烈的屈辱感,偏偏要把她立为贞节牌坊,这就不可避免要起冲突。王中国的死就是为这一冲突献祭的。这里其实无所谓贞节可言,它仅仅是捍卫男性自尊(势能)的面具,与虚伪的民族主义是孪生兄弟。
陈希我:民族主义总是出现在弱的民族,像中国这样的弱的民族又是以男性为主宰,所以他们是民族主义旗帜的主举者。但很奇怪,中国人本来是一盘散沙,怎么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就能那么团结集合?其实是因为,这些男人都有自己的需要。王中国的屈辱感其实在赴日前就有了,而王国民也欺侮中国人,在日本那个中国人聚居的“阵地”,中国人也并不团结,尔虞我诈,但是当跟日本人干的时候,他们就集合起来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需要。所以民族主义只是幌子,捍卫民族是假,捍卫个人尊严是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如果是捍卫民族,作为女性的女娲也是这民族一员,为什么就不能捍卫她的选择呢?捍卫民族,本来就是要捍卫民族里的每个人,民族是由每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个人权益都得到保护了,民族的权益才有所附丽,否则只能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王中国和王国民都是掌握权力的人)的伎俩。
廖述务:从您前面讲的可以看出,《大势》的一个意义向度在于,它特别强调了一种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将身体与国族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您的首创。整个近现代,作家们其实都被“东亚病夫”这个恶毒的殖民魔咒所笼罩。因国家的贫弱,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份认同均遭受严重的危机。废缠足,剪长辫,都是国族现代性的急切诉求。在当代文学中,身体走了两条路:一是被完全套上意识形态的工农制服;二是在各种传媒上,兴致盎然地跳起了收取小费的脱衣舞。据此,我们可以谨慎地推断,百年文学史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修辞残缺:身体是完全被政治、文化、商业所宰制的,它自身的苦恼与抗争都被忽略了。您让我们的身体真正显露出了峥嵘的面孔,它关涉到人类一些永恒的困境,而不仅仅是国族的被动承体。
陈希我:身体是身体,也是象征。“东亚病夫”就是拿身体作为象征。一个人身体不行了,就被认为其它也不行,特别是男人,身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时,是有自卑心态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把“奥运”及体育比赛上的胜利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体育是身体的。一个身体不好的人,首先就是希望身体好起来,一个弱者希望自己强壮,哪怕是成为强盗。至于道义,对弱者还是奢侈的,他只知道不择手段达到强大。看看当今社会上的许多言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体育毕竟只是体育,花拳绣腿,一个体育强国,仍然可能是弱国。这也就昭示了身体其实并不重要,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从身体上说,同属于东亚人种,身高甚至还不如中国,所以被叫做“倭”,“倭”就是个头不高、短小的意思。但是仍然被他欺负,尽管你骂他,但没有用。这就很说明问题,正如鲁迅说的,身体再强壮也只配拿去宰杀。身体不强壮,可以通过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强大,比如体制改革,从而也使身体强壮起来,比如日本人普遍身高现在就比中国人还要高。再回头看日本,日本也是很重视身体的,从明治维新,就开始重视国民的身体,实际上也是当时处在不自信状态中的日本人对身体的看重。日本人曾经也不自信,甚至现在还焦虑于被西方边缘化,在《大势》里,佐佐木后来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了?因为日本社会不景气了,日本景气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他总是受制于美国。这似乎是宿命。中国也在宿命之中,所以无论如何,王中国折腾也罢,仇恨也罢,宽恕也罢,都没有用。甚至遗忘也不可能。
“看”的哲学
廖述务:关于《大势》,一些评论家将其称之为您创作的一个转向。对此我有所保留。相对《冒犯书》《抓痒》,《大势》确实突出、强化了另一些东西,比如,在《我们的罪恶》中已经表达过的。所谓“转向”,隐隐有种劝您“改邪归正”的味道。我冒昧揣测:身体依旧是《大势》的重要主题,而且是它的得意之笔。中国人的虚伪在于,有关身体的,就必然有关堕落。在文化研究领域有所谓的“身体转向”,但在“神圣”的创作这里,它却成了忌讳,不管这个身体在文本里形态如何,意在说明什么,也不管作家是怎么“看”身体的。“写什么”依旧是今天作家们的形而上学。
陈希我:我想的是突破,而不是转向。突破与转向不同,突破是在同一个方向的运动,有力量的延续,而转向则不是。所以那些认为我改邪归正的表扬可以收起来了。从策略上说,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能这写写,那写写,要有一个恒定的写作面目,更不能什么时髦写什么。读者和批评家也不必要求作家“变脸”,那与其是新生,毋宁是毁灭。当今不少作家的覆灭就是例子。当然作为读者,这种期待是可以理解的,喜欢节目多样,但是作家首先是为自己写作,思考和趣味要有个一贯性,作家要有一猛子扎下去的勇气,哪怕死也不回头。当然如果能够突破就更幸运了,那将是更精彩的世界。《大势》跟我以前的作品比,确实企图突破一些东西,责编我《冒犯书》的人文社编辑看了后惊呼:“比《冒犯书》冒犯多了!”这冒犯,不只是身体。其实我的冒犯一直不只在身体,只不过大家总是被身体挡住了视野,排斥也罢,欢呼也罢。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将身体跟堕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也确实,某种意义上说,身体冒犯是最根本的冒犯,身体反抗是最大的反抗。我猜尼采在说“一切从身体开始”时,也是这么想的。性所以被视为洪水猛兽,就因为它是对体制的根本颠覆,所以萨德才长期被囚禁,所以才“万恶淫为首”,所以一场革命,如果没有触及到性革命,就是不彻底的革命。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当今中国“身体写作”已经泛滥,如果说当初写身体,还有反叛的意味,现在已经成了媚俗,走向了反叛的反面,不少作家像洒胡椒粉一样地在作品里点缀性描写。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的作品跟它们的区别,因为我在“看”,他们只是在“写”。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确实存在着只懂得“写什么”的问题,当然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写”也并非没有“看”,问题在于,你要怎么“看”。写身体只“看”到身体,那就问题不大。张贤亮从“改造知识分子”来“看”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相反王小波用身体抵抗“改造”,就有问题了。当然最没有问题的是江姐式的身体受难,这个身体已经不再是身体,而是身体的否定,是像齐泽克说的那样,是“超越了普通生理躯体的崇高躯体”。
必须说明的是,我笔下也并非没有“崇高”,我的人物大多是具有理想精神的。无论是《抓痒》里的男女主人公,还是《我们的骨》里的一对老夫妇,《罪恶》里的作为罪恶一环的那些人,包括《遮蔽》里的行苟且之事的那个残疾人。虽然他们不是完人,甚至还行恶,但是他们有痛苦,在彷徨。为什么有痛苦在彷徨?就因为他们有理想。在我们这时代,这就是理想主义了,旧的理想主义已经遥不可追,而且对处在现代困境中的人,无异于隔靴搔痒。他们甚至因此而偏执。《大势》里的主人公王中国无疑是偏执的,他活得比他周围的国人痛苦得多,为什么?就因为他有理想,他无法搁置自己的心灵。我记得一个批评家批评我的作品只有黑暗,没有“光”,我要告诉他,这就是“光”。比如《大势》里,能解决国族之间的问题吗?能将历史记忆遗忘吗?不能,所以作为弱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受虐升华为虐恋。这就是现代的理想主义。
廖述务:怎么“看”,应当会给当下文坛一个警醒。至于一些批评家还在纠缠所谓的“黑暗”、“消极”,不过是题材决定论沉渣泛起的后续反应。从黑暗中发现黑暗,批判黑暗,这是传统现实主义近两百年来一直恪守的创作方式。在加入现代性的大合唱之后,它很多时候还习惯于陷入一种偏于浪漫的发展主义逻辑,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进步了,“黑暗”就会随之烟消云散。相比而言,您却走了另一条路,在貌似光明的表象中发现了“黑暗”,在看似平静的地表,探测到了潜行的熊熊地火。《大势》中的王中国就是如此。在常人看来,他无端地身陷了个人战争的泥淖,毕竟有千百个退却的理由:他无需为生男生女焦灼不安,无需为女儿的未来操虑过多,也无需对政治的问题过问太多,至于民族主义更是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情感保健操……可以想见,这种固执源自作者自身的执拗。人物虐恋是作者自身精神虐恋结出的一枚苦果。作者内心的凄“苦”(精神虐恋)在日本文学中是很常见的。
陈希我:中国的价值观是成王败寇,虽然有成王之后的空虚,但是成王还是好的。我们历来缺乏讴歌失败者,讴歌另类,我们历来不讴歌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敢于不合时宜的,首先应该得到盛赞。中国历史上历来缺少另类,有的看似很另类,其实是与主流很契合,是同舟共济,只不过他是唱“二花脸”的。我将来会写一部小说谈论这个问题,拟名为《太阳》,这来源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每个人都需要信仰,就像小草需要阳光一样。”中国人没有信仰,所以我们的“阳光”只能是“王”,这是我们文化的问题。在这种文化哺育下,虐恋是难以被理解的。日本也没有宗教,好在日本能够从虐恋中让精神飘扬起来,于是跟我们拉开了距离,我们的文学被抛在后面,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不在一个级别上。实际上,虐恋是一种高级的精神追求,不懂得虐恋,就不能“看”到精神,而文学恰是要抵达这种精神的。我曾说过,文学不是比赢,而是比输。文学不是比快乐,而是比痛苦;文学不是比适宜,而是比不适宜。
作 者:陈希我,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抓痒》《放逐,放逐》等,两度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
廖述务,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