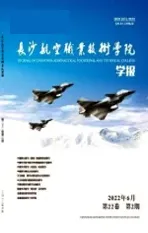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中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2010-08-15易燕明
易燕明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中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
易燕明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思潮,第一次较完整地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确立起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结果,就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法理与理性来对抗外国的侵略,所以湖南维新派极力宣扬公法观念和主张文明排外的思想。不过,湖南维新思潮中的民族国家观念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即对帝国主义侵略性一面缺乏准确的认识。
湖南维新思潮;民族国家;公法;文明排外
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是近代世界列强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统治,拥有一个组织的政府——对外能维护国家主权,对内能有效管理人民。在传统哲学中,是不存在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映民族主义思想的“华夷之辨”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和华夏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而且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认为华夏文明高于其它民族的文明,以文化的优越感来反对异族文化的侵蚀和抵制异族的侵略。正是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造就了人们的自我中心感,造就了无国界的“天下”观念。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政治和文明上的强势地位消失了,处于了挨打的地位,再坚持无国界的“天下”观念,就只会导致民族和文化的消亡,这就有必要突显出国界观念来,以遏制帝国主义的入侵、保持华夏民族的生命和传统人文之根。于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得到了强调和确立。
湖湘文化传统中民族意识历来是十分强烈的,从胡安国伸张“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到王船山将华夏夷狄与君子小人当成天下之二“大防”,表明湖湘学人特别强调民族大义。这种民族主义精神直接为19世纪末湖南维新思潮所继承,并且进行了改造,确立起以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从而超越了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而确立起民族国家观念的结果,就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态度不再是盲目排外,而是以法理与理性来对抗外国的侵略,所以湖南维新派极力宣扬公法观念和文明排外的思想。
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甲午战败,举国为之震动,彻底摧毁了国人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带给整个中国更大的民族悲情。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强调国家的主权,确立近代国家观念以凝聚民心民力就显得尤为迫切。正是这种危急的时势,促使湖南维新派致力于近代国家观念的确立。
首先,湖南维新派明确界定了中国有自己的人口与领土范围,并指出要熟悉他国的领土范围。如唐才常说:“夫中国地方二万万里,则非小脊矣;民有四万万众,则非寡弱矣。”[1]《湘学报》也指出:“划疆自守,局以川原,险要所关,实资防捍,则界务宜悉也。”[2]也就是与外国交涉时,要深知各国的领土范围,以捍卫自己领域,防他人侵占。
其次,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对外能维护国家主权,对内能有效管理人们的组织政府,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如唐才常说:“凡国但有民权国权,能管理界内一切人民物产,即能与他国议战议和。”[3]其实说的就是政府职能,而且民权观念的提出,表明湖南维新派所主张建立的合法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只有它才能代表民意,才能真正有效统治自己的人民与领土,这表明湖南维新派是近代意义上来理解国家观念的。正因为如此,湖南维新派还对清政府对外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对内则压迫人们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如《湘学报》说:“自康熙二十八年至于今,立约换约近五十次矣,受蒙蔽而不知,被迫胁而不耻,虽土地之广,于万国中班在第四,而自主之权,渐为乌有,岂袭一统之虚名,固甘让人以动力哉!”[4]由此感叹道:“以四千三百余万方里之土地,四万万之人民,求其洞达中外,能维一国之权者乃不可得,而海疆各国环伺耽耽。”[5]从这种痛述中表达了湖南维新派企图建立一个能管理人民、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真正政府的愿望。
最后,完整表述了近代国家的主权观念。主权观念是近代国家观念的核心,最能反映近代国家的本质特征。主权不仅使国家具有法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权,同时也是使国家与其它政治单位,如省、州等相区别开来的基本标志,简而言之,主权就是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对外的独立权。湖南维新派对国家主权的这种内涵作出了明确的说明,如唐才常认为一个“自主之国”,应有以下权力:
一能增改其国政,他国不得与闻;二能管辖国内之属地,他国不得占据,国内所有产业由本国自理,不准他国阻饶;三能自保其国,预备战守之法;四能振兴国内商务,俾致富强;五能于界外得新地以为属国;六有全权管理一切人物,即在本国界外者亦能管理;七应保护本国之人,任往何国,如两国民人负欠债项,可以理问,此西人自主之公例也。[6]
这就对主权作出了全面而明确的说明,并且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唐才常还揭示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陷入主权逐渐沦丧的悲惨境地,他说:
今以中国衡之,则国之属地,如安南缅甸琉球高丽台湾乌苏里河以东,沦异域矣;国之产业如上海租界,华人不能买,而西人主之,而福州乌石山九江庐山,盗卖官地之案叠起,非国律所能治矣;国之商务输英人数千万矣,国之游氓见逐花旗,黑奴不若矣。……此犹显失自主之权,其隐失自主之权,……若之何熟视无睹也。[7]
由此可知,湖南维新派已经看到了中国在属地、产业、商务各个方面都丧失了自主之权,中国政府已不能自主管理自己的人民,这种对不能自主的醒觉以及对主权的强烈要求,表明了湖南维新派已经有了维护主权的自觉,对主权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的层面,而且有了实践的自觉,标志着近代国家观念的正式形成。
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来建立国家的,这一点也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内容。湖南维新派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论述,但从他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湖南维新派主张以汉族为基础来建立民族国家。这从他们的反满言论中就可以看出,不过湖南维新派主张以汉族为基础来建立民族国家,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华夷之辨”,从文化上的优越性来反对异族的统治,而是对满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的反对,在这里满族统治者已不成为我们的同胞,而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帝国主义帮凶,所以反满是和反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就指出:清政府不仅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相反,为了图谋“自全”,竟甘心出卖祖国利益,不惜将领土“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于是,谭嗣同果断地提出:“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8]这里,谭嗣同突出了华人观念,并要华人将满族统治者排除在同类之外,其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蕴含了以华人为基础来建立华人之国家的思想。但谭在这里控诉的是异族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而不是满、蒙等少数民族本身,因此他们并不反对以汉族为主体联合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来建立统一的国家。“华人”这一观念可以说便是这种联合意识的反映,而湖南维新派联合光绪帝进行维新变法的行为也表明了这种联合意识,所以排满已不是对汉族旧王朝的留恋,而是一种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向往。不过在谭嗣同那里,排满还是含有反对异族统治的种族意识的,所以其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国家的观念,还是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的。直到梁启超后来将民族观念和联合意识整合起来,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并赋予较为科学的内涵:“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9]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鲜明的体现出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完整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至此才最终确立起来。
通过近代国家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建国观念的形成,19世纪末的湖南维新思潮已经较为完整地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通过确立起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就彻底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其他民族国家,从而将中国和西方诸国放在了同一架天平上,为西方文明的引入打开了一个思想的缺口。同时,通过确立起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也使人们真正意识到要确保一个民族国家的版权、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确立中华民族在国际中的历史地位,就必须通过国际法来作保障,而不是由文化的高低、优劣就可以确保的。这就促使人们去掌握公法,利用公法来捍卫国家的主权。
二、公法观念的确立
公法也就是国际法,是指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准则,正如唐才常所指出:“国与国交涉,设法以联络之曰交涉公法。”[10]湖南维新派确立起民族国家观念,但真正要使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并列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懂得公法、利用公法、遵守公法。所以湖南维新派不仅确立起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公法观念。用公法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准则,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正因为如此,在《湘学报》上设立的“掌故学”与“交涉学”两个栏目里,湖南维新派都对西方公法观念进行了大量的介绍。从这些介绍,足可看出湖南维新派对其的重视,也可以看出湖南维新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公法观念:
首先,从公法的形成来说,湖南维新派都认为是根据天然之理和人们积累而成的习惯条例形成的。如《湘学报》说:
公法家言,人生而具天然之理,好善恶恶之性,人与人交际,则有分所当为分所当得之事,故国内相关,必有治民律法以定其程,是为一国之公法,公法之根源生于天然之理,与行惯之规例,是故有天律,有人律。公义公正公便公理谓之天律,国家所用之律例,历代相承之律法,是谓人律。[11]
正是由于公法出于天然之理,所以公法就是公正无私的,所以它就能作为国际交往的准则。虽然公法观念源于西方,但湖南维新派并不认为公法就为西方所独有,而是将中国古代的《春秋》与国际公法联系起来,认为《春秋》符合公法之旨,从而将公法观念与《春秋》之旨会通起来。如唐才常说:
今夫《春秋》,上本天道,为性法出于上帝之源;中用王法,为例法出于条约之源;下理人情,为民权伸于国会之源。故内圣外王之学,不过治国平天下。平之一义,为亿兆年有国不易之经。即西人之深于公法者,罔弗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登峰造极之境。[12]
湖南维新派将公法之源归于“天然之理”和“相沿之风俗”,表明湖南维新派对公法的形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他们将公法观念与《春秋》之旨相会通,认公法之理为《春秋》之旨,实质上带有以传统人文理想来规导近代国际政治格局的良苦用心,对公法观念的理解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湖南维新派之所以着力突出“平之一义”,正是试图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平等的理想之上,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对等型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民族国家格局,这实质上是继承了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所内含的人文理想,反映了近代世界被侵略民族和弱小国家的声音,表明了他们对世界未来文化格局和政治格局的美好期望,对于建立新型的对等型世界文化格局和世界民族国家格局,意义深远。
其次,从公法的实现来说,湖南维新派已经认识到自强的重要性。虽然湖南维新派对公法观念的理解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是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在现实的国际形势中,往往是强凌弱,大欺小,像欧洲列强,背信而贪利,恃强而凌弱,即使有公法,也无法制止他们侵略其他民族的野心。《湘学报》对当时强国之蔑视公法、欺侮中国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说:
我中国四万万人之众,神州三百五十方万里之大,而受恫喝若此,其何故也,盖西人视我为公法外之国,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与之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13]
由此可以看出,公法并不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公法,而成为列强之间的公法,对于弱小国家来说,西方列强往往不遵守公法,所以仅凭公法是抵制不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要真正发挥公法的作用,还必须以自强为基,这就与过去的公法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公法刚传入中国时,人们认为其很完美,作用很大,相信它就可以保卫国家的主权。而湖南维新志士已经认识到国际法的作用因国家的强弱而异,只有自强,方可借国际法与强国论争,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如唐才常说:“要之虎哥一书,虽情法奥窔,而必先自强以为不拔之基,庶几情法得行于中国也。”[14]湖南维新派对公法观念的这些认识,表明了湖南维新派具有理性的一面,对公法观念已有了完整而深刻的认识。
最后,湖南维新派在对公法的宣传中贯注了经世的目的,主张充分利用公法,挽回已失的利权。湖南维新派认识到虽然西方各国未必都能尽遵公法,但这不是公法本身造成的,世界各国的交往还是需要公法来维持的,也只有通过公法,才能捍卫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自主权。所以维新派极力呼吁国人加强公法的学习,要求士大夫们人人讲求交涉之学,以真正掌握公法,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如唐才常提出了设法律科,开中西条例馆的主张,他说:
余谓无论中西律例,急以开条例管,设法律科为要。日本维新以来,于大学中设立文科,使诸生研求律例,一经考录,充作律师,其门曰代言事务人。由是偶遇西人交涉案件,每能援东西律例,断断与之争辩,故近来美国与日本订约,许复其自主之权(中国即此一事,久失自主之权,而不能复,何论其余?噫!)[15]
湖南维新运动高涨时期,唐才常、毕永年还在长沙创立了公法学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国际法的学术团体,表明湖南维新派对公法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且上升到实践层面,他们已经将力图从法理上收回国家主权的主张化为实际的行动。正如王尔敏说:“其活动中心,虽然是在探讨国际公法,而最终的目的则在于使人认识主权之重要,从而作法理的争取恢复主权。”[16]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湖南维新派对公法观念已经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这进一步促成了民族国家观念与主权观念的形成,并为中国与他国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平等参与到全球化运动中找到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和手段。
三、文明排外的思想和对近代帝国主义的认识
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对外国列强,湖南维新派主张用公法与之论理争权,对国内人们来讲,则反对盲目的反洋教斗争,提倡文明排外的思想。这成为南学会讲学的重点,也是《湘报》宣传的重点。
《湘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表明要善待外国的游历者,反对无故闹教,殴打洋人的事件,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他们主张文明排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通商传教乃成为国际间的一种正常交往方式,因此应该理性对待。如唐才常认为:“通商传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彼通商于我,我亦可通商于彼;彼传教于我,我亦可传教于彼。”[17]所以应该友好对待外国的游历者和传教士。皮嘉祐也在《醒世歌》中说:“中国既与他讲和,客礼待他是礼仪,我是主人他是宾,何得无故打洋人。”[18]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盲目排外不过是徒增祸端,造成国家灭亡而已,如皮锡瑞说:“若而人者(指闹教者——引者著),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19]陈宝箴在南学会第一次讲学中也声称:“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变故既起,徒以上贻君父之忧,下为地方之祸,不更可耻之甚哉。”[20]从这些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里,我们能深深感受到湖南维新志士那种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至诚,那种企图防止闹教而亡国的良苦用心。
反对无故闹教的“文明排外”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与公法观念的提出一样,反映了湖南维新志士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已具有较为理性的一面。他们主张国与国之间正常往来,如通商游历传教等等,这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了,而是看到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主张打破宗教界限、民族隔阂,以实现多教并存。而且在当时的局势下,“文明排外”也无疑可以减少与西方列强的正面冲突,为中国的改革赢得时间。因为即使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应讲究策略,盲目笼统排外,只能付出沉痛的代价,是不值得的。因此,“文明排外”显然比徒以泄愤以反洋教的方式高明得多,理性得多,但却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面认识不足,甚至认识错误。
首先,湖南维新派天真地认为,只要我们不犯事,不闹教,西洋就不会侵犯我们。如皮嘉祐说:“我不惹他倒还好,若不与他为难,洋人岂来相扰。”[21]陈宝箴也说:“内讧不作,则外侮不来,和气流行,则患气消息,湖南永为乐地。”[22]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完全归结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就基本上是站在帝国主义的角度为他们作辩护了。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由于闹教引起的,即使人们安分守己,也阻止不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
其次,湖南维新派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为进行极力美化,认为他们的侵略只是因为同情中国,是要帮助中国推翻君统,建立民主社会。如谭嗣同说:“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23]尤其对日本,更是倚为知心好友,唐才常说:“(日本)日日以亡中国为忧,中国亡则黄种瘠;黄种而瘠,日本危哉!于是上自政府,下逮草野,群有心救世之人,创立兴亚议会,冀扶黄种,保亚东,毋尽为俄德诸雄蚀。”[24]这表明了湖南维新派人士极为幼稚单纯的一面,被外面的表象所迷惑,虽意识到德、俄的瓜分野心,但对英、日的企图却丝毫未察觉到。
最后,湖南维新派还幻想依靠帝国主义联盟来振兴国家。如唐才常就企图联合英、日来对付俄国。谭嗣同则还曾与日本派遣的三个特务分子会晤。此三人虚意表示愿与中国合作,以图互强,谭嗣同对此深信不疑。他在南学会的讲演辞中说:“鄙人顷在湖北,晤日本政府所遣官员三人,言中日唇齿相依,中国若不能存,彼亦必亡。故甚悔从前之交战,愿与中国联络,救中国亦自救也。并闻湖南设立学会,甚是景仰。自强之基,当从此起矣!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25]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毫不觉察,反而认敌为友,这表明以年青人为主体的湖南维新派,多具有天真和理想的一面,对政治之险恶和帝国主义的野心认识不足。
总的说来,湖南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曲解的,这反映了他们对当时的整个中国形势、世界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不在外而在内,只要内强了,国就可保,种就可存,因此他们的重点也就放在宣传维新变法上,甚至企图依靠外国的帮助来获得变法的成功。这种内省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没有去多加分析、认识,从而产生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严重错误倾向,而对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则是一味的贬斥,没有看到其爱国的一面,而去加以依靠。这也反映了湖南维新思潮中民族国家观念的缺陷,他们确立起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缺乏准确的认识。
[1]唐才常.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摺[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154.
[2][4][5]交涉学第二[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2526,2523,2524.
[3][7][10]交涉学第四[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1966:2588,2582,2580.
[6]交涉学第三[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 1966:2582.
[8][23]谭嗣同.仁学[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342,344.
[9]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75-76.
[11]掌故学第四[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 1966:661-662.
[12]唐才常.公法通义自叙[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96.
[13]交涉之学[M]//湘学新报.台北:台湾华联出版社, 1966:2760.
[14]唐才常.论情法[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36.
[15]唐才常.交涉甄微[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46.
[16]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0.
[17]唐才常.辨惑(上)[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167.
[18][21]皮嘉祐.醒世歌[J].湘报,第27号.
[19]皮锡瑞.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五次讲义[J].湘报,第25号.
[20]陈宝箴.陈右铭大中丞南学会第一次讲义[J].湘报,第1号.
[21]皮嘉祐.醒世歌[J].湘报,第27号.
[22]陈宝箴.陈右铭大中丞南学会第七次讲义[J].湘报,第31号.
[24]唐才常.论兴亚议会[M]//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178.
[25]谭嗣同.论中国情形危机[M]//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398.
[编校:丁海燕]
Establishment o f Modern Nation-state Concep ts in the Reform Trend of Thought in Hunan at the 19th Century End
YIYanm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Jiangxi 330022)
The reform trend of thought in Hunan at the end of the19th century established themodern idea of nation-state,thus they no longer took the manner of b lind anti-foreignism in process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ut resisted foreign invasion by jurisprudenceand rationality;therefore they publicized the idea of public law and the thought of civilized anti-foreignism.But themodern idea of nation-state in the reform trend of thought in Hunan had serious limitations,namely,they lacked accurate knowledge in imperialism's aggressiveness.
reform trend of thought in Hunan;nation-state;public law;civilized anti-foreignism
K 256
A
1671-9654(2010)02-068-05
2010-04-05
易燕明(1977-),女,湖南岳阳人,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book=82,ebook=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