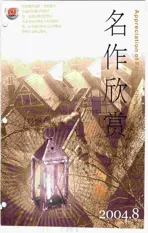郁达夫作品中的自我想象与自我框限
2010-08-15赵艳花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赵艳花(郑州大学文学院, 郑州 450001)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位作家像郁达夫一样对描写自己有如此强烈的、持续的需求,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活动着自己的影子。自传形式的运用往往使读者将他笔下的人物与他本人等同起来,而作者也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误解,“不断进入自己的自我形象”①,用小说、自传、日记塑造、确证与发展一个超越作者本人的连贯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者想象的产物,具有极大的虚构性。在以往的郁达夫研究中,人们忽略或者低估了在个人真实经历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叙事策略对郁达夫取得成功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忽略了这种叙事策略对他后期创作进入低谷所应负的责任。
一
从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开始,将“一己的体验”如实率真地表现出来就成为郁达夫一贯的创作态度,他所有的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分享着作者外在或内在的特征。他们有着与郁达夫相似的人生经历:留学日本,由于弱国子民的身份而受到日本国民鄙视与欺侮;回国后找不到理想的职业,只好卖文为生;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深陷灵与肉的冲突不能自拔。他们的内在气质也与作者基本吻合:忧郁、敏感、愤世,在生人、尤其是女性面前因害羞而显得十分窘迫和尴尬,同时又富有才华,言行风度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这一系列人物反映出了整体的郁达夫,从《沉沦》时期敏感多疑、怯懦忧郁的青年忧郁病患者,到《茫茫夜》时期愤懑偏执、荒唐自戕的颓废派文人,再到《迟桂花》时期尘埃落定、气定神闲的中年文士,勾画出郁达夫由激烈归于平静的整个人生图景。
尽管郁达夫在自叙传作品中提供了相当多与自己相符的细节,但如果把这些人物与郁达夫本人完全等同起来,却落入了作者的叙述圈套。在郁达夫的种种叙述中,真实与虚构完全被糅合在一起,根本无法辨别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孙伯刚在《郁达夫外传》中指出郁达夫日记、书信中存在诸多与事实不相符合之处,日记与书信尚且如此,在可以加入更多虚构的小说创作中就更不能期待得到完全的真实。《迟桂花》中的主人公“我”的名字就是“达夫”,曾在日本留学,写过小说《南迁》,但小说末尾的附注却声明:“读者注意!这小说中的人物事迹,当然都是虚拟的,请大家不要误会。”②这篇小说实际就是作者在1932年秋天偶然闻到桂花的香气之后随意铺演出来的,翁则生和莲儿在郁达夫的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同样,《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因生活窘困不得已卖掉了妻子送的金戒指,这一细节同样出现在《茑萝行》里,说明它具有某种真实性,但《银灰色的死》中妻子病死家乡显然又是虚构的。真实细节的存在使整个作品具有了鲜明的自传色彩,虚构成分的加入却导致其中的自传因素变得无法确定,使郁达夫的每部作品“既不能说完全是想象的,也不能说完全是真实的,而是两者巧妙的结合”③。
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认为:“自传性叙事没有任何理由在作家的非自传性创作世界之外另树一帜,何况自传维度拥有以隐蔽方式显现的无限自由。”④郁达夫正是利用了自传体叙事拥有的以隐蔽方式显现的无限自由,利用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与体验塑造了文本中超越自我的“自我形象”。他的创作实践不仅证明了“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⑤,也证明了作家的自叙传(包括日记和自传)同样可以是文学作品,是一种将生活文学化、“自我”形象化的手段。悲剧式的出生与美好的初恋、地狱般的留学生活与炼狱般的回国生活、轰轰烈烈的恋爱与沸沸扬扬的离婚,如果不是郁达夫的笔让这些记忆变成文字,如果不是他有意无意通过想象将这些记忆美化或丑化,他的一生不可能在时人和后人眼中充满传奇的色彩。通过将生活文学化,郁达夫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他在作品中提供真实的信息,也提供虚构的信息,这些信息就像不同的碎片,通过时间与事件叠加、汇聚在一起,最终树立起一个超越郁达夫本人的自我形象。
二
1921年10月,《沉沦》出版,虽然得到的评价毁誉参半,但三万余册的发行量表示郁达夫和他塑造出来的那个自我已经牢牢把握住了读者的视线。之后的绝大部分小说仍是作家利用自己的真实经历进行加工后的产物,再加上同一时期的日记与散文作为补充,郁达夫想象中的自我形象逐渐丰满。上个世纪20年代,郁达夫在文坛上的影响仅次于鲁迅,这是他的自我想象最为集中也最为精彩的时期。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与散文、公开发表的日记记录着“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记录着“他”情绪的曲折走向,由于正切合了时代的症候“,他”的愤懑与感伤变成共同的愤懑与感伤“,他”的颓唐与痴狂引起的更多是同情而不是贬斥,更重要的是“他”的大胆暴露满足了大众的窥私心理。郁达夫把“他”创造出来,“他”则将郁达夫造就成名人。郁达夫的著作出了名“,使他成了一名众所周知的人物,从而进一步使他进入自己的自我形象。……这样一来,举止行动成了习气;习惯成了癖性;他个人的弱点成了大家的财产”⑥。《沉沦》等作品的成功使郁达夫意识到自己的个人经历具有的巨大价值,如果说在创作的开始阶段运用自叙传形式还是出于偶然,那么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始终坚持这种形式表明郁达夫已经很自觉地在利用它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效应与心理效应。他知道读者喜欢在他的作品中看到那个“郁达夫”的形象,于是他开始纵容他们的这种心理,并不停地在以后的作品中满足这种心理“,郁达夫”的形象不断重复出现,使他的作品变成一系列连续的自传。
一贯的自叙传特色逐渐造成了读者的思维定势,在阅读郁达夫的新作之前,所有读者会事先认定书中的人物就是作者的化身,其中一定还是充满着令人伤感的片断,并“立刻就会构想出那主人公的一定的性格,而且准备好了他们的同情”⑦。当这种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迟桂花》发表时,很多读者都希望它是作者自己生活的写实“:为了篇后‘读者注意!这小说中的人物事迹,当然都是虚拟的,请大家不要误会’一段蛇足的附注,当时着实感到惆怅,说重一点,简直是一种幻灭的悲哀。深怨作者不该在空绣阁之后,一下子又把读者从里面推出来,使他成为呆立画壁下的朱孝廉。”⑧虽然造成这种心理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读者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混为一谈,但与作品中过多的暗示并非毫无关系。郁达夫在小说中采用的很多自传性事实,即使去掉或更换也无损于主题的表达,但他对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真实信息这种做法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郁达夫的感伤艺术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与时代空气已经消失了,对个人感情、情绪的抒写迅速被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叙事所代替。天生的敏感促使郁达夫根据时代的节奏转换自己的方向,他开始在作品中加入写实的因素,试图把握广阔的社会,塑造一些“非我”的人物。但对自我情绪抒发的过于注重,阻碍了他对他人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那些“非我”的人物与丰满的自我形象比起来总是显得过于苍白,流于概念化、平面化。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之后所谓具有了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中,自我形象似乎不再像先前那样始终居于中心的位置,但郁达夫也没有放弃对“我”的塑造。在《薄奠》中,作者表现的重心不是人力车夫的故事,而是“我”对处于相同经济窘况的车夫的同情。整个作品只突出了一个身处窘境却又对劳动者充满同情心的自我形象,与之相比,宏大叙事成则了无根的漂浮物,使小说成为“政治风云与生理苦闷的勉强混和”⑨。郁达夫对新的艺术领域的探索得到的更多是批判而不是赞赏,这颗文坛之星似乎要陨落了。
上世纪30年代的《东梓关》《迟桂花》《瓢儿和尚》等小说使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登上了另外一座高峰,他在转换方向以后重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艺术风格。那个自我形象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他”不再像前期那样狂热地发泄自己的苦闷,强烈的感伤被淡淡的忧郁所代替,作者也不再将“他”勉强放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之下,而是让“他”在恬静淡泊的自然中平复现实生活带来的倦怠。徐竹园、翁则生与瓢儿和尚都是自我想象仍在继续的产物,他们身上分明显现出中年以后倾向归隐的郁达夫自己的影子,虽然“他”与前期相比在心境上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对现实的难以释怀、闲适背后的苦涩等方面仍然可以辨认出那个永远不变的“郁达夫”。
郁达夫对自我的想象为他带来了声誉,但这种想象最终变成了一种局限的牢笼,对自我塑造的迷恋使他几乎已经被这个想象中的形象所异化,以至于无法再去开拓新的艺术空间。虽然上世纪30年代的创作对这种危机有所缓和,但毕竟已经是明日黄花,郁达夫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可以说,郁达夫的自我想象既成就了他,也打败了他。
①③⑥ 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节译)》,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581页,第567页,581页。
②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350页。
④ 安妮·居里安:《自传的诱惑》,施康强译,《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48页。
⑤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80页。
⑦ 韩侍桁:《〈迷羊〉》,见邹啸编选:《郁达夫论》,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17页。
⑧ 韩刚:《读郁达夫先生的〈迟桂花〉》,转引自王观泉:《颓废中隐现辉煌》,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38页。
⑨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