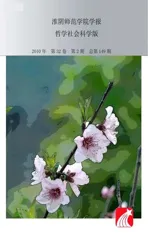论科学划界的标准
2010-04-11周文华
周文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论科学划界的标准
周文华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在科学划界问题上,库恩用科学史的实例使人们认识到逻辑主义的科学划界的绝对标准之谬误;主张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了范式是这个领域成为科学的充要条件,开创了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观。把这种相对主义推向极致,就导致费耶阿本德、劳丹、罗蒂等人的反对科学划界的标准消解观。相对标准观不能把占星术等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消解观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让伪科学有生存的借口。之后的多元标准观越来越复杂,但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科学划界。本文把可证伪性、实质普遍性、一致性和超余内容性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出了一个规范性的对科学的定义。这个划界标准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能够排除形而上学和伪科学,也能得出人们以为科学通常都具有的各种特性。
科学划界;实质普遍性;波普;库恩;拉卡托斯
一
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包括伪科学)?有无科学划界的标准?如果有,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这个科学划界问题,曾被波普 (Karl Popper)称为“康德问题”[1]8,“是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所有的认识论问题都能归结到这个问题”[2]。但对科学哲学中的这个焦点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统一的看法。
现代科学哲学的主流自逻辑经验主义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致有四大类型:(1)逻辑主义的一元的和绝对的标准观;(2)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观;(3)后现代主义的标准消解观;(4)多元标准观。当然,每一类型还可作进一步细分。例如,对逻辑主义这一类型,应区分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这四类观点从它们出现的历史顺序看,又对应于科学哲学发展的四个时期,并且后面的观点既是对前面的观点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生动体现。就是说,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理论,其发展的趋势是:从绝对到相对,从一元到多元,从精确到模糊,从主张有标准到主张无标准 (消解标准)。这里要指出的是,关于科学划界的这四大类型理论 (以及属于各类型之下的更多的具体理论),并非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而是仍然处在相互竞争之中。
我们认为,已有的这些理论都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缺陷,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这些理论提出批评 (只及一点就够,不求全面。因为本文不是对某一理论的综合评论。再说,只要有一个缺陷,就说明它有改进的必要),而在第四部分给出我们对科学的新定义。由于文献上对逻辑主义的批评最多(我在“逻辑主义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两种划界”[3]一文中也已指出一些),所以本文只对后三种类型加以批判。在此之前,我们要讨论一下科学划界的几种含义。
二
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有多种理解:有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的划界,有科学方法与非科学方法的划界,有科学活动与非科学活动的划界,有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的划界,有科学态度与非科学态度的划界,有科学组织与非科学组织的划界,等等。就是说,关于科学划界,要划界的对象是什么,可以有多种解释。
不过,这些不同意义的科学划界中,最重要也最为困难的问题,是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划界问题,它是解决其他意义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的基础或参照物。
例如,假设我们已经有了对科学理论的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科学活动:科学活动就是从事探索科学理论的实践活动,其他的活动不是科学活动。换句话说,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于求知,即在于建立或获得科学知识。而知识的主要形态就是理论。对理论的质疑、检验、比较、演绎、证实或证伪,都是为了获得科学理论。一项活动是科学的还是迷信的、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一看目的就不难知道;这是由于人的目的能够引导其行为。相反,如果不考虑活动着的人的真实目的、内心理念、思想理论,其活动就是难以理解的。从事科学实验与做实验的样子在活动的外表上也许没有什么区别,但本质上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根据目的来断定一项活动是不是科学活动,也是不容易的,问题在于目的的内在性。我们对于自己行为活动的目的可以是清楚的,但他人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尤其是从事伪科学活动的人,他们有的不会诚实地说出自己的行为目的),则不是一个简单的可判定的问题。但是他们所依据的理论、他们所宣称的理论则往往较容易获知。科学活动所依据的理论是科学的。如果所依据的理论是不科学的,那么就可以质疑该活动是不是科学。
定义了科学活动,就不难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科学组织与非科学组织。因为科学家就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科学组织是以科学家为主体的组织,或者是为特定的科学目的而建立的组织。
而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的划界,取决于对领域的理解。领域可以指认识领域或思想领域,也可以指实践领域或行动领域,也可以包含这两个方面。但科学作为实践领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其核心内容也就是科学活动。而对于作为认识领域的科学,其表现形式和中心内容也是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科学理论的形态呈现、保存、学习和流传的;而科学的物质成就则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在充分的科学理论支持下,利用自然资源不难展现科学的巨大物质力量和成就。
就认识领域而言,诚然可以把认识者 (人)和认识对象 (世界)都考虑进去,甚至把认识者的活动都加以考虑 (这就扩大到实践领域了),但认识者的认识仍然表现为一个个的命题;它们或者是观察命题 (作为认识者的直接经验),或者是理论命题 (这里并不意味着在理论命题与观察命题之间有严格的二分)。而且,许多观察命题被概括到理论命题中,加上观察也渗透着理论,理论在整合和建构人类认识。认识也常常以理论的面貌出现。所以,认识的核心是理论,因为理论就是普遍性的认识。认识领域中理论的性质,必然决定整个认识领域的性质。当然,理论认识与其他的具象的认识必然有一种合理的关系,它们实际上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既然科学无论是作为认识领域还是作为实践领域,抑或是兼而有之,其核心内容或者是科学理论,或者依赖于科学理论;所以正确地解决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划界问题,也就解决了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的划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理论脱离其所属的领域而单独地进行划界。
至于科学方法,有两种理解:一是从事科学研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因而也就是科学活动)的方法;一是作为达到特定目的的方法,这个方法因而也就是手段。
作为手段的方法有是否科学之分:符合科学理论的方法、受科学理论指导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方法。当然也有功利性的定义:称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为科学的方法,或称易于达到目的的方法为科学的方法,否则是非科学的方法。功利性的定义是对“科学”一词的借用。之所以能这样借用,是因为这两个定义 (对作为手段的方法的定义)有相通之处:受科学理论指导的方法一般易于达到目的。所以,“科学理论”这一概念对“作为手段的方法”是否科学有决定性作用。
至于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科学方法,它有什么特点,这方面我同意费耶阿本德的看法 (Paul Feyerabend):科学的方法多种多样,“怎么都行”,包括梦想,而不应该人为地设置禁区。当然,有一些方法可以特别地被称为“科学的”,因为它们在探求科学理论上是富有成效的好方法,较之于别的方法更富有成效。但它们不是可用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
最后让我们看看科学的态度与非科学的态度的区分:科学的态度是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时的通常的态度。它是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是不盲从权威的态度,是顽强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怀疑和探究的精神。用波普的话说,也就是批判的和理性的精神。与之对立的就是非科学的态度。
科学与宗教与艺术的不同在态度上表现得很突出:宗教认为信仰大于一切;科学认为真理大于一切;艺术认为美大于一切。唯有哲学可能来协调这三者。
三
逻辑主义提出的科学划界问题,很明确地就是关于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划界问题。只不过逻辑主义 (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还认为,对于一些单个的句子或命题,就有可能根据其是否可检验 (可证实或可证伪)来划界了。因为逻辑经验主义有一个判断句子是否有 (认识)意义的标准,对此亨普尔 (Carl G.Hempel)是这样说的:“一个句子作出了认识上有意义的断定,因而可以说它是真的或假的,当且仅当,或者 (1)它是分析的或自相矛盾的,或者(2)它能够,至少原则上能够用经验来检验。”[4]他们认为所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都是无意义的,因而有意义的句子都是“科学的”(在第一种科学划界的意义上[3])。所以他们的科学划界标准与意义划界标准是同一的,但这个标准依赖于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二分。到了 20世纪 50年代,蒯因 (W.V.O.Quine)等人强有力地反对分析与综合的二分,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5],这与迪昂 (Pierre Duhem)早就指出的“物理学家从来也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经受实验检验,而只能使整个假设群经受实验检验”[6]交相辉映,成为著名的“迪昂—蒯因命题”。于是“只有整个理论才有可能接受验证或否证”成为共识,科学划界的单元定到理论了。
但是历史主义者,如其代表人物库恩(Thomas S.Kuhn),却对“理论 A是科学的,理论B是非科学的”这种说法不太感冒。因为真实的科学史上呈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科学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7]5。被称为是“科学的”理论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才被称为是“科学的”,而“前后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8]。所以,库恩事实上否定了把理论进行科学划界的做法。但是库恩仍然认为科学与非科学是不同的,不过这里的不同是指科学活动与非科学活动的不同,或者科学领域同非科学领域的不同,因为他说:“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事业区分开来”[9],而常规科学是指在范式 (paradigm,或译为规范)指导下解决疑难的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说过:“除了事后认识到这种好处(指获得规范),很难另外找到什么标准可以明确宣布某一个领域成为一门科学。”[7]18因此,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了范式是这个领域成为科学的充分必要条件。范式出现以前的时期被称为前科学阶段,新旧范式转换的时期被称为科学革命阶段,此外的范式较为稳定的时期就是常规科学的阶段。库恩因提出“范式”、“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等有关概念和理论受到科学哲学界的欢呼。用库恩自己的语言,可以说他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因为他用历史主义的范式取代了之前的逻辑主义范式。但是库恩的“范式”这个概念,内涵过于丰富而有些捉摸不定,仅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就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使用“范式”[10]。所以“范式”是有歧义的,有虚假概念之嫌,受到不少批评,晚期的库恩也基本不用这个概念。但是库恩关于科学划界的思想却离不开这个概念。
划界的对象是什么,在库恩那儿总有些含糊不清。他认为常规科学就是处理“这三类问题:确定意义重大的事实、将事实与理论匹配、阐明理论”,“最好的科学家所处理的绝大部分问题通常也是这些问题”[11]。即这些就是典型的科学活动。如果库恩认为科学划界的对象是活动 (或实践、或事业),那么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由于库恩把有没有范式看成是区分科学活动与非科学活动的标准,这就得出产生范式的那些研究活动竟然不是科学这样的怪论。如果库恩认为科学划界的对象是领域,那么由于同一理由,这个领域也只能是认识领域或包含认识领域的更大的领域,而不能是实践领域。再说,一个领域只有出现了范式才能被称为是科学的;那么什么有资格在一个领域中被称为范式呢?于是我们发现,解释什么是范式与解释什么是科学同样困难!例如库恩在“再论范式”一文中用科学集体 (或科学共同体)来说明范式,他认为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范式”的用法可以分为两种:“‘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另一种意义则是把其中特别重要的规定抽出来,成为前者的一个子集。”[12]290而“科学集体”这个概念在直观上已经借用了需要加以定义的“科学”,有循环定义之嫌。因为科学集体指科学家的集体,但什么人有资格被称为科学家呢?为什么占星术士或牧师不可以被称为科学家呢?故对“科学家”的理解又依赖于对“科学”的理解。所谓“特别重要的规定”,库恩列举了三种:符号概括、模型、范例。但是占星术士和巫师也使用这些,所以这些“特别重要的规定”也不能把科学同非科学区分开。
历史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试图把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结合起来。他主张科学划界的对象是一种有着共同硬核的前后相继的理论系列——他称之为“科学研究纲领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与范式相比较,研究纲领完全是由理论组成的,既去除了范式中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这些形而上的成份,又去掉了范式中仪器设备、操作流程这些形而下的成份。这样,研究纲领及属于该系列中的理论,都是在“世界 3”中的了。而前后相继的理论系列模拟了理论的历史发展次序。只是对于当红的研究纲领,在时间尚未进入未来的现在,该系列的下一项、下下一项是什么并不清楚;在时间尚未终结之前,研究纲领像范式一样总有捉摸不定的地方。因为,如果一研究纲领的全部系列可以预见,那么就可以把系列的最后一项或系列的极限那个理论作为该研究纲领的代表,因而划界的对象仍然可以是理论,但这与拉卡托斯的只有理论系列才能是划界对象这一思路相冲突。所以,当我们需要判断一个研究纲领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时候,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我们就要判断它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而这就只能根据系列中已经呈现的项来判断了。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今天是科学的研究纲领明天可能是非科学的,反之亦然。很难说一个研究纲领将来绝对没有希望。这是一种无定论的相对主义的思想,与费耶阿本德倒有些合拍,诚然它给历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留下了余地,却让伪科学永远有生存的借口。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由硬核和坚韧的保护带组成,并且配合有正面启发法与反面启发法。我们想知道的是,一个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是如何区分的?拉卡托斯可以说,保护带是根据硬核的需要 (正面启发法,为了说明现象)而建立的,保护带就是那种可以改变的辅助假说、“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追问:硬核的哪一部分可以降级为保护带?或者某些保护带可以升级为硬核吗?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13],即硬核不同,就属于不同研究纲领,否则就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这样降级与升级之后,相同的理论就会属于不同的研究纲领,这些所谓不同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认为,理论的各个部分之间确实有一种层次结构,而不都是相互独立或相互平行的。硬核与保护带之说只是一种理论的结构,有时我们更加需要另外的可能是更合理的结构以说明一个较为庞大而复杂的理论的运作。再说,一个研究纲领的硬核不是理论又是什么?研究纲领与其硬核在拉卡托斯那里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拉卡托斯评判一个研究纲领为科学的或非科学的 (或者为进步的或退化的)的方法和结论就可以对应地用到那个被称为其硬核的理论上。就是说,我们这样也就得到了一个评判单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或者说,如果拉卡托斯是正确的,当我们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时候,我们只需把这个理论上升为 (或扩充为)一个以其为硬核的研究纲领,然后运用拉卡托斯的方法就行了。这样做似乎没有太大的障碍,因为拉卡托斯并没有在理论成为硬核这方面设置过高的门槛。所以,拉卡托斯似乎也不能反对以理论为单位来划界。
把库恩的相对主义推向极致,就走向了标准消解观。标准消解观是指科学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划界问题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其核心内容是反对科学划界,主张消解 (dissolve)而不是解决 (solve)科学划界问题。其代表人物有费耶阿本德、劳丹 (Larry Laudan)、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费耶阿本德说:“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14]劳丹也认为不同时期的科学具有“异质性”,科学划界问题是“伪问题(Pseudoproblem)”。他说,“我并不认为‘科学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问题 (尽管它们常常在程度上有所不同)”[15]。“我们应该把‘伪科学’或‘非科学’这类术语从我们的词汇中省略掉,它们只是表示我们情感的虚词。”[16]罗蒂则自称是模糊主义者,反对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分,认为“科学”只是一种修辞,而不是一种自然类,“一旦‘科学’不再具有尊敬的意义,我们就无须用它来分类。我们可能就不需要一个词来把古生物学、物理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集合起来”[17]。
我们认为,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振振有词,但他们的论证却经不起严密的分析。即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典型的科学 (如物理学)与典型的非科学 (如占星术、宗教)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不同科学之间有异质性,推不出它们没有共性。他们主张取消“科学”一词,却没有仔细说明如何不用“科学”这个词而达到同样的表达效果。科学沙文主义不是科学划界带来的,相反,它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正是没有成功的划界,以及取消划界这种主张,才让伪科学有了可乘之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看到伪科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十分必要。我想,只要给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划界标准 (这也是本文努力做的),消解观的那些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历史主义揭示出“理论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才能被称为是科学的”的强烈影响下,科学划界的对象显然不能只是孤立的理论,所以,多元标准就应运而生。萨伽德 (Paul R.Thagard)主张,科学划界的对象不是理论或命题,而是领域 (field)。一个领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包含理论及其应用,以及该领域内的参与者的历史实体。就是说,萨伽德认为每个领域含有三个要素:理论、共同体、历史情境 (historical context)[18]138-139。由于萨伽德的领域以理论为其核心要素,所以是认识领域。邦格 (Mario Bunge)就明确地说科学划界的对象是知识领域。他解释说:“一个知识领域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获得、传播或利用某种知识……如逻辑与神学、数学与数灵术、天文学与占星术、化学与炼金术、心理学与心灵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等等。”[19]他的每个知识领域E含有十个要素,其中的要素 C是共同体,要素K是 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储备。如果 E是科学的,那么要求 K是一个由最新的和可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数据组成的集合。所以,多元标准的划界对象是把理论作为其中一个要素 (元),再补充以其他要素,如科学共同体等。即便是这样,现有的多元标准也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国学者王巍指出:“萨伽德的划界标准也带来一些问题:是否目前没有理论与之竞争的,如现在很流行的金字塔学,我们只能认为是科学的……心理学的发展与兴起是在 19世纪晚期,那么在此之前我们是否不应该拒斥占星术?”[18]140而且,萨伽德的“历史情境”这一要素究竟怎么界定,也是很成问题的。萨伽德的标准提出了 5个条件,但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追求精确的邦格为了使划界标准成为充分必要条件,增加到 10个元,12个条件。对此,王巍评论说:“邦格的划界标准也不是没有问题。他在划界标准中提到了‘真正实体’、‘真理’等概念,但这些概念往往在哲学上仍在争论之中。此外,他的划界标准也可能有反例,例如炼金术所写的论文故意很深奥,让人看不懂,反之科学普及的论文却希望普罗大众也能理解……古代科学的定量研究比较少,是否该归入伪科学?”[18]142我国学者孙思老师也指出,邦格的条件 (4)和条件 (5)是成问题的,“条件 (5)是关于哲学观点预设的问题,它并不能区分科学与伪科学”[20]96。
总之,多元标准的复杂,犹如天文学史上的托勒密系统中设置那么多的本轮和均轮,虽有相当的解释力,但终非正解。我们需要寻找一个较为简单的哥白尼式的系统。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标准呢?
四
定义 1:一个理论是一个满足下列条件的命题集合 T:
(1)如果一个命题集合 A中的每一个命题都属于理论 T,那么 A的任何逻辑后承也属于T(这称为理论的逻辑性条件)。
(2)T中的命题均为普遍性的命题 (这称为理论的普遍性条件)。
在定义 1中,我们强调了理论的逻辑性和普遍性要求。此外,理论还应该具有确定性。这是由于任何理论都是用一定的语言中的一些句子来表达的,这样,下面的要求就是不言而喻的:
(3)表达理论中的任何命题的句子的意义是确定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即对其中任何一个句子,不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 (这称为理论的确定性条件)。
这个确定性条件其实是对科学语言的一个要求,所以它不属于对理论的定义。
定义 1使用了“命题”、“普遍性”这样的未加定义的基本概念,这里略加说明一下。任何命题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对象或若干个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或一些对象之间具有某种关系,或存在某种对象。这些对象都称为该命题的论元。任何命题的论元集都不是空集,否则是伪命题。当某个命题的论元是一个自然类(natural kind)且属于该类的个体存在时,若该命题的内容为该自然类中的所有个体都具有某种性质,那么这就是一个普遍性命题。有普遍性命题作为其逻辑后承的命题也是普遍性命题。
波普早已认识到“在普遍概念或名称和个别概念或名称之间的区别,具有基本的重要性”[1]36。他说的“在全称陈述和单称陈述之间的区别与在普遍概念或名称和个别概念或名称之间的区别是密切联系的”[1]36也是对的。他已区别了严格的全称陈述和数的全称陈述,指出后者“实际上等于某些单称陈述”[1]34。但这种从形式上的区分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普遍性与数学上的无穷性是两回事。例如下面的命题:
(P1)所有的天鹅是白的。
由于天鹅是一个自然类,所以 (P1)是一个普遍性命题。但是,如果把无穷性作为普遍性的一个条件,那么 (P1)是不是普遍性命题就会有问题:因为地球上现实存在的所有的天鹅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使我们使用潜无穷的概念,即地球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天鹅的总数量可能是无穷的,(P1)是否因此就涉及无穷的对象呢?但如果某种“科学理论”认为,地球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天鹅的总数量加起来仍然是一个有限的数量,这又怎么办呢?因为宇宙的质量与时间是有限的,其变化因而是有限的。
虽然定义普遍性并非易事,却可以说一个命题比另一个命题更普遍:
定义 2:设命题 P为“所有的A类事物有性质 F”,命题 Q为“所有的 B类事物有性质 G”。若 B是 A的一个子类 (也可以同于 A),且语义上具有性质 F的事物便具有性质 G,则我们称命题 P比命题 Q更普遍 (这里的“更普遍”不排除 P与 Q是相同的命题)。
定义 2中的“语义上具有性质 F的事物便具有性质 G”,表明“具有性质 F的事物便具有性质 G”是一个逻辑结论,而不是通过科学试验而建立的科学定律。
定义 3:称一个命题 P具有实质普遍性,如果 P的内容为:“所有的 A类事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性质 F”。这里 A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自然类。
根据定义 3,下面的命题:
(P2)所有的偶数都能被 2整除。
具有普遍性,却不具有实质普遍性。因为偶数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自然类。所以,具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如果命题(P1)可以理解为:
(P3)所有的天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白的。
那它就是一个实质普遍性的命题。但是 (P1)并不一定要被理解为 (P3)。因为,设想有一类天鹅,在它们生下来的半年内体毛都是黄色的,在半年后毛发都成了白色的 (无论是黄毛剥落而重新长出白毛,或是原来的黄毛颜色变白了),这样任何天鹅成年后都是白的。在这种情况下,(P3)是假的,若 (P1)被认为是真的,则(P1)就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了。
下面我们要使用一个重要的但是我们不予以定义的概念:观察命题。如“今天这里下雨”、“体温计的读数是 37°C”、“张三和李四在打架”、“水烧开了”,这些都是观察命题。观察命题说的都是具体的现象,并且都联系着观察者的感觉。另一方面,它又能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得到相互证实。观察命题严格说来是已观察到的命题的简写,与可观察命题相对应。观察命题是已有的观察经验的记录,所以它属于历史。但是观察命题在语言形式上具有普遍性,如“今天这里下雨”,可以指 1984年 4月的某一天在武汉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指 2009年 6月的某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事实,还可以指将来的某一天在某地的气象情况。因此,一个观察命题如果没有具体的时间空间的限制,它的语言形式就同时能表示其他的可观察命题,代表一类可能会发生的具体现象。
我们知道,观察渗透着理论,一个观察命题得以被表达、得以成立,一定有一些假定、一些背景理论在起作用。也许这些理论并没有被作为观察者的我们所意识到。但是,对观察命题的分析和追究,可以逐步揭示出这些背景理论的一些内容。
定义 4:设 (可)观察命题 p1的背景理论为T1。对于任意理论 T,若 T1⊆T,即 T1是 T的子集,我们称 p1是一个在理论 T下的 (可)观察命题。
定义 5:设一个具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 P为“所有的A类事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具有性质 F”,命题 p1为“一个 A类事物 a1在时间 t1地点 L1具有性质 F”,命题 p2为“一个 A类事物 a2在时间 t2地点 L2不具有性质 F”。
(1)若 p2是一个在理论 T下的观察命题,则称 P在理论 T下被证伪。
(2)若 p1是一个在理论 T下的观察命题,则称 p1是 P在理论 T下的一个证据。
(3)根据观察命题集 O,如果 P在理论 T下未被证伪 (即 O中无上述 p2之类命题),且 P在理论 T下有证据 (即 O中有上述 p1之类命题),则称 P在理论 T下得到验证。
定义 6:一个理论 T是可证伪的,当且仅当:T中含有这样的命题——“所有的 A类事物具有性质 F”,而“一个 A类事物 a1不具有性质 F”是在理论 T下的一个可观察命题。
一个理论只有是足够丰富的 (指它能够包含某些可观察命题的背景理论)才有可能是可证伪的。
定义 7:一个理论 T是准科学的,如果它符合下面四个条件:
(1)T存在一个有穷的子集 T0,使得 T中的所有的命题都是 T0的逻辑后承,并且 T0中的每个命题可由一个有限的句子来表达 (有穷性原理)。
(2)T是一致的 (不矛盾原理)。
(3)T含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 (实质普遍性原理)。
(4)T是可证伪的 (波普原理)。
记命题集合 A的所有的逻辑后承的集合为Logi(A),于是,若 T是一个准科学的理论,则存在一个有限个命题的集合 T0,使得 T=Logi(T0)。T0也称为 T的一个公理集。一个理论可以有不同的公理集,但给定了一个公理集,则该理论也就确定了。
定义 8:一个理论 T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 O(在知识库中)是可接受的,如果它符合下面四个条件:
(1)T是准科学的。
(2)设观察命题集 O的背景理论为 T1(它是O中单个命题的背景理论的合取或并集),则 T∪T1∪O是一致的 (不矛盾性)。
(3)存在一个可观察命题 p,使得:p是 T∪T1∪O的逻辑后承,但 p∉O(超余内容性)。
(4)T中存在一个实质普遍性命题 P,存在一个准科学的理论 T2且 T2⊇T∪T1,使得 P在理论 T2下得到验证 (根据 O)(相关性)。
定义 9:对两个不同的准科学理论 T1与T2,称 T1比 T2更普遍,当且仅当:存在 T1的公理集 A={a1,a2,…,an},T2的公理集 B={b1,b2,…,bn},使得:对每个 i,命题 ai比 bi更普遍 ,这里 0 < i<n+1。
直观上,更普遍的理论描述了更广泛的现象。当然,任给两个准科学理论,何者更为普遍,一般是不能像定义 9那样比较的。
很多特定的现象并不被理论所覆盖,因为理论是普遍的,理论常常描述的是一类现象与另一类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理论 T,可以从一类现象 A的存在来推知另一类现象 B的存在。科学说明或科学预测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说,设 L(L∈T)是自然律,A是先行条件(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B是被说明的已经发生的现象,或是推测出的将要发生的现象,L说的是一种普遍联系,A与 B是这种普遍联系的一种具体表现。给定理论 T,它能说明多少现象,这是一个常规科学 (库恩意义上的)的工作。对理论 T深入地探讨,也许能了解到更多的它可以说明的现象,而另有一些现象却是理论 T至今仍然无法给人以满意的说明的。而且,一个具体现象、具体事物的某一方面通过 L得到说明,不等于说它的另一方面也得到说明。它的另一方面也许需要用 L1(L1∉T)才能得到说明。一个现象只是部分地得到说明,它还属于未解决的问题吗?是把它归入已说明的现象,还是归入未说明的现象呢?所以,一个理论能够说明多少现象,即使客观上有一个量度,但人们了解的往往是一个主观上的量度。但是主观上,人们却可以判断一个理论说明的现象比另一个的多,或者一个理论所说明的现象,都能被另一个理论说明。而这就足以比较它们的优劣了。
定义 10:设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 O,理论 T1与 T2都是可接受的。当下面的条件中的任意一个成立时,我们均说 T1比 T2更科学:
(1)T1比 T2更普遍。
(2)对于任意的 p∈O,O的任意一个有穷子集 C:如果 p∈Logi(T2∪C),那么 p∈Logi(T1∪C)(即 T1比 T2能说明更多的已知的观察事实)。
(3)设 T1的一个公理集为 A1,T2的一个公理集为 A2,且 A1⊂A2。如果:
∀p∀C(p∈O∧C⊆O∧C是有穷的→(p∈Logi(A1∪C)↔p∈Logi(A2∪C)))。
(上式意即:被 T1所说明的观察事实的集等于被 T2所说明的观察事实的集。)
定义 10中的第 (3)点以某种方式排除形而上学。它利用形而上学的命题对说明经验性的观察事实是无益的这一点来排除形而上学。第(1)、(3)点也可以理解为“越简单的理论越科学”。
定义 11:一个理论 T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 O是科学的,如果下面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1)T相对于O是可接受的。
(2)人们已经找到的所有的相对于 O是可接受的理论中,没有比 T更科学的。
五
以上 (定义 1至定义 11)我们给出了“什么样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行吗?它能够导致正确的科学划界吗?这个定义将产生一些富有成果的结论 (特别是在理论和观察的关系上,限于篇幅,我将在别的文章中对此展开讨论)。此处,我们将就以下几点来说明这一定义符合我们对科学的通常看法。
(一)关于科学的一般特征。
逻辑经验主义者费格尔 (Herbert Feigl)曾为科学总结了五大特征: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可靠性;精确性;融洽或系统性;广泛性[18]128-129。库恩也指出好的科学理论具有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12]316。我国学者张小山曾总结说:科学具有系统性、普遍性、精确性、简单性、检验性、有效性、批判性这七个特性,而系统性、可检验性、批判性是科学的三个最根本的特性[21]。张洪波等人主张科学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创新性、可检验性、预见性、发展性[22]。
上述这些科学的特征大都在我们的定义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甚至得到更严格的表述。例如,广泛性、普遍性在我们这里是由定义 1中的普遍性条件(还有定义 7中的实质普遍性原理)来保证的。融洽或系统性、一致性是由定义 7、定义 8中的一致性或不矛盾性来保证的;另外定义 1中的逻辑性条件、定义 7中的有穷性原理也体现了系统性。检验性或可检验性则是由定义 7中的波普原理来体现的。精确性则是由定义 10中的条件 (2)等来体现的。预见性、创新性,以及库恩所说的有效性,都可由定义 8中的超余内容性所体现。简单性为定义10中的条件 (1)和 (3)所具体达成。
至于可靠性和客观性,这应该是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讲的,因为科学理论是可误的。而定义 8中要求理论与观察相一致,能使理论达到相对的可靠性。至于批判性,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理论的特征,而是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品格和精神。
这里我想讨论一下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它们被看作科学的客观性的重要体现。这两个特性如此的重要,以至有人称之为“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被称为“主体间性原则”和“可重复性原则”[23]。朱志方教授曾深刻地指出:“要达到客观知识,最有效的途径是互观性(intersubjectivity),集体性,是认识集体内部的民主的、平等的交流。”[24]朱教授说的互观性,现在一般译为主体间性。
蒋劲松在“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一文中指出,主体间性原则“即坚持认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学研究结果应当是与主体的个体差异无关的,与每个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或者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影响”[23]。可重复性原则“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实验室、不同时间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事实,才可以认定为科学事实”[23]。蒋在该文中论证说,一定的科学研究规则是依赖于一定的自然观的,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很赞同蒋劲松的这一观点。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些规则的来源是什么,即为什么科学一般而言是具有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的。而且,一种自然观是否正确,又要看它是否科学,要看它是不是为正确的科学研究规则所支持;因为蒋认为“这些规则或原则又成为评判科学家所宣布的科学事实和所提出的假说或理论的标准”[23]。这很明显地陷入了一种循环。只是蒋认为这是一种“解释学的循环”,是正常的。
但是循环论证是一种坏的解释。因此,我主张把“解释学的循环”建立为螺旋式的有前进的运动:它回到起点,但是高于起点,并因此而显示它的首尾是连贯的,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又有向未知领域发展和敞开的趋向。纯粹的无进步的循环应该受到抛弃和质疑。封闭的循环中起点是什么并不重要,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起点和终点。但是,开放的螺旋式“循环”以什么为起点则很关键,因为它应该是支点和源头所在。
我们认为,科学理论的核心在于那些具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其实,主体间性也是一种可重复性,即在不同主体、不同研究者之间,实验结果是可重复的。而对于可重复性,我的解释是:这是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实质普遍性的一个结果。由于实质普遍性的特点是:时间上,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空间上,在任何地方都如此;种类上,任何这种事物都如此,或在任何这类情况下都如此。因此,一个具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它的正确性等于保证了相关的现象是可重复的。实质普遍性是起点,它是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的原因。实质普遍性命题是存在的,因为它是对事物的本性的表达。科学的任务就是揭开事物的本性。掌握了事物的本性,甚至可以说明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在某些场合为什么会“失效”。正如牛顿定律可以解释行星轨道为什么是椭圆的,又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行星(如天王星)的轨道不是椭圆的。
因此,我们的定义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具有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
(二)科学理论的历史性。
我们的定义给出的划界标准是规范的、逻辑的。定义 11表明,理论只有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才谈得上是否是科学的。而人类的知识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人们已知的观察命题集具有积累性,即正常情况下,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了解会越来越多,这是科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一个理论在一个时代是科学的,却可能随着人们对自然现象了解得越多,而成为非科学的了。定义 11还表明,理论是否是科学的,除了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之外,还取决于当时人们的研究状况、研究水平,即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多少以及怎样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其中的最佳理论 (可不止一个)才是科学的。这个定义还意味着可供选择的、或相互竞争的理论越多越好,所以与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增生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和人们当时提出的理论集是动态的、历史的、具有偶然性的,所以这个标准也是历史的。可以说,我们对科学理论的定义是逻辑与历史的自然统一。
当在某个知识领域没有任何理论达到上述的标准时,我们就说该领域还处于前科学时期。这也就是库恩的范式尚未出现的时期。逐渐地,人们会提出一些准科学的理论、一些可接受的理论,这样,科学的理论就出现了。当有多个理论达到上述标准时,这些理论可以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有时可能是相互补充的,有些理论可以被综合为一个更广泛的理论。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彼此在某些点上面是相互矛盾的,因而需要我们设计可控的实验,为我们在这些理论中作取舍提供依据。因此,就单个理论而言,它也经历一个诞生 (被提出)、不断丰富和壮大到死亡(被科学家们抛弃)的历史过程。一个理论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更科学的理论出现了并取代了它。因此,我们也能说明科学的发展性。
(三)科学理论的主体之维。
我们没有明显地谈及科学共同体,这不等于说我们认为这个因素不重要或不起作用。我们认为,科学家共同体不是封闭的团体,不断地有新成员加入,也不断地有人退出 (主要由于年龄)。每个科学家受自己的文化、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作为科学家,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如理性、逻辑性)在起作用。我们对科学的定义是不同的科学共同体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个定义当然可以改进,从而使得它更能合乎人们日常使用“科学理论”这一概念所体现出来的理念。另一方面,它作为严谨的规范,规范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引导人们正确地使用“科学理论”一词。
根据定义 11,如果一个理论 T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 O是科学的,那么,T比其他的人已经找到的相对于 O是可接受的理论都更科学。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可接受的理论彼此都是可以相互比较的。我们必须考虑库恩的不同的范式理论之间不可通约的问题。
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如果相对于已知的观察命题集 O都是可接受的,它们不可通约不要紧,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可以作定义 10中 (1)、(2)、(3)方面的比较?如果可以比较,则人们可以依据定义 11作出选择。如果无法比较,则这两理论各有千秋,它们可以都是科学的,哪怕它们彼此不一致,科学家知道它们并不都是正确的,但还没有到其中一个死亡的时候。
我们必须考虑到库恩曾设想的这样一种情况: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 T1与 T2属于不同的范式 P1和 P2,在 P1中已知的观察命题集是O1,而在 P2中已知的观察命题集是 O2,且按照我们的上述定义,T1相对于 O1是科学的,T2相对于O2是科学的。由于处于不同的范式中,所以O1与 O2可以不同。但 O1与 O2作为对已知的观察事实的不同表述,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如果O1与O2分别是不同时代人们的已知的观察命题集,则 T1与 T2也就是不同时代的科学理论。当O1与O2是同时代的人们已知的观察命题集,O1与 O2之不同必定是由于它们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所以,观察命题集既体现了历史的维度,又体现了主体的维度。而对于一个给定的科学共同体而言,一定历史时期的已知的观察命题集是确定的。如果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的已知的观察命题集不相同,则可以通过两个共同体之间的充分交流来逐渐消除差异,这一点是由科学的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来保证的。
(四)如何拒斥形而上学和伪科学?
逻辑经验主义想用无意义来驱逐形而上学,但是没有成功。不仅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是成问题的,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意义理论,所以借助意义理论来驱逐形而上学,希望不大。再说,形而上学也许如波普所认为的那样是有意义的。我认为,在科学上,形而上学是多余的,即形而上学的理论没有经验性的后果。有经验性后果的理论不宜称之为形而上学。利用这一点 (见定义 10之 (3)),我们可以驱逐形而上学。
至于伪科学,它们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但在理论上识别它们并不困难。因为,伪科学一般提不出具有实质普遍性的命题,在理论表达上通常不满足确定性条件。而且,伪科学立论所依据的观察命题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的检验,所以最畏惧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这样的试金石,需要利用“绵羊——山羊效应”,强调“心诚则灵”或“信则灵”。这样,他们的理论又不能满足定义 7所述的波普原理,不具有可证伪性。
让我们以占星术为例。据说,“占星术的预测是可以检验的……费格尔的划界标准并不能把占星术排除于科学之外”[18]129。“高奎林(Michel Gauquelin)用统计评估的方法考察了25 000个法国人的职业和他们出生时间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了杰出运动员和他们出生时刻火星位置之间的关系大大超出了随机概率。”[25]“萨伽德认为库恩的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划界标准也没能把占星术排除在科学之外,因为占星术面临大量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比如高奎林揭示的职业和星宫之间的关系,以及岁差问题……萨伽德提出,占星术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占星术与其他可供选择的理论相比,进步较慢,且其追随者们几乎不努力发展该理论。”[25]萨伽德拒斥占星术的理由更不能令人信服。其实,高奎林的数据是孤立的,因为“其他人所做出的统计结果对占星术的这个论点是负面的”[25]。根据我们的标准 (定义 8中的不矛盾性条件),科学理论必须与所有的观察命题一致,不应该无视对理论不利的数据和观察命题。既然存在这些数据和观察命题就可以否定占星术。因为不存在一个得到所有观察数据支持的关于人们出生时的星宫与其职业的关系的实质普遍性命题。
再如曾在我国闹得沸沸扬扬的人体特异功能理论,其中“外气”一说神乎其神。对用当代心理学完全能解释的现象 (如气功师通过语言、神情动作等暗示手段影响观众),却要借助所谓“外气”来解释,也是一种“多余”的概念和理论。这里,我们利用定义 10之 (3)也可以驱逐它们。
所以,我们给出的标准是能够把伪科学清理出去的。而以前的标准能否做到这一点值得怀疑。例如,以“是否形成了范式”作为科学标准时,有人指出“伪科学共同体没有公认的范式”[20]97,对此我表示疑问,因为师父教徒弟是有范式的,占星术、风水术等也都是有范式的,托勒密的占星术著作之于占星术、《宅经》和《葬经》等书之于风水术就是一种范式。
六
上面我们论证了,根据我们对科学的定义,能够得到人们通常以为科学应具有的那些特征。也就是说,只要是科学,就应该具有那些特征,这当然是逻辑主义的思想。库恩称这些特征为价值,也称它们为评价和选择理论的准则,并承认“像精确性、有效性等价值是科学的永恒属性”[12]328-329。但库恩的历史主义观点使他又认为:“这些价值的实际应用,或者更明确地说它们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以及应用领域的不同而发生显著变化。”[12]329用这些特征来定义科学,或者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根据这些特征把科学的理论挑选出来,这是逻辑主义的理想。费格尔认为可以这么做。库恩对这一理想作过深入的研究,结论是“人们运用这些准则进行选择……会碰到两类困难。个别看,这些准则并不精确……其次,当它们一起展开时,则一再表明彼此有矛盾”[12]316。以一致性和简单性这两个准则为例:当初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与托勒密的地心说的选择中,“一致性准则本身毫不含糊地支持地心说传统。简单性则偏向哥白尼”[12]317。更为严重的是,“科学家如果必须在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中选择一种,即使两个人都采用同一张选择准则表,仍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12]318。就是说,这样的准则表无论怎么详尽也保证不了科学家们有一致的选择,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在选择中会发生关键的作用。所以,逻辑主义的理想“是不大可能达到的理想”[12]320,“要构成一种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是困难的”[12]322。
本文就是从事这一困难工作的初步尝试。库恩列举的那些价值和准则 (精确性、广泛性、有效性等)之所以不完善,之所以在运用时既显得含糊、又时常发生冲突,是由于没有理清这些价值或准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仿佛它们只是外在地摆在一起,至多也就是一盘散沙,而没有发现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上的一些枝节。极为重要的主体间性和可重复性,是这个整体的另外一些枝节。我们认为,这个整体的根,在于任何事物都是有其本性 (nature)的,表述事物本性的科学命题是实质普遍性的命题,别的命题都没有抓住事物的本性。可证伪性和相关性则保证了理论与经验、与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一致性则反映了科学理论是合乎逻辑的,科学是理性的事业!
我们把科学这一概念建立在理论与观察命题(另一种说法是证据)集的关系上。评价一个理论是否科学,是把作为某种整体的理论相对于作为整体的观察来考察的。这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在确证函数 C(h,e)中把孤立的假说 (命题)h相对于孤立的证据 e来加以考察是不一样的。且不说就实际的 h与 e而言,这样的函数计算是否可能;在我们看来,在孤立的假说与孤立的证据之间一切皆有可能,因而这样计算出的数值是否有意义值得疑问。确证函数的计算是要得出定量的值,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奢望,只要求在理论相对于观察的考虑中得到一种定性的结果:即相对于观察命题集而言,给定理论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并且作这种判定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向全社会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他有兴趣他就可以参与到这样一个判定之中,并且他的判定结果也被别人考察,被别人确认或否定。某个人发现理论 T的某个命题 P在 T下被证伪或得到验证,或者另一个人发现 T不一致,或者再一个人发现 T1比 T更科学,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迅速地让社会其他人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我相信,用我们给出的标准可以判断一理论是否是科学的。
[1] K.R.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 [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2] K R Popper.Th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Knowledge[M].NewYork:Routledge,2009:382.
[3] 周文华.逻辑主义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两种划界[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3).
[4] C G Hempel.The Empiricist Criterion ofMeaning,in Logical Positivis m[M].NewYork:The Free Press,1959:108.
[5] 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0.
[6] 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09.
[7] 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8] T S Kuhn.Incommensurability and Paradigms[G]//I Lakatos,A Musgrave.in Criticis 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195.
[9] 托马斯·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伊·拉卡托斯,艾·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
[10] 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 [M]//伊·拉卡托斯,艾·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1] T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34.
[12]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 [M].纪树立,范岱年,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13]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67.
[14] P Feyerabend.AgainstMethod[M].London:New Left Books,1979:306.
[15] 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 [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5.
[16] 拉里·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3-20.
[17]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 [M].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0.
[18] 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9] 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J].张金言,译.哲学研究,1987(4):46.
[20] 孙思.理性之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1] 张小山.简论科学的特性[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3):19-22.
[22] 张洪波,汪青松,等.科学与伪科学的分野 [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75-81.
[23] 蒋劲松.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3).
[24] 朱志方.科学革命与人类知识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272.
[25] 朱彤.20世纪对西方占星术的科学检验[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8).
Abstract:Civil diplomacymove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movementof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became the popularway to fight the aggressive policy of Japan,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Itmade 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 become moderate on the one hand,it impeded Japan attending warlord melee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At the same time,civil diplomacy movements of the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 made the joint interference from the powers bankrupt completely.And it also intensified Japan to look for the new agent from China,which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volution camp.
Key words: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Movements of Boycott against Japanese Goods;Japan;Japan’s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Study ofMarxism Sino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W orld History
YAN Xu
(NationalDefense University,Beijing 100091,China)
The academic circles studyMarxism sinolization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at present.W 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innovation of practice,it becomes the self-conscious pursuit to studyMarxis m sino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world history.Thereby the research pattern covering the visual angle ofworld-history and that of China will be established.
Marxis m sinolization;the perspective of Chin;the perspective ofworld history;
On Criterions of Demarcation of Science
ZHOU Wen-hua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Abstract:As for the criterions of demarcation of science,that the absolute criteria given by logical positivism and Popperian are absurd ismade clear by Thomas Kuhn through his analysis of history of science.Kuhn suggests that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a researching field to be a science is that a paradigm emerged in that field.Kuhn is the father of historicism who holds relative criteria for demarcation of science.This relativis m reaches its extreme at the hands of Paul Feyerabend,Larry Laudan and Richard Rortywho declare 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is spurious.Both their view and Lakatos’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give room for pseudo-science.This paper gives a nor mal definition of science by connecting falsifiability,essential universality,coherency and observational prolificacy properly.The definition is a logical and historical criterion of demarcation which can eliminate metaphysics and pseudo-science.From the definition we can deduc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Key words:demarcation of science;essential universality;Popper;Kuhn;Lakatos
Problem Reductions in the Revolution of Neoteric Physics
SHEN Jian
(Law College,JiayingUniversity,Meizhou,Guangdong 514015,China)
Abstract:Problem reduction(PR)is a new topic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In the paper,the paper tries to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classical PR cases in the revolution of neoteric physics,and by those cases,the paper argues the existence of PR can be verified.Moreover,on the basisof those cases analysis,the paper rejects thewidespread vie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roblem reduction and science revolution are mutually exclusive.
Key words:the revolution of neoteric physics;problem reduction;science revolution;relationship
The Essence and I mpact of Kuhn’s Paradigm ThinkingM ode
WU Chun-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4,China)
Abstract:Kuhn’paradigm thinkingmode is the basic view and method generat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a certain science field.It develops and transfor mswith the advance of the science and is also incommensurable,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e logicalpositivis m and Popper’s falsificationism but having itsown limitations,affects the developmentof SSK significantly from various aspects.
Key words:paradigm;scientific community;thinkingmode;SSK
TheM ovements of Boycott aga inst Japanese Goods and Japan’s Policy toward Ch ina
Y IN Shao-yun
(Law and Politics Institute,Xuzhou NormalUniversit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N03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8444(2010)02-0163-11
2010-01-15
周文华 (1966-),男,湖北武穴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