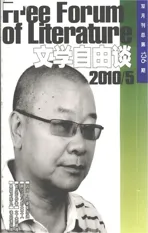世界杯赛季谈文学
2010-03-21李骏虎
●文 李骏虎
曹雪芹怎样评价《废都》
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报告文学家何建明,撰文披露贾平凹《废都》解禁的内幕,从友人的角度对贾平凹和《废都》进行了高度评价,称贾平凹为“大师”。何先生曾是《中国作家》杂志的主编,又是作家出版社的社长,他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判断,我认为是很有权威性的。我个人对贾平凹先生和他的作品也是关注的,因此我也想说说我对贾平凹和他的小说的看法,并且想援引曹雪芹先生对此类小说的判断,给《废都》一个伦理定位。
我认为贾平凹作为作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和对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精神状况的传神反映。以《浮躁》和《废都》为例,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文学价值,而是社会价值。《浮躁》反映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纲转向的历史关头,人们的思想矛盾和精神状况,作品代表性地展现了中国人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的“浮躁”心态;同样,《废都》展现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多元、扭曲,和由此而造成的精神信仰的缺失,灵魂丧失皈依感,整个社会陷入彷徨、低迷、消极、享乐的境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知识分子出现了和明朝某个时期一样的处世姿态,一种“末世情怀”,因此贾平凹就敏感地体察到,并且仿照《金瓶梅》写了《废都》。
如上所述,是贾平凹聪明过人之处,而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被读者热衷,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他一直就是个基层的文学写作者,他对文学的理解,只是限于对中国古典名著的仿效,他的小说方式,是通俗的,因此反而能与中国平均的阅读欣赏水平处在一条水平线上,这条水平线也就是兴奋线,是一种较低层面上的谐振。
说到《废都》,除了《金瓶梅》的余韵,和对其形式的模仿,其实从文学上并没有太大价值,而当年风行时对读者所产生的非正面作用,却是无法抹去的。你去采访一下《废都》的读者,如果他肯说实话,十个有九个是冲着它是“黄书”去的,一本书,读者冲什么去读,直接说明了它的价值。那些“□□□”至少成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精神向度和审美层次的昭示。这样的小说史上不乏,用曹雪芹的原话说:“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八十回《石头记》第一回)虽然现在的八○后、九○后不像当年的六○后、七○后那样对性过度神秘,黄书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兴趣,但这本书当年在社会上对普通读者产生的作用,超过了少数知识分子能理解的精神价值,解禁则解禁了,“平反”实在没必要,拔高更是笑谈。
毋庸讳言,大道德层面上的伦理缺陷,是当下时代小说写作中一道不断“恶化”的伤口。
“跳舞”就能解决问题吗?
我一直有个理想,就是能写出一本书(而不是文学作业),让它风靡全国,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用。这本书的思想性或许不是很高,但它能够传达作者的思想力,能让各个阶层、最大范围的读者都能感知到作者对社会、时代与生存意义的思索,这思索是思考的过程,它也有思考的结论,虽然这结论未必经得住严密推敲,它作为一家之言,却能得到最大范围的共鸣与传播。
当然,这本书按体裁分最好是小说,但在小说里不乏政论、也有议论人生的篇章或者诗歌。对于当下时代的观点,对于现实的批驳,也许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也许作者趁机会发表自己的议论,这都不影响一件事情,那就是,作者有思考社会的能力,更有观察和描摹时代的眼睛和妙笔;读者或同意作者,或同意书中的某一个人物的人生观念和处事行为,或者反对他,并因此急于和作者争论,这都是让作者高兴的事情。
然而,我一直高兴不起来,原因就是,我一直写不出这样一本书,我尝试多次,都觉得准备不充分,所以现在一直还在尝试和准备当中。
同时我发现,当下无论声名正隆、如日中天的“著名”作家,还是偶尔露峥嵘的业余作者,都未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比如刘震云,他早期的作品像《一地鸡毛》是具有思考社会的特质的,但是后来的作品,《手机》,就有些取巧,试图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入手,揭示这个时代的心态和风潮,这是敏锐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但这同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用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故事来展现宏大的社会场景和时代特征,只能借助焦点人物和热门事件来罗织故事,凑成一个载体,这一下子就掉进了以偏概全的泥沼,同时过于娱乐性和市场化的手法让小说的艺术品质一落千丈,成为凡品和俗物。这一类的文学作品最负面的作用是,当它们改编成影视剧后,愉悦和蒙蔽了最大范围的受众,比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手机》和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不如跳舞》,起到的最大的隐形作用就是粉饰现实和掩盖现实,回避社会问题,表现一种歌舞升平的文化假象。这些作品之所以品位低下,是因为它们流于愚民,丧失了文学作品直面现实、引导民众、改良社会的伦理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被认定为大作家及大作品的,往往存在大道德准则上的缺陷,也可以说是伦理缺陷。
问题是否“小儿科”
纵向比较,自中国新文学发端,就充满着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精神。1919年——1949年之间,由于国难积重,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同时在他们的作品中,接连不断的国耻也暴露了中国人道德沦丧、尊严尽失的现实,他们呼唤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当此之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作家却在质疑他们自己发达的文明社会,对文明本身抱有极端仇视的态度,同时剖析人的精神问题。1949年之后,中国的作家和文学一度沦为政治舆论工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后,欧美文学思潮席卷的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三十年之间产生了无数“副本文学”作家和作品,作家思考现实和社会的能力基本退化。世纪之交,文学因为脱离社会而难以避免地被大众漠视,被社会边缘化。
苏童就是“副本文学”作家的典型代表,他的小说《河岸》今年年初在英国出版,英多家大报刊有书评,但稀见褒扬。其中《独立报》1月29日刊发希尔(Justin Hill)的文章指出,苏童作为最知名中国作家的“可疑名望”并非来自他自己的作品,而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他关心人物胜过政治,其笔下东亮的世界也是如此。东亮只在意父母失败的婚姻和自己勃发的性欲,全然不管身边席卷一切的时代大事。他那滑稽的和不那么滑稽的一次次勃起,逐渐成了全书的中心。在西方读者看来,写这么多勃起既没有必要也很幼稚。《卫报》、《泰晤士报》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家严肃大报,对一部赢得了亚洲文学奖的小说指出了作家社会伦理观念的缺失,中国作家作品在国际上的境遇凄凉,说明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当下中国作家的写作,确实存在着致命的问题,悲哀的是,这问题在人家看来,实在是“小儿科”。
票房与民族大义
如今,在作家们普遍精神矮化,写作无思想、无理想、无目标,基本沦为枪手,文学成为影视的附庸的现状之下,影视作品暴露了那些号称关注现实的作品的虚假,在这些热播的影视剧中,农民每天都演绎着衣食无忧的喜剧,官员们的台词在现实生活中听来让人起鸡皮疙瘩,这些精神产品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这样的作品连基本的伦理标准都达不到,根本谈不上把握时代脉搏、引导社会发展。这就是当下普遍存在的“伪现实主义”问题。从“先锋派”到“伪现实主义”,当下文学创作已经和正常的人类精神没有多大关系。
与文学人的委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人替代前者称为社会改良和精神救赎的摩西。《孔子》和《十月围城》重拾社会改良和民族大义,高扬伦理大旗,取代了一直影响中国社会的文学的地位。韩寒在博客撰文,认为《孔子》是一部可以抹去的电影,我对他的说法存疑。韩寒认为电影《孔子》可以抹去,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能用几句子曰诗云就能说服观众的时代了,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了当下人们精神文化上的一个症结,现在正是一个需要讲“仁”和“礼”的时代:社会上普遍的毛病是缺乏“诚信”,拜金产生的是暴发的“跋扈”和底层的“仇富”,如果人们已经不能坐下来读《论语》,有这样一部教人们别卖假药,教交警别“钓鱼”,教二奶别开上宝马车撞人,教学生别去割同学喉管的电影,让人们学会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也让八○后、九○后知道在那些欧陆时尚和韩流之外,还有过一个叫孔丘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让你学会自我之外的担当和责任。在这个利己主义的时代,告诉你“苟利国家,生死以之”,苦口婆心地宣扬“仁者爱人”,它的价值是超越了一部电影的。我们太缺这样的电影了,而《孔子》给我们补了一课。
我不想非议韩寒,他已经形成那样的批判姿态,开弓没有回头箭,但他不知道,其实孔子和他一样也是个社会改良主义者,只是韩寒用的是破,而孔子用的是立。韩寒学鲁迅,但他也不知道,鲁迅当年要打倒“孔家店”,是看到国弱民愚,急需外来的新思想来革命以求得富强和新生。而今时代,中国已然强大,人民身处地球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世界风潮的熏陶之下,正由于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混乱而变得现实、机敏和利益化,生活水平不断升高,精神境界不断下滑,幸福感正在消失,这个时候,不是继续“驱逐”孔子,而是要迎请孔子归来了。看看那些前仆后继的贪官污吏,你难道不觉得,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信仰来约束一下自己,收拢一下散乱的精神,收敛一番为所欲为的心态了吗。
把孔子看做圣人,不是一件坏事,《论语》强调一个“仁”,《圣经》强调一个“爱”,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无形的秩序,约束人的恶,鼓励人的善。学西方的思想,首先要看清“神”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再反观一下我们对传统文化信仰上的缺失。就算从社会改良角度说,电影《孔子》即使没有商业大片那样有观赏性,那样的感官冲击力,它却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要我说,这样的电影才是真正应该组织去看的电影,那么多年不去影院的父母带着孩子去看《孔子》,说明人们对圣人思想还是有信仰的,是愿意以这样的形式寓教于乐的。
港片《十月围城》震撼内地,让号称大片的《三枪》、《花木兰》、《刺陵》捉襟见肘。陈德森,一个名头并不是太响的香港导演,让“国际大导演”张艺谋的精神高度“真的没有”了。
《十月围城》的成功,从技术上就不说了,我想说说它的内因。这些年,我们的大导演们热衷贺岁大片,热衷视觉震撼,一切都奔商业利益去,越拍越俗,没有担当,作品都像没有灵魂的华服行尸。港片的导演回过头来,却玩腻了娱乐,宣扬起对国家民族的担当。这种担当,是一种伟大的情怀,这才是永远不过时的永恒主题。谁不爱国?谁没豪情?谁没情意?你想当舍身取义的大丈夫,还是哗众取宠的小丑?
话说回来,演小丑的小沈阳未必“有罪”,我要说的是导演对演员的尊重,以及对人物的尊重。《十月围城》里那些义薄云天的人物,其实都是些小人物,但导演要把他们灵魂深处的大义都激发出来,让大明星们去演绎这些小人物的伟大,而不是让明星去当行尸和花瓶。而无论腕儿的大小,演员们理解并尊重人物,所以演惯帅哥的黎明、谢霆锋才能把下里巴人演到血肉丰满,给观众以新奇的感受。
即使《十月围城》票房再好,观众也不会觉得它是商业大片,因为它从理念上摒弃了娱乐,选择了民族大义。
瞄准精神的标高
另一个极端,是作家先入为主地从概念角度出发进行的写作,这种写作经过一个阶段后暴露出它的作秀情节和“伪道德”标准,最为喧嚣和贻害极深的就是所谓的“底层写作”。关于以普通群众为写作对象的小说创作,马克·吐温有过这样一个社会伦理宣言:“我甚少刻意教导他们,不过却尽我所能地去娱乐他们。光是娱乐他们便可以满足我最大的野心。”与今天甚嚣尘上的“底层写作”和持“底层写作”姿态、用俯视的眼光、俯就的身段进行创作的作家相比,马克·吐温才是那个真正属于民众的人,正像卡尔维诺所下的断语,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从显要的位置纡尊降贵地降至民众的水平,以便和他们谈话”。
那么,什么是当下时代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行为准则,不必隐晦,现在我们已经往回走了,又在从多元价值观念发展到了一个单一价值观念的时代,正像西方所经历的,伟大的作家们诸如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马克·吐温所写的那些以金钱为主题的故事一样,我们正处在“一个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世界”。(卡尔维诺语)金钱曾是19世纪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今,作为作家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实,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去表现它在当今时代扮演的角色,以及以它为价值标准的社会问题和人性根源。
所谓伦理,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当这种准则面临“一个只以经济观点来思考的世界”,我们是否有能力看清社会现状?是否有能力看到社会问题,是否有洞察社会本质的能力?是否具有思考能力和艺术手段去恰如其分地表现这个时代?恐怕,这是我们的写作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难题。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发展到当下时代,历史遗留的封建意识和规则,在人性和社会当中起着潜在的主导作用,而经济模式的资本市场化,又使我们面临残酷的竞争和生存难题,在这封建意识和资本市场的双重挤压下,作为人的个体丧失了很多可贵的东西,比如尊严、平等、风度等等,而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潜在准则是:出卖灵魂,出卖自我,求得生存和发展。芸芸众生,谋生的手段很多都演化为骗取金钱、变相欺诈的勾当,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人性变异面前,作家应当作何思考和写作?回避现实?描摹现实?还是用更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更强大的思想力去引导和拯救民众的精神、增进社会的改良?我觉得,一个有良知和道德准则的真正作家,应该以后者为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以此为自己的精神标高,这意味着就是以雨果和托尔斯泰为精神标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