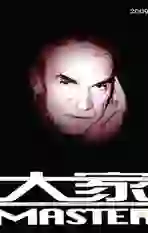故乡故事
2009-12-16何小燕
何小燕
走马村
0
从大足县城往东,坐1个小时的汽车,就到了回龙镇。
回龙镇,镇域北面与铜梁县小林乡接壤,到铜梁县城约30公里。1989年我曾带我的学生去过,参观了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烈士的纪念馆。耸立在纪念馆前的烈士纪念碑高15米,碑顶是烈士5米高的青铜像,碑名由朱总司令题写。西面紧邻保顶镇和智凤镇。宝顶镇的宝顶山是闻名世界的大足石刻主要所在地,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千手观音造像。我不知道智凤镇有什么,只知道它是大足石刻创始人赵智凤大师的故乡。南面与金山镇相邻。金山镇以前叫大堡乡,从2001年开始规划实施的1000亩优质水果带,种植柚子、黄金梨、血橙等优质水果共3.5万余株,正在充分利用现有的水资源和农民的传统养鸭习惯,积极引导农民“鱼鸭混养”,打造“金山鸭”品牌。东靠万古镇和因诞生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而得名的国梁镇。
回龙镇辖区面积为49平方公里。我记忆中的回龙镇可没有那么大。
它那时还叫回龙乡。乡府所在地,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只容得下一辆小型的农用车经过。从街头到街尾,两边是砖瓦结构的平房,低矮的房子里总透出昏暗的光。那幽蓝幽蓝的煤油灯,暗红暗红的烛光,苍白清净的电灯光,伴随着我成长。小街东头,有座石头桥,十分普通,桥面是石头和泥土混合而成。下雨天,桥上满是稀泥浆,若是雨下得大了,还会有很多水坑,盛满浑水。桥下一年四季都有潺潺的水声,但我从来没去摸过那河里的水,也从不知道小桥的名字。
桥旁边,一棵大黄葛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它粗粗的腰杆,在那时就要四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合抱得过来,只是我从来没抱过它。偶尔上街“赶场”,我就偷偷溜到树下,摸摸树干,再摸到它的根。那些根,无论大小、粗细、朝向哪里,都那么坚实地扎进故乡的土地。而今回龙乡成了回龙镇,许多楼房已拔地而起,曾狭小的街道已被宽阔的水泥路代替,大卡车,小汽车,摩托车哧溜哧溜地穿过。曾经荒凉寂寞的回龙场不在了,只有那棵大黄葛树,还那么挺拔,那么茂盛。
从回龙街道东头出去,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马路,总是包包坑坑的,下雨天全是稀泥浆,晴天就黄土飞扬,大概乡村公路都是这个样子的吧。不到半里路,半坡上一个瓦窑厂。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个破落的厂子,厂房是四面漏风的光棚子,没有墙壁,顶上是石棉瓦,瓦窑就建在山崖上。我常常看到那些青烟若有若无地飘,那么小,那么黑。我常常担心它们会飘得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更担心什么时候,那个窑子就会没了。20年过去了,它不但有了砖瓦结构的厂房,还有一座两层楼的办公室了。厂里生产出来的青砖红瓦被大卡车一车车地输送到县里县外。若有若无的青烟也高大,粗壮起来。
顺着瓦窑厂背后陡峭的山路爬上去,就到了母猪坡。坐在山顶上歇歇脚,清凉的山风拂在脸上,使人忍不住站起身来。顺着弯弯的山路,拐下山麓,半山腰又生出一个小坡坡,叫登干坡——登干是方言,即鬼。登干坡顶有一个小土地庙,供着浑身是泥的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方圆十里的乡亲,逢年过节,都会到这烧香膜拜,许愿还愿,多年不曾改变。我们一大家人回老家祭祀祖坟的时候,每次最先到的也是这里。
出了土地庙,顺着登干坡继续往下,穿过一道笔直的石坎子,就到了蒲家店,再走一里多的石板路,就到走马桥了。
这是我的回故乡之路。
1
走马桥在走马村的中心位置,走马村有六个生产小组,我家在第六组。
走马村四处都是小山坡,不像峨眉、泰山那么险峻巍峨,不像桂林山水那么富贵名气,它们圆润,温顺,充满绿意。我曾背着猪草背篼,爬遍了这些小山坡,那些嫩生生的牙舌片,毛茸茸的毛脚杆,甜丝丝的空心菜,都是那些年猪儿们特别钟爱的粮食(现在,猪儿们已经不吃这些了,他们吃的是高科技研制的饲料,长得快,长得肥)。
小山坡顶,半山腰上,山脚下或者山坳里,零星地分布着一些村舍和农家院子。房子有的用黄土砌墙,有的是用竹子和泥混合成墙,还有的是用石板和木头混架成墙。屋顶有稻草的,有青瓦片的,也有一半边是瓦片,一半边是稻草的。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岁月如何流逝,它们都那么沉闷,那么安静地与小山坡为伴,与走马村为伴,像我们的祖辈们。
2
院子旁边一丛丛,一笼笼,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的竹子,忠实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其实它们也不是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
春天来了,大大小小的竹笋破土而出,几场春雨淋下来,有的笋子慢慢长大,成了竹子,没有长大的,就成了菜。
我们把胖嘟嘟的小笋子挖下来,去掉外壳,白生生的。妈妈把笋子洗干净放锅里煮熟后捞起来,煮笋子的水,淡黄淡黄的,又涩又苦,喝了清热解毒。慈祥的妈妈拿着竹子做的“响篙”,站在我们面前,强迫我们姐弟几个多喝,说那样少生病。
我们在响篙的威慑下,皱着眉头咕咚咕咚喝下一大碗,妈妈就笑眯眯地去灶屋了。
她把笋子切成薄片片,放上蒜苗和腊肉炒起来,没等端到桌上,那扑鼻的香气,那勾魂的腊肉的味道,就惹得我们口水长流,肚子咕咕,大闹天宫。吃笋子炒腊肉是最珍贵的,每年农历四月妈妈的生日到了,远在国梁,小林,万古等地的舅舅,二姨,大姨,就会来我们家给妈妈过生日,妈妈就拿出珍藏的腊肉来招待他们,像一个长久的仪式,庄严,却有盼头。
夏天,一张张金黄的笋壳儿,一堆堆,一束束,和干枯的竹叶一起挤在大地上,挤在竹林边。
中午放学回家,我和弟弟背起大背篼,拿起火钳去捡笋壳。
火钳拿久了,手就疼。后来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把小竹棍的一头削尖,用力去扎地上的笋壳儿,一张,两张,很多张,串成一串,挤得满满的,像大大的烧烤串,用火钳把它们从棍子上赶下去,装进背篼里。笋壳上的细毛毛更吓人,要是你不小心被他们劐了,红红的大疙瘩立马长出来,又痒又痛,很久都不得消,加上又闷又热的天气,让人难受极了。奶奶说,如果不小心被笋壳儿的小毛毛劐着了,赶快用头发擦抹那个地方,再涂点口水,蹭几下就好了。一次,我的小手臂真被劐了,我睁大眼睛看着刺进我皮肤里的那一堆小毛毛(多像弟弟短短的头发呀),把手臂慢慢地移到头顶,轻轻地在头发里摩擦几下,痒痒的,有一点点刺痛,有一点点酥,再拿下来一看,小毛毛真没有了,被劐的地方,只有一点点红。真神奇啊!我想,不要剪头发了,头发要越多越好!以后不怕劐。
秋天,爸爸要对竹子的队伍进行大清查:竹林不能过密,否则会影响生长。爸爸背着手围着竹林转几圈,这根瞧瞧,那根摸摸,然后拿起砍刀,把那些“驼背”老竹子,被虫子咬过的“病患者”,老是抢不到阳光雨露而自动枯萎的弱势群体们,一律砍下,拖到地坝上去,再把竹枝剃下去,晒起。等焉了之后把它们挽成一个一个的疙瘩,抱回灶屋,整整齐齐地码好,烧火的时候方便,又不占地盘,再把竹竿砍成一截一截的捆起来,搁在猪圈屋干起,好烧。而竹林经过这样清理,有秩序又有空间,长势更好。
我最喜欢烧竹了,把一个个挽好的竹疙瘩放进灶膛里,火苗一下就蹿起来了,红红的,旺旺的,还发出“霍霍霍霍”的声音,像孩子的笑声,愉快而清新。再往灶里加一两根干竹竿,火苗更大,火苗的笑声更大,燃烧更持久。小时候老家人买煤很困难。因为路途遥远,要经过大堡(现金山镇),再到协和场(现在协和镇)的大山里去挑,得走四五十里路;那时买煤还要凭票;车又少,很难找到车运煤;也不会有哪一家人有那么多钱把煤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存在家里烧,太奢侈了。在我们家,烧煤是过年过节或者农忙季节赶时间的时候才有的事。除了大豆苗,包谷秆,高粱秆子,我家烧得最多的就是谷草和竹了。谷草不耐火,一大把谷草放进灶膛里,火焰亮一下就没了,你得不停地加柴,两只手都无法闲下来。而且谷草灰多,煮一顿饭,存下的灰就把灶膛子塞满了,不掏,火就不旺,整个屋子浓烟滚滚,呛得你眼泪直流。从我七岁会做饭以来,我家院子里的竹子就没少陪我。
我最喜欢一边烧火一边看书。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在黑黑的灶屋里,对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就好像身在火炉里,热得直喘气,我也会捧着自己喜爱的书,忘情而专注地读。寒冷的冬天,坐在灶门前,把一截截干燥的竹竿放进灶膛里,借着熊熊的火光读自己喜欢的书,是多么享受的事啊!我常常忘了累,忘了时间。有一年寒假的一天,爸爸妈妈都上山干活去了,我在家煮饭。我一边把干竹子放进灶膛里,一边捧着从邻居李家哥哥那里借来的《冰川天女传》读。不知什么时候,火苗掉到地上,把地上的竹疙瘩、谷草点燃了。哔哔啵啵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吓坏了,赶紧跑到水缸边,抓起水瓢舀起水朝着火焰泼过去……幸好屋子里堆放的柴不多,不然,我家的房子可保不住了。我被爸爸狠揍了一顿,严禁看书,特别是武侠小说。爸爸说,以后见我读书就打,见一次打一次……仿佛书里那些天生的忧伤和悲情突然降临到我的身上,这不堪的忧伤使我反而更渴望待在书里,即使是像父亲所说的那样的坏书。
唉,没办法了,不看书我没法活,打不死我就得看书。
竹在父辈人们的眼里,是大宝贝。坚挺结实的楠竹可以修房子——做椽子。一根根扎实的大楠竹拿来,熟练的匠人师傅拿起钉锤,叮叮当当地几敲几打,就稳稳地固定在房顶上了,再盖上瓦片,新房子就修好了。再看看这些,圆口的箩篼,敞口的背篼,一字口的箢篼,背孩子的娃娃背篼,睡觉用的席子,打谷子用的斗席,储存粮食用的围席,撮东西用的撮箕,晒东西用的簸箕,做饭用的筲箕,洗锅的刷把,吃饭的筷子,烤火的灰笼,照亮的油筒,捉鱼的罩子、虾筢、笆笼,还有竹椅子,竹板凳,竹板床,竹菜板,竹锅盖,竹扇子,竹扁担,竹甑子,竹扫把……哪一样离得开老家的竹子啊!
还有邀牛棍。你看,耕田的大叔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高高举起邀牛棍——并不砸下,只虚张声势地大声吆喝牛儿快走,快走。牛儿实在不想走了,大叔就照着牛屁股小抽一下,那牛“哞”一声大叫,赶紧加快步子往前走几步,耕牛的大叔也气喘吁吁地跟着跑几步。如此往复。
关于斗腔的记忆是妈妈的。
斗腔就是大簸箕,真大,睡得下几个小孩子。
盛夏的夜晚,煤油灯幽暗幽暗的,没有一丝风吹进屋来,只有蚊子嗡嗡嗡地乱飞乱撞,搅得你耳朵发麻,你在房间里还呆得下去?
赶快跑出来,躺在斗腔里,享受有星星的夜晚,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吃了晚饭,我们把斗腔拖出来(因为大,举不动),再滚到地坝上去,用湿帕子抹干净,晾一下,我们兄弟姐妹迫不及待地爬进去,直直地躺着。
星星也陆陆续续爬满天空了。
亮点的,暗点的,大点的,小点的,像往事,又像小秘密,挤满小小的我们的心。它们有时一动不动,像被老师惩罚的小学生;有时一闪一闪的,像顽皮的孩子突然从你面前跑过去,让你来不及看清楚。
我一直想找到牛郎织女,问问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想看看玉兔和嫦娥姑娘的家,北斗星的小勺子真有点像爸爸的烟斗啊。
看着看着,风就吹过来,低头一看,哦,原来是妈妈拿着麦粑扇(竹篾编织的一尺左右的五边形竹器)在给我们赶蚊子呢。借着星光,我看见妈妈穿着汗褂子,露出结实的胳膊,眼睛像星星扑闪扑闪的,那么美,那么亮。岁月流逝得那么快,妈妈还是没有老。她一边给我们摇扇子,一边给我们哼歌:“月亮月亮光光,我是你的娘娘,快点快点起来,我们要去砍柴。月亮月亮光光……”
妈妈只读过小学一册,因为家境贫寒,外婆说她是女孩子,不让她读书。妈妈经常对人说,如果她有女儿了,砸锅卖铁都要让女儿读书。妈妈是讲信用的女人。当我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爸爸却要我在乡中就读,说可以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妈妈斩钉截铁,不同意。她说,孩子考上重点多不容易啊,别人想去还考不上呢!说就算再辛苦,也要把女儿培养出来。
多么朴实的妈妈,多么大气的妈妈,让我彻底走出了大山,走进了我想要的世界。
如今,我已为人母。那夏夜给我唱歌的妈妈,摇扇为我赶蚊子的妈妈啊……
3
地瓜,长在土地的表层,和茅草混居,有很多很长的深红色的藤藤,最粗的一根是主干,主干上又长很多很多分支,每个枝节下,靠近土地的一面,有许多须根,深深扎进泥土里,牢牢地靠在悬崖峭壁上,比爬山虎更稳实。它的叶子深绿色,小椭圆形。尖端很嫩,用手一掐就断了,所以它还很年轻的时候,是很好的猪食。
地瓜藤藤里有很多白色的浆液,越粗壮的越多。如果不小心手或脚被弄破了血流不止,你就割一根地瓜藤,断处对准伤口,把那些白色的黏稠的浆液涂上去,血一会就止住了。
有一次,我和堂妹秀在一个很陡峭很倾斜的坡壁上打猪草。因为是比较危险,很多人没敢去。所以那茅草林里的猪草比较多,什么毛脚杆啊,什么苦蒿草,白头蒿啊,它们绿油油的,我们俩很高兴,觉得运气真好,就抢着割起来。
背篼放在平地上,割好了猪草要拿回去装进背篼里,我往返在峭壁上,不小心趔趄了,身子在空中摇晃了几下,终于没掉下崖去,但右脚还是没得选择地踩在了堂妹的刀上,小脚趾头被割掉了小半边。我疼得大哭,咬着牙爬上崖坐下。堂妹给我割了好多地瓜藤藤,用浆液抹在伤口上,再找茅草包起来。我一瘸一拐地背着猪草回到家,伤口化脓了。爸爸带我去河对面李叔叔那里包扎了几回,才慢慢好了。可我右脚的小脚趾头,现在也是瘪瘪的,像个小木头人。用地瓜藤的浆液止血,只适合轻微的伤。这是经验,这么多年,我无法忘记。
4
农历六月,太阳猛烈地照着大地,蝉躲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成一片,清脆绵长的叫声,提醒我们,热啊,热啊……
南瓜藤啊,红苕藤藤啊,都被晒得奄奄一息。天底下,稻田光秃秃的,咧着嘴等水喝呢。场院上,金黄金黄的谷子正快活地享受着阳光,晒谷子的妇女们,躲在阳光照不到地方,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拉着家常,有时捞起衣服擦擦汗,红红的脸膛,安静,闲适。那些打了谷子回家的汉子们,也躲在阴凉处,有的裹着旱烟吸,有的喝茶水。
那从茶罐子里倒出的深褐色的水,叫薄荷茶,清热解渴。薄荷也用不花钱买,就长在田埂上或水井边,一大片一大片的,幽绿幽绿,香气扑鼻。用它泡水,大人爱喝,小孩子也爱喝。我们家那时一年四季都有薄荷茶喝。夏天喝新鲜的,才从地里采回来洗干净,丢进刚烧开的水里。其他三个季节就喝干的——秋天我们把它从地里采回来晒干,存起来,要喝,泡上开水就可以了。两种味道差不多,清香,解暑,沁人心脾。
这样的画面,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梦里,比最清最静的水上的倒影更清晰。可是,它真的只是镜花水月了。沿着回故乡的路,我没法拾回往昔。
如今,走马村这个名字也已经不在了。拆乡并镇,它和尖山村合并成了今天的幸福村。两村之间曾比邻的那些田野上,陆陆续续长出高耸的楼房,平整的乡村公路,飞驰的摩托车、小汽车,长出了手机、大彩电、大冰箱……
鸭子
院子里,每家每户都喂着成群的家禽。我们家每年养得最多的是鸭子。
春天,妈妈把谷子挑到回龙场去卖了,回来,就跳了两箩筐小鸭仔仔回来。我和弟弟围着箩筐,看着这些小东西在箩筐里像小鸡一样叫着,唧唧唧唧地你挤挤我,我挤挤你,嫩黄的小衣衫上,点缀着一些黑点点,有点像扑克牌。
妈妈在地坝边用竹子编了一个篱笆,围成一个大圆圈,用一个大盆子装上些水,再用一个大盆子,装上谷粒。怕小鸭子噎住,还在谷粒中间和了些水。这些都好了,妈妈就端起箩筐,把它们倒进篱笆圈圈里面。
它们跌跌撞撞地扑进去,拍拍翅膀,像小鸡一样叫着,然后一摆一摆地去喝水吃食,那样子可爱极了。
鸭子还小的时候,不能放太远的田,妈妈通常把它们赶到院子旁边的水田里。被关闷了的小鸭们终于得到解放了,冲出篱笆,一路跌跌撞撞,一路摇摇摆摆。走出院门,走到岔路口的时候,小鸭子们可聪明了,顺着妈妈的竹竿,往左拐。
走到田埂很窄的地方,有些就扑腾腾地往下掉——有的头朝下,有的肚子先着地,还有的在地上打了滚,又翻身站起来,一拐一拐地,很笨重的样子。终于到了目的地,妈妈一声吆喝,它们就稀哩哗啦地朝田里扑去,你挤挤我,我踩踩你,争先恐后,像刚长出的桑叶,鲜活,热烈,让人心动。
来到田里,小鸭们就不管我了。它们一下子散开,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
春天刚开始,田还没耕种,水清亮亮的,干净得能看见下面的泥土,还有秋后留下的谷桩桩。那些谷桩已经腐烂,经历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它们早就精疲力竭了,但还顽强地保持着最后的完整。小鸭们在田里沸腾,谷桩们最后的完整也保持不下去了,随着田里翻起的浪花,一漾一漾的,碎了,破了,四散了。小鸭子才不理会,你追我赶,有的踮起脚板,立起脖子,朝着自己喜欢的事物,“嘎嘎嘎嘎”大叫。哈,小鸭像孩子一样变声了,会嘎嘎地叫了。它们已在不经意间,长大了哦!
到了农历三月,天底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秧田,像给老家穿上了绿色绣花鞋。走近一看,刚插上的秧苗稀稀落落的,在浑浊的水田里摇摇晃晃。秧苗还没成林,小鸭子是不可以去田里的,得把它们又关回篱笆里。
已经习惯广阔和自在的小鸭子们站在篱笆深处,像绅士似的对着我和妈妈长吁短叹,或对着天空,嘎嘎地大声抒发自己的情绪,既可怜,又俏皮。
养鸭子也有苦恼的事,特别是栽秧季节,母鸭子正在生蛋,妈妈和爸爸不舍得把鸭子关进篱笆里,那样会影响母鸭的生蛋率,不关,又会影响田里的庄稼。于是爸爸就把我家的水井田,先留出来不插秧,把鸭子赶到那块田里放养起来,这个光荣的任务只会落到我的身上。
我最讨厌爸爸不让我上学,让我在家放鸭子。可有什么办法呢?
吃过早饭,爸爸大声说:“二娃,你今天就不去读书了,爸爸今天不上新课,只是做练习册。你就在家放鸭子,晚上回来我给你补起。”我心里很不快,但爸爸不容置疑的样子,我只得乖乖地背起蓑衣,戴起斗篷,拿起长竹竿,灰溜溜地把鸭子赶到水井田去。
被强迫不上学在家里放鸭子的日子是痛苦的。我像个稻草人似的,站在田埂上,拿着长竹竿动也不动。鸭子们才不管我的情绪呢,它们在田里啄鱼吃,啄虾子,有时还互相争抢,甚至打架。我很不痛快的时候,就拿长竹竿对着它们乱打一气,它们嘎嘎嘎嘎大叫,往田深处退去,有的委屈地看看我,有的挑衅地朝我大叫,还狠狠扇动大翅膀,扑腾得水花四溅。我更冒火了,随手捡起路边的石头或土块,朝它们扔过去,准确的时候,正好打在鸭子背上。只听它“嘎——”地大叫一声,赶紧把头埋进水里,好像不再惹我似的。
我并没有解气,还是呆呆地坐在田埂边,坐在蓑衣上。那些新开的野花,已换新绿的桑树,已结出胡豆角的胡豆苗,还有粉嘟嘟的豌豆花,都无法引起我的兴趣,也无法改变我的心情。总之,那是糟糕的一天。
还有更糟糕的时候——下暴雨的时候,小鸭子走丢了的时候。
有一年夏末,我又被爸爸留在家放鸭子。太阳很猛烈地照在身上,像千万棵钢针扎进肉里,疼痛,焦灼。我喘不过气来,就躲在有树的地方乘凉去了。到了中午,天空突然布满厚厚的乌云,接着闪电闪过来了,雷声更响,像万千骏马,轰隆隆地从山那边奔到山这边,不及掩耳,就逼到我的面前。我吓慌了,鸭子们更慌。它们在田里东一头,西一趟的,伸长脖子嘎嘎嘎乱叫。我赶紧拿起竹竿,一边大声吆喝它们,“哩哩哩哩——鸭儿哩哩哩哩——”
它们很听话地跟着我回到家。回到鸭棚子我清点数目,居然还差一只。我急了。
外面已下起瓢泼大雨,雨点打在房顶上,哔哔啵啵地,像打在我心里。我想要是爸爸回来发现鸭子不见了一只,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啊!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我不顾大雨,赶紧跑出去,沿着刚才的路往回找。刚才那块田里,雨花四射,没有鸭的踪影!我又往回跑。风把斗篷吹落了,我顾不上去捡,挨着一块田,两块田,三块……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我哀哀地大哭起来。视线模糊了,我还是找不到丢失的鸭。我不敢回家,一直站在雨里,等着雨停。
下午,雨终于停下来。天又露出原来的白脸,刚才那些黑云,不知道滚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仔细搜索了刚才赶鸭子回家的路,特别的每个渠口。
就在大长田到鱼蛋田之间的渠口处,有一个矮矮的坎坎,坎坎下面有一丛很茂盛的水草,大长田的水,正哗哗地流下来,溅起白浪花。那只可怜的小鸭子奄奄地龟缩在水草中,沙哑地叫着,仿佛在哭泣,在呻吟。我赶紧抱起它,往家里赶。
小鸭病了,几天都不吃不喝,再后来,它死了。妈妈把它打整出来,用海椒煎起,香喷喷的,端放在饭桌上。我的筷子一动也没动。其实那时我还小,并不懂生命是脆弱的。那只死去的小鸭子,让我想到我背着爸爸读的那些小说里的许多事,让我想到了自己。我吃不下那鸭肉。
费尽千辛万苦,总有收获的时候。
那年头,鸡蛋,鸭蛋,鹅蛋通常像猪肉一样珍贵。人们有时把蛋积存起来,等到赶场天拿到回龙场去卖,换一些像盐,肥皂,豆油或者草纸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妈妈那时也把蛋拿去卖,有时买点香皂,有时买点洗衣粉。我喜欢妈妈买的蜀秀香皂,圆圆的,白白的,上面印着两个隽秀的字“蜀秀”。妈妈说不准拿来洗手,只有在洗脸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才能用。那香味真香啊,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换用了各种各样的香皂,可还是不能忘记我家的蜀秀的味道。
我最喜欢一条裙子,那是妈妈卖了鸭蛋,给我买的唯一的一条裙子,也是我小学时期穿过的唯一的一条。
那天中午,我正在灶屋里烧火煮包谷,妈妈赶场回来,兴冲冲地从篮子里拿出一件东西,打开,抖了抖。啊!花裙子!我惊奇的大叫起来!妈妈说:“二娃子,你放鸭子辛苦了,妈给你买了一条裙子,过来穿一下。”我高兴地走到妈妈身边,迅速套在身上,高兴地跳起来,学着小说里的姑娘在地上转了几圈。那白底红碎花的小裙子发出咯咯咯的笑声,飘向空中,停了很久才落下来。
我经常穿着花裙子去上学。它的红花慢慢白了、淡了,最终和它的白底一起消失了。妈妈没再给我买过裙子了,我也没提过。关于穿裙子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也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了。
妈妈也会把蛋存起来,选一些放进坛子里,加上适当的盐,泡成盐蛋,等到农忙季节或家里人过生日时吃。
我很喜欢吃盐蛋,喜欢那金黄的蛋黄,吃起来粉嘟嘟的,偶尔有些沙沙的感觉,却并不影响胃口。巴不得多吃点,只可惜我们那时真的不常吃到。每看到泡盐蛋的坛子躲在妈妈和爸爸卧室的角落,我就想伸手去坛子里抓几个出来,自己煮熟了吃。但不难想象,如果爸爸妈妈发现这个事,会把我打成什么样。生活有时是会把人逼成另外的模样的。于是我常常想,也常常放弃。
那时我们家真穷,鸡蛋或鸭蛋更是珍品。农忙季节,爸爸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妈妈就在米锅里放上几个蛋,煮好后把蛋壳剥掉,然后盛上一大碗米汤,放点白糖还加点猪油,天亮时叫我给爸送去。我常常被那大碗里浮动着的几个滚圆的家伙搅得口水直流。真香啊!
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偷喝一小口汤,可蛋是不能偷吃的。妈妈常常念叨,爸爸是家里最辛苦的人,那么多土地,除了他我们谁弄得动?所以蛋是给爸爸补养身体的。我自然也能明白,更何况,每天妈妈煮多少个蛋,爸爸吃到几个,他们都会知道,我是不敢偷吃的啊。否则,屁股一定开花。
生日的时候,我也能享受到爸爸似的特别待遇。
早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妈妈从灶房走出来,笑眯眯地从荷包里掏出两个蛋,放在我手上,说:“二娃子,又长大一岁了,吃两个蛋,长得结结实实的。”我从妈妈的手里接过来,用两个手捧着,放到脸上滚一圈,放到鼻子边闻了又闻,淡淡的清香就从鼻孔钻进去。我舍不得立刻吃掉,温暖的气息轻轻地蔓延到内心里去,我成了最幸福的人。
吃到蛋了,这一天我就可以比平时顽皮点,可以不小心打坏东西,可以大胆说出自己想吃的菜,甚至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抢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把自己最爱吃的菜碗从桌子中间拖到自己面前来。爸爸是家里脾气最暴烈的人,繁重的体力活折磨得他失去了耐心,我们不敢在他吃饭的时候大声说话,会找离他远点的地方玩耍。要不然,他的巴掌或拳头一不小心就落在我的身上。在他面前,我们真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心惊肉跳。但在生日这天,严厉的爸爸会给我们夹点菜,对我们比平时粗野的行为容忍有加。
所以,我和哥哥、弟弟、妹妹们常常天真地盼望着自己的生日经常到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幸福了。
饭
做饭时,把米淘净放进热水锅里,等米锅刚涨开,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像顽皮的孩子在跳舞似的,就得赶紧把筲箕放在缸钵上(陶做的,下小上大的平底圆锥形),再把锅里的没完全煮熟的稀饭舀在筲箕里,放到火上蒸熟,这叫篥饭。
千万别让它在锅里煮久了,否则饭太软,根本就蒸不熟,成了讨厌的夹生饭。硬着就篥起来,虽然不好,但还有办法补救——在蒸饭的时候,锅里多加些水,多蒸一会。
做饭还是很讲究经验的,不然,那么珍贵的米,被自己不小心煮得倒生不熟的,挨打挨骂是其次,那得多浪费啊!
所以我常常小心地伺候着。每当米锅涨了,我就用锅铲盛一小点去给正在忙其他事的妈妈看看,她说可以篥就赶快篥起来,她说再煮一阵儿就再煮一阵。一来二去,我也慢慢会看了——刚刚可以篥的饭粒体积比下锅之前的米增大三倍以上,你用牙齿咬一粒,其中得有一点点硬心
再把切成小条条的红苕放进锅底,把篥好的饭铺在红苕上面,铺的时候得慢,因为饭粒不多,一不小心就遮不住那些红苕,红苕们没有饭粒的爱抚就会生气啦,然后用筷子在上面插一圈气孔,掺适量的水,盖上竹锅盖,继续往灶里加柴。过一会儿再用筷子在锅里插几下,如果不挡筷子了,说明红苕熟了。
迎面扑来甜丝丝的,香喷喷的红苕饭的味道,叫人忍不住使劲吞口水。
吃饭了,桌子上两碗橙黄色或淡绿色的红苕饭可,像冒尖尖的小山似的堆在碗里,其中很可怜的夹杂着米饭的颗粒,一定是给爸爸和妈妈吃的了。弟弟每次吃饭就大哭,坚决不吃红苕。他小,脾气很坏的爸爸也能忍耐他,所以白饭就盛给弟弟一碗。
我们几个,就白饭和红苕搭着吃。
多病的奶奶总是把自己碗里的白干饭悄悄地分给哥哥和我,哥总是拒绝,而我开始接受,次数多了,我也学着像哥哥拒绝奶奶。奶奶总是叹口气,爱怜地看我,还摸摸我的头。在那段岁月里,不光弟弟不喜欢吃红苕,我和哥哥也不喜欢,我想爸爸和妈妈,甚至更多吃红苕的乡亲们,都不喜欢吃吧。但有什么办法呢?填抱肚子是多么重要的事!
常年很少沾肉腥腥,食量居然大得惊人。吃了大碗大碗的红苕饭,我们还要守在灶前,等奶奶或者妈妈把锅里剩下的红苕饭舀起来搁到筲箕里晚上热着或者用米汤泡起当夜饭吃,然后把锅底的红苕锅巴铲起来,再裹上一些米饭和红苕,捏成红苕锅巴饭团,那金黄金黄的,喷着香气的红苕锅巴饭团吃起来,脆脆的,还会发出叽叽嗑嗑的声音,叫人越吃越想吃。而今,早已不用靠红苕充饥,我也一直不愿意吃再红苕了。但小小的我,因为吃红苕锅巴饭团才品尝出点点吃饭的快乐的记忆,却一直美丽地压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
在我记忆里,跳饭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大铁锅里,水烧开了,把米放进锅里,等米锅涨几分钟之后,就把砍得大块大块的红苕们倒进去,用锅铲拌匀,以免它们生在锅底了。继续加热至红苕变软。这时,把一个或两个准备好的空碗放进饭锅里,碗随着米锅沸腾的节奏一蹦一跳的,开始碗也蹦得老高,接着急得在锅里直打转转,慢慢的,就变得安静下来。千万别以为它被烫死了哈,也别以为跳累了,泄气了,其实是它的肚子了慢慢被填满了。那些可爱的米饭,还有少量的小块红苕和米汤们,纷纷跳到碗的肚子里去了。它饱了,它不跳了,它想节约体能,所以就满足地停下来,或端正地、或歪着头,靠着大锅睡觉去了。等红苕稀饭彻底煮好了,就用筷子和锅铲夹住“吃饱了”的碗,端起来,搁灶头上,再把稀饭舀在缸钵里。
跳饭给谁吃啊?哦,这可不是难题了。在我们家,我们都知道,谁最小谁就吃。所以,从大到小的排列,哥哥,我,弟弟,小弟弟,我们都轮流吃过跳饭的。我们都经历过那种自己端着仅有的白花花的跳饭吃得狼吞虎咽的,家人们却稀里哗啦地喝着米汤,大口大口地嚼着红苕和泡萝卜的场景,那时好像谁也没有礼让过,谁也好像不会礼让。哈,因为都是最小的吃嘛,大的或老的们都很清楚了。
那些关于吃的经历为什么总是源源不断地涌到我的眼前来呢?
爸爸为了鼓励我们好好吃东西,会经常变戏法似的把红苕换成不同的花样。蒸耙红苕就是其中的一种。
先把红苕洗干净,不削皮子,再在锅里掺水,放一个泡菜坛的盖子,口朝下,正好盖住水。然后把准备好的红苕围着坛子盖盖,摆好,一圈一圈,再往圈上重叠放,对准其中的空隙摆两层,然后加热,直到煮熟为止。好吃得很,又甜,又香,底下那层还有锅巴哩!最好吃的莫过于盖子底下的残存的水,其实那已经不是水了,是酱色的红苕汁。喝一口,甜得让你心醉。我们几个常常争着吃,喝完了汤还伸出红舌头,把自己的嘴唇“扫”一圈,再咂几下嘴,很回味的样子。
真不是装的,是那甜,一直在嘴里,再到心里,在记忆深处。
吃红苕汤更是难忘了。把红苕切成细长的条状,先用少量的猪油和盐煎一下,放上姜颗颗,掺上适当的水煮熟。起锅的时候,撒上早切好的葱。葱是山坡上的野生的葱,很细很绿,奇香。如果遇到家里还有熬猪油时剩的油糟,爸爸还会在起锅的时候放进去一些,煮几分钟再舀进碗里。先前还皱着眉头的油糟,就骄傲地浮在汤里,或巴在红苕条上,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在里面翻找骄傲的油糟,实在找不到了,就吃红苕条条,再稀哩哗啦地喝汤。那个香啊,简直没法说了。吃完了,照样伸出红舌头,把嘴唇里里外外的“清扫”一圈,再咂几下嘴,很回味,很陶醉的样子。
每当这个时候,严厉的爸爸就偷偷地笑了,我们也会跟着笑起来。
而今,我们有不一样的生活了。那些在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在物质文明疯狂发展21世纪,你一定会觉得我说的红苕多么可爱,多么新鲜,多么好吃。你也许已经产生了现在就去买点红苕来,照着我说的那样去做起来尝尝。可在就连红苕干饭也是难得的美餐的年代,每天靠红苕充饥,是何其苦涩的事!而我一贯严厉的父亲,却会做出那么细腻而智慧的红苕大餐,不露声色地喂养我们,又是何其幸福的事。
感谢父亲,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让我们乐此不疲地吃红苕,让我们长得像小肥猪,让我们有这么多温暖的记忆和健康的怀念。
小梅花
不管是单家独户,还是大院子,走马村都养狗。
我一直不明白,在人肚子都填不满的岁月里,人们为什么还那么喜欢养狗?瞧,那条浑身黑毛的母狗是张叔叔家的,它经常大着肚子,一窝就会生下三、四个小狗崽。可爱的小狗崽像小猫一样叫着,争先恐后地爬到妈妈身下找奶吃,慢慢长大。等到满双月了,张叔叔就把小狗抱出来,装在一个小背篓里面,给邻居们或亲戚家送去。
刘家院子的大黄狗,常常把尾巴和两只后腿当凳子,两只前腿撑在地上,站在刘家大院的芭蕉树下,对来往的行人眈眈相向,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有时还远远地朝着人们“汪汪汪汪”地大叫,好像在说:“哼,来啊,看你们谁敢过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既威武又蛮横。
很多路人都不敢轻易从那里经过,我更是不敢了。实在要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站在院子前面的水田边上,扯开嗓子使劲喊:“是哪个的狗?快点邀一哈哈儿!快点!”喊几遍后,就有一个像小脚的老太太走出来——她不是真小脚,是老了,身体瘦小得很,脚也和小脚差不多大了。她眯缝着小眼睛,一边喊:“莫怕得,你走嘛,它不咬人,只是做得凶哦。”一边大声吆喝她的狗。狗先是龇牙咧嘴,然后乖乖地进屋去了。
这么凶恶的大狗,怎么会被那么小的老太太喊进屋去呢?一直到我家养了狗之后,我才明白,狗是最认主的!
好多次,我背起猪草背篼站在那块田边使劲喊院子里的主人来邀狗,都是那个小脚老太太出来。原来有劳动力的人都上坡干活儿去了,留在家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养狗自然可以看家护院,还能陪伴老人和孩子了。从那里经过的次数多了,我就知道那个小脚老太太叫刘三婆婆,后来我干脆叫她三婆婆了。
看她撅着小脚,一跳一跳地走路,我常常担心她会摔倒,但她似乎很健朗,也很和气,像我的奶奶。她家的大黄狗也慢慢和我熟悉了。我背着满背篼猪草,靠在三婆婆院子的墙根下歇气,看夕阳和黄昏慢慢爬上村子,看辛苦劳作的人们收工回家,看村庄里冉冉升起的炊烟,那条狗跑到我脚边,吐着红舌头,伙伴一样,让我不再惧怕。
我家也养狗了。只养过一条。
它是我从大伯母家抱回来的,来到我家的时候刚满月,又小又瘦。全身的毛是黑的,只有尾巴尖白白的,非常光亮。四个脚爪爪也是白的,像开过的白梅花。尽管它是公狗,我们还是叫它梅花。
梅花常常和我们抢东西玩。我和院子里的伙伴踢鸡毛毽,它开始装得很乖巧,像孩子端坐在地上,很认真地看着。
毽子从我左脚飞到右脚,再从右脚飞到左脚,有时从左脚飞出,在身子背后转一圈,再稳稳地落在我右脚上。梅花黑亮亮的眼睛流露出既羡慕,又佩服的表情,时不时还抬起一只左前脚,呜呜呜地发出声音,好像在说:“亲爱的小主人,给我踢一个嘛,给我来一个嘛。”
玩得兴致的我们才懒得理会它呢!它也不放弃,一直呜呜呜地叫着,叫着,等到我们把毽子扔给它,它就跳起来,张嘴衔起鸡毛毽子,提起两只前脚,学着人的样子,在地上转圈圈。我们故意不看它,它就跑过来,咬住我们的衣裳或者裤腿,它不真咬,只咬一下,放一下,我们只好又看着它。有时我们踢得实在热火朝天,不分高下,来不及理会小梅花,它就坐在旁边呜呜呜地叫着,或着急地在原地转圈,实在没招儿,垂头丧气地走开,跑到墙角下去蹲着晒太阳去了。你看它眯缝着眼睛,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着不理我们,其实还是蛮兴致地看着呢。忽然,天空中飞来一只花蝴蝶,那一闪一闪的红翅膀好像要摸到梅花的脸了。梅花从地上一跃而起,追着蝴蝶跑啊跑,跑出墙角,蝴蝶摇摇翅膀朝更高的天空飞去。梅花很沮丧,刚要回到墙角继续假寐,不知道从哪里又飞来一根鸡毛,落在它面前。梅花赶紧跑过去,对着那鸡毛又抓又咬,把我们给它受的气都撒在那根无辜的鸡毛上了。
梅花长到两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帅家伙了。黑黑的身体,白花花的尾巴和四个白脚爪爪,青春意气的少年郎啊!嘿,那滚圆滚圆的肚子,结实的四肢,更惹眼的是那光滑的毛,乌黑亮堂,柔和光洁,让人忍不住摸了又摸。我时常假靠在小梅花的身上,摸着它的肚子,想它和我们一样,每天就吃点耙红苕,或者一碗红苕汤,最多运气好的时候啃点骨头,怎么就能长得那么帅气那么健康呢?
除了睡觉,它一步也不离开我。
我背着猪草背篼去上学,它就跟着我蹦蹦跳跳地到学校去,我进教室里读书,它就在教室外面转悠,不时跑到门口来看一眼。课间我们在操场上跳橡皮筋、踢毽子、“斗鸡”(玩的人分成两拨,让自己一只脚,各自金鸡独立,盘起一条腿,双手抱住至胯骨边,准备好了,就向对方阵营冲去,用盘起的膝盖左右上下冲撞对方,谁先放下那只盘起的脚,谁就输了)。梅花就在旁边兴奋地看着我们,和我们一起跳呀蹦呀,那样子别提多高兴了。
放学后,我背起猪草背篼爬坡上坎去打猪草了,梅花也跟着。我割猪草,它摇着可人的白尾巴,围着猪草直转,有时还用嘴巴咬。猪草打满了一背篼,我们要往家里赶了,梅花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像小爱人一样护卫着我。有时它也会跑到前面去,这里嗅嗅,那里闻闻,好像侦察敌情的士兵。
有时走得远,回家的路就远。我背着沉沉的猪草背篼,一路上要歇好几次脚。我常常靠着石壁或山崖,伸伸被压弯的腰杆,揉揉被绳子勒得发红甚至肿起的肩,喘口气。
实在背不动了,梅花就会很着急地围着我转,并咬我的衣裳,还拿它的前脚来拉我。
天空并不因为路远就黑得晚。每当夜幕降临,看到远远近近的村落闪烁着煤油灯昏黄幽暗的灯光,我急得满头大汗,甚至大哭。梅花会很安静地望着我,幽蓝的眼神也很安静。我们在夜幕中相守,直到家越来越近,灯光越来越亮。
梅花还会刨地瓜——不是我们当蔬菜吃的那种白生生,甜脆脆的地瓜,是我们老家人人都那么叫的一种野生水果,我不知道书面名字叫什么。
每每大人们稍微闲暇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是最自由的了,于是就开始了刨地瓜大行动。
我和哥哥,弟弟妹妹们,还有小梅花,拿着塑料盆子或者水瓢,女孩子穿着露膀子的小褂褂,男孩子们干脆光膀头,都打着光脚板,出发了。晌午,路已经被晒得滚烫,我们在路上边走边笑,有时把茅草扯下来,塞到嘴里,吧嗒吧嗒地嚼,有时还把黄荆折下来,一小把一小把裹紧,挽成一个圆圈,当帽子戴在头上。大家就你逗逗我,我搡搡你,似乎忘记了热。有时也干脆跑起来,这样脚就不会感觉到太烫。
我们专门选有草、又有些倾斜的坡坡头,别人不敢轻易去爬的地方。拨开那些茂盛的草,地面上就露出很多长长的地瓜藤来,清香扑面而来。在大太阳的照射下,我们都能闻到地瓜的味道了。我们赶紧低下头,把身子巴在坡壁头上,仔细地分开地瓜叶儿,在有须根的泥土里,会很轻易地找到一些深红的或暗红的果实,形状大小和桂圆差不多。我们小心翼翼地摘下来,放进身边的器具里。小梅花当然不示弱,它滚动圆圆的身子,挤到我们几个之间,这里闻闻,那里嗅嗅,不时地用前爪在土里刨来刨去的。那样子,很专注,绝不偷懒。有时它真能从土里刨出地瓜来。看着红红的小东西从土里冒出来,小梅花来不及想到偷吃,更没等它去抓,地瓜就顺着倾斜的坡坡滚到崖下去了。一次,两次,很多次,小梅花辛苦地把地瓜刨出来,结果都掉进崖下去了。小梅花可泄气了,沮丧地对着山崖大叫几声,以表示自己的愤怒与无奈。当然,也有它抓住的时候,可被它狠狠按在爪子里的小地瓜们,早已咧开嘴哭了。
看着可爱的小梅花,我们心里更高兴了,便刨得更积极了。
当我们像泥鳅一样凯旋的时候,我们带去的盆子啊,水瓢啊,都满满的了。哥哥把所有的果实都倒进桶里,跑到水井边,仔细清洗。
那些小家伙们颜色虽然好看,但表皮上有凹凸的颗粒——熟透的地瓜的颗粒是白色的,没有熟透的就是紫黑色的。地瓜很柔软,不能用力过猛,不然也会像在小梅花的爪子下的一样咧着嘴大哭呢!我们都耐心地在竹林边等着,小梅花更是一点不着急,悠闲地看看这个,闻闻那个,样子很绅士。哥哥终于洗好了地瓜,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围上去。真漂亮啊,那些深红的,暗红的,紫红的地瓜们,乖乖地躺在木桶里,亲密地挤在一起,那么安详,那么动人,像我们孩子心中渴望的火。